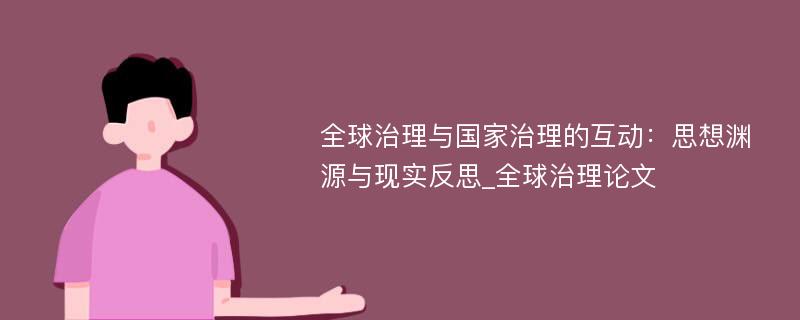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渊源论文,现实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是当今人类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两大核心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权国家界分的藩篱就开始被全球性问题渗透和跨越。①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成为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新常态,并引起了各个学科的广泛关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探索。 一是以琳达·韦兹和海伦·米尔纳等人为代表的探究国内治理变革与全球经济治理互动的研究。两人都试图通过对全球开放经济与国家经济治理变革关系的研究,为解释国内治理机制变迁提供一种国际与国内因素同等重要的解释框架。②二是以罗伯特·基欧汉、里斯-卡彭等人为代表的跨国关系分析。这类学者关注国际组织、跨国利益集团、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跨国社会力量在某些议题领域对国家治理进程的影响。③三是以利莎·马丁和贝思·西蒙斯等人为代表,提出了关于拓展国际制度规范与国内制度变革互动的研究议程,该研究意图对国家选择遵守全球治理规范或采取抵制行为背后的动因进行解释。④四是切克尔、江忆恩等人关于主权国家与全球治理规范的互动研究,该研究拓展出了国家社会化、规范内化、学习与模仿等重要理论和概念。⑤ 在中国学术界,该议题的研究起步稍晚,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如蔡拓对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的分析以及王逸舟对中国与国际制度互动的分析。⑥近年来,以田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聚焦于国际制度与国内变革关系的分析等。⑦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和分析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发展脉络和理论要义,探究其中的学理意义。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渊源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及其互动关系的思想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导引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和罗马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指出,城邦政体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制,其优劣会决定城邦间是否会发生战争。柏拉图认为坏的政体对内会导致暴政,对外会带来战争,凡是僭主“总是首先挑起一场战争”。⑧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强调了城邦治理方式与战争的关系。他认为斯巴达实际上是“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为整个政治体系的目的”,公民“受到以暴力侵凌他国的教导”,“专意训练其邦人以求克敌制胜、役属邻国”。⑨古希腊时期具有重大思想影响的斯多葛派更是贬低单个城邦,推崇世界国家。斯多葛派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国家是一个“世界国家”,一切人“都是统一的世界国家的公民,而每个人则是宇宙公民”;世界分裂为许多国家只是“偶然”的,“并不对整个人类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一切制度,包括国家和法律”都必须服从于自然法的理性,而“作为世界整体的一部分的人类共同体”就体现了这种理性。⑩深受斯多葛派影响的罗马法学家西塞罗也认为,由于人类都具有理性,共享一个理性的法,“因此就应该把共享法和正义的人们看做是同一国家的成员。”(11) 中世纪时期虽然神学思想一统天下,但是像奥古斯都关于“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两种不同性质统治的思想仍给人以启迪。奥古斯都指出,“地上之城”由于人的罪恶而常常失去秩序,和平是短暂的,而“上帝之城”是造物主与人类达到的最高度的有秩序的一致,因而是永久和平的。(12)奥古斯都为人们反思“地上之城”的治理缺陷和克服这种缺陷提供了思想工具。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思想家们的方案虽然从现实上来说行不通,但却为我们探索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源泉。当然,受时代条件所限,上述思想与今天人们对这一主题的思考还相距甚远。对这一主题的深入思考还要等到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全球得到扩展之后。 (二)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先声 中世纪末期,西方社会中王权力量的崛起导致冲突和战争频繁,于是构建一种超国家共同体的治理模式以克服王权暴政和从国家法律秩序推导出国家间法律秩序的思想,就成为自中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人类探索公共事务治理的思想先声。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认为,要解决国家间纷争,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即世界帝国。(13)但是同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皮埃尔·杜波瓦则不赞成世界国家的设想,他主张成立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理事会,来裁判国家间纷争。(14)意大利国际法先驱贞提利斯认为,陆地和海洋利用以及自由航行等属于全人类普遍享有的权利,任何人对这种权利的侵犯不仅伤害了受害者,而且是对全体人类的挑战。(15)著名的国际法思想家格老秀斯更是为当时陷于冲突的欧洲国家建立起了包括战争法、条约法、外交制度等一整套完备的国际法律体系。同时他还提出了“人类共有物权”的概念,认为如海洋利用和自由航行就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据为私有”的权利。(16)法国人圣-皮埃尔在《欧洲永久和平计划书》(1713)中提出了一个将欧洲国家融入一个邦联体的详细计划。为此,他还设计了一些专门机构负责规范各国贸易和统一各国的度量衡标准。(17)康德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认为,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就是探寻在各个民族中普及世界公民权利,建立国家的民主治理体制,进而缔造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18)这些可贵的探索为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人类对超国家治理的探索和实践开启了思想先河。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人类对公共事务治理的探索被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所激发。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民主法治、现代财税和国防制度等在19世纪被一一创造出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国家治理机构国际联盟也于“一战”后诞生。虽然国际联盟的实践仅维持了二十年,但是人类对超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探索并没有止步。20世纪上半期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围绕国际联盟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的国际制度设计,功能主义理论创始人戴维·米特兰尼提出了国家间在技术领域走向一体化的理论。这些思想探索最终汇聚成联合国体系等超国家治理的实践,预示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时代的到来。 (三)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展开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和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理论探讨也在多个角度展开。 首先是可持续发展引发人们的关注。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揭示了杀虫剂的滥用将导致生物物种的消失。(19)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发布的《只有一个地球》报告,揭示了地球环境污染危机。(20)同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提出了“地球是有限的”和“均衡状态中的增长”理念。(21)当代著名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也都较早地阐述了全球化和工业化将现代性风险加强为一种世界风险的危机。(22)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3)可持续原则关注资源利用的公平原则、发展不能超过地球承载力的可持续原则和人类保护地球的目标与行动的共同性原则。 其次是“失效国家”(failed states)概念和“作为责任的主权”理念的提出。“失效国家”问题较早是由罗伯特·杰克逊以“负价值的主权”概念提出。(24)他认为官员擅权无度,政府腐败,基本的安全与司法秩序缺失等是治理失效的主因。(25)1995年威廉·扎特曼又提出了“崩溃国家”的概念,并探讨了人道救助、外部干预和民主化的治理作用。(26)“作为责任的主权”理念较早是由弗朗西斯,邓等人提出并将主权界定为一种责任而非仅指权利。(27)后来这一概念在“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保护的责任》报告中得到进一步阐释。该报告声言主权“意味着双重责任:对外尊重他国主权,对内则要尊重国内所有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当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责任时,国际社会有责任提供保护。(28)“失效国家”和“作为责任的主权”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国内治理不再仅仅是主权内事务,而且也是全球治理的对象;同时还意味着全球治理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某种规范框架和指向。 最后是治理与善治理论被创造性地提出。治理与善治理论较早是由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提出,指公共事务管理由国家垄断的权力管制转向多中心、自主、互补的管理模式和过程,而善治就是各行为体互补合作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方式。全球治理机构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衡量善治的标准。(29)治理理论的提出在国际事务领域引发了全球治理的“范式革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从全球角度来说,治理事务过去主要被视为处理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现在必须作如下理解:它还涉及非政府组织、公民的迁移、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资本市场。”(30)这意味着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更多地出现了交叉渗透与重叠,也预示着人类公共事务的治理领域的“新中世纪主义”时代的到来。(31) 全球危机与风险社会理论、“失效国家”与主权责任理论把国家治理的外部性问题提了出来,可持续发展与治理理论让世人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治理的问题,“世界风险”的危机、“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发展“不能超越地球承载力”等理念促使理论家们超越传统的政治共同体局限,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理论家们第一次建立起了阐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理论框架和多维路径。 (四)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思想深化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得到拓展和深化,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比较政治学等理论范式得到广泛运用。 理性主义在分析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时,建立起了议题联系、政策约束与成员资格条件、社会动员等理论模型。例如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的谈判机制就常常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议题联系在“一揽子”政策方案中,以抑制国内的政策反对者,推动国家治理的变革。(32)在政策和成员条件方面,田野的研究说明了加入WTO的成员条件和政策约束对中国国内改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33)在社会动员方面,贝斯·西蒙斯认为,来自国际的治理规范能够为国内社会的政策诉求预支政府承诺(因而增强了问责的渠道)、扩大政策诉求的联盟规模和提供无形的资源和政策支撑、拓展策略选择的范围。(34)在分析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方面,理性主义强调国内制度开放性和政策偏好等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产生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全球治理的政策和制度。(35) 相比于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关注更直接。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国家治理的偏好乃至制度规范都是基于全球治理行为体主动地“传授”和“说服”而形成的,与此同时也是国家主动地“学习”和“模仿”或者“被灌输”和“被说服”的结果。例如玛莎·芬尼莫尔就运用案例阐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会”国家建立科学科层组织。(36)杰弗里·切克尔认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学习和自上而下的精英学习是国家社会化的重要方式。(37) 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中,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规制做出反应以及国家治理变革的研究更受重视。(38)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就认为,在国际压力下国家内部利益网络很容易分化出新的利益集团和政策诉求联盟,从而导致国家治理变革和政策调整出现。(39)此外,美国学者福山的“国家构建”理论也更加典型地触及到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问题。福山认为国家职能弱化问题和“弱国家”的国家构建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40)在福山新出版的著作中,他还提出,国家建构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应该使“国家、法制和问责制”三套体制“处于某种平衡状态”。(41) 应该指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渊源除了西方文明的启迪之外,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也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在人类公共事务的治理中,中国历史上关于治国理政的思想博大精深。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了“保民”、“慎罚”思想;在诸子百家时期,孔孟提出了系统的仁政和王道理念,《礼记》描绘出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慎到和韩非提出了系统的崇尚法治和反对人治的思想,道家和黄老学说崇尚顺应民情和无为政治;《公羊传》提出了“华夷之辨”和“尊王攘夷”的文明间秩序理念,《太平经》则提出了财物公有、互助互养的“太平盛世”设想;此外,还有唐宋盛世时期“民本”、“爱民”和“公天下”的理念,明清时期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对专制暴政的深刻批判等。上述治国理政的思想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为后世思考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今天,人类各种文明在公共事务治理上的经验和智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社会对安全议题的思考产生了“无核世界”和“人类安全”的理念,在发展议题上提出了人类“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环境议题上提出了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上为人类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贡献,在理念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向世界展示了新的治理理念和价值。在全球与国家层面的治理互动中,人类各种文明在展示世界多样性的同时,正向着文明共享、互鉴互赏和命运与共的道路前进。 总之,追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一议题的理论思考基本上是围绕着国家治理的脆弱性和不足以及通过外部理想世界的设计给予有效的补给而展开和发展,而最近几十年来各种分析路径的引入和拓展,推动着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形成了今天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发展方向。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现实反思 考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发展路径,可以看出,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和治理实践能力的提高,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已日益呈现出统一性,二者互动互融,日益形成一种“整体性治理”。这种良性的互动状态,有助于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向着整体性善治的目标迈进,对于塑造一个共享共融、和合共生的全球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 首先,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为寻求改善人类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了一种开放性框架。国家、国际机构、公民组织网络发挥各自的优势,把来自世界各个地方、各种行为体的经验和理念,输送到各开放性框架中,形成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但是,21世纪以来,全球反恐呈现出强劲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传统大国主导地位的衰落导致单边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盛行,新兴大国的快速成长衍生出民族主义倾向,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导致各种排外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纷纷登台亮相,成为当前治理全球性问题的新障碍。面对21世纪的全球危机,人类已不可能再退回到领土范围内来解决问题,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一定必须是开放性治理,二者的有效互动将为此搭建起开放性治理的框架。 其次,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为全球与国家两个层面的治理革新提供重要的动力和支撑。新世纪以来,无论全球治理还是国家治理的日程都出现了“治理任务拥堵”,而议题难以治理和无力治理的背后,是“全球治理失灵”和“国家能力弱化”。在主权之内,长期以来主流的国家治理理念崇尚自由放任,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几乎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国家来解决;在主权之外,主权间对抗的思维驱使国家热衷于以武力解决问题,面临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相关国家治理能力缺失暴露无遗,美国治理金融危机不力和运用武力手段反恐的失效可为佐证。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框架形成于二战结束后的政治安排,其运作规则过于依赖大国主导。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和不对称、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国家间主义基础,成为各领域治理失灵的“病灶”。因此,21世纪人类公共事务的治理变革,必须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基础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再造,而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相互提供变革的动力和支撑。 最后,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能够产生出世界文明间的“熔炉效应”。来自世界各地的文明价值和治理经验在互动中包容互鉴、竞合共进,有助于促进一种共享共融、和谐共存的全球秩序的形成。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伴随着金融危机的难以治理和保护主义盛行,全球贸易多边体系停滞不前,少边、区域小边、选择性利益同盟大行其道。再加上近几年大国军费高涨、零和思维和对抗思维甚嚣尘上。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走向和平与繁荣,就需要摈弃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通过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营造出文明并举、兼容互补、多样并存的价值共识,创造一种相互尊重、和合共生的世界文明秩序。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当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还面临着若干更具根本性问题的困扰,需要人类更深刻地反思才能寻找到解决的出路。 一是奠定全球治理基础和支撑其运作的规范体系的权力结构问题。当今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规范原则面临着“宪政性的”大博弈。(42)世界主导性大国已从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谈判场离开,并新组少边的贸易团体;世界银行的改革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并没有认真对待新兴国家的参与积极性,世界不能坐等旧的规则体系慢慢变得无效并走向死亡,而新的治理规则又分崩离析,全球性危机问题会永远得不到治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必须拿出大的政治勇气,就全球治理规则的核心价值和权威结构达成共识与合作,为全球规则体系奠定新的宪政性基础。 二是国家的能力建设问题。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在核能力上十分超强,能够将地球毁灭很多次,但是在治理气候变暖、艾滋病流行、毒品泛滥和全球贫困等问题上,则既缺乏意愿也缺乏能力。国家能力应该用于提供其国民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提供能毁灭他们的东西。(43)应对21世纪的挑战,国家能力的再造需要政治大智慧。世界主要大国必须放弃零和对抗思维,重建21世纪的国家哲学,在国家建构中锻造出治理贫困、温室气体排放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能力。 三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星球级别的”威胁,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问题。当今气候变化的治理如此之差,它已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降到了道德的层面:有能力的发达国家不愿履行减排责任和援助义务,却苛责没有治理能力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排放大国退出或拒绝一体化减排而找各种“替罪羊”推卸责任。治理气候变化,需要人类每个成员拿出大的政治抱负。在国家治理的议程上,必须课责每一个政府和公司的减排责任。在全球治理议程上,气候治理规范必须得到强化和提升,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具体化过程中,应该增强能力责任的考量。 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谱系中,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既是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自我利益的对立统一体,同时也是全球共识与民族个体价值的对立统一体。其中主权民族国家特别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很容易从自我中心主义出发,以“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之名行一己私利之实。这种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当今全球治理规范体系在很多领域还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其对非西方文明和价值的包容性严重不足。二是在西方价值观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一些领域,其治理规则倾向难以真正符合解决问题的需要。如在“保护的责任”规范形成中,其主要理念侧重于对人道主义灾难的干预,几乎不涉及产生人道灾难背后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的解决。(44)三是在国际多边机构的治理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持有价值偏好和规则霸权,在发展中世界强制推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常常给很多国家带来消极性影响甚至是灾难。 今天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全球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危机。如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将自身的国家治理实践与全球治理任务相协调并相互促进,这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时代课题。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有必要也有责任回应这一时代要求,制定并实施积极的国家治理战略和全球治理参与策略,为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整体善治目标的实现,做出自己的努力;一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为,以自身日益成长的能力和影响力,参与支撑全球治理体系,增强全球治理权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二是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三是积极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既要善于学习有价值的东西,也要防止坠入西方模式的陷阱。四是积极挖掘中国国家治理的潜力,以自身的治理经验和理念,丰富和发展世界的多样性,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 ①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Jr.,"Introduction," in Joseph S.Nye Jr.and John D.Donahue,eds.,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p.18-19. ②Linda Weiss,ed.,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Br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Robert O.Keohane and Helen V.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③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s,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Jr.,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④Lisa Martin and Beth Simmons,"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729-757; Dai Xinyuan,"Why Comply? The Domestic Constituency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2,2005; Beth Simmons,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⑤Jeffrey Chekel,"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3,2001,pp.553-588; Alastair Iain Johnston,"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5,no.4,2001,pp.487-515. ⑥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王逸舟:《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 ⑦田野:《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刘兴华:《国际规范与国内制度改革》,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林民旺、朱立群:《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传播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国法律制度改革》,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 ⑧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7页。 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90—391页。 ⑩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蔡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15—222页。 (11)西塞罗:《论法律》,法学教材编辑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6页。 (12)奥古斯都:《上帝之城》,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31—633、931—932页。 (13)但丁·阿利盖里:《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页。 (14)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 (15)寺田四郎:《国际法学界之七大家》,韩逋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22页。 (16)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5—126页。 (17)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132—140页。 (1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7—114页。 (19)参见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62. (20)参见Barbara Ward and René Dubos,Only One Earth: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New York:Norton,1972. (21)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6、135、139页。 (22)乌里尔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7、110页。 (2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81页。 (24)Robert H.Jackson,"Negative Sovereignty in Sub-Saharan Af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2,no.4,1986,pp.247-264. (25)Robert H.Jackson,"Quasi-States,Dual Regimes,and Neoclassical Theory: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1987,pp.519-549. (26)I.William Zartman,ed.,Collapsed States: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Boulder,Colo.:Lynne Rienner,1995. (27)Francis M.Deng et al.,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Conflict Management in Africa,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6,p.19. (28)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2001,p.7. (2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法治、公共部门效率和参与度等评估指标。DAC Expert Group on AID Evaluation,Evaluation of Programs Promo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Good Governance:Synthesis Report,Paris:OECD,1997,pp.7-23. (30)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2页。 (31)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254. (32)Christina Davis,"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Issue Linkage:Building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Trade Liber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no.1,2004,pp.153-169. (33)田野:《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第188—217页。 (34)Beth A.Simmons,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44. (35)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曲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36)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37)Jeffrey T.Checkel,"Norm,Institution,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1,1999,pp.88-113. (38)参见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Thomas Risse-Kappen,ed.,Br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39)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40)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5—96页以及“序言”第1页。 (41)Francis Fukuyama,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4,pp.524-548. (42)潘德:《有效的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 (43)戴维·赫尔德、凯文·扬:《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南开学报》2012年第5期。 (44)Thomas G..Weis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pp.82-86.标签:全球治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