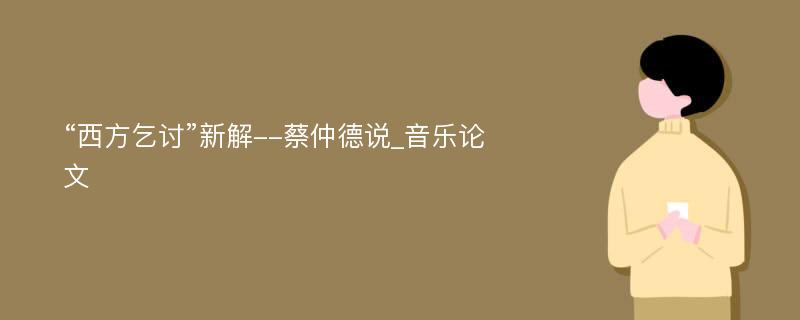
“向西方乞灵”新解——接着蔡仲德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解论文,蔡仲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499(2010)03-0005-05
20世纪30年代初,青主就如何发展中国近现代音乐问题,提出了一个命题——“向西方乞灵”。此言一出,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讨论中国近现代音乐道路问题时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批判、声讨之声不绝。1994年,为纪念青主逝世35周年和五四运动75周年,蔡仲德撰写了《青主音乐美学思想述评》。论文着重对青主的两个主要观点——“音乐是上界的语言”和“向西方乞灵”做了理性的、正面的解读。在这种解读的基础上,从人本主义出发,于1998年蔡仲德就中国音乐出路问题撰写了《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该文完稿后,在全文公开发表的过程中,又是几经坎坷。发表后又受到许多批评。[1](P10)用蔡仲德自己的话说,此文“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与否定,赞同者……未超过十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反对与否定“向西方乞灵”的意见几乎呈压倒之势,而“向西方乞灵”仍像一个幽灵,总在当代中国音乐生活中徘徊。
笔者认同蔡仲德对“向西方乞灵”的解读。简言之,即:“乞灵”就是求道,就是寻求音乐之道,寻求音乐的根本精神。“研究西乐、借鉴西乐……以制造崭新的中国音乐”。只要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稍作考察,我想,不难发现青主的命题和蔡仲德的解读,其实只不过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成就的方方面面的一个基本概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学习与借鉴西方音乐文化的成果,也就没有中国近现代的音乐文化。此话并非妄言,而是有大量的事实为依据的。
譬如在音乐创作方面,黄自如果没有系统地学习西方音乐,并且在创作上具体学习借鉴了西方音乐的清唱剧,那就不可能创作出他的《长恨歌》;冼星海如果没有系统地学习西方音乐,并且在创作上具体学习与借鉴西方音乐的康塔塔,那就不可能创作出他的《黄河大合唱》。至于近现代中国作曲家们在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等领域所取得的创作成就,不都是中国作曲家经过系统的学习西方音乐和具体学习与借鉴西方器乐音乐的各种体裁所取得的成果吗!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在我看来也是学习、借鉴西方音乐的成果。人们往往称《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优秀的群众歌曲,而群众歌曲作为一种体裁概念,界定起来又“弹性极大”。[2](P186)姑且在此对“群众歌曲”的体裁界定存而不论,只对群众歌曲的艺术渊源,作一点粗略考察,我觉得中国近现代群众歌曲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群众歌曲的影响,而苏联群众歌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的《马赛曲》、《国际歌》等的影响(这可以以十月革命前俄国出现《工人马赛曲》为例)。如果对《马赛曲》的音乐风格和群众集体咏唱的特点再追寻其艺术来源的话,恐怕又与宗教改革后产生的众赞歌有艺术上的联系。行文至此,不由得想起恩格斯关于众赞歌《我们的主是坚固的堡垒》所说的话,恩格斯说这首众赞歌是“16世纪的《马赛曲》”。所以,从艺术渊源上看,《义勇军进行曲》也属于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所取得的成果。
又譬如在专业音乐教育方面,粗略地看,从国立上海音专到当下中国的9所音乐学院以及设在诸多高等院校的音乐系科,所有这些音乐教育机构都不是以中国古代的梨园、教坊的模式办学。从系科设置到课程结构、授课方式等无不参照西方音乐学院的模式与经验。在今日中国音乐生活的各个岗位上从事工作的音乐家们,绝大多数正是从这样办学的音乐专业教育中成才的。我们还应看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家,比例相当多的人都是直接在西方接受的专业音乐教育。黄自、冼星海等人用今天的话说,都属于海归学子。聂耳这样的天才为了在音乐上更好地成长,也是想“向西方乞灵”而出国。不幸的意外,使中国痛失一位大有发展前途的作曲家。1949年以后,中国又选派了大批赴苏联音乐院校学习的留学生,这些人学成归来后成为一代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的主力军。还应看到,当代中国从事传统民族音乐(常被称之为“国乐”)创作和表演的作曲家、演奏家、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音乐学家,恐怕绝大多数也都是中国现代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当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不但以西方音乐院校为办学模式,而且这种办学模式培养的人才完全适应了当代中国音乐事业的需要。
再譬如中国近现代音乐表演艺术方面也取得了辉煌喜人的成就,中国的歌唱家、演奏家多次在世界性的声乐、器乐比赛中获得各种奖项。如今活跃在世界乐坛上的中国音乐表演艺术家大有人在,有的还处于世界顶尖级艺术家的地位,令人刮目相看。当代中国的音乐演奏团体——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歌剧院、舞剧院、歌舞团等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在世界各地的巡演均获好评。其中还应指出的是推动当代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模式之一,也在向西方学习,即大家所知道的民族乐团交响化,有的直接称自己的民族乐团为民族交响乐团等等。这一切成就如果离开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文化成果,那是根本无法取得的。
此外,诸如音乐演出场所的建设,不但学习、借鉴西方音乐厅、歌剧院的建筑经验,而且像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场馆建设,更是直接聘请西方建筑师来设计建造。而这些现代化、高水平的音乐演出场馆不但满足国人音乐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也充分显示了当代中国音乐生活的硬件水准。中国在乐器制造方面不仅生产研制和改进了大量传统民族乐器,而且据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钢琴生产大国,小提琴制作方面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名师、名琴。学习钢琴与小提琴等西方乐器的中国儿童,在数量上领先世界各国,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种种不过是对中国现实音乐生活的一个极其粗略的鸟瞰,但足以说明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向西方音乐文化的学习与借鉴。而青主的命题只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对这种基本事实的一个早期肯定与表述方式。蔡仲德的有关文章只不过是当代音乐学家对这一命题的现实解读。他们都只不过道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一个基本事实。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当下中国音乐界许多人士如此忌讳说出这个基本事实的话语,并产生如此强烈的对立和批判意识。浏览有关文章可以得知,反对青主命题和蔡仲德观点的意见,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于政治义愤;二是出于文化焦虑。但笔者觉得,冷静思考起来二者均无真实的依据。
所谓出于政治义愤,是指把近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出现,看成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主义的结果。对这类观点,早已有人进行了澄清。本文认同冯文慈、蔡仲德等人的观点:即以学堂乐歌为发端的中国新音乐是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不再赘言。仅在这里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来支持这一观点,前文提及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所有成就取得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时期,恰恰是在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实现的。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人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是绝不会容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国人的屈辱现象继续存在一天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以为已经很清楚了,不必继续多谈了。那么,对青主命题的政治义愤是不是也与晚近的冷战思维之间有某种联系?二战后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时代,我们一向致力于东风压倒西风,岂有向西方乞灵之理!不过冷战已成历史,青主提出“向西方乞灵”原本也是在思考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问题。因此,更没有必要往政治方面去联想了。
所谓出于文化焦虑,核心的问题既涉及到传统问题,也涉及到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民族特色问题。
首先,让我们对“传统”问题做一点研讨。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总是坚守“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思路,这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这样的心态必然排拒“向西方乞灵”。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睁开眼睛看世界。一方面在眼界上、认识上和理论上终于超越了夏夷之别的老眼光。但另一方面夏、夷之别的思维惯性以一种新的形式显现出来——中学、西学之争。在这里本文关注的不是去分析中学、西学之争中的各派观点的是非优劣,更无意贬低争论中涌现出诸如严复、梁启超等先进人物在思想上的建树,而是关注这种争论本身在文化观念上所产生的一种消极影响。这个问题,笔者赞同何兆武的观点,何兆武说:“从近代中西思想文化接触的一开始,中国方面就陷入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思想误区而不能自拔,即她给学术思想划定了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认定了有中学、西学之分。……假如说有所说中学、西学,那只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而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是属于某一民族的文化所独有的。”[3]此话千真万确。以中、西医为例,中医、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但绝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能学西医,西方人不能学中医,也绝不意味着中医不能给西方人治病,西医不能给中国人治病。任何学术的目标,总是以探索真理为目的。凡是真理,对人类来说,必有普遍价值。故有所谓学术乃天下公器之说。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也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4](P154)晚清关于中学、西学的斗争给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带来了一个消极的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中国人在面对中西文化问题时,常常在“思想上划定了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这样的思想误区,自然会令一些人在“向西方乞灵”面前保持着高度警惕与对立。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思维定势所导致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现象。
传统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担心“向西方乞灵”会使中国音乐传统发生断裂,为了维护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不能不否定“向西方乞灵”。谁能反对继承传统和弘扬优秀传统呢?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传统”?怎样做才是继承“传统”?这倒是讨论“传统”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
日常口头用语上,人们往往把“传统”等同于过去。如甘阳在指出这一看法时所说的,“‘传统’只不过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过去的思想,过去的精神,过去的心理,过去的意识,过去的文化,以至于过去的一切。”[5](P48)这样使用“传统”,在日常关于时态的口头用语上,也已习以为常。例如,当我们欣赏中国戏曲时说,“这是一出传统剧目”,倒也无妨。但是,当我们研讨有关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时,这样理解“传统”,必将产生一系列认识上的混乱。最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传统”等同于“过去”,那么,“继承传统成了复制过去,光大传统也无非加大投影。”[5](P52)其结果“必然以牺牲‘现在’为代价”。[5](P49)显然,这样理解“传统”必然成为我们在历史发展面前裹足不前的理论依据,继承传统岂不是只有消极意义了。
那么,“传统”到底应该是什么呢?黄翔鹏认为,“传统是一条河流”。他以此来命名自己的音乐论文集。甘阳认为,“传统”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实体”。他说“‘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5](P53)黄、甘二位的“传统”观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强调“传统”的流动性,而不是凝结不变的“实体”性。以“传统是一条河流”为例,如果要使“传统”这条河流浩浩荡荡、川流不息,唯一的前提只能是让新鲜的活水不断涌入传统之河,否则,传统之河必然干涸。果真如此,传统岂不真的要断裂了!这样的“传统”观,告诉我们“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实体。那么,从正面看,“传统”究竟应该是什么呢?在黄翔鹏、甘阳“传统”观的启发下,笔者想说,“传统”就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力。这种能力的历史传递就是传统的继承。了解这种能力是如何促成的,就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认识与研究。只有这样的“传统”观才能保证我们在强调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时,传统不会成为历史前进的沉重包袱,而相反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以这样的“传统”观,我们应该怎样继承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传统呢?大家知道,唐代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极为兴盛的时代。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自然应该研究促成唐代音乐文化繁荣兴盛的种种因素。在这种种因素中,有一个方面恐怕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唐人海纳百川式的博大胸怀。隋、唐有所谓九部乐、十部乐,其中近半数属于中亚、东亚和南亚等古代中国周边国家的音乐。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唐代先人既未因这些音乐非我华夏自古以来固有之乐而拒之门外,也未见有谁因此担心唐乐是否会“变于夷”而出现民族自性危机的焦虑,我们见到的只有诗人咏叹当时音乐盛况的名篇佳句。这一现象充分显示出唐人在观念上对夏、夷之别的突破与超越。回顾古代中国这一段音乐历史,在发展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问题上,我们应该怎样思考和对待“传统”问题呢?首先,我认为唐代音乐文化的历史经验的确给我们留下一个值得继承和弘扬的好传统。其次,我认为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并非以再现和复制具体唐代音乐(这当然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方面十分有意义的课题)的方式来实现。只有今天的中国音乐家们,通过自己的创造,使一部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昔有天竺乐、安国乐之花盛开,今有交响乐、协奏曲之花怒放,才会使我们无愧于祖先,才是真正的继承和弘扬了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一切正是实践了甘阳所指出的,传统“不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之自然延续、……而是‘传统’负有着一种‘过去’所承担不了的必然使命,这使命就是:创造出‘过去’所没有的东西,使‘传统’带着我们的贡献,按照我们所规定的新维度走向‘未来’”。[5](P54-55)回顾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以学堂乐歌为发端的新音乐文化,不正是这样发展壮大的吗!不正是这样完成了中国音乐从古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吗!青主的命题和蔡仲德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不正是对这一历史所做出的概括吗!据此,还有什么必要对“向西方乞灵”加以批判和抵制呢!
以上是本文对“传统”问题的一点研讨。下面再就音乐的民族特色问题谈谈看法。
我认为,关于音乐的民族特色和音乐审美的民族习惯是一个客观存在,似无人否认。因此,担心“向西方乞灵”会使中国音乐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作曲家们所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尽管其成就和影响有高低大小之别,但有哪一部作品失去了民族特色呢?就连青主本人的音乐创作不是也充满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吗?又有谁会把贺渌汀的《牧童短笛》误听成是格里格的抒情钢琴小品呢?无论是哪国作曲家,即使有意要求他在音乐创作上完全去除自己的民族特性,表现出纯正的其他民族的风格特色,应该说是一件极难实现的事。柴科夫斯基在《胡桃夹子》中有一段“中国舞”(“茶舞”),尽管这是一曲很动听的音乐,但若以是否表现出中国风格来衡量它,则实在不敢恭维。
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印记,其实是很难磨灭的。即使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大变化,也依然如此。请看,世界各地凡有华人聚集之处,往往就有“唐人街”“中国城”出现。逢年过节还会有舞龙、舞狮等活动。这是不是印证了那句老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因此,我想因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向西方乞灵”,担心中国音乐文化将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无法满足国人音乐审美习惯而焦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但是,在我们肯定音乐的艺术表现及审美都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强调艺术的民族特色和审美习性又都不是僵死凝固、永远不变的。这个问题本文认同蔡仲德在他的论文中已有的阐述,[6](P618)这里只想补充几句。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处在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艺术风格、音乐审美习性也不例外。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中,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需求,总是随历史前进而发生变化。不能因为中国人过去穿长袍布鞋,就否认西装革履是现代中国人的衣着。同样,也不能因为中国过去在器乐合奏方面有江南丝竹,就否认交响乐队是现代中国器乐的演奏团体。
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看法的人,可能要提出诘问: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异彩纷呈,为什么偏偏“向西方乞灵”?这难道不是欧洲中心论吗?非也。西方音乐的发源地虽在欧洲,但这种音乐的学名之所以不叫“欧洲音乐”而叫“西方音乐”,乃是因为这个概念既非地理的,也非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即所谓西方文化中的艺术音乐部分。这种音乐的诞生和早期发展阶段,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还未出现,故不能说它是哪个民族或哪个国家的音乐。当时它是在欧洲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文化共同体的音乐。在中世纪,它主要是为了适应基督宗教的宗教生活而发展。文艺复兴以来,宗教性的西方音乐创作虽仍有发展,但更值得重视的是,这种音乐迅速世俗化,并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这种扩散现象,我认为是西方音乐历史发展的极为重要的过程之一。它意味着西方音乐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更广泛地区的音乐家们参与对它的创造和培育。地理大发展以后,为西方音乐向世界扩散提供了条件。至于西方音乐向中国的扩散,我们可以从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中略见端倪。但西方音乐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应以清末明初学堂乐歌的出现为标志。中国人习惯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视野去思考学堂乐歌的意义,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以为,中国人也可以而且应该从西方音乐史的视野去思考学堂乐歌的意义。以西方音乐史的视野看学堂乐歌的意义,那就是在学堂乐歌出现以前的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曾有过欧美各国音乐家们做出的贡献,从此以后,中国音乐家也将对西方音乐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只有这样,西方音乐才能真正实现为世界音乐。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杨荫浏已称西方音乐为“世界音乐”,称西方音乐的乐器为“世界公共乐器”。这显示了这位研究中国音乐文化的大学者,对整体人类音乐文化大格局的洞见。
毫不夸张地说,从学堂乐歌的出现开始,中国音乐家大约历经了一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不仅使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取得长足发展,而且在国际音乐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前文提及的中国歌唱家、演奏家在世界乐坛上的业绩,仅仅是一个方面。其实中国近当代音乐家对世界音乐文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我们还应看到现代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其中有的作品在国际竞赛中获奖,有的作品在国外首演。外国的演奏、演唱家或乐团在音乐会上演出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已非个别。不少中国的音乐专家在欧美各地音乐院校任教,在世界各种音乐竞赛中任评委。这种种迹象表明,“向西方乞灵”其意义不仅仅是发展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出路问题,而且也体现了西方音乐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吸收更广大地区音乐家参与创造的历史大趋势的必然。西方音乐如果没有这一文化特点,它能成为世界音乐吗?对此,人们或许会问,世界上举不胜举的各地区的民族音乐难道就不对其它地区、其它民族发生影响,进行交流?为什么它们不能成为世界音乐,偏偏是西方音乐成为世界音乐?不是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不清楚认为艺术形式“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判断中,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世界的”这一概念。但笔者认为,说西方音乐是世界的音乐,这里“世界的”概念是十分明确的。它指的是这种音乐文化是非民族的、非地域的,而是由世界各地音乐家共同创造,其成果又为世界各地人们共享的一种音乐文化。属于这样意义的世界音乐,除西方音乐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种了。
至于西方音乐为什么会发展成世界音乐,这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需另文专题研讨。这里只想提出一点基本想法。
一、西方音乐本体的存在与发展是独立的,不受制于其它文化;
二、西方音乐在风格方面更重视审美共性的追求,而不强调地域性或民族性;
三、西方音乐在人文价值取向方面更强调普世性,民族或地域的殊别性的表现总是寓于普世性价值表现之中;
四、西方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经过理性归纳整理,形成各自的学科体系。这样,就使西方音乐文化脱离自发存在状态(德国音乐学家埃格布雷希特称,理性是西方音乐的“标志”①)。平时我们所说的“学习”或“借鉴”西方音乐,主要都是通过学习西方音乐的理性成果实现的。
……
一定还有更多应该思考的方面。以上仅仅是一种范畴概念的初步设想,说明西方音乐能够实现向世界扩散,必定是因为它自身具有的某些文化个性所起的作用。
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应该说既是一部中国音乐家运用西方音乐文化的成果创造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国音乐家带着中国的文化基因参与创造西方音乐文化的历史。这一历史并不因“向西方乞灵”使中国音乐遭到损害,相反,使中国完成了从古代音乐向近现代音乐的历史转型。也没有因“向西方乞灵”使中国音乐家的艺术创造才能受到压抑,相反,中国音乐家在参与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创造中,不断取得喜人的成果。本文完稿之际,网上传来令人鼓舞的喜讯,中国歌唱家和慧刚刚荣获“奥斯卡歌剧金像奖”。这是中国音乐家在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创造上的最新喜人成果,也是中国音乐家对世界歌唱艺术的又一重大贡献!
收稿日期:2010-09-10
注释:
① 详情请见[德]埃格布雷希特著,刘经树译《西方音乐》一书中“反思之一:西方音乐”的相关内容,2005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