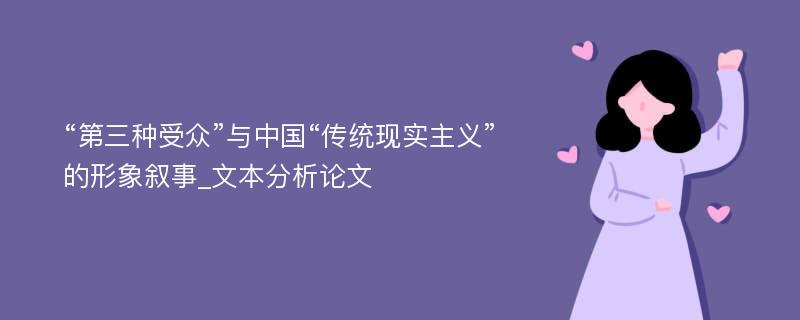
“第三种观众”与华语“传统写实”的影像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语论文,第三种论文,影像论文,观众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台湾影片在国际影展中频频得奖。得奖是一种喜讯,但观照得奖的影片内容,以及展现形式,却令人忧喜参半。
这些得奖影片,大都枯燥无味,影像叙述呆滞沉闷。因此,即使得奖,影片也几乎没有放映机会,即使放映,最多一个星期就匆匆下片。反讽的是,越枯燥无味的电影,文化论学者越倾向为其戴上炫人的光环。
由于文化论学者也经常是电影杂志的编者,或是撰稿人,甚至是台湾影展的评审员,这些获奖的导演,更有意或是“刻意”以迎合这些文化论述的偏好来摄制电影。电影制作似乎是“目的论”的化身,以得奖为职志,以文化论述的焦点为标的。
反过来说,有些文化论学者,缺乏细致品尝影像的能力,所谓的阅读与诠释,经常以理论的框架套用文本,迎合其品味的电影制作,正好提供了论文写作的案例。因此,台湾所谓的第八艺术,不时陷入电影制作与电影评论的共谋。“共谋”是另一种“诠释循环”,造就了台湾电影得奖但极其可悲的境地。
在这样的共谋下,当年的《童年往事》与《悲情城市》,以长镜头拉出影像纵深的侯孝贤,到了《戏梦人生》与《海上花》,重复呆滞的长镜头,为“沉闷的艺术”继续造景。
在这样的共谋下,蔡明亮在《爱情万岁》里,让演员杨贵媚对着不动的镜头哭泣五六分钟,得奖后,到了《河流》,在连续十二三分钟不动的镜头里,观众在几近全黑的画面里,不知道影像“所为何事”,①而濒临耐性崩溃的考验。所谓“看”电影,竟然是观众耗费时间心神所接受的折磨。
第三种观众
由于蔡明亮与侯孝贤的部分作品,经常是文化(尤其是本土文化论述)学者讨论的焦点,但许多观众却避而远之,有关影像叙述的论述,必然会进一步追问到谁是真正的观众。有关观众的定位是本文聚焦的重点。
目前的“观众”似乎被一般电影理论家定位成两极:
有些影片以盛昌流行口味的大众为观众,这几乎是好莱坞文化的整体诉求,电影经常以煽情与制式耸动的场面,邀约其投入,这样的观众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有些影片以台湾当地的(文化)理论家作为主要观众,这些影片经常也是奥斯卡以外的影展的得奖者。但反讽的是,这些影片若是将文化论述抽离,大部分却是枯燥无味。文化论述所网罗的是欠缺生命跃动感的制作,虽然这些影片经常号称是生命现象的印证与批判。换句话说,影片经由意念或是意识形态操控,一方面向理论发声,一方面也是理论的回音,因而是理论家的最爱。
其实,在这两极之外,有“第三种观众”。这些观众可能不认同影片被当作“文化论述”处理,但他也不是《泰坦尼克号》、《魔戒》、《哈利·波特》、《第一滴血》、《终极警探》的爱好者。他可能喜欢伊朗的《柳树之歌》(Willow and Wind)、越南的《恋恋三季》(Three Seasons)、德国的《走出寂静》(Beyond Silence),大陆的《洗澡》、《那山 那人 那狗》,台湾李安的《饮食男女》、杨德昌的《一一》等等,因为这些影片让他“感动”。
他可能被侯孝贤《悲情城市》感动,却为他的《戏梦人生》与《海上花》里漫长的道白与重复的场景感到不耐。理由不在于长镜头(long take),因为两者都是大量长镜头的制作。真正的关键在于,后者不像前者动人。当理论家经常为一些场景的光影,或是场面布局所代表的文化意涵,而加以理论化推崇时,我们是否要有点自觉,美学的价值判断,应该先有整片的感受或是“感动”,而不是对个别现象的单点倾斜?
所谓“感动”,并不是好莱坞式的滥情诉求,而是观者被影像叙述吸引的“瞬间的遗忘”。日本莲实重彦在讨论侯孝贤影片《恋恋风尘》的某些片段时提到“考古学的恍惚”。“感动”的瞬间有点像这种“恍惚”,观众浸淫于影像的流动中,忘掉要去分析、要去运用理论。诠释是观赏过后的回忆,将感动中的沉默化成语言。因此,一部技巧或是理论痕迹很明显的电影,其技巧可能有问题。
在“考古学的恍惚”中,观众有点类似布莱(Georges Poulet)与伊塞尔(Wolfgang Iser)所说的,③沉湎于阅读中的读者,以几近入神的状态感受文本。若是影像能如此观赏,观众感受的瞬间,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批评家,也不会意识到要以某种文化理论作为阅读的框架。伊塞尔认为美学的展现,是在阅读中的读者的体验,也就是“隐藏读者”的体验。阅读中,若是“隐藏读者”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真实读者的身份,美感的经验刹那间可能烟消云散,因为文本中的情境,已经被真实读者生活中的情境所取代。
台湾大部分评述电影的学者,大都以“真实读者”的身份看电影。他们退出文本的场域,而以其知识理论比对电影的文本。他们的评论因而也少了一段“遗忘入神”的经验。如此的阅读是一个批评家对一个“他者”的分析,而非“暂时遗忘”现有的批评知识后,被感动后的诠释。
相反地,“第三种观众”经常在电影文本里,随着影像的流动浮沉,感受电影呈现人生的渲染力,体会生命的深沉与厚度。观众暂时忘掉其现有的知识,因为看电影中,意识到的“知”会干预到感动的强度。
但是“第三种观众”并没有将“知”抛弃,而只是暂时将其悬置。正如上述布莱与伊塞尔所述的阅读过程,当“第三种观众”从文本中退出,要进一步做诠释时,原有“存而不论”的“知”会回返意识;但是由于经历“瞬间的遗忘”与感动,回返后的“知”必然融入先前影像文本的体验。阅读影像时,“第三种读者”与套用文化理论的学者最大的不同是:前者经由感动后,原有的知是人生的哲思与美学的深化,而后者则是在对“文化知识”强烈的意识下对影像的“分析”与理论的套用。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有关“了解与诠释”的论述,曾经告诫:不要让理论在意识里主导论述,因为“主导”本身暗示非经了解、非经感动,而是引介外在的思维,强制框限多面向的文本。④
另外,以现象学的思维观照“第三种观众”,能让影像展现潜在的纵深,但前述有关“他者”的讨论需要进一步辩证。感动的瞬间,“第三种观众”与影像文本,没有“我”与“他”之别,因为“我”已经融入文本中。但现象学哲学家梅卢庞帝(Mauric Merleau-Ponty)在《观照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中说:只有自我意识到“他者”时,才有“我”的存在。⑤这与上述的论点似乎有矛盾。仔细思维,其实不然。若无影像文本的“他者”,观众的自我就难以立足。但“他者”的确立,需要观众先有某一瞬间的腾空自我,不以“我”的理论主导影像文本。另外,能被影像的文本所感动,“第三种观众”必然意识到电影所描述的人生,也就是另一个“他者”。感动的基础在于,瞬间能将“他者”与“我”融为一体;电影所呈现的人生,观众也感同身受。反过来说,套用文化论述,倾向将影像文本视为跟“我”无关的“他者”。两者极其不同。
隐藏于“传统形式”的深度叙述
和蔡明亮与侯孝贤相对比的是,类似台湾李安的《推手》、《饮食男女》与杨德昌的《一一》,以及近一二十年来的大陆一些影片。这些影片,“第三种观众”观赏过后,回味再三。回味是因为其中隐约意涵,经过细心品尝后,变成挥之不去的影像。这些影片在表象的“传统论述”里,潜藏了颇富深意的布局。由于“潜藏”、“隐约”,以理论标签作为研究的学者,经常视而不见,但是“第三种观众”却视为瑰宝。究其原因,当代很多学者或是理论家,假如离开“文化”的命题,就缺乏细读文本的能力,只能以“文化理论”的大框架套进各个文本。对于这样的电影,这些学者大都只能“说故事”,也因此把这些影片贬抑成“只是说故事”。当代电影评论的悲哀是:只有“文化”的粗枝大叶,却欠缺观照文本细致内涵的慧眼,无视其生活情境中幽微的纵深。近十几年来,海峡两岸不乏这样表象“传统”却蕴含丰富意涵,甚至散发后现代精神的影片,《洗澡》、《草房子》、《孔雀》、《蓝色的爱情》、《卡拉是条狗》、《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那山 那人 那狗》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试以大陆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卡拉是条狗》以及台湾杨德昌的《一一》为例说明“第三种观众”如何看待这样的电影。
1.《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影片的迷人,部分原因来自于叙述角度所呈现的多重意涵,以及声音与影像的异步。“第三种观众”在感受这样的叙述方式时,影像的渲染力是主体,阅读的敏感度很自然与影像相呼应,并不需要特别在“理论”无边的海域上,搜寻可以攀附的线索才能上岸。
影片以文革知识分子下放为背景,一开始,主角罗明与马剑玲两人到凤凰山报到,两人从山脚往上爬,与影像重迭的是幕后背景的女声合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有感觉的“第三种观众”几乎马上意识到他们两人可能不是红卫兵,因而才会被下放,而且是从城市来到乡下。歌声与画面恰好形成对比。对比是本片细致隐约的反讽,隐藏了时代性的批判。马剑铃去拜访民歌手,民歌手演唱一首曲子,要他猜其中的谜底。歌词隐含性的暗示,与歌声重迭的影像,是罗明与小裁缝在溪水中性与爱的嬉戏。“第三种观众”看到的是两个空间的迭置,以歌词的内涵来说,是一种对应,以马剑铃也暗恋小裁缝来说,是一种对比。影像与声音又是一种异步的艺术。
另外,本片声音与影像的异步所潜藏的讽刺、批判与反讽,莫过于:马剑铃和罗明是反动的知识分子,下放是为了接受群众的再教育,但真正被“教育”的是凤凰山的劳动阶层以及他们的队长。这两个年轻人被派到城里看电影,回来后向群众报告电影的内容。结果,画面上,仰角镜头中的他们高高站在台上,以语言的穿透力让台下的听者动容。叙述的情境在黑暗中撩拨坐在地上的群众;语音在空间中飘扬,回响的是观众不能抑止的眼泪。影片展现的不是知识的反动,而是知识难于操控的力量,使本来社会体制要求再教育的对象,变成教育这个社会体制的“主体”,进而显现一个时代的愚昧。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虽然暗藏讥讽,但是却非常隐约自然,就是因为隐约,更显现了本片丰富的艺术性。“声音与影像”的异步是“第三种观众”对文本的敏锐所感受的印象。阅读观赏的当下,他并不需要“异步”的词汇,初次观赏,虽然没有这些术语,但是仔细聆听旁白,他会发现画面似乎是旁白的反制与消解,而感受趣味。换句话说,趣味来自于观众与文本的第一次的照面,而不是观众心中有预设的理论,将其套用。某方面说,观众能感受趣味,在于能将心中的理论腾空。
2.《卡拉是条狗》
相较于《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卡拉是条狗》“似乎”没有在国际影展引人注目,但是本片的叙述,却不时运转着强烈的戏剧张力,而这样的张力不是经由夸张的“戏剧性”呈现。进一步说,本片是极其写实的影片,而“写实”这样的字眼,在当代又被批评家贬抑成“无甚可谈”的代名词。《卡拉是条狗》与当今大陆许多动人心弦的影片(包括上面所提的所有影片)都有很浓郁的写实痕迹。这些影片不卖弄表象技巧,也不以“文化论述”的理论故弄玄虚,而是以“字质”增加文本的稠密度。
以《卡拉是条狗》来说,这是一部平凡人因为养的狗卡拉对自己的贴心,想尽办法要在下午四点前将其从派出所救出来的故事。影片写实,因为它反映了1995年以来,大陆有关养狗政策所带来的生活的变动。影片感人,因为它呈现了小人物为狗的小生命专注的付出与无奈。最令人感叹的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几乎每一个人,包括抓狗的警察,都有相当的爱心,但人们的爱心抵不过体制与法律的规范:养狗需要昂贵的代价,养狗一定要有养狗证,而养狗证的申请费要五千元;付不起申请费的,只能眼睁睁看到爱狗被捕捉。
这是反映社会情境的作品,内含无声的抗议。抗议之所以无声,因为全片没有任何一段场景,没有任何一段对白,表达“抗议”。假如“抗议”是一种政治社会意识,这种意识不流于呐喊,也不流于造作的影像叙述。
正如大陆其它类似这样的“写实”影片,《卡拉是条狗》的成就绝非只是传达某种意念的目的而已。在“写实”流畅的叙述下,叙述所呈现的情境,在有意无意之间,会在既有的“意念与目的”之外延生。“第三种观众”对于叙述如此延生枝节,并不尽然是当代理论的指引,而是对文本专注,所发现的现象。对文本前后的发展有强烈感受后,回顾影片的开始,他会发现意义似有似无在影像中浮现。假如我们将片头女主人带着卡拉等电梯时,走廊上的电灯忽明忽暗,当作是一种生活无奈,或是后来遛狗时卡拉被抓的伏笔,类似巴特所说的影像的第二意义;那么后来老二从杨丽家走出来,有人向他借钱,他摸摸口袋没有适宜的钱的这一景,可以说又类似巴特所说的第三意义。严格说来,巴特的第三意义指的是,在电影中,那些出人意料而导演无法控制的影像。以上所描述的景象,当然还是编导“控制”的影像叙述,因此应该是第二意义;但是以整部影片看待,这段借钱的场景和老二救狗的主要叙述,似乎很难有意义明确的归属。这是叙述的延生,也似乎是主要叙述的旁生枝节,因此意义在第二意义与第三意义之间。
因此,在一般批评家眼中,被简化成“说故事”的写实片,反而蕴藏了第三意义的可能性,因为“写实”涵盖生活的呈现,而生活随机动态性的点点滴滴,很难能以完整的逻辑统筹,更难以被规划成封闭性的意义。
假如“第三种观众”并不知道巴特的第二意义与第三意义的内涵。以上诠释的文字不太可能出现。但是类似的体验与书写仍然存在。他们也许会感受到意义的未定性、意义的朦胧性、意义的必要性与非必要性。关键在于,文本的密度与吸引力促成阅读与诠释,但阅读之后,再看到巴特的见解,他会很“乐意”将既有的看法与巴特的见解结合。当然,也可能“第三种观众”在观赏前已经看过巴特的书写,这时,观赏中的感动与外来的理论并行交融对话,甚至是交互激荡成阅读经验。
3.《一一》
最后以杨德昌的《一一》为例作为此节说明的总结。杨德昌是台湾最能以影像面对社会现实的导演。⑥但和《卡拉是条狗》一样,他对于现实的批判与讥讽全部融入艺术匠心,不做口号式的呐喊。《一一》敏感捕捉了台湾人文风景的点滴,如婚礼的场景,满月酒的餐会,在喧嚣中,散发台湾文化潜在的荒谬与叙述语调淡淡的无奈与哀伤。但是在呈现如此具有现实意义的气氛中,镜头保持相当的冷静,杨德昌对于镜头的推拉移动非常审慎,和蔡明亮相似,但和后者不同的是,在这样几近不动的场景中,不时蕴藏戏剧力,以及影像的思维纵深,试举例说明如下。
《一一》里,小儿子洋洋的角色非常讨喜。杨德昌让一个年龄最小的小孩带出全片最大的哲学深度。⑦当然哲学的呈现,不是空泛的言说,而是有力的影像叙述,以小孩的情节呈现哲学思维,也暗藏危险与造作的可能性。影片中,洋洋的语言仍然是个“小孩”,洋洋无意也无能演说哲学,哲学事实上是他的“童言童语”,启动父亲以及观众的思维。他问他的父亲说:“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我们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看”与“是否看见”是电影里洋洋的主要意念,以及因为这个意念所牵引的情节与叙述。影片开始,照团体照,洋洋站前排,后排站了一群女生,前后分别用手摸他的头,他回头但找不到当下摸他的人。这和他的“看不见”有关。后来,他用照相机一再照人的后脑,洗了相片后给对方,说:“因为你自己看不见啊”。这和所有角色以及人在人生中的“看不见”有关。
影片中,洋洋为了躲避训导主任与女纠察队员,而躲进放映影片的教室一景,非常值得深思讨论。洋洋进入黑暗的放映教室后,躲在门旁边,这时教室正在放映云雨的形成。不久,女纠察队员(高年级同学)随后也进来,开门时裙子被门上的钩子钩住,露出内裤,看在洋洋的眼里。也许这是洋洋第一次看到“大”女生的内裤,他显现特殊(而不夸张)的表情。女纠察队员走到放映室前面,站着东张西望找寻洋洋,人影投射在影幕上。这时影幕上乌云密布,在天空中快速窜动,老师讲解的声音说,这是云的舞蹈,雷雨的因缘。老师说:“小冰粒在空中留下了正电,把自己变成负电的雨滴。两种对立而又相吸的能量,互相越来越不可抗拒。终于在一个闪电的瞬间,正电和负电又激烈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雷。我们地球一切的生命,应该就是闪电创造的。”影幕上的画面似乎就是洋洋当下的映照与启蒙。小孩子幼稚的心思,因为女生的内裤,可能“看到”从来未有的“景象”,异性的吸引正如正电与负电的纠缠。值得注意的是,当老师的语音说:“小冰粒在空中留下了正电,把自己变成负电的雨滴”时,画面上正是女纠察队员裙子被钩住而露出内裤的瞬间。而有关正负电的结合以及闪电雷声的言语,女纠察队员庞大的影子投射在影幕上,她是观众的焦点,也是洋洋唯一注目的焦点。对于“第三种观众”来说,影像叙述细致幽微,但镜头除了一两次的切换,呈现洋洋的表情与女纠察队员的左顾右盼外,大致保持几近静止状态,但是所酝酿的情境引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紧接的下一场景,是洋洋的姊姊婷婷拿着伞在天桥下走过,似乎放映室里的雷雨,感染了现实的天空。接着她和隔壁女孩子莉莉的男朋友有了进一步的交谈,并到附近喝咖啡。这算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影片借由雷雨或是雷电的影像,推动两个不同年龄层有关“情”的叙述。
不论是洋洋的“童言童语”引发观众的哲学思考,或是洋洋在黑暗中的启蒙,而打开了两性的新天地,“第三种观众”都不必去套用任何文学或是文化论述,就能感知其影像丰富的内涵。他也许不必有“哲学”的意念,甚至对于“黑暗中启蒙”词语中的吊诡,也可以当下浑然无知,但事后回想后感受其中的戏剧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戏剧力,编导并非经由镜头一再提醒观众的注意,而悠远的情境就在那里,静静地邀约第三种观众的“精读细品”。换句话说,“第三种观众”观赏的当下,不是“知”的指引,而是“感”的投入。没有这一层“感”的体验,任何价值判断都可能变成“目的论”的投影,因而对于文本的纤细经常“视而不见”。
最后,表面上,杨德昌与蔡明亮一样,擅长用抽离冷静的长镜头,但是呈现的效果却迥然不同。可见“呆滞”并不是台湾电影的特色,更不必以为呆滞是特色而为了尊重个别差异,而让其得奖。假如上述蔡明亮以镜头静止不动作为他个人风格的标签,因而电影的沉闷变成他“理直气壮”的理由,《一一》却明白告诉电影界,“完全不动的”的长镜头却能布满剧力,动人心弦。杨德昌的可贵就在于,他能拿捏长镜头的奥秘,能让静止的画面注满美学的滋养,而不是像蔡明亮在“个人风格”的迷思下,让静止镜头变成“沉闷呆滞”的同位语。
“写实”的再思考
综合上述,由于“第三种观众”不以文化的大框架套用文本,而是以文本的质地是否具有感染力为依归,但所谓“感染力”又与好莱坞常见的煽情与滥情不同。另外,造成渲染力的电影,也与卖弄形式、耍弄镜头而被贴上“后现代”标签的电影不同。第三种观众肯定“创意”,但不是“布满凿痕的创意”。他肯定影像叙述的“当代性”,但并不是把“当代”变成形式戏耍的代名词。他不认同“刻意制造形式差异的后现代”,却经常在外表传统的电影文本里看到“后现代的多重视野”。因而,第三种观众对于“写实”有了更细致的体认,经常在表象的“写实”中,发现新的“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内涵,正如上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与《卡拉是条狗》。因而,所谓“写实”值得进一步深思。
1.“写实”与隐喻
当代,“写实”经常被放在贬抑的词汇里。“写实”经常被误解等同于写实记录,等同于社会伦理的道德观。但在贬抑中,批评家经常忘掉了19世纪末写实宗师豪韦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经典告诫:伦理不能以美学作为牺牲品。有趣的是,若是以上的影片因为被冠上“写实”的标签而被简化,其美学幽微的纵深却因为“第三种观众”而得以彰显。以隐喻来说,场景“写实”,用之于比喻的,必然要能取自现场的自然感与说服力。由于来自现场,场景的布局,更加费心,更加不着痕迹,更需要“第三种观众”的慧眼与想象。以《卡拉是条狗》来说,片中偷卖狗的小贩大都躲藏在即将拆除已经破败的平房里,而背景则是高耸的现代大楼。一种过渡性即将消失情景油然而生。养狗需要高昂的代价,卖狗的人当下即是养狗的人,当然没有执照,必然在大楼的阴影下残活。隐喻是最常见的比喻,但是这些隐喻是经由空间上的场景安排,因而也是转喻。由于比喻来自于现场,非常自然,几乎没有刻意的痕迹,一般观众与一些学者经常习以为常,而无视其影像丰富的意涵。但是最平常的可能是极不平常,正如惠尔莱特(Philip Wheelwright)说:“最平常的事物,每天的场景,有如我们最没指望的个人,在响应想象的引爆下,可能突然显现惊人的可能性。”⑧
若将惠尔莱特的言语引申于电影文本,将意味两种意涵:一、电影日常写实的场景,可能蕴藏宝藏,平凡的角色也不能等闲视之。二、若是启动想象力与观察力,“平常的”观众也能看到不平常。当观众能如此感知,他将感受到“日常现存的是一种神秘,……一种让我们惊觉的神秘。”⑨
2.“写实”与叙述声音
再者,《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但画面与声音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布斯(Wayne C.Booth)所提到“告诉”与“显示”得以展现更驳杂的面向。影像的呈现是“显示”,是画面呈现的当下,虽然它可能发生于过去,而叙述的声音则以“告诉”观众当下的“现在”。有时画面是“现在”,语音叙述的是“过去”的当下。不论“显示”的是过去或是现在,不论“告诉”的是现在或是过去,声音和影像都不时会产生异步的美感。
进一步说,“告诉”与“显示”所显现的声音与影像的异步,也正是对于事件时间与言说时间相互纠葛所显现的趣味。在《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中,当马剑铃以回忆述说往事,影像“显现”的是过去的故事时间,但叙述语音却一再提醒观众这已经是时过境迁的当下。叙述语音是“言说时间”,“告诉”观众有关他过去的种种行径与思维。“显示”与“告诉”会相依相对,“故事时间”与“言说时间”也会对应或是对比。观众透过这样的叙述,可以感知各种意识(编导,不同时间的角色,不同声音与影像异步中的角色等等)的互动状态。有趣的是,“写实”反而有益于叙述的多重性,因为有人生真实的情境支撑,因此比较有说服力。
若以如此的面向审视“声音与影像的异步”后,再细致品尝《一一》,“第三种观众”当有进一层“惊觉”。影片中,NJ与当年的初恋情人阿瑞在日本旅游,与婷婷和刚结交的男友胖子在台北街头散步,藉由语音与影像的异步,将两种场景有机衔接串连。有时,父亲与阿瑞对话的语音,与其同时对应的影像是女儿与胖子散步的画面;同样,有时女儿与男友交谈的声音,画面映显的是父亲与初恋情人在日本风景里的身影。这是当代“写实”美学的新幅度,两种场景经由声音与影像的异步交织,两代的情感似乎相互成为对方镜子与影子。果然,父女最后都与对方分手。
再者,“写实性”并非封闭“幻想”的出入口。再以婷婷手拿纸鹤的一景为例。婷婷看到长久卧病在床的奶奶,终于醒来了,还为她编了一个纸鹤,婷婷安心地在奶奶的膝盖上睡着。醒来时,家里人声沸腾,原来奶奶已经过世。先前在奶奶膝上睡着的一景,是婷婷的梦境还是幻境,若是,为何手上的纸鹤还在?若不是,难道是奶奶的鬼魂真的编了一只纸鹤?叙述留下没有答案的开口。表象,这违背真实,因而不是写实,但人生违背常理,不能以逻辑诠释的,不时有之,这种现象反而是一种真实。
最后,虽然有意无意间,“写实”受到理论家的贬抑,但是在强调《河流》的乱伦同性恋是反映现代人的苦闷时,文化批评家已经暗指其“写实”。与《河流》相比较,《一一》是更难得的“写实”,因为父子乱伦毕竟不是常态,⑩而《一一》所呈现的是你我熟悉的人生。越熟悉的题材越难展现创意,因为新的创作者很难跨越既有的叙述与论述。当一个刻意惊悚的题材被认为是反映现代人的苦闷,而竟将其镜头的呆滞诠释成创意,一个反映大众人生而拓展深远的影像叙述,却可能因为“写实”以及不够标新立异而被忽视。这是“第三种观众”面对台湾电影论述所感受的悲哀。
结语
文化论述可以延伸思维的广度,但不知节制的套用理论,可能忽视了影像文本应有的密度与深度。“第三种读者”不迷惑于好莱坞式的煽情,但也不让理论扼杀了文本的生命力。他不因为煽情的影片卖座,而将枯燥无味的作品误解成艺术。影像成为一种邀约,在于它是动人的叙述,而不是文化论述的代言人。“第三种观众”的观念,让我们体会到:真正难能可贵的想象力,在于平常中显现的不平常,因为那就是你我可能仰俯其间的人生。
注释:
①所有的观众,包括文化论述的学者,都必须先知道蔡明亮一段“现身说法”才知道,原来黑暗中是一段父子同性恋。高荣禧在论文《蔡明亮作品中的孤寂主题与情色策略》里,引用了导演的这一段告白。蔡明亮在拍《河流》时,曾经自问:“本来只拍到父子在三温暖碰到就好,没做爱,只发现彼此都是同性恋,但最后却决定要拍比这更极端……就是父亲和儿子在黑暗里做爱。”高荣禧的文章发表于《电影欣赏学刊》(FaAs)134,第26卷第2期(2008年,1-3月号),页142。
②参见:莲实重彦,《考古学的恍惚——谈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张昌彦译,《电影欣赏》73期(1995/1.2):80-87.
③参见Iser,Wolfgang.The Implied Reader: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Chapter 11.Poulet,Georges."Critic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teriority,"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Eds.Richard A Macksey and Eugenio Donato.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2,pp.56-72.
④参见Heidegger,Martin.Being and Time.Trans.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62,p.200.
⑤这是梅卢庞帝《观照现象学》的核心观点。请参阅Merleau-Ponty,Maurice.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2.
⑥信手拈来,孙松荣说,“他展现了其捕捉都市变迁与脉动的精准能力”(孙松荣,《迎向恐怖的时代——台湾新电影时期的杨德昌》,《电影欣赏》(Fa)134期,第26卷第2期(2008年,1-3月号,页52))。詹明信(Jameson),焦雄屏,黄建业,冯品佳等都有类似的看法。李秀娟进而强调杨德昌的创意,在于拒绝复制既有文化,以及以后设态度创造差异,因而如此的“新”台北,也变成新影像,请参见她的《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杨德昌电影中的后设“新”台北》。
⑦李纪舍也有类似的看法:“杨德昌很明显地让家中幺儿扮演智者的角色”。参见李纪舍,《台北电影再现的全球化空间政治:杨德昌的〈一一〉与蔡明亮的〈你那边几点?〉》,《中外文学》387期,第33卷第3期(2004年8月),页93。
⑧⑨Wheelwright,Philip (1968) Metaphor and Reality Bloo-
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156,158.
⑩批评界经常将蔡明亮打破社会禁忌,或是跨越伦理尺寸的电影,误以为有创意;除了《河流》外,《天边一朵云》,也因为突破现有的裸露与性爱尺寸,而颇受肯定。
标签:文本分析论文; 卡拉是条狗论文; 杨德昌论文; 蔡明亮论文; 华语论文; 河流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