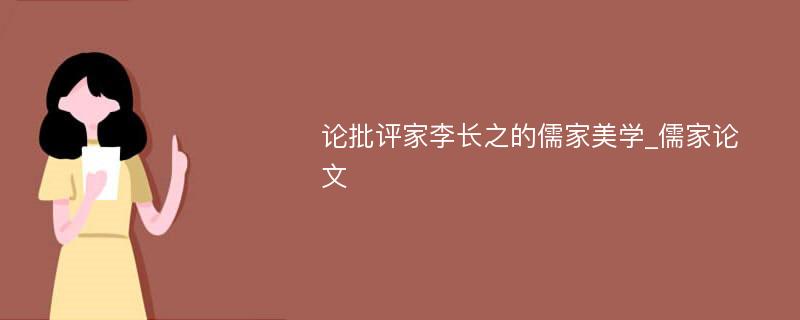
论批评家李长之的儒家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批评家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长之先生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文学家、翻译家,一生著述甚丰,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颇具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但学界对其研究起步晚、成果少、范围窄。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于对其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其他领域如美学、文学创作、翻译、文学史研究、教育理论等,或则略有论及,或则根本未论及。这样的研究现状无疑是与李长之的学术成就不相称的。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李长之的儒家美学研究加以探讨,希图以此揭示他的儒家美学研究的实绩,明确他在现代古典美学研究中的独特贡献,并借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古典美学研究在现代奠基阶段的学术理路。
一
儒家美学是李长之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对儒家(尤其是孔子)思想的推崇是密切相关的。他的儒家美学研究主要涉及孔子、孟子、《易传》、《诗序》等,是从根源入手挖掘儒家原典中的美学思想。那么,他为什么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呢?这关涉到他研究儒家美学的动机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他对儒家美学的具体评价。
李长之进行美学研究的时期正是国难深重,国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走向感到困惑,学界普遍在进行文化反思的时候。当时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层出不穷,形成了一股文化热①。李长之也于此时开始了较系统深入的中国文化研究。当然,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他的研究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明确的现实指向,甚至有失之偏颇的情绪化褒贬。他在此期的思考成果后汇编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1946年)。他有感于当时国防文化的弊病,提出文化国防的概念,并进而从文化角度对五四运动做了精彩评述。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希图在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中,缔造一个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在他看来,要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就要坚守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五四运动于传统文化颠覆太多,它不是如时人所言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只是做了一些启蒙工作,因为它“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②!“孔子之刚健雄厚的气魄没有被人欣取,孟子之健朗明爽的精神也没有被人欣取,被人提倡的却是荀卿,王充,章学诚,崔述一般人。”(《李长之文集》第一卷,P22。以下凡引李长之文集处,只标卷数和页码。)很明显,他要提倡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儒家精神,更具体地说就是孔孟相传的原儒的真精神。他在精神建设的施行方案中主张提倡新儒家精神,也是因为“新儒家精神不是别的,只是原始的儒家精神”,“直接探源于孔子孟子的真精神”。(第一卷,P106)
李长之认为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维系所在,是其他思想不可比拟的。与五四时期“打到孔家店”的做法不同,进入上世纪30年代,学界逐渐开始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重新审视,儒家思想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肯定。李长之更是斩钉截铁地提出:“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历久不变,能够浸润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够表现中华民族之独特的伦理价值的话,这无疑是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卷,P58。)明确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儒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儒家的根本精神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是需要一番仔细论证的,即使这样,结论也会是多样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阐释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文化心态、切入角度等均会影响到对阐释对象的评价。基于当时特殊的抗战语境,李长之有意对儒家思想做了如下概括“儒家的根本精神……其本质是刚性的,但其表现却无妨是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那就是珠圆玉润,温柔敦厚。”(第一卷,P63。)这一概括的现实指向不言而喻,而这也直接影响到李长之对儒家美学乃至整个古典美学的评价。他说:“只有从这种根本精神上可以了解中国人的美感——美感是文化的最高结晶。……中国的真正艺术造诣是壮美而不是优美。”(第一卷,P64。)他的这一观点也成为写于同一时期的《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一书的中心论点。这样我们就可明白,李长之认为儒家美学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流,它影响到了后来整个中国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姑且不论他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他至少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给予了儒家思想以充分肯定,重新确立了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审美观。
当然,李长之对儒家刚性传统的张扬也不是没有同调,在当时就有人持与他相近的观点。陈高佣就认为,孔子思想中表现着两种民族精神——刚与大,“因为能‘大’的精神然后可以同化异己包容异己;能有‘刚’的精神,然后可以克去私欲,抵御外侮。所谓‘仁’之一字,即包括‘大’与‘刚’两种精神之总和也。”③
既然张扬儒家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新文化的建设,那么为什么要着意张扬儒家的美学思想呢?这是受了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影响。他们是中国最早倡导美育的人,都将美育作为新民之路,且都予古典美学以充分肯定。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年)一文就结合西方美学探讨了孔子的美育思想。蔡元培则为美育在现代中国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李长之为蔡元培的去世专门写了纪念文章《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为纪念蔡孑民先生逝世作》。受他们的影响,李长之也意识到文化建设离不开美育,他认为“不懂美学,不懂教育,没法谈审美的教育。中国古代的美育很好,这是因为那时有极健康,极正确,极博大精深的美底概念,而教育的建设又那么完备之故。要建设美育,只有先建设美学。”(第一卷,P65。)他的思路是由文艺而美学而美育而文化建设。
二
李长之对儒家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孔子、孟子、《易传》、《诗序》等的美学思想的整理和阐释上。他认为这是儒家美学的传承谱系,其间在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又在不断丰富发展。限于篇幅,下面即择要论述他对孔孟美学的研究情况。
李长之对孔子可谓推崇备至。他说“讲儒家,就先要讲孔子,——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第一卷,P56。)他将孔子的美学概括为“古典精神”的,理由是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认为,孔子以上论述所体现的对于中正和谐之美的追求正与古典精神相通。而“古典精神乃是艺术并人生的极则”,是美善合一的,人生的并艺术的,是人生化的美学,这与道、墨、法诸家绝不相同。“儒家的根本精神是人本主义……一切在人情之中。”(第三卷,P480。)这种对人情的强调,在儒家那里就是礼,礼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礼不仅表现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在李长之看来,“礼就是人情的美化,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第三卷,P483。)他引用《礼记·玉藻》中的话“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认为这是人性的极致,也是一种美的极致。还不止此,他进而提出在中国古代“审美生活最发达的是周(周像希腊一样,值得人向往!),表现在社会各方面的是秩序,是数量,是节制,是井然而非散漫”。(第三卷,P482。)于是,他果断地下了这样的断语:“周文化的特点,可说就是在这一种审美文化。能负荷了这种文化使命的,就是儒家。儒家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道家(除了庄子)和法家所不能梦见的。”(第三卷,P483。)这里,李长之将周文化视为一种审美文化,是独具慧眼的发现。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孔子就是周代审美文化的传承者,他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古典诉求就是周代古典精神的延续。
当然,以孔子之伟大,也不会因一味追求古典之雅而失之偏颇,李长之也很好地揭示出这一点。他指出,孔子也有浪漫情调:“司马迁之赞美孔子乃是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立场而渴望着古典精神的。……他的一生,可说是浪漫而挣扎到古典的奋斗过程。从心所欲,是他根底上的浪漫主义,不逾矩就是那古典精神的外衣。——原来孔子乃是把浪漫精神纳之于古典的!”(第三卷,P186。)这就探到了孔子的丰富多彩处。正因为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所以孔子时时处处注意人格修养,他懂音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他的作人“是作到了像一件极名贵的艺术品的地步”。(第一卷,P69。)“孔子在人生里,已是一个可以把形式运用自如的大艺人。”(第一卷,P264。)这艺术化的人生是孔子美育思想的核心,是他美善合一主张的具体化,因为“艺术的原理也就是人生的原理,美的极致也就是善的极致”。(第三卷,P66。)那么,何谓艺术化的人生呢?对此,李长之有明确表述:“所谓艺术化的人生就是不牺牲自我,却也不给别人以难堪的人生。自我相当于创作意欲,与别人的关系相当于艺术形式,好的艺术便须既不委屈前者,又不破坏后者。”(第一卷,P265)
应该指出,李长之特别拈出孔子的人生艺术化追求,除了肯定儒家深切的现实关怀,其深层用意则在反对战争、批判充斥于现实社会的非艺术化生存方式。诚如斯言:“从温暖的人情出发,当然反对战争”(第一卷,P259。),“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安定,是统一,是人情化,是伦理化,是教育化,是文化高于一切,是美育建设在刑法制度之上”。(第一卷,P260。)与之相反,现实中弥漫的是远离艺术、审美的功利主义风气。对此,当时不少思想家、艺术家均提出了改造现实的理论主张,其中朱光潜、丰子恺等人就鲜明地标举人生艺术化的主张。与之相比,李长之则到原儒那里找寻理论资源,希图以古救今并借此改变时人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比如与一般人批评儒家过于现实功利不同,李长之认为孔子恰是反功利的:“孔子是知道美学的真精神的。美学的真精神在反功利,在忘却自己,在理想之追求。孔子对小人君子之别,即一刀两断地从功利与否上划分,他的话是:‘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现在是‘小人’的世界啊,也就是‘喻于利’的世界啊,无怪乎反功利的主张总为人所不省了。孔子自己一生却秉着反功利的精神——也就是美学的真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奋斗下去。”(第一卷,P69。)我们于此可见,李长之的儒家美学研究不是局促在象牙塔里的,而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
他认为道、法、墨、佛诸家都有或隐或显的功利动机,只有儒家在根本上是反功利的。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甚或在今天恐仍为许多人所不解。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儒家美学的功利取向较道家、佛家要明显得多,孔子关于艺术功用的“兴观群怨”说即是一例。如此看来,李长之似乎是张冠李戴了,要谈反功利应该讲道、佛二家才对。其实不然。这关涉到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撞击交汇及中国美学如何以西释中的大问题。
多数研究者都将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说在中国的被广泛接受归因于国人思想中的庄禅文化积淀。如有论者指出:“康德美学中的‘审美无利害性’显然与庄禅美学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现代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内心中认同、接纳审美无利害的思想。”④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因为,儒家美学与审美无功利说并不相斥,对审美无功利说的肯定不一定就意味着对儒家美学的否定。现代美学家译介包括康德美学在内的西方现代美学是为了补本土美学传统之失,纠传统美学之偏,并借此实现改造社会现实之目的。如果这种引入以动摇传统文化根基为代价则是得不偿失的。因而,就有问题的另一面——在肯定审美无功利说的同时予儒家美学以新的阐释,使其由被否定对象转化为可以借助的传统资源。
事实上,现代美学对儒家美学的批判主要指向的是其“文以载道”的思想,而这并不是原儒的本意。早年对传统文化抨击甚烈的王国维就肯定了儒家美学的正面价值,他认为:“孔子之学说……审美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⑤ 李长之的好友、著名美学家宗白华也充分肯定了孔子的美育理想:“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实在就是美感教育。”⑥肯定儒家的美育主张,其实就是肯定儒家的审美无功利观,因为现代美学家们就是将审美无功利观视作美育的基础的。在现代中国反思传统的文化语境下,审美无功利的命题顺应了时代潮流,有利于对传统的批评继承。现代美学家接受与提倡这一命题不是为了从现实中逃遁,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有力地介入现实,而介入现实是与儒家相近而与道佛二家相远的。因此,审美无功利观与儒家美学是可以相融的。由此看来,对于有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鲜明的介入现实态度的李长之,他之特意阐发儒家的无功利美学思想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其实,用西方美学资源激活中国古典美学,使其焕发新的生机,是当时许多关心民族文化走向的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恰如有论者所言:“在美学学术方面,审美无利害观念意义重大,尽管现代知识分子重视它的纯使用,假定它的先验性,但是他们在对社会文化关切的过程中,显然没有被审美无利害概念所限制,审美无利害提供给他们出世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没有使他们退隐这个世界,相反,这反而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审美无利害的积极意义也表现出来。这在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身上得到显著的表现。”⑦这段概括同样适用于李长之,在看似矛盾的审美话语背后他们都进行了巧妙地择取和整合。
以上是李长之对孔子美学思想评价之大端,他的观点可以凝结为一句话:“孔子一生的成功,是美学教养的成功。”(第一卷,P69)在他看来,正是美育的成功使孔子成为人类永久的导师。
三
再看李长之对孟子美学思想的研究。他注意将孟子置于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进行知识谱系学的考察。《从孔子到孟轲》一文即在重点论述孔孟思想传承的基础上形象生动地阐明了他们人格精神的不同:“用齐和鲁的精神比,孔子的精神是纯然鲁,孟子却不免沾染了一些齐气。用科学和艺术比,孔子的精神是较近于科学,而孟子的精神则更近于艺术。倘只以艺术喻之,孔子是近于音乐的,内容含蓄而丰富,暗示性强;孟子是造型的,单纯而明了。”(第一卷,P271。)简言之,李长之认为孟子的浪漫色彩比孔子浓,艺术气质比孔子重,“其审美态度乃尤纯粹而鲜明”(第一卷,P69。)。因而,李长之对孟子美学的阐释较孔子美学更全面充分。
其一,李长之着重阐释了“充实之谓美”的命题,认为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定义”,并将其作为古代有“健全的美学”的证明。他认为,孟子所谓“充实”与荀子所谓“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的“全之尽之”及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信”是同一含义。进而言之,他从美学的学科属性出发揭示出孟子等人之所以能对美的本质做出明确的概括在于他们“有一种深厚雄健的形上学为之基础故”。在李长之看来,每一种美学(除却实验美学)都有它坚实的哲学基础,孟子美学自然也不例外。那么,作为孟子美学基础的是怎样的哲学观呢?在李长之看来主要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就是孟子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也就是将小我的生命无限扩大而为一大我,从而与宇宙融通为一,个体生命无限充盈,而充实之美就是生命充盈的美,精力弥满的美。
不仅如此,李长之还揭示出“充实”是孟子所谓美的首要条件。他对孟子的美学论述加以归纳,认为孟子论及的美的条件有三:充实、完成、有生命。关于“充实”已如前述,关于“完成”,他解释说:“完成,换言之,即是须把原始的一点好的根苗发挥尽致,发挥彻底。”(第三卷,P193。)如孟子所言“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告子上》)“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行。”(《尽心上》)关于生命感作为美的条件,李长之则是从孟子对濯濯牛山的惋叹中看出的。于此可见,李长之对孟子美学思想的挖掘并不限于其显明的论美文字,而是注意揣摩其言外之意,借西方美学烛照传统美学,掘微探幽,使原本潜隐的美学思想得以清晰呈现。这与一般治美学者仅拘泥于显明的论美文字不同,更利于完整把握研究对象的美学思想。
当然,“充实之谓美”的命题在孟子的论述中不是孤立的,其前有对“善”和“信”的论述,其后有对“大”、“圣”、“神”的论述,其中“大”与“美”之关系最为密切。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尽心下》)这里,孟子的本意是讲人格修养的六个等级,或曰六层境界,它们是前后相续,逐层递进的。“美”是人格美的中间状态,它是“在个体人格中完满地实现了的善,并且它自身就具有同善相融洽统一的外在形式”⑧。孟子继承了孔子美善合一的观点,提高了美的地位,美不再是外在于善的,它以美的形式体现着内在于自身的善。结合前述我们可以看到,李长之在解释“充实之谓美”的命题时在孟子本意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多的生发。他关于“大”的阐释也是如此。
李长之是结合康德关于优美和壮美的划分阐释“大”的:“近人讲美学,称‘美’有两种。一是优美,二是壮美。其实壮美不能称美,因为它已别是一个范畴了。孟子在说‘充实之谓美’之后,又紧接着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公孙丑说:‘道则高矣美矣’;这‘大’与‘高’颇相当于壮美。但是它究竟是否是美的一种,还是和美并列,二者究竟有何种区别与关系,这时是还不曾深究的。”(第三卷,P194。)简言之,李长之认为孟子已论及优美与壮美两大范畴,但对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尚缺乏清醒的认识。这里,李长之只是说“大”相当于壮美,并不是说它就是壮美,这个把握是准确的。对照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对李长之的阐释有更明晰的认识。李泽厚、刘刚纪认为:“‘大’是‘充实而有光辉’的意思,也就是比一般的美在程度和范围上更为鲜明、强烈、广大,是一种辉煌壮丽的美,包含有一般所谓‘壮美’的意味。”⑨
其二,李长之深入阐释了孟子的美善合一观。这一理论是由孔子奠基的,孟子对此加以深化,使之成为中国美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李长之在评析孔孟的美学思想时重点分析了儒家美学的这个核心命题,显示出他对儒家美学的准确把握。我们知道,“儒家美学的中心是反复论述美与善的一致性,要求美善统一,高度重视审美与艺术陶冶、协和、提高人们伦理道德感情的心理功能,强调艺术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作用。”⑩ 那么,孟子对孔子的美善合一思想的深化又体现在哪里呢?对此,李长之在较早完成的《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一文中概括尚不明晰,但在《批评家的孟轲》一文中则有了明确的概括:“美和善的合一,以善为一种审美的对象而欣取之,而执著之,而热爱之,这是道德家的最高境界,也是美学家的最高境界。孟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极多。”(第三卷,P194。)他认为孟子所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是“把理义之可爱,比作好吃的肉之可爱,宛然是柏拉图形容理念之可爱之意”(第一卷,P70。)。这样的评价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因为这正是孟子美学超越孔子美学之一方面。
其三,李长之结合西方哲学对理想境与现实境的划分对孟子的美感理论进行了全面评价。孟子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告子上》)这里,孟子触及了美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美感的普遍性问题。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一个不同处即在于人有美感上的共同性,这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美感的普遍性问题。李长之以其深厚的学养挖掘出孟子这一重要美学观点,可谓言他人所未言。他认为孟子对美感普遍性的认识不限于理想境(即一种理想状态),对现实境亦有论及,所谓“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告子上》)即是。这样孟子就兼顾了美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发现在当时亦是难能可贵的。
不仅如此,李长之还明确指出孟子对美感的认识是同他的性善说紧密相关的,后者是前者的哲学基础:“所谓在理想境,就是在形上界,就是在还没有接触于物质之际。关于味觉的讨论,自不能和性善的体系划分。性在形上界,都是善的。孟子的性善学说,只有从这一个观点可以了解。”(第三卷,P195。)正是有感于孟子美学思想的精深,其创造力之丰盛,李长之对孟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孟子为孔子后唯一有创造性的美学大师,实践与理论,均极可观。中国古代的美育,即是在孔孟二人的辉光下面发挥着,作用着,灌溉着。”(第一卷,P71。)
其四,李长之借鉴克罗齐美学阐释了孟子的美学批评方法。他认为“以意逆志”就是“直觉的了解”。他首先解释了何谓直觉:“直觉是混一的,其着眼是整个,其所见是林而不是树,是全而不是分。”(第三卷,P197。)直觉说是克罗齐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克罗齐正是从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不同界定直觉的内涵的。他说:“知识有两种形式:不是直觉的,就是逻辑的;不是从想象得来的,就是从理智得来的;不是关于个体的,就是关于共相的;不是关于诸个别事物的,就是关于它们中间关系的,总之,知识所产生的不是意象,就是概念。”(11) 可见,克罗齐对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直觉思维的特征是想象的、个体的,其结果是形象化的意象,而非抽象概念。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就是李长之所说的“直觉是混一的”,“而不是分析的”,“是全而不是分”。
基于对直觉的界定,李长之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做了颇有创见的阐释。孟子是在回答弟子咸丘蒙的问题时提出“以意逆志”说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孟子认为仅就字面意思理解诗会导致误读。李长之指出,以文害群、以辞害志的人之所以会犯错误就是因为“缺少深入的直觉”,而“以意逆志,就是用批评者的心灵,去探索那创作家的灵魂深处”。在此基础上,李长之还分别对孟子所言之“文”、“辞”、“志”、“意”做了详细阐述。他说:“孟子所说的文,可说相当于所谓花词(Figurative expression)。所说的辞,可说相当于事物(Things),所说的志,可说相当于作家的观念或意匠(Idea)。所说的意,可说相当于批评家的审美能力或了解能力(Taste)。”(第三卷,P197。)这是直接借用西方美学概念对中国传统美学概念的阐释。这种简单类比可能并不恰切,比如“志”就不能与“Idea”完全对等。但李长之在阐释时也很审慎,他反复用到的词是“相当于”,也就是说大体上可以这么类比,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区别。
此外,李长之还指出孟子所谓“何必同”体现出的是一种平等的批评态度,与克罗齐的批评观相近。他认为,在艺术创造上往往难有高下之分,对古典、浪漫、写实、表现等流派不应妄加轩轾,即使对李白、杜甫也不应拘于成见而强分优劣。这是因为“凡达到某一个限度的伦理造诣或艺术造诣,就是平等的,就是没有高下之别,也不必迁此就彼的。”(第三卷,P197。)如果强分高下优劣就有违于基本的批评原理。正因此,李长之充分肯定了孟子这一批评方法,认为:“孟子提出的方法,是克罗齐的方法,是真真正正欣赏艺术的方法,却也是真真正正以艺术为立场而欣取人生的方法。”(第三卷,P198。)
综上所述,李长之立足现代,参照西方美学对孔孟美学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触及了儒家美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其研究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传统美学研究的现代奠基阶段,他的研究工作还是弥足珍贵,颇具启示意义的。
注释:
① 相关论著参见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陈高佣还在书中提出了建立“文化学”的设想。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主要思考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矛盾价值、中西文化之异同、中国新文化建设等问题。
② 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5页(以下凡引自《李长之文集》的只在文中注明卷数和页码,不再另注)
③ 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10-111页
④⑦ 杨平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44页、70页
⑤ 佛雏.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56页
⑥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63页
⑧⑨⑩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74页、174页、33页
(11)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7页
标签:儒家论文; 美学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论文; 孔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李长之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