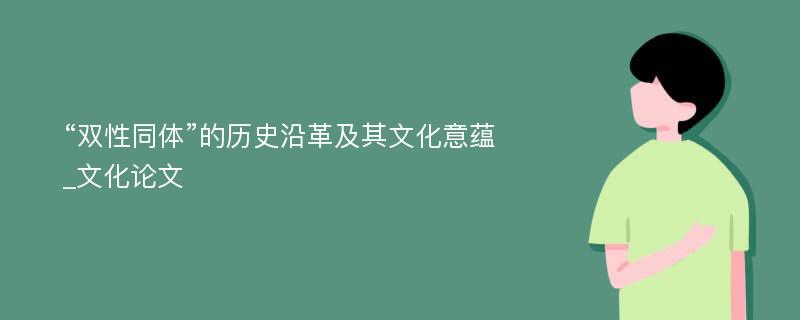
“双性同体”的历史演变及文化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体论文,蕴涵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双性同体”(androgyny)一词的生物学本义, 一般用于表述动植物的雌雄同株或一些罕见的生理畸形者,本文所涉及的“双性同体”则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因为性别矛盾使人类距离两性和谐的理想一直相当遥远,在伴随人类不断追求性别意识真理性的过程中,“双性同体”的蕴涵也不断发展变化,并在现代回归中成为诸多学者重视和探讨的对象。
一、“双性同体”观念的产生
各远古文明普遍认为:造物主是半阴半阳的,或者是雌雄同体的,这非常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彼此封闭的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物和其他遗物中。这种奇特的共性包含了一个共同文化代码,反映了人类的原始思维进化到语言阶段后形成的“双性同体”神话。
艾利亚德在《比较宗教学模式》中“神圣的双性同体的神话”一节中写道:“由于在神性之中同时存在着所有的禀赋,所以完全必要的是从神性中或明或隐地看到两种性别的合并表现。神圣的双性同体只不过是表达神的二位一体的一种原始公式;早在形而上的术语或神学的术语表达这种二合一神性之前,神话和宗教思维就已首先借用生物学的双性这一术语表达了它,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这样的情况:远古的本体论用生物学的语汇表现出来。……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信仰中看到的神圣双性同体都有其自身的神学和哲学的蕴涵。这个公式的本义在于用生物性别的语汇表达在神性核心中同时并存的两种对立的宇宙论原则(阳与阴)。”(注:艾利亚德:《比较宗教学模式》,希德英译本,希德与沃德出版公司1958年版,第420—421页。)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暗含了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天和地本是联合为双性同体的,他们永恒地结合在一起,后来才相互分离,并且成为单一性别的一对。传说华夏种族由伏羲和女娲兄妹相婚而产生的,正因为伏羲和女娲之间是一种既是兄妹又是夫妻的关系,由此也能理解两者为何是双头人首蛇身的神(注:何新:《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80页。)。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断言:人类最初是半阴半阳的,是宙斯把他们分成单性别的两半,他们渴望重新结合,以此来解释男女之间的恋爱和结合倾向的根源。基督教的《圣经》中认为上帝是雌雄同体的,上帝把亚当分成两个有性别的组成部分,一个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夏娃,来自他的一半,这个原本双性的人被分为两半,爱情使他们渴望重新结合,这种渴望是性快乐的源泉,而性快乐则是一切犯罪的开端(注:(美)O.A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5页。)。
在埃及神话中,始祖之神也是双性同体的。地神格卜和天神努特原来相互拥合,难以分离。后来其父(一作其子)大神舒将努特即天宇高高举起,努特才同她的兄长,也是她的丈夫地神格卜相分离(注:安西斯:《古埃及神话》,见塞·若·克雷默编,魏庆征译:《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2页。)。
婆罗门教的圣书《往世经》说:“至高无上的精神在创世的行动中成为双重的:右边是男性,左边是女性。她是玛亚,永恒不灭的。”又说:“神圣的创世因体验不到极乐,是孤独的。他渴望有一个同伴,直接满足欲望。他使自己的身体分成男性和女性。他们结合,创造了人类。”(注:(美)O.A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68页。)
在墨西哥先民的眼中,“太阳和大地也被视为丰饶之源以及万物之母,被想象为二元(二性)实体。他既不失其一性体(在古歌中,他始终为单一神),却又被视为二性神,即人类之繁衍的男主宰和女主宰,在神秘的宇宙结合和受孕中,此神为宇宙万物奠定了始基”。这一双性至高神看来不仅担负起开天辟地的伟业,而且也是创造生命和人类的始祖(注:莱昂,彼蒂利亚:《墨西哥神话》,见《世界古代神话》,第416页。)。
“双性同体”观念还通过凝固在雕塑画像等上画的“双性同体”形象,直观地得到展示。在欧洲发掘的公元前七千年到六千年间的雕像中,具有明显女性和男性结合在一个雕像上的特点在公元前六千年以后也没有完全消失。印度古代塑像把湿婆和他的妻子雪山神女表现成一个具有雌雄同体性质的存在物。湿婆和雪山神女的这种阴阳合一的形式,叫做维拉吉(注:(美)O.A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6页。)。 在中国已在多处发现类似的“双性同体”形象,如在青海乐都柳湾出土过一个两性人陶壶,此人面部粗犷,体魄魁梧,明显是一个强健有力的男子形象,但其生殖器既似男根,又有女阴特征。河南禹县民瓷窑贴保留着一种传统图案,有一种抓髻娃娃,头扎双髻,具有女性特征,但长有男根(注:宋兆以:《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出版,第77页。)。
“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在先民原始思维中的流露及其在神话中形成跨文化的神话原型,并非偶然和巧合。神话思维中双性同体的阶段,在历史上对应着的是人类处于无性意识的阶段。“双性同体”的无性阶段,反映了原始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由上述众多例子可以看出,这一原型包含的最基本的意义是:宇宙万物、人类以及自然的创造,是由两性共同(通过合体形式)完成的。从这一基本意义可以推导出另一重意义,分体初始状态(性别意识产生的标志),女性与男性有同等的创造力,两性没有身份、地位和尊卑的差异(注:周乐诗:《“双性同体”的神话思维及其现代意义》,《文艺研究》1996年5期。)。 反映了史前伊甸园的生活情景和原始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
二、“双性同体”观念的演变
当父权代替了母权制后,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动,明显加速了双性同体观念的转变和分离。而双性被切割后的分体,则意味着性别意识得到了强调,无性阶段进入了有性阶段,性别矛盾由此产生和激化。
在双性同体转换为分体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激烈的斗争。如流传在两河流域、世界上最早的苏美人“创世神话”中,女性太阳神后为男神替换,而被贬谪到陪衬的月亮神位置。在原来的传说中,女神Nammu不但创造了宇宙,还独立生下了天空、大地及其间的万物,但在日后被修改过的神话中,这位女神的名字变成了Tiamat,只代表咸水女神,另外出现了一位甜水之神的男神Apsn。Tiamat在Apsn的帮助下,生下众神,同时也生下蝎子、半人半马的怪物。后来另一位英勇的男神在雷电、暴风雨及烈火的帮助下,追杀Tiamat,把她杀死了。在这个神话的衍变中,女神从创造万物的至高之神,到和男神分担职能,直到最终成为邪恶的代表,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了女神被贬低的过程。它是社会中女性被贬低的历史过程的镜像再现(注: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出版,第212页。)。
罗马人认为,天和地(乌拉努斯神和盖亚神)最初曾是以一种无限的性拥抱或作为一个雌雄同体的神而永恒结合在一起的。在许多神话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观念,其中大多数神话记述,这两个始基(雄性乌拉努斯和雌性盖亚)是后来被割裂开的。在赫西俄德(Heslnd)所著的古希腊人的《神谱》中,也记载着有关克劳诺斯(拉丁人的农神)如何用镰刀从他的父亲乌刺诺斯身上割去性器官而把天和地分开的故事(注:(美)O.A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6页。)。
在新西兰的土著居民毛利人中,也流传着天和地被扯开而分离的故事。天神拉吉和他的妻子芭芭在无止境的性拥抱中联为一体无法分开,他们产生了诸神和万物,后来这对夫妻被他们的孩子(其他神)扯开而分离(注:(美)O.A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68页。)。
在中国神话中,天公地母从合为一体到一分为二,“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天公地母以清浊作了区分。而在汉语中,清浊的褒贬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女娲神话也有一个演化过程。女娲曾在远古神话中占据过一个非常显赫的地位,以炼五色石补天,杀黑龙,断鳌足以济民生而著称于世。然而到了《淮南子》中,却成了辅佐丈夫“伏羲治天下”的配角。秦汉时候伏羲、女娲的交尾双头人像也表明了女娲为人类始祖的史前神话,由伏羲、女娲共同造人的神话所替代,这种替换很明显是一种性别角色的调整。
在民俗的层面上,男女双方的割礼是一种最古老的风俗,也是一种性文化的反映,包含建立性别意识的观念,具有生理和宗教的双重意义。蒙昧的少年正是通过割礼,确立自己的性别意识,而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注: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出版,第257页。)。“行割礼,……乃是跟先天双性同体的恐怖作斗争手段之一”。在西文中,英语“性(scx)”一词,便由拉丁文sccus一词衍生而来,它渊源于seco一词,意为截下、切割开(注:(美)O.A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6页。)。
在社会的层面上,双性同体的分离则表现为阉割文化的出现。双性分体标志了父权制的确立,随生殖器崇拜的转变和女性贞操观的加强,而以生殖器官为惩治对象的阉割应运而生,成为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维护父系社会的有力工具。
在宗教的层面上,引发了“双性同体”的一种异化,即通过“无性”而达到两性间的平衡。由于宗教神话中最古老的崇拜对象是双性同体的,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神职人员用阉割的方式,象征自己超脱于男女性别对立之上,达到双性合一的神圣境界。更有学者从宗教学、语源学和人类学的多重视野审视《诗经》与“双性同体”和阉割文化的密切关系,对殷墟卜辞里字(寺字所从)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寺字又有寺庙、寺院等宗教方面的含义,进一步解析证明寺的原型就是主持祭礼的宗教领袖,《诗经》中的“寺”就是指寺人,即被阉宦官和太监。寺人与神圣之“诗”虽然伴随着祭政合一体制的分化而日趋衰亡,但始自史前时代的净身祭司传统却在中国古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从中人人格中直接派生的中性化伦理观,极为鲜明地体现在《诗经》所标榜的“温温恭人”式的君子理想中,成为后世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思想源头”(注:叶舒宪:《“诗言寺”辨:中国阉割文化索源》,《文艺研究》1994年2期。)。
在政治的层面上,突出的反映是中国宦官制度。为解决王朝子嗣延续而专门设置的大规模女性集团及一整套相应的管理体制的中国后官制度,是全世界帝国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管理体系最完善的。其内部结构是:皇帝是唯一真正拥有后宫性权力的人,以森严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庞大的女人群,以“中性”奴隶宦官作为中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性文化形态。
三、“双性同体”的现代回归与文化蕴涵
苏格拉底认为,人起初是圣洁的和无性的。只是在产生了罪恶之后,才失去了他们的精神实质,获得了他们的动物性质,具有性的差别。女人是男人肉欲的堕落性质的人格化和体现,但最终返回神圣的同一后,所有性的特点都将消失,最初的精神实质重新获得。乃至当代也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是最初的两性人的退化的代表,雌雄同体实际上只是在类型上向“最初完美的两性人”的一种回复变异(注:(美)O.A魏勒著,史频译:《性崇拜》,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26页。)。“双性同体”观念中反映的人类追求双性平等的愿望,经过数千年的产生、异化,重新在现代社会回归,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1.“双性同体”与生理学和心理学
西方关于心理双性化的研究历史悠久,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著名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理论,用“男性的女性意向”和“女性的男性意向”两个术语,说明人类先天具有的双性化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人类学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雌雄双性体,这个双性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因为只有这样,两性之间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协调,达到真正的理解,因为人真正能理解的其实只是和自己同类的事物。为了使个体人格得到健康和谐的成长,应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因素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因素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一定的展现,否则这些被压抑到意识深处的异性因素的逐渐积累,最终会危及生命主体的存在(注: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第53页。)。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弗洛姆提醒说:“我们必须永远记着,在每个个人身上都混合着两类特征,只不过与‘他’或‘她’的性别相一致的性格特征更占多数而已。”(注: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第259页。)
性别的中性化或双性化,决非一般的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的同义语,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较多的男性气质和较多的女性气质的人格(心理)特征。这是一种超越传统的性别分类的、更具积极潜能的理想的人类范型。在丰富多彩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双性化心理和行为特征的人,往往能较好地适应多变的生活环境。双性化者比所谓纯粹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家庭婚姻更容易和谐,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更积极、肯定的自我评价。既然人类在很多方面和不同程度都是双性化的,那么,消除男性本位的性格,回归男女本来的尊重平等、和谐的关系应该是可能的。人的心理—行为的双性化这一“革命性”进化的完成,将会成为人类理想的角色模式(注:转引自韦澍一:《从两性关系重组谈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2期。)。
2.“双性同体”与教育学
当代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风俗,也在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两性结合模式及其伦理道德。许多人抱怨:“现在的男孩子怎么了?”有的研究指出,在中国实际生活中,有不少男女已冲破了陈旧的性别行为差异的框框,显示一代新女性和新男性的“特点”,并预测“未来的男性和女性在人格特征上的差别不会消失,但差别不会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具有双性化人格特质的人会越来越多。”“传统的绝对化的性别角色是不尽理想的”,“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在现代化快节奏、高开放度的信息社会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成年进入社会以后,都将很难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一个适应能力良好的人,应该拥有刚柔兼济的双性化人格特征,即男性要具有部分女性人格物质,女性也应具有部分男性人格特质”(注:转引自陈建强:《独生子的人格双性化》,《当代青年研究》1995年4期。)。许多人从两性心理发展所存在的客观差异分析入手,针对目前由于忽略性别特征所导致的种种问题,批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实施“因性施教”原则的必要性,希望通过教育改变性别角色的软性化倾向和课余生活取向软性化形象(注:转引自胡江霞:《论“因性施教”及其实施策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5期。)。
3.“双性同体”与文艺理论
回顾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欧美的女权主义运动,向传统的男性社会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挑战,“双性同体”观念又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女权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演化中得到了再现。尽管在女性主义批评界内部存在着矛盾和歧异之处,但却能普遍引入了这一概念,并且都将它作为一种文学的理想境界提出。这意味着一种更高境界的超越性别的角色认同,即两性精神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在她们的作品中,出现明显的“双性文化完善互补”的理想,即力图使人们认识到,基于生理不可克服的男女差异,将是各自的优势,而不成为权力压迫的借口;通过互相补充,最终建立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这种不带性别偏见的文化设想,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虽然就目前而言,距“双性文化完善互补”的理想似乎还较为遥远,男权中心依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男权文化的巨大网络仍渗透于各种缝隙之间,阻碍女作家的思考及言说,但“双性文化完善互补”仍不失为一种文学写作的理想,也就是说男女作家都应在两性的互补共存之中,在探索存在意义的高度上确立文学的坐标,从而将人类生存的境界推向更完善和更高级的层次(注:参见周乐诗:《“双性同体”的神话思维及其现代意义》,《文艺研究》1996年5期;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4.“双性同体”与中国现代社会
近年来中国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与日益西化的当代商业文化现实相纠缠,使两性之间布满了暗礁险滩,双性两败俱伤的情形屡屡发生,构架了当代男人与女人非常独特的心态,充满了两性现实生存的焦虑感,尤其需要“双性和谐”的文化情调和氛围滋润,从不堪回首的双性关系现状达到理想的“双性和谐”境界。中国现代学者已经跳出“双性同体”这一西方化的概念,开始使用“双性和谐”的术语,从文化和政治的高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希望使其于双性关系之上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多一点“双性和谐”,多一点真诚,多一份宽容,少一些人性的异化,少一些两性之间的勾心斗角,都显示了“双性和谐”文化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力量,为“人文精神”作了中肯而不无宽容的注释(注:万莲子:《掇拾“双性和谐”的文化意义》,《文学自由谈》1995年4期。)。 近几年驰名于文坛的一些中青年女作家如毕淑敏、赵玫、迟子建、王晓玉、马瑞芳、叶广芩、徐坤等,均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艺术追求,她们尽力拓展艺术视野,以女性的目光去穿照历史与现实生活内容,从中获得关于人类命运的永恒话题,显示出极高的审美价值。她们的文学探索表明,女性文学正在逐步走出单一的情感及性爱的天地,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男性话语的接轨,以抵达文学“双性和谐”的理想境界(注:周艳芳:《世纪末:女性文学话语的复归与重建》,《小说评论》1997年2期。)。
结语
大自然对于人类两性奇妙的创造,虽然为人类实现两性的互补互助,从而获得共同的幸福和为社会的共同利益提供了自然基础,但两性关系的矛盾,使人类距离实现两性和谐的理想仍相当遥远,因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也就牵一发而动全身,联系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运作规律。换言之,由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带来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展开的人类的一切行为,无不打上双性制衡的烙印。
由于信息社会的来临,地球正变得相对缩小,世界文化发展一体化趋势日渐分明,因此倡导“双性同体”这一理想文化模式具有世界文化战略意义恐不为过,它与大文化时代相适应,使活动在地球村的男人和女人们,既是塑造文化品质的主体,又是影响并改变文化品质的客体,两性的和谐关系可以造就稳定进步的人类未来。也正由此,“双性同体”作为一种理想文化境界,特别值得人文工作者关注。
从哲学意义上说,双性和谐与双性差异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差异先在地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之中,形成了人类行为的性别差异,而双性同体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真理性,强调性别意识的合理度以及人类对性别平等的认同程度。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具备的性别意识文明进步程度总是一定的。但由于人类总是在不断追求性别意识的真理性,这一追求过程已成为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象征,因而双性差异中的不平等层次将终究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形式,它迟早会被人类自己淘汰。一句话,“双性同体”的存在是与人类的本质相同一的,是与双性差异相辅相成的。至于与差异伴生的性别不平等等一系列现象,人类一定会通过自身性别意识的演化而在不断的双性和谐追求中克服,从而在冲突与和谐的斗争中,建立一个崭新的双性关系价值世界(注:万莲子:《掇拾“双性和谐”的文化意义》,《文学自由谈》1995年4期。)。
毕竟,男女性别有其自然的区别,双性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同体。“同体”一词似也不能形象地概括哲学意境上的“双性平等”这一文化理想状态(注:萧兵、叶舒宪:《〈永恒回归〉与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而中外学者认为“双性同体”的伊甸园、桃花源寻找母型的努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只有超越性别的种种努力,才可能使两性实现真正的平等,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和文化模式,这才是“双性同体”或“双性和谐”的真正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