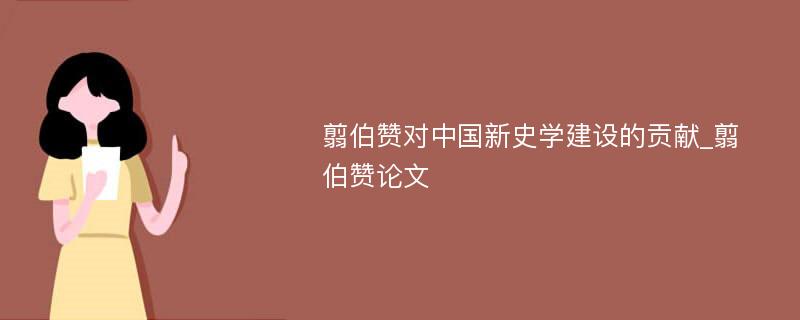
翦伯赞对建立中国新史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贡献论文,翦伯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翦伯赞(1898—1968年),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
翦伯赞幼年接受清真学校启蒙,1919年夏,毕业于武昌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后留学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学。1926年11月在长沙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次年1月, 奉命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北上太原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后,遭通缉。后活动于北平(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从事理论宣传和统战工作。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以前, 任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私人秘书,做了许多掩护和救助革命同志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除了继续保留覃振的私人秘书名义之外,还先后任或兼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历史教师,郭沫若任主任委员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专门委员,陶行知任校长的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教授,上海大夏大学和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天津《丰台》旬刊、湖南《中苏》半月刊、上海《大学月刊》、香港《文汇报·史地》副刊主编。在重庆时,还曾以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兼《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建国之后,兼职更多,最多时达三十余个。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等。
翦伯赞著作等身,共发表论文三百余篇,专著和论文集十余种,共约四百万字。其中名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一、二两卷,《中国史论集》一、二两辑,《历史问题论丛》等。所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外历史年表》以及众多的其他著作尚不在内。
翦伯赞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史学成就占主要地位,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宣传并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中国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但比较全面、具体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以后,翦伯赞在这时已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热切地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于历史研究。他于1930年11月至次年2月, 为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而发表的论文《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三篇(注:北平《三民》半月刊,5卷6、7、8、11期。),都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剖析论证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他相继发表的《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以及《介绍柯瓦列夫〈古代社会论〉》、《介绍一种历史方法论的名著——盛岳译〈史学的新动向〉》(注:南京《劳动季报》8期, 1936年3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3期,1936年秋季,同卷2期,同年夏季;上海《世界文化》1卷2期,1936年12月。)等,则主要是阐述或评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或有关的重要著作的。
1938年8月, 翦伯赞在长沙由新知书店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可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却视此书为大逆不道。次年此书再版时,即被当局列为“禁书”。此书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系统全面地讲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书中,翦伯赞密切联系中国的现实或历史,进行论述。他说: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
此书观点鲜明,批判有力,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痛恨。
建国之后,翦伯赞仍是一如既往地宣传、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表现尤为突出,贡献巨大。1958年初,极“左”思潮已在中国萌发。2月, 陈伯达适时地以其特殊政治身份在国务院科学规划会议上,以《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为题,发表了一次演说。至5月初,他又在北大校庆60周年的万人大会上, 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又一次发表演说。这连续两次演说,都有强烈的煽动性,为极“左”思潮的掀起推波助澜,起了极坏的作用。于是在史学界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吹起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和浮夸、浮躁的歪风。表现在史学领域,出现了抽象化、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错误倾向,严重破坏了人们在教学和史学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翦伯赞于1959年开始,连续发表抨击极“左”思潮的论文,其中主要有《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等。1961年夏至1963年春,他还先后发表了《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还将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向一些高等学校师生和文化、学术工作者发表演讲。这些论文和演讲都结合当时史学界和其他学术界的实际,着重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严厉抨击了一些违反乃至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划清了一些重要是非的界限。
1962年夏天以后,高等学校和学术界中的极“左”思潮有所收敛,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如何对待和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次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第五次党代会召开, 研讨在北大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新的教学计划,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在大会上,翦伯赞以《巩固地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注:《北京大学》校刊第441期,1963年3月13日。)为题,做了重要发言。他明确指出,要贯彻执行好这次党代会提出的任务,“首先要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教学、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他对当时在教师和学生中忽视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批评,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战斗精神。
二、建立中国史学的新体系
中国旧的传统史学是在封建时代产生的,为当时的封建地主及其统治者所需要,其基本内容和体系,是王朝兴衰史或王朝的某些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史。此种史学可称之为封建史学。有人斥之为“帝王家谱”,过甚其词。民国初年,史学为之一变,“新史学”一词屡见于报端。这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学者从欧美、日本等国引进了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并做出了不少成绩。可是,其论著的主要内容仍为王朝兴衰史或政治事件史,略有文化思想杂于其间。其写作方法仍为史料排队。此种史学可称之为资产阶级史学。翦伯赞为之开拓、建立的新史学与此不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此新史学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中外关系,以及重要人物等等,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以求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进而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特点。翦伯赞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所发表的论文都属于此类。他的“西周封建论”即于此时提出,他的战友吕振羽、范文澜亦持此观点;郭沫若持“春秋封建论”,后改为“战国封建论”;侯外庐持“西汉封建论”。这三种观点,在表面上,分歧很大,可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是相同的。他们之间的分歧,正反映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与史料相结合问题上的审慎态度,使历史唯物主义在对中国的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尽可能做到具有中国特色。
翦伯赞的新史学体系最早体现在他于抗日战争时期所著《中国史纲》中。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夏代为原始社会,商代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周到战国时期,为封建领主制度,称“初期封建社会”;第二阶段从秦汉到清朝中英鸦片战争以前,为封建地主制度,又分为“中期封建社会”和“后期封建社会”两个小的阶段;鸦片战争之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翦伯赞为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史学体系,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资料之研究,以批判的、革命的态度进入了史学的深层。司马迁曾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注:《史记·三代世表·序》。)翦伯赞对这些远古文化遗产还是十分珍视的。他在审慎地利用古代文献的同时,又大胆地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及民俗学等资料,并使之互相印证、结合。他说,辨伪学的发展,“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金石学的发展,“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商代器物和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新石器文化之发现,“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猿人化石及旧石器文化之发现,“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上述情况都在翦著《中国史纲》第一卷中体现了出来。翦在该书《序》中说:“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
翦伯赞在建国以后,仍坚持“西周封建论”。在某些次要问题上,其名称或观点有所调整。如“前氏族社会”改称“原始群”,“夏代”归入“奴隶社会”,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不再用“中期”、“后期”分段等。体现这一情况的,除了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外,最系统完整的,是在60年代前期,由他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其论证方法当然更加科学完善。
三、大力倡导组织研究少数民族历史
翦伯赞大力倡导组织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固然与他出身于少族民族有关系,更主要的,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贯彻了这一主张,还坚决维护这一主张。如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他曾于1945年1月16日和17 日两天,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连载《我的氏姓,我的故乡》一文,其基本观点主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是中国国家社会的成员,他们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构成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文所讲为维吾尔族一支自今新疆内迁湖南的历史,其目的则是对蒋介石的那本反动小册子《中国之命运》所鼓吹的“大汉族主义”、“种族奴隶主义”及“封建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
建国以后,人们的生活安定,科研条件改善,翦伯赞又担任了一些与少数民族有关的重要职务,如中央民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民委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和条件倡导乃至组织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例如他在建国之初,参与筹建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在该校成立后,他兼任该校的《中国少数民族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当时说:“我们希望今后能够有计划地组织民族史资料编纂工作,一方面继续整理历史文献上的民族史资料,另一方面整理新近调查得来的民族史资料,同时也要整理和翻译各少数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写出来的资料。此外,还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收集地下埋藏的史料。只有大规模地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和编纂工作以后,才有依据对于民族史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从而才有可能写出各族的专史,并在专史的基础上写成一部包括各族历史在内的完整的中国通史。”(注:翦伯赞:《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第一编《序言》,中华书局1958年版。)翦老在世时,他亲自参加编成的《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之一、二两编(自《史记》至《隋书》中的“民族传记”和“外国传记”中的有关部分),于1958—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50年代参与策划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民族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编写工作。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这些工作即已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同时在全国16个省市展开,而且先后出版了多种图书。
翦伯赞曾多次到民族地区考察、访问,与许多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单位进行座谈或发表讲演,鼓励这些学校和单位要大力培养研究本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专门人才,有计划地加强对本地民族的社会历史研究。他的名文《内蒙访古》就是1961年7—9月在访问内蒙古之后所写的。所述曾参观考察过的古迹、文物,属于历史上的十余个北方民族,绵亘时间上下约两千余年。他还发表了《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历史文物》、《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文成公主说了话》等(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都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视和他对少数民族的热爱。
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除了存在着重视与不重视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此外,还要注意对民族政策的学习和贯彻。这些问题在50年代中后期的民族调查和“三套丛书”的编写中时有暴露,而且不断引起争论。翦伯赞所写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文,就是对上述部分问题的回答。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翦伯赞谈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注:《新建设》1962年第6期。)等文, 都是对一些有关问题进一步作出的阐述。
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第二章《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简明扼要地从正反两方面,多角度地回答了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在研究或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说:“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原则。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就要犯错误。但应用这种原则去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是用简单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者从那些不平等的关系中挑选一些类似平等的个别史实来证明这个原则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实现,更不是把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而是要揭露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这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实质。”又如说:“反对大汉族主义,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一个原则。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汉族在中国史上的主导作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另一个原则。但不能因此就说我国古代的各民族就没有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好像解放以前,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大家庭而不是一个民族大牢狱。”
四、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必须重视史料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当重视理论,只有资产阶级史学家才重视史料。翦伯赞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论调。他说:“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翦伯赞早期的著作就以资料翔实著称。其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论著,不仅充分利用了经、史、子、集四部中各种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还冲破旧的研究传统,充分利用了当时已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等。他这时的史料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于1945年5 月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的一次学术讲演中。讲题为《历史材料与历史科学》,内容分三部分:一、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这个讲演的大部分内容不久即公开发表。有关考古学部分在1954年结合新的考古发现改写发表(注:《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1954年5月22日《光明日报》。)。
翦伯赞较大规模地发动组织历史资料的搜集与编纂是在解放之后。1949年7月,中国历史学会在北平(今北京)成立,郭沫若任会长, 范文澜任副会长,翦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他们共同发起组织编辑巨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约有两千多万字,为68册。翦伯赞主编了其中的《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两个专题,共8册。
翦伯赞为在我国长期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搜集、发掘、整理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还倡议、创办了两个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基地,一是1952年创办的“考古专业”,设在北大历史系;一是1959年创办的“古典文献专业”,设在北大中文系。北大考古专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里的第一个考古专业。为筹建此专业,他煞费苦心,任劳任怨,总的说来,还算顺利。而创办古典文献专业的情况则大大不同。此专业是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时, 决定创办的,并设在北大,筹备工作由齐燕铭、翦伯赞、吴晗、金灿然、魏建功5人负责。可也就在这时, 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提出了一个所谓“厚今薄古”的口号来。由于他的政治地位特殊,加上媒体的大力宣传,一时人们视此口号为党的新的文化方针,这无异于给古典文献专业的筹建工作打入一个楔子。可是翦伯赞等人还是按照计划将此专业建成,并定于1959年夏公开招生。
为回答“厚今薄古”论者对设置古典文献专业的责难,翦伯赞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于此专业招生之际,即在1959 年7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一文,开宗明义说:
“北京大学今年新设了一个专业,名曰‘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材,主要的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
文章讲了三大问题:第一是“整理古典文献和厚今薄古的方针有没有矛盾”,第二是“整理古典文献是不是一种没有思想性的纯技术工作”,第三是“整理古典文献,算不算科学研究工作”。翦伯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在文章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现在正在招收学生,我希望不久就可以看到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整理古典文献的队伍成长起来。”(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61年,他为批判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的代表性口号“理论挂帅”及“以论带史”时,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第八章《理论、史料与文章》中说:
“理论挂帅,不是只要理论不要史料,不是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只是说要用这样的原理原则分析具体的历史。”
“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作出理论的概括。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
“理论挂帅,也不是先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使理论与史料分离;而是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让读者自己从史实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论。”
当然,翦伯赞的这些意见都为当时热衷于制造极“左”思潮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陈伯达之流视为叛逆。后来翦伯赞遭到批判,并在“文革”中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罪名”被打倒,乃至致死,这也有其必然性。
1998年4月14日,北京大学为配合百年校庆, 举办了盛大的“翦伯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教授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翦先生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前期,坚决地批判极“左”思潮,“是一次有代表性的双重意义的抗争。一是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反对破坏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抗争;二是政治上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的错误路线的抗争。它表面上只是个人或少数人支持的行动,实际上它反映的是相当范围众多人的认识、愿望和要求。从今天来看,它的政治意义远重于思想理论意义。”(注:刘大年:《历史学的变迁》。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我认为刘大年教授的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是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