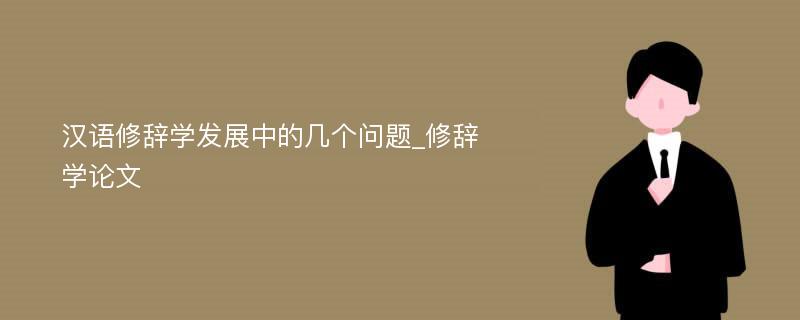
汉语修辞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汉语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一百年来的中国修辞学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马鞍形的道路。30年代,以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为代表,形成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次繁荣。90年代以来,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二次高潮,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成熟时期,是中国修辞学走向世界的开始。
现在,21世纪就要来到了,对于汉语修辞学的跨世纪的发展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历史地宏观地思考一些问题是越来越迫切了。发展的需要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本着对学术负责的精神,对问题不对人,不以感情用事,坦诚地交换意见。本着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要引起更多的人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中国修辞学落后论
1.1 正确地估计现状,是更好地前进的一个必要条件。正确地评估80年代的中国修辞学,是开创90年代修辞学所必须的。正确地评估一百年来的中国修辞学,是开创下一个世纪的中国修辞大业所必须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大家重视。
张静在《总结成绩,开创未来,把修辞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中国修辞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会开幕词》中说:
几十年来中国修辞学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创新,但严格说来还没有超出《修辞学发凡》的格局,应该说中国修辞学这个学科长期处在落后状态中。修辞理论研究多年来还没有突破,诸如什么是修辞,修辞的对象和范围,修辞学的方法论之类最基本的问题,大家一直没有形成共识。我们的修辞研究更是远远落后于语言实践的。[1]
张静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是很值得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
1.2 第一,中国修辞学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吗?
我们认为,是不能够这样看待问题的。
中国古典修辞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世界修辞学中占据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容怀疑的。郑奠和谭荃基编辑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和郑子子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就能够证明中国修辞学并不是长期处在落后的状态之中的!
这一百年来的中国修辞学同样是成功的。二三十年代里,修辞学的成绩与语言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决不能认为是落后的。80年代里,中国修辞学同样是成功的,同其他语言学科相比也决不可以说是落后的。
第二,到了1990年,中国修辞学是“还没有超出《修辞学发凡》的格局”么?这是我们很难同意的,这不符合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修辞学的实际情况。
陆俭明在一些场合和文章中一再说80年代的中国修辞学还没有超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的那一套,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只研究语法而不研究修辞,对于修辞学难免有些儿隔膜。
张静作为中国修辞学会的领导人,在这个学会成立10周年大会的开幕词中这样说,可就太不适当了。因为如果对现状估计失误,那么就很难进行正确的导向。
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在修辞学理论方面真的并“没有突破”么?我们认为,并不是这么回事情。其实,是突破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了重大突破。在“诸如什么是修辞,修辞的对象和范围,修辞学的方法论之类最基本的问题”方面都是如此。应当公正地说,80年代的中国修辞学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中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是整个中国修辞学中的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对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有所继承,但是却是同《发凡》全然不同的,这是《发凡》所无法概括的。但是,中国人是比较厚古而薄今的。所以,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成功很难得到当代同行学者的公认,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修辞理论研究多年来还没有突破,诸如什么是修辞,修辞的对象和范围,修辞学的方法论之类最基本的问题,大家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应当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取得了某些共识的。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一致同意,因为这是学术问题。其实,在学术问题上,百分之百的一致可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并不是学术进步和繁荣的表现,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反之,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也决不意味着我们的修辞学就是落后的,还没有重大突破的。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一些重大的突破,才一时难以形成共识的吧?
1.3 中国修辞学落后论,事实上是中国修辞学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其实是说的落后于欧美!——的修辞学(其实是说的落后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修辞学)!而且是,有人说,中国修辞学同西方修辞学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这是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事实上,中国古典修辞学并不落后于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修辞学,自有自己的特色。现代中国修辞学同西方修辞学的所谓差距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样的大,更不是越来越大了,而是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及发展的道路,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所取得的某些进展也是世界性的。
1.4 张静批评说:“我们的修辞研究更是远远落后于语言实践的。”如果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那么,理论既然是实践的反映,就必然是跟在实践的后面;修辞研究落后于语言实践也就是正常的了,可以理解的了,不可以加以指责的。
二、政治和学术的关系
2.1 政治和学术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中国修辞学的进一步继续发展中是不可回避的。
多年来,极左思潮阻碍了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教训是沉痛的。在极左派的手中,政治和学术的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正是一根大棍子,是阻碍中国学术发展和繁荣的一根大棍子![2]
极左思潮在修辞学界也是有所表现的。
2.2 张静在《总结成绩,开创未来,把修辞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中国修辞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会开幕词》中说:
最后我讲点政治和政治方向问题。学会是搞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组织,但也有政治和方向问题。我认为“政治”和“学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必须区别对待。但我也认为政治和学术是密切不可分的,你那个学术离开了政治、政治方向,将会一文不值。[3]
在这样的场合,张静的这样一番话,很有一点儿把政治当作棍子来打击别人的味道。你看,你听:“你那个学术离开了政治、政治方向,将会一文不值。”作为中国修辞学会的一个负责人,代表学会领导阶层作导向性的报告,是应当占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人们可以要求张静:请你举出一个人——一个中国的修辞学者,一篇修辞学理论,一本修辞学著作,来证明你的指责吧!“你那个学术离开了政治、政治方向,于是就一文不值”了!
张静在中国修辞学会成立10周年大会上大谈政治和学术的时候,按理说,应当具体地列举中国修辞学界所存在着的背离了政治大方向的具体表现,并且提出解决这种现象的办法。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打算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居高临下地说说而已!或者说,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也不需要、也不能去谈什么解决的办法吧?
我并不否认政治和学术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但是反对把政治庸俗化,作为打击别人的棍子,这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2.3 这使得我们想起80年代初关于修辞学的阶级性的争论。
在1982年出版的张志公主编的电大《现代汉语》(下册P.8—10)中,张志公主张修辞具有阶级性,得到了天津甘玉龙的大力支持。当时的《文摘报》还摘要了他的高见。他的意见是,张志公,高举修辞有阶级性的大旗,指引中国修辞学向前进;而王希杰则主张修辞没有阶级性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起这个阶级性的大问题了。
在那个时候,大谈阶级性,其实是极左的流毒。多少有一点“拉大旗作虎皮”的意味。其实,主张者自己也未必就真的相信修辞有阶级性的,他自己也并不打算去搞一个具有阶级性的修辞学的,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其实,张志公、田小琳等鼓吹修辞有阶级性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没有认真研究过修辞的阶级性问题,在那以后也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研究。
其实,修辞和阶级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不应当是一个禁区。同样,语言和言语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也同样是很值得研究的呢。问题是,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也同样应当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具体地说,修辞有没有阶级性同修辞学有没有阶级性,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2.4 当张志公提出修辞学有阶级性的时候,我们想:如果修辞学真的有阶级性就应当有人写出无产阶级的修辞学,也有人写出资产阶级的修辞学。可是没有。
最近重读倪海曙的《初级修辞讲话》[4],似乎有那么一点儿味道。虽然从定义方面看并没有主张修辞有阶级性:
写文章的语言要特别讲究达意传神。
“达意”使人明白得透;“传神”使人感动得深。
因此,写文章的语言需要加工。
这种加工,有个专门名词叫作“修辞”。
但是,作者行文显然是自觉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例如:
“这些都不是写文章的好的语言,都不是我们劳动人民写文章应该采用的语言。”
“我们劳动人民写文章,应该……”
“我们劳动人民写的文章,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
倪海曙的《初级修辞讲话》,在现在的人们看来,是多少有些儿奇怪的:难道非劳动人民就不修辞了么?你讲修辞就讲修辞吧,大讲那许多政治口号干嘛呢?
修辞学的规律规则当然是没有阶级性的,对社会的各个阶级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每个阶级都是要运用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来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吧?再,修辞规律规则虽然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描述这规律规则的人却是具有阶级性的,那么任何一本修辞学著作是不是多少有那么一点阶级的味儿呢?在《修辞学发凡》,陈望道正是自觉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呐喊助威的。《修辞学发凡》所总结出的修辞规律规则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修辞学发凡》这样一本著作就没有一定的思想倾向。
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不管是哪一个作者,在写作修辞著作的时候,多多少少是站在某一个阶级的立场上的,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连物理学家在观察宇宙的时候,在研究物理现象的时候,也不能排除主体的影响,一个修辞学家在构建自己的修辞学理论大厦的时候要完全地排除主体,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就我自己而言,我主张修辞和修辞学都没有阶级性,但是决不排除阶级对修辞和修辞学的影响。虽然我没有像倪海曙那开口闭口“我们劳动人民”,但是,在我的修辞学论著中,明显地表现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修辞学论著是为千百万真正的中国人服务的,为一个崇高的目的服务的,决不为阴谋家、两面三刀者等服务的。这一点,有时候,甚至是非常自觉的。因此,我决不否定倪海曙的这一写法。甚至认为,在今天是很需要这样的修辞著作的,为普通工人,普通农民而写作的修辞学,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工人”或“我们农民”的修辞学著作。而且,我们不能说,这就是没有科学价值的,只是修辞术而已。
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修辞和修辞学都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我认为,修辞和阶级、修辞学和阶级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也是应当研究的,甚至是必须研究的。问题是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态度,决不把“阶级性”当作大辊子去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三、思想水平和修辞技巧
3.1 思想和语言技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学界是有人把修辞问题同思想水平混为一谈的。例如,有人强调对于修辞学,应当“从阶级观点来认识这门学科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有人则认为,修辞“归根结蒂,取决于作者的立场、世界观及其政治水平。”我在《修辞的定义及其他》中明确地说:修辞问题“‘归根结蒂’,这还是一个语言技巧问题。”
3.2 李晋荃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修辞的要求吗?》一文是新时期中国修辞学中的一篇重要的文献。作者说:
修辞必须“准确地反映客观实践”吗?诚然,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精妙言语是大量的,但是,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极为普遍。骆宾王的《讨武(日月空)檄》列数武则天的罪状,有许多是莫须有的,但语言生动有力,修辞水平很高。庄周、孟柯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言论有不少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修辞水平不能低估,他们以雄辩著称于世,被誉为大散文家。在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中,许多骗子专门说假话,但照样能滔滔不绝,精采动人。诸如此类,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真是平常又平常。这毫不足怪。因为,思想才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语言只是表达人的思想,并不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不论人的认识正确与否,运用语言的能力并不随之而变化。“准确地反映客观实践”的要求,只适用于思想内容,不适用于语言的修辞。[5]
这段话中提出了不少的问题,是很值得认真地再思索一番的。
3.3 这段话是很值得讨论的。
第一,“骆宾王的《讨武(日月空)檄》列数武则天的罪状,有许多是莫须有的,但语言生动有力,修辞水平很高。庄周、孟柯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言论有不少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修辞水平不能低估,他们以雄辩著称于世,被誉为大散文家。”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个是,对于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修辞本应当是一视同仁的。不应当、不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我们并不能够认为“唯物主义者就一定是修辞水平高的,而唯心主义者则一定就是修辞水平低的”。其实,唯心论者可能修辞水平高,而唯物论者也有可能是修辞水平低的。但是,不能从这里就得出一条结论:“‘准确地反映客观实践’的要求,只适用于思想内容,不适用于语言的修辞。”另一个是,当一个人的言论是不符合事实的时候,即使他的言语是生动活泼有力的,我们能够赞美这一修辞技巧吗?如果修辞可以完全不管内容的正确与否,只要言语生动活泼有力,“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话语,也是漂亮的修辞,那么这种修辞学的社会地位就很值得怀疑了!
第二,“在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中,许多骗子专门说假话,但照样能滔滔不绝,精采动人。诸如此类,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真是平常又平常。”这也是修辞吗?如果承认这也是修辞,也就太可怕了!英国哲学家洛克说:“我们必须承认,修辞学的一切技巧(秩序和明晰除外),和演说术中所发明的一切的技巧的迂回的文字用法,都只能暗示错误的观念,都只能够动人的感情,都只能够迷惑人的判断,因此,它们完全是一套欺骗。”[6]卡西欧说:“修辞艺术在诡辩派的手中变为最危险的武器。它变为一切哲学和一切纯正道德的敌人。”[7]PeterDlxon在《论修辞》第五章“修辞学的摒弃”中写道:
从牛津英文词典中,修辞学一词列有下述一意义:修辞学是具有劝服性的语言或文字,因此(常就其劣义说)修辞学的语言是人工化的,虚饰的。从字典上所引用的说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至少早在17世纪初期,修辞学一语的使用,便已具有贬抑的意味了。试看1615年理查(Ricdard Brathwait)鄙视当时的打油诗人,嘲笑他们的作品:“了无内容,只不过是一篇漂亮而俗气的修辞文字罢了。”1642年富勒(Thomas Fullev)也提到某些人“诅咒修辞学原是谎言之母。”……攻击修辞学为谎言之母的论调是继承苏格拉底的:“修辞学歪曲真理,障蔽真理。”[8]
在我们看来,“在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中,许多骗子专门说假话,但照样能滔滔不绝,精彩动人。诸如此类,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真是平常又平常。”都不是修辞,而是反修辞,伪修辞,是必须排除在修辞学之外的。
第三,“修辞必须‘准确地反映客观实践’吗?诚然,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精妙言语是大量的,但是,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极为普遍。”这话的意思是: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精妙言语是大量的,但是,不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精妙言语也是极为普遍的。这后一种情况,当然是存在着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准确地反映客观实践’的要求,只适用于思想内容,不适用于语言的修辞”。在我们现在看来,修辞是必须从“准确地反映客观实践”开始的,必须把“准确地反映客观实践”当做修辞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而不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精妙言语的出现和存在则是受到另外的原则所制约的。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不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话语就不是精美的言语,是不可能取得好的表达效果的。
钱伟长在中国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他给刘焕辉的《交际语言学导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一书所作的序言,首先大谈索绪尔和《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崇高的地位。然后写道:
刘焕辉教授的《交际语言学导论》,在充分肯定索绪尔的历史功绩基础上,敢于冲破现有“规范”,避开语言静态所轻车熟路,另劈蹊径,对现代汉语动态结构系统展开了全面的分析、描写,证明语言的运动的状态并不像索绪尔说的那样“不知道怎样理出它的同一”。就此而论,“导论”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本世纪末语言学界具有某种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其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是值得称道的。我以为,索绪尔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结束了语言研究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在于他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焕辉同志的“导论”值得称道之处,也在于此。
钱伟长并不是语言学家。我想,他是不可能有许多时间来阅读语言学论著的吧?现在他对读者说:
刘焕辉=索绪尔 刘焕辉《交际语言学导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我想,只要是还有些语言学常识的人,大概都不会同意的吧?
钱伟长的这篇序言写得很有文采,可是,如此地言过其实,甚至是没有根据的话,谁能说是成功的修辞呢?
第四,“思想才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语言只是表达人的思想,并不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说语言并不直接反映客观事物,这值得讨论,值得研究。
第五,语言同思想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语言同思想并不是一会事情。但是,这可能并不能够成为修辞只关语言的形式方面,而不问话语的内容吧?这个问题也很值得研究。
3.4 这是我自己在1980年很支持的一段话,后来长期也认为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却发现这段话是很值得讨论,这里有许多层关系,这些关系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更不用说取得共识了。我很坦率地说:这段话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我现在是反而糊涂了,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说才是最正确的。因此,我再一次地深深地感到,修辞学的发展还得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因为我们的头脑里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正是修辞学进一步发展繁荣的障碍。
收稿日期 1996-07-14
注释:
[1]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6集)第6页,第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2]参看王希杰《三十年来我国语言学中极左思潮》,《语言学论文集》,新疆大学编辑出版,1979年
[3]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6集)第6页,第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4]倪海曙《初级修辞讲话》,《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5]《语法修辞论集》第114——115页,语文出版社1993年
[6]《人类理解新论》(下册)第49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7]《语言和神话》第128页,三联书店1988年
[8]《论修辞》第72页,台湾黎明书店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