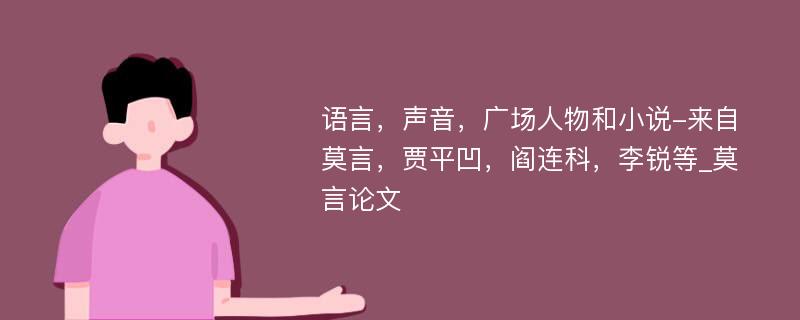
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块字论文,开去论文,声音论文,语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郜元宝:我们这次打算从汉语言文字的角度出发,谈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某些问题。 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现当代文学,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种学术与批评的兴趣。过去,也 经常有人谈到所谓“文学语言”,但那只是把语言当作文学的工具,当作从属于文学的 一个次要的问题,而没有认识到语言文字对文学的根本性决定与制约,因此也很难从根 本上思考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最近看了莫言的《檀香刑》,启发很大。我不太喜欢这部 作品,但我认为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讨论中国文学与汉语言文字的关系的一个相当合 适的话题。联系到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其他几位当代作家创作中出现的大致相似的 语言意识,我觉得有必要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加以认真的审视。
葛红兵:汉文学语言在20世纪变化很大,主要是“启蒙化”了。但是,看了莫言的《 檀香刑》,我非常惊讶,因为莫言在尝试反思这种启蒙语言,这在20世纪以来的汉文学 中非常少见。他采用的是一种“前启蒙”的语言,没有受到“五四”启蒙话语的熏染, 来自民间的、狂放的、暴烈的、血腥的、笑谑的、欢腾的语言。他模仿的对象是“猫戏 ”,是民间戏曲。莫言的这种“前启蒙”语言把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改造后受到遮蔽 的声音再次发掘出来了,比如赵甲这个人物的声音,放在鲁迅笔下可能就会变成《药》 里面的康大叔或是《阿Q正传》里的阿贵,变成受批判、谴责的对象,而不是发声对象 。这种尝试贾平凹也做过,他也曾尝试回到前“五四”去,但他效仿的对象是《金瓶梅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人”语言,一种浸染了古代文人气的语言,和莫言的 《檀香刑》不同,后者更恣肆、更狂放、更自由。
郜元宝:把莫言和贾平凹联系起来谈中国文学语言的变化,的确很重要。我记得莫言 刚出道时的语言和现在大不一样,非常强调个人感觉。不过,当时许多批评家都是把语 言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来认识,不能从根本上看到语言的问题。莫言、贾平凹、李锐包括 王蒙这些作家使我意识到应该思考文学和语言的关系这个问题,而不是把语言纳入文学 中去思考,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把文学纳入语言中去思考。我们的文学的基础是语言 ,但我们究竟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我们文学的基础?“五四”启蒙话语对中国语言进行 改造,以改造过的汉语作为我们新文学的基础,这样就演化出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现在 许多作家对于自身所处的这个历史感到不满,首先希望在语言上有所突破,比如莫言现 在就开始自我检讨了,他认为自己最初的语言并不好,书卷气太浓了,为了追求一种“ 民间气息”、“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他宁可作出“牺牲”,也要放弃原来的语言, 而制造另外一种适合在广场上高声朗诵的语言,这种语言应该具有“流畅、浅显、夸张 、华丽的叙事效果”。你认为这是对“前启蒙”时代语言的一种回归,但你所说的回归 这种“前启蒙”话语,也就是回到“五四”以前的文学语言,难道是可能的吗?莫言、 贾平凹等人求学和创作之始,直接面对的都是“五四”之后文学/语言的现实,他们真 的能够跨过“五四”话语而回到“五四”前的话语,即回到处于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的 民间文人的白话与说唱传统中去吗?当然,这个问题背后还潜藏着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 题,那就是包括莫言在内的当代中国作家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究竟怎样?在语言上 ,“五四”文学革命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遗产,以至于使他们对这份遗产感到不 满而竭力要摆脱它?
一、语言与语言的传统:前启蒙语言是否可能复归?
葛红兵: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观察到“五四”作家对文学语言的革命不是从修辞 手段的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从整体的文学精神的角度上来讲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 、郁达夫这些作家都是把自己的精神母亲放在了西方,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谈到了语 言的改造——他们要到西方去找一种新的语言。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觉,以为“五四”文 学是接续了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传统,但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的。这种错觉是怎样造成 的呢?周作人、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以后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专著论证文学革 命的合法性,硬是给自己找了个中国“古已有之”的理由。但实际的情形是“五四”时 期周作人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民谣基本上是反对的,比如他把《西游记》看作是神魔 小说,对民谣中的文学成分他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所以说“五四”作家的启蒙语言是从 西方借鉴的。这从他们语式的欧化上可以看出来,这种语言上的欧化与精神上的欧化即 启蒙化完全一致。比如说鲁迅对阿Q的批评,在启蒙话语中,阿Q是没有地位的,我们从 阿Q身上看到的是愚昧、自欺、受骗等国民性的缺点。这种遮蔽的东西在莫言的《檀香 刑》里被颠覆了过来。比如说赵甲这个人物,变成了一个充满敬业精神的,无论怎样都 要活下去的,充满仪式感的人物。他身上的这种韧性是来自民间的力量。我认为这一点 与莫言对语言体式的选择有关。你刚才说中国当代作家跨越20世纪中国启蒙话语的障碍 很难,但不排除莫言这个独立的个人能部分地做到,就像贾平凹当初到中国古代小说中 去寻找语言一样。
郜元宝:我注意到你和其他一些朋友对《檀香刑》、《酒国》等小说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评价莫言的早期作品像《欢乐》、《大风》、《石磨》、《透 明的红萝卜》等的。那时候的莫言从直接的生存体验出发,似乎随意抓取一些天才性的 语言纵情挥洒。一般认为(连莫言自己也认为)这是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结果,但在我看 来,这种比较文学的所谓影响研究,至少疏忽了莫言开始文学写作时所依靠的包含了“ 五四”启蒙话语、与启蒙话语同时存在的民间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彼此混合的一个语言的 背景。这个语言的背景虽然没有鲜明的旗帜,标志它具体属于哪一种语言传统,但正因 为如此,莫言在语言的选择上才显得十分自由,从而更加有可能贴近他的文学创作爆发 期的丰富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近来的创作相对来说是一种退步,即从对于一 种混合的语言背景的依靠撤退到对于一种旗帜鲜明的所谓民间语言的单一传统的依靠。 在这点上我与你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莫言是在刻意依赖一种非西方(非欧化)非启蒙的语 言,因此很难再像前期创作那样自由地释放自己的欢乐和狂放的体验。我觉得,莫言所 谓具有“民间气息”和“纯粹中国风格”的语言,对作家来说确实是一种诱惑,因为它 似乎未被开垦过,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股潜 流,就是中国的通俗文学。现在有许多中国文学的研究者都在大声疾呼要研究中国的通 俗文学,似乎通俗文学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就会永远迷失在启蒙话语的一元论模式 中。我认为应谨慎看待这个问题。对莫言来说,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讨论他所选择的语言 传统本身如何如何,而是应该仔细分析民间语言资源的引入对作家个人生存体验带来的 实际影响。莫言所引入的传统语言如说唱文学形式,究竟是更加激发了他的创造力,还 是反而因此遮蔽了他自然、真诚而丰富的感觉与想象?
葛红兵:莫言的语言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像苏童一样以个人的才情轰动文坛,这对 当时王蒙、梁晓声等作家普遍使用的新启蒙语言也是有反拨作用的。但一个作家不能永 远依赖个人才情来写作。莫言今天的这种倾向是把个人才情与广泛的民族根基结合起来 的一种尝试,在这种语言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个人的力量,而且看到了民族的力量。要做 到这点很困难,并不是戏仿一个西方作家、流派的语言,或者学习一种所谓的民间“精 神”就能做到的,他需要很强的个人力量。20世纪中国语言经历了“五四”启蒙语言、 文革语言、新时期新启蒙语言等一系列巨变,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随着语言走,被语 言主宰,而不是相反。例如文革意识形态语言,那种暴力的、战争倾向的文革语言对我 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扬州作家申维的《红旗大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在这部 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语言的普遍体式,可以看到“放哨”、“忆苦思甜饭”、“打 击一小撮”、“血泪仇”、“批斗会”、“反动”、“除四害”、“深挖洞广积粮”、 “一打三反”、“阶级斗争是纲”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语言怎样影响了60年代出生 的作家。申维是在有意地清理自己的童年记忆,有意地对这些语言进行再现,对这种语 言进行还原、复归、呈现。当然这部小说也让我们看到了文革语言中的分裂现象,在意 识形态语言的宏大背景中,主人公的母亲还在朗诵“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一种传统的意象化的、具有文人趣味的、人情味的语言……的确,任何一个时代 其主导语言中都存在分裂、矛盾的因素,但是那种主导性的语言依然是坚不可摧的,它 主宰了我们的文学。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文学家如何超越 这种主宰,他需要巨大的个人才情,同时单单只有个人才情又是不够的。
郜元宝:我们今天的谈话已经触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语言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 。中国语言,具体来说,就是所谓“现代汉语”,乃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我倾向于 把它想象为一种吸收了多种因素、无法预计其未来发展的变动不居的活的本体。我们两 个在理论上并无分歧,也就是说我们都赞同作家在文学上要想有更深的发掘,更大的突 破,就必须超越所谓纯粹个人的才气和个性,回归到一种传统,借助传统的力量说出自
己的话。但作家要建立与传统的关系,并不等于简单地回到具体的某一种传统。不错, 闻一多曾经批评郭沫若等作家缺乏传统,而只知道撇开传统说自己的话,他认为那是一 种浅薄的“伪浪漫派”。但反过来,要克服这种“伪浪漫派”,是否就应该毫无批判地 回到某个一度被忽略的传统?比如,像贾平凹那样回到传统文人小说的话语传统,或者 像莫言那样回到“猫腔”?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总以为,所谓回到传统,必须 警惕传统对作家的消化和诱惑。传统有两面性,一方面使人有力量,一方面又会把人淹 没。就贾平凹和莫言来说,他们从“五四”以来混合的也是日益收缩的语言背景中脱出 来,转身回到一个具体的语言传统中去。在这转变当中,传统对他们的淹没,显然要超 过他们自己的生命力从传统中的再生。不妨再拿另外两个作家为例,说明这个问题。40 年代末以后占据统治地位的“革命话语”以及“文革”中囊括一切的“政治语言”,无 疑是许多当代中国作家深入骨髓的语言传统。那么,如何面对这个语言传统?王蒙和阎 连科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模式。王蒙确实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大量使用他所“熟悉”的 革命话语和政治术语,但在这过程中,他并不是单一地显示这种语言本身的历史信息, 而更多地倒是要显示处在这种语言洪流中个人的扭曲和被伤害、被迫害的那股子可怜劲 儿。所以在强势的语言暴力之中,我们还能够听到一点几乎没有个人语言的个人的呜咽 。阎连科最近的《坚硬如水》则不同,表面上,他是想通过对铺天盖地的文革语言的频 繁使用,再现那个时代的个人生存的真实。而实际效果,却仅仅是“文革语言”的大展 览,个人和时代语言的关系,被简单化处理了。
“五四”时期,在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中国文学几乎一夜间挣脱了与 母语的天然联系,落入瞿秋白所批评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不人不鬼的”尴尬境地 ,造成新文学语言大面积的粗糙。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苦涩的遗产。然而,也必须看到 ,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破碎局面中,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语言传统的普遍反抗中,我们产生 了鲁迅这样的作家。对于他和语言传统的关系,我们不能像对其他作家那样进行简单的 理解。比如,他对文言文有铭心刻骨的仇恨,而实际创作中与文言文的关系又非常紧密 ,他很好的吸收了口语,但决不像胡适之那样过分推崇讲话风格对写作的绝对统治,他 也不满于青年作家的生造字句,但一直更加坚定地为“欧化语体”辨护:他是要在多元 的似乎无路可走的语言困境中走出一条语言的道路。其中既包含对传统的批判,又包含 了对传统的新的认同,同时包含了对当时所有的各种语言资源巧妙的改造。我们无法用 “回归”、“依靠”这样的概念来定位他与任何一种传统的关系,只能说他与纷乱的中 国现代传统有一种鲁迅式的关系。在讨论当代作家与汉语言文字传统的关系时,我总是 忘不了鲁迅。我以为他至今仍然不失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最大的提醒,即提醒我们 不要简单地面对传统,尤其不要自以为发现了某一件传统的宝贝而沾沾自喜。否则,我 们的格局将日见其小。
二、无声与有声
葛红兵:汉语小说写作对世界文学究竟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定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贡 献呢?以前我们说人家不给我们诺贝尔文学奖是歧视我们,但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是否 与诺贝尔文学奖有距离?汉语写作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哪里?就文学发展而言,20世 纪中国一直存在两条思路:一条是欧化思路,一条是民族化思路,如20、30年代的沈伊 默、俞平伯,40年代的赵树理,现在的金庸等等。但除了鲁迅,大多数人的尝试都不成 功。其原因与汉字的自身特点有关。其一,汉字是表意的语言,大多数作家都忽视了汉 语的意象性。其二,汉字是单音节性的语言。就第一点来说,表意性的语言并不适合西 方化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式的文学作品,像巴尔扎克的硬描述、硬叙述的文学作品,用汉 语翻译出来就显得索然无味。汉语小说有自己的意象主义传统,一种类似庄子风格的传 统。这种语言的魔力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就第二点而言,我看到《檀 香刑》很欣喜,因为它使用的是有声音的语言,这部小说能发出适合汉语音韵节奏的声 音,具有音响效果。
20世纪中国小说存在着一种悖论,这个悖论在“五四”时期就露出苗头了。一方面它 要用白话,另一方面它又向着西方式启蒙文学的案头化方向发展:它要向白话前进,而 实际走向却离口语越来越远,成了一种无声的语言,“案头的”文学。简单地说20世纪 中国文学的语言大多是一种“书面白话语”或“白话书面语”,鲁迅的语言就是代表, 实际上鲁迅的语言是读不出来的,只能看的语言。而《檀香刑》是充满了声音的,如媚 娘的浪语,钱丁的酸语、赵甲的狂言等等,它基于中国说唱艺术语言、戏曲艺术语言, 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乃至仇恨,这种声音不同于西方式的 阳春白雪的描述的、叙述的(具有逻格斯效应的)声音,它是猫戏式的、顺口溜的、犀利 的、高亢的、昂扬的、悲凉的、唱腔式的声音。这种韵律来自汉语自身,它不是莫言本 人的,它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的生存历史中逐渐找到的,它在民间戏曲艺术中隐现着, 莫言发现了它。
郜元宝:我一直在考虑文字与声音的关系这个问题。最近在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这门课上,我专门谈到了“字本位”和“音本位 ”的语言观念,如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个问题。看了《檀香 刑》的“后记”,更加迫切地意识到声音和文字的关系,不仅是语言学上一个难解的问 题,也是文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声音吗?那么文字的地位又 如何界定?文字只是记录作为语言的本质的声音的 工具吗?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我们难道可以想象离开文字的所谓“文学语言吗”?莫言很 得意的是,《檀香刑》主要以“声音”为主。然而,究竟什么是文学上的声音?它是否 等于口语的声音即人们说话的声音?我认为未必这样。中国几千年文学所表现的中国, 在鲁迅看来是“无声的中国”。他所说的“无声”之“声”是有特指的,在他看来,文 学上的声音首先是生命的表达,由于中国传统文学简单粗暴地把自然说话的声音改造成 与文字的一定结构相符的人为的声音,用文人的吟咏遮蔽了百姓说话的声音,这就是鲁 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
像莫言、贾平凹、李锐这些作家是否能使文学语言摆脱这种文人的传统和字面的传统 ,彻底回归到一种自然的声音,从而使文学更能表现中国人的生命呐喊呢?我认为这里 首先应该区别两种声音:文学家制造的声音和人们生活中自然的声音。如果说文人的声 音对人们自然的发声构成了一种遮蔽,那么我怀疑莫言们所推崇的“声音”,也会造成 对中国人生存表达的新的遮蔽?如此用一种声音遮蔽另一种声音,恰恰是德里达分析的 一个有趣的问题。德里达认为,在没有明显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非欧洲世界,比如在东 方世界,也很有可能存在着“声音中心主义”,即通过东方思维的理解赋予声音以特权 。我觉得莫言、李锐就是如此。我记得李锐曾经很自豪地说,他已经摆脱了白话文的书 卷气,而进入了身边的百姓的口语的汪洋大海;他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就是摒弃 一切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完全让人物——农民——自己说话。但是我想指出,这其实 并不是莫言、李锐的发明,“五四”文学革命对于口语在文学语言乃至整个民族语言中 霸权地位的强调,早就是我们现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了。口语不断侵蚀着文字, 使文字降低到奴从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在40 年代,周扬就曾经根据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指出:中国文学在人物语言上有所进步,而叙 述语言仍然是知识分子式的,因此应该对叙述语言来一场“打扫”。这种文学理想是把 文学建立在声音层面上的,把文字视为一种记录工具即声音的载体。胡适就曾经说过, 作文就是用文字记录说话。他也把文字降到从属地位,在对文字进行善恶的评判之后, 使文字驯服于声音。而一旦如此,文字就会反过来报复文学,报复声音,使之成为新的 案头文学,新的无声的“死语言”。在这种情况下面,声音也不会从工具式的文字中透 视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充分发掘了文字功能的古代文人的小说和古典的诗文 词曲都是可以吟咏的,同样充分发掘了文字功能的鲁迅的小说和散文也是可以吟咏的, 而贬低文字的功能、单纯依靠声音的莫言们的小说,反而没有真正创造出文学的声音, 反而不能吟咏。我曾经听过莫言在《收获》杂志举办的作家朗诵会上朗诵他自己以为非 常适合朗诵的作品,结果什么也没有听到。
葛红兵:理论上,“五四”文学的确存在你所说的这种错觉,即言语对文字有革命性 的作用,文字是腐朽的,声音是革命的,文字是衰颓的,声音是活跃的,只有让文字臣 服于声音,我们的文学革命才能完成。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到的,“五四”作家 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个理论的层面实践自己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在反文言文的口号下,走 的并不是声音中心主义的路子,相反是文字中心主义的路子,鲁迅就是个例证。鲁迅并 没有接受中国古代话本白话小说的传统,没有接受话本小说的那种发声方式,而是走向 了西方的人文小说传统,这种传统是基于把文字看成是小说的中心,讲究看的效果,而 不是听的效果之上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谈文学的有声和无声还只是触及了皮毛,真 正的声音应当是内在生命的呐喊,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实际上,我所说的莫言向声音 的回归并不简单地指他的语言是可以吟、可以唱,唱腔式的,有语调可以真实发声的, 而是指莫言在文学发声学上拥有了另一种立场。如果说,启蒙作家的发声方式是西方式 的,是理性的、大写的“人”的发声方式,是一种统一于启蒙主义意识的单一的声音, 那么我们可以说《檀香刑》发出的是另一种声音,一种由杀戮者发声效果、受刑者的发 声效果、狂浪者的发声效果、观众的发声效果等等揉合而成的综合的多声部的声音,这 种发声在启蒙话语的理性主义思路中是受到遮蔽的,它包含了许多非理性的成分,包含 了把生活看成表演的仪式主义的成分,死的欢乐、施虐的快感、受虐的痛楚、表演的雄 心等等参杂的形式感的成分,即使无价值也要把生命延续下去的成分,这些东西可能愚 昧却是任性的、狂欢的、坚韧的,它猫戏地在民间戏剧中藏身,但也正是这种声音使忍
受了内忧外患、压抑的惨痛、饥馑的折磨、专制的苦难的民族得以延续下来。但恰恰在 20世纪以后,这种声音在小说中几乎绝迹,20世纪中国多的是赵树理式的发声,是士大 夫气的发声,是文人式的发声。在这个角度上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并没有延续“五四” 文学文人的理性的做出来的发声效果,而是回到民间的唱腔式的语言中去。
郜元宝:也许我们今天思考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还为时过早,因为清理中国文学的语言 传统的确有很多困难,这也不是单纯依靠西方哲学能够解释的,它也许需要哲学以外的 东西来解释,比如说神学的传统。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什么是声音这个问题,仍然值 得我们一再地进行追问。我一直认为文学中的声音并不等于人们特别是某一部分人群( 比如老百姓)自然的发声。鲁迅作品中的声音,主要还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效果,他以全 部生命的力量呐喊,这种呐喊不是模仿自然,不是模仿一次性的说话行为,更不是模仿 中国人说话的某种强调(即使他所珍视的“女吊”的唱腔)。可以说,在鲁迅的作品中, 就其所要传递的整体的声音来说,我们在中国当时乃至现在的活人的口中,是无法找到 任何对应物的,因为那是鲁迅的精神的整体呈现,是通过看上去无声的文字把全部精神 思辩和情感力量“组构”而成的呐喊。
说到这个问题,不妨就把莫言的“猫腔”与贾平凹的“秦腔”稍做个比较。贾平凹很 聪明,他知道单纯用文字来模仿秦腔是无力的,所以他采取了迂回曲折的方式,通过不 断的铺垫、烘托、描写、暗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秦腔。他没有用文字去“模仿”声音, 而是用文字去“描写”声音。声音在贾平凹这里不是简单地发出来,而是通过文字曲折 地传达出来。而莫言简单化的把文字作为模仿的工具,这就很容易让另一种属于作家自 己应该制造出来的声音受到遮蔽。
三、方块字与小说
葛红兵:这也就接触到我们今天谈话的最后的一个问题了。中国人创作文学作品只能 用汉语言。一方面,文学创作对汉语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现代汉语 言就是在现代白话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方面,汉语言本身对汉语小说有很大的限制 ,或者说先天性的规定。我们过去过分强调作家、文人、学者为现代汉语言奠基的力量 ,改造现代汉语言的力量,夸大了作家在语言面前的能动性。现在我们能否反过来思考 ,来看看汉语小说如何从汉语言本身的规定性出发创造自己的形式。在这条路上,贾平 凹、莫言、李锐等作家可能有些极端,但是,却是我比较欣赏的。而鲁迅的做法可能更 为你所欣赏,但我依然认为鲁迅的语言思路可能并不适合中国文学整体,以后是否有反 过来的道路呢?即不是过多的依赖个人的才华,个人的理性思考,个人的精神品质,而 是奠基在汉语言文字固有的规定性上的以方块字为本位的道路?
郜元宝:从个人爱好来说,我更喜欢善于驱遣文字的作家,他们的文字具有一种雕刻 的力量,一种不可动摇的稳定性,可能开始是无声的,可是当我看完他们的作品以后, 有一种声音却从无声的文字中弥漫了开来。我不喜欢那样一种作家,他们一开篇就给我 很多的声音,就像走进一个广场,进入闹哄哄的群众集会一样,而文字反而变成了模糊 的可有可无的影子。在前一种类型的作家中,我会深切地感到在静悄悄的文字的徐徐展 开中有一种声音被建构出来,漫漫地弥漫开来,而在后一种类型的作家如莫言、李锐以 及阎连科的作品中,一种未必经过作家自己的精神咀嚼过、而是通过单纯模仿所获得的 外界的声音,总是就喋喋不休地传来。不管这种声音是人物的说话,还是作者的说话, 都给我以压抑感,使我难以进入他们的声音世界。他们的这种声音是以牺牲文字为代价 的,就好像把生活中的声音以录音的方式搬到文本中去,使文本成为一种装载的工具, 并最终使文本淹没于这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相当熟悉的声音。
此外,我还认为应该警惕两个概念:一是民间,它是一个很大的文学史的或者哲学的 概念,不能仅仅理解为具体的文学创作;二是莫言所说的“中国风格”,这是一个具有 危险性和蛊惑力的概念,就像传统,所谓“中国风格”,可能给人以力量,也可能把人 淹没。在某些文人学者呼吁对“全球化”作出反应的今天,中国文学中仅仅出现了这种 对声音的重视,对民间的重视,对“中国气派”的可以追求,这难道就是中国文学对“ 全球化”所能作出的唯一的回应方式吗?
葛红兵:我完全赞同你对民族化、民间精神这些概念的怀疑和反思。我提倡在汉语本 身、方块字本身的规定上使汉语文学发声也完全没有要中国文学回到民间戏曲或者什么 有形的东西上去,相反我对汉语言发声机制的欠缺很敏感,我在“全球化:对现当代文 学研究的影响”研讨会上作的发言中对此也做了总结。汉语发声机制中缺乏一元论哲学 重本体、整体、大全的思维基础,因此缺乏“全球化”关怀。另外,我比较了中国现当 代文学作品和妥思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作品之后,感觉汉语言中缺少超越者的声音, 缺少更大的更神圣的启示性的声音,这使汉语言发声缺乏“信”的基础。无论是中国现 代启蒙作家还是莫言等,他们只是部分地找到了自己的发声方式,还没有从更高处把握 文学声音效果,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只能听见“人”的声音(人的对话、诅咒、誓言、 梦呓等等),“物”的声音,而没有超越“人”和“物”的超越者的声音。
郜元宝:你提出“超越性”概念,这很重要。同时,我认为思考中国文学和语言的关 系问题,应该回到“五四”尽管所谓“回到”“五四”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成一种形式 化、仪式化的口号)。所谓回到“五四”,不是回到今天一些学者所总结的几条关于“ 五四”的结论,也不是回到“五四”人物的气派、成就,严格说来,这也是不可能,不 必要的。回到“五四”,主要是回到“五四”所提出的我们至今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上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自己的来历和来路,看清楚自己实际的文化和语言的 处境。“五四”文学革命开辟的语言天地很广阔,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缩小。在我看 来,即使“五四”人物对汉语言文字粗暴的指责与简单的改造,其中也包含着决心引入 异质因素的要求,我们今天所说的鲁迅式的绝望的反抗,就是在这个过 程中产生的。“五四”以后,我们的文学又经历了30年代、40年代、50、60年代、文革 和新时期、90年代以及世纪之交的心理转变,文学所可依靠的语言资源益发显得丰富驳 杂,而我们的作家在进入这个丰富驳杂的语言传统之时,也就更容易碰到选择的困难, 重新认识传统的困难。如果我们轻视这个困难,随意选择某种传统作为自己的文学的依 靠,就很有可能因为自己对传统的误读,而为自己所误读的传统所欺骗。老实说,当我 在李锐的《无风之树》中持续地经受他的人物语言单调乏味的重复叙说,当我在《檀香 刑》的最后,只能听到一地的猫声时,我是有一种恐惧感的。不是因为听到“瘤拐”说 话、听到人言变成猫叫而恐惧,而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些有才华的作家那里路子 越走越窄但自信心反而越来越大而感到恐惧。
标签:莫言论文; 贾平凹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论文; 阎连科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檀香刑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