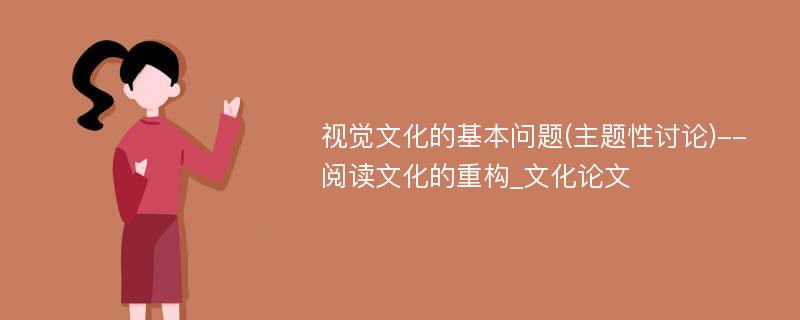
视觉文化的基本问题(专题讨论)——重建阅读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视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文化时代。它给我们带来许多值得深省的文化问题。
视觉文化首先表现在当代文化的高度视觉化。从广告形象,到影视节目;从印刷物图像,到服饰、美容、建筑、城市形象;在教科书和其他读物中,在教室、博物馆、百货商店、大街上等公共空间里,在家居环境、室内装饰等私密空间中,视觉图像无处不在;甚至在医院里,诊断和治疗也日趋视觉化和图像化了;天气预报不再是简单的天气状况的言语描述,径直转化为卫星云图的动态模拟;购物活动不只是购买商品,同时也是对商品的包装、商场内部环境的视觉快感的追求;过去像音乐这样典型的听觉艺术,在当代媒体化条件下也越来越趋向于视觉化;体育运动不但是身体技能的竞技,更是争夺人们视线的“战争”,以至于申办“奥运会”也成为各国文化的视觉形象的展示和较量。一言以蔽之,视觉因素一跃成为当代文化的核心要素,它们成了我们创造、表征和传递意义的重要手段。今天,在比较的意义上说,我们越来越多地受到视觉媒介的支配,我们的价值观、见解和信仰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视觉文化强有力的影响。
在视觉文化的蓬勃发展进程中,似乎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那便是图像对文字的“征服”。有人形象地把这个时代称之为“读图时代”,这一不那么严格的说法很是传神,它揭示出当今文化的某种变迁。说图像压倒了文字,并不是说文字不存在,也不是说文字不重要了,而是在历史比较的意义上说,文字曾经具有的优势衰落了,而图像取而代之地成为文化的“主因”。由此引发的一个忧虑是,阅读在“读图时代”的境遇如何?
所谓“读图”,就是指印刷物本身的图像化趋向正在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把我们从抽象的文字解读中“解救”出来,转向了林林总总的图像,所以,“读图”已成为一种时尚。不但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爱“读图”,甚至大学生和成年人亦热衷于卡通读物和其他图画读物。从图书市场的趋势来看,各种“图配文”书籍大行其道,这些读物与其说是图像“注释”文字,不如说是文字“注解”图像。如蔡志忠漫画系列,将诸子经典中的独特表述和精深思想,图像化为一种漫画形式,虽然这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古代经典,但同时又存在着将古代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漫画化和简单化的可能性,假如读者对古代智慧和思想的了解只限于这些漫画式的理解和解释,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有这些平面化的漫画图像,这是否会导致古代经典中的深邃意趣的丧失呢?又如唐诗宋词这样纯粹的语言艺术作品,被转化为漫画时,文字独特的魅力及其所引发的丰富联想已被僵硬地凝固于画家给定的画面,这是否会剥夺读者对文学作品诗意语言的体验呢?
除了印刷物转向读图外,电视作为最重要的图像优势媒体也在争夺或排挤阅读。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对电视、广播、报纸等不同媒体的接受效果做过试验,结果表明,最有力、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当属电视。诚然,看电视本无争议,但问题在于,如果电视在当代文化中耗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侵吞了我们太多的精力,这就造成了对阅读的挤压,问题便值得警惕。尤其需要思考的一点是,电视似乎是特别适合中国“家文化”的传统的媒体,它作为一种“装置范式”(阿伦特语)融入了国人的家庭生活,成为我们家庭文化的“核心装置”。当电视与我们的“家文化传统”合谋时,当官方政策和民间娱乐合力于大力发展和消费电视节目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怠慢阅读、冷落阅读、甚至远离阅读。经验事实和统计资料都表明,看电视花费时间较多必然是会减少阅读,而沉迷于电视则会失去阅读的兴趣。
图像对文字的“战争”还表现在电影对文学挤压。就电影与文学的关系而言,近些年来发生的变化值得考量。毋庸置疑,视觉文化时代就是影视产业空前发达的时代,在影视作品的巨大诱惑力面前,单纯的文学读物面临着难免尴尬的“边缘化”。文学名著不断被拍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人们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有时是通过影视作品而非文学文本。青年人不读作品但却爱看文学作品的影视版。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文学越加显著的“电影化”趋向,歪打正着地“成就”了文学。小说家期待着电影导演青睐自己的原作,进而使文学作品被电影或电视所“收编”。有的小说家干脆为电影来撰写,进一步强化了小说转化为视觉影像的冲动,这在相当程度上淹没了文学本身的语言魅力和特性,导致有些小说作品带有相当程度的“视觉化”倾向。过去,文学作品或电影脚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电影的质量或成败,今天的法则颠倒过来,文学性不再是电影的基础,电影的视像化压倒了文学性,出现了“第五代导演”们所热衷的“奇观电影”。这类电影不需要精彩的文学性、叙事性、人物塑造,而是强调突出的视觉奇观效果,从场景到武打,从画面震撼力到场面的刺激性。种种变化了的情况表明,文学在视觉文化时代遭遇到空间的危机。
至此,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浮现出来:传统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边缘化”,而各种视觉文化实践则独领风骚。这个结论看起来有点夸大,但正是在这夸大了的视角中,我们才可能看到问题的严峻性①。
二
从历史角度看,阅读,亦即对书面文字或语言的阅读,乃是印刷文化的典型范式。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高度电子化和媒体化的时代,它显然有别于印刷文化。从印刷文化到视觉文化,可以看作是以语言及其阅读为中心文化,向以图像及其凝视为中心的文化的转变。诚然,理想的方式是两种文化平安相处,但视觉文化的异军突起的确对阅读文化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压制和排斥。造成这一文化张力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从文化形态学上看,人类文明经历了从口传文化到读写(印刷)文化,再到电子文化的两度转变。电子文化和视觉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匈牙利电影研究者巴拉兹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电影的发明缔造了一个不同于印刷文明那种概念文化的新的视觉文化;本雅明也发现,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使得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有影响力的媒体,将导致“传统的大动荡”;鲍德里亚则断言,数字模拟技术的发展必然产生一种独特的“仿像”形式,它将取代传统的图像而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种种说法都强调了一个事实,文化的当代发展把图像推至文化舞台的前沿,图像构成了这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
从比较的角度说,图像与语言有诸多差异,而相对说来,图像似乎更加切合这个时代的文化潮流。视觉文化的图像狂欢,乃是由于图像本身的特性更符合“注意力经济”的要求。因为图像是感性的、直观的,它与快感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从阅读文字的智性快乐转向图像的感性直观满足,也许在相当程度上揭橥了当今社会文化的转变逻辑。从学理上说,语言是线性的、抽象的和思考性的,阅读语言不但给读者以反思的可能性,而且为读者自己的想象提供了更多空间。相比之下,影视图像的传递是单向的,是从影视作品到观众,它培育了观众的被动型接受;另外,影像的动感超越了文字的静态特性,提供了感性直观的当下体验,同时也取消了观众掩卷沉思的契机。显然,文字性的静观体验被影像动态的感性直观所取代。视觉文化时代的法则是:人们爱看图像更胜于文字。道理很简单,看图是直觉的、快感的和当下的。与文字相比,图像显然更具诱惑力。我们似乎正在冷落那种独自沉思的阅读状态,失去对文字阅读的热爱!这便使得图像的狂欢成为新的文化仪式!
视觉文化对阅读文化的压制,我认为还有一个当代图像拜物教的原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当代有一个从商品拜物教向图像拜物教的发展。依据法国哲学家德波的看法,古典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被马克思描述为从“存在”转向“占有”的堕落,亦即人们从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退缩为单纯地对物品的占有关系,他人的需要转化为自我的贪婪。而当代景象的社会则是另一种情形,是“占有”向“展示”的堕落,特定的物质对象让位于其符号学的表征,亦即“实际的‘占有’必须吸引人们注意其展示的直接名气和其最终的功能”②。在我看来,这个转变非常值得注意。从商品的“占有”向“展示”的转变,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景象的社会”。德波特别强调指出:“景象使得一个同时既在又不在的世界变得豁然醒目了,这个世界就是商品控制着生活各个方面的世界。”③从这句话的逻辑关系来推论,当一个世界由于景象而变得显著可见时,它一定是由商品控制的世界。“景象即商品”的公式,深刻地昭示了当代社会的性质。我想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时代,从存在向占有的堕落,相应的是一种商品拜物教;而在德波时代,从占有向炫示的转变,则由于景象的彰显而导致了某种对景象或图像的拜物教。因此,在“读图时代”,图像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和消费资源。这种资源的争夺、开发和利用,隐含了某种图像拜物教冲动。这种冲动夸大了图像的生产性功能,也在某种程度上缔造了图像的神话。
在视觉文化中,图像是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图像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能的生产性要素。所谓“生产性”,这里不仅是指图像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对象被生产出来,同时还指图像本身也在生产出更多的这一生产本身所需要的条件和资源。正像马克思谈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消费中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另一方面,生产为消费提供了材料和对象,决定了消费方式,创造对产品的需要。④用这种观点来看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生产性,可作如下表述:图像的生产性为不断发展的消费创造出新的对象、方式和需求。于是,图像就是一个最为重要、最具潜力的生产要素之一。图像既是被生产的对象,同时又是因此而生产出更多对特定生产的需求和欲望的手段。简单地说,图像不但使得商品成为现实的商品,同时也创造了对商品的现实需求和更多的欲望。
当“读图时代”中图像从各种媒体中凸显出来,成为这一时代最具权威和优势的媒介时,图像也就被“魅化”了。它可以决定特定商品的市场份额,它可以左右人们对一个品牌的认知和接纳程度,它甚至可以让某些人塑造或确认自己个体认同,以及民族的、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集体认同。它还可以营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虚拟的想象世界,可以提供这个时代特有的感性的、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等等。最重要的是,当商品转变为形象时,商品拜物教也就合乎逻辑地转化为图像拜物教,人们在商品上误置的许多神奇魔力,便顺理成章地误置到图像上来;对商品魔力的膜拜也就自然地转向了对图像魔力的崇拜。各类“读图时代”的印刷物所以流行,正是把“卖点”维系于图像之上,把吸引眼球作为书籍营销的新策略,这恰好符合“读图时代”的“注意力经济”法则。在商业竞争中,商品自身的品质也许大致相当,但其图像的公众认可程度不同却使得该商品的成为现实商品的可能性大相径庭。这显然就取决于商品图像的魔力,取决于其图像创造出来的消费者特定需求的“生产性”。反过来,从消费者方面看,拥有名牌商品最终不过是一种对商品,图像的幻觉,一种在其图像中实现了的符号价值或象征价值(商标、广告、明星生活方式、时尚、社会地位等)。在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也许比商品本身的品质或使用价值更为重要,它构成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象征价值。
图像拜物教本质上就是对图像所具有的虚幻魔力的崇拜,这种崇拜乃是夸大了图像功能并把它加以“魅化”的后果。图像对文字的“霸权”说到底正是这种拜物倾向的体现。图像所以具有这样的魔力,乃是由于图像作为文化“主因”正适合于消费社会的主导倾向。“商品即形象”这一表述本身标明了形象具有消费特性,形象作为消费对象不但提供了物质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提供了更多的符号或象征价值。在这种价值实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滋生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三
不同的文化形态塑造了不同的主体模式,而不同的主体模式又反过来作用于不同的文化。从比较的意义上看,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有许多不同的特征。这里不妨借用英国社会学家拉什的分析来说明。他认为,这两种文化在六个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话语的文化意味着:(1)认为词语比形象具有优先性;(2)注重文化对象的形式特质;(3)宣传理性主义的文化观;(4)赋予文本以极端的重要性;(5)一种自我而非本我的感性;(6)通过观众和文化对象的距离来运作。而图像的文化则相反:(1)是视觉的而非词语的感性;(2)贬低形式主义,将来自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的能指并置起来;(3)反对理性主义的或“教化的”文化观;(4)不去询问文化文本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做了什么;(5)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原初过程”扩张进文化领域;(6)通过观众沉浸其中来运作,即借助于一种将人们的欲望相对说来无中介地进入文化对象的运作。⑤在这一比较中,拉什指出了这两种文化的几个重要区别。首先是媒介差异性,话语文化以语言为核心,语言或文本具有至高无上性;而在图像文化中,图像压倒了语言转而成为主导因素。其次,话语文化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它注重形式,宣传理性主义价值观,尤其是用精神分析的概念来表述,这种文化依据的理性原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原则”。较之于话语文化,图像文化则明显趋向于感性,它摒弃了理性主义的说教,转向感性快乐,排除了形式主义原则,并把符号与日常生活现成物等同起来。这样一种文化必然导向精神分析所说的“本我”,用“快乐原则”取代了话语文化的“现实原则”。因此,话语文化必然是一种“静观型”的文化,文化活动的主体与对象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而图像文化正好相反,它排除了对象的“韵味”(aura),转向“震惊” (shock),于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便消失了。⑥正像一些学者所发现的,在当代视觉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中,感性的、快感的、当下即时的、无距离的体验成为主导形态⑦。最典型的形态差异就是阅读文字与看电影的不同。阅读是“静观”(contemplation)的典型形式,它允许读者不断地体验作品的深刻含义,反复地吟咏和停下来沉思,因而审美主体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看电影则不同,观众完全沉浸在电影情境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失了,片刻的、当下的快感使主体忘却了自身现实存在,主体的欲望直接进入对象情境。
更进一步,语言与形象的讨论不仅仅涉及两种媒介自身的特性和交往方式的差异,它们还深刻地触及当代社会中主体性建构等复杂问题。语言作为一种线性的、具有稳定结构的符号,带有明显的理性建构原则。因此,重视理性的种种观念总是与关注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在语言中,通过线性的、逻辑的阅读,便建构起一个理性的主体。正像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说,“知书达理”。相反,对形象的分析,则倾向于形象与主体感性层面的密切关联。波斯特在比较电视与文字两种交往形态时,就比较了这一差异:
电视语言/实践同化了文化的多种功能,其程度比面对面交谈或印刷文字来得更深刻,而它的话语效果也是为了从不同于言语或印刷文字的角度建构主体。言语通过加强人们之间的纽带,把主体建构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印刷文字则把主体建构为理性的自主自我,构建成文化的可靠阐释者,他们在彼此隔绝的情形下能在线性象征符号之中找到合乎逻辑的联系。媒体语言代替了说话人群体,并从根本上瓦解了理性自我所必须的话语的自指性。媒体语言,由于是无语境、独白式、自指性的,便诱使接受者对自我构建过程抱游戏态度,在话语方式不同的会话中,不断地重塑自己。⑧
如果我们注意到主体塑造的差别,那么,就应该关注视觉文化强势所造成的阅读文化困境,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和立场。事实上,不同国家对于电视媒体的策略有所不同:美国以发达大众文化产业为标志,电视业的高度发达使得美国公民看电视的时间远多于其他国家公民,也许,他们阅读时间也就相对较少;相反,法国似乎并不特别鼓励电视业的发展,无论电视节目的数量还是电视台的数量或是播出时间,均远远低于美国。法国人有着良好的阅读文化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法国是西方国家中人均读书时间最多的国度。这个比较对我们来说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历史地看,中华民族具有古老的阅读文化,有着深厚的、足以自豪的阅读传统。今天,在大量视觉媒体急速扩张的条件下,如何有节制地控制视觉媒体对公众闲暇时间的侵占和剥夺,如何倡导和鼓励一种阅读文化,提倡从小开始培育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我以为这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个严肃的、不可推诿的任务。虽然我们不能断言沉溺于电视会使人变得平庸浅薄,但是却有理由认为,不读书和少读书将会使我们的思维和修养变得简单、越来越贫乏。因此,警惕视觉文化的快感主义政治和消费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正视的问题。这也是笔者呼吁重建阅读文化之原因。
注释:
①一些学者指出:“以往文章解释图像,现在则是颠倒过来:照片图解报纸上的文章;照片使报纸文章再度具有魔术性。以往是文章主宰,现在是照片主宰。在技术性图像主宰的这种情况下,文盲有了新的意义。以往文盲被排除在被文章符码化的文化之外;现在文盲几乎可以完全参与被图像符码化的文化。未来,如果图像完全使文章臣服于它们自身的作用中,我们可以预期一种普遍性的文盲状态,只有少数专家受过写作训练。”(傅拉瑟:《摄影的哲学思考》,第 78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
②Guy Debord,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Zone,1994),# 16,#17.
③Ibid.,#37.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⑤Scott Lash,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London:Routeldge,1990),175.
⑥参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3。
⑦参见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⑧波斯特:《信息方式》,第65-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