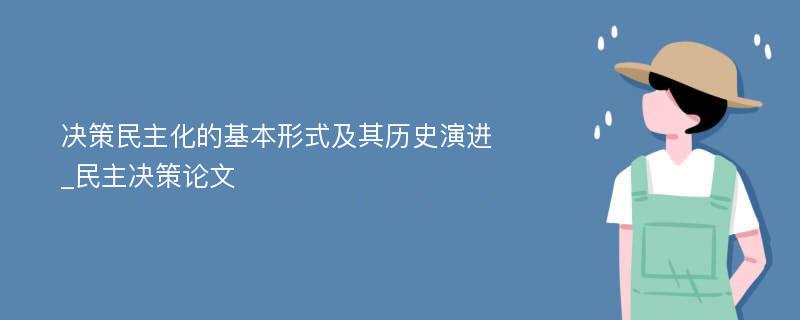
决策民主化的基本形态及其历史沿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沿革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决策民主化是指决策权力的运作形式,即领导决策必须要充分发扬民主,不能个人说了算。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的说法,就是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这就是决策民主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决策民主化的宗旨。
决策民主化关系到决策权力的归属问题,关系到领导决策思想、决策意图的来源问题,关系到领导决策的群众基础问题,同时也关系到领导决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因此,决策民主化必须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决策程序,确保领导决策的民主性(但并不排斥领导者的主导作用)。 决策民主化的核心是民主。民主在阶级社会中既是一种政治形态,又是一种决策形态。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一般是指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是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概念。而民主作为一种决策形态,则是指决策权力的行使主体和行使方式而言。即领导决策一方面必须要以民为主,或由民做主,或为民做主,充分发挥民众在领导决策中的作用,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要群策群力,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既不搞家长式、一言堂,也不搞神秘主义。即使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原则进行决策,也不能忽视民众在领导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决策民主化是个历史过程,是在历代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一般具有以下三种基本形态。
一、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
全民公决是民主决策的原始形态。早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即原始公社时期,就已出现了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谈到古代易洛魁人的选举制度时所指出的那样:易洛魁人在选举氏族首领时,“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2页)这就证明,全民公决是一种古老而又原始的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不仅在一些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中充分体现出来,就是在我国解放前夕,在后进的兄弟民族地区也完整地保存下来。如尹达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有关苗族实地调查的报告中,就曾详尽地记述了这种决策形态:“苗民有事,一以公意决之。故事必会议,议必实行……其召集方法,由苗头(众所选举)砍木刻,使人示区内各寨,急者加枯炭鸡毛,又急者加辣椒火绳,尤急者则烧之使然。苗瑶睹此,立即奔走骇汗,齐赴会场……首吹芦笙,众肃然。次由苗头宣布开会理由,次讨论提案,到会者均有发言权及表决权,每次一案则取一木置之。会讫,当众数草,表决此届决案若干,而后会务终矣。自是而后,区内所属苗民,对于决议各案,遵奉唯谨。此种会议,苗人谓之‘埋埃’。”(左东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第17页)这就说明,以“民众大会”的形式出现的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曾是原始部落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不仅带有全民性,而且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体现了民主的本义。民主就其最初的本义来讲,就是以民为主,或由民做主,或为民做主,民众是决策的主体,而领导则是普通的一员。中国古代的“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之说,就是这种本义的体现。只是到了后来,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民主才变成了“国家形态”。即使这样,民主也不失其为一种决策形态。在民主制的国家中,民众的主体地位仍在某些方面起着决定作用。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以及在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民众的投票仍是入选或下最后决心的关键。这就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现仍存在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民公决,由于选民受到财产状况和居住年限的限制,一些人被排斥在外。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民公决,实质上并不带有全民性,起码在资本主义初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第248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民公决的局限性。同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使命是“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他说:“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07页)。这就告诫人们,实行全民公决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必由之路,只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全民公决的决策形态只能在县乡两级政府选举中试行,全国范围内的全民公决,尚须等待时机,一旦条件成熟,未来必将实行之。
二、群体参与的决策形态
群体参与是民主决策的过渡形态,是从全民公决向领导专断,或从领导专断向集团决策的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具有双重特性的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的决策主体虽然不是人民群众,但民众(含咨询参谋人员)在领导决策中却保留参政议政的权利,对领导决策仍起着影响与制约的作用,因而属于民主决策的范畴。至于这种决策形态的民主性的大小,一般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取决于领导者(即决策主体)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及自身的“纳谏”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广大民众(含咨询参谋人员)的参与程度。因此,在不同社会,面对不同的领导者,群体参与的民主化程度也有所不同。
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部落联盟的扩大,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不断增大,因而决策主体发生了异化,由原来氏族公社内部的群体决策即全民公决变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即领导者)决策。部落联盟首领(即领导者)成了决策的主体,而民众则失去了决策主体的地位,但却保留了参与或制约(通过舆论影响)领导决策的权利,这就形成了群体参与的民主决策形态。不过,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领导体制的限制,参与的对象就中国而言主要是“四岳”(即氏族首领),而民众则只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管子·恒公问》)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原始社会末期,“四岳”的参与对部落联盟首领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尧在选拔继承人的决策过程中,“四岳”的群体意见(即共同意见)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奴隶制社会中,由于血缘宗族占据着统治地位,天子虽然在名义上是奴隶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却处于各诸侯国的“共主”的地位。因此,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天子不能自专,而必须要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一是要征询世袭贵族的意见,即盘庚所说的“与旧人共政”(《尚书·盘庚上》);二是要征询卿士(即下属、谋臣和策士)的意见;三是要征询国人(即族众)的意见;四是要征询神职人员(即卜和筮)的意见。正如箕子在向周武王传授统治经验(即决策经验)时所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其中,除最高统治者(即天子)之外,卿士、庶人和卜筮(即神职人员,一般由贵族担任)都是领导决策的重要依靠对象,在领导决策中都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特别是神职人员的意见,在神权领导思想占主导的奴隶制社会,对于最高统治者(即天子)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高统治者的领导决策,只有得到神权的有力支持,最终才能得到贯彻和实施。否则就要受到遏制,对领导活动极其不利。
此外,在奴隶制社会中,有些公卿不仅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参与最高统治者的领导决策,而且还可以决定废立国君,代国君“摄政”。至于国人(即民众)也可以指责国君或驱逐国君。有的朝代甚至还公开设立专职官员(小司寇)专门从事征询民众(即国人)意见的工作,使民众(即国人)在“国危”、“国迁”、“立君”等重大事情的决策上有发言权。或像商王盘庚那样,“命众悉于庭”(《尚书·盘庚上》),通过民众大会的形式,由国人做出决定。可见,在奴隶制社会中,群 体参与带有更大的民主性。只是这种民主,从总体上看属于奴隶主贵族民主制,同“原始”的民主制相比,有着本质的差别。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君主专制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央集权的政治领导体制赋予国君(即皇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重大事情的决策都是皇帝说了算。因而,群体参与的民主决策形式无论从参与的对象还是参与的程度上看,都比其他社会大为逊色。但这并不等于说封建社会没有群体参与的决策形态。事实上,秦汉以来的“朝议”(明朝叫廷议)以及幕僚制度,就是群体参与的一种特殊形态,只是这种形态是以“众谋独断”或“兼听独断”的形式出现的,其民主程度比其他社会小得多而已。因此,不能由此而断言封建社会就没有群体参与的民主决策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政治上标榜民主,经济上提倡竞争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为民主决策奠定了社会基础。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决策形态,一切重大事情都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的。不过,由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只是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所以对于广大民众(含专家和咨询参谋人员)说来,除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外,对于其它事情的决策只能参与,即直接或间接参与其它事情的决策。这就说明,群体参与(主要是专家和咨询机构的参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主要决策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领导则是公仆。因而,在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人民都有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不仅参与的领域、对象极其广泛,而且参与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必然趋势。
三、集团决策的决策形态
集团决策是民主决策的现代形态,是现代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普遍运用的一种决策形态。这种决策形态的决策主体既不是全体民众,又不是孤立的领导者个人,而是领导班子或领导集团的全体成员。集团决策从其外部形态来看,古代社会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决策形态。比如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末期的“长老议事会”,奴隶制社会中的“贵族会议”、“诸侯盟会”、“民众大会”或“国人大会”以及满清入关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等等,从形式上看都类似现代的集团决策。但从其决策主体大都不是与会成员,或与会成员同会议的召集人并非处在同一权力等级线上看,上述会议除满清入关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均不属于集团决策的范畴,而是全民公决或群体参与的决策形态。满清入关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属集团决策,但又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少数民族处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的决策形态,入关以后立即改变了这种决策形态。现代意义上的集团决策,起码要具备以下五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具备普遍性,必须是一切民主制国家普遍运用的决策形态;二是必须具备群体性,集团本身必须是领导群体,每一成员必须具备领导职能和领导权限;三是必须具备主体性,集团本身必须是领导决策的主体,承担领导决策的基本职能;四是集团成员之间必须是平等的关系,必须处在同一的权力等级线上;五是必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每个成员在决策过程中只能起到一票的作用(当然,一把手的核心地位不容忽视)。
现代意义的集团决策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决策,一般都必须通过议会(参、众两院)来决定。不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只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列宁选集》第3卷,第209页)所以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畴。而社会主义社会的集团决策,则是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形态的集团决策。这种集团决策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体。所以同资本主义的集团决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团决策,必须注重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注重充分发扬民主,不能搞一言堂;另一方面必须注重维护领导的权威性,特别是要注重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及其主要领导者的权威性,确保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切重大决策的贯彻和实施。这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