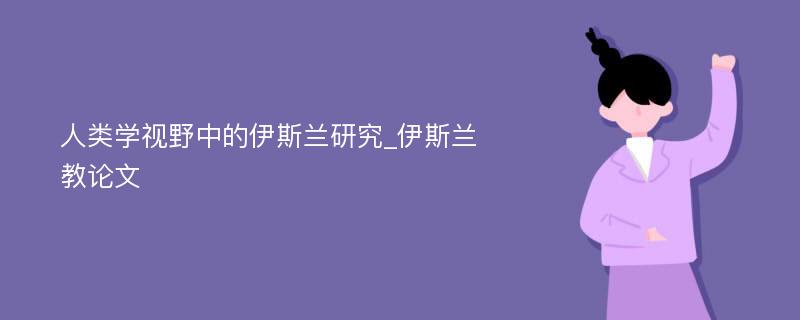
人类学视野下的伊斯兰教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人类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B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07)02-0013-09
研究伊斯兰教比较困难也比较重要,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的出版,把中东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推到了人类学关注的前沿。认为学术不仅面临着纯粹的事实,也面临由学术传统和历史论述框定的事实。萨义德指出:
“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1978:5)
详述了地区学术共同发展和政治形势之后,萨义德总结到:没有可能从理论上理解中东或伊斯兰教实践,广而言之,理解国际权力结构的历史发展独立性。很明显,这种论点与人类学田野情境相悖,但出于对伊斯兰文化的尊重,它不仅具有长期的历史根源,而且也是经济和政治的尖锐交锋。地缘安全关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民族的对抗环境,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可能存在的核竞赛,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萌芽的经济权力,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持续了10年的海湾两伊战争,拉史迪(Salman Rushdie)事件和欧洲的反穆斯林风暴,苏联的解体,对持续不断的政治分裂和全球权力平衡变化的恐惧,都使研究穆斯林社会显得敏感并有争议。从另外一个——穆斯林的角度来理解,用Lila Abu-Lughod谈到的贝都因人(阿拉伯、叙利亚、努比亚或撒哈拉沙漠的游牧部落中的阿拉伯人)的话,“知识就是力量……美国人和英国人……想知道我们的任何事务。以便他们到了某个乡村,或者去统治它,他们知道人们需要什么,也知道如何来统治。”(L.Abu-Lughod 1989:267)
欧美民族社会学对穆斯林社会流行的“西方”式理解出自三个方面:(1)地理术语和宗教传统之间,中东和伊斯兰显得“属于”互相排它;(2)宗教传统及其尊奉者的行为之间,部分或全部穆斯林的活动作为有动机的系统归于伊斯兰教;(3)作为实践的伊斯兰教和存在于观念系统的伊斯兰教之间。这种持续的特点不仅是民族社会学,而且是一些地区东方学学者的特点。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将伊斯兰视为一个可与伊斯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分开研究的‘文化综合体’”(1978:105),这种形式使伊斯兰教变得“立刻意味着一个社会,宗教,封闭的传统社会原型和现实。”(299)
作为创造了穆斯林社区区域社会学的因素之一,人类学显然也高估了宗教的作用。正如Raphael Patai(1952:19)的观点,“宗教在中东文化的很多状态和方面都是原动力,实际上在生活中每个行为和时刻都有自己的方式。”(Patai 1976)由于人类学文化概念的潜在宽泛性,这一观点仍然有一定吸引力。“所有的习俗和传统都基本上是宗教的……因此,习俗的所有领域渗入日常生活时宽泛而没有限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宗教分不开。”(Patai 1952:19)当然,对文化或宗教更加复杂的解读,在人类学观念中很容易被分成两个概念。除宗教外,人们还有其他信仰、观念、动机和活动。
穆斯林将伊斯兰教和标准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达到认同的因素比较复杂。对有文化的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更像是许多西方的东方学家们架构下的“高层次文化”。
伊斯兰教是社会秩序的蓝图。它认为存在一系列永恒的,神圣注定的秩序,独立于人类的意志之外,规定了社会的合理秩序。这一模式在写作中有用;它同等的、平衡的对所有文化人和所有注重文化的人有用。这一规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Gellner 1981:1)
如同任何一个“至上”传统,穆斯林遵守的标准系统独立存在于当地环境之中。但实际上,即便是对如信仰、礼拜、封斋、天课和朝觐等宗教“基本”特征的理解和实践,各地都有差异(Muson 1984:28,Bowen 1984,1989,1992b; Woodward 1988)。
理解各地伊斯兰教遗产表现的复杂性部分起源于伊斯兰世界地理区域的观点。由于麦加是伊斯兰教圣地的中心,而其余几亿人口分布于伊朗和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口相当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人口(Eickelman 1989:10)。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有20多个,分布于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到孟加拉国,几乎所有西、南亚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岛诸国、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的阿拉伯国家),北非国家(从索马里、苏丹、埃及、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以及中亚的许多前苏联国家。穆斯林占相对少数的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和尼日利亚。北美和欧洲也有很多穆斯林人口(例如在法国和美国都各有300万),同时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少量的穆斯林人口(Eickelman 1989:10;中亚参照Eickelman and Pasha 1991;美国参照Haddad and Lummis 1987; Haddad 1991)。
不幸但可以理解的是,即使在一个单独的复杂社会也有必要投资以掌握文献,在不同的穆斯林社会中,仍有相对不太明确的、大量的民族史学工作要做。格尔兹(Geertz1968)对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圣徒角色和象征性的著名比较至今仍很显著,总体上说两者都正确并在理论上有助于宗教体系的研究。Gilsenan(1982)研究了也门、埃及、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等地伊斯兰教的呈现,深入关注了由殖民和阶级渗透形成的持续变化。Munson(1988)讨论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下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这是人类学唯一试图与中东伊斯兰教的现代政治角色达成协议的尝试。Antoun(1987)比较了约旦和伊朗的宗教领袖,而Bowen(1992b)从事于摩洛哥和苏门答腊岛(在印尼西部)献牲的不同逻辑,Meeker(1979)调查了阿拉伯和北非田园风味及文化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除了格尔兹和Bowen之外,所有这些工作都局限在中东。为了在时空上对比较穆斯林社会的理论问题予以补充,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1990年代建立了多学科的穆斯林社会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Societies)。
在穆斯林的理论中,伊斯兰教起源于伊布拉欣(Abraham)服从安拉的命令,自愿向其祭献儿子伊斯玛因(在阿拉伯语中,“伊斯兰”一词是元音,词根可以派生很多单词,有不同的意思,具有安全、保护、服从、和平和屈服的意思。表明个人完全听从安拉的意志)。伊布拉欣建造了克尔白(Ka‘ba),成为穆斯林每年朝觐的中心。
世俗的宗教学者追溯伊斯兰教的起源,始于公元610年哲百勒依(Gabriel)天使向40岁的麦加商人穆罕默德传达安拉的启示。《古兰经》是未经任何更改和人为的安拉的语言,是安拉对人类的最后启示。它跟早期降示于闪族语系使者如穆萨(Moses《圣经》中的摩西)和尔萨(Jesus《圣经》中的耶稣)的启示一样(但随后被犹太人和基督徒社会歪曲)。由于早期穆斯林牢记和背诵了原文(Nelson 1985),《古兰经》、圣训(Sunna)及穆罕默德和其弟子的传统习惯成为随后伊斯兰教神学思想和法律的基本源泉,(想了解穆斯林神圣历史的可读性材料及宗教制度概要请看Esposito 1988)。
穆斯林的太阴历不同于其它历法,既不始于伊布拉欣,也不始于《古兰经》首次下降的时间,而以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受到麦加人的迫害,在叶斯里布(Yathrib)建立了政治组织为开端。叶斯里布是麦加北部的一个绿洲,后来以麦地那(先知之城)而闻名。穆斯林神圣历法不以首次启示为开始,而以建立政治公社为开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者都引用这一特点强调伊斯兰教注重政治和社会事务。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限制建立正式的、寺院式的僧侣制度,尽管各种宗教专家都可以充当宗教导师、圣徒、教师、法官及政治领袖,但没有明确的牧师角色。宗教领袖通过起源于穆圣家族,通过个人具有超凡能力或学习的名声而受到保护。
早期伊斯兰社会的实力和组织使其版图迅速扩展,公元7世纪在联合了阿拉伯半岛上各部落之后,势力直达拜占庭(Byzantine)和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an)。穆罕默德去世仅40年后,穆斯林军队向西到达摩洛哥,16世纪时势力扩展到印度北部。在非洲,穆斯林穿过撒哈拉沙漠沿着商道向南,向东到达印度洋和东南亚,10世纪时就取得了西部非洲的统治权。14世纪穆斯林进入爪哇(Java),用商贸和文化把世界连为一张大网(J.Abu-Lughod 1989)。
有关蒙昧和伊斯兰教传播时期的大量历史文献在Hourani(1988)的阿拉伯人历史中很容易找到,还有Hodgson(1974)对世界伊斯兰文明著名的大部头的阐述(非洲部分看Clarke 1982),及Rodinson(1971)的有争议的穆罕默德传记。Wolf(1951)和Combs Schilling(1989)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简明扼要地分析了伊斯兰文明的起源,但不符合Muhammad Bamyeh应用目前欧洲社会理论来解释伊斯兰教起源的理论雄辩。
父系(Combs-Schiling 1989; Delaney 1991)、母系(Rasmussen 1989,1991,1993)和双系亲属制度(Ong 1990)使伊斯兰教具有社会宗教倾向;有些学者关注了农村生活(EvansPrichard 1949; Lewis 1961,1986; Ahmedand Hart 1984)、农民(Bowen 1991; Delaney 1991)和都市社会(Gilsenan 1973; Fischerand Abedi 1990)。这些用完全相反的权力和社会思潮体系为社会提供了主要观念和象征(Geertz 1968),并关注了特殊社会中不同的阶级(Bujra 1971; Kessler 1978),接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Horvatich 1992,1994; Loeffler 1988; Eickelman 1992),不同的政治观点(Fischerand Abedi 1990)及男女两性(Macleod 1991; Tapper 1987)。这可以提供一种法律、风俗和族群划分(Ewing 1988)的根据,也是强大军事抵抗的基础(Shahrani 1984)。
穆斯林学者认识到不同社会结构和历史变化过程的重要性及其联系。早在14世纪就出现了用历史社会学分析阿拉伯帝国崛起和衰落的重要作品(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967; 1377)。相反,早期欧洲人类学作品对伊斯兰教倾向于详细描述的专论,缺乏伊本·赫勒敦般的生动,但对社会实践和民俗仍有价值资源。Edward Lane(1963)详细叙述了19世纪开罗的衣着、物质文化和风俗。例如他对巫术活动、护身符和宗教节日的描述至今出类拔萃,得益于他在埃及长期居留和流利的阿拉伯语。Edward Westermarck(1911,1914,1926)对摩洛哥信仰、仪式和民俗的记述同样真实,Sir Richard F.Burton(1964)装扮去麦加朝觐而完成的编年史。最后这部作品包含朝觐和城市神圣范围内有价值的现代民俗,包括一种奇怪的见闻——学生总是问那些令现代的、东方式理论作品完全沉默的问题(比如克尔白里有什么?)。
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穆斯林社会专门的人类学研究不多。当然,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 1949)有关赛努西(Sanusi)的社会历史研究是一个特例,涉及19世纪利比亚部族间的宗教兄弟关系。Greenberg(1941,1946,1947)重点详细地分析了伊斯兰教与传统宗教接触和融合而产生的影响,以及尼日利亚北部豪萨Hausa部落的社会组织。Skinner(1958)描述了象牙海岸的类似过程。
如上所述,如何研究伊斯兰教至关重要。当然最好的开端是格尔兹(1968)的《伊斯兰观察》,比较了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神秘派,一方面对个人神秘性活动,另一方面对坐静式的精神休养进行了比较。同时也大体上对两国伊斯兰教在政治发展中的角色予以了关注,本书也代表了格尔兹有关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最细致的讨论,以及在获取信仰的现象学方面人类学所面临的困难。该书持久的影响在于受整体观点的影响,作者认真考虑社会结构、历史和文本资源对伊斯兰化的贡献,“采取普世的、理论上标准化的、本质上不会改变的……仪式体系和对本土,甚至个人、道德和纯粹哲学的信仰”的双向影响,而同时“争取保持伊斯兰教的特点……通过使者穆罕默德的优先预言能力作为安拉与人交流的特殊指示”。
神学在此过程中的矜持也是人类学的压力:如何以神圣的典范来应用于世俗的生活。
人们的宗教是其特殊的内容,根植于恪守者的思想和隐喻中,利用它来刻画现实;这会产生很多不同,你可以把生活看作梦境、朝觐、迷宫或狂欢节。但这样的宗教历程,其历史过程反过来建立在把这些想象和隐喻归还给那些拥有它的人们可以利用的制度上。
其他学者也沿着这条路前进,勾画伊斯兰教实践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历史变迁(Bowen 1991; Eickelman 1976; Woodward 1989),也有人仅限于狭小的政治(Bujra 1971; Kessler 1978)、心理学(Crapanzano 1973,1980; Ewing 1990)及穆斯林体验的性别区分领域(L.Abu-Lughod 1986,1993b; Boddy 1989; Delaney 1991; Holy 1988,1991; Tapper and Tap per 1987)。
已经有一些略显陈旧但很优秀的评论伊斯兰教的人类学作品,恰恰强调了格尔兹提出的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分析对象的问题。人类学对伊斯兰教研究的意图是什么?是文本?制度?一系列仪式?祷告类型?还是社会体系?由于讨论穆斯林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所以这四个方面都需要考虑。Eickelman(1982),Asad(1986),Lila Abu-lughod(1989)都认为:
在当地语境中研究伊斯兰教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描述和分析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原则是如何被不同社会和历史语境认知的,而无需一面把伊斯兰教描述成为没有瑕疵的精髓,又将其刻画为信仰和实践可塑性的聚集体。(Eickelman 1982:1-2)
此外El-Zein(1974)讨论了本土经验的重要性,指出伊斯兰教“本土化”模式是否为分析的起点,“是可以进入并在任何一点深入挖掘的体系……没有自动的实体,并且没有固定和专门孤立的功能意义可归于一些基本的分析单元,它是象征、制度或过程,不会从外部给系统强加人为的秩序。”(251—252)这种解读结果不是人类学研究伊斯兰教大传统,而是研究众多的伊斯兰教小传统。“不管在民俗还是正式的神学中其内容都没有根本的不同,暗示一方比另一方客观、有思考性或系统性……他们只在表达方式上有区别:一方以制度形式存在,而另一方以作品形式存在。”(249; Woodward 1989:63)而主流研究有时区分“真正的”伊斯兰教和“退化的”本土变异,带有前伊斯兰教时期的习俗或现代革新思想(Antoun 1989; Bowen 1984,1989; Horvatich 1994; Woodward 1988,1989)。同样案例是非主流研究会区分“政府的伊斯兰教”和民间的伊斯兰教,与主流研究对本土化的理解和实践评价明显相左(Loeffler 1988; Eickelman 1982)。
Asad(1986)消除了el-Zein和Gellner有关伊斯兰教是一个明显的社会蓝图的争论,阐明了有选择性的观点,最近许多学者都对此做了阐发。根据Asad的说法,如果我们避开把伊斯兰教作为研究对象要么扼要表达,要么模糊演绎两种难题,我们就得承认“伊斯兰教既不是明显的社会结构,也不是信仰的异类堆积、人工制品、风俗和道德。它是一种传统。”(14)伊斯兰教用特殊的方式连接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总结这一观点,L.Abu-Lughod(1989)以为,这种三方联系的研究聚焦于“每日功修、演说和调用的宗教文本,身为其中一分子的历史,及其参与的政治事业之间的互动。”(297)
很多学者都致力于使这种理论关注适应于现实生活,著名的有Bowen(1984,1987,1989,1991,1992a,1992b),他研究了“叙述的选择和确立的过程……着重于扩大文化传统和降低过程水平之间。”(1992a:495)他记录了苏门答腊岛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过程:
伊斯兰和当地认识之间的变化,不仅是我个人解释的策略,也是Gayo穆斯林的意识。Gayo人通过参考经文,来自中东的宗教书籍以及使者的故事而享受知识的阳光雨露,教给我有关宗教和社会的知识。Gayo的男女有时用Gayo的谚语解释阿拉伯语文本(或其翻译),或比较穆萨和当地祖先灵力的权能。就像各地的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一样,Gayo人从基于经文的库存中,通过叙述和多义的社会世界,把世界勾画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宏大的受宗教限定的社会。(496)
穆斯林利用伊斯兰教的财富作为其理解和实践的唯一资源。同Fischer,Abedi(1990),Lambek(1990),Launay(1990,1992),Messick(1986,1993),Woodward(1988,1989)一样,Bowen由对本土语境中的伊斯兰教进行直接研究,转向理解在特殊语境中穆斯林实际上是如何利用特殊文本的。Woodward(1989:49)提醒我们,“对文本的分析应该采取像对神话、仪式、社会行为和其它文化材料一样的态度……文本的意义或文本本身只能决定于其所指的具体文本的语境。”研究“政治经济意义”(Roff 1987)很重要,因为伊斯兰教可以被理解为“在本质上是象征和原则的庞大的复合体,在很多问题上提供多种可能性,甚至是相反的观念、意义、态度和思考方式”(Loeffler 1988:246-247)。
必须消除人类学研究把共享文化当作神话的观点。不然人类学家实际上在其作品中提出的是合成的画面,以及从非常表面的、详细和似是而非的、存在于任何研究对象的理由中小心翼翼地凑合起来的系统。这种方法的难处在于它给人以任何事情都平淡无奇之感,而实际上名家和人类学家合作才能创造出可信的文本。(248)
合理的知识分配反应了对权力的分配。不管一个穆斯林社会如何组织,对其是否是伊斯兰的界定,可能与社会如何密切地反应一个已知的文本蓝图无关,而是有关什么人如何使用特殊文本来保证特殊的实践和对权力的一般观念。矛盾的是,Asad写道,“并不仅仅是观点本身,而是明显的关系——权力关系。这里穆斯林有权来规范、支持、询问或调整正确的实践,同时谴责、排斥、削弱或替换不正确的,正统是有范围的。”(Asad1986:15)。Antoun(1989),Messick(1986),Woodward(1989:63)说明了本土的知识分子如何进行对于真实的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建构,宗教教职人员是如何产生,以及他们怎样进入个人和权力的制度网络中,进入解释经典的传统,以及如何理解大众的社会事务。
伊斯兰教文献是通过传统和革新的交流渠道及文化实践解释社会真实的。20世纪70年代,传播阿亚图拉霍梅尼在流亡期间发表演说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录音媒体,首先在伊拉克,然后在巴黎向伊朗发表了反对顽固派的宣言。技术在穆斯林世界的其它领域内有同样的影响,这是很多学者都评论过的进步,但没有人系统地提及。Messick(1986),Fischer(1980),Fischer,Abedi(1990),特别是Antoun(1989)和Gaffney(1987a,1987b,1991),研究了宗教学者和传教士创立的道路,并按照历史上形成的正统派观点,研究了伊斯兰教特殊性和“权威性”知识的交流方式,主麻(星期五)的宣教及清真寺下午的学习。
知识向普通大众传播以前是伊斯兰教学者的产品,是通过传统清真寺教育体系传播的学问。Fischer(1980),Fischer,Abedi(1990),Mottahedeh(1985); Eickelman(1978,1985),Messick(1993),Wagner及其同事(1980,1983,1987b研究初等教育)详细描述了内部学习组织。根据一本文集的记录,伊朗、也门和摩洛哥传统教育的内容、学习方式和对权威学者的态度各地有很大不同,从伊朗的宗教学校(madrasa)犹太法典式的师生互动,到摩洛哥对提问的排拒。这种对知识再生产及权威的研究是通过对宣讲、教学和合法履行宗教功课的研究来完成的,但特殊的是,重点研究这些体系的变化情况是目前人类学伊斯兰教研究中的主流,试图阐明文化创造、再生产、传播以及在其它文化传统中调适的过程。
要求出身于先知穆罕默德世系(bujra)的群体,要求特殊权力来调节与安拉的关系的个人和群体(Eickelman 1976; Gellner 1969; Gilsenan 1973),对培养穆斯林学者感兴趣的群体(Eickelman 1978,1985; Fischer 1980; Fescher,Avedi 1990; Mottahedeh 1985; Messick 1974,1986,1993),以及那些控制了现代政治和教育设备的群体(Eickelman 1986,1992; Starrett 1991)对正统和政治秩序的创造,是最近人类学研究的焦点。显然,这些实际上是穆斯林世界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个人无需经过特殊教育成为宗教学者或专家,声称体面的血缘可能接近宗教知识。出版业和高等教育发展迅速(Eickelman 1992),小学和中学里文化传播很快(Starrett 1991),电子媒体的传播(L.Abu-Lughod 1993a)在穆斯林世界对宗教权威的结构影响巨大。
社会认可的宗教学习过程不再限定于那些在相当于宗教大学环境中学习过传统文本的人,他们赞同精英们的观点……宗教知识学习的过程日益会面向任何认可伊斯兰教义务之人,就像许多接受了教育的农村青年一样。远离记忆的控制,宗教知识可被抽象或灵活地描绘和解释。跟从某人学习的长期学徒身份不再是使其宗教知识合法化的先决条件。打印或油印的小册子以及录制用来秘密派发的学习磁带开始代替了清真寺,成为传播伊斯兰知识的中心,以挑战国家认可的形式。(Eickelman 1985:168)
这种对以前文化“禁锢”的开放(Messik 1974; Niezen 1991; Street 1984; Wagner and Lotfi 1980,1983; Wagner and Spratt 1987a,1987b)激起了政治和宗教领域当权者的普遍不满。在印度尼西亚(Bowen 1984; Nagata 1982)、马来西亚(Banks 1990; Nagata 1987)、菲律宾(Horvatich 1992,1993)、摩洛哥(Munson 1986; Eickelman 1992)、伊朗和美国(Fischer and Abedi 1990)、埃及(starrett 1991)及其它地方,世俗教育的年轻受益者和日益增长的流动性,通过他们新发现的获得知识和世俗资源的方法维护着宗教权威。
这种权力依赖于社会和政治环境,会向悠久的伊斯兰教本质形式的操守者施压,产生新与老(Woodward 1989:79)、传统与现代、阿赫麦迪耶派(Ahmadi:现代派改革运动的遵奉者)和正统派(Horvatich 1994)之分。不满会相继出现,以反对国家机构对经典合法解释的垄断。
对Gellner(1981)而言,这种“平等的经典主义”是伊斯兰教社会秩序蓝图的自然特征。
伊斯兰教虽然不是现代化的源泉,却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实际上它的主要、正式、“纯洁”的变量是平等的、有学者风度的。同时,专制和狂热适合于可消耗的、最终否定的、外围的形式,极有助于其适应现代世界。在渴望普通文化的年龄,学问的开放会面向整个社会,这样就可以实现知识平等,这是接近所有信仰者的“新教”理想。现代平等主义者应该满足……重新觉醒的穆斯林有平等经典主义的倾向,事实上会与民族主义者融合,所以很难讲谁对谁更有益。(5)
从专制到平等的转变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在宗教权力机构和渴望权力的群体之间的艰苦斗争。伊朗和埃及、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专制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20世纪宗教和政治当权者之间的冲突有时采取暴力冲突的形式,时下流行的运动被贴以“原教旨主义”、“激进主义”或“战斗的伊斯兰”、“伊斯兰复兴”、“觉醒运动”等等标签。历史地看,建立在“净化”本土伊斯兰教,远离蒙昧时期或外部影响名义下的伊斯兰改革运动,不仅在中东,而是在各个地方(有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看Peacock 1978,Nagata 1984)都司空见惯。这种运动可与其它社会运动相比(Burke and Lapidus 1988),试图推动政治结构和社会实践向宗教或政治理想前进。在西非和东南亚地区,回国的本土学者和雇用工人,以及去沙特的朝觐者经常发起改革运动,认为新的伊斯兰知识比在家里实践的更加“合理”,或传播来自中东伊斯兰教中心地区的材料(想了解返回工人要求行为改革的例子读Boddy 1989:51-52)。
由于西方工业利益注意力集中于得到中东的石油,给这一地区的宗教和政治运动带来了很多隐患,特别是伴随着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和革命”等标题下的出版工业也发展起来。不幸的是,许多作品都质量差,很少有人类学家的作品。Keddie(1981,1983,1986)和Fischer(1980)对伊朗,Kepel(1984)和Sivan(1985)对埃及有较好的历史和解释作品。记者Edward Mortimer(1982)总结了中东伊斯兰化改革的历史,Munson(1988)和Stowasser(1987)从总体上对中东的伊斯兰教和现代运动做了很好的分析,Piscatori(1991)讨论了1991年海湾战争对穆斯林政治运动的影响。
Fischer(1980),Beeman(1983)和Hegland(1983a,1983b,1987)提供了对革命的民族志观察,他们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从事田野工作。所有作品都涉及现代宗教象征因革命需要而动员和变化的方式。此外Fischer和Abedi(1990)还讨论了霍梅尼和伊斯兰教教法的思想体系,分析了革命艺术和意象,写了大量有关伊斯兰共和国旗帜多重象征意义的评论,从伊朗人特有的和一般的伊斯兰文化资源两方面,说明其形式如何同时又天衣无缝地结合了意象,以及其符号反过来在当代实践中被利用和转变的。
伊斯兰“觉醒”的一个非常显著而固定的特征是妇女回到面纱时代,这种潮流实际上并非回到任何形式的传统服装风格,而是解释在现代穆斯林社会如何做妇女,用十分新颖的手段重新确认身份。El-Guindi(1981)早期对埃及妇女面纱的优秀作品最近又得到Zuhur(1992)和Macleod(1991)长期研究的补充,他们认为端庄的穿着同时也是对男权结构的调适和保持运动以反抗这种结构,抗议现代埃及妇女相较男子地位低下。埃及的案例可以同Fischer(1980)描述的chador对伊朗革命非同寻常的反抗符号做比较。
女性蒙面符号的特殊情况在Lila Abu-Lughod(1986)和Delaney(1991)的优秀作品中有对应,他们分别详细分析了包括埃及、苏丹、土耳其的农村地区妇女蒙面和遮盖羞体的真正思想。Abu-Lughod特别指出蒙面和遮盖在埃及农村实际上有别于“传统”的贝都因人,阐明了许多有趣的关于庄重的非连续性观念。认为蒙面与特定范围内的荣辱关系有关,与伊斯兰认同的观念有关,在感情和认知意义上完全不同。
像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继承了悠久的父权制传统,在经文、法律和穆斯林世界各地的习俗中有反映。Delaney(1991)和Combs-Schilling(1989)指出中东妇女在伊斯兰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民族信仰中普遍无权的状况(Delaney 1986)。Combs-Schilling通过对历史上控制亲属关系、初婚和每年朝觐期间的献牲仪式,分析了男性权威习惯的产生。开始于16世纪,伴随着从摩洛哥到欧洲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转变,摩洛哥君主政体攫取了权力的核心象征符号——血统和交往,保证了王室的权力,通过拉拢王室家族成员参与权力中心,同时使女性和年少的男性受缚于年长男性的控制之下,从而对缺乏实际霸权予以补偿。“《古兰经》中关于伊布拉欣的故事和穆罕默德有关宰牲的教导,帮助在伊斯兰文化阵营中建立父权制和父系的统治……有力地巩固了父亲对儿子、长者对幼者、所有男性对女性和儿童的合理支配权。”(Combs-Schilling 1989:57)
Bowen(1992b)批评这种实在论的观点,认为印度尼西亚有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教性别和权力观,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对献牲和男女性别意义的不同解读。正如Eickelman(1989)指出,Mernissi(1987)或Bouhdiba(1985)这样的学者,暗示穆斯林对性角色和两性关系具有独特的、定义清楚的解读,这种观点无论从单一社会或没有背景的文学作品来理解都过于笼统。Fernea(1985)和Fernea,Bezirgan(1977)搜集的作品是过去对穆斯林妇女刻板描绘的有益创新。
Lila Abu-Lughod(1993b,1993c),Boddy(1989),Delaney(1991),Holy(1988,1991),Nancy Tapper(1990),Tapper and Tapper(1987),Rasmussen(1991)讨论了一些穆斯林社会宗教工作的性别分界。在他们有影响的作品中,Tapper and Tapper(1987)强调在不同穆斯林社区中就性别和宗教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通过研究男性和女性接近某种仪式的不同方式得出结论(经常在死亡或生命危机时才背诵纪念穆罕默德诞生的诗篇),他们:
并不认为妇女和男子一定拥有端庄的信仰和实践系统……但宗教体系的不同方面可能是一种性别或另一种性别领域,理解任何一种特殊的伊斯兰传统有赖于对两者都进行检验……我们一方面认为男子每日遵守外在的正统毫无疑义,另一方面主张妇女的宗教生活没有男子重要或处于男子的边缘,这是不对的。妇女不仅恪守重要的日常宗教功课,而且在她们的履行中附带着宗教重担,对社会常常有比男子更加超凡的重要性。(72)
Holy对苏丹妇女礼仪社会重要性的分析,Boddy对精神自制,Abu-Lughod对哀悼仪式的研究认为,男女仪式工作的区别可以形成相互依赖性,妇女的仪式表达了心理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方面,伊斯兰教的象征不适中或过于保守,甚至这种分野会导致伊斯兰关注的与霸权有关的妇女地位降低(l.Abu-Lughod 1993b,1993c)。Friedl(1980)和Ong(1990)一方面扩大到伊斯兰神学和实践关系领域,另一方面关注构成社会秩序的妇女关系。Ong特别调查了在快速变化的经济和政治语境中,如何用宗教思想加强性别不平等和家庭认同中男性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迄今为止,对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研究在人类学研究领域是最小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对伊斯兰教仪式的研究就相对缺乏(Martin 1985)。最近,人类学家才找到有效处理伊斯兰教仪式的方法,从理论上同性别、权力观念、代表新旧文化方向的两种政治争论,或他们对建立一般的实践方向所做的贡献联系起来(Bourdieu 1977; L.Abu-Lughod 1989)。
除了上文提到的Antoun和Gaffney对主麻聚礼活动的研究外,Bowen(1989),Horvatich(1992),Rasmussen(1991),Starrett(1993)研究了要求穆斯林正式聚众礼拜的不同意义。Abu-Zahra(1988)关注了传统祈祷,雨中祈祷的特殊形式。
朝觐和旅行的重要性最近也得到很大关注(Eickelman and Piscatori 1990),特别是通过观察其性别符号(Delaney 1990,1991; Young 1993)以及创立关于朝觐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竞争视野(Fischer and Abedi 1990)。Bowen(1992b),Woodward(1988)和Combs-Schilling(1989)分析了献牲和仪式的物品。(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有很多对献牲的有趣的讨论,读William Robertson Smith 1956)。
此外,Starrett(1991)和Peacock(1978)讨论了人一生的仪式,L.Abu-Lughod(1993b),Ahmed(1986),Antoun(1989),Bowen(1984)论述了有关死亡、葬礼和哀悼的仪式和信仰,Haddad和Smith(1981)从文本回顾了仪式。Fischer和Abedi(1990)描述了什叶派哀悼侯赛因(Husayn)的特殊仪式。
马强,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马强(1972-),男,回族,宁夏西吉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副教授 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人类学和伊斯兰文化研究。
注释:
①本文选自Stephen D.Glazier编著的.宗教人类学手册[M].格林武德出版社(Greenwood Press),1997。作者Gregory Starrett是北卡罗莱纳大学人类学副教授,1992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标签: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穆斯林论文; 古兰经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