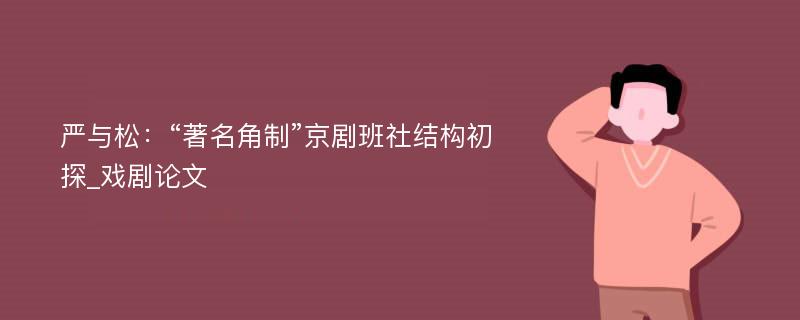
森严与松散:“名角制”京剧班社结构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角论文,森严论文,松散论文,京剧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名角制”指的是以名角作为班社组织和运营核心的班社体制,它是京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京剧班社区别于传统的昆班、徽班和其他地方戏剧班社的主要差异所在。中国传统戏剧自南宋戏文至传奇之大成,由生、旦、净、末、丑五门脚色为基础而交互作用的体制——“脚色制”逐渐发展成熟,成为“我国传统戏剧的文学剧本结构、场上艺术表现结构、班社建制结构的凝聚点”①。在“脚色制”班社中,演员按照所属脚色相区别,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彼此之间对等互补,并无地位高下之分,这是一种组织稳定、流动性较低的班社建制结构。
尽管京剧艺术直接承袭自“脚色制”的徽班,京剧班社体制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之后,最终形成了与之根本相异的“名角制”。在京剧班社的前身进京徽班中,“脚色制”逐渐瓦解,演员之间对等互补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名角在班社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作用日益增强。延至清末,名角逐渐成为京剧班社组织和运营的核心。以光绪十三年(1887)谭鑫培等人组织同春班为标志,“脚色制”开始为“名角制”这一全新的班社组织形式所取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名角纷纷挑班,“名角制”已经成为京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
戏剧班社是承载戏剧艺术的物质实体,正如与“脚色制”相适应的是明清传奇的舞台艺术,深入分析“名角制”京剧班社结构,也将是我们理解京剧的艺术构成和艺术规律的有效途径。笔者认为,相对于以往的研究多偏重描述一时一地京剧班社的具体现象,深入探讨“名角制”京剧班社的一般性结构特征,可能是更重要也更困难的工作。在此一般性特征的基础上,进而比较北京、上海等地“名角制”的不同表现,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京剧艺术中“京朝派”和“海派”的差异。
一
在“名角制”京剧班社中,名角居于班社组织和运营核心的地位,名角和其他演员之间呈现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这是“名角制”京剧班社区别于传统的“脚色制”班社的最大差异。
作为一种班社建制结构,“脚色制”的基本特征是每一门脚色都有特定的性能、技能和功能,在剧中所扮演人物的性格、所运用的表演技艺、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有定规;各门脚色在班中的地位是对等互补的,演员不论其工于哪门脚色,也不论其有名与否,都可以在某些戏或某场戏中为主角,在某些戏或某场戏中为配角,班中没有专门跑龙套的演员。宋元以来的“七子班”、“八仙子弟”、“九脚头”、“十门齐全”、“江湖十二脚色”等,都是如此。即使由于演员先天禀赋和后天修炼的差异,技艺必然有高下,一部分较为优秀的演员可能赢得较大的声名,然而在班规的制约之下,他们并不能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名角,所谓“艺有高低而戏无参差,名有大小而人无贵贱”②。而在“名角制”京剧班社中,演员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脚色之间互相协调、互相制约的平衡被打破,而代之以一种以名角为中心,从头路、二路、三路直至龙套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
位于这个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是名角,也称头牌,多属老生和旦,偶有以武生、花脸和小生、丑挑班者。这是因为名角既为班社组织和运营的核心,在一切演出剧目中也居于主角,这在各门脚色中发展最充分的老生和旦自然并不困难,而武生、花脸、小生和丑却缺少足够多的以该门脚色为主角的剧目。因此,若老生和旦以外的演员作为名角挑班,大多持续时间不长,或者须不断编演新剧勉力支撑。以武生挑班而时间最久的当推杨小楼,自清末以迄1938年逝世前,前后约有三十年,论者以为“不能谓非异数”③。而花脸金少山自1937年由沪返京,自组松竹社,挑班挂头牌,前后共贴演二十几出传统剧目,因其懒于排演新戏,未几年已渐趋潦倒。
头牌以下是二牌和三牌演员,头牌、二牌和三牌总称为头路。如果头牌是老生,则以旦脚挂二牌,武生挂三牌;如果以旦角挑班,则以老生挂二牌,武生挂三牌;如果挑班名角是武生,则二牌一般是花脸,旦脚挂三牌。挂二牌、三牌的演员主要为名角配戏,行话叫做“挎刀”,意谓“挎刀保驾”。他们必须熟悉头牌的师承、戏路、唱念的尺寸、场上的位置,揣摩头牌的需要,在配戏的时候才能够严丝合缝,充分发挥烘云托月的作用。1935年、1936年,奚啸伯两次陪梅兰芳去武汉、上海、香港、天津等地演出,可谓称职的二牌老生:
啸伯与梅挂二牌时,为用心研究梅台上需要,必充分供给,使梅能得到满意。如生旦唱对口时,打鼓人或将尺寸起得与梅平时唱的不合适,必能由奚将尺寸唱好,使梅接唱时十分合适,故梅对啸伯极表满意,愿同啸伯合演。此为挂二牌之难,因二牌者,必须揣磋头牌之满意及需要,方能合演长久。如今之二牌,则不能如从先挂二牌者之虚心也。倘头牌之需要,而二牌并不供给,使头牌永远感觉同演之不合适,何能长久耶?④
正因为二牌、三牌演员都必须服从名角的需要,与名角的表演取得一致,而各个京剧班社的名角在剧目、戏路方面又有不同,因此演员搭班之前所学的东西,未必都能用上,所以就有重新学习的问题。旧时戏班有一句谚语:“搭班如投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头路演员以下是二路演员,一般包括老生、旦、净、武生、丑各二三人,老旦、小生、武旦、武丑各一二人。二路演员在演出中多扮演地位较重要的配角,以辅佐头路演员。也有名角非常倚重的二路演员,如荀慧生的留香社中,金仲仁(小生)、马富禄(丑)、芙蓉草(旦)、张春彦(老生)称为“四大金刚”。杨小楼之有迟月亭、钱金福、钱宝森、王长林、王福山、范宝亭、许德义、傅小山、刘砚亭等演员追随多年,武戏才显得出色。
二路演员以下是三路演员,同样包括生、旦、净、丑各个家门,他们在演出中扮演次要的配角,为头路、二路演员服务。三路演员数量较多,按照齐如山先生的统计:“每班须用老生七八人,旦行十余人,净行六七人,小生二三人,老旦一二人,丑行四五人,武生二三人,武旦二三人,盖非有此数,不敷调遣。”⑤
三路演员以下是龙套。龙套是京剧班社中扮演士兵夫役等随从人员及群众的演员的统称。龙套一般不以个人为单位,而以四人为一堂,分头、二、三、四家(或头、二、三、四旗),以头家为带头人,在舞台上用一堂或两堂龙套,以示人员众多,起烘托声势的作用。在“脚色制”班社中,再次要的剧中人物,照规矩也派给各门脚色,班中没有专门跑龙套的演员。周传瑛回忆昆剧“传”字班:“不管你造诣有多高,声誉有多大,在台上(或说在老郎菩萨面前)大家都一样,人人要做‘小搭头’跑跑龙套。”⑥作为独立成行的龙套,是在“名角制”京剧班社中出现的。
这样,从名角到头路演员、二路演员、三路演员以至龙套,“名角制”京剧班社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演员结构。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关系,最突出地体现在演出剧目的先后顺序和主次搭配上。和“脚色制”的昆班、徽班相比,其中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脚色制”班社中演员地位平等,演出剧目以内容区分前后,对于每个演员来说,顺序是不固定的。如苏州昆班之一的全福班,“每天戏目的安排,大致是纱帽生戏开场,其次老生戏、大花面戏、小生戏、二面戏,最后压台的总是一部传奇里凑成四五出比较轻松有趣的戏,譬如《金雀记》的《觅花、庵会、乔醋、醉圆》,《风筝误》的《惊丑、前亲、逼亲、后亲》。”⑦到了“名角制”班社中,剧目的先后则取决于演员在班中的地位。一般来说,挂头牌的名角总是演大轴;二牌演员演压轴,或是在大轴为头牌配戏;三牌演员演倒第三,或是在大轴、压轴为头牌、二牌配戏;二路及以下演员依次往前推。
名角出于私交,或者作为一种拉拢手段,偶尔会让二牌演员唱大轴,或者为二牌演员配戏。这种行为并非兴之所至的率意之举,其中的意义必然使双方都郑重对待。1913年,梅兰芳初次随王凤卿赴沪演出于丹桂第一台,挂二牌,戏码列压轴,很受上海观众欢迎。王凤卿遂提议让梅兰芳唱一次压台戏(相当于北京的大轴戏),并“约定以后永远合作下去”。梅兰芳认为“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拿什么戏来压台,可以使观众听了满意,这真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了”⑧。后来听取冯幼伟、李释戡等人的建议,特别新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1941年前后,程砚秋挑班的秋声社演出于新新戏院,大轴《四郎探母》由二牌老生王少楼主演杨四郎,程砚秋为他配演铁镜公主;另外一次,程砚秋压轴与张春彦合演《三击掌》,大轴是王少楼的《珠帘寨》,程砚秋为他配演二皇娘。论者认为:“他这样捧法,王少楼自然死心塌地、忠心保国的为他唱二牌老生了。”⑨
在等级森严的“名角制”班社中,演出剧目的前后顺序和主次搭配,都关乎演员名分,不容参差。偶有排列不甚妥当,演员会认为自身地位受到轻慢或威胁,激烈者竟至辞班。1925年秋,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老生言菊朋挂二牌。12月3日,协庆社在三庆园夜戏,尚小云、侯喜瑞、朱素云、范宝亭、尚富霞演出大轴《红绡》;为增强阵容,邀请老生谭小培与王长林演出《天雷报》,码列压轴;而言菊朋与尚富霞的《胭脂虎》派在倒第三。言菊朋认为此举严重侮辱其名誉地位,当晚演出结束,立即辞班。1930年,言菊朋以二牌老生的身份搭入杨小楼挑班的永胜社,二牌旦角为新艳秋。3月1日永胜社在开明戏院夜戏,大轴是杨小楼、钱金福的《铁笼山》,压轴是新艳秋、王又荃、文亮臣合演《鸳鸯冢》,而言菊朋的《上天台》列倒第三。言菊朋演完该场,又一次因戏码先后之故辞班。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杨小楼挑班的永胜社,1928年11月底永胜社贴演《状元印》,按照演员在班中的等级,应由许德义饰演赤福寿一角,管事刘砚芳却派了他的哥哥、地位较低的刘砚亭出演。结果许德义极为愤慨,当场报复,把杨小楼的盔头掭了,制造了严重的演出事故。言、许的行为虽不能说和个人脾性全无关系,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却是“名角制”等级森严的特点所决定的。在当时人眼中,剧目先后、主次颠倒是破坏规矩,而他们的行为却属于可以理解甚至同情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中,中国传统戏剧“脚色”的意义已经被置换。以老生而论,对于戏剧人物来说,它是在性别(男性)、年龄(中年以上)、性格(正直刚毅为主)、作用(正面)等方面区别于其他的一类人物;对于戏剧演员来说,它是以一整套独特的舞台技艺(重唱工、用真嗓、念韵白、做打庄重端方)区别于其他的一类演员。而在“名角制”京剧班社中,头路老生扮演剧中主角,里子老生扮演剧中配角,底包老生则扮演牙将、朝官、旗牌、家院、苍头、百姓之类人物。这是对演员等级的一种划分,而不复区分角色性质和舞台技艺,因而它们并不是中国传统戏剧“脚色”的性质。“脚色”之间互相依附、互相制约的力量,对于“名角制”京剧班社的演员来说,虽不能说消弭于无形,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
二
“名角制”京剧班社等级森严的特点,很容易给人班社组织严密而稳定的印象,事实却恰恰相反。在传统的“脚色制”班社中,每个演员都担负特定的职能,都是班社中不可或缺的,因此班规特别强调“忌在班思班”、“忌背班逃走”,演员一旦加入某班,流动性很低,一般不能轻易改搭他班,从而保证了班社的正常稳定的运营。而“名角制”京剧班社以等级排列演员,脚色之间互相依附、互相制约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因此,这一班社结构就表现出另一个基本特征:流动频繁、组织松散。
“名角制”京剧班社组织松散的特点,首先可以从经励科的出现得到印证。在经励科出现之前,京剧班社中最主要的管理人员称为管事,他主要负责班社的内政。民国以后,京剧班社中管事这个名称虽然没有消失,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却已经为经励科所取代。以往的相关研究论著往往将经励科与管事混为一谈,事实上,经励科和管事的性质是不同的,他们的职能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经励科最重要的职能是邀角组班,充当演出经纪人的角色。他们需要熟悉演员,了解观众,知道哪位演员的什么剧目能叫座,和戏园、税警机关、报馆等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才能出面组班,以某某班社的名义,招兵买马,罗致演员演出。一些经励科本身即从事戏园业,如二三十年代北京的经励科以前门大街为界,马路东为“东半边”,马路西为“西半边”。东半边指的是万子和、刘铁林两家,他们掌握的剧场是华乐园。西半边是赵砚奎、佟瑞三,他们掌握的剧场是三庆、开明、中和园和长安大戏院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励科是独立于京剧班社的,和京剧班社不存在稳定的隶属关系。只有在成功组班之后,留在班社管理内务的经励科,才略同于管事的职能。由于传统的“脚色制”班社人员稳定,并不需要这类邀角组班的经纪人,从根本上说,经励科是在“名角制”成为京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之后才产生的,是“名角制”这种组织松散的班社体制之产物。
“名角制”京剧班社组织松散的特点,更显著地表现在班中演职人员的频繁流动上。对于京剧班社中的名角而言,受外地戏园之邀而跑码头流动演出,自清末至民国日趋频繁,其中尤以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济南等地为盛,北京的名角没有不跑这些码头的。这是因为“头牌演员在北平演出,一周只有两三次,只够维持开支,盈余有限;就指着跑外码头赚大钱,顶好一年能多出几次门最好”⑩。程砚秋在挑班鸣和社期间,从成立的次年1926年以迄1937年4月改组秋声社,除却赴欧洲考察的一年六个月,先后七次赴上海演出于共舞台、荣记大舞台、天蟾舞台和黄金大戏院,几乎是一年一次,并多次赴济南、沈阳、哈尔滨、南京、重庆、成都、长沙、汉口、开封、香港等地演出。另一方面,对于上海等地的名角而言,如果能够在京剧发祥地的北京站稳脚跟,才有可能摆脱“外江”恶谥而归入“京朝”正统。宣统三年(1911)花旦贾璧云进京搭三庆班,“声名之盛,冠绝一时,豪贵招邀,盖无虚日”(11)。1912年、1914年、1921年,武生盖叫天三次进京,演出于文明园、吉祥园、第一舞台。
“名角制”京剧班社的“跑码头”和宋元以来“脚色制”班社的“冲州撞府”有明显相异之处。它不是后者那样的整个班社的活动,而是由名角带上若干主要配角(一般是京剧班社中的二牌、三牌和个别二路演员),以及各自的琴师、鼓师、检场、梳头、跟包等人,组成一个私房小团体而脱离班社流动演出。谭鑫培曾在光绪五年(1879)、光绪十年(1884)、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统二年(1910)、1912年和1915年六次赴沪,分别演出于金桂园、丹桂园、云仙园、新舞台、新新舞台等戏园。其中1912年偕花脸金秀山、武二花金少山、青衫孙怡云、小生德珺如、老旦文蓉寿、小丑慈瑞泉等同行,已属“伶界大王”的特别阵容。1913年、1914年,上海丹桂第一台进京邀角,都只有王凤卿、梅兰芳二人,王挂头牌,梅挂二牌。1916年,梅兰芳第三次赴沪演出,改挂头牌,王凤卿挂二牌,除了琴师和鼓师之外,演员只加入小生姜妙香和花旦姚玉芙。这种小规模的跑码头,成为清末以来半个世纪京剧班社营业戏演出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名角制”班社松散性结构的集中表现。
除了名角之外,其他演职人员一般可以同时搭多个班社,同样表现出很大的流动性和松散性。从“脚色制”的徽班到“名角制”京剧班社,这一变化是很显著的。张次溪《近六十年故都梨园之变迁》有云:
往者四大徽班,皆有一下处之设(亦曰总寓)。凡无家口而隶于此班者,皆住宿其中,即不演戏之时,衣食亦告无缺。遇有疾病死亡,其一切费用,悉归班中开支,法至善也。故其时一人之终身隶于一班者,所在皆是。同、光以来,戏班屡有变动,本在此班者,因戏班改组,可以改搭他班,然定例亦只许搭入一班,不准同时更搭他班演唱。从未有若今日一个净角、小生、丑角等,一日内可以赶数个戏园子也。(12)
民国以后,随着“名角制”成为京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除了名角之外,一般演员已经鲜有专搭一个班社的了。老生谭富英在1924年至1925年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游击政策,陆续搭了徐碧云、朱琴心、杨小楼、荀慧生等人的班社,连武生马德成的临时班,都插上一脚。1930年,郝寿臣同时搭杨小楼的永胜社、马连良的扶风社、高庆奎的庆胜社、程砚秋的鸣和社、朱琴心与吴铁庵的忠信社,一共五个班子。老生李洪春在《京剧长谈》中也说:“那时演员不像现在固定在一个剧团中,除新编剧目需要排练以外,其他老戏都是‘台上见’。只要不耽误场上的演出,你参加几个剧团也没人管。我不但参加了高庆奎的‘庆兴社’演出,而且又参加王又宸、黄玉麟(绿牡丹)、朱琴心等几个剧团同时演出。”(13)他和武净侯喜瑞曾在华乐戏院演《打严嵩》,一个邹应龙、一个严嵩;接着赶往吉祥戏院唱《下河东》,分饰呼延寿、欧阳芳;随后返回华乐戏院演《反西凉》,李的马超、侯的曹操;最后到开明戏院陪高庆奎唱《失空斩》,一个王平、一个马谡。由于演员和戏班不再有长期稳定的隶属关系,演出收入也由原来按年计算的“包银”改为按日计算的“戏份”,演员演出一日,便领取一日的戏份,同时搭多个戏班赶场演出,就可以领取多份戏份。
更为奇特的是,龙套逐渐脱离班社,成为可供不同班社租用的独立组织。由于龙套通常以一人为头目,代表同人与戏班接洽,代领戏份,因此龙套头可以舞弊,比如领取三堂十二人的戏份,而实际只用两堂,便可中饱私囊,一旦有临时的需要,就向别班借调。在这种情形下逐渐产生了独立的龙套头,管辖有为数众多的龙套,各戏班根据演出需要向其租用,由此龙套于京剧班社的隶属关系转变为租赁关系。北京著名的“流行头儿”施启沅,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联络众多菜贩、轿夫等贫民,加以训练,使其掌握龙套的舞台走形,并从中培养出能够独当一面的分支头目,从而建立起一个以他为首的龙套组织网络,专门承接各戏园的跑龙套业务。
这样,通过经励科或类似的经纪人邀角组班,“名角制”京剧班社演员的流动非常频繁,头路演员可以跑码头,二路、三路演员可以搭多个班社,龙套则成为可供各个班社租用的独立行当。而对于“名角制”京剧班社的场面和后台人员来说,他们最大的变化则是其中一部分由原来隶属于班社转为依附演员个人。
场面指的是京剧班社中的乐队伴奏人员,最初一般为六人,包括文场(管弦乐器)的京胡、月琴、三弦,武场(打击乐器)的鼓板、大锣、小锣。随着京剧音乐的不断发展,京剧的伴奏乐器也日趋丰富,场面的人数也随之增加至每班二十人左右,一般包括胡琴三四人,鼓板三四人,弦子、月琴、大锣、小锣、笛、笙各二人。在“脚色制”班社中,场面为全班共用。三庆班班主、大老板程长庚虽然“以章圃司鼓、桂芬操琴,为自用场面之渐,然皆隶本班,初非为一人专设”(14)。京剧班社名角自带场面,可以追溯至光绪二十三年(1896),谭鑫培通过宫中总管太监明心刘、祥五等人介绍,私人聘请场面,包括鼓师李五、琴师孙佐臣(后换梅雨田)、小锣汪子良、月琴浦长海、弦子锡子刚等。在“名角制”取代“脚色制”成为京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之后,名角自带场面成为惯例,而由班中聘定公用的场面人数则减少。
私房场面与官中场面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隶属于班社,而是依附于名角个人、只为名角服务的,他们的酬劳不是由京剧班社或戏园支付,而是由名角个人支付。名角的“私房”场面中,以琴师、鼓师为最要紧,如徐兰沅、王少卿之于梅兰芳,穆铁芬、周长华之于程砚秋,杨宝忠、李慕良之于马连良,李佩卿之于余叔岩,高联奎之于高庆奎,王瑞芝之于孟小冬,杨宝忠之于杨宝森,赵济羹之于谭富英,陈鸿寿之于王少楼等等。除了在北京演出,名角到各地跑码头时,这些“私房”场面一般也会随行。
“名角制”京剧班社中的后台人员情形和场面颇为类似。据齐如山先生《戏班》一书中所列,京剧班社中的后台人员主要包括:管衣箱人、管盔箱人、梳头人、管旗包箱人、管后场桌人、检场人、打门帘人、催戏人、管彩匣人、管水锅人、扛砌末人、查堂人、司账人,等等。在“名角制”成为京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之后,部分后台人员不再隶属于班社,为全班演员服务,而成为依附于名角个人的私人助理,最典型的就是跟包。跟包原意是“跟行头包”,由于二路以上演员都须自备私房行头,因此演戏之前须由专人将行头送到戏园。后来跟包也协助管衣箱人扮戏,以及携带暖水壶并帮助饮场,种种诸如此类的事宜,因此名角所用跟包往往不止一人。如果说雇佣跟包的门槛还不太高,专门的检场人则只有名角才有能力雇用。如谭鑫培的跟包、检场都是自带,“所以每逢谭一上场,上下场门,总是立着三四个人,都有得意之色”(15)。此外,讲究扮相的旦脚,一般都有专门的梳头人,如长期为梅兰芳梳头的韩佩亭等。
从名角到龙套,从场面到后台人员,“名角制”京剧班社成员对于班社的隶属关系都是非常松散的,正如有论者指出:“夫社者,聚会结社之意,演时则聚,演罢则散,此今日戏社之情形也。”(16)此时,整体的京剧班社实际已趋于瓦解。
三
作为京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名角制”虽然具有等级森严和组织松散的一般性结构特征,然而由于京剧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名角制”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域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班主负责型”、“名角负责型”和“园主负责型”。其中,北京的“名角制”京剧班社主要是“班主负责型”和“名角负责型”,尤以后者为典型,而上海的京剧班社则基本都属于“园主负责型”。
以“班主负责型”组织的“名角制”班社,是由名角以外的一人或数人出资组班,此一人或数人即为班主。班主可以是梨园行以外的富商大贾,这种情况下,他一般只对京剧班社的财务负责,并不过问班社内务,具体的组织、运营事项都由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也有班主本身从事梨园行,并在班中担任演员的,如田际云组织的玉成班(后改翊文社)、俞振庭组织的双庆社、朱幼芬组织的桐馨社等。由清末至民初,京剧班社越来越倚仗名角的作用,班主往往聘请名角作为班社的头牌,或者专门为某一两位名角组班。1914年梅兰芳第二次赴沪演出时,双庆社班主俞振庭专程南下邀约,才使梅兰芳脱离翊文社,改在双庆社挂头牌。1917年,由于约请到谭鑫培,双庆社班主俞振庭特意为此新组春合社,因为“谭老板的晚年不常露演,每演也不过几天,谁要能够邀到他,就用一个无主的旧班社的名义,先向‘正乐育化会’申报开业。其余的角色,临时再向各方面邀请”(17)。1919年,姚佩兰、王毓楼组织喜群社,梅兰芳挂头牌;1921年,刘砚芳、姚玉芙组织崇林社,杨小楼、梅兰芳挂头牌,都是为名角组班的典型例子(18)。
民国以后,随着“名角制”成为京剧班社的主要组织形式,一种新的组班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即名角自己出资组班,自挂头牌,并集班社的财政、人事、业务、外联等大权于一身,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最典型的“名角制”班社——“名角负责型”。杨小楼挑班的陶咏社、中兴社、松庆社、双胜社、忠庆社、永胜社,金少山挑班的松竹社,余叔岩挑班的云胜社,言菊朋挑班的民兴社、咏评社、宝桂社,高庆奎挑班的庆兴社、玉华社、庆盛社,梅兰芳挑班的承华社,周信芳挑班的移风社,尚小云挑班的玉华社、协庆社,荀慧生挑班的留香社,马连良挑班的春福社、扶风社,程砚秋挑班的鸣和社、秋声社,徐碧云挑班的云庆社,谭富英挑班的扶春社、同庆社,杨宝森挑班的宝兴社,李万春挑班的永春社,叶盛章挑班的金升社,李少春挑班的群庆社,张君秋挑班的谦和社等等,都是“名角负责型”的班社,名角即为班主。
一般来说,“班主负责型”和“名角负责型”在北京的京剧班社中较为常见,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大多实行戏班、戏园一体,前后台统一管理的制度,戏园的园主(或承租人)即是京剧班社的班主,如上海的许少卿、尤鸿卿、吴性栽、周剑星、孙兰亭、金廷荪、顾竹轩,天津的李华亭、孟少宸,沈阳的何玉莽、于德宝、于德瑞等。尽管京剧班社以戏园为单位,但其中名角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日益凸显。自清末以来,各戏园老板除了雇佣一部分演员组成较为稳定的班底长期演出外,同时不断聘请名角挂头牌短期演出,由此形成名角/班底的格局,这是“名角制”另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上海的丹桂第一台、天蟾舞台、黄金大戏院、共舞台等,天津的北洋戏院、新明戏院、中国大戏院等,南京的贡舞台、世界剧场、中央大舞台、南京大戏院等,都是采取这种流动名角和固定班底相结合的班社体制。
比较“名角制”的这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就等级森严的程度而言,“名角负责型”显然是最高的。因为名角自己成为老板而不再是班主或戏园园主的雇员,其地位和自主权不受他人制约,避免了在卖座不佳的情况下受到班主或戏园园主的掣肘。相对而言,“园主负责型”中的等级划分较不明显,名角之于戏园,如行人之于逆旅。尽管戏园方面一般对于远道而来的名角极为礼遇,但是名角在宣传和交际等方面都必须仰仗戏园,加之短期演出的性质,一般都尽量和戏园以及班底演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不特别彰显自己的地位。固定班底演员虽然有优劣之分,也不像“名角负责型”那样严格划分等级,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脚色之间对等互补的传统。
在人员流动性方面,“园主负责型”同样较“班主负责型”和“名角负责型”弱。除了经常邀请名角挂头牌短期演出之外,“园主负责型”京剧班社的班底演员一般来说比较稳定,演员大多隶属于某一个戏园,按月计算演出收入,除非因某种原因跳槽去其他戏园,一般较少同时在几个戏园搭班演出。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应邀赴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时,该园的班底演员有武生盖叫天、杨瑞亭、张德俊,老生小杨月楼、八岁红(刘汉臣),还有双阔亭,花脸刘寿峰、郎德山、冯志奎,小生有朱素云、陈嘉祥,花旦有粉菊花、月月红等,阵容非常整齐。1914年第二次去的时候,丹桂第一台班底演员有一些变化,少了武生杨瑞亭、老生小杨月楼和八岁红、花旦粉菊花和月月红,增加了花旦赵君玉、老生贵俊卿和红生三麻子,其他演员都没有变动,且并不同时在其他戏园演出。
这种不同类型的“名角制”之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京剧艺术的风格,如我们习惯上称为“京朝派”和“海派”的不同表现,正是和这两个地区京剧班社结构相适应的。在京剧班社结构多采用“班主负责型”、尤其是“名角负责型”的北京地区,“名角制”等级森严和组织松散的特点得到了最典型的表现。“京朝派”演员更看重的是通过提高个人技艺,在班社的金字塔结构中不断提升,逐渐居于更高的地位,并获取与之相应的更高的收入。因此,“京朝派”演员在唱念做打等个人技艺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往往是“海派”演员所难以企及的。
另一方面,正因为在这种班社结构中,角色主次和剧目先后都必须按演员等级严格排列,演员和观众都更多注目于个人技艺的展示而较少关注戏剧的整体呈现,因此,一些需要各门脚色通力合作的老戏,像《法门寺》、《龙凤呈祥》等,一般京剧班社都不常演,只有在集合众多演员的义务戏中才比较常见,而像三庆班的全本《三国志》等戏,就逐渐成为冷戏,甚至逐渐失传。民国时期,名角竞相编排本戏,剧评家张肖伧注意到:
北平京朝派名角的编排本戏,其剧本的编制,都以主角一人为重。梅兰芳的戏,当然在梅剧中,千篇一律惟梅独尊,而其余一切的剧中人物,都列于配角和零碎的份儿。其余程砚秋编的戏,也是如此;荀慧生、尚小云编的戏,依然如此;朱琴心、徐碧云编的戏,何尝不是如此?……你如要想以后梅程荀尚以及马连良辈能编出一种好戏,仿佛与旧戏里的《群英会》的各种角色表演出来,铢两悉称,毫不偏重,是千万不容易得见的了。(19)
相对而言,上海京剧班社编演的新戏不似“京朝派”突出名角的地位和作用,而更加注重戏剧的整体呈现。这些“园主负责型”京剧班社的演员较为稳定,等级不像北京那么森严,彼此之间较容易通力合作。加之这些演员并不同时搭多个戏班,所属戏园的卖座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计,园主为营业计,常常可以集合全班力量编演新戏,其中尤以连台本戏最具“海派”特色。
连台本戏并不是上海戏园的首创,事实上,四大徽班时期就编排了不少连台本戏,如三庆班的《取南郡》,四喜班的《雁门关》、《五彩舆》,春台班的《混元盒》、《铡判官》,以及福寿班的《粉妆楼》、《施公案》、《儿女英雄传》等等。当京剧班社体制发生变化,这种需要短则数天、长则竞月逐日排演,剧中人物繁多且难以排列主次,以情节取胜而较难凸显技艺的剧目,显然已经不适应等级森严而组织松散的新的班社结构。连台本戏只能产生在演员相对平等、组织较为稳定的班社中,“园主负责型”京剧班社显然比“班主负责型”或“名角负责型”京剧班社更具备这个条件。清末以迄民国,当上海的戏园园主感到邀请名角的投资收益率太低时,编演连台本戏就成为一时的风尚,如丹桂茶园的《五彩舆》、《左公平西》,天仙茶园的《铁公鸡》、《绿牡丹》、《九美夺夫》,新舞台的《济公活佛》,大舞台的《西游记》、《封神榜》、《神怪剑侠传》、《荒江女侠》等,甚至天蟾舞台、丹桂第一台、大舞台和世界乾坤剧场等四个戏园同时演出《狸猫换太子》,以奇幻剧情和灯光布景争奇斗胜。连台本戏的艺术价值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社会文化环境之外,班社结构的差异也造成了“京朝派”重技艺求精,而“海派”则重情节出新。
当然,不管是“班主负责型”、“名角负责型”还是“园主负责型”,都只是“名角制”京剧班社的不同形式,名角作为班社组织和运营核心的地位没有本质区别。在1949年以后的“戏改”中,原有的“名角制”京剧班社被合并、改组成民营公助剧团,并逐渐过渡为国营剧团。在演出方面,这些新成立的京剧院团设有专职编导人员,建立起从西方引进的导演制。“名角制”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作为长期承载京剧艺术的物质实体,它对京剧艺术本身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消弭。认识到“名角制”京剧班社等级森严和组织松散的基本特征,对于京剧的艺术构成和艺术规律,尤其是它区别于传统“脚色制”班社的特殊舞台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①洛地:《“一正众外”、“一角众脚”——元曲杂剧为“正外制”论》,《洛地戏曲论集》,台北:“国家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②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昆剧生涯六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③丁秉鐩:《菊坛旧闻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第99页。
④《名伶访问记——奚啸伯》,《立言画刊》第158期,1941年10月4日。
⑤齐如山:《戏班》,北平国剧学会,1935年,第6页。
⑥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昆剧生涯六十年》,第40页。
⑦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4页。
⑧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第134页。
⑨丁秉鐩:《菊坛旧闻录》,第220页。
⑩丁秉鐩:《菊坛旧闻录》,第430页。
(11)罗瘿公:《菊部丛谈》,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785页。
(12)张次溪:《近六十年故都梨园之变迁》,《剧学月刊》3卷7期,1934年7月。
(13)李洪春:《京剧长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80页。
(14)陈彦衡:《旧剧丛谈》,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866页。
(15)齐如山:《戏界小掌故》,《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459页。
(16)张次溪:《近六十年故都梨园之变迁》,《剧学月刊》3卷7期,1934年7月。
(17)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第452页。
(18)梅兰芳乳名群子,故班名喜群社;杨小楼、梅兰芳姓字皆从木,故班名崇林社,由此亦可见其为名角组班之初衷。
(19)张肖伧:《皮黄的将来》,《戏剧旬刊》193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