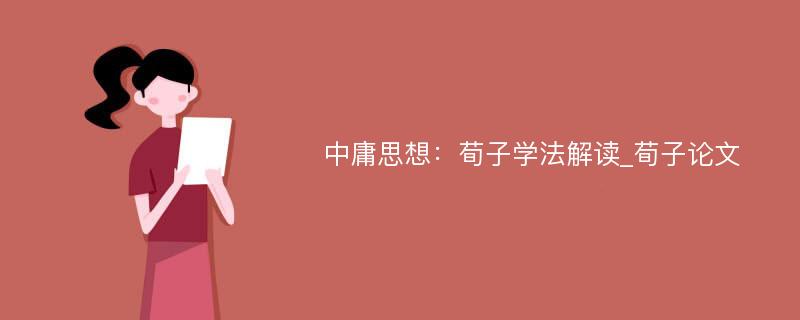
中庸思想:荀學進路的詮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庸论文,思想论文,荀學進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宋明儒以孟學進路爲主的深入詮釋下,《禮記·中庸》被编入《四書》,成爲孔孟儒學的核心經典。此後一直到今天,在一般的印象裹,《中庸》的孟學性格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然而必須注意到,在這個脉絡之外,至少鄭玄、孔穎達的《禮記注疏·中庸》、司馬光的《中庸廣義》、戴震的《中庸補注》,還有近代康有爲的《中庸注》和陳柱的《中庸注參》,以及日本學者安井衡的《中庸說》等,都是跟孟學不盡相同甚至大大不同的詮釋理路。當然,恰恰因爲這點,它們在過去不是被忽視就是被質疑、批駁。不過筆者認爲,如果改從荀學(或孟荀並重)的立場,以及從荀學的進路來檢視的話,它們或許就都可以得到比較正面、充分的理解與肯定。①
當代其實有若干學者論及《中庸》跟荀子的相關性,但他們通常以爲那只是個次要部份,或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前者如錢穆(150)說《中庸》“性善雖近孟子,其善言禮意卻近荀子”;戴君仁(236)說《中庸》“不僅是《孟子》,亦通乎荀學”,而畢竟與《荀子》道性惡异趣;胡志奎(35)說《中庸》“尤多掇取《論》、《孟》之語而入說”,不過“已有綜合道家乃至晚期儒家如荀子之言”。後者如佐藤將之(2009∶58、36),他强調“以‘誠’爲主要價值的《荀子》倫理學說,與《禮記》《中庸》後半以‘誠’爲主的倫理學說具有相同的思想立場”,主張“荀子的‘誠論’基本上應該是從《中庸》的‘化育萬物’的政治理論發展而成”。②
不管怎樣,《中庸》屬荀學,這個觀點在大批簡帛文獻出土、子思學派(以及思孟學派)具體浮現、子思作《中庸》(因而《中庸》屬孟學)的可能性大幅升高的今天似乎更顯得邊緣化了;不過,本文仍然要就這個觀點,整體地從荀學進路詮釋《中庸》思想。筆者的理由和基本想法如下:
第一,郭店楚簡出土以後,許多學者認爲它們都是或多半是思孟學派作品,並且據此推論《中庸》也是子思所作;但部份學者如李澤厚(8-9)仍然認爲它們整體上“更接近《禮記》及荀子”。在思想文本的學派歸屬上,不同的立場、價值觀本來就會導致不同的詮釋結果。宋明以來,以孟學爲標準來解讀和論斷儒家文本幾乎已經成了習慣。我們很難說目前《中庸》的孟學性格究竟是原來如此,還是先入爲主的詮釋所造成。既然《中庸》出自荀學色彩濃厚的《禮記》,它的文句、思想跟荀子有交集,尤其是郭店楚簡中並没有出現《中庸》一篇,因此《中庸》晚出並且屬荀學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我們能够對《中庸》做出另一個進路的詮釋,那麽《中庸》的思想性格就有重新論定的空間。
第二,荀子哲學縝密開闊,嚴整一貫。然而,在特殊時代情境的影響下,他幾個關鍵學說的表達太極端太特殊(如單單强調天人之分,如性惡,如禮義非人之本性);一般直接按著這些話語表層的意義脉络(傅偉勛所謂的“意謂”)來做各種相關的比較和研究其實未必準確,意義也有限。本文則以筆者(2011∶161-162)先前所建構所提議的“荀子哲學(所蘊涵)的普遍形式”爲參照,或許能揭示某些向來遮蔽、隱藏的面向,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第三,郭店楚簡出土以後,梁濤(266-278)、伍曉明(10-21)等對《中庸》的重組、分篇,基本上是根據其哲學詮釋的結果所提出的。而就筆者自己的詮釋來看,《中庸》全文的一貫性仍可成立,不須重組。可能的情况是,荀子的同時或之後(之前的可能性不大)的學者,基于荀學的立場和性格,選錄、编輯前人文句(可能包括思孟學派的文本在内),在上面做必要的改寫,並添加新撰部份而完成了《中庸》。這樣選錄、編輯、改寫、添加之後的整個文本,某個程度仍然可以看作一種立場一貫的荀學性格的撰著與創作。本文大致如此看待《中庸》。
一、引論:荀子哲學的普遍形式與孟子、荀子的“中”
先談荀子哲學的“普遍形式”。筆者(2011∶161-162)曾經依傅偉勛“創造的詮釋學”的構想,鬆解《荀子》的概念界定,參酌後代荀學(包括漢代儒學、明清自然氣本論)的理路,建構一個比較符合民族心理傾向、比較具有普遍意義、比較適合做爲參照標準的荀子哲學的“普遍形式”。這裹歸納爲最基本的兩點如下:
1.這世界起于有陰有陽的自然元氣。而在一氣流行的世界裹,天的運行有其常則,人事的變化有其常道,天、人之間既有連續又有差异,彼此是合中有分的關係。此外,天廣義地說是全世界,狹義地說則是自然元氣的集合;因此在必要時天也可以具有些許人格神義涵(雖然荀子反對這一點,但這點跟荀學性格並非截然對反,董仲舒思想就是一個例子)。
2.欲望、情感的自然表現固然是人性所涵有,但心的活動、努力的種種樣態與可能的結果也可以是人性所涵有。禮義其實就是事物、情感、欲望中“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的律則的提出與凝成(因此不在人性之外),它是天地内在之理的一環,並且可以随著情境脉絡而損益更新。心在虛壹而静時具有價值直覺,能肯認禮義和實踐禮義因而逐漸調節、轉化欲望與情感,能經由一次次的嘗試錯誤,讓身心逐漸朝向禮義來轉化、净化、美化。整體來看。這是有別于孟子思想的另一種性善論,可以稱作“人性向善論”或“弱性善論”。
整體地說,在荀子哲學裹,宇宙有個從自然到人事彼此連續一貫而有等差的秩序、律則作爲最終的價值根源。人在具體情境中有一個有限度的價值直覺可以作爲認識價值、實現價值的依據。這樣的觀點,雖然是從《荀子》的文本意謂提取出來建構而成的,但它跟荀子表述的思想在“值”上相等,而比較符合中國人的一般心理傾向。我們可以非正規地借用社會學家韋伯(M.Weber)的概念,把它稱作荀子哲學的“理想型”(ideal type)。
接著談孟子的“中”。孟子說:“中也養不中。”(《離婁下》)又說:“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盡心下》)。這都表彰了“中”的概念。他又說:“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盡心上》)。造就間接提出了“執中而權”的觀點,也間接說明了他所謂“中”,跟他所謂的仁義禮智一樣,都是先天內在、本有固有的價值,具有本體論的意義。是實踐時“用權”的依據與前提。③
再來談荀子的“中”。令人驚訝的是,荀子其實比孟子更多也更鮮明地談到“中”。他說:“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事行失中謂之奸事,知說施中謂之奸道。”(《儒效》)原來中就是禮義,它跟禮義一樣,都是人所以踐行的群居和一之道。荀子又說:“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禮論》)這就再度說明了“中”跟“禮”(即“節”)在理論地位上的同一與相通。
不妨說,從禮義來說明“中”,其實就是用相對熟悉的“禮義”的性質來定位“中”的意思。這點絕不會讓“中”淪爲外在形式與刻板僵化,因爲荀子的“禮義”本來就不是外在的、强制加在人身上的東西。荀子說:“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禮論》)又說:“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論》)。可見禮(禮義)是人類情感、欲望、事物裹頭所潜在著的條理與節度分寸的外在具體形式。它跟孟子那種自動地、直接地萌發的仁義禮智(所謂四端)不同,它是内在于人身心活動中的適當條理、和諧韻律的提出和凝定。荀子本人由于在定義上區分性、偽,所以加意地强調禮義“生于聖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性惡》);但我們今天若鬆開、跳出這樣的定義,便可以重新看見荀子的禮義其實並非來自人性之外的一個侵入者與宰制者。總之,荀子的“中”雖不是個純精神的形上實體,卻也不是一個純客觀的外在規範;它是身心事物裹頭的一個恰到好處的節度分寸。
荀子又說:“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樂論》)這裹,應該是關聯著“禮即是中”的一點,荀子把樂說成“和”,以及“中和之紀”(顯然這是因爲依禮成樂,而樂中有禮)。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字面上,《荀子》跟《中庸》確實有更明顯的交集。
二、性、道與中、和
這一節,我們一邊對《中庸》第1章做徹底的重讀,一邊進行討論。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謂性”一句其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理學家從形上天道、天理的下貫來解釋,這是孟學的進路。若依荀學進路,則我們可以說,自然元氣流布,賦予每個人一份大致相同但同中有异的禀氣,作爲其本性的實體,這樣的過程就是“天命之謂性”。然後,以這樣的“禀氣/性”爲基底,人的一切身心活動,包括欲望、情感、知覺就都是性的作用和表現,這是從自然義來講的性。要注意的是,在這些欲望、情感、知覺的作用裹頭,有個潜在的價值傾向;這價值傾向也是性中所有,它是從價值義來講的性。一定得補上這一點,我們纔能把後面的“率性之謂道”以及更後面有關“誠”的部份貫通起來。
“率性”的“率”,可以按照舊說看作“循”和“順”,但相關的意義脉絡大不相同。應該說,依循著人的情感、欲望直接發出來的未必是道,只有依循著其中的價值傾向所提出來的實踐路徑纔是道。這樣的道,並非性所直接發用出來,也並非絕對不變確定不移,因此必須有人在必要的時候重新出來斟酌、損益、論定,這就是“修道之謂教”。
“率性”的“率”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廖名春(59)指出,“率”應當解釋爲統率、率領,而這樣的“率性”就相當于《性自命出》的“長性”。這個解釋比較明快也頗值得采用。依照這個解釋,我們可以說,道是從人性的自然内涵裹頭,就著其中所蘊涵的價值傾向所提取出來的,然後這樣的道又是用來引導、統領整個人性朝向美善去發展的。《性自命出》以喜怒哀悲之氣(等于情)、好惡之情爲天命之性,主張“道”是情的進一步提煉所成(“始者近晴,終者近義”),而這樣的道可以“長性”。這樣的理路跟《中庸》此處(依本文前面的詮釋)大致相似。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内在于本性,是順著本性而提出的。但它不是一個獨立自在的終極實體,它不能直接地、自動地發用出來。事實上它只不過是本性所潜在著的和諧條理的外在形式而已,必須由人定意照著它來實踐纔能在志思言行裹具體地凝定和呈现。因此,人若要追求生命的美善,就不能一刻離開它。所謂的“不可須臾離”,正是從這樣的理路和工夫實踐的層次而來的一個實質的、必要的、强烈的提醒。⑤而所謂在人們不睹不聞不知的時候也要戒慎恐懼,這便是著眼于實踐以及從時間的向度來具體地說明“不可須臾離”。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隱、微、獨指的都是内心。内心隱微的狀態和動向,是實踐工夫的基底和關鍵;這個地方一旦顯明了或被揭露了,反倒是眾人所共見而遮掩不得的,所以必須“慎其獨”。然而“慎其獨”只是一個原則性的提示,没有具體的内容。這兒應該注意到,接下來提到的中與和,並非另起爐灶的論題,事實上它是關聯著“慎其獨”的實踐原則所提出來的進一步說明。
宋明以來,一般都比較是把“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句,當作對“中”、“和”的直接界定來理解,于是形成了孟學性格的“性情/中和/體用”解釋圖式。但戴震(22)已經說過,古文中凡說成“之謂”的,纔是“以上所稱解下”;而凡說成“謂之”的,則只是“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這個說法提醒了我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句,可以只是就不同脉絡、層次來關聯地說明中與和,而未必是要直接地解釋中與和;因此“中”就未必是喜怒哀樂根源處的超越性體,而“和”也未必就是那個“中”的直接發用。應該說,“中”是跟喜怒哀樂等情緒無關的,是人、事、物之脉絡情境裹頭一個恰當條理分寸;“和”則是基于對這樣一個恰當的條理分寸的理解,于是情緒發用時所能够達到的一個恰到好處的狀態。總之,君子内心莊重自持(所謂“慎其獨”),于是對人、事、物總是能盡心盡力地衡量、斟酌來掌握一個“中”,然後當其在事物脉络中情緒具體發出時就能因著這樣的“中”而達到“和”,這是從内心開始,從空間(内外)的向度來具體地說明“不可須臾離”。
孟學進路從性體及其發用來講中、和。但是重新細膩地體會這裹文意的轉折變化,我們便可以改從君子慎獨的實踐成果,從內在用心所關聯著的兩個方面來講中、和,這是荀學的進路。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事、物條理脉絡裹蕴涵著一個“中”,它正是天下得以安定的一個根本;人基于對這樣的“中”的理解與掌握因而在情緒向外發露時能够“和”,這便是遍及天下可以通行的大道。由于這樣的中與和都不是現成可得的,而是在慎獨的修養工夫裹所掌握和做到的,所以後面纔會說個“致”:一旦能掌握到中,能做到和,自然就跟天地萬物的内在條理、韻律相通,自然就能真實地感受到天地的安穩、萬物的順暢了。
值得一提的是,既然“和”是天下之達道,而“和”的前提是“中”,所以“和”這個天下之達道其實就是“中”的實踐之道,因此也就可以說成中和之道。從這樣的中和之道,推進到後面的中庸之道就順理成章了。
以上的理解,跟孟學進路全然不同。這是重讀《中庸》的關鍵之一。
三、中庸之德與中庸之道
《中庸》從第2章起一再出現的“中庸”,一般解釋作“用中(完整地說則應是用中和)”或“中(包括中、和)、常”,兩者各有道理也各有根據。如果直接體會各個句子裹“中庸”的用法,那麽中庸應該是中、和在言行舉止裹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表現了中與和的德行(《論語》所謂的“中庸之爲德”)或行動與作爲(所謂“中庸之道”)。此外,既然首章說到“和”是天下之達道,那麽中庸其實也一樣可以說成“天下之達道”。
《中庸》許多地方未必出現“中庸”一詞,但是看得出來全文各處(包括各種不同措詞的“道”)所談的還是中庸的概念和中庸之德以及中庸之道。而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第12章)、“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13章)、“素其位而行”(14章)、“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15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33章)等語,也都是從不同角度對中庸之道的說明。不妨說,這些說明恰恰是晚周時期《中庸》對其他各家(如墨家、道家、法家)的挑戰與質疑的一個回應。儒家的實踐從眼前從身邊開始,平常平實,然而一樣可以達到極致,臻于美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極高明而道中庸”便是對這種精神這種性格的一個最好的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第7、8章說“擇乎中庸”,第11章說“遵道而行”、“依乎中庸”,第20章說“擇善而固執之”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些地方都說明了“中庸”並非由内在性體直接發用出來的(那是孟學進路的解釋),而是人事物所能達到的一個恰當和諧的狀態,並且是在現實情境中具體斟酌衡量出來,然後遵循實踐的結果。第13章的“忠恕”,把自己對別人(子女、下屬、幼弟、朋友)的要求當標準而反過來檢視自己,便是這種斟酌衡量的一個很好的方法和例子。必須澄清的是,這樣的斟酌衡量並非全屬外在的客觀思辨活動。應該說,身心、天地萬物都潜在著“中和”的價值傾向,因此,這樣的斟酌衡量,一方面是對外在事物的拿捏、感知、揣摩,一方面還是内在生命的共鳴與印證。
第16到第19章論及祭祀、鬼神等似乎有些突兀,但它們其實恰恰反映了“中”跟“禮”密切相關的一個背景。梁濤(273-274)已經指出,“中庸”的方法是在日用常行也就是禮的基礎上推衍出來的,是對禮的哲學化、理論化;他據此認爲《中庸》這幾章的出現完全可以理解。此刻我們還可以補充道,這幾章,以及更後面“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20章)、“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27章)、“議禮……制度……考文……作禮樂……夏禮……殷禮……周禮”(28章)等文句的出現,都恰恰說明了《中庸》的荀學性格。
四、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中庸》第20章是從中庸之道朝向誠、明問题的轉折點。這章談爲政,基本上是德治主義的談法。其中,“爲政在人”(爲政在于得人)讓人聯想到《荀子·君道》的“故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好學近乎知”也讓人聯想到《荀子·勸學》的“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此外,那作爲治理天下國家的“九經”,非常地注重具體實務,如“修身”一項的“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親親”一項的“尊其位,重其禄”,“勸大臣”一項的“官盛任使”,“勸百工”一項的“日省月試,既禀稱事”等,也都比較是荀學而不是孟學的性格。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修身則道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上面是第20章比較前面的部份。其中,君臣、父子等五種“天下之達道”單單從字面來看顯得有些空洞;但是關聯著第1章“和也者,天下之達道”的理路,我們可以把它們理解爲關聯著五倫的五個方面的中庸之道。
這裹有個重點是“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必須厘清的是,首先,引文開頭說“修身以道”,後面卻反過來說“修身則道立”,可見“修身”跟“修道”是個雙向循環:一方面藉由既有的道的典範來修身,一方面又藉由修身的成果來凝定、彰顯、校正道。其次,跟“仁”相繫聯的有仁、義、禮一組(屬道或善),又有知、仁、勇一組(屬德),兩者性質不盡相同。不過,引文開頭有個“修道以仁”,中間有個“知斯三者(知、仁、勇),則知所以修身”,後面又有個“(禮)所以修身也”。可見這兩組同時跟“修道”、“修身”兩個層次都有關,不必特別區隔開來。
因此,“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完整的義涵,應該是根據、參照著具體的美好品德(如知、仁、勇)和道與善的榜樣或典範(如仁、義、禮)來修飭或調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五個方面的中庸之道(如仁義之道、禮義之道等,這是修道立教的層次),然後随時思量著、體會著、遵循著這樣的中庸之道來修身成德(這是修身行道的層次)。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引文中“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一句,從“親親”等人際情感說仁,從“尊賢”等價值判斷說義,然後進一步從那情感增減、尊卑等差的斟酌來說明禮的所在,這也比較靠近荀學的理路。
第二,“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樣的話語、措詞在今天看來很自然,是孔孟思想的常態表達;但仔细追究起來則起初未必如此。先就“修身”來說,筆者經考察(1992∶140-141)發現,《孟子》裏雖然出現“修身”二次、“修其身”一次,但更主要的用語是“誠身”、“誠其身”(2次)、“反身而誠”、“反身不誠”、“守身”(2次)、“不失其身”、“失其身”、“潔其身”、“身之”、“身正”等。然而《荀子》裏卻整個都是“修身”(4次)、“修其身”、“正身”(6次)、“正身行”(3次)、“端身”等彼此相似的用語。可以說,孟子是在性善論對身心表現樂觀看待的立場上,偏愛“誠身”、“身之”、“身正”一類當下自誠自正意味的措詞;而荀子則是在性惡論(或者說弱性善論)對身心表現心存警惕的立場上,全面采用“修身”、“端身”、“正身”(這個“正”是修正的意思,《孟子》裏“身正”的“正”則仍是“誠”的意味)一類對付、修治此身意味的用語。
再就“修道”來說,《論語》、《孟子》裏根本没有這個語詞出現。《荀子》則說:“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⑥(《天論》)又說:“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正論》)這當然是基于“心也者,道之工宰”(《正名》)和“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性惡》)的觀點而來的一個理所當然的語詞。
總之,當跳出習以爲常的感受,重新追究語言底下的思想脉絡,便會發現,“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樣的話語實在是比較接近荀學性格的表達。其中“修道以仁”相當于製作禮義的層次,“修身以道”相當于“積善成德”的層次;兩者都屬荀學那種内外交參互證的型態。
五、博學、明善、誠身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只是個静態的藍圖,距離實踐還差一步。所以《中庸》20章在揭示這藍圖,陳述爲政九經的具體措施後,接著便提出一個從“明善誠身”做起的實踐次序,然後又從21章起整個地進入“誠”的主题。這個轉折有一定的理路,《中庸》全文就此前前後後整個連貫起來。這一節我們先討論博學、明善、誠身的部份。
《中庸》第20章“明善誠身”一段,在《孟子》以及漢代所撰輯的《孔子家語》裏面都有,底下是三者的並列(加底綫處是大致相同的部份):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
子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反諸身不誠,不順手親矣……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誡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有弗思……有弗辨……有弗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中庸》)
孔子曰:“……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孔子家語。哀公問政》)
這三個材料中,前面幾處關鍵語詞以及末尾的内容都顯示了《中庸》跟《家語》的高度相似:
《孟子》:居下位/事親弗悅/反身不誠/不誠其身/是故/思誠者/至誠而不動者……
《中庸》:在下位/不順乎親/反諸身不誠/不誠乎身/(無)/誠之者/誠者不勉而中……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審問、慎思……
《家語》:在下位/不順于親/反諸身不誠/不誠于身/(無)/誠之者/夫誠,弗勉而中……誡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教民睦……教民順……
看得出來,相較于《孟子》,《中庸》、《家語》兩者高度相似的措詞和文句比較是更晚出更明朗的形式,這應是《中庸》(以及《家語》)晚于《孟子》的一個證據。⑦
如果說,是晚出的《中庸》采用了《孟子》這個材料(或采用了跟《孟子》同一個來源的材料),那麽,重要的是,《中庸》又在《孟子》那段話的末尾,删去“至誠”等語,改就“誠者”和“誠之者”兩層發揮,並且加意地表彰“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用來作爲“誠之者/人之道”的實踐方式;這便是從荀學立場來改造這個材料了。也就是說,雖然接受“明善誠身”的提法,甚至沿襲了“誠身”這個孟學式的用語,但是關于怎樣明善,還是表現了荀學“學知禮義”的立場。經由博學、擇善而後明善,而後誠心執守,這就跟《大學》經由“格物”(學習、思量禮義等)而後致知,而後誠意信守一樣,都是荀學性格(劉又銘,1992)。
附帶提一下,第27章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其中的理路應該是,人性的自然表現頗不確定,其中雖有德性的存在,但這德性並非一個可以自動發用的實體,因此在初步地、原則地尊德性之後還必須進一步藉由問學的幫助,纔能將它認取、開發出來;這也是博學而後可以明善的意思。
六、與“誠”相關的其他諸面向
首先,《中庸》第20章末尾提到“誠”有“天之道”、“人之道”兩個層次:
1.誠/天之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
2.誠之/人之道/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這裏的“天之道”,應該關聯著第26章的“天地之道”來理解: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詩》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26章)
這一段著重說明了天地之道的“爲物不貳”,它其實就是第20章“天之道”的“誠”的具體内涵。這樣的意思,《荀子·不苟》說得很明白:“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簡單地說,天地四時的恒常表現就是天地的誠了。必須說,《中庸》、《荀子》二者的“天之道(誠)”跟《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那種天、人“同一”甚至“是一”的理路下的“天之道”不同;它是天、人合中有分觀點下的一個相對素樸的天道,它是人之道的本原與基底,是作爲人之道的一個範式一個隱喻而提出的。天覆地載,博厚高明,悠久無窮,于穆不已,天、地這樣的“誠”,如此確定現成,昭然信然,值得人來效法。但人通常處在現實的、充滿凶險的、未知與莫測的處境中,無法直接地、樂意地去誠,所以必須學、問、思、辨,一步步擇善、明善,然後纔能全然放心地信守篤行。當人最後終于能够純熟確定地擇善明善,那就可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彷彿天道般地自然而然,那就是聖人了。也就是說,《中庸》第20章把聖人歸在天之道底下,是就人“誠之”的實踐結果來說的。或許聖人禀氣超出眾人,更容易達到這樣的境界,但絕對不是天生直接如此的。
在這章之後便接連出現了許多關于人的“誠”,但它們指的可能是“人之道”層次的實踐工夫的“誠之”,可能是“誠之”達到純熟圓滿的境界而後等同于“天之道”的果位的“誠”(例如“至誠”),也可能同時包括兩者,必須随文衡量。
第21章從“性”、“教”兩個方面來談“誠”:
1.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
2.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
跟前面“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樣,這兒也只是用“性”、“教”兩個概念來提示“自誠明”和“自明誠”的區別。有些道理或認識,心一誠就直接知曉明白,因爲那是本性所能直接觸及直接發露的。但另外還有許多道理或認識,必須要先學明白弄清楚了纔能誠心信守,因爲那是本性不能直接觸及直接發露而必須經由教導來獲得的。因此,並非說有些人(例如聖人)天生能一切“自誠明”,更不是說那些“自誠明”的東西就一定高于“自明誠”。應該說,這裏的“自誠明”指的是一般人基于本性總是能直接明白的一些起碼的基本的道理。然後,在這之外還有更多的道理就必須經由教導來得到了。此外,也並非說,“自誠明”纔是“率性之謂道”(這兒“率”理解爲“循”)而“自明誠”就不是。應該說,自誠而明的以及自明而誠的,都是“率性之謂道”,只不過有些較直接顯現有些則必須“修”了纔能呈現罷了。
第25章談到的,是基于“誠”所開展、鍛煉出來的兩種“性之德”:
1.誠者:自成己/仁(性之德)
2.誠者:所以成物/知(性之德)
只有真誠地面對自己,纔能有動力讓自己生命逐步成熟圓滿,這樣逐步成長的成果就是“仁”的完成。也只有真誠地接納、面對他人,纔能有動力逐步克服人己的隔閡跨越生命型態的障蔽逐步達到更廣大的理解和包容,這樣逐步發現逐步拓展的成果就是“知”的純熟。“仁”跟“知”都是本性裏所潜在所蘊涵著的德的展現,都是統合人己、物我、外内之道;不過它們不是本性所直接流露出來的,而是逐步開發鍛煉出來的。這樣的“性之德”,並非孟子性善論那種全性是德的德。依荀學理路,人性包括自然情感欲望在内(見前),它們的自然發用蘊涵著德卻不全都是德,所以這兒纔會特意說個“性之德”,表示是本性所蘊涵的德,是從本性中所提取出來的德。
七、至誠配天地的圓滿境界
《中庸》第22章起,大部分都在談至誠的圓滿境界。首先: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22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23章)
一般依《朱注》將這兩章分别看做聖人、賢人一高一低的兩種誠,其實它們都一樣是在講聖人至誠的表現,必須連貫起來讀成:“唯天下至誠,(1)爲能盡其性……可以與天地參(2)其次致曲……爲能化。”依此,至誠的人,首先原則地、基本地說便是能盡人之性(充分理解、貞定人的本性,不會任由它流蕩外逐),能盡物之性(充分理解物的本性,能恰當面對和運用),可以幫助天地的化育,可以與天地相參(或者說與天地並立爲三);其次具體地說則是能隨時随地真誠地、有效地關注、照顧、轉化其所遇到的人與物。這樣讀,纔能合理解釋第23章末尾爲何也要說個“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荀子·不苟》有段話跟上引第23章相似:
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
這裏,如果說君子的“誠心守仁”、“誠心行義”一開始還比較是《中庸》的“誠之(人道)”的階段的話;那麽當一步步實踐到了圓滿成熟的地步,神而明之,能化能變,變化代興,那就是具備了“天德”的聖人,完全等同于《中庸》第22、23章的“天下至誠”(也就是“天之道”)的層次了。附带提一下,這段話也是把天地的誠、聖人的誠並列,拿天地的誠以化萬物來譬喻聖人的誠以化萬民;這都透露了《荀子》跟《中庸》在思想上的相通與交集。
接下來: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24章)
至誠的人,的確更能掌握人事物隱微的消息,洞燭機先。“禎祥”、“見乎蓍龜”等則只是個平行的印證,並且它們多少是《中庸》那個時代的特殊印記,不足爲病。荀子雖然否定天神的存在,反對卜筮,但是這個屑面的出現並不會根本地改變《中庸》的荀學性格;這跟董仲舒講天人感應但基本上還是荀學性格是一樣的(劉又銘,2007)。
最後: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26章)
至誠無息(更完整地說,就是肯認、持守仁義禮等中庸之道,至誠無息地實踐),生命格局在持續積累中逐漸變得博厚與高明,能載物如地,能覆物如天,而終于能悠久以成物,匹配天地。值得注意的是,第22章已經講過“與天地參”,這裏又講“配天”、“配地”;類似的提法在《荀子》那兒非常普遍(但在孟子那兒卻没有):
1.君子……擬于舜、禹,參于天地,非誇誕也。(《不苟》)
2.習俗移志,安久移質。並一而不二,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儒效》)
3.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王制》)
4.奪然後義,殺然後仁……功參天地,澤被生民……湯、武是也。(《臣道》)
5.天有其時,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天論》)
6.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性惡》)
7.有物于此,居則周静致下……大參天地,德厚堯禹……(《賦》)
上面的第二、六兩則,簡直可以采用《中庸》的語彙改寫成《中庸》式的句子:“至誠無息則通于神明而參于天地矣。”《中庸》跟《荀子》之間這樣的符應現象再度透露了兩者的密切相關性。就思想層面來說,孟子側重從形上精神實體來講天、人關係,往往單提一個天來跟人並列,而天人同一或是一;荀子則從存在全體來講天、人關係,往往兼提天、地來跟人並列,而天、地、人合中有分,于是纔有個基于“分”而來的相“參”可說(劉又銘,2007∶38-39)。對照來看,《中庸》的“與天地參”和“配天”、“配地”顯然是荀學的性格。
結語
本文從荀學性格的天命與性來談道與中、和,從這樣的道與中、和來談中庸之德與中庸之道以及修道和修身,然後從荀學的修養工夫來點出博學、明善、誠身的內在邏輯關係,最後從這樣的邏輯關係來談誠的其他諸面向以及匹配天地的圓滿境界,總之大致呈現了一個從荀學進路來解讀《中庸》的詮釋理路。雖然還不能算是全面以及充分地證成《中庸》是荀學,但至少已經從哲學層次相當地揭示了這樣的可能性。
筆者過去(1992,2005)曾經回應馮友蘭的“大學爲荀學說”,全面地證成了《大學》的荀學性格。如果今天能再度確認《中庸》也是荀學性格的話,那麽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揭示更多新的可能,例如:
(一)周秦之際,荀學一路的哲學型態雖然以荀子爲巨擘,但在孔子、孟子思想的影響與牽引之下,也同步地出現《大學》、《中庸》這樣的個別文本。它們比較明顯地運用一些具有内在性的價值概念,但仍然一起分享了荀學那種自然本體觀、弱性善、問學以致知的哲學典範。把它們包括在内,連同《荀子》,一起作爲早期荀學的重要資源,這對于理解漢代以後的思想發展,將有重要的意義。
(二)如果《大學》、《中庸》都是荀學的話,那麽它們在宋明時期對孟學的召唤,以及被孟學認取並且被整個地改造爲孟學性格,就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奇妙的事件。宋明理學裏頭所潜藏著的荀學成份,也必定比向來所以爲的還要多。這些都值得重新研究。
(三)如此一來,包括《論》、《孟》、《學》、《庸》在内的所謂四書學,就呈現爲一個全新的面貌了。它不再是單單孔孟之學,而是包括孔孟荀在內的一個更完整的雙核心(孔孟、孔荀)或三核心(孔、孟、荀)的儒家四書學。但既然如此,我們何不根本地重新做個考慮和安排?梁濤(2008∶536)曾經提議過一個“新四書”的概念。他主張,不是從“一綫單傳”的道統觀,而是從“真正能代表、反映以及涵蓋早期儒家文化生命與精神内涵”的視野,將《論語》、《禮記》、《孟子》、《荀子》訂爲“新四書”。這便是一個正式涵蓋孔孟荀在内的“新四書學”的構想,這個方向值得考慮。
注釋:
①晚近已經有少數幾個這樣的例子,如張晶晶(2007)論司馬光的《中庸廣義》,張晶晶(2005)以及郭寶文(2011)論戴震的《中庸補注》。
②佐藤將之此說將這個論題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不過他認爲《中庸》作于《孟子》之後《荀子》之前,本文則認爲《中庸》作于《荀子》之後(見下文)。
③孟子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離婁上》)這裏,“據禮行權”的思維,正好跟“執中而權”的思維彼此一致。
④本文凡提及《中庸》文句,以朱子《中庸章句》的分章爲準。
⑤朱子《中庸章句》說:“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又說:“其實體備于己而不可離。”其實他說的是道的實體的内在于己,那樣的實體只會被遮蔽、遺忘,卻是毋需警醒也不會須臾離開的。
⑥此據楊倞本。《荀子集解》引王念孫說:“修當爲循字之誤也。”其實荀子本就有“修道”的概念,“修”字不必改。
⑦佐藤將之(2007∶109)做過類似的比較並且同樣認爲,《中庸》這段話來自《孟子》的可能性比較大,而反之的可能性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