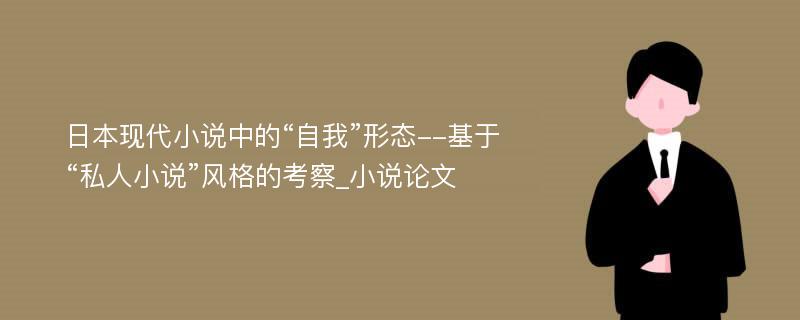
日本现代小说中的“自我”形态——基于“私小说”样式的一点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样式论文,形态论文,自我论文,现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出现与时兴,较法国自然主义文学迟滞三十余年,但它却标志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肇始。根据一般的日本文学史记载,日本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是小杉天外的《初姿》(1901)。但也有人将永井荷风(1879-1959)看作自然主义文学的开山之祖。虽然永井荷风日后成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但他的早期名作《地狱之花》(1902)等颇似正统的自然主义文学,据说就是以左拉的小说为范本的。真正代表日本自然主义的作家是稍后的岛崎藤村与田山花袋。岛崎的自然主义名作《破戒》(1906)曾被夏目漱石誉为“明治以来的第一部小说”。田山花袋则以貌不惊人的小说《棉被》(1907)超越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棉被》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也是日本自然主义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则具有别样的史学意义。如果说《破戒》较多地具有社会性视点,《棉被》则更多地沉迷于日本式的个人化世界。《棉被》可以说是一块界碑。自此日本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样式——“私小说”。
日本“私小说”给人的印象趋于消极,因而从未听说“私小说”在小说技法上有所创新。有人称“私小说”作家是“半封闭性的逃亡奴隶”。而笼统地说,“私小说”植根于日本文学或文化的传统,又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变种。在田山花袋以后的日本文学中,各具特色的“私小说”作家层出不穷。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德田秋声、葛西善藏和太宰治等等,几乎都是现代文学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直到二战之后,“私小说”创作才逐渐式微。但它现在仍是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评论的中心话题之一。评论家中村光夫曾在《日本现代小说史》中断言,日本所有的现代作家都写“私小说”。这自然也囊括进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等精神实质上与“私小说”特质迥异的作家。但这种绝对化的断语,至少也说明了“私小说”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文坛对于“私小说”的定义的确模糊不清,且历来众说纷纭。虽各家各说中亦有共通之处,但仍旧令人难于把握。因而在简要评说“私小说”生成状况的基础上,对日本作家、评论家对“私小说”的论说稍加整理和评述,有助于认识“私小说”的特质,加深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理解。
自然主义文学与“私小说”
田山花袋在《近代小说》一文中说,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根本特征“不在文章或文体,而在于它是包含着某种意愿的运动——破坏旧日本的习惯、道德、形式、思想或审美情趣”。这一概括是准确的。《破戒》与《棉被》尽管视点不同,创作意愿中却包孕着同样的精神追求。《破戒》通过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客观化的写实文体中,涉及当时社会的部落民歧视现象和近代式的个体觉醒意识。《棉被》则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殊途同归地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苦闷。有趣的是,《棉被》不过是一部短篇小说,却更多地具有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想必田山花袋当初并不晓得自己的作品会受到特别的关注,更没想到它会成为一代文学样式的滥觞。他不过想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体现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1904年,田山花袋在《太阳》杂志上刊出“露骨的描写”,主张一种“没理想、没技巧的平面描写”——不论现实美丑,一味照现实存在的本来面目去描写。这种主张是自然主义的,也为“私小说”的未来发展定了调子。然而作为小说在着负面效应——文坛的过高肯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是作家本人亲历的生活体验,就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作品中去。无论怎样表现,都有其特定的意趣与价值。田山花袋依据这个理论,轻易地抹去了岛崎藤村那样的社会性视野,推出了一种主体意识消极、拘于个体现实的“私小说”样式。
其实,日本自然主义的重要作家除了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尚有国木田独步、德田秋声、正宗白鸟、青山真果和岩野泡鸣等。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德田秋声(1871-1943)。评论家生田长江称德田为“天生的自然派”。原因在于德田的作品甚丰,且多为“私小说”。或者可以说,是德田秋声真正确立起所谓“私小说”的文学样式。在德田秋声的小说作品中,既没有岛崎藤村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没有田山花袋的精神感伤,甚至看不出他对生活中遭受的苦难有过任何反应,整部作品贯串的是彻底的客观描写,似乎完全取消了主观。德田主张完全的“无理想或无解决”,他的小说《糜烂》(1913)、《胡闹》(1915)等被称作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顶峰之作。德田的“私小说”代表作则是《假面人物》(1935)和《缩图》(1941)。这些作品进一步实现了德田特有的文学主张——所谓“无方法的方法”。有趣的是,《缩图》又被川端康成奉为“日本近代小说的最高杰作”。
在日本当代文坛上,也有人将“私小说”的根源上溯至公元10世纪前后的日记文学,如纪贯之的《土佐日记》等。这样就扯出了“私小说”与特定文学传统或审美情趣的契合问题。其实远的不说,当我们悉心考察明治初期近代文学启蒙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时,亦可发现那种崇奉写实的理阐述中,包含着日后现代文学发展的基因。坪内强调的文学理想首先是表现“真实”。在此意义上,不回避人类生活的任何层面,包括丑陋与罪恶。这种理念其实已经接近田山花袋等人的感觉至上的文学观。或者说,坪内逍遥的理论已经体现出自然主义或“私小说”文学观念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自然主义和“私小说”,说到底同样属于写实性的文学范畴。此外,坪内逍遥的观点亦体现在他与森鸥外的一系列争论之中。坪内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极其自然的,宛如造化一般,而“造化本体是无心的”,所以是“无理想的”。这种自然的、“无理想”的写作论,与日后自然主义、“私小说”作家的“无理想”论何其相像?
但不管怎样说,将“私小说”这颗果子挂在自然主义一棵树上,总有些不妥。因为此前写实主义文学发挥的铺垫作用也是一个显在的事实。除了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亦值得一提。倘若将《浮云》中的第三人称换为第一人称,该篇中的文三似乎正是日后“私小说”中的标准造型。《浮云》第三卷几乎是“完全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私小说”部分地模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心理表现”,作者融进了内海文三的内在精神,和文三一起怀疑、苦闷、踌躇、错乱、不知所措。(注:桶合秀昭《二叶亭四迷与明治日本》,文艺春秋社1986年版,第120页。)总之,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西化运动中,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率先开始思索近代化中的“自我”定位问题,且将近代以后的日本文学表现方式,基本确立在形形色色体现主流文学动向的写实之中。
当然,似乎可以认定“私小说”的母胎是自然主义文学。一方面如前所述,包括田山花袋、德田秋声等在内的诸多“私小说”作家,本来就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私小说”样式的特征与实质,亦与自然主义文学有着诸多关联或相似。我们在此不妨回顾一下左拉关于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的描述,就会更加明确地认可这种血缘关系。左拉说,“……想象在这里所占的地位是多么微小。……小说的妙趣不在于新鲜奇怪的故事;相反,故事愈是普通一般,便愈有典型性。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注: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页。)左拉的这个自然主义定义对日本的自然主义乃至“私小说”作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我们在承认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影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西方自然主义与日本自然主义的微妙差异。1888年,左拉第一次被介绍到日本,应当说日本的自然主义始自于此。紧接着,左拉、莫泊桑等人的代表作品大量、迅速地译介到日本。许多作家、评论家亦纷纷撰文,介绍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不过说起来,日本自然主义统治文坛的时间并不太长。从《破戒》算起,充其量也就是四五年时间。而纵观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史,文坛主角的频繁更替亦为一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时期的砚友社文学、大正时期的唯美主义文学以及昭和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等等,兴盛过后便成为某种历史;唯独自然主义文学,兴盛之后化为一股潜流。(注:相马庸郎《日本自然主义论》,八木书店1982年版,第3页。)或许,日本的自然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自然主义。因为虽然二者都强调自然与真实的重大意义,在对于“自然”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田山花袋说过,“小说必定是自然的缩图。其次仍旧是自然。没有道德,没有伦理,没有社会,没有风习。”(注:相马庸郎《日本自然主义论》,八木书店1982年版,第16页。)这样绝对的论点在左拉的理论中似乎不曾见。就是说,西方当时的自然观,应当说已经建立在发达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是一种基本合理的自然观或人类观。而田山花袋的自然观却仿佛原始的感性本能。“本能的嗫嚅即自然的嗫嚅。本能的力量即自然的力量。本能的显现即自然的显现。本能将征服一切。”(注:相马庸郎《日本自然主义论》,八木书店1982年版,第16页。)由此可以看出,田山花袋的所谓“自然”,是受性欲支配的形而下的存在。但恰恰是在这种自然观的作用下,出现了《棉被》那样富于日本特征的自然主义小说。换句话说,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阐释法国自然主义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时,或许时有故意的误解或歪曲。他们一方面受到了科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所偏向,他们关心的是文学科学化造成的结果而非文学科学化本身。当时的“破除因袭”,“打破形式”,体现了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浪漫主义的自我解放欲求。一句话,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所追求的目的,与左拉等人未必相同。这正是自然主义演化为“私小说”的一个基因。
关于“私小说”特质的种种评说
在简单描述了日本“私小说”产生的背景或与自然主义文学的直接关联后,有必要考察日本作家、评论家关于“私小说”的种种评述。虽然人们已经形成了某种成见,认为早期(甚至包括中期、近期)的“私小说”论缺乏理论性,大多属于感觉性、议论性的表述;但这些评述仍旧是深入研究的基础。无可否认,“私小说”的基本规定源自久米正雄的《私小说与心境小说》。久米认为日本的“私小说”不同于西方的第一人称小说。“私小说”在表面上固然是一种自传体的写实性叙事,但这种“赤裸裸剖露作家自我的小说”,其第一规定仍旧“必定是小说是艺术,而不同于一般的告白小说或自传”。“私小说”与自然主义“走近真实”的区别在于,“私小真实的客观描述——“将自我的心绪转化为自我的感慨,进而直接地加以陈述”(注:久米正雄《“私小说”与“心境小说”》,刊于《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日本角川书店1983年版,第50-58页。)。那么“私小说”与“心境小说”又是什么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久米的观点有些牵强。实际上“私小说”与他所谓的“心境小说”同属一物,只不过后者更加纯粹,是“私小说”的高级形态。久米认为,心境小说是将私小说中的“自我”凝聚、过滤、集中、搅拌,尔后令其浑然再生。换句话说,作者在描写对象时,令对象如实地浮现,同时主要表现的则是接触对象时的心绪和基于人生观的感想。这就是所谓“心境”,亦是作家创作的根据。久米断言,没有此类心境的“私小说”,便是文坛拒斥的纸屑小说或糟糠小说。这些说法给人以暧昧之感,却也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早期的“私小说”代表作家田山花袋认为,“小说的定义就是作者原封不动地描写自我的经验”。在作家看来,评论家总是画蛇添足。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一句话,田山花袋认为关键在于表现真实,“私小说”发生于“迫近真实的要求”之中。问题在于,田山花袋的这种概括很难区别于当时盛行的自然主义文学观或创作手法。且无可否认的是,评论家的肯定与复杂的评说,也是“私小说”盛极一时的原因之一。例如,正是久米正雄积极地将私小说奉为“散文艺术的根本、正道与真髓”。他反复强调,无论是多么凡庸的自我,只要如实地加以表现,只要表现了真正的自我,就有蹿的价值。久米的这种观点,成为当时“私小说”的一种定论,对日后的“私小说”创作和“私小说”论也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当然诸多名家对于“私小说”的肯定与支持,更是“私小说”成立与发展的保证。佐藤春夫就在《心境小说与正宗小说》一文中说,“心境小说给人一种散文诗般的趣旨或阴霾式的美感。它取材于人类生活,且在简素的笔致中捕捉日常生活的心理阴翳”。佐藤春夫也指出了心境小说给人留下的“不良印象”。他说心境小说有“变态感,诉诸一种变形的美感”。佐藤是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大家,代表作品有《田园的忧郁》、《都市的忧郁》等。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等曾受佐藤文学的极大影响。郁达夫的代表作品《沉沦》也具有浓重的“私小说”特征。同样,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也对“私小说”和“心境小说”推崇备至。他在《没有情节的小说》一文中强调,决定小说价值的不是故事的奇绝和情节的长短,而是诗性精神的深浅有无。芥川最喜欢的作家志贺直哉被称作“短篇小说之神”,也是极富特色的“私小说”代表作家之一。
此外,另一位“私小说”代表作家宇野浩二也说,应在作家探究人性的深度上追究“私小说”存在的意义。然而对于“私小说”的种种肯定,并不能掩盖这种样式与生俱来的诸多缺陷。有趣的是,指出“私小说”种种短处的,恰恰也是那些重要的“私小说”代表作家。例如佐藤春夫认为“私小说”始终拘泥于个人的身边世界,结果令作品的世界过分狭小。亦即“私小说”过分个人化,过分耽溺于日常性和生活细节。德田秋声则认为“私小说”乃至“私小说”作家一味寄寓于东洋式的孤独境地之中,结果陷于偏狭;应当从心境世界走向客观的世界。田山花袋也说过,应使主观客观相互交融。其实在早期对“私小说”的否定性观点中,评论家生田长江的批评较为尖锐。生田认为“私小说”具有反艺术和风俗化的特征,且作家精神过于稀薄。他认为这是一种恶劣的倾向。私小说不是将日常中的低俗生活提升为创作时的高尚生活;相反,却把创作时的高级生活降格为日常中的低级生活。生田的批评针对当时备受注目的“私小说”,也抨击了当时将“私小说”等同于纯文学的固有观念和菊池宽、久米正雄鼓吹的“作家凡庸主义”。(注:胜山功《大正·私小说研究》,明治书院1980年版,第181页。)生田对于小说的期望值或许太高。但无可否认,在许多“私小说”作家的创作中,确实表现出一种“凡庸化”的倾向。
日本作家、评论家关于“私小说”的种种评说,使我们对“私小说”的形态、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其实,感觉式的评论有时也能切中肯綮。只不过比较而言,小林秀雄较富理论性的《私小说论》(1935年)更有说服力,被称作划时代的创作。他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探究了“自我”问题的不同阶段与层次,进而论证了日本“私小说”特质的基本成因。他认为“私小说”首先是近代文学的产物;从人类历史上说,则是个人具有重大意义之后的产物。在小林秀雄眼中,“私小说”就是“自我小说”。因而他指出,法国“私小说”的产生可追溯到卢梭的《忏悔录》;而作为文学运动则与日本同样始于自然主义烂熟期的纪德和普鲁斯特。不同的是,法国的自我小说创作倾向源自某种重塑人性的焦躁。这种人性是自然主义思潮重压下业已解体的人性。就是说,法国作家研究的“自我”不同于日本“私小说”作家眼中的“自我”;因为西方人的“自我”,早已是充分社会化的“自我”。对他们而言,他们所关注的已不是“自我”的形态,而是“自我”本身的问题或社会之中“自我”的位置。换句话讲,他们意欲探寻的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相对性的量的规定方式。他说这就是法国“自我小说”正常发展的秘密。
但是日本“私小说”的产生,却与法国截然不同。这里有日本人精神气质、国民性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且小林秀雄认为日本没有产生西欧“自我小说”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这一点,从二者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差异亦可察知。西欧的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精神和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而日本的自然主义,却源自对西欧自然主义文学方法、技法的模仿。法国作家用科学的方法计量一切,他们深知由贪婪的梦想走进人生的绝望,以及无奈之中诀别现实生活的痛苦。但在日本,无论是田山花袋还是岛崎藤村,似乎都无法真正理解福楼拜和莫泊桑体验到的那种痛苦。此外,日本作家所不能理解的尚有,为何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积极地运用当时的时代思想或实证思想,最终却丧失了现实中的“自我”。因此小林秀雄断言,日本作家充其量只是小说技法的模仿者,他们不想了解或无法了解技法之后的思想背景或社会状况。(注:小林秀雄《私小说论》,刊于《近代文学评论大系》(7),日本角川书店1982年版,第181-202页。)很显然,小林秀雄的“私小说论”并未就样式论样式,他所探究的是样式的生成基础和构成样式中心问题的“自我”性质。这样的评论给人以更多启示。
小林秀雄的“私小说”论,至今仍是探究“私小说”本质的重要根据之一。此外,对“私小说”做过重要评说的作家、评论家尚有中村光夫、尾崎士郎、平野谦、荒正人、伊藤信吉等等。这里仅对评论家中村光夫的观点略加评述。中村认为,“私小说”实际上已经成为支撑日本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他说:“私小说”的兴盛、成熟决定于下述三种要素的微妙调和:一是源于江户时代的强大的封建文学传统;二是明治以来的社会状况;三是左右当时作家观念的外国文学。中村断言,三者舍其一,就无法把握私小说的性质。他认为田山花袋的《棉被》是日本自然主义的经典之作,是日本现代文学得以确立的基础。他将花袋与福楼拜、莫泊桑对比,进而说明日本“私小说”的特殊性。他说:“但凡文学,皆为作者心灵施诸读者的方术。然而坚信如此素朴的形态(《棉被》)即可同化读者,却是日本‘私小说’特有的性质。在这里,并非作品的力量使读者同化于作家,不妨说一开始读者就被同化于作者的感性与心理之中。在作家生活情感与社会生活情感相互调和的外部环境影响下,产生了‘私小说’朴素的手法。这种手法贯穿了‘私小说’运动。它一经确立,即构成强大的传统,至今仍在日本文学中居于支配地位。”(注:胜山功《大正·私小说研究》,明治书院1980年版,第197页。)
此外,中村又对“私小说”特质做了进一步说明:“私小说”家们“时而破坏道德,不过那是为了将反抗的自我展现给社会。此时,他们与观众面前展示演技的戏子没有本质的分别。因此,即便破坏道德的结果是痛苦,他们也坚信不疑。他们认定那种痛苦的素朴表现足以打动社会。在这里,存在着贯穿我国‘私小说’传统的浪漫派性格。那是一种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对于‘写实’的尊重。”(注:胜山功《大正·私小说研究》,明治书院1980年版,第200页。)
总之,“私小说”样式是日本现代文学中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正如伊藤所言,明治以来“随着新作家的粉墨登场,不断地形成新兴的文学性格。而像私小说这样确立起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性格、且保持了恒久生力者,殆未所见”。(注:胜山功《大正·私小说研究》,明治书院1980年版,第210页。)
样式的现状与“自我”问题
既然“私小说”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传统的性质,那么,在战后至今的当代文学中,它以何种形式存在呢?进而言之,当代作家、评论家又是如何审视、评价“私小说”呢?从创作上讲,“私小说”逐步衰微,明显地呈下降趋势。但是战后初期,“私小说”兴盛一时。从小说创作形式上讲,战后文学总体上呈现出超越“私小说”传统的趋势。尤其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文学也出现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趋势,出现了一批代表当今文学特征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对“私小说”式的“自我”写实没有兴趣,却在有意无意之中执迷于某种打破结构与模式的自由文体,例如村上春树、田中咏美的小说。他们被称作“后现代”,在纯小说(纯文学)不景气的今天,却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作品印数动辄几十万、数百万。但是二战结束后的一批先行者——太宰治、伊藤整、高见顺等——仍旧是以“私小说”式的告白起步的。尤其太宰治,其小说某种意义上不同于传统的“私小说”,他那与生俱来的毁灭、负罪、“丧失为人资格”和不厌其烦的自杀冲动,显然包含有文学的虚构。可以说,太宰治从骨子里就是一位私小说作家。其次,战前、战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上拒斥“私小说”式的写实。但在战后,一些代表作家如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和中野重治等,居然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私小说”作品。中村光夫称之为“社会意义性私小说”。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私小说”传统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说明,战争时期的思想压抑扭曲了这批作家的创作与生活,使他们的个人生活体验和感觉与社会性的心理趋向重合。当然,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私小说”作家亦有作品问世,如上林晓的《圣约翰医院》、尾崎一雄的《小虫种种》和外村繁的《梦幻泡影》等。的确,随着战后的世态变迁与文坛变化,“私小说”作品日见稀少。这种传统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渐渐地退至幕后。不过许多文坛巨匠仍然喜爱这种创作方法。如以《忍川》获得“芥川”文学奖的三浦哲郎,曾被看作战后当代文学“私小说”代表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屡有私小说作品问世;还有现在十分活跃的“私小说”作家日野启三、佐伯一麦等。总之,“私小说”创作的香火未断。即便在年轻作家的作品中,亦时时可见“私小说”技法的痕迹。
因此,“私小说”现象依然是当代作家、评论家时时关注、议论的焦点之一。近期评论家三浦雅士和前述两位“私小说”作家的一次对话(注:日本《群像》杂志,1993年第8期,第199-221页。),就较为深入地涉及了“私小说”样式中至关重要的“自我”问题。“对话”体现出当代日本文坛的特定视点。不过三浦雅士首先强调,“私小说”毫无疑问被看作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极其重要的要素或传统。这种认识到二战以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三浦说,只是有的人如今脱离“自我”的探究而论“私小说”。其原因在于六七十年代以后,“自我”成为一个谜,含义明显地趋于暧昧,相应的研究也陷入某种观念的泥沼。三浦认为“自我”的暧昧化亦源自整个社会的变化。就是说社会的加速发展,令现实呈现出多维层面,此时的“自我”便不再像世纪初那样构成社会的感觉中心。在这里,三浦雅士是由“私小说”研究、评论的角度出发的。实际上,“自我”的暧昧化也正是“私小说”创作日渐稀少的根本原因。“自我”说到底是“私小说”样式创作的基础,无论这种“自我”是小林秀雄所谓的前近代自我,还是其他任何层次的自我,总之离开了“自我”,“私小说”便无法存在。“私小说”本身就是某种自我意识过剩的产物。
然而两位“私小说”作家并没有顺着三浦的思路去展开“对话”,他们只是强调了当代“私小说”作家关于“自我”的认识。日野启三认为,应当由写作行为本身的特征来强调自我的意义。就是说,“自我”并非“私小说”独有之物,“自我的暧昧化”并不一定扼杀写作。写作首先需要的是自身的体验。写到写小说,日野启三认为可以写“自我”、写他人、写物体、写树木、与夕阳……人的一生中可数万次观赏夕阳,但是,自我真正地观照夕阳,遭遇夕阳,进而自我被夕阳观望的体验,一生之中却非常少。这样的体验,乃是文学的核心所在。日野的表述是一般性、文学化的、泛指一切的写作,当然也包含了“私小说”。他们作为作家探究的似乎并不是“自我”的历史性存在本身,而是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例如佐伯一麦也表示,自己在创作时,经常一口气写二三十页,但是到第二天又废弃了,因为“我”在不断地变化,作为探究对象的我并不一定就是现实的我。显然,他更加关心“自我”对于创作的意义,或对于“私小说”的绝对真实性表示出一种怀疑。日野认为最最棘手的,是考察基于哪一层次之上的“自我”或如何复合性地把握“自我”。换句话说,作为对应物的非我是什么?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但对立物总是存在的,他人与我或者世界与我、虚无与我等均是涉及自我的对立项问题。他说“自我”一开始就不是封闭的单元,在现实与“自我”的关系中,二者具有互损性,即相互作用与改变。这些关于“自我”的理性认识,反映了当代“私小说”作家的认知方式。不论传统“私小说”作家是否这样看待“自我”与外界的关联,这种认识本身是不会错的。
三浦雅士亦表示同意佐伯和日野的观点。他说所谓“自我”,一开始便处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有我与反我之分。“我”之概念原本包含着他人的关注。而他人的目光犹若方程式,首先必有一个X,X的变化值无限大。其实这样一来,“自我”就成了一个不确定值。那么如何以这样的“自我”来框定传统“私小说”的特定含义呢?显然,三浦也在怀疑传统“私小说”样式上的纯粹性。他说,“我”一涉及“私小说”,总要发生混乱。你们所谓的“自我”说到底是一种人类存在。非常奇怪的是,一般论及“私小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私小说”,其人物必须众所周知。这里的现实与作品,总在寻找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创作与批评上的认同,贯穿了战前的大正、昭和年间。换句话说,阅读原本意义上的“私小说”,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比如说阅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需要具备阅读的前提亦即事先了解大江健三郎这位作家过去的生活方式,以及与这部小说无关的其他小说或其他行为。三浦非常婉转地指出,日野、佐伯二位作家的“私小说”定义,给人以过于宽泛的印象,因而不同于三浦指称的感觉性“私小说”。毫无疑问,当代作家、评论家面对“私小说”苦思冥想时,亦会存有很大的认识差异。
其实,三浦雅士从根本上就怀疑作家自我与作品人物的同一性。他说,说到底,人类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对自己说谎。对自我而言,在编织有关自己的故事时,也是在编织一种谎言。……不过一种体验越到后期,越能允许种种不同的解释。
“私小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人们又为何始终无法释怀呢?对此,大江健三郎近期也说,对于日本的“私小说”,国外的研究者也关注备至,“私小说”的确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但要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原因在于“自我”的多样化与意义不确定。也许某种模糊的文学性描述更加贴近样式的本义。前述佐伯一麦的说法富于启示性。他说手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私小说”的原型。此时亦即在这种想象中,意念是绝对地脱离自我的。自我此时被客观化,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我在生存的过程中,会将体验性的伤痛转化为浮夸式的能量。总而言之,“私小说”对于作家,毋宁说是一种自戕式的享乐。在某种精神“力比多”的释放过程中,作家自得其乐地享用自我客观化观照的快感。但说到底,它又是贵族文化的产物。因为这种精神自慰无论从创作上讲,还是从阅读上讲,都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文本预置。否则无法获得快感,更无法观赏客观化的自我。
综上所述,“私小说”的确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传或自我小说。但是这种小说样式,外观上、本质上的确又包含了自传的特质,同时“自我”问题始终构成它的一切问题的中心。也许,“私小说”同样也属于雅克·德里达所谓的“臆说”。德里达说并非所有的文学都属于“虚构”体裁,但所有的文学中都存在虚构性。同时,碰巧德里达对自传类文体有着特殊的好感,他说“在最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搜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的确是使我发生兴趣的地方。我并不是唯一对这种机制的能力感兴趣的人。我努力去理解它的法则,而且还想界定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法则的形成永远不能结束或完成。”(注:[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即便这种引用只是一种误读,它同样构成了深入探究的一种动力。
标签:小说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棉被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文学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日本文学论文; 破戒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明治时代论文; 田山花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