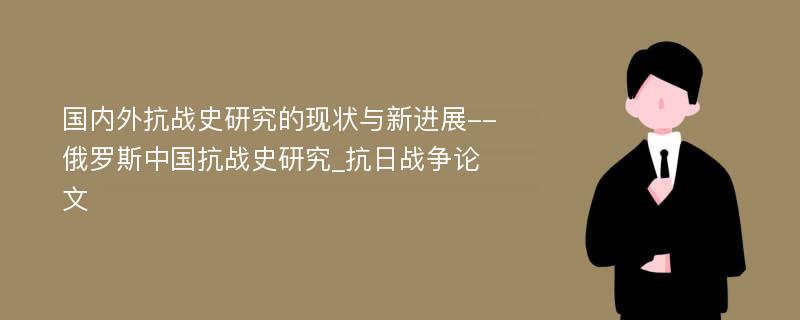
“国内外抗战史研究现状与新进展”笔谈——俄罗斯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笔谈论文,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全世界都要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些国家的元首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亲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中俄两国也要共同举办一系列活动。 众所周知,中俄两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而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8年多的时间里,在日本侵略势力猖獗的东方,是中国独力抗战,支撑着东方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场。 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很多。俄罗斯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此文只能简述近十多年来俄罗斯的研究特别是史料方面,重在介绍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引发的某些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近十多年来,俄罗斯学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即中国抗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中能够看出俄罗斯学界的动态。为了解其变化,首先需要做一个极其粗略的回溯作为铺垫或衬托,以说明某些重要问题在并不缺乏史料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得到客观阐述。 苏联时期,这类方面的研究论著有一定的数量。 最基本的文件见于苏联外交部所编的24卷本《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涵盖年代是1917~1942年,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从1958年开始至2000年出齐;此外有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编辑的《苏联、斯大林与中国命运》(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多卷本大型档案文件。 专著类有季托夫:《为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奥夫奇尼科夫:《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尤里耶夫:《20~4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中共武装力量》,1981年版。 重要回忆录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大使回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崔可夫:《军事顾问出使中国纪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回忆录集有《中国旅程1937~1945》(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在苏联时期,由于苏联史学的意识形态化或曰布尔什维克党化,即使有足够的史料,一些重要问题也遭到屏蔽或片面阐述。如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咄咄逼人,中国急需全国团结抗日,但苏联和共产国际依然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把国民政府置于被推翻的地位。在外交上,苏联对中国继续推行其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谋求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改善关系,设法保障苏联东部边境的平安;另一方面又通过共产国际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对抗并试图推翻取代这个政府。最明显的是1932年10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在这次全会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号召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因为此时的“蒋介石仅仅是向国际联盟发一些电报哀求后者主持正义”,并不认真抗日(参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党务出版社1933年版)。 在同一年,国民党从国家利益和世界局势考虑,决定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在1932年12月12日由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颜惠庆与苏联代表李维诺夫换文,仅仅用10分钟就交换了复交文件,是日下午5时成为中苏关系上的重要转折点,中断三年的中苏外交关系得以重续。 但是两国关系并不和睦。在中国遭到日本侵略的形势下,在上海发生一·二八抗战的重要事态后,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人民“保卫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苏联,要求“中国工人奋起回击资本的进攻”,从而激化了中国的劳资矛盾,“任何经济斗争都发展成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斗争”。至于中国抗战,共产国际立足于让中国共产党立即掌权,相信它“定将在帝国主义反苏和反华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速记记录》下册,第22页)。为加速中共掌权,共产国际让中国无产阶级通过组织罢工运动等立即实施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共产国际向世界共产党传达的声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要支持中国人民反蒋和倒蒋。文件称国民党一直在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罢工,1931年镇压了73万人的罢工,1932年头4个月受到镇压的就有43万罢工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速记记录》下册,第168页)。 共产国际的政策激化了国共关系,国难当头时,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依然决定“嗣后仍须努力清剿”中共及其红军,使之不“得以死灰复燃”(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蒋介石的政策从“攘外应先安内”发展到“攘外必先安内”,连续以几十万大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共产国际的方针有激进之嫌,指导中共“大力发展”中国苏区和争取无产阶级在抗日斗争中的领导权”,导致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会速记记录》下册,第175页)。 其间,中东铁路再起风波,不仅有伪满洲国的出现,而且因苏联决定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伪满洲国事实上得到苏联的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益发有恃无恐。中国有人愤怒指出“国联各会员国,尚无一国承认伪国为独立国”,苏联的做法与其宣传的“爱好和平之愿望相反。”(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舆论认为这是苏联昧于法律之观念,蔑视中国主权。 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苏联史学长期以来延续着的观点,无非是蒋介石不抗日、反共,共产国际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奥夫奇尼科夫:《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然而,这样的结论似是而非。1931年开始的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苏联史学中一度云遮雾障或出现一个断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即共产国际档案馆等部门组织名学者编选并公布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重量级的档案史料。主要有如下史料和著作。 《二十世纪俄中关系》中的第3、4、5卷《苏中关系》,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2000、2005、2010年出版。文件涵盖了从1931年到1950年中苏国家关系的史料。这些珍贵文件是收集的俄罗斯总统的档案,一般人很难看到。 《季米特洛夫斯大林通信1934~1943》,2000年,英文版。这是美国利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文件编辑而成的(下用《通信》)。 《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共产国际1919~1943》,莫斯科:社会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这本书是原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一批专家编辑的(下用《政治局》)。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合编,5卷8册,系大型档案文件集,取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出版单位先后不同。书的第一卷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有不同的译本。 《中国通史》一书,由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主编,责任编辑玛玛耶娃。书的上限是远古,下限到21世纪初。其第7卷《中华民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作者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一批汉学家。 这些文件和著述为研究者冷静地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进行分析和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以上档案史料是研究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和多边国际关系的重要依据。因篇幅所限,笔者仅仅介绍新出现的材料本身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的突破。 1.蒋介石一度是“革命对象”。新公布的档案文件集《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卷中有大量文件说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活动及其与中共配合反蒋,争取中国的苏维埃化,所以这一卷的书名就叫《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1927~1931》。尽管如该书编者在导言中说,当时中共的许多“左”倾决策共产国际并非完全知情,但莫斯科对中国政策的基本脉络依然清晰可见并且因书的出版而更加充实。 传统史学观点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政策的转折点。事实上莫斯科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因此决议而泾渭分明。 在对华政策上,莫斯科政策的真正转变要晚得多,是在1936年中后期,中共完成长征恢复同共产国际一度中断的联系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收到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的电报,才了解了中共情况,1937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发言为中共政策定调,其中的要求尽管充满矛盾(如让中共一面扩大苏区、进行土地革命,一面又要中共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激进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成为建设民主中国和抗战的中流砥柱,因为蒋介石不想建立“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故要以中共实力逼蒋抗日),但是无论如何,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中“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已经淡出(《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下册,莫斯科:社会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2~1063页)。7月的这个指令明确,中共的任务不应当仅仅限于“扩大苏区”了。 新公布的史料告诉读者,在此前后莫斯科出现过一个鲜为人知的计划和为实现之而进行的工作,这就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度筹备的组建“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为形式的民主政府的计划,其要旨是以19路军和中共的红军为主干建立抗日联军,收复失地,立即组织抗日。中共应当成为该联盟的实际领导者。为此,陈铭枢到了莫斯科,并与有关的中外人士具体讨论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中共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初次披露了这件事情的始末。但是种种因素使这个计划搁浅了(《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下册,第1040~1076页)。不过反蒋的调门直到1936年年终也并没有因之降低。 2.新的史料充实了关于西安事变的酝酿和解决过程,揭示了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态度,以及事变后共产国际何以急剧改变对蒋介石的政策。 就西安事变的处理和结局,《政治局》《通信》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把许多事件有机地链接为一个整体。如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1936年11月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等事件,引起了世界局势的进一步动荡,苏联的国际环境恶化。德、日法西斯政权决意共同对付苏联等共产党势力。就中国而言,日本认为可以利用国共关系的复杂状况以及国民政府对苏关系中的不睦因素而拉拢之,但蒋介石立场鲜明地表示,“我恃自力抗战”,没有加入德日的“反苏”行列。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审视其对日政策。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对待日本奉行的是“超谨慎”的方针,那么西安事变的发生使苏联对日的基本态度有了更加明显地表露。 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去苏联史学界强调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2月16日的电报,似乎这个电报对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作用。但是其前因并不清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上册,第1084~1087)和《通信》新公布的文件让人看到,这乃是莫斯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的结果。 原来得知事变的消息后,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和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季米特洛夫都有些不知所措。电话一端的斯大林质问另一端的季米特洛夫对事变是否知情,斯大林怀疑过王明参与其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紧急连夜会商。翻阅反映莫斯科上层精神状态和处理此事件的新史料,读者会产生类似看好莱坞大片的印象。 实际上这里另有隐情。在上述那个拟议中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革命联盟”里没有蒋介石,他是被推翻的对象。西安事变发生,在张学良掌控蒋介石,甚至可以说完全有可能立即将其“推翻”的时候,莫斯科并没有喜形于色。它一方面立即公开利用《真理报》发表声明,指责张“受日本支使”,认为张的行为“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莫斯科根据其所持“超谨慎”以免刺激日本的立场,把自己与此事切割得干干净净。此外,是苏联极力避嫌,不刺激国民党,通过共产国际于1937年1月指示中共“不要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同时指示中共“不宜过分强调同苏联结盟的口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就和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3页)。 《苏中关系》第4卷的一些文件,清晰地勾画出苏联的担心。前述那个政府性质的“中国人民革命联盟”已经成为泡影。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得利的只能是日本,而苏联的东部边界将陷于日本侵略威胁之中。 在中国国内,中共据共产国际指示,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工作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并做出4条保证: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在特区内实施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指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8页)。 但是蒋介石对中共依然不依不饶,上电两天后,国民党于1937年2月12~22日举行五届三中全会。他激烈批判中共历来推行的阶级斗争把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阶级斗争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被其斥之为“谬说”,全会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声明要把“赤化宣传”及红军一律“根绝”(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5页)。这就是一些著述中常说的蒋介石要继续“剿共”。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促进中国国共两党抗战继续做着努力。半个月后,1937年3月8日,进一步做出积极促进中苏关系的姿态,包括安排在苏联生活达12年之久的蒋经国回国,承诺向中国提供相当于五千万墨西哥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同意在苏联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等。援助固然重要,由苏联派遣一个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国际上又是一个重要的姿态。当英美等国“谨慎”对待日本的时候,苏联的这一外交举措对艰苦抗争的中国人民是一个有力的国际声援(《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40页)。 研究者可以根据新旧史料特别是新出版的档案文件,以《蒋经国归来》为题足以写出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剧。 3.关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秦孝仪主编的《战时外交》公布了比较全面的珍贵史料。《苏中关系》第4卷中公布的蒋介石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人员的通信和谈话,就涉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史料,对于秦书是重要的补充。 该书发表了蒋介石致斯大林的十多封函电,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中国的艰难处境,从中能够看出从1931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近十年里,中国如何苦苦支撑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战场,使日本侵略军在这里陷入深深的泥潭,为其后来的灭亡埋下了种子。这本身就是中国的巨大贡献。 这些文件丰富了战时蒋介石与斯大林交往的内容。蒋介石主张与苏联携手对付日本侵略,具体地是请苏联出兵。苏联史学界过去的观点是蒋介石想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人们从蒋介石本人的信件和他做的外交试探中能够明白,为什么直到1945年8月苏联才出兵中国东北。中苏围绕这个问题的交涉前后延续8年,几乎贯穿中国抗战的全过程,直到1945年。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拒绝,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理由,但他的基本考虑是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所以,他支持中国抗战,把日本拖在远东,减轻其对苏威胁。 这五个阶段大致是:1937年11月至1938年初;1938年2月苏联承认伪满洲国至1939年8月;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珍珠港事件后至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苏联出兵(李玉贞:《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斯大林》,《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131~134页)。 蒋介石最早提出请苏联出兵,是在1937年10月淞沪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他通过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命令正在苏联的杨杰向斯大林打探苏联能否立即出兵(《战时外交》,第334页)。11月1日,杨杰正式向苏联提出这一问题。伏罗希洛夫表态:“苏联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敌人都不少。我们还没有为全线出击所有敌人做好准备,不过,很快就会做好准备的”(《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136页)。 蒋介石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让杨杰再次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传达:苏联是中国唯一的盟友,中国不是想立即把苏联拖进战争,但是请苏联保障东西方的和平。斯大林却十分巧妙地为杨杰“鼓劲”,实际是给以拒绝。他说:“即使现在日本把中国打败了,日后中国也一定能报仇雪耻。”(《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136页)至于苏联的立场,斯大林谈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苏联肯定帮助中国抗日,而且要派遣技术专家和军事顾问前来,但是他希望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和军事工业,这是根本的,比如可以自己造飞机,甚至可以造木质飞机;二是苏联坚决支持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而且为他牢牢掌握军权“出招”:伏罗希洛夫显然传达斯大林的意图,认为此时蒋介石应该“当一个独裁者”,要用铁腕保证军令畅通,务必把“每一个不听调遣而动摇不定的将领和督办牢牢掌握起来。如果形势需要就把任何一个拒不从命或变节的将领通通除掉”(《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138页)。 蒋介石没有罢休,他于11月30日再次致函斯大林称:“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挽救东亚之危局,巩固中苏永久合作之精神,皆维先生是赖也。迫切陈词,尚希垂察。”(《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164~165页) 1938年2月,当孙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莫洛托夫回答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卷入战争,那么锋芒就会指向我们”,“中国就没有可能再利用其他国家的援助,届时有些国家会转而支持日本”。而且,虽然日本经常试图侵犯苏联边界,但毕竟苏联领土上还没有日本兵。如果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就自然会认为这是侵略行为,而且这种做法会在日本人民中引发日本军阀企图煽起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199页)。 当孙科在该年5月23日再次提出请苏联出兵牵制日本远东的兵力并抑制其侵略势头时,斯大林明确说“不”,因为“苏联军队已经牵制了40万日本精锐部队”(《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249页)。 1939年苏德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波兰受到沉重打击。蒋介石希望看到相对弱小的波兰能够得到国际援助,而不是相反任由大国宰制。他担心中国沦于进一步被侵略而得不到正义援助的境地,便径直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发问:一旦希特勒进攻法国,苏联会采取什么立场?英日之间是否会有类似的条约出现,等等。但其中最敏感而直接涉及中国的便是:苏联是否准备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487页)。孙科自然希望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但是他在莫斯科无可奈何地建议蒋介石,同苏联“接洽,切勿要求参战,转移中倭战争为苏倭战争”。不过,此时苏联并没有改变援华抗日的方针。通过与苏联领导人的一系列会晤,孙科告诉蒋介石的是:“苏援我程度,似限于器械供给与技术协助,若求其仗义参战,解决战局,恐不可能。”(《战时外交》,第81、82页) 珍珠港事件爆发,斯大林于1941年12月8日“恳请”蒋介石“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然而斯大林毕竟承认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对轴心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况且苏联并没有拒绝,反而正为击溃日本做实际准备(《战时外交》,第392页)。那时苏德战火正酣,苏联不可能出兵对日是不言而喻的。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立场:在某个特定时期前,苏联不直接与日本对阵。苏联愿意并且帮助中国抗战,把日本兵力拖滞在东方战场。 至于1945年的苏联出兵,这里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战争期间,苏联从国家安全考虑,不再坚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再坚持消灭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因为首当其冲的是,苏联在国家安全方面需要做出实用主义的选择。《政治局》中有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解散时的一段话:“无论马克思和列宁在世时的经验,还是今天的经验,都已经表明,不可能从一个国际中心去领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当初建立共产国际时,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能够把全世界的运动领导起来。这是我们的错误。”这话意味深长。它与1937年季米特洛夫同蒋经国在后者回国前就中国苏维埃问题的谈话,可谓异曲同工。 4.关于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就这个条约的性质,《苏中关系》一书和新出版的《中国通史》公布的史料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种。 一是《苏中关系》一书中公布的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在1949年1月底到2月7日访问西柏坡时,于2月6日对中共领导毛泽东等人说的话。他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欠妥的,是“不当”的,不平等的。他举出了旅顺和大连的条款为例,并说如果中共同意,苏联可以尽快撤出。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表示惊奇,不同意苏联立即撤军,认为要等待时机[《苏中关系》第5卷下册,中文参见王福曾译:《俄罗斯公布的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与米高扬的会谈记录》(上、下),《党的文献》2014年第2期、第3期,分见第3~18、3~13页。李玉贞:《毛泽东同米高扬谈建国蓝图》,《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第1~9页]。 二是《中国通史》认为这个条约是“建设性的”(《中国通史》,第407页)。 把米高扬的上述说法与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和《我在苏联的日子》,以及当时的《东方杂志》和《中央日报》等相对照,对于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获得新的感悟。 众所周知,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就中国问题做出了违背中国利益的决定,大国背着中国拿中国主权做交易。协定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做了明确规定。苏联要使用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从那里到大连及旅顺港的铁路线,以及从哈尔滨向东到尼科尔斯克再到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的铁路线,在那里同哈巴罗夫斯克铁路线连接;苏联需要中国的旅顺和大连这两个不冻港作为出海口。1945年7月中苏条约的谈判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外蒙古问题和旅顺、大连问题,谈判遇阻,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撤回并中途换马。谈判中,宋子文则把斯大林的立场与沙皇俄国相比,他反驳称:“旧条约即无战事亦当满期,且为帝俄所为之宣言,余思阁下不致以该条约为依据。”(谈话的俄文记录在《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75页没有“余思阁下不致以该条约为依据”这个语句。此处引自《战时外交》,第580~581页)。 中国以艰苦卓绝的抗战和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中国并未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得到一个战胜国应有的全部成果。种种情况令人扼腕,个中教训值得深思。 苏联从条约得到了什么?俄罗斯权威学者们认为,这个条约“的确具有重大意义。苏联拿回了俄罗斯据1896年条约、同中国签订的其他条约所享有的,但由于俄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和日本后来的其他侵略行动而失掉的权利和优越权益。苏联了收回了利用旅顺、大连海军军事基地的权利。这两个不冻港为苏联的军舰和商船驶入太平洋和世界广阔水域开辟了一条无障碍通道。苏联得到了和中国共同利用当年由俄罗斯出钱建造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这两条铁路保证苏联拥有一条从莫斯科到远东疆界的捷径……苏中在满洲的合作可以成为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的强大基地和极大的推动力”(《苏中关系》第4卷上册,第23~24页)。 对于上述论点,研究者可以仁智各见。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上述观点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沙皇时期的俄国对华政策区分开来。确如一些俄罗斯学者所说,共产国际的活动,“从来没有站在违背苏俄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政治局》,第5页)。意识形态因素从这里淡出了,苏联史学界长时间里一再重复的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等字眼不见了。事实上,与其说什么主义,莫如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更容易把问题说透。 收稿日期 2015-05-16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斯大林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历史论文;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论文; 中国通史论文; 通信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莫斯科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