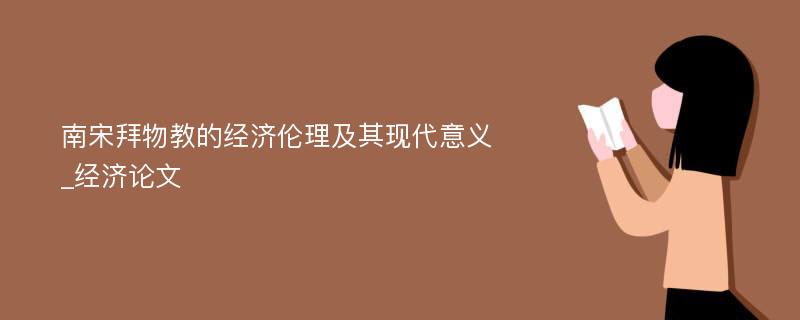
南宋事功学派的事功经济伦理及其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功论文,学派论文,南宋论文,伦理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07(2014)03-0035-07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浙东地区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在浓郁的商业氛围中,形成了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他们倡导务实事、求实功的事功伦理思想,特别是在继承和发展唐代以来重商思潮的基础上,倡导以农商并重、四民平等、藏富于民和保护富人为核心,极具事功色彩的经济伦理思想,在理学大兴的南宋思想界独树一帜。 一、农商并重的生产伦理 事功学派的重商思想得益于浙东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是唐代以来重商思潮的延续和发展。然而。事功学派并没有忽视农业的重要性,陈亮明确表达了农为国本的主张,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墮农有罚,游手末作有禁。”[1](P215)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石,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衣食温饱,也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实现国家富裕的基本前提,必须“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1](P215),劝民农耕,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才能实现国家稳定。陈亮希望后世君主效法汉文帝与民休息、鼓励农耕的政策,使农民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明确反对把农业看作“日用之粗事”,赞同周公视农业为“王业”的观点,认为“此论治道者所当深体也。……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能君其民未有不能协其居者”[2](P71)。在叶适看来,农业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如果不重视农业,就谈不上国家治理。 在重视农业的前提下,事功学派阐发了“农商并重”的思想。陈亮认为农业和商业均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并无高低、轻重、本末之分。“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1](P140)农业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二者不是矛盾对立,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是基础,如果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商业繁荣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商籍农而立”;同样,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商业,商业交换活动的活跃,将加速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增强经济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农赖商而行”,因此,农业与商业必须“有元相通”,“求以相补”,而不能“求以相病”。叶适批评了传统的厚本抑末论,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P273)。他运用借古论今的方法,认为厚本抑末并不是古人之意,恰恰相反,在汉代之前,对工商业不但不加抑制,还给予鼓励,他说:“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2](P273)其实,在汉代之前,重商思想十分流行,但亦有重本抑末的思想,法家的韩非子就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工商业者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他们“不垦而食”(《韩非子·显学》),是国家的“五蠹”之一。 事功学者重视商业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主张四民平等。“四民”即士、农、工、商,这种职业划分早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周文王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逸周书·程典》)要求士、大夫与工、商等每个阶层各司其职,各专其业,否则,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都不可以成治。秦汉之后,历代统治者大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很低,常处于四民之末,甚至不可以入仕为官。从唐代中期开始,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有所改善。到了宋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商业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官员经商和商人入仕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和尊卑关系开始逐渐被打破,范仲淹曾作《四民诗》:“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四民诗”)陈亮、叶适等人认为“四民”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经商并不是件羞耻的事。陈亮在科举失意时,曾有经商的念头,他说:“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1](P321)。有学者认为,陈亮确实从事过商业活动,并以此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叶适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的作用不同,但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同样重要,“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2](P273),四民应当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作用。当然,叶适并不认为四民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相反,他认为商人可以进入士人的行列,入仕为官,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参政机会和权利。 客观而言,在以农为国本的小农经济时代,陈亮、叶适倡导四民平等说,旗帜鲜明地要求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反对针对商人的各种限制措施和歧视,努力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体现了对封建特权阶层的抗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个性自由和个体解放等近代思想的意蕴,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然而,中国古代的商人并没有真正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完成向近代资本主义商人的转变。其原因十分复杂,如果从商人自身来看,尽管他们之中不乏一些掌握巨额财富的大商巨贾,却并不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到商品再生产领域,使其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将大部分的商业利润用于购买土地、建造房屋,以保障财富的稳定性并满足自己的享乐,或者投资政治、买官入仕,谋取政治权力。这样一来,商人实质上依旧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地主或官僚,“不能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从而无法在政治上获得西方社会市民阶级那样的自治权利”[3](P152),因此,很难成为推动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主要力量。 二、富民为本的分配伦理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农业生产提供给社会的财富总量有限,其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财富的分配便显得尤其重要。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二是不同阶层或不同劳动者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 两宋时期,理财问题或者说富国与富民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统治者。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统治者的奢华生活和数额巨大的官俸,宋王朝不得不在如何理财上大费脑筋。叶适认为理财是历代圣君贤臣的职责,如果认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将理财仅仅理解为普通百姓之事,就大错特错了。他进一步指出,要制订正确的理财政策,必须认识到理财与聚敛的不同,树立正确的理财观,他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4](P657-658)在叶适看来,真正的理财是理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取之于民而不使民贫,其实质是财富在君与民之间的合理分配,也即富国与富民的问题;聚敛则只考虑“供上用”,而不关心民之“用”,只求富国而不关心富民。前者是与天下为利,后者是君主的自利。周衰之后,人们混淆了理财与聚敛,甚至把理财误解为聚敛。从表面上看,聚敛的方法能够迅速地将财富聚积于朝廷,可以实现富国,但这只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并非真正的理财之术和富国之道,必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叶适指出,正确的理财方法不仅应当处理好敛与散的关系,有敛有散,还应当从“开源”做起,所谓“开源”,即发展生产,最大可能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的财政危机。 叶适等人宽民、利民、富民以及民富而国自富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这种呼声对于减轻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利益的侵害和盘剥,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事实上,民富与国富是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的。人民富裕了,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必然为国家繁荣富强所做的贡献就多。同样,国家富强了,具备了雄厚的财力,才能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 财富在不同阶层或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问题也历来受到重视。如果大量的财富积聚于少数富人之手,必然增加贫困人口的数量,拉大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的分配原则。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人群体的产生和壮大。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使得商人数量迅速增加,富人群体不断扩大,同时伴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富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羡慕和赞美,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浙东地区,经商致富为荣的观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陈亮在《东阳郭德麟哀辞》和《何夫人杜氏墓志铭》中称赞家资巨万的富豪郭彦明、何坚才有过人之智,何坚才“善为家,积资至巨万,乡之长者皆自以为才智莫能及”[1](P499)。陈亮不赞成财富的平均分配,他认为,人的地位有高卑之分,能力有大小之别,所以财富分配不可能也不应该平均。陈亮还进一步指出,富人的存在不仅是合理的,还应当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如果抑富扶贫,就会挫伤人们致富的积极性,使那些能力低、不努力的人分享别人的劳动财富,社会便会失去前进的动力。 叶适跟陈亮一样,明确主张保护富人,反对抑制土地兼并。自北宋开始,由于奉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土地买卖成风,土地分配不均现象日益突出,为改变这种状况,一些人提出抑制土地兼并,恢复井田制的主张。叶适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其意图虽好却不可行,因为富商大贾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将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政府养小民,富人不仅向穷人出租土地,借给穷人耕种所需的劳动资料,还借钱给穷人救急或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供上用,富人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不但养小民,还养天子、官吏,因此,叶适认为通过抑制兼并来掠夺富人财富,并不是明智之举。当然,对于那些为富不仁、违法乱纪的富人,叶适认为应当由官吏加以惩处,但对于所有的富人来说,如果“豫置疾恶于其心”,一概施以惩抑之策,则有违富国利民之道,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 叶适等人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极力美化富人,为富人辩护,扮演了一个工商业阶层代言人的角色。客观而言,叶适对富人作用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保护富人的思想对于鼓励人们致富,发展私有经济,促进工商业发展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这一思想的局限性甚至谬误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穷人被迫向富人租地、借钱,甚至不得不沦为富人的奴仆,受富人的剥削,叶适却认为这是富人在替政府“养”穷人,明显歪曲了富人与穷人关系的本来面目,掩盖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剥削关系。 三、事功经济伦理对浙东精神的浸染 事功学派经济伦理思想中的重利富民倾向在浙东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以后,这种重利、重商和富民观念在浙东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到晚清时期的孙诒让、宋恕等永嘉学者,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念,经过数代浙东学人的努力,重利富民观念逐渐深入到浙东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浙东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动着浙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陈亮家乡——永康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以五金制造最为有名,在元末明初就有了“百工之乡”的美誉。时至今日,五金制造业仍是永康的特色产业,永康也因此被称为“五金之都”。浙江经济的另一个重镇——温州,近些年经济迅速崛起,也受益于浙东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商业精神。温州人不仅善于经商,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还特别勤奋,他们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温州经济以富民为核心,被人称为“民营经济”或“老百姓经济”,[5](P308)这与永嘉事功派“藏富于民”的富民思想一脉相承。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者,温州政府部门特别重视对“民利”的保护,“从承认‘商户’到扶植‘两户’,从保护‘挂户’再到支持‘联户’等形式的股份合作制,在温州经济前进的每个关节上都甘为民仆,保驾护航,充分展示了温州政府执政为民的现代风范,也弘扬了温州本土永嘉学术以民为本、德政双修的传统官德”[5](P309)。为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保护个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生产积极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市委、市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关于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定》等等,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 当然,重利富民的事功经济伦理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浙东地区的并不全是积极影响,由于自身的理论局限性,事功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浙东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尽管事功学派力图将道德与事功统一起来,把事功标准纳入到道德评价中,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是,当重实事、求实功的事功经济落实到社会实践中时,容易使人在追求利益时忽视道义原则,一旦将事功追求凌驾于道德原则之上,为求一己私利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便会引发社会冲突,最终使个人的正当利益也无法实现。以温州为例,在温州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也有少数温州商人急功近利,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偷税漏税,或者利用政策和制度上的不完善,投机钻营,获取不义之财。近些年来,更有一些企业不顾社会责任,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违反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将生产过程中的污水、废气违规排放,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行为与事功经济伦理存在着某种联系,也可以说是这一伦理观念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如果将这些行为完全归咎于事功经济伦理,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事功学派并不是教人追逐个人私利,也不是教人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他们提倡的事功是指国家的事功、社会的事功,实质是一种公利主义伦理。所以,对于事功伦理的实际影响应当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能过分抬高它的现实价值,也不能因为一些负面效应而否认其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意义。 四、事功经济伦理对韦伯命题的回应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因归于基督教新教伦理。他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先产生于西欧这一事实着眼,在系统分析和比较了犹太教、基督教新教、儒教、道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基督教新教的伦理观念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其它宗教则做不到这一点。在他看来,儒教的内圣之学是完美的,但由于缺乏一种实用有效的工作伦理,导致内圣的理性主义无法对现实生活的理性化发生作用,内圣和外王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韦伯视儒家为儒教的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因为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从他对儒家伦理的分析来看,还是很有见的的,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儒家伦理的实质,但由此得出儒家伦理阻碍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结论,却是值得怀疑的。 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成长来看,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作坊和雇佣劳动,但中国的确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如果从伦理观念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寻找原因的话,不可否认,宋儒过于强调成圣成德的内圣之学,以为专心于内圣工夫就可以开出外王事业,特别是朱熹理学将传统儒家的德性伦理推到了极致,视义利关系为“儒者第一义”,告诫人们专向义边作,这种重义轻利的德性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求利行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尽管陈亮、叶适试图以事功伦理补理学德性伦理的偏失与不足,同时为人们的商业活动的正当性提供伦理支持,这对于萌芽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不幸的是,事功伦理终究没能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发挥更大的影响,很快便被理学的德性伦理所湮没了,这也是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此而言,韦伯关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关系的观点确有合理之处。 如果将儒家伦理分为两派的话,一派是德性伦理,另一派则是事功伦理。韦伯对儒家伦理的认定,无疑是将儒家伦理等同于德性伦理,忽视了事功伦理。其实,德性与事功的分离、对峙彰显于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在孔子那里,二者是综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轻重之分。孔子重视德性修养,但并不否定事功的重要性;重视农业,但从不贬抑商业,也不轻视商人,善于经商的子贡,是孔子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之一。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商业不但没受抑制,反而一度十分兴盛,人们发现从事商业活动比从事农业生产的获利要丰厚得多,于是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竞相逐利的风气,进而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剧,也凸显出道德与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这样一种‘逐利’之风感受至深并给予莫大关注的既不是道德至上的儒家,也不是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而是主张对商品货币关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消灭的法家。……众所周知,韩非是‘重本抑末’思想最为彻底的阐发者,而且他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发展成为现实国策,一次又一次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后世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P32)由此可见,先秦儒家的“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德性伦理与抑商思想之间并不存在因果性的必然联系。反倒是法家成为最激进的重农抑商派。到了汉代,儒学被“定于一尊”之后,许多儒家学者将先秦法家的重农抑商思想奉为治世良方,使重农抑商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以韩愈、李觏、苏轼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儒者仍然坚持重商思想,二者之间的争论长期存在,所以,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判定儒家伦理阻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南宋事功学派兴起之后,儒家伦理思想中注重事功的一面彰显出来,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事功派学者公开为商人辩护,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发展商业,以实现富国强兵。这种事功经济伦理无疑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当然,事功伦理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促进的,陈亮、叶适等人倡导的事功伦理为浙东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重要的伦理支持,同时,事功伦理之所以能够在南宋浙东地区兴起,而没有在其它地区产生,也得益于南宋浙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由此而言,儒家德性伦理是否对商品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不易确证,但事功学派的事功伦理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契合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收稿日期:2013-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