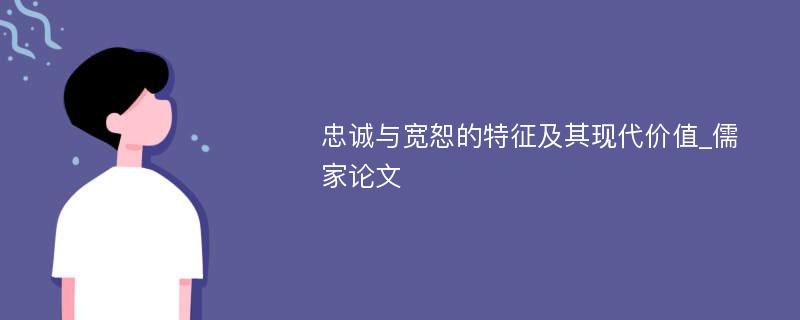
忠恕之道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特质论文,价值论文,忠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忠恕之道:儒家的人道理念
忠恕之所以被称为“道”,是因为它表达了儒家的基本理念。在儒家观念中,“道”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天道”,二是指“人道”。人道与天道只是一个“道”,即如程颐所言:“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当然,程朱理学所谓的“道”和“理”都已经把天所含的义理实体化了,即已经作了形而上学的抽象,使之成为一个包容所有善德的实体。其实,在先秦儒家那里,“道”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超越者,不是一个包容所有德性的精神实体,而只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行为趋向和行为方式,由这种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具有精神意义的结果,就是“德”。这也就是儒家基本的思维逻辑:在“道”中有所“得”,就是“德”。这样,天道的集中体现就是“生”之德,人道的集中体现则是“仁”之德。而“忠恕之道”指的就是人的行为之道,即人道。
作为“人道”的忠恕之道,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忠道和恕道。
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直接给“忠”释义,《论语》记载了孔子一段话:“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一般认为这就是“忠道”。关于“忠”,《论语》倒是有不少的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学而》)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从以上的引录中可以看出,“忠”往往和“信”、“恭”、“敬”等概念并用或连用,可见“忠”主要表达一种态度和精神,即一种极负责任、极端正、极虔诚、极守信用的态度和精神。朱熹在解释“忠恕”时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又说:“或曰,中心之谓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他还引程子的话说:“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朱熹用理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把忠作了形而上的抽象,认为忠和恕分别表达天道和人道,从而认为忠与恕的关系就是体与用的关系,笔者认为,说忠与恕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说它们一个是天道,一个是人道,则有些勉强。其实,它们都属于人道的范畴,因为孔子明确地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称为“仁之方”,即实现仁、践履仁的方式,可见还是在人道的范畴内。
关于恕道,《论语》有这样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是指的要推己及人,自己所不愿意、不希望的事物,也不要加之于别人。《大学》对此有个较详细地说明:“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絜”本来是指用绳子来衡量、度量、推度物体的形状、粗细等,此处指衡量事物的准则、规则和法度。“絜矩之道”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自己所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它表示的是对别人的理解、尊重、体谅和宽容。
忠和恕一般并称为“忠恕之道”,因为它们表达的都是做人和待人的一种方式,也是求仁、行仁的基本方式。但是,忠与恕其实是两个概念,表达的是两个意思。根据朱熹的说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或者“中心之谓忠,如心为恕”,这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虽然都是实现仁的方式,但究其对象而言,前者是对自己本身的要求,后者是自己对待别人的方式;就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而言,前者是自己对仁道之觉识,以及这种觉识之后的“正己”、“勉己”、“成己”的精神与态度,即前文所说的一种极负责任、极端正、极虔诚、极守信用的态度和精神;后者则是在有了“忠”的态度与精神的前提下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即由己对己的关系延伸到己对人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忠”是对仁的意识、体验之后主体所具有的精神、境界、和态度的准备,而恕则是对仁道的具体之实施。所以忠与恕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是不可分的,若没有“尽己之心”(忠),就不会有“推己及人”(恕),或不会有正确的理念推己及人(如以恶念为前提推己及人);反之,若没有推己及人的恕道,“尽己之心”就永远只会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求仁和行仁最终就不可能实现。这正如南宋儒者陈淳所言:“大概忠恕只是一物。……盖存诸中者既忠,发出外来的便是恕。……故发出忠的心,便是恕的事;做成恕的事,便是忠的心。”在这个意义上,忠和恕的关系基本上相当于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笔者已在前文指出,“忠”往往和“信”、“恭”、“敬”等概念并用或连用,这不仅是因为“忠”涉及到行为者的品质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因为“忠”是对仁道的深刻体验。而仁道也就是人道,即如孟子所言:“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处的“道”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道指与天道对应的人道,其核心理念就是仁道,即人以其仁德来配天之“生”德,达到天与人的合一。另一方面,道指为人之道,即处理人与人关系之道,它是仁道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哪种含义,都包含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只不过,所谓“立”与“达”,从直接的意义上讲,是成人(即使自己成人,也就是成己)之意;但从间接的意义上讲,则是实现仁道之意;而往深处讲,那就是实现天之“生”的目的性的行为。所以程颐说“以己及物,仁也”。“以己及物”就是充分尽己之心、尽己之性,去成就万物(包括他人),这其实也就是以仁道(人道)配天道,通过人的积极行为实现天之生德。在这个意义上,朱熹所谓“忠者天道”有一定道理,但“忠”本身并不是天道,而是人在“替天行道”。
人以其仁道实现天道,需要一种能动的、负责的、积极的精神与意识,因为这不仅需要对天之“生”意与“生”德有深刻的理解和体悟,而且还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勉力行道。天之“生”意与“生”德,儒家用了一个极抽象、极有包容性的概念“诚”。儒家认为,天极有诚意化生万物、养育万物。认为“诚”是天之性和天之德,它对世间万物都是真实无妄、诚心诚意的,人就应该去领会、理解此“诚”,将之化为自己的品质与信念,然后去践履“诚”,使之变为现实。
因此,儒家大都认为人应以“诚”之精神去实现仁道。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他进一步论证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这里强调了“诚”的极端重要性和其强大的功能:天之诚,能够化生万物,人之诚,能够化融各种关系,乃至成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
这说明,“诚”被儒家理解天的一种精神,一种德性,一种品格,天对万物都怀着诚意,都以真实无妄、诚心诚意来对待人间的一切事物。那么,人要行人道,成仁德,就应该具备“诚”这种精神与品格。《礼记·大学》是专讲修身的学问,其中讲了八德目,但王守仁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这的确是抓住了《大学》的要义。《大学》在讲“诚意”时说:“所谓诚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谓诚,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世俗目的的手段,而只是因为“应该如此”,因而“诚”的第一要义并不是不欺人,而是不自欺,即“慎独”。只有首先不自欺,才可能做到不欺人,所以说“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需要说明的是,“慎独”并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极度的诚意和虔诚来行仁道,是对天之诚意的深切体悟和人之心性的透彻观照,即如有儒者言;“道者至诚也,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非他也,此尽性命之道也。”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忠”与“诚”是两个意义最接近的概念,是两个可以同构甚至可以互换的概念,今天我们已经将“忠诚”连用,正是由于它们原本具有相近的含义。虽然“忠”往往和“信”、“恭”、“敬”等概念并用或连用,但这都是“忠”之外在表现,即“忠”之精神和理念表现在外就形成了“信”、“恭”、“敬”等品质,但就其内在特质而言,“忠”是可以与“诚”通读的。既然“诚”是人“尽性命之道”的一种精神,因而它与天化育万物之诚是相通的,人以此行仁道(人道),以与天道合。在这样的意义上,“忠”就是人以诚信、诚意、诚信的精神与恭敬虔诚的态度去尽性命之道,即勉力行仁道,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兼善天下。
至于“恕”所表达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即如程颐所言属于“推己及物”的层面。尽管从字面上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出发点都是“己”,即观察、思考与行为的主体,但事实上,这两个“己”所表达意蕴是有区别的。前一个“己”是不自欺之“己”,是具有诚意、诚心之己,是以人道(仁道)去践履天道之己,这是一个“自立”、“自达”的过程,而此过程内在地就包含了“立人”与“达人”,因为人自成(成己)与“成人”是一个统一体。后一个“己”是不欺人之己,是以诚信、诚意待人之己:以爱己之心爱人,以待己之心待人;在不自欺的前提下不欺人。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为一种进取、刚强、虔诚、恭敬的精神与态度,那么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宽容、理解、尊重和仁慈的情怀,借用《周易》的说法,前者相当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后者则相当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们都服从于天的“生”之目的性,从而也服从于“仁”这一根本之人道,只不过侧重点各有不同。
二 忠道之现代价值:诚信与敬业
在儒家那里,忠和诚总是相伴相随的。诚是天化育万物的意志和精神,人“思诚”或“诚之”是人与天沟通的桥梁,是人的根本之道,人以此道行就是忠。诚如蔡元培先生所言:“子思之所谓诚,即孔子之所谓仁。惟欲并仁之作用而著之,故名之以仁”而孔子所谓忠,乃实现仁之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就是诚,诚也就是忠。此外,在《论语》中,忠与信又是经常连用的,如“主忠信”、“言忠信”、“必有忠信如丘者焉”等,说明忠与信本身就具有某种同质性。因此,从忠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演绎出诚与信这两个概念。
我们今天常将诚信作为一个词用,实际上,诚和信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词。诚在儒家那里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已如前述,它是和人道紧密相连的概念。在生活层面上,诚主要是一种虔诚、恭敬、诚实的精神与态度,总体上是一种真实无妄的品格。这一品格用于对己,就是不自欺;用于对人,就是不欺人。信与诚近义,也是指诚实、不欺诈、守信用。所以古人一般将诚与信互训。许慎《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言。”其实意思是大体相同的。信是儒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孔子这里,信还是一种内在品格,而到了孟子那里,信成了一种交往伦理:“朋友有信”,成为五伦之一。到了汉儒那里,信成了“五常”之一。
信从一种内在品格演变为一种外在的交往伦理,就开始显现出其与诚的区别来。虽然它们都还是表示真实无妄,表示诚实、守信用,但此时,诚主要是不自欺,信则主要是不欺人。即一个主要是对内——诚;而另一个主要是对外——信。根据《大学》“诚于中而形于外”的道理,我们可以说“诚于中而信于外”。这样,诚就是一种内在的品格、情操和境界,而信则主要是一种交往伦理和行为品质。根据这种思路,诚就成了信的根据和内在规定性,信就是诚的外在表现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为体,信为用。当然,我们把两个概念拆开分析,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它们的内涵,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诚与信是无法分开的:诚如果不表现为信,就不是真正的诚;信如果不是以诚为根据,所表现的信就是不可信的。正是由于这样,诚与信总是如影相随。
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在培养诚信品质时,就应该主要在培养内在之诚上下功夫,首先要培养自己对人、对事的恭敬、虔诚、认真、负责、尽心竭力的态度和品格,以此态度和品格来为人处事,自然就会有信了。
面对我国当前的诚信缺失,人们呼吁要加强法律监管,完善制度体系,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凭个人的良心自律来达到诚信是不可能的,利益诱惑常使得良心遮蔽甚至消失,常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做出违背良心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强大的法律监控和制度约束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人们的良心自律,没有内在之诚,任何外在的约束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人们的内在品质和精神素质达不到制度的要求,那么即使有完备的制度体系,人们也会千方百计钻制度的空子,制度和人的关系就变成了猫和老鼠的关系。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制度建设会永远赶不上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监管就会陷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恶性循环。
因此,今天除了加强制度建设之外,还应大力加强公民的诚信观念和诚信品质的培育。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秉承儒家的思想精华,首先在培养“诚”上下功夫。儒家的诚是实现天道的一种精神和品格,或者说,是以人道配天道的精神和品格;在此基础上,才是一种待人的品质。今天,我们虽然不必以诚去实现天道,但这种超越性境界还是我们今天所必需的。其次,诚信观念与市场活动联系最紧密的是,将诚作为一种内在品格,以此为基础,使信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品质,使内与外达到统一,即我们所说的“诚于中而信于外”。在这方面,儒家关于成人、成己、成物的理念仍然是我们应继承的思想资源。经济活动绝不仅仅是谋取利益的活动,而实际上是“成人”的活动——服务于他人;是“成己”的活动——成就自己,使自己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成物”的活动--将自然物通过劳动变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如此说来,经济活动就是人展示生命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活动。正因为如此,在经济活动中,人首先要有“忠”的理念,以虔诚、恭敬、诚实的态度支配自己的行为,做到“毋自欺”,做到“慎独”,这样才能对外做到“不欺人”,做到诚实守信,其结果就会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除了诚信之外,忠道里还包含有现代人所必备的敬业精神,因为说到底,敬业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一方面,敬业就是对己之诚:敬业本身就应该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即“毋自欺”。在一个岗位工作或从事一种职业不是为别人做的,而是展现自己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平台。因此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地做好每一件事,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自己对得起自己。对工作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实际上也就是在欺骗自己。或者说,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在贬损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敬业还包含了对他人之诚,即所谓“为人谋而不忠乎?”是不是虔诚地、恭敬地、诚实地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尽力地服务于他人?这虽然表现为“不欺人”,但实际上还是“毋自欺”,因为只有发自内心之诚,才有对人之诚。因此,敬业实际上是现代人的一种超越方式,是现代人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它靠的是主体的精神自律和高度的自觉性与能动性,而不是单靠规章制度的约束和物质利益的奖惩,后者也许能规约出听话的、守纪律的员工,但不能培养出敬业的精神品质。
三 恕道之现代价值:对他人尊重、仁慈及和平的理念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包含了儒家对每个人的人格独立的肯定,由此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志向、见解、行为方式和利益需求,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得到别人尊重的。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可见独立人格与独特志向在儒家眼里多么重要。因此,不管你自己认为自己的观点多么正确,你自己的用意是多么好,你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多么合理,都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你自己对有利于自己的事物的追求,不要妨碍他人也能实现自己的追求。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希望别人对你也这样做。这种品质同样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疏远、不和和矛盾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利益纠纷和利益矛盾,因此,以恕道来对待利益关系,处理利益矛盾,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费尔巴哈在论述他的幸福观时,就引用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样的话。认为这个朴素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他说:“当你有了你所希望的东西,当你幸福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把你不愿意的事施诸于你,即不要对你做坏事和恶事,那么你也不要把这些事施诸于他们。当你不幸时,你希望别人做你所希望的事,即希望他们帮助你,当你无法自助的时候,希望别人对你做善事,那么当他们需要你时,当他们不幸时,你也同样对他们做。”在利益角逐表面化、公开化、市场化的今天,树立理性的利益观,以恕道为理念处理利益关系,是当代中国人的重要课题。这样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承认每个利益主体具有独立、平等的人格。承认这一点,其实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是和自己一样,具有人格尊严和利益需求的人,你自己想要的事,也是别人想要的;你自己不希望的事,也是别人力图避免的,这是履行恕道的前提。
其次,尊重各方利益。在市场经济社会,人格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或某种名称,而是具有实际内容的利益载体。对利益主体人格的肯定,是通过对其利益的尊重来实现并确立的。承认别人和自己有着相同的利益需求,充分尊重别人的利益,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因为市场活动的利益主体并不是互不相干、彼此独立的孤立个体,而是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有自己明确利益趋向的行为主体。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每个利益主体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天然倾向。而“趋利”和“避害”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总是相伴相随的,在市场竞争中,如果某一利益主体不约束自己的求利行为,那么它的趋利行为就会对对方或第三方造成侵害,从而使对方或第三方的避害成为空话。在市场活动的利益关系中,每一个利益主体都可能成为别人的任性和不负责任行为的受害方,因此,如果你不想别人这样对待你,那你就不应该以损害别人的方式对待别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市场竞争中的运用。
再次,认同普遍的市场准则。市场是各利益主体获取利益的场所,正常的市场秩序是市场参与者顺利实现利益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市场一般潜在地就包含有“市场准入”或“市场参与者”资格审查“的要求,即只有遵守市场规则的人才能在市场上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一般认为,市场规则是一种强制性约束,其实不然。从表面上看,市场规则是一种他律,而实际上则是各市场参与者的自我约束,是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利益与价值所进行的自律,因为一个有正常秩序的市场对各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市场参与者对市场普遍规则的认同实际上是市场竞争各方的一种合作。没有这种合作,正常竞争就无法进行。若是每个人都能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在行为前对自己的动机进行一番拷问:“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就能使自己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的准则。因为它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任何外在的道德戒律更为有效。
除对他人的尊重之外,仁慈之心也是恕道的内在要求。在神圣时代,仁慈一直是作为人的基本德性来要求的。几乎所有宗教的教义都强调仁慈,佛教要求以慈悲为怀,基督教要求人们要仁慈、宽容,儒学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它的超越性理念和终极关怀实际上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因此作为一种“准宗教”的儒学,仁慈自然就成了关注点。
仁慈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的蛮荒时期,是不可能有仁慈这一概念的。自从人有了自我意识和类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情感和生理方面的需要,并由于类意识能意识到别人和自己具有相同的需要,才有可能以己之心、之情、之欲去推知别人的心、情、欲,从而对别人的灾难、不幸和痛苦产生怜悯、同情和不忍之心,这就是仁慈。可见仁慈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在要求。
儒家仁的概念以及此概念在人的行为中表现,都与仁慈有着紧密联系。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其中的“爱”就包含有仁慈与同情;孟子所谓“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也就是仁慈之心,他所说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就是对别人的灾难、不幸和痛苦产生怜悯、同情和不忍之心;儒家要求以“赞天地之化育”的精神成人、成物,要求“以厚德载物”,要有“民胞物与”的情怀等,都凸现了仁者的胸怀和境界,都是仁道的要求,也体现了恕道之仁慈。
人类进入世俗社会以来,宗教性的情感随着物欲的膨胀而日益淡化,仁慈也似乎随着宗教性情感的淡出而飘逝,而理性崇拜则把任何同情、恻隐、慈悲等情感性的东西作为非理性进行嘲笑。以理性为支柱的“理性经济人”把自身利益最大化视为天经地义,大家都在“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一名正言顺的口号的掩护下,拼命为自己争取利益和好处,而又把害处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转嫁给别人。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对别国进行攻城略地、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战争、灾荒、饥饿、贫困等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可以说,人类已经到了检讨自己的人文情怀的时候了。
儒学不是宗教,但它却具有宽容博大的胸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最集中的表达,因而富有同情心和仁慈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我们可以从一位日本人的论述中看到中日两个民族在这方面的差异:“仁慈是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共同美德,而日本则根本就没有提到它。”“忽略仁慈而强调忠诚,只能被看作是日本的儒教所独具的特征。”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自恃国力强大的日本就开始以侵略别国、奴役贫弱民族来表达对其天皇的“忠诚”了。这正好从反面说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里所包含的仁慈观念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仍然不应丢掉这种情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今天的中国人所展示的第三个意义是:坚持和平的理念。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并已成为中华民族性格中一种稳定的趋向。在中国强盛的时期,我们没有欺负过别人;在我们实现复兴和崛起的今天,我们同样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尽管在历史上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其对别国的侵犯,往往诉诸武力与战争,但中国一直要成为世界各民族和平的榜样。
这里必须消除一种误解,以为主张和平是无能、软弱的表现。其实,和平本身就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不以武力侵犯别国,二是不容许别国以武力侵犯我们,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和平理念。中华民族正是将这两方面结合的典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外患从来未断。但任何国家,不管它多么不可一世,只要它侵略我国,必将遭到迎头痛击。因此,我们虽然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但更是多次兑现“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诺言。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理念。据《论语》: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可见,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里所包含的和平理念,是双向制约的:对己而言,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他方之己)而言,他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因为这一原则是具有普遍效力的。由于这一原则也约束他方,所以一旦他方不遵循,那么我“以直报怨”就是合理的。因此,和平理念并不是被别人打了左脸之后再送上右脸的逆来顺受,而是既以和平的方式和态度待人,又敢于以“直”的态度维护和捍卫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