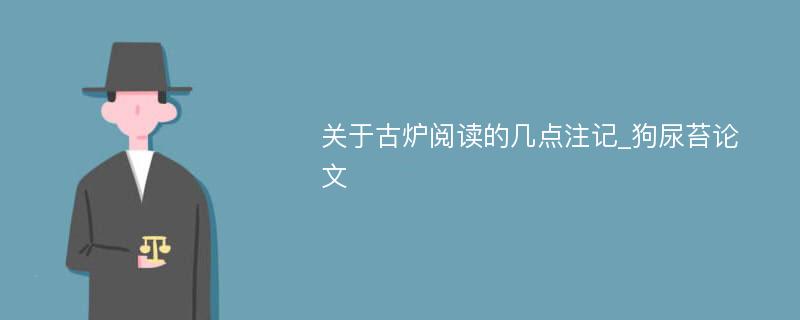
《古炉》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界曾普遍认为,《秦腔》是贾平凹乡土书写的终结之作,“废乡”的主题以及饱满的乡村生活经验的大量呈现也似乎验证了这样的观点。然而,《古炉》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人们的认识与想象,对贾平凹来说,乡土经验不但没有“终结”,反而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与“可能”。从题材与主题层面来说,《古炉》确实有着巨大的开拓性以及对于宏大叙事的追求,那就是对于“文革”在乡村展开的方式与过程的全景呈现与反思,如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反复强调的:“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过人或被人迫害过,只要人还活着,他必会有记忆。”“其实,‘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是一个大的事件,对于文学,却是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它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当年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我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和走进,似乎更无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却离山还远。我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地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①但是,对于小说来说,《古炉》的成功其实远远超越了作家对于“文革”反思的理念与勇气,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其卓尔不群的“经验”美学。小说中的“古炉”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的缩影,作家以百科全书的方式尽态极妍地呈现了贫穷、沉闷、无聊的乡村的方方面面,既有日常生活的全景画面,也有乡村政治、伦理、情感、权力的剖析,既有生老病死、人情冷暖的体验,也有“革命”的狂热冲动所激发的人性扭曲、欲望疯狂场面的刻画,就乡土经验的原生态、丰满性、开拓性以及思想、情感、人性的容量与开掘深度而言,《古炉》无疑又是一部突破了贾平凹自身审美极限的优秀作品。
《古炉》的力量首先来自于小说对于乡土中国立体式、全方位的审美呈现与原生态的“还原”。“文革”前后的中国乡村在文学想象中曾经被高度政治化、抽象化和符号化,“乡村”成了一个空洞的所指与符码,而“古炉”则被还原为了一个充满原生态、活生生的日常生活气息的感性而具体的“乡村”。这是一个“有病”的古炉村,小说写了古炉村人的各种各样的“病”:“古炉村里许多人都得着怪病。秃子金的头发是一夜起来全秃了的,而且生出许多小红疮,婆让他用生姜汁抹,拿核桃的青皮和花椒籽一块捣烂了涂上拔毒,都没用。马勺娘一辈子心口疼,而马勺又是哮喘,见不得着凉,一着凉就呼哧呼哧喘,让人觉得他肚子里装了个风箱。来运的娘腰疼得直不起,手脚并用在地上爬了多年。六升的爹六十岁多一点就夹不住尿了,裤裆里老塞一块棉布。跟后的爹是害鼓症死的,死的时候人瘦得皮包骨头,肚子却大得像气蛤蟆。田芽她叔黄得像黄表纸贴了似的,咽气那阵咽不下,在炕上扑过来扑过去,喊:把我捏死,把我捏死!谁能去捏死他呀,家里人哭着看他这折腾了一夜,最后吐了半盆子血人才闭了眼。几乎上年纪的人都胃上有毛病,就连支书,也是在全村社员会上讲话,常常头要一侧,吐出一股子酸水。大前年,自从长宽他大半身不遂死了后,奇怪的是每每死上一个人,过不了两三个月,村里就要病或死一个人。水皮他大是和水皮的舅吵了一架,人在地里插着秧,一头栽下去再没起来。后来是护院的大瘫在炕上,再后来是八成媳妇生娃娃生了个肉球,没鼻子没眼。”病态的村庄内的生活自然也是病态的,小说也写了开合媳妇的难产、狗尿苔认干儿子、霸槽与杏开的爱情、天布与半香的偷情、来声与戴花的偷情等乡村生活的微观层面,而正是通过对这些“古炉”特色的生活场面的呈现,小说实现了对世道人心精妙至极的挖掘与把握。古炉村同时还是一个充斥着各种节气、习俗的村庄,是一个生活的气息与文化的气息混杂的村庄,小说写了各种死人的场景与葬礼,马勺妈的病死、欢喜的被毒死、满盆的被气病与吃肉被噎死、开石的生疥而死、立柱的被气死、灶火的被炸死、马勺的被打死、霸槽等的被枪毙,都是沉静的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因素,其附着的文化含量与人性含量极为丰厚。古炉村还是一个由各种生活的细节堆砌而成的村庄。贾平凹是一个真正的细节大师,他对乡土生活可以说烂熟于心、完全吃透了,小说中的叙事不急不躁,充满耐心。在他的笔下,“古炉村”徐徐展开就如一幅清明上河图,男女老幼各式乡村人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流水账一般呈现在小说中。小说就仿佛是乡村生活细节的“百科全书”,各种细节的描写高密度地铺陈在小说的空间里,让人目不暇接:“狗尿苔又回到了场上,却发现几乎所有歇下的,并不是坐在场边的碌碡上,他们从麦草集子那儿过来坐在了麦粒堆上,或者在麦粒堆上躺下伸懒腰。三婶坐下后在腰里抓痒痒,顺手将一把麦粒放在了裤腰里。上了年纪的妇女都是扎了裤管的,在裤腰里塞进什么都不会漏下来。”这是村里人偷麦子的细节;“婆在门槛上梳头,她的头发还厚实,但全白了,梳一会就要从梳子上取下一些脱发,绕一绕,塞到门框边的墙缝里。”这是婆梳头的细节;“猫钻在桌腿下,说:啊疼,啊疼?狗尿苔把猫踢了一脚,没喊疼。婆说:打你你还不跑?!狗尿苔这才往门外跑。婆还撵着打,其实她已经把笤帚朝狗尿苔的腿后的地上打;狗尿苔都跑到巷口了,婆仍在拿笤帚打着院门框子响。”这是中国式老人打孩子的细节;“狗尿苔不吐核儿,趁不注意把柿把子塞进鞋壳。”“狗尿苔是一出门就开始吃饼,那不是吃,是尝,忍不住尝尝,拧下那么一点塞在嘴里,再拧下那么一点,塞在嘴里,才走到河堤上,饼子就剩下手大一片了。不准吃,坚决不准吃了,狗尿苔警告着自己,就蹴在河边掬水喝。”这是饥饿年代人面对食物的细节……可以说,就小说细节的密度和原汁原味的浓度而言,当代小说对乡村经验的挖掘还无出《古炉》其右者。
当然,在小说中,贾平凹对“古炉”的塑造与还原其实是沿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外在的、日常的、表层的“物态”乡村,一是内在的、心灵的、情感的、政治的、伦理的、人性的“乡村”。因此,表层的、原生态的细节和场景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古炉村人的心理与人性的真实。比如:“狗尿苔看不见自己耳朵,用手摸摸,是干了,说:那是冻的!狼吞虎咽吃起了,他觉得那一碗饭是那样香,一口饭还没咽下喉另一口就吃进去,喉咙里像是伸着一只手,要把饭和碗都要拉进去。一碗饭吃完,他的脑袋上热气腾腾,再去锅里盛时,竟然能端着空碗一个跃身从丁香树下跳到了上房台阶上,婆说:你疯啦,你疯啦!狗尿苔走过了婆的面前,婆的碗里却是米汤菜糊糊,里边仅有一根短面,漂着像一条鱼。狗尿苔愣住了,说:婆,你没吃面?婆说:我先把面捞的吃了。狗尿苔进了厨房,发现锅里也仅是米汤和菜,知道婆是把所有的米和面条都捞给他吃了,便拿过了辣子瓶子,说:婆,我给你夹些辣子。辣子是腥油炸的,狗尿苔给婆的饭碗里夹了一疙瘩辣子,又夹了一疙瘩辣子,腥油花花漂起来,油是多了,却辣得婆吃不下去。”从这样的吃饭细节里,我们看到的是婆婆对狗尿苔无尽的爱以及婆孙两人相依为命的情感。而同样是吃饭的细节:“迷糊的碗里是白玉白银一样的米饭,冒着一团热气,热气就像是米饭闪出的光亮,太阳从屋檐上斜着照下去,光亮里有了五彩的颜色。面前的地上是一碗酸菜,迷糊夹起一筷子酸菜了,放在米饭上,绿是绿,白是白,然后连菜带饭抄起一疙瘩,那疙瘩足足有烧酒盅子大,他眼睛看着,嘴就张开了。他的嘴那么大,能咧到耳朵根。当饭菜送到了黑窟窿嘴上,舌头就和嘴唇一起响,而眼睛却受活得闭上了。狗尿苔的嘴也动起来,但没有响声,满嘴里却有了唾沫。迷糊耸了耸肩,伸开一条腿来,浑身却透着一种满足和舒服,开始往下咽了,眼睛仍未睁,嘴皱紧了简直就像鸡的勾子。牛铃已经不看了,小声说:吃你妈的×哩!坐在地上生气。”迷糊在家“偷吃”的场景,则把饥饿年代人对食物的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再比如,从“霸槽打狗”与狗尿苔“放狗”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人心深处野蛮与善良的分野。而“霸槽似乎很失望,伸手把墙角的一个蜘蛛网扯破了,那个网上坐着一只蜘蛛,蜘蛛背上的图案像个鬼脸,刚才狗尿苔还在琢磨,从来都没见过这种蜘蛛呀,霸槽就把蜘蛛的一条长腿拔下来,又把另一条长腿也拔下来,蜘蛛在发出咝咝的响声。狗尿苔便不忍心看了,他身子往上跳了一下。霸槽是古炉村最俊朗的男人,高个子,宽肩膀,干净的脸上眼明齿白,但狗尿苔不愿意霸槽这么拔蜘蛛的腿。他跳了一下,想去把霸槽额颅上的一撮头发拨开去,这样可以阻止拔蜘蛛腿,可霸槽的个子高,他跳了一下也没有拨到那撮头发。”在这个细节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霸槽内心的残暴与黑暗,以及狗尿苔的善良与仁厚。此外,霸槽分粮失败后,对于田芽、灶火、土根、半香四人关于“霸槽吃肉问题”的查问,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乡人的聪明与狡猾。再比如,守灯中漆毒后,请蚕婆治疗,水皮找支书告状,守灯恼羞成怒就把漆毒传染给水皮,“守灯给水皮勾手,水皮就走过去,守灯突然一下子抱住了水皮,把自己的脸在水皮的脸上蹭。水皮挣扎,但挣扎不开。守灯的脸在水皮的左脸上蹭了右脸上又蹭,然后一推手,水皮坐在了地上。水皮娘就骂守灯:你中了漆毒了还让水皮也中,你狗日的咋这瞎呢?守灯说:我是阶级敌人我不瞎?!”从这样的细节与场景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人内心世界共同的阴暗。与日常生活相比,古炉村的政治生活是表现得比较隐蔽的。但权力、阶级、出身、分配等引起的政治性也时隐时现。水皮对迷信的告密事件、村人的互偷钥匙事件、守灯的毁坏天布家长藤的事件、开会时婆与守灯的站着被批斗事件,等等,就都是乡村生活政治性的体现。当然,对权力的追逐仍然是乡村政治的核心。古炉村唯一的刑事案件就是麻子黑对于欢喜的谋杀,他的动机就是为了村长的位置。而对狗尿苔来说,他最大的焦虑就是身份焦虑和出身自卑,“狗尿苔确实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直到两年后,他才从村人口中得知自己就是要来的,至于是如何要来的,谁也不直讲,他也不再追问了,可从此身世成了一块疤,不想让谁去揭。”而正因为这一点村里人面对他时就有着政治上的优越感:“秃子金并没有恼,竟然摸了狗尿苔的头,说:啊狗尿苔呀狗尿苔,咋说你呢?你要是个贫下中农,长得黑就黑吧,可你不是贫下中农,眼珠子却这么突!如果眼睛突也就算了,还肚子大腿儿细!肚子大腿儿细也行呀,偏还是个乍耳朵!乍耳朵就够了,只要个子高也说得过去,但你毬高的,咋就不长了呢?!”“霸槽说:你得听我的!我告诉你,我和你不一样,我是贫下中农,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你出身不好,你就得顺听顺说。”古炉村政治性的大爆发得之于“文革”的到来。“文革”延伸、渗透进古炉村后,古炉村的平静被打破,日常生活让位于政治生活,乡村生活的政治性走上前台,“潘朵拉的魔盒”被打开后,人性的贪婪、残忍、丑恶、阴暗更是得到了放大式的表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古炉村的革命,仍然不是抽象化的革命,而是日常生活充盈着的、充满了乡村式的阴谋与狡猾的革命。小说淋漓尽致地呈现了“革命”山雨欲来的过程性,痒病的漫延、洪水的泛滥、猪瘟的恐怖都是“革命”的象征性前兆。在小说中,革命有着阿Q式的特征,跟后因灶火曾经抢了他的模范荣誉而有报私仇的快感。牛路的革命动力也来自于曾被少记了三个工分的仇恨。水皮喊错话的“反革命事件”、守灯和麻子黑的“复仇”心态都是古炉村人心灵世界的展示。黄生生吃麻雀和蛇的画面、牛铃偷鸡杀鸡的情节、天布他们杀水皮家猫吃的场景同样都是对于人性凶残、丑恶一面的揭示。
与此同时,《古炉》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相融合的世界。狗尿苔是连接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的桥梁。狼、狗、猫、猪、牛、鸡、乌鸦、燕子、苍蝇、蜜蜂、蛇在小说中自成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世界,人与动物通灵,动物的故事参与人的故事,动物的命运投射着人的命运。在小说中鸡过生日的情景、牛与欢喜的感情、杀牛及分食牛肉的场景、偷吃死猪的情节等等背后都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批判内涵。而在狗尿苔的视角中,人与动物其实就是同类:“把霸槽认定了是白熊转上世的,霸槽就从此真地有意学着白熊的模样,他走路胳膊都是在身后甩,步子再不急促,岔着腿走,原来发问说:咹?现在动不动就低沉地吼:噢?!笑起来头仰在肩膀上突然嘎嘎嘎地笑,能把人吓一跳。而狗尿苔也更怯火了霸槽。他越是怯火着霸槽,但霸槽越是对他亲热,竟然有兴趣和他给全村人判定谁是啥转上世的。比如支书老披着衣裳,走路慢腾腾的,没事就低眉耷眼的,嘴窝着又腮帮子鼓圆,吃东西整个脸都在剧烈地活动,但眼要一睁,嘴要一咧,却特别厉害,是老虎变的。灶火眼突出,嘴张开是方形,能塞进个拳头,是蚧蚪子蛤蟆变的。半香腰这么细,一走就扭,是水蛇变的。面鱼儿圆脸没胡子,额颅上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是猪变的。马勺坐没坐相,总爱窝倦在那儿,别人说起与他无关的事他霜打了一样蔫,一旦与他有关了,眼睛忽地就睁开,尤其他能和戴花半香杏开她们说话,越说越有精神,而戴花半香杏开和他说过话后都喊叫乏困,那马勺就是老狐狸变的,他和女人说话就是吸女人气的。麻子黑的目光游移不定,声又破,狼变的。长宽是树变的吧,噢,应该是核桃树。老顺是老榆木疙瘩变的。迷糊一定是狗变的,瞎狗。水皮呢,水皮也是蛇变的,他这蛇和半香的蛇不一样,他是草丛里或墙缝里钻着的蛇,衣服华丽,这种蛇按不住它的三寸,能把你缠死,但按住了,提起尾巴一抖,它的骨头就一节一节碎了,像一条草绳。他娘是鸡变的。牛铃的耳朵被老鼠咬过,老鼠爱啃土豆,但他不是土豆,绝对是个山猴变的。满盆是牛变的,鼻子大,爱叫唤。天布死犟死犟的,像驴像牛像狗像狼,也都不像,是四不像。田芽话多,除了吃饭睡觉嘴就没闲过,是蛤蟆变的,可蛤蟆大肚子,她肚不大呀,啊是麻雀变的。他们每判定一个,就十分得意,而且越想越得意,就张狂得大呼小叫。霸槽说:狗尿苔,那你就真是狗尿苔转上世的。狗尿苔说:我是老虎。霸槽说:屁,说是老鼠还行。狗尿苔说:我才不是老鼠。霸槽说:老鼠好哩,有人吃的就有老鼠吃的,虽然老鼠上街人人喊打,可五年前闹地震,头一天老鼠满巷道跑,去年州河涨水,河堤上老鼠都上了树,老鼠精得很。狗尿苔说:老鼠有板牙,我一口碎牙能是老鼠吗?霸槽想不出狗尿苔是啥转世了,说:来回是从河里捞的,又是噘噘嘴,可能是什么鱼变的。狗尿苔心里咯噔一下,倒害怕霸槽从来回的身世联想到他的身世,就赶紧说:我啥也不是。霸槽说:你长成这个样子也实在不容易,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狗尿苔想了想,石头也好,守灯恐怕也是石头,但守灯是厕所里的石头吧。他说:那我是陨石!”
其次,《古炉》的力量还来自于小说以群像化的方式对“革命”年代乡村人物谱系的成功建构。小说塑造了古炉村“夜”、朱两大姓几十个乡村人物,所有的人物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典型性内涵。这些人物的出场方式都是平等的、原生态的、非道德性的,作家以平面扫描、散点式的方法让人物一个个轮番登场,演绎他们的故事与人生,无论男女老少视角上并无侧重,每个人的故事和性格都很完整,每个人都有其独立的话语方式和完整的性格逻辑。从谱系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主要提供了五类人物谱系:一是乡村政治性人物谱系,以支书、霸槽、黄生生、马部长、灶火、马勺、天布、磨子、水皮等为代表;一是地痞无赖式的乡村人物谱系,迷糊、秃头金、麻子黑、守灯、牛铃等为代表;一是典型的传统乡村农民谱系,以满盆、欢喜、老顺、面余儿等为代表;一是游离于乡村结构中心的边缘人物谱系,以善人、婆、狗尿苔、来声等为代表;一是各种各样的乡村女性典型形象谱系,半香、戴花、来回、杏开等为代表。在这些人物中,又以支书、霸槽、狗尿苔、善人、婆五个形象的塑造最为成功。
支书朱大顺是乡村权力的化身。小说对其的塑造是比较含蓄而中性的。在古炉村,他虽然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但是在小说中他并不是以性格张扬而霸道的形象出现的。相反,他行事低调而沉稳,处事公道、周全,有较高的威信。如果不是“文革”到来,他在古炉村的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只是在偷吃牛肉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凭特权多吃多占的隐秘的一面。他私占公房给儿子结婚的做法也堂而皇之看不出任何问题。如果不是霸槽革命时期的查账,他贪污瓷器的事也不会暴露。被夺权后,他的表现也不失尊严,其遭遇和行为还很令人同情。在作家笔下,他是一个有着鲜明历史时代痕迹的政治人物,其思想行为有着自身的逻辑,小说既没有丑化他,也没有漫画化他。
霸槽是“革命”年代躁动不安的具有流氓无产者特征的新型农民的代表,是乡村秩序与权力的挑战者与颠覆者。在狗尿苔眼中,“霸槽是古炉村最俊朗的男人,个头高大,脸盘棱角分明,皮肤又白,如果不说话不走动,静静地坐在那儿,他比洛镇学校的老师还像老师,可他一走动一说话,却有一股子霸气和邪劲能把人逼住。”他有着流氓无产者的习气,有着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怒。他蛮横霸道,与杏开恋爱气死了队长满盆,开小店、投机倒把、耍无赖,村里人谁也奈何不了他。“文革”给了他机会,他迅速嗅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与黄生生联合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狡猾、凶狠、残暴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他挑动了村里的武斗,并使多人丧命,最终自己也被枪毙。霸槽是古炉村陷入“文革”灾难的关键人物。但是,小说中他也没有被符号化,而是呈现为自身逻辑与历史逻辑、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时代悲剧与性格悲剧的融合。
狗尿苔是小说真正的中心人物,他是作家观察世道人心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小说最重要的批判与反思维度,某种意义上他就是隐含的作家本人。狗尿苔有着预言灾难的奇异嗅觉,“狗尿苔觉得很委屈,因为他真的能闻到那种气味。而且令他也吃惊的是,他经过麻子黑的门口时闻到了那种气味,不久麻子黑的娘就死了,在河堤的芦苇园里闻到了那种气味,五天后州河里发了大水。还有,在土根家后院闻到了一次,土根家的一只鸡让黄鼠狼子叼了,在面鱼儿的身上闻到了一次,面鱼儿的两个儿子开石和锁子红脖子涨脸打了一架”。而这种嗅觉无疑对于小说具有特殊的叙事意义,它其实正是小说情节演进的一种内在动力。他是一个弱者,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狗尿苔毕竟是有大名的,叫平安,但村里人从来不叫他平安,叫狗尿苔。狗尿苔原本是一种蘑菇,有着毒,吃不成,也只有指头蛋那么大,而且还是狗尿过的地方才生长。狗尿苔知道自己个头小,村里人在作践他,起先谁要这么叫他他就恨谁,可后来村里人都这么叫,他也就认了”。“狗尿苔完全忘却了婆的叮咛,他觉得这日子就像是节日,天天都是节日。他是不嫌人作践的,到哪儿受人作践着就作践吧,反正是苍蝇,苍蝇还嫌什么地方不卫生吗,被作践了别人一高兴就忘了他的身份,他也就故意让他们作践。水皮说:狗尿苔,你身份那么不好的,咋比我活得滋润,你知道为啥?狗尿苔偏说:我人缘好么。水皮说:啊呸!你是个狗尿苔,侏儒,残废,半截子砖,院子里卧着的捶布石!人自己把自己看大了也就大了,自己把自己伏小了也只是小。”在小说中,他的最大幻想就是有一件隐身衣,能躲避别人对他的嘲笑与欺侮。但同时,他又是良知和美德的化身,他至善至真,能与万物通灵对话,有着对于自然万物和对于动物的悲悯与热爱,是一地鸡毛的古炉村的“天使”。他虽然很卑微,但是心地纯洁、高尚,对他人宽容而有同情心,守灯做坏事他替他顶罪、霸槽被人诅咒他悄悄把霸槽他大坟上的木橛子拔了。只要与牛铃对比我们就能充分感受到狗尿苔这个形象的美与善。因此,小说最后,善人要把古炉村的希望寄托在狗尿苔身上:“善人却对狗尿苔说:你要快长哩,狗尿苔,你婆要靠你哩。狗尿苔说:我能孝顺我婆的。善人说:村里好多人还得靠你哩。狗尿苔说:好多人还得靠我?善人说:是得靠你,支书得靠你,杏开得靠你,杏开的儿子也得靠你。”贾平凹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狗尿苔的喜爱,在《后记》中他说:“狗尿苔,那个可怜可爱的孩子,虽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原型的身上,但在写作的时候,常有一种幻觉,是他就在我的书房,或者钻到这儿藏到那儿,或者痴呆呆地坐在桌前看我,偶尔还叫着我的名字。我定睛后,当然书房里什么人都没有,却糊涂了: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着这个人物,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当他被抱养在了古炉村,因人境逼仄,所以导致想象无涯,与动物植物交流,构成了童话一般的世界。狗尿苔和他的童话乐园,这正是古炉村山光水色的美丽中的美丽。”②
婆也是小说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是与狗尿苔具有互补性的人物。因为丈夫逃到台湾,她背负了一辈子的重负,是批斗会上的固定对象。但是她善良、宽厚、隐忍、博大,是中国传统女性伟大品格的化身。她是古炉村的灵魂,也可以说是守护神,是民间伦理的化身,为人治病以及为人喊魂是婆一辈子热衷的两件事。同时,婆也是一个能超越个人好恶而对于所有人物都充满同情、悲悯,具有大爱大德并真正能与万物对话的具有宗教情怀与境界的人物。“在古炉村,牛铃老是稀罕着狗尿苔能听得懂动物和草木的言语,但牛铃哪里知道婆是最能懂得动物和草木的,婆只是从来不说,也不让他说。村里人以为婆是手巧,看着什么了就能逮住样子,他们压根没注意到,平日婆在村里,那些馋嘴的猫,卷着尾巴的或拖着尾巴的狗,生产队那些牛,开合家那只爱干净的奶羊,甚至河里的红花鱼、昂嗤鱼,湿地上的蜗牛和蚯蚓,蝴蝶、蜻蜓以及瓢虫,就上下翻飞着前后簇拥着她。这些动物草木之所以亲近着婆,全是要让婆逮它们的样子,再把它们剪下来的。”
善人的形象相比而言虽然有某种理念和说教的特征,但对贾平凹来说他却是小说不可或缺的另一个重要伦理维度,他代表了古炉村神性和形而上的一面,其实也是贾平凹反思“文革”、反思“文革”之所以会在古炉村造成巨大灾难的一个重要角度。贾平凹在小说中是从宗教和哲学层面上定义他的:“善人是宗教的,哲学的,他又不是宗教家和哲学家,他的学识和生存环境只能算是乡间智者,在人性爆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他在村里给人说病,针对的主要是人的内心的疾病、伦理的疾病和精神的疾病。他仿佛是一个布道者,又如一个启蒙者,他试图不断地唤醒人们沉沦的心灵。“善人说:这就对,社会就凭一个孝道作基本哩,不孝父母敬神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惜元气,医药无益;时运不济,妄求无益。一个人孝顺他的老人,他并没孝顺别人的老人,但别人却敬重他;一个人给他的老人恶声败气,他并没恶声败气别人的老人,但别人却唾弃他。伦常中人,互爱互敬,各尽其道,全是属于自动的,简单地说,道是尽的,不是要的。父母尽慈,子女尽孝,兄弟姐妹尽悌,全是属于自动的,才叫尽道。”他同时也是一个殉道者,最后善人与古炉村的风水树白皮松同归于尽,善人自焚时的冲天火光无疑是对古炉村人的最后一次警诫与呐喊。
再次,从艺术上看,《古炉》是“新写实”手法在乡土小说中的成功实践,他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把琐碎、庸常、一地鸡毛式的日常叙事提升为具有震惊效果的美学形态的审美能力与审美经验。贾平凹是写实的大师,擅长于大巧若拙的日常叙事,总是把宏大叙事融入日常生活,从而整体上呈现出见微知著的文化反思品质与大智若愚、浑然天成的审美风格。正如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的:“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建设着那个自古以来就烧瓷的村子,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以我狭隘的认识吧,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着就是那个村子发生的故事,等他们有这种认同了,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小说开辟了一条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呈现的充满艺术张力的小说方式。就小说美学风格与思想、情感、艺术结构而言,小说达到了在快与慢、静与动、宏大与微观、叙述与描写、写实与写意、野蛮与善良、阴冷与温暖之间的巧妙平衡。比如,就动与静的平衡而言,小说前半部以静态展示为主,叙事耐心舒缓,充满生活密度,小说后半部则以动态的情节展开为主,直到榔头队和红大刀的武斗,充满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加速度运行态势。但是,这种“静”和“动”又不是绝对的,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充满着结构的张力。小说开场所描写的乡村场景就是“静景”,就如鲁迅在小说《风波》中所展现的那样,无聊、沉闷如一潭死水。沉闷的打破或戏剧性的出现来自于狗尿苔的出现以及对狗尿苔的捉弄。其后,杀猪、看病、皮影戏、水皮与霸槽比吃豆腐、看星妈与儿媳的吵架、天布媳妇的骂街、野狗与跟后家母狗的连蛋等乡村戏剧性的事件则不断地使沉闷的乡村生活泛起涟漪,静态就这样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回归平静。而下半部虽然总体上是动态化的戏剧性情节的展开,特别是武斗时的狂热与血腥成为小说下半部的主线,但“革命”的缝隙仍然如前文所说的充满着静态的乡村生活的场景与片断。即使在小说最后霸槽等被枪毙时,小说也穿插了围观者们准备抢食脑浆的“闲笔”,让人不能不想起鲁迅《药》中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的笔墨。再比如,就语言而言,原汁原味的民间方言、粗俗化的生活语言与政治性、伦理性的语言的张力也使小说的语言修辞充满魅力。很多人对《古炉》语言的粗鄙化颇有微词,认为小说有太多的屎、尿、屁的描写,但我觉得语言的还原正是作家还原真实的古炉村及其芸芸众生的重要手段,这种充满屎、尿、屁的语言其实就是原生态的真实的人物语言,或者说就是人物的生活本身,离开了这种语言,人物就不成为他们自身。另外,语言审丑也是一种文学风格,并不是粗鄙一词所能说明的。在小说中,作家这样写狗尿苔与牛铃比喝尿:“返回走到三岔巷,放下柏朵去一个厕所里要尿,厕所里咳嗽了一下,里边有人,他们就绕到厕所墙外的尿窖池子边去尿,从裤裆里一掏出来,却兴趣了比谁尿得高,两股子尿就高高地扬起来,在太阳底下银亮亮发光。牛铃先伸着脖子拿舌头接了一下尿水,说:咸咸的。狗尿苔也伸出舌头尝了尝自己的尿,说:就是咸的。”这样写迷糊在厕所里吃凉粉:“迷糊一出厕所就端起了锣,说:啊狗尿苔,吃凉粉呀不?狗尿苔说:你才在厕所吃了,还吃呀?!以为迷糊说诳话。但见锣里果然是凉粉,就说:吃哩!迷糊夹了一疙瘩凉粉给狗尿苔,狗尿苔发现了迷糊的手指上有一点粪便,说:看你这手,你这手!迷糊一看,有些急了,却立即把手指在嘴里一舔,说:酱辣子,酱辣子!狗尿苔没有吃,一转身,咕咚一声恶心得吐了。”这样写公鸡母鸡的吵架:“一只黑公鸡在骂一只母鸡:你的公鸡弄我的母鸡就弄啦?我要弄你呀你就上了墙?!双方叽叽咕咕吵架,后就相互掐斗,落了一地鸡毛。”此外,小说写到的迷糊养母猪兽交、明堂咬毬等场景也是这种原生态语言的代表。与此对应,小说又充满了政治性的语言,比如面对狗尿苔,村里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具有政治、道德上的优越感:“秃子金便恼羞成怒了,说:你个残渣余孽,我抽了你的舌头!”“霸槽给他讲,出门带火有啥丢人的,你个国民党军官的残渣余孽,是个苍蝇还嫌厕所里不卫生?何况这只是让你出门带火。”“狗尿苔说:我也爱戴毛主席!水皮说:你是啥出身,你没资格爱戴毛主席,重造!”在这两种语言形态的张力背后,我们既可以看到人性的元素,也可以看到文化的、伦理的反思。再比如,就叙述与描写以及写实与写意的张力而言,小说把白描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对生活细节的捕捉与描写可谓淋漓尽致,但同时小说中又不乏象征性的意象、浪漫甚至诗情的描写。如贾平凹自己所说的,“写实并不是就事说事,为写实而写实,那是一摊泥塌在地上,是鸡仅仅能飞到院墙”。他重视美术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而中国的书,我除了兴趣戏曲美学外,热衷在国画里寻找我小说的技法。西方现代派美术的思维和观念,中国传统美术的哲学和技术,如果结合了,如面能揉得倒,那是让人兴奋而乐此不疲的。比如,怎样大面积地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渲染中既有西方的色彩,又隐着中国的线条,既有淋淋真气使得温暖,又显一派苍茫沉厚。比如,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没工整,胡摊乱堆,整体上却清明透澈。比如,怎样‘破笔散锋’。比如,怎样使世情环境苦涩与悲凉,怎样使人物郁勃黝黯,孤寂无奈”。③例如,小说对于太岁意象的表现就是虚和实结合的典范。而白皮松意象在小说中也具有文化和人格的象征意义。狗尿苔不满霸槽与杏开恋爱时,对两棵树的描写更是无疑充满了浪漫的诗情和童话色彩:“墙拐角是两棵树,一棵是香椿树,一棵是榆树。两棵树近是近,并没有挨着,原本树干光光的像柱子一样,但榆树却从一人高的柱杆上生出一丛枝条,伸向了香椿树,香椿树的柱杆上也生出一个枝条伸向了榆树,枝条和枝条就扭扯在一起。”
总之,《古炉》是贾平凹式审美观念与艺术能力的又一次极致的表演。他以对于乡土经验无所不包的挖掘与呈现,拓展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重新确证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现实主义的力量,展示了文学与生活的双重魅力。当然,对于小说来说,琐碎转换成美学,也必然会带来艺术上的风险。这表现在,其一,琐碎的美学有时会因为其沉闷、平面化、缓慢性、静态性而构成对读者阅读耐心的挑战;其二,高密度的细节固然会强化小说思想、生活含量的浓度与密度,但这本身也是对作家写作难度的一种考验,也可能会导致小说前后内容的重复、遗忘,甚至矛盾。比如关于霸槽鸡巴上痣的问题以及天布照壁上的藤萝开花的问题,小说的前后叙述就有矛盾之处。
注释:
①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后记》,《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
②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后记》,《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
③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后记》,《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