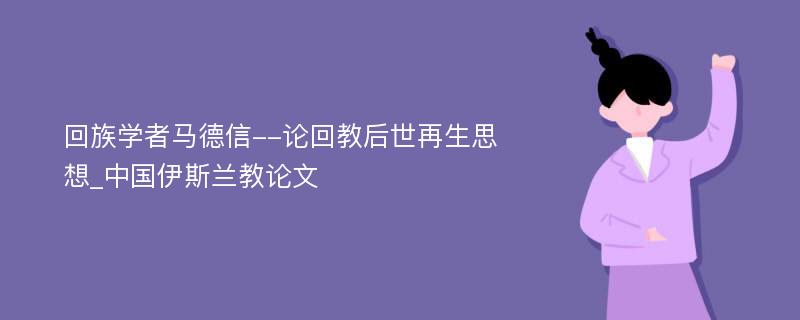
幽明与会归——回族学者马德新论伊斯兰教的后世与复生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回族论文,幽明论文,新论论文,后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0.3“2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2-0051-08
“幽明”一词在汉文中共有五义,一,泛指有形和无形的物象,《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二,指天地,《大戴礼·曾子·天圆》:“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三,指昼夜、阴阳,《礼·祭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注》:“幽明者,谓日照昼,月照夜。”《史记·五帝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正义》:“幽,阴;明,阳也。”四,指善恶,贤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步黜陟幽明。”五,人鬼的界域,地下为阴,故称幽;人间为阳,故称明。马德新借用“幽明”一词并赋予其独特的涵义:“浮生若梦故称幽,后世真常故称明。”在此,“幽”,特指今世,因今世短暂故称幽;“明”,特指后世,因后世永久故称明。“幽明”思想即伊斯兰教的两世观。“会归”则指伊斯兰教的复生思想。
消解死亡、超越现实、追求永恒是宗教的灵魂所在。伊斯兰教以信末日与复生为基本信条之一,并坚持两世思想,认为人不仅有短暂的今世生活,还有永久的后世生活。相信世界有末日,届时人人都要复生,接受安拉公正无私的审判。如何把复生与后世这一伊斯兰教极为重要的信条介绍给中国广大穆斯林,如何系统阐释伊斯兰教的生死观及后世说,同时又要避免受到在生死问题上持自然主义态度的儒家学者的批评,如何将“灵魂不朽”转化为儒家可以接受的思想而又不沦为“荒诞之说”,确非易事,这正是汉文伊斯兰教著作“认主认己之学发达,而后世复生思想缺略”的原因所在。马德新著《会归要语》、《大化总归》、《醒世箴》、《性命宗旨》、《幽明释义》(《四典要会》之第三卷)等书,谈生死,说会归,论复生,述后世,重点强调伊斯兰教的幽明与会归思想,并充分阐释了幽明与会归思想的宗教及道德意义。
一、幽明与会归说的思想根源和现实意义
明朝后期,随着回族穆斯林学者开展的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义、教法及宗教哲理的学术活动不断深入,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及《古兰经》内容的了解日渐增多,愈来愈多的穆斯林希望能系统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思想。信末日与复生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之一,《古兰经》全部6000多节经文中约有700多节论及复生与后世。因此,全面、系统阐述伊斯兰教的根本信条,引导广大回族穆斯林全面深入地了解伊斯兰教,使他们将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是身为伊玛目的马德新的重要职责。此外,马德新之所以反复强调复生、后世思想,更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其一,清朝后期云南社会动荡不安,回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与仇杀此伏彼起,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怖之中,遭受着肉体的、心灵的以及情感的痛苦。显然,自然主义的生死观无法抚慰特殊时期的普通民众,他们对死亡充满恐惧。马德新以伊斯兰教的生死观和后世、复生思想,消弭人们的恐惧心理。他发挥伊斯兰教的情感慰藉功能,化解人们因死亡而引起的悲痛和苦恼,最终引导人们达到超越死亡的精神境界。
其二,批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生死观念,指出死亡是生命的正常现象,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报应或上天的惩罚。清朝后期云南社会失序,道德失衡,民族之间的仇杀不断。少数邪恶之徒为给自己图财害命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散布谣言,说被他们无端杀害的人都是恶人,这些人之所以死于凶劫(被残杀),是上天对死者的惩罚。马德新指出死生是自然现象,一个人怎样死亡与其生前的行为没有丝毫关系,比如死于洪水、地震、雷电等自然灾害的人,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绝大多数是无辜的善者、弱者。“天不容留”不过是暴徒残杀无辜的借口而已,从而为弱者、善者摆脱宿命,走向抗暴之途提供理论根据。
其三,面对当时云南社会失序、道德败坏、法律松弛、政治无能的状况,马德新试图诉诸宗教,借助安拉的威严与无私,通过赏善罚恶的机制,通过地狱的恐怖等,制止邪恶,制止暴行。他认为人性之恶欲和贪婪是社会混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人们生理的、身体的疾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而治愈贪欲、制止恶欲的唯一方法就是死亡。因此,他强调死亡,强调死后复生,强调末日审判,目的在于为那些放纵私欲、残害生命、屠杀无辜的恶人敲响警钟,以期制止恶行,恢复社会秩序。
其四,马德新的复生说和后世说,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他对后世美好生活的描述,对天堂永恒福乐的渲染,对火狱无尽痛苦的描绘,目的在于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现实的不公,痛斥吏治的腐败:
杀千人只抵一人,害数命只偿一命,不公平孰于是乎?[1]
恶人偏受全恩,富贵荣华而为善者所不及;善者遍遭大困,冻馁穷恶而为恶者所贻讥。[2]
循理而遭祸患,肆毒而得安康,恶不见罚,善不获报,屈不见伸。[2]
人间案卷,以待告者言情,诉者鸣冤,而有文吏可以舞弊,有财帛可以赎罪。夫国家问罪,有下刑拷打之说,诚以不拷则不招,不打则不认。且虽招而招非真,虽认而认亦伪。要皆不离乎强逼者近是。[2]
黑暗的现实社会,没有正义,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只有暴力;没有公平,只有怨愤。苦难的人们期盼公平,希冀安宁,渴望善人得享永福,恶人得受永祸。马德新宣扬伊斯兰教天堂地狱及赏善罚恶的思想,意在唤醒众生追求良善、阻止邪恶。云贵总督张亮基对他的苦衷深怀敬意,赞叹“其识甚远”①,云南地方官员吴存义称其“彻上彻下,贯古贯今……可谓大智慧”②。
二、诠释死亡
肉体生命的结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如何赋予死亡这一自然现象以深刻的文化意义,在精神层面上沟通生死,这是一切宗教孜孜以求的目标。按照伊斯兰教的解释,世界万物以及人类作为真主安拉的造化物,都有规定的期限。人人都会经历死亡,无人能够逃避。伊斯兰教同时认为人的生命有两个阶段,一是今世的生命,一是后世的生命。二者相比,今世的生命是短暂的,后世的生命是永久的。人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在复活日接受安拉的审判并进入永久的后世生活。
关于生命的存在与消亡,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们多受希腊理性哲学的影响,一般以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加以解释,并以灵魂不灭诠释伊斯兰教的复活及后世思想。肯迪、法拉比、迈斯凯维以及伊本·西那等都认为,人的死亡是肉体永久的毁灭;身体死亡后,灵魂将永远存在于脱离了肉体的理智世界中。中国回族学者王岱舆在其《正教真诠》“生死”一章中即持此观点。
然而上述伊斯兰哲学有关肉体泯灭、灵魂不朽的思想与《古兰经》的精神不尽一致,“我以复活日盟誓,我以自责的灵魂盟誓,难道人猜想我绝不能集合他的骸骨吗?不然,[我将集合他的骸骨],而且能使他的每个手指复原”(75:1-5)[3]。此外,以肉体泯灭、灵魂不朽解释死亡,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真主的赏罚是针对每个人(包括灵魂与肉体)生前行为的善恶,肉体在今世既然担负着许多义务和责任,就不应该逃避后世的奖赏或惩罚。因此,安萨里等伊斯兰学者认为不能否认肉体复活的可能性。受其影响,马德新坚持肉体与灵魂的复生,认为善与恶既是身体与灵魂的共同行为,则赏罚不应由灵魂单独承受,故而复活定是灵与肉的复活。如何既承认肉体与灵魂的永生又能合理解释现实生命的必然死亡这一现实问题,是历代穆斯林学者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
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对生死问题持自然主义态度,没有天堂地狱的彼岸观念,也不以肉体与灵魂的对立关系来解释生命和死亡。为使伊斯兰教的教义思想符合中国穆斯林的理解方式,也为了避免伊斯兰教的复生及后世思想受到儒家的抵制和非议,马德新利用身与性、今生与后世、善与恶、奖赏与惩罚等广大中国穆斯林可以理解的术语与范畴来阐述伊斯兰教关于生命、死亡以及复活、后世及天堂火狱等思想。他一方面指出死亡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死亡将使一个人拥有的一切——财富、名利、地位、子嗣等全部消失殆尽、化为乌有;另一方面以永久的后世满足人类渴望永生的美好愿望,消除人对死亡的恐惧,突出强调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不朽以及绝对公正的末日审判,以宗教的形式劝善戒恶,以后世的赏罚引导现实的良善,从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他用身性关系论述生死,认为身性的结合是生,身性的分离是死,在复活日人之身与性将再次复合,人即可进入永久的后世;他用两世关系论述生死,认为今世是人的短暂的、有限的生命,后世是永久不朽的真乐世界,死亡则是人由尘世进入后世的必经之栈;他用善恶报应和天堂地狱论述生死及两世,“后世者,真主审讯斯人而大彰其赏善罚恶之权,以完其今生之事也”[2],“夫死之必复生,是真宰统会斯人于无涯岸,无参差之大世界中,分班列等,按其次第,而显其尘世所作之善恶;以为判理之场”[2],“后世则灵性常昭、身体复活,永久不朽报应之理亦无以变”[2]。
1.生死是自然规律
生死不停,为天地自然之机,这是东西方智士贤哲的共识,也是古今芸芸众生的常识,有生则有死,正如有始则有终,这是自然变化之常理。因此,《易传》曰“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庄子亦言“死生,命也”[4];“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5];扬雄感叹“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6];张载提出“存,吾顺事;没,吾宁也”[7] 的顺从生死之道的态度。生死是自然规律,不容否认,也难以抗拒。马德新告诉我们:昼夜的更替,四季的变化,万物之荣枯,人之生死,都是自然现象,好似江河之波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仿佛枯树落叶,生之又落,落之又生。他批判当时社会上恶人诛杀无辜的错误理论依据,“传曰生死有命,非为过恶太甚,而天下不容留也。使为天不容留,则前世过恶彰彰,何以不诛而必待诛于不见过恶之际,此招众人之怨恨不平也”。“死生为天理之当然,命分之不得不然。非恶人必死于凶劫,善人必死于善劫”[8]。死生是生命的自然现象,“善人死于善劫、恶人死于凶劫”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是坏人为了掩盖罪行而散布的谬论。马德新指出,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在天地万物人神天仙等各种存在中,唯有真主安拉的本然是永恒的、不朽的,此外一切都有朽坏,都要灭亡。不仅人不能永远生活在世上,天地万物都不能摆脱终得毁灭的结局。
既然死亡是人之必然,那么无人能够逃避,痛哭流泣者、百端悲鸣者、畏死幸生者、恶死好生者、避死贪生者,均不能避免。马德新告诉人们,与其生活在对死亡的畏惧、恐怖中,不如顺其自然,“死未至而淡然相安,并去其畏避之心;死既至而欣然顺受”[2]。这样不仅是对于人们精神压力的舒缓,也最终回归到一切都是主命的伊斯兰的终极信仰中。
2.死亡是身性的暂时分离
然而对于万物之灵的人类,对于拥有情感、思维和智慧的人而言,面对亲人的永远离去,面对自己现实生命的终结,何以能不伤心欲绝,怎么能不备感畏惧,如何才能做到顺受?马德新指出人之死是客观存在,人之痛苦情感是无法抑制的。“清真之道以死亡为正命,哀感为人情,首重本源,次言礼仪,不特悲伤而已,必兼之和顺。”[9] 人是充满智慧的群体,唯有人类才赋予生死深刻的含义,使人摆脱了物性,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现实生命是短暂的,死亡仅是尘世生活的终结,是今世生命的结束,是身与性的暂时分离:
其死也,非绝生也,人惟体朽而不能承性,故身之离性[2]。
身有性为生,离性为死[10]。
来为生,去为死,死则身性相离,是身散也,非无也[2]。
人有身也,身有性为生,离性为死[10]。
死亡不是生命的永远消失,只是由于身体的朽坏而与性命暂时分离。生命是身体与灵性的结合,死亡则是二者的暂时分离。死亡不是无,不是生命的终结,只是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马德新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死亡仅仅是身体与性命的暂时分离,就不会把死亡看作非常可怕的事情,就不会被死亡战胜,相反,人们会以平常心坦然面对自己或者亲人的死亡。
3.死亡是复生的必经之栈
在马德新之前,王岱舆曾经概括地阐述了伊斯兰教的生死观,指出“人死之后,其灵性长在不灭”[11],认为人死身灭,灵性不朽③。马德新以为,身死性存不能解释伊斯兰教的复活思想,也无法避免与伊斯兰教赏善罚恶思想之间的逻辑矛盾,因此他以身性的暂时分离诠释死亡,以身性的复合解释复生,从而赋予了死亡这一自然过程极为重要的意义。死亡是真主创造的万物复归真主的大化之链上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人由有限生命进入永恒生命的一个重要阶梯,至此“死”便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死之“义理”在于:
前古后今,人民实繁,必一一由死而继以复生者,殆如一一由梦而继以复醒焉。天下无不由梦而复醒之人,亦无不由死而复生之人[2]。
变者终必散,生者终必亡。非生必无死,非死无复生[8]。
夜尽而昼显,表尽则里明,梦后而复觉,死后而复生[8]。
生与死没有本质的区别,生存是走向死亡的历程,死亡则是后世永恒生命的开始。既然死不是生命的终结,既然死是复生的必需,“死亡”就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生者必朽,朽者必复生,返本还原,这是自然之理。死亡是人摆脱有限之尘世、进入永恒之后世的必经之路,“死者,人所必由之路”[2],既然死是人进入永久不死大化全归之后世的开端,那么死还有何畏?身体暂时死亡,但是灵魂常在不灭,现实生命的结束就像人脱去了一件衣服,身体并不因衣服的脱离而消失,性命也不会因肉体的消失而毁灭。身性的分离,不会引起生命的腐朽;肉体的损害,不会带来性灵的变异,人的灵魂是永存的,它将在末日之际,再次与人的身体结合,人将得到复生,并永久地生活在后世。后世说为人的心灵提供安顿之处,从理论上消除人们死无所归的恐惧。
4.死亡使囚人离囹圄、为病人除痛苦
马德新进一步指出,死亡不仅不是现实生命的永远终结,不仅不是痛苦,反而是人解脱现实苦难的途径。“彼人之生也,贪贱逼之,坎坷逼之,患难逼之,为俗情所困者,故生独见其难。人之死也,怨我者不顾,谤我者不顾,杀我者不顾,而世累尽绝者,故死倍觉其安。”[2] 人生之烦恼何其多也,为生活奔波却不能摆脱贫贱,为利禄奔波却遭遇坎坷,为功名奔波却得不到满足,为父母儿女妻妾奔波却难以如愿以偿,可谓人生在世,苦恼繁多,唯有一死才能解脱。死亡使人摆脱现实苦难,获得解脱。人生受到种种限制,被欲性困扰,被俗物拖累。既然如此,人又何必为今生的短暂而忧伤,为死亡的降临而悲哀呢?把人生看作苦难,把死亡视作脱离人生苦难的途径,看作囚犯离开牢狱、患者除去病痛的事情,表面上看,这种论调与伊斯兰教正统派倡导的谋求两世幸福的思想大相径庭,也不符合中国穆斯林的人生观。事实上,在当时社会动乱、道德沦丧、生灵涂炭的环境中,有识之士深感人生悲凉苦楚,功名、利禄均不能长久,难免会产生尘世如梦的消极思想。加之《古兰经》中有大量的经文宣扬今世不过是嬉戏、今世欺骗了精灵和人类(6:103)[3] 的思想,且反复告诫人们莫要贪恋今世而忽略后世,不要喜爱今世胜于喜爱后世(9:38)[3],此外还多次强调后世是真实的,是永久的(28:64)[3],要人们坚信不疑。马德新坚持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他不主张弃世,而主张穆斯林应当寻求两世的幸福。但是为了消弭人们畏惧死亡的心理,为了引导特殊时期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马德新突出介绍了《古兰经》有关今世短暂、后世永久,今世为幻、后世真实的内容,是出于当时的社会需求,这与正统派立场不矛盾。
5.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
马德新引导人们以平常心看待死亡,引导他们理解死亡中蕴含着的人生意义:
人以死为脱俗体,其视死犹小;以死为显灵性,其视死乃大。以死为脱俗体,而出于有形天地之外,其视死愈无不大,以死为出乎有形天地之外而消乎幔障之己私,超乎无形天地之中而至于会归之真境,其死乃大之又大,而无有出乎其大矣。[2]
把死看作生命的结束,只看到死亡的表面意义,把死看作灵性生命的解放,死就有了更深层的意义;把死看作对永恒的追求,则死亡的意义是最深刻的。唯有充分理解了死亡的深刻含义,才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死亡:“死未至而淡然相安,并去其畏避之心;死既至而欣然顺受”[2],不仅自己临终之际能够安然顺受,还能做到“即我有慈父母,临终而守其难舍之志,劝以顺主,则子为孝子。我有孤儿女,临终而忍其大痛之心,训以顺主,则亲为义亲”[2]。人临死而顺之,因有一永久之后世;人对所亲、所敬、所爱之人的死而顺之,亦因有一永久的后世。此后世不仅使人永生,更给人公正、公平和幸福。只有认识到死是“真主超拔斯民离乎幻世而归于真境”的时候,才能像“众流之趋海、游子之赴家”[2] 一样,以健康的、积极的心态对待死亡。伊斯兰的重生而不畏死、求生而不苟活的独特生死理念在马德新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扬。
三、生命的超越——幽明说与会归说的宗教意义
宗教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地探索世界和人自身的意义,不断引导人们彻悟自身的有限和无常,引导人类超越世俗生活,朝着终极实在的方向不断超越自己、提升自己。伊斯兰教以其对现实的超越性,以其与永生的关联性,以及终极关怀的神圣性,引导人类超越人生种种局限,实现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马德新则以幽明说和会归说来揭示人类对超越的渴望和对永恒的不懈追求。
幽明即指两世,按照马德新的解释,“人有生死,物有起灭,来有所始,去有所归。人由生至死皆在天运循环之间,新故交接之会。今日有起尽,先后无终穷。生之日甚暂,可不勉而自修乎?浮生若梦故称幽,后世真常故称明”[8]。伊斯兰教基于人之现实生命的短暂和有限,突出后世的永恒从而引导人类实现超越,既不同于基督教从人之原罪而发的超越(灵魂救赎),又不同于佛教从人生之痛苦、染业、执障而发的超越。伊斯兰教的两世观(幽明说),不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不否定人的现实生命,不主张通过弃世来寻求解脱,而是要引导广大穆斯林追求两世的幸福、两世的吉庆。幽明说的目的不在让人远离现实生活,而是引导人们对照安拉的永恒、无限、全知、全能和绝对公正,体悟自身生命和现实世界的短暂、无常及有限,以死超越生,以后世的永久超越今生的有限,以理性超越情欲,彻底摆脱自我的、自然的以及社会的局限,实现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
马德新对儒、佛、道各家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儒家倡导以修身为本,通过成就道德君子和济世伟业而提升个人的生命境界;道教以性命双修以炼就长生不老之体,以此实现对自然生命的超越;佛教让人修炼心性,通过灵魂的轮回转世解释生命的不朽,以涅槃成佛实现人的超越。在马德新看来,各家学说都在引导人们超越现实人生和肉体生命,但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完全达到目的:儒家将自我的超越建立在个体的理性自觉的基础上,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修之有何益,不修有何伤”,对修与不修的最终结果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而儒家纯义无利的、完全依赖理性自觉的道德修养只能引导君子,不能约束小人;佛道二教所宣扬的“常(长)生不死,修之而死后托生为帝为王;修之而留名于万世者,是皆贪生畏死,希富图名,舍红尘而复求红尘,尤非主宰生人之意”[8],为了长生不死或死后转世为帝为王、留名后世等目的而修行,终究还是对世俗幸福、世俗生命的追求,是舍红尘而复求红尘的举动,不是真宰创造人类的真正意图。显然,马德新对佛、道教的了解和理解是粗浅的,远不如他对儒家真髓的洞彻,但他所提出的超越精神,确有启迪意义。
仅仅依赖人的理性自觉和个人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超越。对长生不死、帝王福禄的追求本身是对超越精神的玷污。世俗人伦以及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本身有其局限性,尤其在社会动荡、人欲横流的时代,世俗的道德是苍白乏力的,是没有权威的,很难约束人心、制止邪恶。只有通过宗教的神圣性和善恶报应的权威性,才能使道德规范成为信徒无条件遵守的绝对命令,才能保证道德的约束力量。马德新指出,唯有伊斯兰教的后世说,才能引导人们实现超越。实际上,任何宗教都无法避免功利主义,不同宗教、不同信徒的追求确实存在着层次的高低差异,即便追求伊斯兰教所描绘的天堂,也是功利的。这是一切宗教的内在矛盾。
马德新提出了存在的四境界说,真一之境、天国之境、尘世之境、梦中之境四者中,最高的境界是真一之境,它纯真无幻,没有任何限制,在此境界,能够拥有绝对性、永恒性、至上性,这是人所渴望而不可及的境界;其次是天国之境,它有开端却没有终结,天国无死亡,生活在天国中的人们可以实现长生不死的梦想,并且可以摆脱尘世生活的种种局限;其三是尘世之境,这是人的现实社会,尘世无长生,人们在此会受到种种限制,但这是人们种植后世善恶之果的场所,今世的生活虽然短暂,但人在今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的所作所为,直接决定着人在后世生活中的归宿,行善者将进入天堂,永享福乐,作恶者将下火狱,饱受痛苦;其四是纯幻无真的梦中之境,作为一种生命境界,这是毫无意义的、虚幻的境界。四种境界中,真一之境属安拉独有,人永远不能企及,但人同样可以实现超越,后世则是人类摆脱种种局限,实现生命超越的理想境界。
人在后世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届时一切束缚都将解除,人的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与升华,人可以超凡入圣而归真,能达到无所不能的超凡境界。在这“万化长生不灭、天得之而长清、地得之而长宁、物得之而长存、人得之而长生”的“无复无迁、万古恒然”的后世,人的主体性被高度张扬,永恒的人、伟大的人跃然可见。获得超越的人,可以成为《中庸》所说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
马德新坚信这种永恒的后世生活是真实存在的,为避免“浮浅之辈以眼见者为真实,以不见者为虚幻”从而否认后世并视之为穿凿附会或虚妄荒诞之说,马德新一再说明后世、复生是经验无法证实的,它们不是人们感觉经验的对象,不能被人的经验所认识,“幽明之事本属隐微,五官不能知,智慧不能达,而其说历乎数百代圣人授受相传,且有百卷天敕,分明详阐”[8],是历代圣人代代相传并有《古兰经》详细阐明,意在引导人们超越今生、把握永恒,不能因人固有的思维方式而轻易断定它是虚无或荒诞之说,相反,人们可以参照有限的尘世生活去体认无限的后世生活。
因现实人生有限,所以要寻求后世的无限;因现实人生有对(相对),所以要寻求后世的绝对,因现实人生有生有死,所以要寻求后世的不生不死,实现生命个体的自我超越。现实世界是不完满的,是充满痛苦的,是不幸的,而人则渴望幸福的、美好的、完满的生活。
两世观中,马德新一方面阐扬后世的永久、美好、真实。另一方面又指出“两世者非真有彼此之别而为两境,不过化乎彼此之间而为两面,如一物之有表有里也,今日之对乎己者,为今世。明日之背乎己者,为后世。今日去,明日来,后世之里面从今世之表面而转……今世后世为两面,而非两境”[2],“在外虽各别而本然原相通……是两面而实为一体也”,在突出生死之事的自然而然的规律性,同时又试图证明两世不是两个世界,后世不是彼岸,而是一体之两面。隐约表现出马德新对彼岸后世真实性的思索和困惑。
四、劝善戒恶、导人于至善——幽明与会归思想的道德意义
生活在暴力冲突下的云南回汉族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与恐惧。残暴者的肆无忌惮,纵欲者的有恃无恐,当政者的无能,法律的形同虚设,传统道德观念的全面崩溃,更使无辜民众在社会动荡之中陷入对生的绝望、对死的恐怖中。社会需要稳定,更需要一种新的道德理念维护社会的健康发展;民众需要保护,更渴望心灵、情感的慰藉以及生存的信念。马德新反复阐明伊斯兰教的幽明与会归思想,突出强调后世与复生,打破了经验主义的一死无余的断灭论,打破了生与死的界限,让人超越有限、追求永恒。幽明与会归固然有其宗教意义,更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后世、复生、末日的赏善罚恶以及天堂、地狱,意在抑制扭曲的人性、泛滥的人欲。永久的后世,是给绝望者的希望;美好的天堂,是给良善者的安慰;后世的惩罚,是对纵欲者的警诫,地狱的烈火,是对残暴者的威慑。
在马德新看来,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在当时人欲泛滥、仇杀不断的动荡社会中,完全失去了约束力。仅仅依赖人的理性自觉而实现道德至善和理想人格,由于缺乏可行性而流变为圣人的消遣品。长期压制的人欲、极度扭曲的人性在无序的社会中空前释放,行为主体的道德自觉受其冲击几乎荡然无存。忽视外在力量(神意或法律)对人的行为的强制性,忽视外在的奖惩机制,忽视合理的利益的引导,使得制度化的纲常思想严重僵化,完全丧失了合理的内涵,不仅不能发挥正常的社会功能,而且是形形色色不道德行为横行肆虐的深层诱因。马德新宣扬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和道德理念,以解决普遍的信仰危机。他以为,此时唯有借助安拉的绝对权威和伊斯兰教的赏善罚恶机制,才能制止人欲的泛滥和道德的堕落,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他甚至把清真与克己、复礼等同,倡导“存天理、灭人欲”。“我教复命归真,以全真宰生人之正义,不图超常异众,而显诸神奇觉照也。其究竟,惟在克去己私,复还天理,所以名为清真教此耳。夫克己之谓清,复礼之谓真,其功在除妄绝私,其效在化己还真。”[12] 马德新此举,绝非对僵化的纲常思想的回归与倒退,更不是对腐朽思想的复辟,他赋予“天理”、“人欲”新的意义,肯定天理、否定人欲,不是压抑人性、扭曲人性,而是针对清末整个社会人性的普遍堕落、精神的极度空虚而提出的治世良方,有其特殊意义和作用。
幽明与会归思想的道德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复生的目的看,不仅要实现人之生命的超越,更为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复生意味着全部消除个人的贪欲和伪善,意味着良善本性的彻底显现,意味着社会正义、平等的真正实现。其二,从复生后的归宿看,人之宗教境界——天堂、地狱与人的现实的道德境界完全一致,后世的天堂地狱,就是今世的善恶行为,天堂就是天理,地狱就是人欲;天堂就是善,地狱就是恶。
针对人的贪欲、私欲,马德新以后世、会归作为克复贪欲、恢复善根的唯一良方。所谓复生,所谓会归,其意义在于恢复人的良善,重现人的本性,消除人的贪欲。马德新一方面抨击现实人性的贪婪、堕落、奸诈、虚伪、残暴,另一方面承认人性包含着良善、光明、积极的因素;一方面批判无限膨胀的个人私欲及其带来的社会灾难,另一方面又在树立健康的社会风尚,承认人性之本善,承认人有改邪归正的能力。所谓后世,不是与现实无关的彼岸,它与人在今世的善恶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因果关联。复生必定接受赏罚,届时安拉基于每个人在今世的行为,要作出公正无私的判决。这种审判是绝对的,无人可以逃脱,尘芥莫能隐蔽;是公正的,人人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须代他人(人祖、父母儿女或亲友)受过,也不由他人分担自己的过恶,人是自己行为的主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接受相应的果报。恶人的归宿是地狱,是熊熊燃烧的烈火,是没有尽头的痛苦。地狱刑罚的轻重,与人的过恶等量。人之暴虐,必将焚毁自身;人之罪过,必将危害其身。马德新描述地狱的恐怖,以告诫那些放纵私欲、损人利己、倚强欺弱、仗势凌弱、剥取民财以饱私欲的坏人,“惟图眼前细小之逸乐而招将来无限之罪孽”[8]。地狱是恶人的永久归宿,马德新以地狱的永久之苦威慑恶人,同时指出无心犯罪或有悔改之意者,将会得到真主的赦免,由此引导恶人改邪归正。有过者,视其罪孽,“有可赦者,有不可赦者。偶然于咎而无心过犯,是误为者,可赦;显然为非而无所忌惮,是故为者,不可赦;故为而有改悔之心者,可赦;故为而无恐惧之念者,不可赦;推之失于过宽、出于过忍者,可赦;以势凌人、以权傲物者,不可赦;自知其短无可如何者,可赦;鬼魔居心奸诈百出者,不可赦”[2]。
针对无辜的民众,马德新以天堂引导他们的良善;人在后世的地位、命运,取决于今世的行为。行善者将进入天堂永享天国的无尽福乐,通过天堂的美好,“唤醒众人,同归于善”。
针对受欺凌、受伤害的民众,则以真主公正无私的赏罚安慰他们,真主是绝对公正的,真主的末日审判将施及每一个人,在今世,常有作恶不罚、有功不赏、有了冤屈无法申诉的情况,但是在后世,今世所有的行为都将受到回报。尘世生活中,会有屈我、欺我之人,但是真主绝不会屈我、欺我,不仅如此,真主还会惩罚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使圣人也不能拯救他们。但是如果出于怜悯之心,自己主动原谅那些曾经屈我欺我者,真主也会饶恕他们。
对于饱受伤害的人们,马德新以真主的绝对公正、丝毫不谬的赏罚平衡其心理,在为他们伸张正义的同时,又引导他们以大仁大慈之心,忘记仇恨,化解仇恨。历史上回汉民族积怨较深,代代为仇,冤冤相报,没有尽头。为解决由来已久的民族冲突,马德新借助宗教的宽容精神和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以仁慈化解仇恨,以宽容取得谅解,“己能容人、主能容己”,意即人人宽容,自能得到他人的宽容。倘若如此,民族之间的矛盾就会得到缓和,和平就能实现,社会就能稳定,甚至就能建立人间天堂。
马德新以安拉在末日的审判以及天堂地狱作为社会道德的保障机制,目的在于为道德寻求一种外在的权威,借助于宗教的最高神灵安拉的全知与全能,通过安拉的威严与仁慈,引导良善,制止邪恶,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的融洽及民族关系的和谐,恢复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其积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这正是宗教道德的力量所在。
现实社会中战争、凶杀、欺诈、掠夺等恶行随处可见,暴露了人性中邪恶、卑鄙、狭隘的一面,尤其是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严重践踏了人类的生命尊严,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马德新提出以宗教道德抑制人们的恶行、暴行,以末日审判和地狱的火刑来约束、抑制人性中恶的倾向,以减少或避免伤害人类生命的恶行,这是作为宗教家的马德新唯一的选择。但是他的主张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丑恶与残暴。对人性之恶的批判,终究不能消除社会的罪恶,因为导致社会动乱、民族仇杀的根本原因,并非人性的恶欲和贪婪,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正是学者的马德新不能摆脱个人局限性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不能摆脱个人以及民族悲剧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马复初:《四典要会》,咸丰八年成书,光绪二十四年重刊本,页五眉批张亮基写道:“提出天堂地狱,无凭而有凭,是复初一片婆心。”
②同上,页十八吴学院评。
③王岱舆认为人性包含生性(草木之性)、觉性(鸟兽之性)和灵性(人性)三个方面,生、觉之性赖于身,身死而随灭,但人之灵性不依赖于身,仅为身所役,身死后灵性归回原所,永生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