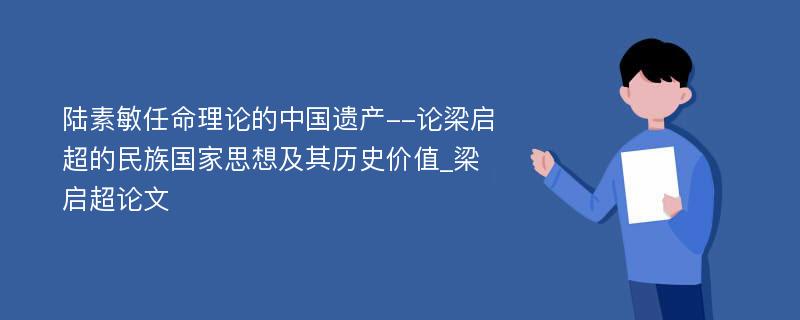
卢梭民约论的一份中国遗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及其历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梭论文,中国论文,遗产论文,国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8-0108-06
建构以国民为主体的国民国家,是梁启超在探索近代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思想。从这一思想的立论理据来看,主要是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民约论的影响和启迪。鉴于以往学术界对此问题所作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略加论析,祈识者不吝赐正。
一、梁启超对卢梭民约论的认知
梁启超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了解可追溯至甲午前后。自1890年购阅《瀛环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注:《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下称《文集》)之十一,第16页,《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后,他便注意广泛搜阅西书。至1896年撰《西学书目表》时,梁启超寓目的西书已达300多种,其中不乏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西政诸书”。(注: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3页。)通过这些著作,他对近代西方“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读“畴昔未见之籍”,探“畴昔所未穷之理”,(注:《论学日本文之益》,《文集》之四,第80页。)对西方政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其中,卢梭的民约论是他接触最早、受影响最深的一种社会政治学说。1899年,他在《清议报》上撰文,明确表示:“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注:《自由书·破坏主义》,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8-99页。)同年,在赴檀香山游历途中,他又赋诗将卢梭与另一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一起誉为“孕育新世纪”的“先河”。(注:《壮别二十六首》,《文集》之四十五(下),第7页。)1901年,梁启超撰《卢梭学案》(下称《学案》),在《清议报》上连载,向国人介绍卢梭学说。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将深奥费解的《民约论》阐释得主旨明确,通透易解,而且还在文后按语中盛赞卢梭的学说“精义入神,盛水不漏”。1902年,他将此文改题为《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在《新民丛报》上转载。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近世欧洲四大政治学说》一书时,他又将该文收入其中。可见,梁启超对卢梭学说是何等推崇。当时的留日学生,对于梁氏崇信卢梭,几乎尽人皆知,有人甚至直呼他为卢梭。(注:1902年春,马君武作《壬寅春送梁任公之美洲》一诗,其中就有“春风别卢骚”之句。参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9页。)
事实上,如果我们以卢梭所著《社会契约论》为学理依据,将《卢梭学案》作为“文本”,加以检视的话,便可大致梳理出梁启超对卢梭学说的认知。
在《学案》中,梁启超首先介绍了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他认为卢梭关于人们在自愿的前提下通过订立契约而结成共同体,从而形成国家的思想,建基于人人“皆有平等之自由权”的观念之上,实际上是从“立国之理义”方面阐明了国家的起源问题。“要而论之,则民约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王与臣庶之别,则无论由于君王之威力,由于臣民之好意,皆悖于事理者也。”(注:《卢梭学案》,《文集》之六,第100页。本节下引出于此文者,不具注。)为了揭示社会契约思想中蕴涵的自由之精义,梁启超还反复从责任伦理和道德伦理两方面申论了卢梭关于自由权不可放弃的观点。他指出,“自由者,凡百权之本也,凡百责任之原也”,人若无自由权,则“善恶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
当然,作为一位有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家,梁启超也发现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的内在矛盾。在卢梭看来,国家的建立以订约者的权利转让为基础,个人愈是毫无保留地献给整体,国家就愈完美。为此,他要求赋予国家以“普遍的强制性力量”,(注: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版,第41页。)以卫护其作为契约共同体的“统一性”与权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个人通过契约而转让的权利是有限度的,“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整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而国家也“决不能给臣民以任何一种对于集体毫无用处的约束”。(注: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版,第42页。)这样,卢梭在理论的逻辑周延性方面必然难以自洽。对此,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谈民约,始以保护个人自由为起点,后论及共同体,反而重国家而轻个人,将人民等同为国家之“附庸”,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在他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之所以有缺憾,是因为他深受古希腊罗马政治学说的影响,以致各种“以国为重”的“旧主义”,“往来于胸中,拂之不去”。显然,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梁启超更注重前者。
立基于民约思想之上,卢梭提出了著名的主权在民说。对这一思想,梁启超同样颇为推崇。他引述卢梭的观点说,在契约未立之前,个人的主权与自由权合为一体;及契约达成后,则主权由个人之手转归为众人之“公意”。所谓“公意”,是指全体国民共同一致的自由意志。与那种由“一时之私意”聚合而成、以“私利”为目的的“众意”不同,“公意”“必常以公益为目的”,所以能赋予国家主权以生命和意志。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具有不可让渡与不可分割两个基本特点。近代西方国家的体制建构,之所以采取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正是为了保证主权时时能完整地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使之合于一而不可分”。
虽然国家主权源于“公意”,但“公意”毕竟是“无形”的,在生活实践中只能表现为某种形式的规约,这就是法律。卢梭认为,法律“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既是“公意”的“记录”,又是其“行为”。(注: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版,第51页。)对此,梁启超作了诠释:“法律者,以广博之意欲与广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因此,根据“公意”制订并遵守法律是全体国民“公有之责任”,而国家执行法律实际上就是运用“公意”来保护人们的天赋自由。就此而言,法律体现了治者与被治者的辩证统一。
建基于主权在民说之上的政府论,是卢梭社会政治学说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学案》中也作了介绍。他说,所谓政府就是“受民委托以施行其公意之一机关”。其职责在于沟通国家与国民,并执行法律以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根据自己对卢梭政府论的理解,梁启超主张发挥中国固有的“民间自治之风”,并“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建立“邦联民主之制”,从而“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过对卢梭民约论的译介和批判,梁启超实际上已认同和接受了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基于个人本位立场上的自由、权利观念以及以此为内核的社会契约、人民主权以及民主政府等思想。这对他的政治思想和国家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梁启超民权思想的升华与“国民主体”论的确立
众所周知,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已经形成了以开民智、兴绅权为主要内容的民权思想。但这一时期,他因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君权主义倾向,加之西学知识有限,故而其民权思想的内涵还较为肤浅。流亡日本后,通过研习和接受卢梭的民约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因增添新的内容而有所升华。
东渡扶桑之前,梁启超就指出,中国贫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历代统治者“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以致民众“缺权”甚或“无权”。(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文集》之一,第99页。)到日本后,因受卢梭的影响,他更多地从“天赋人权”的角度来谈民权。他指出,所谓权利就是“天生物而赋之以自捍自保之良能”。人之为人,除了有“形下”生存之外,更有“形上”生存。“形上”生存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具有权利意识。在他看来,有无权利意识不仅关乎个人的生存状态,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盛衰安危。“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专集》(下称《专集》)之四,第39页。)民众若无权利思想,国家就如无根之槁木,在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打下,势必难逃衰萎的恶运。数千年来,正由于广大民众断绝“‘权利’二字之识想”,一直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因而政治参与意识淡薄,政治能力低下。有鉴于此,梁启超提出,“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注:《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文集》之十四,第31、30页。)进而他大声疾呼举国上下应以“勿摧压权利思想”、“养成权利思想”、“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专集》(下称《专集》)之四,第39-40页。)
与权利观念紧密相联的是,梁启超民权思想中的自由意识也有所增加。他说:“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日生命,二日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文集》之五,第45页。)将自由视为人生的一项基本权利,与生命同等重要,说明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已触及卢梭民约论的核心,即保护个人天赋自由问题。梁启超认为,“民权自由之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注:《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文集》之十四,第30页。)是欧美各国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石,自然也应适用于中国。梁启超将自由分为四种: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与生计自由。其中,他最关注的是政治自由和民族自由。所谓政治自由,是指“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其关键在于人民有政治参与权。而民族自由,实际上就是“民族建国问题”,即“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注:《新民说·论自由》,《专集》之四,第40-41页。)从谈个人自由上升到讲政治自由与民族自由,这是梁启超对卢梭自由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实质是凸显了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时代主题。
由上可见,自融入权利观念和自由意识之后,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不但理论色彩增强了,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其主旨已不仅仅局限于主张让人民分享部分政治权力,而是要求建立一个以权利和自由理念为价值基核的近代民族国家。
立足于新的民权思想之上,以卢梭的民约论为理据,梁启超首先在“国民—国家”的框架内系统地检讨国与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勃兴,在于各国民权发达,国民“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而中国之所以颓然日危,是因为民众缺乏“爱国之性质”,对国家的兴衰荣辱漠然视之。可见,国与民,实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注:《爱国论》,《文集》之三,第69-73页。)舍君权而言民权,视民权兴灭为国权盛衰的前提条件,表明梁启超国家思想的重心已经下移,而其民主意识相应地有所提升。继而,梁启超又进一步就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界定。他说:“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辱,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文集》之四,第56页。)显然,作为近代民族国家赖以建构的人格载体,国民是有高度自治精神的“政治存在”,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而且有相对独立的政治行为能力。国民与专制统治下无权利和自由意识,唯君命、上命是从的封建臣民性质迥异。梁启超认为,“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注:《新民说·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专集》之四,第7页。)换言之,“国家之强弱,一视其国民之志趣、品格以为差”,“政府之良否,恒与国民良否为比例”。(注:《中国积弱溯源论》,《文集》之五,第14页。)非但如此,国民之优劣还主宰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成败,因为时至今日,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一种“其力强”、“其时长”的“国民竞争”。(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文集》之四,第57页。)
通过对国民重要性的论证,梁启超确立了国民是国家主体的思想。以此为理据,他提出了“欲维新吾国,必当先维新吾民”的全新命题,进而形成了体制完备的“新民”说。他指出,“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注:《新民说·叙论》,《专集》之四,第1页。)鉴于中国一向只有“群族而居,自成风俗”的“部民”,而没有“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的“国民”,(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专集》之四,第16页。)梁启超主张全国民众在“萃沥其本有”的基础上,“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专集》之四,第6页。)其中,他特别强调应注重“养吾人国家思想”,以使民众在面对自身、朝廷以及外族或世界时,“知有国家”。将梁启超的主张置于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耻的重创后,国内民气嗒然不振的历史语境中来看,这实际上是要求人们破除一己之私心私念和狭隘的王朝意识,荡涤夜朗自大的虚骄之气和奴颜卑骨的媚外心态,树立起崭新的国民意识、国家和民族观念。
“国民主体”论构成了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的基础。它强调更新民众的思想观念,养成国民资格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不但极大地张扬了近代民主意识和社会变革主体意识,而且在近代中国率先设计出一条旨在通过民众自我改造,自下而上实现民族自新的救国方略。
三、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立足于清末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以卢梭的民约论和“国民主体”论的内在理路为逻辑基点,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思想主旨,梁启超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国民国家思想。大体而言,这一思想是从以下几个向度展开的:
1.批判专制王权。戊戌以前,梁启超就曾指出专制统治的本质在于“以独术治群”。(注:《〈说群〉序》,《文集》之二,第4页。)流亡日本后,受卢梭主权在民说的启迪,他对专制王权的批判更加深入,并明确提出“完全国家”论。他说:“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土地之事,自治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所谓之完全成立之国。”(注:《少年中国说》,《文集》之五,第9页。)以此为标准衡鉴历史,可见几千年来,中国实际上只有朝廷的更迭,而无国家的进化。所谓唐虞夏商周直至后世的唐宋元明清,不过“皆朝名耳”,何尝有“国家”?即便是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民主制度典范的禅让制,亦不过是“以国家为君王所有物”而“私相授受”而已,实为中央集权统治的滥殇。(注:《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殇考》,《文集》之六,第22-23页。)正因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总是视国家为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注:《中国积弱溯源论》,《文集》之五,第28页。)1902年,他相继发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分别从历史和理论上剖析和批判了专制统治。事实上,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政治上一度趋于激进,与这种立基于“国民主体”论之上而形成的批判意识是分不开的。
2.憧憬理想国家。基于对卢梭“契约国家”学说的理解,梁启超曾先后提出过“种族国家”与“家族国家”说,并指出远古时代人们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于保护种族或家族全体成员的安全与利益。(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文集》之四,第61页。)而后世暴君民贼却以天下为私,将国家变成奴役人民的专政机器。显然,专制国家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有鉴于此,梁启超提出理想国家的立国原则当以“保护国民权利”、“为人民保安全谋安全”为根本。(注:《商会议》,《文集》之四,第2页。)基于此一原则所建立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代民以任群治”,其职能无外乎:“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至于政府的权限,则“随民族文野之差而变”。具体而言,当一国之民处于“野蛮时代”,政府之权限“不可不强且大”;而对于“开化之民”,若无侵犯人民自由权的事发生,“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勿宜过问也”。(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文集》之十,第2-3页。)这里,梁启超实际上表达了近代西方关于政府是“守夜人”的自由主义立场。不过,应指出的是,他对政府权限与民众素质之间相对关系的认识,也为其日后转向“国家主义”,主张开明专制埋下了思想种子。
3.吁求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注:《论民族竞争大势》,《文集》之十,第11页。)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道德情感,民族主义唤起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心理基础。在梁启超看来,西方各国的发达与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而中国的民族主义“犹未胚胎”。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培育民族主义。(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文集》之六,第20页。)虽然由于受革命党人的影响,梁启超一度曾视“讨满”为“唤起民族精神”“最适宜之主义”。(注:《致康有为书》,《梁启超选集》,第322页。)但从总体上看,他更多的还是从抵御外侮的视角来谈论民族主义。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就相继作了《瓜分危言》、《灭国新法论》等,揭露列强对华侵略已由掠夺土地之类的“有形之瓜分”转向攫取各种利权的“无形之瓜分”。世纪之交前后,他又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欧美各国由民族主义时代向“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过渡,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竞争必将转化为国民之间的竞争,因而主张建立以国民为主体的国民国家,“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文集》之四,第60页。)可见,反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始终是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的重心所在。
4.企盼新型社会变革主体。戊戌以前,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保皇”、“尊皇”。但自确立了“国民主体”论后,他就明确表示自己“所思所梦所祷祈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注:《过渡时代论》,《文集》之六,第32页。)显然,在构想民族振兴和国家重建的蓝图时,梁启超已不再寄望于“上层社会”和少数千载不一遇的圣君贤相。相反,他强调指出,中国要在列强纷争的世界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人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注:《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专集》之四,第2页。)1902年前后,他还提出了“惟中等社会为一国进步之机键”(注:《雅典小史》,《专集》之十六,第8页。)的观点。从圣君贤相、草野英雄到“国民”与“中等社会”,梁启超论述话语的变化,不仅是政治目光和思维取向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历史的理性自觉凸现了他对新型社会变革主体的企盼。
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的发展客观上已向中国人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课题。作为回应,梁启超外察世界大势,内省中国国情,以卢梭学说为理据,构建出具有强烈变革意识和理性精神的国民国家思想,不但凸现了这一时代课题,适应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现实诉求,而且其特有的理论魅力唤起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并为时人及后人进一步探究国家问题提供了精神支援和思想资料。具体地说,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率先摒弃传统的朝代意识和天下观念,代之以近代国家观念,将建立独立的“国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的任务提上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中心日程。二是牢固树立国民是国家主体的思想,将民主观念和社会变革的主体意识渗透到国家思想中去,对破除传统王权观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新民”说,影响既深且巨,开启了20世纪初年“国民性”讨论的滥觞。三是提倡民族主义,反对外来侵略,有助于培育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推动民族觉醒,促进国家的独立。
由于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直接关乎民族独立和国家重建的宏大历史主题,满足了所有不甘国家沦亡的有识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精神渴求,因而在当时的思想舆论界引起广泛的共鸣。翻检这一时期的报章杂志,可以发现,喧腾于国人脑中笔端的诸如自由、平等、国民、国家、民族主义等思想观念几乎无一不是梁启超言论的翻版。例如,《国民报》所载《原国》、《说国民》以及《湖北学生界》所载《论中国之前途与国民应尽之责任》等文,就因袭了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的某些观点。而邹容的《革命军》甚至直接移植了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的一些段落和文句。对梁启超的影响,郭沫若曾作出过公允的评论。他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20世纪初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注: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2页。)事实上,正是经过了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的陶冶,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才得以挣脱传统的王朝观念和忠君意识的束缚,牢固树立起近代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实现了国家理念的近代转型,并投身于为建立新型理想国家而斗争的洪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