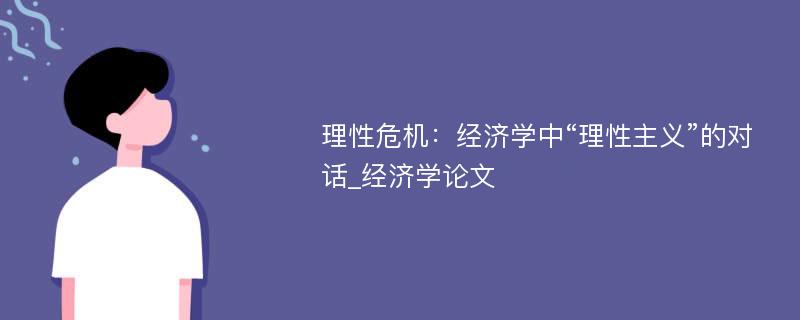
理性的危机——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亚里士多德传统、奥古斯丁传统,以及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包括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等等。处于不同传统中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他“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于是,在我看来,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的经济学家们(至少是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迫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关于经济学“理性”含义的经典性看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个含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虽然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的假设,但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原本是包括“自利性”和“社会性”的,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
第二个含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个体对自身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
第三个含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
叶:我理解,经济学“理性”最关键的含义应该是“极大化原则”。“自利性假设”和“一致性假设”只是“极大化原则”的前提,是对“极大化原则”的某种限制和规定,从而把这一原则限定在以下两个“边界”内:
第一,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个人效用或单个厂商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某个集体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建立在“极大化原则”基础上的个人经济行为并不意味着个人行为的“绝对自由”,个人的自由行为必须以不破坏他人的自由行为为边界。
汪:我同意你的理解。但我认为,上述经济学“理性”的经典含义已经在许多方面遭遇到不可克服的现代危机:
首先,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自利性假设”被当成“工具主义”假设是符合“大数原则”的。
其次,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自利性假设”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发问: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这个“自利性假设”呢?它现在完全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它甚至使演化成为过分简单的从而最终会消亡的过程。
叶:但是,我以为如果我们坚持经济学“理性”的逻辑主体是“极大化原则”,那么仍然可以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主流经济学采取毫无批判的态度。
首先,“极大化原则”的含义是指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效用”一词的内涵,从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穆勒,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戈森、杰文斯,一直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都把它定义为一种“使人们感到幸福和满足的心理状态”。即便在萨缪尔森最新出版的《经济学》教材中,“效用”仍被定义为一种“主观上的享受或有用性”。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通常,人们会错误地理解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把它看做一种外在的、物质的、独立于行为主体的“东西”;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这样一来就大大缩小了“效用”的外延。其实,如果我们坚持“效用”只是行为主体主观上、心理上的“满足感”,它的外延就会非常宽泛;它既可以包含人们的物质享受,也可以包含人们的精神享受。
其次,我认为,进化论无论就其逻辑框架还是实证判据来说,从来就不支持“线性”的进化观。40亿年地球生命的进化史无不证明,竞争不但不会导致“多样性”的缺失,而且恰恰是“多样性”产生的重要条件。说到“效率”,我们总是指“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我无法认同“效率”仅仅用来指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进化有所谓的“目标”或“目的”的话,那它只能是“进化”本身。因此,进化的“效率”就是更有效的进化。
汪:可是,我要指出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三种“危机”,恰恰是针对“极大化原则”本身的!
经济学“理性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这里,我们看到的“理性”行为已经不单纯是个人“效用”的“极大化”行为了。因为,一次博弈的均衡可以使所有的博弈者都不满意(例如,所谓的“囚徒困境”)。不论如何,博弈的结局(例如,某种社会制度的实现)并不符合个体博弈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使工具主义“理性观”很难立足。于是,经济学家必须放弃“作为价值最大化”的理性,而如阿马蒂亚·森那样,把“理性”理解为“作为内在一致性的理性”。
叶:确实,传统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及其内核“极大化原则”在“博弈”行为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是来自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的: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个体理性的“极大化原则”,这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逻辑自恰所要求的,那么我们在博弈过程中就不得不接受“帕累托无效”的结果;如果我们要坚持获得“帕累托最优”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逻辑自恰所要求的,那么我们在博弈决策中就不得不放弃“极大化原则”的初衷。
经济学“理性”的要义是“效用最大化”,而“效用”是指行为主体的“满足感”;更进一步,“效用”是被一个人的“偏好”决定的。当一个人具有“公平”的“偏好”时,他就会从“公平”的事件中获得“效用”;当一个人因为追求“公平”而放弃金钱时,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对他来说,“公平”的效用大于“金钱”的效用。因此,在这个场合,他的行为是“理性”的!
在所有上述语境中,经济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跨越了它自身的边界。因此,我更倾向于把这些看法和观点称之为一种统一的、演化的“理性主义”。
汪:你终于提到了制度的“博弈”与“演化”。但我要指出的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必须面对的第四种“危机”,恰恰是关于“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是在1989年以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同,“制度变迁”的研究注意经济运作的政治、法律、历史及文化环境,力图从这一环境中抽象出对特定制度的“运作成本”有重大意义的非经济因素来。在制度与经济史研究领域里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立场:
一种以诺斯的观点为代表,认为一个社会可能长期“锁入”贫困状态内;与此对立的是主流经济学家,例如华盛顿大学新制度经济学家巴塞尔的看法,认为一个社会长期停滞在低水平发展阶段是不可能的事情。后者的论据在于,国际竞争迟早会迫使这一停滞社会要么改革以求发展,要么就消亡;而前者的论据是历史的,即目前所见到的各种社会经济当中,确实存在着长期停滞的经济。
我认为,就制度的大范围变迁而言,没有哪一个个人的选择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的大范围变迁基本上是社会博弈的结果,不管“理性”的个人喜欢还是不喜欢。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大范围制度变迁的研究所涉及的对所谓“制度非理性”问题的解释,使得传统的行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即“是否理性”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叶:“锁定效应”或者如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正是“进化”或“演化”的本性。经济学家总是习惯于从一个维度,即“经济增长”的维度来考虑“效率”。但在整个生命的进化史中,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单一的维度吗?
如是,我们将不得不暂时脱离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范式,对“理性”一词的本意进行一番回溯。根据《哲学大词典》释义,所谓“理性”,是指“人的一种认识能力、精神机能,可分为广狭二义。就狭义说,即专门作为一个认识论的范畴,理性指人的高级认识能力或阶段,同‘感性’认识能力或阶段相对应。就广义说,理性泛指人的健全的理智、健全的思想和知识,与迷信、愚昧无知相对立”。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一个“理性”人所要最大化的“效用”恰恰就是可以表现为“偏好”的情感、欲望。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理性”对于经济学和哲学来说,几乎就像两个毫不相干的范畴。
汪:叶航,如果要“回溯”,我们知道,西方的“理性”一词是来自拉丁文的,但“理性精神”则来自古希腊语词“gnoo—”(即“知一”)的字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的吠陀典籍的名称“Vid—”,其义为“知道”,但含义复杂得多。在哲学中,对“理性”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通常,我们可以区分出所谓的“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就前者而言,也许更适合你上面所讲的,强调“理性”是对“人性”的超越,其主要代表是康德,向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强调理智对情感的克制。就后者而言,主要代表是洛克和休谟,把“理性”回归到“人性”,强调“感觉”、“意志”甚至“激情”对“理性”的作用,向上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主要来自“英美传统”,因此不能说它和哲学的“理性传统”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