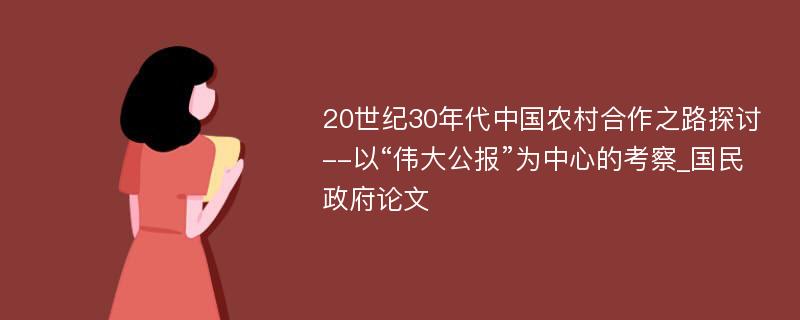
19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道路问题的讨论——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中国论文,农村合作论文,道路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自兴起到进入农村复兴运动高涨的30年代已走过大约10个年头,而1933年到抗战爆发的三四年间则是其发展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合作运动或合作事业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合作社数量发展速度愈来愈快;(2)以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单一结构和以单营为主的合作社经营方式有所变化,运销合作社、兼营合作社(主要兼营运销)发展较快;(3)国民政府对合作运动的推动力度明显加强;(4)推动合作运动的力量更加多元化,除华洋义赈会、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团体外,商业银行亦纷纷提倡合作并向农村合作社投资放款。时人将之称为合作运动“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①。由于这一时期为合作运动实践运作及发展的关键时期,自然成为社会各界在理论上探讨的主题,而《大公报》作为当时享有盛誉的舆论媒体积极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或发表社论或刊登相关文章及报道,其中“商资归农”、“合作社兼营”、“合作事业发展速度”及“合作事业发展道路”等问题成为讨论中最集中的几个主题。是故,笔者在讨论前三个问题后②,拟再以“合作事业发展道路”问题为中心,来考察该报报人及相关学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与主张,检视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其实践取向。
一
实际上,合作界在讨论合作事业发展速度之时,与之相关的另一问题的讨论亦在进行,即中国合作事业应走合作政策之路抑或合作运动之路?
然何者谓“合作政策”又何者谓“合作运动”?简言之,自上而下者系合作政策,自下而上者即合作运动;由政府推动者是合作政策,由民众自发者为合作运动。正如王志莘所解释的那样:“政策之与运动迥然不同,前者为政府有整个目的之计划,后者为人民自觉之表现。申言之,政策须有政府强有力之援助推动,与夫严密之统制;运动则为民间逼于实际需要而发生社会性的动作,政府仅能在旁予以若干之维护而已。”③关于这一点,不论当时还是现在似乎均无什么争议,但对于社会团体所推动的合作事业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时人认识颇有不同——有人认为属于合作政策,如吴华宝、方显廷即是;有人认为属于合作运动,如英国施克兰(C.F Strickland)即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团体所推动的合作事业与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注重社员自动性。以华洋义赈会为例,犹如章元善所言,“义赈会认明合作是农民们自己的事业,应由农民们自己去经营,不容局外人干涉。可是在这教育落后的农民社会里,若无局外人来协助鼓励,农业合作是不会有天然的动机的,因此立定在第三者的地位去提倡农业合作,在没有动机的农村唤起农人们的注意、给他们明了合作的便利,等到有了动机,促成他们的组织,此后并不断地关心他们的工作、改善他们合作社的组织、增加新社社务的效率、介绍各社的联络、在农业与金融界尚未发生接触时期供给必要的资金。……自始至终,保持各社的独立,同时引导农人们的自动。”④本文所述的关于中国合作事业应走何种道路的争论亦主要围绕合作事业应由社会团体还是政府推进的问题。
换言之,中国合作事业所走的是合作政策之路还是合作运动之路?1927年前,合作事业由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农学院等社会团体或学术团体推动,尤其华洋义赈会;1928年后,先是政府加入,而到30年代则有更多力量参与,其中国民政府的推动力度日渐强劲。依据对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各种推动力量作用大小的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中国合作事业自始所走的就是合作政策之路,有人认为1927年前所走的是合作运动之路而1928年后乃是合作政策之路。同时,有人则认为1928年后实际是两条道路同时并进,尽管从指导合作社的机关看,政府机关占了绝对多数(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统计,在内地15省3市中共有合作指导机关524个,其中政府机关专任或兼任合作指导者457个,占总数87.2%,社会团体专任或兼任合作指导者67个,占总数12.8%,而在担任合作指导的社会团体中由合作社联合会担任合作指导者仅8处,占总数1.52%)⑤。
从中国当时农村合作实践观察,合作事业所走之路除“运动与政策两条道路并进”且以“合作政策道路”为主的特点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倾向即两条道路之融合,定县实验县和邹平实验县就是典型例子。这两个县政建设实验县都是根据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有关县政改革决议,以及次年内政部有关尽快设立实验县或县政建设实验区通令而于1933年成立的。其中,定县合作事业以1933年秋为界可划分成两个时期,1932-1933年秋属第一时期,合作事业由平教会独立推动,或者说“不论积极的推进和消极的指导都完全由平教会独当一面”;1933年秋实验县成立后,合作事业则由平教会设计而由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推动,这一时期“关于推动中积极工作的‘组织’,关于消极工作的‘视查’、‘考核’,都由平教会转移到研究院。这时候平教会只在作合作设计的研究和专门教材的编撰,仅仅保留了设计和一部分的训练工作。”邹平实验县合作事业以1935年为界也可分成两个阶段。1931年邹平已被省政府定为实验县,同时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1935年在邹平推进和指导合作事业的有三个机关:(1)指导棉花运销合作及其他部门农业合作的研究院农场,(2)提倡庄仓合作的县政府,(3)组织信用合作社的县金融流通处。这些“机关只是在作片段的实验并没有整个的计划”,邹平合作事业实处“推动分立时期”。1935年后,为改变这种分立状况,成立了“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以县长为委员长并选聘研究院经济合作教授、研究院农场主任和有关职员、县政府第四科科长和技术员、县金融流通处经理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共同组织,这个机关兼管设计、组织、训练和指导各方面事工,邹平合作事业进入“推动调整时期”⑥。定县与邹平社会团体与政府结合的方式虽不同,但“政教合一”却是共同特征。此外,从国民政府与华洋义赈会之关系看,1931年长江大水灾后义赈会受政府委托于受灾地区办理农赈、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1934年义赈会协助陕西省政府办理合作事业,1935年最高合作行政机关合作司成立后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担任司长一职,则说明在推进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显现出日渐融合的趋势。
二
那么,中国合作事业究竟应走合作运动之路还是合作政策之路?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早在20年代就存在,汤苍园和薛仙舟就是两种不同主张的典型代表。早期合作主义者汤苍园认为,“合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其势力所及,将破坏经济帝国主义而有余,但它的方法则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合作主义不注重革命而注重建设,不假手国家而真成于团体,其进也渐,其行也远。”⑦这里所谓的“不假手国家而真成于团体,其进也渐,其行也远”,则表明汤氏主张中国应走合作运动之路。而薛仙舟因与国民党要人陈果夫有着密切的师生关系,所以在其1927年为国民政府撰写的《中国合作化方案》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合作政策”的思想。他说:“我们应该以国家的权力,用大规模的计划去促成全国的合作化,实现全国共和,而为世界倡。”⑧
30年代,随着合作事业进一步发展及其发展过程中种种问题的出现,这一问题再度引起合作界关注,有人主张走合作运动之路,有人主张走合作政策之路,还有人主张走两者相结合之路。主张中国走合作运动之路的即法国季特(Charles Gide)教授所谓的“真合作派”,其中以1934年来华讲学的英国施克兰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合作事业的组织与指导应由社会团体而非政府负责,政府只宜担任合作社的考核、登记等行政事务并在法律上业务上从旁协助而已。其理由如下:第一,合作事业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只应由社会方面而不应由政府方面推进,因为“合作事业是民众的自觉、自动、自主的社会经济事业,是目的,不是手段。它是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它一天一天的扩大,资本主义势力就一天一天的缩小,合作经济制度的成功便是资本主义的消灭。这种事业是自由的、和谐的、由下而上、由近而远的发展,应该由社会方面去推进,不应由政府方面去推进。”第二,由政府方面推进合作事业存在诸多弊端:(1)从中国政治状况来看,“目前政治未全上轨道,吏治未清,行政效率低下,仍不免有衙门习气。遇事只讲官样文章,不求实际,且‘官高皇帝远’不易达到平民。”在这种情形之下,由政府机关担任合作社指导与组织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尤其不能建立真正的合作基础。(2)从中国民众心理来看,“吾国民众受官吏之欺骗压榨为时已久,犹惊弓之鸟,望而生畏”,故由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很难受到民众欢迎。(3)从经济费用来看,政府机关开销较大,大多数政府性质的合作指导机关所经手的合作贷款的费用占到了贷款额15%,即每贷出100元,费用即15元。(4)从政策稳定性来看,由政府推进合作事业不仅易受政治变动影响且易受人事变动影响,“因政府多以政党为背景,一旦政党失势、政府改组,他党当权政策变更,合作事业即受其打击。即在同一政府之下,其政策亦随时变易,每遇政策变易,则影响合作事业。”再加上“吾国行政人员随时更易,且各人有各人之见解与主张,每遇人事更易,合作政策亦多随之更易”。因此,由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很难保证政策的稳定性⑨。有鉴于此,他们认为只有由华洋义赈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担任合作社组织与指导工作才能避免上述弊端,并收到“费用小而成功大”的效果。
主张走合作政策之路的以王志莘、寿勉成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推进中国合作事业应由政府担负组织与指导之责,理由是:(1)由民众自动或社会团体推动不合中国国情,因“吾国目前民众缺乏知识、组织与技能,若由彼等自动推进合作事业实不可能。即由社会方面推动,亦非常缓慢,且有许多地方因经费、人材、政治等困难,由社会团体担任合作指导为不可能。”“如欲由合作运动方式俟其自由发展,则以我国目下社会经济情形之急迫,殊有缓不救急之感觉。”故非由政府大规模推行不为功。(2)中国具备由政府推动合作事业的政治基础,因“吾国现为党治,其建国设施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欲实现民生主义则有赖于实施合作政策,先总理在其民生主义中曾经提示,近亦为一般党政领袖所推崇。又吾国目前合作指导机关87.2%属于政府,可知采取合作政策为建国所必需。”(3)由政府推进合作事业符合世界潮流,“最近世界潮流,已趋于统制与计划经济,俄、义倡之于先,德、英、法、美、日继之于后,因在此资本主义经济机构崩溃,国际竞争无法调和之时非取自卫的国家经济对策不可。目前中国内部经济机构散漫冲突,外受国际经济帝国主义之掠夺榨取,尤有采取统制与计划经济之必要。又一国既采统制与计划经济政策,对于合作事业亦必须有相当之统制与计划。各国皆然,我亦不能例外。”⑩寿勉成的分析更具代表性,他指出:要改变中国生产状况混乱以及资金短缺、财富浪费的局面并建立全民族独立的经济体系,惟有推行计划经济一途。“然推行计划经济非合作社不可,盖必经济、社会之各部分均有其组织与系统而后计划经济之拟订与推进,方能运用尽利也”。“中国的计划经济当然是三民主义的计划经济,而合作社的组织正是最适于三民主义的一种组织。”(11)
前述两种主张不免有些极端,故又有人主张走两者相结合的道路,此观点在合作界占多数。张国维指出,上述两种主张各有长短,“彼方之长,即此方之短;此方之长,即彼方之短”。由合作运动推进合作事业的最大优点在于能“稳固基础,健全组织”,而由合作政策推进合作事业的最大优点则在于能“通盘计划,收获速效”,双方优点均为推进合作事业所必需。因此,“苟单走合作政策或单走合作运动的道路,无论其理由如何充分,进行如何顺利,不免有其重大之缺点,亦不能解决此当前问题。”“目前推进吾国合作事业比较适当的途径须由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两方面同时进行,并须使此两方力量沟通调和、截长补短、相互为用。由政策以促成运动,由运动以完成政策,以期建立适合民生主义、世界潮流(即有统制与计划性)的民治、民享、民有的合作经济制度。”(12)宋之英在1935年全国合作讨论会召开前也提出:“在此时政府亟应组一强有力之监督与指导机关,以统一全国之合作指导方针与步调,但同时亦应承认社会团体之合作指导权,只要社会团体不背现行合作法规、不以营利为目的、真正为农民谋利益者皆可承认。”(13)
怎样结合又如何把握结合的“度”?这是主张走结合道路者所关注的问题。一般的看法是,政府既有提倡的必要又须注重民众的自动,而政府提倡须注意两点:一是政府提倡只适于合作事业初期,二是政府提倡要保持适度。张鸿钧在谈到印度合作时说:“政府提倡监督之外不要忽略了人民的自动,合作事业的重心本在乎初级合作社的各个社员,如果他们诚意的自动的去做,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在民智未开的地方,人民不知合作是什么东西,这时候若无私人团体担得起这个运动,政府是应该出而提倡推行。印度以庞大的国家、愚昧的国民,在短期间内能普及合作运动确应归功于政府提倡的努力。提倡一种运动,政府固可以由上而下的推行,等到运动已然兴起、真正要办理合作事业的时候,则人民非自动的诚意合作不可了。合作这种工作不是旁人能代替的,不是强迫能生效的,更不宜以政府的大量贷款诱惑人民,所以政府加入应该适可而止,包办是不可的。”(14)施克兰、黄肇兴等人也持类似观点,他们在谈到热带国家合作方法时指出,“热带人民知识幼稚、思想落伍、自动与自治能力之缺乏,不言可知。然自动与自治之能力实为合作运动必要之条件。……热带人民既缺乏此种必要条件,则合作运动不得不有赖于政府之提倡与管理,由政府担任合作金融、合作检查及合作宣传、教育与指导等任务。”但是,政府管理合作社虽有必要性,“惟此仅为权宜之计,非永久之政策也。”“政府管理合作事业,无论于合作金融、合作检查或合作宣传、教育与指导,任何一方面仅宜于合作运动之初期,其最大危机为合作事业官僚化,其最大成功为逐渐培植合作者自动与自治之能力,庶几他日合作运动可脱离任何依赖而跻于独立自治之境也。”(15)他们都强调政府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合作事业初期,以后则应逐步将权力下放给合作者。章元善则特别强调政府提倡要遵循“适度”原则。作为社会团体负责人,他主张合作事业初期需要政府提倡,走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相结合之路,即“政府提倡合作是有必要的,因为合作虽是人民的运动,可是现时正在萌发时期,农业向来所享的机会不与工商业平等。此时若不提倡,合作运动的发展一时不能很快,当此民不聊生的时期不应袖手旁观、听其自然。”(16)他在给1935年召开的全国合作讨论会提交的《规划责任案》中提出,监督合作社的责任应由政府所组织的专门行政机关担当,在合作社省联合会未成立前指导一省合作社的责任可由省监督机关兼理或委托适当的社会团体代管;至于合作社的金融调剂,在省合作金库成立之前也应由监督机关代筹资金(17)。但他认为政府提倡力度要适当,绝不能损害合作本质,特别是“提倡的方法极应研究,合作运动有他的本能,不希望获得含有救济性质的赐与,不需要分外的优益权利。给予优良的环境,使他可以自由发展,已是很好。所谓优良的环境,就是使他与一般工商业得到同样的待遇。过分的提倡,非但于合作无补,反而要损及他的本质。过分的美意,使得合作运动沦为一种慈善事业,那就铸成大错了!”“依我看来,政府此时对合作运动应为之解除一切可以迟缓他进展的种种束缚,在不妨碍合作原则范围以内应予以自由发展之机会。用种种法令来取缔妨碍合作者是可以的,但是要留神不要同时亦阻碍了合作的正当进步。”消极的解除束缚(如印花税、登记手续之繁琐)“有时比积极的加以助力收益远大”。“吾国农业向来不得享受与工商业均等之机会,一切交通设备、金融便利,前此皆为工商业而设。今如提倡合作,政府应为农业设法,给予前此得不到着的种种便利,尤其是金钱的通融。”“除此之外,政府应深切认识合作运动有自立之能力,无需分外之优遇。即是消极的解除束缚、积极的给予便利二者亦不过是在创办时代的一种特殊设施。”可见,在他看来,政府在推进合作事业中的作用应限于为其创设一种良好环境或是消极地解除束缚,或是积极地提供便利而已(18)。
总之,主张走合作运动之路者视合作为目的,注重合作事业的“质”;主张走合作政策之路者视合作为手段,更注重合作事业发展速度;而主张将两条道路相结合者则力图探寻一条使合作事业“量”与“质”能够兼顾并进的可行路径。因此,凡主张合作运动者大多会认为当时合作社发展速度“过快”。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认可合作政策者都认为当时合作社发展速度还不够快。例如,方显廷就认为在农村破产、农民既穷且愚的情形下,“穷则不能有积蓄,无积蓄则难求外界金融之贷助;愚则不克将社务办理得当,盖欲社务办理得当,最低限度须能读能写”,故“惟有稳固有力之政府出而厘定合作政策,予农民以教育上及金融上之协助,合作运动始能得以促进。”他反对合作社发展过速,认为当时中国合作事业中的许多困难皆因政府“促进太速”,“政府此种欲求速效之政策实为目下合作事业失败之主因。”(19)反之,这也并非说主张合作政策者就完全不顾及合作事业之“质”。
三
从1933年到抗战爆发前,虽有许多人已意识到由于合作事业发展太速造成合作社“量”进“质”不进或“量”进“质”退局面,并感慨地说:“今日我国合作事业,在正面看,似有蓬勃兴起之象,但在背面看,确已危机四伏,稍一不慎,必致全部失败,为世诟病!”(20)但此后合作社发展速度并未因此放缓。抗战期间,尽管沦陷区合作事业基本陷于停顿,然大后方合作社却以更快速度发展。如贵州到1939年10月底,登记的合作社已达6490社、社员245963人、社股251683股、股金517332元,合作社社员数已占全省总人口2%强(21)。1937年,全国有合作社46983社、社员数2139634人,而到1945年年底达民国时期最高峰,即社数172053社、社员17231640人(内战期间合作社发展基本停滞,合作社数大致维持在16万左右)。八年间,全国合作社增加125070社,平均每年增加15634社,与战前发展最速的1934、1935、1936年相比(1933年底为6632社,1936年底为37318社,三年共增30686社,平均每年增加10229社)平均每年多增5405社。同期社员人数从2139634人增至17231640人,共增15092006人,增加七倍多(22)。
抗战期间,全国合作社特别是大后方合作社高速增长,其主因在于国民政府强力推动。或者说,这一时期中国合作事业作为“合作政策”的特点越发凸显,即国民政府在战前基础上就合作立法、合作行政、合作金融与合作教育等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在合作行政与指导方面,1938年1月国民政府在紧缩战时行政机构时将实业部改归经济部,原隶属于实业部的合作司撤销,合作行政归经济部农林司第五科主管。随着后方合作事业迅速发展,1939年经济部设立合作事业管理局(后改归社会部)负责统筹全国合作事业。随后,各省设立合作事业管理处,各县普遍设立合作事业指导室。这样,从上至下的全国合作行政系统基本形成。在合作立法方面,1940年8月为配合新县制的推行,国民政府颁布由合作事业管理局所拟具的《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规定组织保、乡镇合作社及其县合作社联合,先从乡镇合作社入手,然后及于各保。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并严格限制合作社解散和社员出社。如,第七条规定:“保合作社非因左列各款情事之一,不得解散:一、与他社合并。二、破产。三、解散之命令。”第十四条规定:“社员非依第七条规定之解散时,不得出社。”1945年6月,社会部修正公布《合作法施行细则》。在合作金融方面,其中一项重大举措是1939年成立四联总处(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该处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充当着“银行之银行”和统筹全国“金融总枢机构”的角色(23)。其设立标志着以国家行局为主要支柱的合作金库得以广泛建立,对于改变战前各银行杂投的混乱局面以及日后中央合作金库的组建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确立了国家行局在农贷中的主导地位。在合作教育方面,上到中央的合作事业管理局下到各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及各县的合作行政指导机关,都设有合作训练机构,而且教育形式多样。以贵州为例,大约到1939年年底计举办特别见习班(以加深指导人员的研究)人员300人,举办合作讲习会训练合作社职员7000余人,办合作函授学校(招生对象为各级合作社职员社员及有志于合作事业的人士)招生170余人,办合作巡回书库110库(24)。
上述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合作社数量的发展。但是,作为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典型举措则当属1940年8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由于乡镇保合作社及县联社是靠行政力量强制推动,因而发展速度很快。从1942年开始,每年以2万左右的速度递增,抗战结束时已达7万多个(与此同时,一般类型的合作社也有显著增长,最高时曾达14万个),占同期全国各类合作社总数(17万多个)40%左右(25)。以江西为例,截至1948年底,加入乡镇合作社的社员有2372852户,而加入专营合作社的社员仅为608538户(若以每户4.5人计,加入两类合作社的社员总人数达1340万人,超过全省人口84%)(26)。可见,该大纲在合作社普及中所起的作用。
正是由于抗战期间合作事业带有浓烈的政治和强制色彩,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合作社和社员数迅速膨胀,另一方面也因违背社员自觉自愿和循序渐进的建社原则而使合作事业越来越背离本质。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间合作事业在“质”的某些方面的改善。首先,合作事业更趋系统化。从合作行政上中央、省、县各级机构的建立到合作组织上保、乡镇合作社及县联合社的组织,莫不如此。其次,合作金库广泛建立,合作人才进一步充实,合作事业的资金条件有所改善。此外,单位合作社的规模有所扩大,社股股金有所增加,生产、运销、消费、保险等非信用合作社的比例也有上升。同时,我们也承认社会力量仍在发挥作用。从中央到各省的政府合作机关往往由原社会团体或学术团体的合作专家担任,如合作专家寿勉成任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经济学家何廉担任农本局局长、合作专家于永滋一度在贵州省政府所设的合作委员会担任总干事。不过,从总体上看,合作事业某些“质”的改善不能改变合作事业偏离本质这一前提,社会力量发挥作用亦未超然于政府合作政策之外。国民政府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尽管强化其作为“合作政策”的特点具有客观原因并因之得到社会力量认同,但合作事业既已背离本质亦就失去了应有发展力。
综论之,1933-1937年间关于农村合作运动的讨论是在农村濒于崩溃的大背景之下针对当时合作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展开的,这场讨论本身是为了给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以图通过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而达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之目的。合作界人士就这一时期合作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各抒己见,这既是理论学术上的争鸣,同时亦是对农村合作实践的积极回应。当然,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或“现代化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在理论界的一种反映。对于这样的讨论,时人嘲讽为“合作者不合作”,“唱‘消费合作中心论’者与‘唱生产合作中心论’者、唱‘合作政策论者’与‘唱合作政治运动论’者,彼此俱充分表示其各有天地的样子。凡此种种俱可作……‘合作……不合作’之论证。”(27)所以,我们在肯定这种“不合作”状况是对合作化道路积极探索的同时,亦不能不承认时人嘲讽的某种合理性。此外,从1937年之后合作事业的发展走向看,出于抗战建国、经济统制、地方自治等需要,国民政府对合作事业的推动趋于强制化,亦即合作事业作为“合作政策”的特征更突显,甚至走向“异化”。其对于战前合作界讨论中的种种主张或采纳或置之一旁,应该说主要基于这一前提。而以国家行局为主要支撑的合作金融系统的逐步建立,兼具多种经济职能甚至政治职能的兼营合作社的优先发展,尤其大后方合作社数量的急速增长,均是国民政府推行“合作政策”的产物,同时亦是中国合作事业最终选择“合作政策”道路的不同侧面的表现。
收稿日期 2008-03-01
注释:
①章元善:《合作运动之现状及其与乡村建设之关系》,《大公报·乡村建设》1934年11月22日;吴华宝:《中国之农业合作》,《大公报·经济周刊》1936年4月22日。
②有关前三个问题的研究见2007年《安徽史学》(第4期)、2008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晋阳学刊》(即将发表)。
③王志莘:《合作运动与合作政策》,《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4月5日。
④章元善:《我的合作经验及感想》,《大公报·社会问题》1933年4月29日。
⑤⑨(12)张国维:《推进中国合作事业应走合作政策之路或合作运动之路?》,《大公报·经济周刊》1936年6月16日。
⑥李文伯:《县政实验县区合作事业之比较》,《大公报·经济周刊》1936年12月9日。
⑦林善浪:《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⑧闫应福、张贺敏:《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初探》,《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⑩王志莘:《合作运动与合作政策》,《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4月5日;张国维:《推进中国合作事业应走合作政策之路或合作运动之路?》,《大公报·经济周刊》1936年6月16日。
(11)寿勉成:《合作事业与计划经济》,《合作月刊》第5卷第1-2期合刊,1933年10月。
(13)(20)宋之英:《所望于全国合作讨论会者》(续),《大公报》1935年3月6日。
(14)张鸿钧:《印度合作给我们的启示》(续),《大公报·乡村建设》1935年2月3日。
(15)施克兰:《热带国家合作方法》,黄肇兴译述,《大公报·经济周刊》1936年6月3日。
(16)(18)章元善:《合作运动在现阶段需要的助力》,《大公报·乡村建设》1935年4月14日。
(17)《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章元善等之提案》,《大公报》1935年3月1日。
(19)方显廷:《中国之合作运动》(续),《大公报·经济周刊》1934年5月23日。
(21)(24)杨纪:《贵州视察记——西南建国巡礼》,《大公报》1940年1月11日。
(22)寿勉成、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史》,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第103页。
(23)黄立人:《四联总处的成立、改组和撤消》,《四联总处史料》(上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4页。
(25)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3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469页。
(26)《本省各县合作社统计表》(1948年5月底止),《江西合作通讯》第3卷第1期,江西省合作事业管理处1948年5月30日编印,第13-16页。
(27)《中国合作事业界之诸相(续)》,《大公报》1936年9月24日。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农业合作社论文; 大公报论文; 1930年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民合作社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