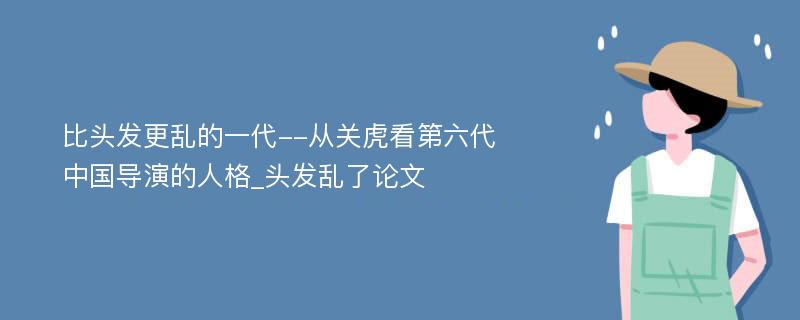
比头发还乱的一代——从管虎看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个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六代论文,导演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电影到底是否出现过“第六代”?何谓“第六代”?谁是“第六代”?这些可以说仍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尽管批评界一般把20世纪60年代出生,90年代初期开始电影创作的一批导演称为“第六代”,但这仍然是一个过于松散的定义。这些导演无论是从影片主题、美学风格还是文化立场都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如果硬要找出他们作品中的共同性,从而确立一个代系的共同特征的话,我们难免会陷入以偏概全的尴尬。踏入21世纪,中国电影学界又出现了“新生代”这个名词,主要用来描述大多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更年轻的一批电影工作者。就好像我们在历史命名上犯的幼稚错误还不够,仍不汲取滥用“新”、“现代”一类词语进行命名到后来所产生的混乱,忘记了时过境迁,“新浪潮”、“新时期”一类名词如今给人们带来的疑惑。
本文通过分析管虎1994导演完成的电影《头发乱了》,并通过与其同时同代的《北京杂种》(张元导演,1993)的文本比较,阐述当年以个性化为标榜的一代年轻人对于电影创作的一些独到尝试。落墨尽管只是一两部影片,本文的意旨却在于提出在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化的1990年代,用代系的观念分析中国电影发展已经不科学,“第六代”更只是一个符码价值远远大于内容涵义的“时髦”名词。当然,如果姑且用“第六代”这个不太科学的名词,在这个导演群中,1990年代初就在国际上稍有名气的屈指可数,张元和管虎却都各占一席。碰巧他们导演的成名作又都是反映都市摇滚歌手生活的,因此曾被广泛地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第六代”导演。尽管他们所代表的“第六代”从来没有在文化或艺术体制上成型过,他们确实应该算是20世纪90年代同龄导演中的佼佼者。有关张元1990年代的其他电影作品,林勇已在另文中作过讨论。[1]
二
管虎1969年生于北京,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2年他为自己的处女作《头发乱了》筹集到独立资金,并顺利地在政府建立的体制中独立完成影片。这部低成本的电影在1994年完成,并于同年在国内外发行放映。
《头发乱了》一方面较为自觉地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社会的蜕变,另一方面却又能不流于牢骚与反叛的悸动。影片中,女大学生叶彤从中国当年改革开放的门户广州回到故乡北京,在医院参加实习。然而,北京早已不是她记忆中的北京,和全国上下一样,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着巨变。她一直思念自己童年的伙伴,回来后却发现他们全都长大了。郑卫东当了警察,彭威成为摇滚歌手。彭威与郑卫东翻了脸,先是郑卫东不能理解和接受彭威使姑娘未婚先孕的“生活作风”,彭威也看不惯郑卫东刻板的行为准则,后来又由于郑卫东未能通融,致使他们另一位发小雷兵被关押,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叶彤尝试着让这两位昔日的朋友重修旧好,而她自己也被彭威的乐队所吸引,迷恋于摇滚乐中寻找黯然逝去的童年。她与乐队一起唱歌,并开始爱上了彭威。可是乐队在当地居民中并不讨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排练的破房子,却又因为成员间吵架意外失火。越狱的雷兵刺伤了郑卫东,在逃跑时又意外摔死。在意外发现彭威与另一女人同床之后,叶彤找到了郑卫东。在她的怂恿与协助下,受伤住院的郑卫东从医院里“逃”出来,在行将拆迁的叶家老宅与叶彤共赴巫山。对爱情和这座城市都感到失望的叶彤决定再一次离开故乡北京,并在临行前的露天校庆晚会上唱了一首摇滚歌曲。
作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拍片的年轻导演,出于突破“第五代”屏蔽的本能,管虎有意地与1984年—1987年间的经典第五代电影(如:《黄土地》,陈凯歌导演,1984;《猎场杂撒》,田壮壮导演,1985)背道而驰,在影片《头发乱了》中避免使用那些电影中常用的象征符号(尤其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仪式和色彩绚丽的视觉元素),削减了表现主义的痕迹,采用较为写实的手法表现他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而影片中较为传统的线性叙事、明晰的影像和流畅的节奏,恰恰也是突破了早期第五代和其他所谓“第六代”电影的生涩(或美名曰“前卫”)叙事新“传统”。
《头发乱了》的确是一部具有很强自觉意识的电影,它不仅如其他“第六代”的早期作品表达了青春期焦躁和迷惘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它企图从历史的视角给这种焦躁和迷惘找出原因以及解决的方式。影片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改革为中国带来了繁荣,带来了西方文化,也带来了商业化。剧变之后杂糅的语境令很多中国人感到不适,更令年轻人对历史、对社会有一种空前的疏离感。中年人和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的行为(尤其是彭威和叶彤都沉醉其中的摇滚乐),而年轻人则在摇滚乐中或如彭威那样逃避成长的现实,或像叶彤一般缅怀童年,追求当年未能完成的梦。影片中年轻人的迷惘和叛逆并不是完全缘于本能的青春冲动,而是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影片将近结尾处重复地使用了这样两组镜头的平行蒙太奇:一是郑卫东和叶彤做爱的场面,一是郑卫东怀孕的姐姐及前来看望她的郑卫东的朋友一起看电影。郑卫东的朋友为了给郑的姐姐解闷,带来了一些“史前”的电影胶片,在她家里架起了16毫米放映机。平房中墙上放映的是仅仅十多年前发生却又仿如隔世的历史:长安街两旁洒泪为周总理洒泪送葬的人群;逮捕“四人帮”后长安街上的庆祝游行。这些都是1976年的新闻纪录片片断,这些画面代表了这代人(影片中人物及导演)脑海中有关中国政治事件的最早记忆。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叶彤看着郑卫东姐姐的新生婴儿说:“萍姐,这孩子长大了,肯定不知道毛主席是谁了吧?!”成长于相对比较自由、现代化环境下的管虎,描绘了这样一代年轻人:他们不再为民族的、集体的方向而焦虑,而是为自己的前程、生活和爱情感到迷失。
管虎将历史的变迁、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融入个人的体验之中,既避免流于过度的个人感伤,又脱离了第五代宏大的集体叙事模式。影片结尾虽然没有给这种矛盾一个积极的解决方式,然而这个无奈的结局仍然表现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女主角终于跨出了焦虑的青春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步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人生阶段。而这种人生的成长过程也似乎暗示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这次悸动终将面对的一个结局。
很多自觉意识强的西方电影工作者都曾在其影片中表现过传统和后现代特性之间产生的冲突及后现代焦虑,《头发乱了》也触及到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是,影片主要还是从传统意识出发,表述社会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间的冲突,以及传统最终如何适应新型社会的过程,而非着眼于后现代社会中特有的一些矛盾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影片与侯孝贤早期的几部影片(如:《风柜来的人》,1983;《恋恋风尘》,1987)有着异曲同工之效。虽然发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头发乱了》和侯孝贤早期作品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它们表现的都是关于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改变对于个体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成长的历史性影响。所不同的是,侯孝贤的影片更着重于描述都市化过程给农村青年(尤其是外出到城市工作的一群)带来的冲击;而管虎的这部影片则是描述了都市内青年在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中的成长过程。
三
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某种原因,同为“第六代”代表人物张元的成名作《北京杂种》所表现的题材与《头发乱了》十分类似:摇滚乐队、青春的躁动与迷惘、青年对传统桎梏的不满以及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追求。然而,我们看到这两位导演无论是在影像语言的处理上还是对题材的诠释上都大相径庭。如前文所述,相对于《头发乱了》中较为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北京杂种》的影像语言中则充斥了大量形式断裂、直接电影(如乐队排练和表演的纪录片段)、非常规机位等一系列手法,这些手法本是西方电影在二战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前卫”风潮,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第六代”导演艺术理念成形期接触较多并备受垂青的一些欧洲电影流派。另外,两部影片中也将类似题材放置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一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头发乱了”),一个是无专指的时空(《北京杂种》)。管虎在影片中明确地表现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一特殊的历史变迁过程,以及各类人物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所感受到的不适和焦虑。而在《北京杂种》中我们却找不出有关历史背景的明确描述,影片中摇滚青年的躁动和反叛是出于青年一种本能对于社会传统约束的叛逆,既不是与中国某个历史时期有着明确的关联,更不必与某个历史时期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这个故事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有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年代的青春叛逆故事。
而这两部影片的另一个共同瞩目之处,就是它们都是以独立资金制作完成,这在中国是脱离固有经济文化体制的一种全新尝试。类似的题材、同样的制作方式,却由于是否挂上国营制片厂的厂标而使得这两部影片无论是在国内的发行还是在国际的影响都大不相同,也使得这两位导演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艺术创作道路。《头发乱了》虽然在当时获得公映,取得的商业成绩却并不算大,影片在海内外评论界所获关注也有限。相反,没有获得公映权的《北京杂种》却得到了国内外影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并获得了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特设评委会奖(1993)和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1994),“成就”辉煌。其后这两位导演的发展也成为一个更值得关注与分析的事实:张元虽然在当时受到了电影管理局的“禁拍令”,即禁止所有国营制片厂与其合作拍片,其新作却在国外资金的赞助或投资下一部接一部顺顺当当地完成,其本人也以中国“独立电影人”的身份享誉海内外。1999年更是凭借自己在海内外的影响,用一部《过年回家》,以一种“地下导演”走出地面的特殊身份,在电影管理局的鼓掌欢迎下,在海内外影评界和观众的高度关注下,高姿态地进入了体制内的制作。而老老实实走电影审查路线的管虎却并没有因为他的中规中矩获得任何好处,在《头发乱了》之后即转入电视剧创作长达十余年。一个颇有才华的年轻电影导演,在其处女作获得公映之后却黯然离开大银幕,个中缘由笔者虽然无法细知,其中的无奈却并非难以猜测和感受。
然而在对这两部影片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同属独立制作的《头发乱了》,《北京杂种》表现的内容并没有更为激进或是对政府的过去与现在更具批判性。影片《北京杂种》淡化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影片中对传统和政治制约不满的叛逆青年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存在的(不同的只是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而《头发乱了》中却明确标明了故事发生的年代,并表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政治经济变革给人们,尤其是给青年人带来的影响。可以说,《头发乱了》中的政治性批判比《北京杂种》更为直接和明确,也更为敏感。然而《头发乱了》却没有遇到任何审批发行上的麻烦。可以假设,如果张元的电影按部就班地采取政府(不成文规定中)要求的所有步骤,也未必会在审查中遇到什么麻烦。① 那么当时张元不挂中国国营制片厂厂标,不送审,无视中国政府的反对,以独立电影身份将《北京杂种》送往香港国际电影节参展,到底是无奈之举还是一种政治姿态就很值得商榷了。香港电影评论家登徒就曾经说过:“《北京杂种》可算是今年国际电影节(香港,1993)的瞩目影片,不在于其电影成就,而是与之牵引而来的一连串列政治事件。”[2] 说是政治事件,或者言之过重,这些在影片的发行、放映以及国际电影节参展一系列过程中表现出的与政府的不合作、不妥协,充其量是一种政治姿态。然而,正是这些“政治化”事件,更精确地说是政治化的发行过程(即不待申请审批,私自将影片出口参展),使张元之后拍摄的几部影片,都倍受国内外影坛的关注,并最终功成名就地进入体制内制作。从此,“独立”、“地下”、“被禁”常常成了中国所谓“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代名词,也成了海外媒体以及国内非正式碟片发行市场在宣传“第六代”作品时惯用的“品牌”。相比之下,没有“遭到”被禁的《头发乱了》,倒反而少了这一层层的“政治”光环作为卖点。这两位同因年龄、电影题材而被视为“第六代”的年轻导演,也由于其发行策略,或曰政治策略的不同,受到了不同的关注与对待,有着如此不同的命运。
四
通过管虎的《头发乱了》,尤其是通过这部影片和张元《北京杂种》的比较,我们发现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成长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所谓“第六代”电影工作者的生活环境再不像第三、第四、第五代电影工作者那样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给年轻的影人更为个性化的生活体验和创作空间,杂糅的文化语境也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发展方向。因此,再一次产生如第三、第四、第五代导演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已经不再具备,用代系来分析中国电影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概述性的方法,当中本来就存在着不少以偏概全的弊病。而这样的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就更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第六代”这个名词还是出现了,而它的出现则是中国电影理论界、中国青年电影工作者、中国电影业界以及国内外观众多方“合谋”而成的。
首先,中国电影理论界和评论界目睹了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就,对于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种想当然的代系期盼。同时,以群体的状态形成“势大力勃”的阵势面对外部世界(国际影坛)也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在第五代的神话逐渐没落之后,还没有习惯于个性化的影评界,仍然期待着中国电影创作以一个“集体”的姿态出现,而没有意识到随着第五代集体寓言的终结,中国电影创作的集体时代也随之结束。
其次,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一面本能地企图突破前一代影人,一面又期待着一个与前辈类似的命名确认他们的身份。因此无论“第六代”这个名称合理与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他们与第三、第四、第五代导演相仿的地位。同时,张扬个性化的他们也渴望仍然着“代群”所带来的“人多势众”的强势力量。更重要的是,“第六代”这个名词作为一个商标,使他们在国内外影坛不断地名利双收。因此他们一面反对“第六代”这个名称消解了他们的个性化,一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享受着代群命名所带来的一切利益。
最后,对中国的电影业界、发行商和国内外广大观众而言,“第x 代”已经成为了一种公认的品牌标志。从电影发行商的角度来说,对于新进导演的群体化命名绝对有利于对这些中国导演的作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进行概念化的推广,是一种通过舆论,而非通过产品本身打造品牌的宣传手段。所以如果能把年轻导演塑造成为所谓的“第六代”的话,它们本身就有了品牌效应。而从电影观众的角度来说,品牌是后现代消费模式中最为重要的元素,远远超出消费品本身的价值,他们(尤其是国际观众)也需要“第六代”这个标签作为他们消费中国电影的指引。
在近期的一次专访中张元这样说:“我记得在我们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不管以后拍不拍电影都盖上了‘第六代’的帽子,那个时候我们在电影学院都还没有毕业。”[3] 为一个无中生有的群体命名,或者说对一些本无代系特征的影片作概念化的归类,也正符合后现代社会中商品宣传最常见的一种手法。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德(Jean Baudrillard)说过:
一件物品要成为消费品,首先要成为一个符码。也就是说,物品本身要抽离其所代表的所指,这个所指与该物品的真正关系变成了随意的、不一致的。而要达到一致性,最后产生意义,则靠着个别符码与所有其他符码既抽象而又有系统的关系。[4](P22)
为了使这一批年轻导演的作品最终投入市场,早在他们还没有毕业甚至还没有作品的时候,人们已经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标注了符码。这个符码——第六代——既是随意性的,因为人们还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否会有代系特征;也是通过与其他符码,如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抽象而又有系统的关系”产生意义。鲍德里亚德还说:
当今的抽象化不再是一张地图,一个仿制品,一面镜子,或是一个概念。摹仿已不再以一幅土地,一个参照物,一件实体作为蓝本。抽象化是在没有原物或实体的环境下对真实的塑造:是超越真实。[4](P166)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尚未形成的(甚至永远没有可能形成的)代系的全景描绘(cognitive mapping,也就是上面引文中所指的没有土地作为蓝本的地图)又使得这个后现代符码具有了比真实更真实的真实性(hyperreal)。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五代的影片是一种有关中华民族整体的寓言,张元的《北京杂种》是现当代社会(地区不局限于中国)上一个特定团体(一群失落的摇滚乐手)的寓言,而管虎的《头发乱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寓言,其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适应社会新环境的一群青年。但是,《头发乱了》追求的却不是一个集体的寓言,影片结束时不同人物由于不同的人生观、生活方式、个性与态度,结局也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社会已经再也没有一个把全民塑造成为一种理想模式的条件与机制了,我们从《头发乱了》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多元化的新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电影工作者也无可避免地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产生一个具有共同经历、共同目标、共同题材的新的电影代系的社会条件早已荡然无存。所谓的“第六代”导演本身就是一群从人生阅历、艺术风格到作品题材、理想追求都各自不同千奇百怪,根本无法归纳入某个“群体”的年轻人。《头发乱了》也在这个层面上成了“第六代”根本不可能产生的一个寓言。无论是对于“第六代”定义的标准,还是它所代表的这一群中国导演,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乱”。
注释:
① 张元1999年导演的《过年回家》便顺利通过审查在国内外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