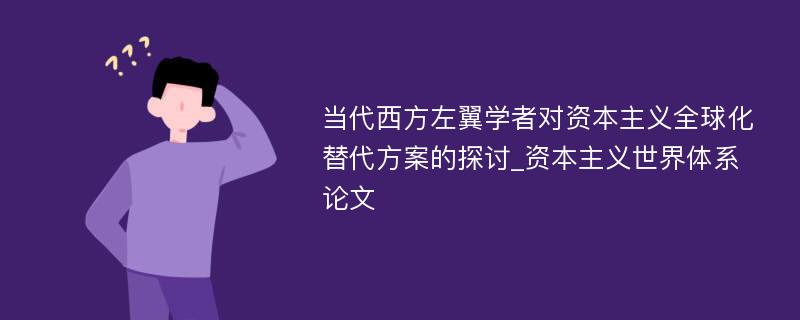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替代方案的探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学者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 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以及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扩张,然而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持续的繁荣和发展,反而导致了世界的动荡、冲突、危机不断出现。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弊端和缺陷更加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问题何在?有没有一种新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建构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全球化理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诊断和批判,并寻求和探索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一种新的全球化方案。 这一阵营可以说代表人物很多,如果从理论的深度和思想的影响力两个维度去衡量的话,无疑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哈维(David Harvey)、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罗宾逊(William I.Robinson)、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等几位学者是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西方左翼全球化理论各异,但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和对未来理想社会执着追求的精神,并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了拓展,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本文以这几位学者的理论为范本,重点分析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替代方案的探寻,最后对这些思想的意义和局限进行剖析。 一、沃勒斯坦:“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世界体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作为当代著名的左翼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就提出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不断发表文章进一步阐释和拓展自己的思想,并不断探索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道路。他虽然很少使用全球化概念,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就是全球化思想的一种表达。 在他看来,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一种现代世界体系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在西欧形成,并最后扩张到整个世界。世界体系在开始时虽然是世界性的,却并没有把全球所有地区都纳入它的结构,后来它不断地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在19世纪下半叶最终扩展到整个世界,成为目前地球上唯一的历史体系,“在今天,我们拥有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覆盖了全球,除了它以外不存在其他体系。这是一种新形势。”①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单一的劳动分工基础上一体化的不平等的经济网络,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是由“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部分所构成的结构。现代世界体系由资本主义驱动,它的基本逻辑是积累的剩余价值被不平等分配。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作过程中有两种基本矛盾: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基于资本的无限积累之上的体系,必然无法摆脱最大限度获取利润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两极分化,必然激发阶级斗争和不同国家冲突,所以它也无法消除反对者和反抗运动。正是这两种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而且不断产生危机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将会因其自身矛盾的积累而崩溃。当前这一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中,而结构性危机是一种体系的根本性危机,最主要特征是失序,这种危机往往意味着这一体系即将终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且会一直持续到大约2050年前后。“1997年亚洲债务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现代世界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延续的债务危机所导致的持续且远未终结的经济泡沫”。②这一体系在未来20年或30年后将会消失,并且被另一种世界体系完全取代。 既然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陷入结构性危机中,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就不是是否保留现行体系的问题,而是有关何种类型的世界体系将取代现行体系的问题。究竟何种体系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认为具有不确定性,存在多种可能性。究竟哪种可能性会实现,则取决于人们的努力、斗争和选择。在早期,他更强调“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近年来则回避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提出应该建构一种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世界体系。认为,“在历史上尚未出现过任何意义上的民主或平等的世界体系,一个拥有这些特征的体系将截然不同于此前历史上所有的世界体系”。③在沃勒斯坦那里,所谓民主是指“大众统治”,而大众并非其中特定集团,它应该包括每一个人;所谓平等则包括教育、医疗服务、终生的体面收入水平等各方面的平等。 那么,目前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他认为,除了上面的长期规划外,区分出短期策略和中期策略是十分必要的。短期策略即三到五年的选择,就是要防止事情变得更糟,短期在没有其他可行选择时,我们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切合大多数群众需要和期望的更轻的恶,包括投票、罢工、示威游行和武装斗争,等等。中期则尽可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建设一个更好的民主和平等的世界体系,具体包括:第一是要对严谨的理性分析和讨论给予足够重视,这不仅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还要在世界上所有人群中进行;第二是最大限度地以去商品化来代替以全球经济增长为目标;第三是努力增强各地和各区域自给自足能力,特别是在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住所等方面;第四是我们必须立即进行终结外国军事基地存在的斗争;第五是大力推动终结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宗教、性行为以及其他社会不平等现象。④ 二、哈维:“另一个共产主义是可能的” 大卫·哈维作为当代地理学马克思主义代表,对马克思思想的重视是人所共知的,他挖掘并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建构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他是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或不平衡地理发展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并由此出发去寻求替代方案的。 哈维认为,作为过程的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内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1492年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系统与生俱来的趋向。在他看来,“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之源”⑤,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而资本积累离不开不断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扩张。如果没有自己的“空间定位”,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它正是通过不断的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其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由此按照自己的面貌建立和重建地理”⑥,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空间扩张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命,当代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⑦。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上是通过空间生产和地理扩张把世界上每个人以及每样可以交换的东西拖入了资本的轨道,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包括不平衡地理发展状况的加速,收入和财富的贫富分化,几乎失去控制的环境问题,公益事业的瓦解,政治法律机构、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摧毁,而且这些问题在全球不同层次、不同地点、不同空间规模都在发生着。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一直存在着资本积累的潜在无限性和生产的潜在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一旦受到自然、市场有效需求、技术、地缘政治、反对力量等限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不断处于危机和解决危机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受阻所产生的一次比较严重的危机。以前靠不断扩展空间即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和统治来克服危机,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扩展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了吸收剩余资本的空间。由此,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了。 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机和困境,哈维认为,没有有效的长期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可能恰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一个拐点。与此同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实践的不均衡发展已经引起了各地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虽然还没有形成坚决的、足够统一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可以对资产阶级的再生产及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力量过程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和挑战,“但我们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是,不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实现的,……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另一个共产主义也是可能实现的。”⑧ 哈维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寻,在2002年《希望的空间》一书中就提出了建构一种辩证乌托邦的设想,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具体化。那么,在哈维那里,所谓的“另一个共产主义”主要是指怎样的社会呢?他认为,这是一个对自然和人类负责的社会,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组织生产、分配、控制过剩产品的社会,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夺和实现世界平衡的社会,具体包括:“尊重自然,社会关系上的彻底平等,基于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民主管理程序,直接的生产者组织劳动生产,将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关系和生活新方式的自由探索,专注于服务他人的自我实现心态,以及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技术和组织创新。”⑨哈维还指出,这当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我们不能不如此。 为了实现这一“乌托邦”,具体途径是什么?哈维认为,全世界无产者必须打破地方性局限而团结起来,对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任何运动而言,工人运动的各种斗争力量和那些被剥夺了文化、政治、经济资产的人结成同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他认为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只有通过斗争即直接对阶级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攻击,甚至不排除暴力斗争,这一理想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在2011年发生在美国等地的“占领运动”中,他到占领运动现场发表演讲为抗议者鼓劲,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斯克莱尔:“社会主义全球化” 莱斯利·斯克莱尔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全球体系理论,阐述他对全球化问题的看法,近年来则一直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并把关注重点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替代问题的探讨。 与沃勒斯坦和哈维把全球化看成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倾向不同,斯克莱尔认为,资本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之后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性质上全新的全球化阶段,即由国家间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跨国实践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逐渐形成、发展并成了支配性的全球体系,这一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当今世界变化的最大力量。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是建立在跨国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跨国公司是跨国经济实践的主要场所,而以跨国公司为物质基础的跨国资本家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跨国性的各种政治组织来进行政治上的跨国实践,与此同时,资本家阶层及其代理机构为了操纵消费需要并创造消费需求,宣扬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以为其资本积累提供文化上的支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力图控制全球资本和物质资源,跨国资本阶层力图控制全球权力,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跨国性行动主体和机构力图控制思想领域”⑩。 在斯克莱尔看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和深化,其问题和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两方面危机:一是世界性的阶级两极分化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很富和很穷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种两极分化表现在财富、教育、基础设施、其他服务、居住条件以及信息的拥有等多方面,这种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是否占有经济资源,所以这是一种阶级危机;二是生态不可持续的危机,全球层面的生态正处于紧张状态,全球环境灾难正在形成,虽然人们对此有所认识并行动,但很多人却忽视了这种整体性生态危机实际上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既然资本主义全球化面临的这两个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它不仅无法解决这两个危机,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从两个方面看正在走向失败”(11)。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斯克莱尔在总结近些年出现的各种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经验和局限基础上,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案即“社会主义全球化”,并且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这种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斯克莱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中的跨国社会主义全球化实践体系,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的社会中,经济上的跨国实践的特有制度形式是各种类型的生产-消费合作社,而不是寻求组成卡特尔的跨国性大集团企业;政治方面的跨国实践的特有制度形式,将是自己管治自己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社区,在真正民主决策的基础上纳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单元;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全球化特有的文化-意识形态跨国实践,将为广泛多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和价值提供空间,这些实践和价值积极鼓励普遍人权和生态可持续性。(12)社会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有着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为资本家阶层赚取利润,而社会主义全球化则根据生产者、消费者和环境的利益来运作,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全球化完全可以克服两极分化和生态不可持续的危机。 那么究竟如何从资本主义全球化走向社会主义全球化?斯克莱尔指出,人权的全球化是从资本主义全球化过渡到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关键环节。所谓人权的全球化也就是要在全球所有民族的人民中实现普遍的人权,这种普遍人权包括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到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所有权利,“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刻挑战”(13)。同时,在社会主义全球化实现方式上,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不能通过革命手段夺取国家权力,而只能靠成功的社会实验来实现。 四、罗宾逊:“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 威廉·I.罗宾逊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位左翼学者,他坚持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来分析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并根据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条件探讨了未来社会的前景。 在他看来,全球化本质上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扩散的顶峰,其特点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了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把从15世纪末产生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区分为四个阶段,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四阶段资本主义才进入了全球化阶段。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跨国的或全球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世界资本主义正在从各自拥有不同的体制、组织、政治和管理结构的民族国家阶段向跨国家阶段或全球阶段过渡,而且,“这一仍在形成的资本主义跨国家阶段是在质上崭新的阶段。”(14)跨国资本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而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活动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流动和生产全球化改变了阶级关系,使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成为新的世界性统治阶级,跨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创造出了一种包括经过变革的民族国家以及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等新的跨国国家机构,这种跨国资本家集团以及跨国国家成了当代世界新的统治力量。同时,以市场意识形态、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竞争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日益占据统治地位或者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霸权。 罗宾逊认为,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孕育了技术的动力机制,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剥削关系之上的,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固有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而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阶段所面临的危机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球的过度生产或需求不足即积累过剩;二是全球社会的两极分化;三是国家合法性和政治权威面临的危机;四是可持续发展危机。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些问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正面临一场空前规模的全球危机,我们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在我看来,全球资本主义与‘人类的面孔’实际上是相冲突的。”(15) 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存在的种种危机以及为人类社会带来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贫穷乃至生态灭绝,罗宾逊进一步指出,在当代逆转全球化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改变目前的发展进程,把资本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变成自下而上的、完全民主的全球化。从20世纪末期开始,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已经出现了各种反抗力量,显然反对霸权、追求全球公正的运动已是大势所趋。但要建立一个对立性的霸权,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提出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可行性方案。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一个权力不再通过民族国家来调节和组织的时期,如何才能重新构建全球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因此“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许是人类社会‘最终、最好’而且也许是唯一的希望”,(16)反对跨国资本家的全球反霸权斗争必须变成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全球性斗争。人类社会的希望存在于跨国社会对全球生产与再生产的统治方式中,即为弱势大众群体实现财富和权力再分配。这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发展道路——国际社会为跨国资本带来无穷利润的组织形式,最终必须被另一条发展道路取而代之,这是满足人类需求、符合劳苦大众利益的道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统治权力比以前更加分散和多元化,并已经渗入世界的每个地方和社会的每个领域,因此罗宾逊指出,要实现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就必须通过跨国、跨地区联合各种反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来挑战统治集团的权力,把本土变革和全球变革结合起来。要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只能夺取跨国资本及其机构对人类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源的控制权,所以政治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五、奈格里和哈特:“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方案” 安东尼奥·奈格里和麦克尔·哈特两位学者在2000年提出了帝国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奠定了他们激进左派学者的地位,近年来又出版了《多众》(2004)和《联邦》(2009)等著作,并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断发表文章,进一步表达和拓展其思想。 他们虽然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但认为这种新政治秩序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基础之上的。他们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已经结束,而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向信息化经济的后现代化转型。当今的信息化经济标志着人类活动的一种新模式。这一生产方式是以知识、信息、情感和交际的生产为主,这种劳动是一种非物质劳动。这种信息化经济的地理后果是生产的一种戏剧性的非中心化、网络化和非地域化。所以,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全球化阶段。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全球化时代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即“帝国”开始成型,“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17)这一替代了民族国家主权的新形式,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并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帝国与过去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帝国主义不同,它不建立权力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而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全球领域的统治。帝国的这一网络结构完满地适应了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本生产循环的需要。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后现代转型和政治上帝国的出现,并没有消灭剥削、社会不平等和分化,而是在很多方面变得愈加严重,“现代性辩证法的终结并没有带来剥削辩证法的终结。今天,几乎人类的全部要么被吸纳入资本主义剥削之网,要么屈从于它。今天,越来越多的财富控制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民众依旧生活在贫困与无能为力的极限边缘,贫富分化越来越走向极端。那些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圈划好的、进行压迫和剥削的界限,在今天,在许多方面非但没有收缩,反而在爆炸性地膨胀。”(18)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和剥削已变得愈来愈复杂和破碎,它们贯穿了每个国家和地方的空间,而与等级和剥削的对抗在全球的生产网络中体现出来,并决定着各个节点上的危机,危机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后现代的整体共同扩张,这是帝国控制所独有的。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虽然作为新的经济方式的信息服务经济及其帝国的出现并没有摆脱剥削和压迫,但这却孕育着未来新社会的萌芽。非物质生产及其扩张使劳动越来越社会化,随着劳动者的共同基础不断建立,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日益趋同,结果是减弱了不同劳动者区分为不同阶级的基础,因此这使多众(multitude)作为一种政治主体的出现成为可能,这就为形成一个共同的替代全球资本主义方案创建了基础。这种替代方案是什么呢?2004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他们提出了一种“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认为这种新的政治方案在于在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基本目标是建立“全球民主”的新政治秩序,“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制定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那么,首要之处就在于在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而且,它是能将争取平等的斗争统合进来的。”(19)近年来,他们为了突出这种方案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又进一步把这种方案称为“共产主义的新方案”,并指出,“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建立一个消除资本剥削与屈从于国家的新世界”,(20)共产主义意味着把共有的东西还给社会大众,共产主义既不是公有,也不是私有,而是共有。所谓“共有”就是多众对公共产品的公共管理,本质特征是多众的解放和民主的真正实现。 怎样实施全球民主的共产主义或后社会主义战略?奈格里和哈特给出了三个具体的政治任务:一是争取全球公民权,即流动的大众通过重新夺取空间,将其自身组成一个积极的政治主体,使每个人在居住和工作的国家拥有完全的公民权;二是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即要求一种社会性的酬劳和所有人有保障的收入;三是再占有的权利,核心是再占有生产方式的权利即民众自我控制和自主的自我生产权利。当然,要达到这一点,离不开罢工、怠工、骚乱、起义等各种自发运动和有组织的革命等方式。 六、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替代方案”思想的意义和局限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左翼思潮在西方乃至世界范围的复兴,西方左翼学者的全球化理论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他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以及对替代方案的探寻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但也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尽管视角、观点存在一定差异,但我们看到,他们都表达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极度重视,基本上都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了政治经济维度的批判,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这对于身处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这些学者而言,无疑是难能可贵和值得称道的。与此同时,他们又结合当代社会历史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开拓,这些左翼学者的理论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预示着自20世纪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次重大转型,即从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政治经济的批判,从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无疑对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弊端、矛盾及其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这对于如何促进全球化朝着公正的、合理的方向发展,如何促进人类的解放和发展,如何构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 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虽然都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剥削、异化和支配形式进行了尖锐批判,提出了摆脱和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种方案,但在这些方案中难免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分,而且有的思想已经溢出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另外,他们虽然都力图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和孕育的可能性来规划替代方案,并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途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与争取“另一个世界”的现实政治仍然存在某些脱节之处。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但如果仅仅把这些左翼学者的努力看成“只是装出严肃的态度在理论上作秀而已”(21),我觉得是不公允的。 注释: ①Gregory P.:Williams,Interview with Immanuel Wallerstein:Retrospective on the Origins of World- Systems Analysis,Journal of World-System Research,Vol.19,2013,p.207. ②Immanuel Wallerstein,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World-System: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Monthly Review,Vol.62,2011,p.36. ③Immanuel Wallerstein,Remembering Andre Gunder Frank Whil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Monthly Review,Vol.60,2009,p.51. ④Immanuel Wallerstein,2011,pp.38-39. ⑤[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1页。 ⑥[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⑦同上。 ⑧[美]大卫·哈维,2011年,第219页。 ⑨同上,第222页。 ⑩[英]莱斯利·斯克莱尔:《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11)[英]莱斯利·斯克莱尔,2012年,第354页。 (12)同上,第358~361页。 (13)Leslie Sklair,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o Socialist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Democratic Socialism,Vol.1,2011,p.3. (14)[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5)William I.Robinson,Global Capitalism and its Anti-"Human Face",Globalization,Vol.10,2013,p.660,p.669. (16)[英]威廉·I.罗宾逊,2009年,第232页。 (17)[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1页。 (18)同上,第49页。 (19)[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天涯》2004年第5期。 (20)[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共产主义:概念和实践的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8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21)俞吾金:《西方左翼思想家并未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日。标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大卫·哈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