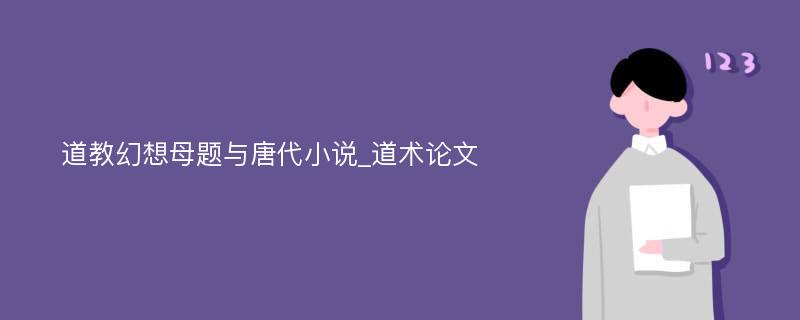
道教幻术母题与唐代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幻术论文,唐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8-8865(2000)03-0065-05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唐代小说是唐代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形象化反映,透视出唐代社会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唐代比较开放的政治思想统治,儒、释、道的三位一体,孕育衍生出奇光异彩的多元文化。明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序》云:“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籍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道教思想对唐代小说的影响毋庸置疑,唐代小说中表现出的博大玄妙的道家思想文化也应值得我们重视。本文拟就唐人小说中的道教幻术母题在唐代小说的表现作一番探讨,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社会,认识道教思想文化大有裨益。
一、道教幻术母题在唐代小说中的表现型式
唐代小说中,大凡得道之人都有一套奇异的道术,他们或床前犁地,或剪纸雕木,或投符念咒呼风唤雨,或虚设幻境役使鬼神,或隐身易形刀砍不死等等,不一而足。其主要表现型式如下:
1.开花结果术。薛渔思的《河东记》写板桥三娘子在箱中取木牛木人,耕床前一席地,让小木偶人种上荞麦,“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硙(磨)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箱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五代徐铉《稽神录》也称:“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世。其荚丰大,又异于常者。日获百钱,则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除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十数枚种之。少顷既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晓,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掇,伐其树,锉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杜光庭《续神仙传》写杭州监官人马自然,曾于宴席上施展其术,“以瓷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
2.剪纸雕木术(木鸟故事)。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天宝年间深于道术的孙甑生,“善辏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冯翊子《桂苑丛谈》写咸通初年颇有道术的进士张辞,能用纸“剪蛱蝶二三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用片楮也可“剪二鹤于厅前,以水骋之,俄而翔翥”。张鷟《朝野佥载》卷六云洛州县令殷文亮“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小木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同书又载:一个技巧的木匠杨条廉能“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柳祥《潇湘录·襄阳老叟》写老叟教授工匠唐并华制作木飞鹤的故事。并华得到老叟授予的斧后,“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爱上容色姝丽的王枚之女,就做成一双木飞鹤,夜间与之乘木鹤归襄阳。杜光庭《仙传拾遗》中的韩志和也“善雕木为鸾鹤鸟鹊之形,置机捩于腹中,发之则飞高三二百尺,数百步外方始却下”。其实这种道术,《列子·汤问》中就记载了一个惬师,也曾造过一个外貌跟真人一样但会千变万化的木人。晋人傅玄《马先生传》也记载有人造出会击鼓吹箫,会跳丸掷剑,会缘绠倒立的大木人。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志怪》也曾衍述《列子》的记载。这类型式的道术,严格说来算不上道术,只能反映能工巧匠们精湛的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表达了实现理想的愿望和要求。
3.投符念咒术。投符之术是道家最基本的法术之一,这一意象在唐代小说中是很普遍的。葛洪《抱朴子·退览》曾介绍过一种与剑术相联系的幻术,其中就谈到用符之事,“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成河,振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为也”。张读《宣室志》载程逸人会符术,萧季平无疾暴卒,程于是“朱书一符,向空掷之,仅食顷,季平果苏”。同书《骆玄素》载小吏骆玄素曾向一老翁学习符术,回家后,“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符”。康軿《剧谈录》写金陵人许元长、王琼“善出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同书还写张定“每见到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者,以手指之,皆能飞走歌舞,言笑趋动,与真无异”。《续神仙传》中的马自然会书符召鼠,令之出城。念咒也是道家惯用的手段,念咒可以治病,可以改变事物,如《酉阳杂俎·王先生》载,当里中火起烧到庐舍时,王先生“厉生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仙传拾遗》中的叶法善会投符让拦路石飞去。《续神仙传·马自然》写马自然能够“指溪水逆流食顷,指柳树令随溪水来去,指断桥令断复续”。当他南游越州洞岩禅院时,三百僧人傲不为礼,自然运用法术使之无法下床。
4.呼风唤雨,虚设幻境。唐人小说中的道术往往能呼风唤雨。戴孚《广异记》写一道士收下弟子辅神通后,“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可见该道士会避水法能够生活在水中。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道士欲度杜子春成仙,虚设恐怖幻境考验子春,在考验之前,道士告诫说:“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子春经受住各种恐怖惊吓,但当孩子被撞死时,子春“噫”了一声,终因“爱”心未忘而没入仙籍。段成式《酉阳杂俎·王先生》里的王先生也擅此术,能够在瞬间让门庭变成险峻的悬崖、重叠的山谷。《宣室志·周生》中周生的道术更让人惊奇,他能够在昏暗的虚室中用数百根筷子做成梯子到天上把月亮摘下来,当中秋之夜客人们在庭院中等着时,“忽觉天地嚷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口:‘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通肌骨。”皇甫氏《原化记》中的潘老人能够于空室中幻化出异常华盛的茵褥翠幕和丰盛的宴席,又能用拳头大的宝葫芦,把幻化出的“床席账幕,凡是用度,悉纳其中”。《仙传拾遗》写张定更是道高一丈,他能用一瓶水“置于庭中,禹步绕三二匝,乃倾于庭院内,见人无数,皆长六七寸,官僚将吏,士女看人,喧间满庭。即见无比设听戏场,局筵队伙,音乐百戏,楼阁车棚,无不精审。……至夕,复侧瓶于庭,人物车马,通澳俱入瓶内”,道术真可谓奇幻无比,小小的宝葫芦、水瓶竟有这么大的容量,这是唐代小说家们对于佛经故事母题的一个发展,这一主题意象以致成为后来《西游记》的主要情节之一。
5.隐身易形术。隐身易形是道家奇术的主要手段,专业道士们的隐身易形术更是老道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或隐身、或变形、或分身、或分解肢体然后聚合为人,打不痛杀不死。张荐《灵怪集》写鄂州关司法的佣人钮婆,带有一孙名万儿,同主人的小男封六年龄相仿,常在一起玩耍。“每封六制新衣,必易其故者与万儿。一旦,钮婆忽怒曰:‘皆是小儿,何贵何贱?而彼衣皆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关妻责怪钮婆不知贵贱有别之理,于是钮婆即施展法术:“遂引封六及孙,悉纳于裙下,著地技之。关妻惊起夺之,两手悉为钮婆之孙,形状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技之,即各复本矣。……”后来当关司法夫妇时,钮婆早变作关司法到观察使那儿了,关回到家,堂前也有一关司法先回来了,关妻也难以辨认。薛渔思《河东记》中的板桥三娘子做的烧饼让客人们吃了结果变成驴。叶静能因事得罪玄宗,被斩首,天宝末年玄宗幸蜀时却又遇见他。叶法善会用巨橡化作麦处主。张定能“自以刀剑剪手足,创剔五脏,分挂四壁,良久,自复其身。晏然无苦”。皇甫枚《三水小牍》写樵夫侯元家道贫寒,遇到神君相助,教给他变化隐显之术,可以变化百物,驱使鬼魅,草木土石,都可以被他变成武器、士兵。同书还写温璋因一老者挡住了去路,惩罚老者二十大棍,老者却无痛苦状。温璋派人跟踪,原来老者正是庙中神仙所变。
6.役使鬼神术。李枚《纂异记·陈季卿》中的终南山翁能以竹叶作舟,放在图中的渭水上面,一夜之间送其回家,又回到青龙寺。《酉阳杂俎》前集卷五“云安井”条,写长江支流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翟乾佑乃施展法术如群龙,“一夕之间,风雪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张读《宣室志》写杨居士有奇术,因得罪太守,乃作法让众妓“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追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续神仙传》中的马自然能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掷之皆青铜钱,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人有收取,顷之复失”。
此外还有炼丹术、摄魂术等,也有施假道术的江湖骗子,难于一一类分。业浅的小道只会雕虫小技,艺深的老道往往数艺压身,显示出变幻难测的本领。小说也揭露了一些利用幻术行骗自食其果的术士,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当然,上述类分不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仅举其荦荦大者,实际上道教的玄妙幻术还远远不止于此。
二、道家与道教传统对唐代小说作者的浸染
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外来文化的加盟,使唐代小说中的奇术更为绚丽多彩。《庄子·逍遥游》中即有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形象描绘,秦汉时代,长生不死升天成仙的信奉大为倡扬,秦皇汉武的求仙访道声势浩大,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游仙主题[1],历久传扬。封建帝王的崇拜道教,更激起了士子文人们的浓厚兴趣,于是他们在作意好奇的心理驱使下,无意识地融进了道家的思想文化,致使唐代小说中的道家思想尤其是令人企羡的道家奇术蔚为壮观,成为一道亮丽的主题风景。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早在秦汉时代,有关神仙方术的思想就已相当发达。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丰富及佛教的广为散播,佛道互相渗透,到唐代,作家们所承受的多元文化的影响就更为丰富复杂了。他们从历史文化积淀的母体中又培育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主题。
道家幻术这一主题意象系统,源自汉魏六朝,如西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中,就曾对道家的奇术作过一番精彩的描述:“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彩……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百兵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其后历经时代风云的洗礼,不断进行着嬗变。而在以道教为国教的唐代,对于道教的尊崇是前所未有的。《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载乾封元年(666),(高宗)“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李耳)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本纪又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大大促进了道家思想的传播。据《唐会要》“缘祀裁制”条记载,唐代每年有80多次的朝廷祭祀。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每岁有可行祀典者,不可胜记,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小说中表现的屡见不鲜,也就并非突兀。
唐代小说的作者们生活在道教盛行的社会环境里,无疑会受到道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因为唐代社会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平民,对道家思想无不尊崇备至顶礼膜拜。小说作者有的和道士是亲朋好友,有的本身就是道士(如杜光庭)而有的则喜欢神仙怪异之事。也正由于多种思想并存,彼此并行不悖,唐代小说家们的思维想象空间比较广阔,从道释两家思想体系中吸收了许多可供想象生发的因子,再加上民间文学的滋养,激发出不少蔑视庄严正统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传统的异端之说,显示了自由纵放的艺术精神和生机勃勃的审美创造力。
三、唐代小说中幻术母题的制度与社会环境成因
唐代的社会思潮影响是幻术母题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唐代社会,“封建礼教的束缚相对松弛和人的主观精神的昂扬奋发,它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的价值,强调个性的自由,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2]这是中肯而令人信服的,对于道教幻术母题也是如此。
唐代的士子们要参加“明经”(玄学)考试,对道家的教义可谓了如指掌,有的作家喜记神仙怪异之事(如裴铏),有的作家身为道士(如杜光庭)。道家主张炼丹服药、成仙升天的神秘教义也使一批作家心向往之。唐代知识分子们的思维想象空间比较开阔自由,他们创造出一大批饱含神秘宗教色彩的道术,创造出许多非人间的世外桃源,充分显示出他们“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的无畏精神和创造力。
其次,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解放的重要时期。儒道释三教并存,彼此虽相互斗争、又相互渗透而呈现合流的趋势。以原始巫术为基础,又吸收佛教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道教,经统治者大力倡导,在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崇道氛围。而较为宽松的思想统治,给士子文人们提供了大胆驰骋想象的良好社会环境;而良好的创作环境,有利于幻术思维不受羁绊地大规模展开。
其三,从文学与艺术互动整合的层面上看,在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的道术描写中,也展示出唐代社会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多元艺术互动的文化氛围。从开花结果、剪纸雕木的道术表演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代杂技表演艺术的高度繁荣,手工艺人那精湛娴熟的剪纸雕刻技巧,街头卖艺人那“开花结果”式的魔术杂耍表演,吞云吐雾、吞剑吐刀的杂技表演,而且,在作家们的幻想演绎下,竟成为带有神秘道教色彩的道术。李冗《独异志》有一条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揭开道术神秘的面纱: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乐都大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冥。”于是“脱去缞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栗”。可见,这类颇似人类学仪式中“展演”的综合性艺术活动,有着丰富的民俗内蕴,对于文学中相关描写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四、唐代小说道术描写折射出外域宗教文化内涵
唐代小说所描写的种种道术,从宗教哲学的层面看,带有神秘化的宗教特征,道家所主张的炼丹服药、吸气吐纳等带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其贡献不容抹杀。但道家念咒投符、呼风唤雨、隐身易形、驱使鬼神等神秘法术显然和有“上帝”一样都是一种宗教信仰,它包含着人们对道术的非科学认识,反映了人们征服自然、超越自我的天真幻想和欲望渴求。
对于佛教相关观念故事的吸收,也是道教杂糅并包特色的一个突出的体现。曾几何时,佛教在刚刚进入中土时,是尽量吸纳中土文化因子,以期能够为中土文化所认同。但是后来兴起的道教,却有意识地吸收了佛教的营养,为我所用。像当初本是佛经故事的幻术,如宝葫芦,就为《原化记·潘老人》所采;《仙传拾遗·张宝》也为论者多认为出自东晋荀氏《灵鬼志·外国道人》,而事实上故事情节源自《旧杂譬喻经》里的梵志故事。其称某太子在山中见梵志作术先口吐一壶,壶里有一女,而女又作术吐一壶,壶里有一少男,遂与女卧……其间母题传承的轨迹是很明显的。
元魏时代的译经写,有个辟支佛入城乞食无所得,饥饿中遇见个卖柴人,后者把卖柴所得食品施给他吃,吃完,辟支佛飞腾到虚空。卖柴人道见一兔,他以杖撩之,兔变成了死人,起来抱住了他的脖子,推挽不脱,归家后这个死人自动堕于地下,变成了真的金人。卖柴人截其头,头生,截其手脚,手脚生,不多时屋里就堆了不少金头金手。但闻讯赶来的国王使者,看到的却是烂臭死人的头和手;其一到了卖柴人手里便又成了真金,国王认为这是个有福之人。[3]由兔变人,人又变金,故事还与“逐兔见宝”母题(注:关于“逐免见宝”母题,是一个由佛经到史传文学的幸运母题,专文另见。)相联系。
该故事的另一异文还说,阿泪吒入泽取薪,“到(道)见一兔,意欲捕取,走逐转近,以镰遥掷,即见堕地,适欲捕取,化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头,尽力推却,不能令却,……”担惊受怕回家后,变成了一具阎浮檀金。据说这种金明净柔软,令人喜爱。可是每当王派人来察看,就是死人,这样往返了七次,王亲自来看,也是死人,而且臭了。后来还是阿泪吒本人取了一小块奉王,并说明是由于施舍辟支佛的缘故,王才心悦诚服,慨叹着拜其为大臣。[4]
还有的译经说,佛与阿难在旷野中见一大毒蛇,一耕人听见消息后到近处一看,是一块真金,自言自语:“沙门所言毒蛇者,乃是好金。”就拿回家,发家致富了。国王奇怪,就把他捕系狱中,要加刑戮,这人说:“毒蛇阿难,恶毒蛇世尊。”王得悉后询问,这人说出原委,口诵一偈,称此时才悟解佛言,认识到:财宝真是使人心迷苦恼的毒蛇。[5]
显然,佛经故事为中土道教幻术,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跨文化参照系,从小说母题角度上说来,它简直是神变思维的源头活水,让幻想不够开展的华夏古人禁不住大开眼界,可以说直接地启发了道教法术思维向更大胆、更丰富的路径上渐次生发。
尤其是前所列举的“种植速长”的幻术,其实也并非唐人首创,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谈祝师幻术时称其“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十变五化。人力所为,尚能如此;何况神通感应,不可思量”。王利器先生集释引卢文昭曰:“《御览》载孔伟《七引》云:弄幻之术,因时而作,耕瓜种菜,立起寻尺,送芳送臭,卖黄售白。”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景乐寺》则记载:“寺中杂技,剥驴投井,掷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而班固《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早有:“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屿眩人献于汉”,唐人颜师古注曰:“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种瓜种树,屠人截马皆是也。本从西域为。”而实际上,像这类隐身易形之术,葛洪《抱朴子·对俗》中早将其划入道教神仙术的范围:“余数见人……隐形以沦于无象,易貌以成于异物,结巾投地而兔走,针缀丹带而蛇行,瓜果结实于须臾……而此术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也。”
其实,对于这一母题的渊源,清代学者也不是没有注意的。从母题史的角度,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八就指出:“《搜神记》载:‘吴时有徐光者,常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其所卖,皆亡耗也。’按蒲留仙《聊斋志异》,有术士赠桃事,即本此。乃知小说家,多依仿古事而为之也。”俞樾敏锐地注意到先在的小说母题模式对于后世小说家创作的功能,而此处所说的故事母题,的确见于干宝《搜神记》卷一。但是,我们却不能停留在此。
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将翻译文学也纳入考察范围之列,就能够取得前所罕有的发现。南朝萧齐时代外域僧人的译经,写菩提树的神变能力,其可以隐形,只留下一枝,使国王和众僧拜服,王还发誓将树送往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置于金盆,放在七宝师子座上,树才恢复原貌。菩提树还能“大枝长十肘,复有五枝,枝各长四肘,五枝各生一子,复有千小枝”,并且能在虚空中停留,为龙王拜为王,种种变化,令众人惊叹欣喜。“是时摩哂陀与僧枷蜜多王及国人民,来集于菩提树,时众人见北枝有一子而熟,即从枝堕落,以奉摩哂陀,摩哂陀以核与王令栽,王即受于金盆中,以肥土壅,又以涂香覆上,须臾之间即生八株,各长四肘。王见如此惊叹,以白伞覆上,拜小树为王。……以菩提树故,国土安然无有灾害。”[6]这不是直接启示了前揭开花结果术,即种植速长母题了吗?可惜前贤竟没有发现。
应当说,中古佛经传译,对于道家思想向道教衍化,乃至道教幻术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或离的作用。这里不可能全面总结,但由此一个母题的检索,可以略见一斑。
五、道教幻术母题对于后世的影响
当然,所谓道家的道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家有意渲染演绎的结果。对唐代小说中所描写的道术这一主题意象进行研究,对揭示唐代社会的文人心态,全面了解一代之奇的唐代小说,其积极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首先,唐代是我国小说文体独立的时代,许多幻术描写,尽管前代也有不少,但却是唐代小说家真正将其确立到小说文体中来,又是如此的丰富集中,多彩多姿,这不能不说会对于后世小说有相当大的影响。
其次,种种幻术描写,对于后世神魔小说以及历史演义小说中的神变斗法,产生了重要的楷模示范作用。尤其是对于道教小说如《封神演义》《西游记》《东度记》《女仙外史》等等,更提供了不少可资构思生发的艺术机杼。某种意义上,的确起到了补充华夏民族艺术想象力不足的缺失,其成为许多叙事作品最为具有吸引力的情节关目之一,此由当代武侠小说及其影视文学中发展到极致的类似描写就可以看出来。
其三,古代文言笔记小说中,有不少神奇怪异的载录,尽管其中也不乏写实的因素,也有许多幻异的渲染,而唐代小说中的幻术母题,为汉魏六朝佛经传译故事和道教法术描写,起到了重要的中介功能,从而为后世小说相关母题的产生与拓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生长点,其积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收稿日期]2000-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