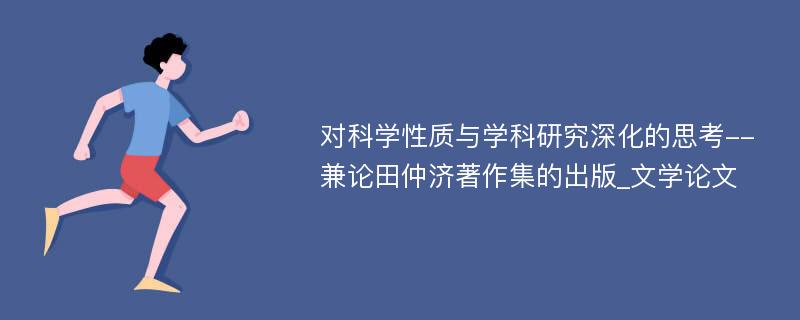
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走向深化的思考——兼谈《田仲济文集》的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学科论文,走向论文,文集论文,田仲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田仲济先生是我所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学者,为他的学术成就,为他民族苦难时期的热诚和奉献,更为他的为人的精神品格与魅力。
田仲济先生1940年代所著《中国抗战文艺史》一书,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和书史者的眼光,丰富的史料,简约的文字,为那个多少作家以生命铸成的一段特殊年代里的文学足迹,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实和记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留下了一副永久的面影,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朽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将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历史中一份永久的记忆。自1960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起,这本书就素为我所喜爱。我之走近、了解、认识和景仰田仲济先生,就是自这本不厚的小书开始的。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在一些有关鲁迅、现代文学等的学术会议上,我曾多次见过田仲济先生。由于自己的疏懒,或怯于拜会名人,与田先生,单独请教或接触的机会很少。田仲济先生抗战时期所写的杂文集,修订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一书,出版之后,先后都曾寄赠给我,我从心里感谢田先生的盛情。那本杂文集,我曾认真拜读过,对于先生抗战时期里,作为一个年轻作家葆有的那种政治坚守,犀利眼光,创作热情,抗争精神,隽思妙语,是非常敬佩的。为此书召开的那次研讨会,因为有事,没能参加,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至今想起来还是很遗憾的。
《田仲济文集》(杨洪承主编:《田仲济文集》,四卷本,江苏文艺出版2007年版)在今天出版最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唤醒我们后来者如何重新认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活跃于新文学文坛的那一代人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很多是被“五四”文学革命和启蒙光辉唤醒或哺育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早些时候已经开始走上文学道路。抗战开始之后,他们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知识人。到抗日民族战争至解放战争十多年最艰难最严酷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知识界民族自救和夺取新生的文化搏求者的代表。无论是活跃在前线,或搏斗在大后方,或坚守在沦陷区里,他们很多人,都能够以自己生命无代价的奉献,自愿地掮起了搏求民族解放新生和真理正义的大任。有一些人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宝贵生命。他们用自己坚硬而贫瘠的脊梁,筑起了我们民族精神与现代文化走向新生的长城。也用自己的生命,心血,和不屈的笔,写下了中国文学创作和学术发展别具精神蕴藏的历史辉煌的一页。我们这些后来者,无论我们这样渐入老年之境的笔耕者,还是正富壮年的新生代的知识人,对于田仲济先生所代表的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与灵魂,他们留下的文字与人格,都应该抱有一种由衷的肯定、认同和赞誉。读他们留下的那些粘满个人心血和时代风烟的文字,即使是最客观最严峻的纯学术研究,也应该持有一种“回到现场”境遇的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随着历史时代的移动和文学选择眼光的改变,我们审视和评价历史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科学的多种层面和向度的再认识再评骘,可能会凸显某些文学现象,淡化某些历史行迹,依据个人选择的价值视域,进行或高或低的多元阐说,但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田仲济先生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所拥有的永远不可复现的精神光亮,我相信,是永远不可能被历史淡漠或随意抹煞的。
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历史文献的更深发掘,随着时代蜕变反复波折的过程,出于对于某种日渐缺失的精神的重认和呼唤,学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反思自身研究中对于极不平凡的那段历史的文学实绩,对于那些可尊敬的知识人群,对于那时人们所张扬的精神,采取一种过于淡漠或轻漫的态度,是多么大的历史无知和谬误。人们会更加觉得那个时代文学和知识人所拥有的精彩丰富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值得珍视,也会更加觉得被我们自己写人文学历史的一些声音和文字,是多么的干瘪苍白黯然失声而缺少历史的多彩和丰灿!
接到杨洪承教授邀我参加田先生《文集》出版座谈会的邮件之后,在复信里,我表示一定参加这个座谈,同时还特别发送给他一篇将于《新文学史料》发表的文章,告诉他这样一件事:我新近在搜阅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自集中营脱险后的冯雪峰,刚到重庆不久,在一份不太为后人或文学史所知的《文学修养》杂志上,发表的一首珍贵的短诗《呼唤》。我由此考释了这份杂志与“归来”的雪峰及其他“文协”作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为此,顺便在1944年出版的《文学修养》第2卷第2期、第2卷第3期杂志上,分别读到了田仲济先生的《典型的事件》、《当前创作的考察》两篇文章。当时还没看到《文集》,不知里面有没有收入?杨洪承教授当夜即要前往北京,来不及仔细翻阅文集,也没来得及回答我的疑问。在这里拿到《文集》后,匆忙翻阅一遍,知道这两篇文章,作为先生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作文修养讲话》一书里面的两章,已经收入《文集》中了。《文学修养》是一本辅导青年写作的小刊物,过去很少为抗战文学史研究著述所提及。翻阅刊物后才发现,当时不少文学大家,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包括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孙伏园、丰子恺、冯雪峰、以群、马耳(叶君健)、蔡仪、钟宪民、徐霞村、王平陵、常任侠、高植、任钧、王亚平、姚雪垠、梅林等,以及其他当时活跃于重庆、成都等地的作家,都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从田先生发表的两篇文章里,可以看出先生对于指导文学青年写作所倾注的热情和心血。两篇理论文章,涉及问题很广,论析也非常清晰,看得出田仲济先生对于苏联和世界文学的名著以及文学理论很熟悉,对于鲁迅、茅盾、老舍等人的创作和理论思想也非常熟悉。他阅读了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认真评骘,有推举,有批评,很实在地谈了一些创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如谈及作品艺术魅力根源的时候,他结合流行甚广的张恨水的小说,肯定其艺术表现上注意“动”的特点,并以此为标准,分析了芦焚、舒群等人小说的成功和不足,都是很有见地和眼光的。
由此也可以说明,我们对于抗战时期文学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了解得还很不充分。即使是已经研究得很充分的作家,他们原生态的文学踪迹,作品发表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许多文人之间的交往与行踪,很多也不是弄得非常清楚的。如曹禺这样的大剧作家,抗战期间在重庆,亲自动手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曾演出获得成功,剧本后来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里单行出版,这些情况,曹禺传记和一些文学史里,有所记载;但是该剧的译本,最初分两期连续刊载于这个不太起眼的《文学修养》杂志(1944年2月15日出版的第2卷第3期和1944年6月20日出版的第2卷第4期)上,目录均标为:“《柔蜜欧与幽丽叶》(舞台本),曹禺改译”,这是过去未为人所论及的。我昨天晚上翻阅专门撰述的曹禺传记和有关年谱,也没有记载的。
《田仲济文集》的出版,雪峰佚诗《呼唤》以及《文学修养》杂志中一些文章的发现,我又想到《文集》出版的另一番值得提及的意义,即我们现代文学史研究,如何更加重视原生态史料的开掘发掘,如何处理一些作家的《全集》、《文集》、选本与原始资料的阅读引用关系之问题。我们常喜欢说,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已经成熟了。我于此总有些怀疑。我自己觉得,说现代文学学科成熟,似乎还嫌过早了一点。首先,我们学科的领域与界限,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它与近代文学、当代文学的联系与区分如何界定?将眼光放得远一点,这种格局的划分,究竟生命能有多久?它所应该包含的文类领域和地域文学现象,如现代旧体诗和文言散文笔记、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民间文艺、口述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台湾等其他地域的文学等,如何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历史与叙述的视野?其次,我们的学科研究,还缺少像古典文学史研究所具有的那样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我们缺乏科学的稳定的学术标准,缺少必须严格依据史料进行论析的学术风气和研究心态,缺少对于随心所欲过度阐释等非科学现象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批评的正常学养和理论氛围。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带着很大的短暂性与波动性。一个作家作品的评价,一些文学现象的言说,根据某个社会思潮认知与个人意志传达的需要,今天可以这么说,没有多久,过些时候又可以那么说,一会儿可以贬入地下,一会儿又将之捧至天上。历史评述与理论阐发如“翻烙饼”一样变来变去。现代文学本身与现代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特征,一些研究者受实用主义学术观的影响,也带来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联系与距离如何恰当处理问题。以学术研究作为参与意识形态发言的工具,让学术研究承担学术之外现实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任务的工具化角色,在我们学科的研究中还时常出现。这些都或重或轻地影响着历史性质学科的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客观性质和科学性品格。第三,有些研究者自身甚至还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意识。以纯属主观猜测和想象臆造来代替严肃学术研究的风气,甚至完全放弃科学化准则的肆意“猜想”,还能够在不小的范围内流行,或被一些学者认定为是学术的“创新”与“突破”,加以赞许和评骘。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近一百年前发生过而早已被否定了的某些非文学性的,也是非科学性的作家作品研究方法,如任意的主观猜臆或脱离文学创作的“索引”派,在现代文学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中,竟还能通行无阻,得到认可。学术研究的自由性与学术研究的任意性之间之界线模糊,比起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以及其他学科来,显得更加突出和明显。第四,学术规范训练薄弱和学术评审体制制约,使得这个学科的研究里,所表现的学风浮泛化与急于求成的仓促性,比起其他一些成熟的学科来要严重得多。过分依赖于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依赖于坊间流行的第二手文献资料,依赖于晚近出版的文人《全集》、《选集》,以及各种随意得到的畅销选本,而不去花多一点的工夫翻阅自己研究对象生产的最初版本、原始杂志、报纸副刊,不去花大力气发掘发现别人未曾用过而是自己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如此下去,不仅可能出现研究成果中的许多错讹,陈陈相因,出现不应有的学术硬伤,还会使得自己的宏大论述缺乏深厚的历史感,现场感,和立论的坚硬性。《田仲济文集》出版,为我们研究的深入,一方面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捷径。运用方便很好,走捷径就不一定都好了。放弃真正走进历史的代价付出,单图快出成果而一味走捷径,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就可能会炮制出很多理论泡沫来,而丧失自身的鲜活、创新、严谨与悠久的学术生命。
《田仲济文集》的出版,还可能会激活起一点我们关注和研究抗战期间文学的更宽广、更深层也更鲜活的一些历史细节的冲动。在既成文学史理论框架和模式化叙述之外的一些历史场景,文人风貌,文人交往,作家心理,文化趣味等等,过去往往被史家之视野和笔触所忽略了。在给《新文学史料》的那篇文章中,我用很大篇幅引述了《文学修养》上梅林发表的日记体《文林琐记》的文字,意图即在为今日读者提供一些那个年代里作家们之间的一些鲜活图景。从那些文字中,可以看到许多文学史叙述之外的东西,看到当时在重庆的许多作家的生活风貌来。比如一、当时作家的生活非常艰苦,经济很窘困,但他们都为民族的光明解放怀有光明理想与斗争精神。二、他们之间很密切友好,经常往来,小聚交谈,切磋艺术,畅谈理想,在艰苦环境中建立了一种亲密的情谊。三、他们也在交谈中流露出丰富的兴趣与自由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活生生的作家的人生情怀。有些很有兴味的文字,因碍于篇幅,被我删去了。如1943年夏天梅林与田仲济先生两个人小聚夜谭的情景:
七月廿九日,星期四,炎热。……
晚九时许田仲济来,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闲谈着恋爱的故事。
“歌德八十岁时还和十多岁的女孩子恋爱呢。”
“屠格涅夫说,没有恋爱即没有创作。到晚年他还坐在人家会客室里的白熊皮上。”
“如果现在还会为了一个女人而自杀,这在我是不可思议的。”
“你没有遇到可以震撼你灵魂的对手,比如,她美,一切都美,对事物不会比你懂得更少,又那样爱你,使你一看到她,即感到深入灵魂的大幸福,有一天,她忽然爱别人去了,而你正在热情达到最高度的时候,在这种场合,对于自杀就会变成可以思议了。”
“世界上没有这种女人呀。”
“有的,你没有碰到罢。”
但是结尾还是“完了”和“现在没有恋爱的心情了。”
两天之后的八月二日日记里,面对极度的收入微薄与生活窘困,梅林发出了包括田仲济先生在内的抗战时期一些作家们内心里存在难以生活下去的艰难痛苦而又挣扎坚持的矛盾声音:
怎么办呢?如所有“没有办法主义者”的人们一样,我们也变成了“没有办法主义者”。我们不断的谈起“从前”,一如乡村的老太婆。
从前稿费千字最少二元,多则三元五元或十元,即以二元计,亦等如现在二百元;现在呢?千字稿费最多六十元,平均三十五或五十元,赶不上“从前”五角钱,如以“生意眼”来看,我们在做着倒贴本的生意。然而,更悲哀的是,一些站在云端上的人们,一些骄傲的人们,却给我们以斜视,斥责,我们这群头发散乱,双颊下陷,脸色苍白,胡须乱得如饭锅刷子,整天关在屋子里提笔苦思的人,啊啊!我们真如讣文上所必书的“罪孽深重”,啊啊,我们我们,啊啊,我们的“命运”何其悲苦哉!
只好以忧郁来喂养自己的贫血的心,只好以“理想”,以“未来”,以“黎明”,以一切心造的正直光明的幻影来安慰自己,同时只好更坚持文艺事业,更坚持创作态度,更坚持“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生活态度;不然,怎样生活下去呢?
一段闲谈场景谈话的记录,一段自我叩问的内心自白,将抗战时期大后方那些熟悉的青年作家们的淡宁心境,丰富情趣,熟稔知识,严肃思考,内心矛盾,情操坚守,个性声音,都比教科书里那些许多枯燥的历史叙事,更鲜活地留在那一页页陈旧纸张的字里行间了。它让我们读到了那一代青年文人在战争和物质的重压下,还葆有着怎样的生活乐趣、自由思想和高尚情怀。我们作为后来的文学历史的叙述者,应该从《田仲济文集》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当年更富原生态与现场感的文字里,从一些报刊杂志的充满生活热度的话语中,读出更加真实更加活跃的历史的灵魂来。由此我也越来越痛切感觉到,作为现代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我们对于抗战时期的文学历史以及作家的成绩与精神,个性与风貌,还挖掘得很不够。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比田仲济先生的《中国抗战文艺史》更加规模宏大更加论述科学的沉实厚重的抗战文学史著作产生。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还有许多被忽略的盲点和空白。我希望,也期待《田仲济文集》的出版,对于改变这种情况,推进抗战文学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理论研究的拓进与深化,最终获得更大更多的成果,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促进。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抗战精神论文; 田仲济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科学性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