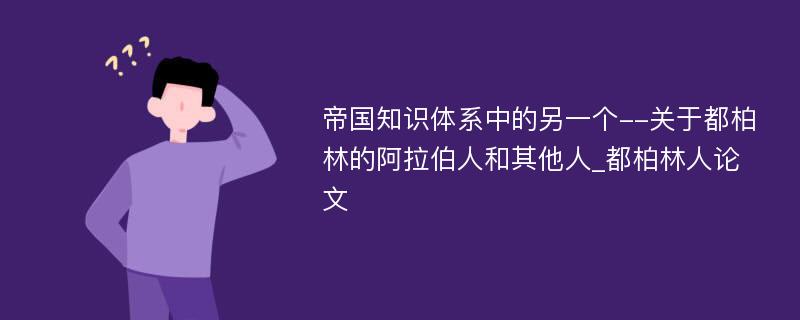
帝国知识体系中的他者——论《都柏林人》中的阿拉伯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柏林论文,阿拉伯论文,帝国论文,及其他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至今日,在后殖民理论研究和具体文本批评中,关于帝国-他者之间权力关系的论述,已可谓洋洋大观。然而,正如浩瀚的帝国由无数形态各异的被征服疆域组成,构成帝国政治地图和帝国-他者错综复杂关系的,也绝非殖民权力中心与某一个边缘文化的单一互动。在后殖民语境中,一个文化他者如何呈现另一个文化他者?这一种呈现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追寻和真实的认识,还是在帝国操控的视角里生成的又一个幻象?对这幻象的觉察,只是知识的纠误,还是会更积极转向对自身困境的醒悟与思考?——这些都是现有理论阐发涉猎不多的话题。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早在《都柏林人》中就对这一文化困境予以了独特的关照。尽管从乔伊斯的思想发展历程观察,他作品中“精神瘫痪”等所谓爱尔兰国民性的最初提出,可能部分受帝国建构的爱尔兰形象的影响;①但是,《都柏林人》中的爱尔兰则逐渐脱离了帝国视角而转向对自身身份的自觉拷问,对殖民话语所传达的关于阿拉伯等东方异域文化的知识,也经历了从接受到质疑再到颠覆的转变过程。通过用文化他者爱尔兰以帝国操纵视角想象另一个文化他者阿拉伯做喻,乔伊斯在小说中凸显了帝国对爱尔兰无处不在的渗透与禁锢。不过在此,他者对他者的想象并非导向对帝国权力的无奈认识,而是展现了更为积极的意义,因为正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所开启的这一话题——对帝国炮制的阿拉伯东方镜像之虚幻实质的最终顿悟——使隐形控制一切的帝国现形,并激发乔伊斯笔下成长中的都柏林人觉察到,自身身份亦同样被殖民权力所言说、所建构,从而微妙地开启了对帝国神话的祛魅和爱尔兰人的文化寻根和自我重建之旅。本文拟将焦点投向《都柏林人》中《阿拉比》这一对阿拉伯文化具有强烈指涉与想象并被誉为“艺术家少年时的画像”的故事,②探求乔伊斯揭示的这一个体成长和文化觉醒的历史内涵与现时意义。
一、阿拉伯——在场或缺席
乔伊斯在《阿拉比》中建构了一个充满欲望的想象迷图——一个对都柏林沉闷生活倍感失望的小男孩试图寻找新的希望,他将自身的欲望投向邻居的姐姐;后者对阿拉比③这一名字听着极富阿拉伯魅力的郊区集市的提及,激起男孩心中对浪漫东方的无限想象与憧憬,然而当他克服重重阻挠抵达那个集市时,却发现那里只不过是另一个无聊都柏林的翻版。对这篇故事的传统诠释常常将它视为成长小说,或者是对欧洲中世纪圣杯故事的现代滑稽模仿,以昭显逃脱的困难与对困境的顿悟这一现代命题。④不过也有评论家已注意到其中“东方”母题的存在是乔伊斯试图展现都柏林本土经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⑤另一些则将地理与空间引入对主人公的心理分析,揭示出东方与西方在《都柏林人》中的隐喻意义,⑥如英格索尔发现开篇三个童年故事存在都柏林人向东探求这一趋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终章的公共生活故事《死者》中的主人公则选择向西方即爱尔兰自身回归。⑦
这并非简单物理意义的位移。尽管乔伊斯在故事中从未直接提及帝国的存在,但帝国及其创造的知识体系却在人物的思考与场景的描述中时隐时现,最终在故事行将结束时显性登场。如果追溯《阿拉比》里那个爱尔兰小男孩对阿拉伯的认知,我们会发现,这个从未离开过故土的小男孩或其他都柏林人,他们对遥远东方的理解远非自然的产物,而是帝国的转述或投射的镜像;所获得的也是经过权力过滤所派生的“知识”。⑧
在《阿拉比》中,东方的浪漫与都柏林的苦闷隐约形成对照。故事一开始,当小男孩翻检死去神父留下的书籍时,乔伊斯就暗示小男孩所拥有的东方知识的某种可能起源:
在其中,我发现一些平装本的书,书页都卷起而且发潮:瓦尔特·司各特的《修道院长》,《虔诚的领圣餐者》,《维多克回忆录》。⑨
小男孩在对其所发现的三本书的描述中,只单独列出司各特的名字,可见乔伊斯暗示小男孩对司各特的熟悉。诚然《修道院长》讲述的是苏格兰玛丽女王越狱的故事,但其英国作者司各特却以东方情调著称,是19世纪西方对东方的公共意识形成中的关键人物之一⑩,其描述十字军东侵的小说《十字军东征记》展现了西方对异教东方充满偏见的再现,并“对东方学话语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Orientalism:99)。在《都柏林人》另一个童年故事《路遇》中,老水手向渴望逃脱的小男孩推荐的作者,恰恰也是司各特。
同样,小男孩对单恋少女的姓氏“曼根”(Mangan)的提及,也不乏对(想象的)东方的指涉和对其真实性的隐约怀疑:那少女与喜爱描写“Araby”题材的19世纪爱尔兰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詹姆斯·克莱伦斯·曼根(James Clarence Mangan)同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虽然甚至声称他的诗歌有些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而成,他本人却根本不懂阿拉伯语。(11)
当小男孩急于出发,他那穷极无聊的姑父追在后面大声咏颂《阿拉伯别马歌》(“The Arab's Farewell to his Steed”)时,爱尔兰人心中阿拉伯知识的真实源头以一种更清晰的方式浮出水面。该诗吟诵的虽是阿拉伯青年与马的故事,但作者却非阿拉伯人,而是英国女诗人凯罗琳·诺顿,她的身份与帝国和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诺顿出生于19世纪大英帝国首都伦敦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地事务官员家庭,祖父为爱尔兰著名戏剧家谢里丹。她曾委身时任英帝国爱尔兰事务大臣、后任英国首相的墨尔本爵士,当过他的情妇;而墨尔本曾支持制定严厉镇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法案。诺顿这首关于阿拉伯的诗歌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爱尔兰风靡一时,被广为传颂,据考证“在爱尔兰的每个诗选中都能找到”(12)。
同样,在小男孩两次直接描述他对东方的憧憬和想象时,乔伊斯的选词本身也充满了寓意:
我的灵魂沉浸在一片寂静中,阿拉比这个词的音节在我脑海里被唤起,散发出一片东方的魅力(enchantment)。我请求周六能出发去集市,我的姑姑吃了一惊,她希望那不是什么共济会的勾当。
在我面前,是一个庞大的建筑,上面写着那充满魔力(magic)的名字。(Dubliners:32-34)
在这里,语言大师乔伊斯选用的“enchantment”、“magic”等形容小男孩对东方感知的词汇,本身就蕴含异教巫术、外力施魔而产生幻觉之意;而他虔信天主教的姑姑则认为阿拉比跟19世纪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的共济会相似,都属于异端。由此看来,伴随着阿拉比这一个词汇和它的音节,在普通爱尔兰人心中唤起的是帝国的传说、文学和官方学术研究所灌输的经典阿拉伯形象:异教的、浪漫的、非理智的、魔幻的——一种如雨果所言,具有“普遍迷惑力”的东方(Orientalism:101)。
最为重要的是,甚至“阿拉比”这个词本身也是虚幻的,是真实的缺席。笼罩着整个故事、跳动在字里行间、散发着东方诱惑的“Araby”一词是19世纪西方关于东方想象的产物,它在欧洲语言中的诞生与流行,象征着西方征服和刻板再现东方的开始。据当代乔伊斯研究专家华莱士·格雷考证,“阿拉比是指称中东的一个浪漫术语,但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度。这个词在19世纪非常流行——用作表达自拿破仑征服埃及后[欧洲]所形成的对东方的浪漫主义观念”(13)。爱尔兰民歌中的《阿拉比之歌》就径直嘲讽着爱尔兰东方想象的虚幻:
我将为你唱起阿拉比之歌,
我将吟诵美丽的克什米尔故事,
狂野的故事骗取你一声叹息
或引诱你落下一滴泪水。(14)
在《阿拉比》中,乔伊斯用互文展现了东方在爱尔兰的生成,他对帝国各类有关东方的作家的提及和对一系列别有深意的意象或词汇的使用,几乎对应着70多年后萨义德关于东方的著名定义:
在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中,东方与其说是一个地域空间,不如说是一个被论说的主题,一组参照物,一个特征群,其来源似乎就是一句引语,一个文本片段,或他人有关东方著作的一段引文,或以前的某种想象,或所有这些东西的结合。(Orientalism:177)
二、遭遇帝国与个体觉醒
如果说乔伊斯在《阿拉比》开篇后的大部分段落中,仅仅以诸多暗示来隐喻爱尔兰人对阿拉伯的想象如何受帝国操纵,那么在故事的结尾,他让小男孩与英国在阿拉比市场径直相遇,直接展现了他者对他者的想象中帝国存在的实质。这并非单纯是对荒谬想象的纠偏,而是暗指爱尔兰人在其中也隐约联想到自己对自身的理解亦被帝国所控制的命运。
都柏林郊外那个号称阿拉比的集市就像一面魔镜,本应每天安然无事地向少女曼根、小男孩或者那些从未跨出国门一步的爱尔兰人投射遥远东方神秘莫测的镜像;然而,在某个星期六夜里行将关门时,随着小男孩不期而至的闯入,一切幻象不攻自破——在市场里,小男孩发现占据这想象的中心的,不是真实的阿拉伯,而只是英国人和一堆阿拉伯器物的仿制品,或者说是帝国无处不在的存在:
我搜索枯肠,才想起我为何而来。我走到一个铺子前,端详瓷瓶和印花茶具。在铺子门口,一个年轻女士正和两个年轻绅士谈笑风生。我辨出了他们的英国口音,模模糊糊地听着他们的交谈。(Dubliners:35)
在此,一个充满反讽和象征的微妙时刻就此降临——爱尔兰小男孩与帝国直接遭遇。这一遭遇,并非只是在语音上识别出英国口音,更富寓意的是,随着阿拉伯镜像的破灭,径直显形的是镜后英帝国对这一系列幻象的操纵和爱尔兰自身的困境。乔伊斯似乎将整个世界压缩成阿拉比这一个小小的点,在这个微观的世界里,小男孩既在与英国人的狭路相逢中醒悟到原有的阿拉伯虚妄形象的源头,同时更在那附和着两个英国男人调笑的爱尔兰女人身上依稀看见爱尔兰被帝国控制和言说的类似境遇——英国是男性的,爱尔兰是女性的;英国男人可以对爱尔兰女人加以嗔责,而后者只能被他们限定,只能一再被动而徒劳地辩解“没说过”,最后不得不屈从甚至附和他们的话语,承认他们的话是对的,而她是在说谎:
“哦,我从没说过!”
“哦,你说过!”
“哦,我没有。”
“她说过吗?”
“是的,我听见了。”
“哦,那就是……撒个谎而已。”(Dubliners:35)
在这个故事的尾声,我们不难看出一种试图与帝国既有知识体系相分离的努力。小男孩对东方世界的最初想象,总是与他渴望逃离苦闷甚至丑陋的都柏林联系在一起;而浪漫的阿拉伯和庸俗的爱尔兰尽管形象迥异,但从故事的最初开始,却似乎都来自帝国的界定。如前所述,当一个爱尔兰小男孩翻阅讲述苏格兰女王被英格兰囚禁并杀害的《修道院长》时,故事主题一开始便已伏下爱尔兰自身同样被帝国主宰的隐喻。而更值得警醒和推敲的是,这“泥泞”、“喧闹”、“喝得醉醺醺”的都柏林与它的民众那著名的“精神瘫痪”,也有可能是来自帝国的叙述,而非真正的爱尔兰国民性,第克兰·基伯德的《构想爱尔兰》一书通过勾勒爱尔兰近千年的文学与文化演进,就指出所谓爱尔兰特有的诸多负面国民性很可能是英国施加的偏见。(15)具体到乔伊斯作品中关于爱尔兰人“瘫痪”等特性的描绘,基伯德强调,“在乔伊斯从事创作的20世纪初期,绝大多数工业国家,而非仅仅是它们外围的殖民地,其实都弥漫着混乱无助感”(Inventing:330)。同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乔伊斯研究者通过版本整理与历史背景研究发现,甚至连“瘫痪”这一命题的提出,也许也并不完全源于乔伊斯本人的意识,而或多或少有着英国的视角。“瘫痪”(paralysis)一词,首见《都柏林人》开篇故事《姐妹》中小男孩的喃喃自语,因其高度凝练而被后世广为传颂,但卢克·吉本斯指出,“瘫痪”一词在《都柏林人》的最早版本中其实并不存在。它被添加进《都柏林人》,是在英国著名记者兼作家菲尔逊·扬游历爱尔兰并于1903年出版轰动一时的《十字路口的爱尔兰》一书之后,而正是在此书中,菲尔逊·扬提出爱尔兰民族“精神和肉体的疲惫”、“麻木”与“瘫痪”一说。(16)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因为吉本斯进一步发现,乔伊斯藏书中就有扬的著作,而他更曾邀请扬为其1915年出版的《都柏林人》作序。乔伊斯作品中对爱尔兰人精神瘫痪及其他国民性的几处经典例证,或多或少都与扬有着某种暗合:如《斯蒂芬英雄》中“[爱尔兰人在]教区教堂与精神病院阴影下战战兢兢与机变逢迎的生活”无不回荡着扬对爱尔兰国民性的叙说,而扬对隐居莫勒雷山的修士古怪睡眠习惯的描述,几乎被直接借用至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死者》中。(17)
由此,当我们回顾《阿拉比》时,不禁会问,正如小男孩对阿拉伯的理解一样,他对爱尔兰的理解,是否完全出于自身的体验,还是部分源于帝国的构建?乔伊斯主人公心中所展现的贫穷落后的爱尔兰和她黑暗中的首都与肮脏喧闹的市场,难道不正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自16世纪的斯宾塞开始形成的“野蛮”、“落后”、“吃土豆”的爱尔兰形象?(18)基伯德更是尖锐地将《都柏林人》称为“学徒故事集”,并指出帝国那无处不在的铁幕:
回荡在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中的,是回声与阴影,这个地方尽是从他处模仿和衍生的姿态,对它的人民从里到外的呈现,是为了服务于远在伦敦的权力。这一本学徒故事集,今后数十年任何一个新兴的民族精英阶层成员,只要他或她对其殖民处境感觉羞愧,并想在一种以恶的精确性诠释所有虚幻的手法中寻求苦涩的安慰,都会这样写。
《都柏林人》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追寻自由的破产,这种追寻无疑受到诅咒,因为它自身就蜷缩在敌人设定的形式和语言中;这也预言了那种坚持将其自身的定义限定在殖民者所设置的种类框架中的民族主义的失败。(Inventing:330)
但是,如果乔伊斯仅仅是在扮演一个向处于中心的帝国提供素材与佐证、以满足其偏见的知情人角色,他绝不可能成为20世纪公认的大师。文森特·程在《乔伊斯,种族和帝国》一书中,一方面认为乔伊斯作品中的国家与民族身份“是一个文化构建”,但另一方面,他也在其中看见了“对类似意识形态话语的尖锐分析和潜在批判”。(19)如前所述,正是在《阿拉比》中,乔伊斯冷峻调动各类意象,以爱尔兰对阿拉伯的想象被帝国操控为对照,折射出爱尔兰自身认知中的困境。而且在故事尾声中,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人更是直接挣脱了帝国的束缚,通过行动撞破东方镜像。
或者,正是这一对镜像的撞击,不无痛楚地割裂了爱尔兰小男孩既有的经验体系。不过正是这痛楚,将小男孩从迷幻中唤醒。这里展现的痛楚与顿悟是多重的,他既清醒看见帝国构建的东方神话是那么不堪一击,又隐约觉察到帝国自身瑰丽传奇的虚幻——难道这黑暗的阿拉比市场、疲倦的数钱人,就比故事开篇他所厌恶的喧嚣的都柏林市场和那些喝得醉醺醺的男人、讨价还价的女人及哼歌的民歌手要富有魅力?难道这些英国绅士无聊的问题、无聊的重复,就比小男孩的姑父无聊地背诵《阿拉伯别马歌》要更高雅?同时,小男孩最终的顿悟,隐约暗示了“我”对自身身份是被帝国所创造这一真相的洞察:
我抬头凝视着那黑暗,看见自己就像被虚荣心驱使所嘲弄的生物;我的眼中充满痛苦和怒火。
(Gazing up into the darkness I saw myself as a creature driven and derided by vanity; and my eyes burned with anguish and anger.)(Dubliners:35)
在此,一个新的都柏林人隐约出现,他不再是乔伊斯所指称的“慵懒的都柏林人,几乎不外出,只凭道听途说认识自己的国家”(20);他走向阿拉比集市,通过行动觉察了东方和自身的虚幻。在小男孩的顿悟中,“vanity”除指虚荣外,亦有徒劳之意,暗示小男孩意识到对东方认知的失败。而乔伊斯巧妙的选词“saw myself”、“creature”则使叙述者将关注目光由东方进而转到自身的归属;他游离在帝国知识体系之外,并从一个更超然且清醒的外部,全方位立体审视自己的存在:“我”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而是被外部力量所创造的生物(creature)。在这一对自我的解剖中,“我”作为一个被殖民话语所创造的生物的社会属性得以展现。
三、成长中的新都柏林人
如果说乔伊斯在《阿拉比》中只是隐约开启了对帝国和被帝国构建的身份的质疑,那么从这篇“童年系列”的最后一个故事开始,新的都柏林人开始成长:帝国关于神圣自身和肮脏爱尔兰的神话尽管被一些都柏林人以崇敬的口吻公然提及,但这一切却逐渐受到另一些都柏林人的质疑与消解,他们开始一次次拷问自身的身份和帝国的真相。在《阿拉比》之后的《一朵小小的云》中,乔伊斯立刻转向对帝国中心的解构。当都柏林在小钱德勒心中以“古板,毫无艺术气息可言”的经典形象出现时,当帝国首都伦敦对他而言充满各种勃勃生机与机会时,当他手捧拜伦诗集、渴望像拜伦那样逃离苦闷并以一个凯尔特诗人的身份打入伦敦评论界时,帝国的中心是那样的瑰丽!但是,熟悉英国和英国文学史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深藏的反讽和对帝国神话的颠覆:对渴望像拜伦一样流亡、寻求新的生活和生命的钱德勒而言,帝国的首都伦敦是精神的归宿——但正是伦敦或英国,当年无情地放逐了拜伦!而真正走进并居住在帝国心脏的钱德勒挚友加勒赫“面色苍白”、“眼睛灰暗”、“双唇毫无血色”,“头发稀疏”(Dubliners:75),他漫不经心间对伦敦的提及,似乎瓦解了小钱德勒心中的帝国中心的形象,同时加勒赫在调侃中对都柏林充满温情与亲昵的赞叹,又无疑在小钱德勒耳畔增添了几丝异样的声音:
[伦敦的]出版社工作让你的身体都垮掉。总是忙碌不堪……我可告诉你,跑回老家真够让人乐颠颠的……自打踏进亲爱的肮脏的都柏林,我可舒服多了。(Dubliners:75)
而随着加勒赫用“历史学家一样平静的语气”严肃地描述欧洲各国首都的腐化堕落时,这样一种异样的声音逐渐加强,以致平生未出国门半步的小钱德勒“不禁愕然”:
伊格纳提斯·加勒赫在沉思中抽着雪茄。然后,他用历史学家一样平静的语气,简洁地向朋友讲述了国外比比皆是的腐败场景。他总结了许多国家首都的罪恶,其中最厉害的是德国柏林。有些事他没法证明(都是听朋友说的),但另一些可是他亲身经历过……他描述了上流社会盛行的种种行径,最后将他知道真实内幕的一个英国公爵夫人的秘闻向朋友抖了个干净。小钱德勒不禁愕然。(Dubliners:78)
而在《死者》中,主人公加布里尔试图摆脱他的爱尔兰文化身份,他只在欧陆度假,声称“要跟那里的语言保持接触”,并拒绝承认爱尔兰语是他的母语,宣称“我的国家让我厌恶”。他对故土的视角不是爱尔兰本土的,因为他的同胞敏锐地发现他“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一无所知”,因此称他为“西不列颠人”(Dubliners:189)。但是,是在故土中,加布里尔发现他妻子和美少年迈克·弗里真挚的爱,足以击破帝国叙述爱尔兰丑陋粗鄙的任何神话,而死去的迈克·弗里、苍老好客的姨妈,隐喻着行将消亡的慷慨热情的爱尔兰凯尔特人传统。《都柏林人》这一终章故事的主人公第一次公开放弃了短篇小说集开篇中的向东进发,最终选择“向西跋涉”(Dubliners:223),去寻找那逝去的爱尔兰。
在1906年5月5日就《都柏林人》写给出版商的信中,乔伊斯宣称他的写作目的“是为我的国家撰写一章道德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是因为它是瘫痪的中心”(21)。但是这样一章道德史和它所描述的“瘫痪”并非消极确认一个丑陋的爱尔兰形象或是奏响一曲关于民族精神沉沦的无奈挽歌,而是具有一种“召唤行动”的积极力量。(22)很少有人留意到,当不久后乔伊斯在另一封致出版商的信中明确再次提及“道德史”一词时,它被赋予了破解“瘫痪”的更为积极的意义:“我相信我遵循一贯的创作途径,在对此道德史篇章的创作中,业已迈出通向我之国家精神解放的第一步。”(23)同时,乔伊斯坚信,他的《都柏林人》能“让爱尔兰人看见自身”(24),因此在以精神瘫痪警示爱尔兰人之外,他亦以他自身的抉择和他所塑造的人物,让国人看见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然通过切实的行动,展现出潜在的解放意义——在真实世界里,爱尔兰人乔伊斯用自我流亡和艺术创作试图更好地认识爱尔兰;在想象的世界里,从突破东方镜像到消解帝国神话和自身亦被构建的身份,实在的行动给予那些爱尔兰人以精神突围和自我重建的可能。
注释:
①See Luke Gibbons,"Have you no home to go to?:Joyce and the politics of paralysis",in Derek Attridge and Marjorie Howes,eds.,Semicolonial Joy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0-151.
②See Harry Stone,"Araby and the Writings of James Joyce",in Dubliners:Text,Criticism and Notes,New York:Viking Press,1969,p.345.
③阿拉比是阿拉伯的古名。
④See John Freimarck,"Araby:A Quest for Meaning",in James Joyce Quarterly,7(1970),pp.366-368.
⑤See Robert Scholes and A.Walton Litz,"Editors's Introduction to Criticism Section",in Dubliners:Text,Criticism and Notes,p.300; William York Tindall,A Reader's Guide to James Joyc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5,p.24.
⑥See Jackson Cope,"Joyce's Wasteland",in Genre,12(Winter,1979),p.516; Maria Tymoczko,"Translation of the Themselves:The Contours of Postcolonial Fiction",in Sherry Simon and Paul St-Pierre,eds.,Changing the Terms: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Otta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2000,pp.154-155.
⑦See Earl G.Ingersoll,"The Psychic Geography of Joyce's Dubliners",in New Hibernia Review,6(4,2002),pp.98-99.
⑧See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London:Tavistock,1977,p.27.
⑨James Joyce,Dubliners:Text,Criticism and Notes,New York:Viking Press,1969,p.29.中文译文均为作者本人所译。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⑩See Edward said,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New York:Vintage,1979,pp.60-16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11)See Harry Stone,"Araby and the Writings of James Joyce",p.348.
(12)See Harry Stone,"Araby and the Writings of James Joyce",pp.357-358.
(13)Wallace Gray,"Araby",http://www.mendele.com/WWD/WWDaraby.notes.html此为哥伦比亚大学已故英语教授格雷建立的《都柏林人》个人研究网站。
(14)See Vincent J.Cheng,Joyce,Race and Empi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91.
(15)See Declan Kiberd,Inventing Ireland:th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Nation,London:Random House,1995,pp.9-6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16)See Luke Gibbons,"Have you no home to go to?:Joyce and the politics of paralysis",pp.150-151.
(17)See Luke Gibbons,"Have you no home to go to?:Joyce and the politics of paralysis",p.151.
(18)See 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1994,pp.285-286.
(19)See Vincent J.Cheng,Joyce,Race and Empire,p.9.
(20)James Joyce,The Critical Writings,eds.Ellsworth Mason and Richard Ellmann,New York:Viking Press,1959,p.229.
(21)James Joyce,"The Evidence of the Letters",in Dubliners:Text,Criticism and Notes,p.269.
(22)See Paul Delany,"Joyce'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Aesthetics of Dubliners",in College English,34,2(Nov.,1972),p.257.
(23)James Joyce,"The Evidence of the Letters",p.277.
(24)James Joyce,"The Evidence of the Letters",p.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