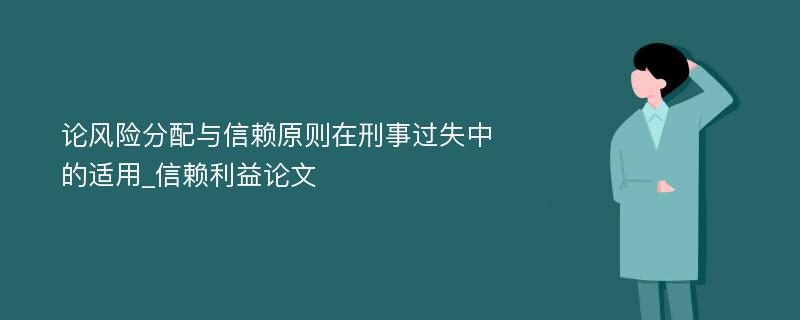
试论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在犯罪过失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失论文,则在论文,试论论文,分配论文,危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刑法犯罪过失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司法实务在处理职务、业务活动的责任事故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我国学者对此理论探讨的不多,司法实务中尚未自觉运用这些理论。因此,合理借鉴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
一、危险分配的概念及理论发展
所谓危险的分配,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为理论基础,在“过失犯处罚减轻合理化”口号下提出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从事危险的业务或者事务时,参与者应当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地实施,相互间分担回避危险,使危险减轻或者消除。危险的分配的理论,虽然从客观上说,是对涉及危险业务、事务的当事人应当合理地分担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的注意义务,但其理论的重点,学者认为,并不在于危险预见义务的分担,而在于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注:参见[日]大谷实:《危险的分配与信赖原则》,载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109页。)。
然而,从刑事责任的分担上,无疑危险的分配要涉及到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回避义务依据何种原则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为回避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科以参与者在从事危险业务、事务活动中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对一方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多,则对另一方就应当要求的少,反之亦然。例如,驾驶汽车撞死了行人,就该事故论及有关人员的过失时,就必须考虑驾驶员和行人各自负有什么样的注意义务,是哪一方违反了注意义务。为保障交通安全,应当科以驾驶者和行人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要求驾驶者的注意义务多,则要求行人的义务就少,相反,要求行人的注意义务多,对驾驶者就应要求的义务少。那么,应以什么样的原则合理的分配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从其实践以及理论发展的情况来看,应当说直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通常是基于行为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以“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注:[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为根据, 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与多少。
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司法实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与危险的分配理论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日本,随着社会对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不同评价,危险分配的理论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社会,汽车持有的数量少,道路及交通设施也极不完备,道路狭窄,没有行车与行人道的区别,只是在主要路口设置交通信号灯,行人亦不太讲究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务中几乎就不承认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地位,因而强调对行人安全的保障,在社会观念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妥。所以,就科以驾驶者广泛的注意义务,对行人则要求极少的注意义务,给予行人相当的行动自由。当发生事故时,大都会认为是驾驶者的责任。
例如,在日本大正时期,大审院的判决作过如下说明:“汽车的驾驶者在操纵汽车时,应当努力注意警戒道路的前方,防危害于未然,乃是其业务上当然的义务。在汽车行驶中,有人横穿马路,渐渐接近时,只鸣笛、减速尚不够,还应当注意行人的态度、姿势等其他情况,采取随时都得以停车的措施,使用避免急遽危害的方法,留有防危害于未然的余地。”还有判例要求驾驶者暂时停车,待行人通过后再启动行驶。如果驾驶者违反了上述注意义务,就应当构成业务上的过失致死罪。对于科以驾驶者如此广泛的注意义务,从而使汽车不能发挥其作为高速交通工具作用这一点,司法实务中虽然有明确的认识,但却认为:“如果因为驾驶者缺乏上述业务上的注意,使其操纵的汽车冲撞了行人,产生了死亡结果时,就应当构成业务上过失致死罪,即令因此而使具有高速度的汽车丧失其本来的机能,也不能免除其罪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昭和30年,汽车在日本得到迅速的普及,道路和交通设施也逐渐完备,国民的交通道德意识也逐步加强。以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为背景,汽车的社会作用也显著增大,与此相适应,社会广泛地认识到汽车必须要能够快速行驶,从而要求行人应当为不妨碍汽车的行驶进行必要的协助。驾驶者的注意义务被缩小而行人的注意义务相应被扩大这种变化,是以昭和32年5月10 日福冈高法的判决为开端的。该判例认为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行人突然跑到汽车的行驶前方,从而相撞,发生死伤时,行人一方违反了注意义务,汽车的驾驶者没有过失。这样一来,关于汽车驾驶者与行人之间的危险的分配,从过去几乎是使驾驶者一方负担,转而把相当的部分转移到行人一方,减少了驾驶者所负担的危险(注:参见[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7页。)。
适用危险分配理论处理交通事故在日本战前、战后实务中的变化,应当说是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又考虑到处于对立关系的双方利益的平衡。当然,以危险的分配理论确定参与者各自的注意义务,是要求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具体情况。例如,在对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者与行人之间的危险的分配就不同于普通公路。因为,作为汽车专用道路的高速公路,本不允许普通行人进入,所以原则上不发生危险的分配,但是,在行人因故而进入的情况下,行人即使不负担百分之百的危险,也要负担保证安全的广泛的注意义务,而驾驶者的注意义务则大大缩小。而在普通公路上,则与此不同,因为在普通公路上,不仅车要行驶,人也要行走,而且原本就是人行走的场所,所以,行人对汽车的高速行驶的必要协助也是有限度的。因此,牺牲汽车速度,应尽可能保障、顾及行人的安全,则成为对驾驶者要求的注意义务。
另外,在日本,危险的分配的适用也并不仅限于交通事故的场合,而在广泛论及处于对立法律地位的人的过失时,都考虑危险的分配问题。然而最终科以行为人怎样的注意义务,则不外乎是根据具体社会的要求(注:参见[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二、危险分配与注意义务的分担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有关危险分配的理论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践中完全不运用该理论的合理内核确定行为人注意义务的范围。下列案例,对被告人注意义务范围的确定,应当说是体现了危险分配理论合理内核的实例。
甲是某企业的司机,被派车去机场接来洽谈业务的外商,因通知发车较晚甲恐误接,在市郊便以80公里/小时超速行驶,在距事故发生点约十七八公尺时,突然有两名儿童相互嬉戏追打,从行车前方右侧防护林带跑上公路,甲虽然立即采取了紧急制动、避让等措施,但终因距离较近,未能避免,造成两名儿童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经查甲驾驶的汽车车况良好、制动灵活。法院认为被告人某甲应当认识到在市郊超速行驶易发生事故,却对此疏忽大意,以致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但两名被害人,居住在公路旁,根据其本能和生活经验,也应当知道在公路上嬉戏具有危险性,未观察来往车辆贸然跑上公路,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决定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本案中,法院在确定被告人注意义务的范围时,并没有明确提出依据的是“危险分配”的理论,但从本案刑事责任的确定来说,无疑包含着这一理论的合理内核。
笔者认为,在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日益现代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许多社会发展必需的行为所蕴涵的巨大危险性,使得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保障国民人身生命、健康、财产以及环境安全需要之间产生矛盾,将日益尖锐化。如何合理借鉴国外刑法理论中“危险分配”的理论,是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于危险分配的理论,要正确处理保障发展与保卫安全这两者间矛盾,决定于寻找一个适当的结合点,即正确的价值评判。“这种价值取向将对过失犯罪中的危险分配发生重要的和直接的影响。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必然会迷失方向,导致危险分配的分配失衡和判决的不公正。”(注: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根据1997年刑法修订),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当然,我们借鉴、研究危险分配的理论,不仅仅是为合理、正确地确定注意义务的范围,从而公正地适用法律,也应当是“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促进社会的发展。根据危险的分配确认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分担,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第一,该种危险必须是“经验性”的。所谓经验性,是指根据社会实践参与者在客观上对危险的发生有预见可能性。经验证实该类活动确实存在着实害发生的危险,才需对参与者的注意义务实行分担。如果,某种危险只是抽象性的无具体实害结果发生的不安感的危险,也就是说参与者在客观上对危险发生不具有实在的预见可能性,则不能以危险分配确认参与者的注意义务。例如,首次的实验性生产作业中发生的严重伤亡事故,如无经验可言,实害发生的可能性尚无法预见,就不宜以危险分配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过失责任。
第二,实施的行为的危险性,必须是被社会所允许的危险的范围之内。即该类活动虽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应对社会发展有益时,才有适用危险分配确认参与者注意义务的必要。如果行为本身是非法或者是为牟取私利不顾公益和他人利益,就不宜以本意是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危险分配来确认其注意义务。如,违章携带易燃品上火车,被其他乘客不小心引燃,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则不能以危险分配来确认其他乘客、司乘人员的注意义务。
第三,应根据危险性的程度合理地确认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例如,在火车与汽车发生相撞的责任事故中,因火车具有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惯性和制动后不易立即停止的较大危险性,因而相对于火车司机应承担的注意义务而言,汽车司机应承担范围更广泛一些的注意义务。
第四,应当从消除、减少危险发生的目的出发,依据依赖原则合理地确认参与者的注意义务。例如,行人与汽车司机之间的注意义务,根据危险分配的目的,从行人一方来说应承担遵守交通规则,不妨碍汽车正常行驶为目的的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从司机一方来说,应承担遵守驾驶规则、交通规则,以保障汽车能正常行驶为目的,消除、减少危险发生的注意义务。
此外,如果参与者在参与危险活动中本身对危险的发生不可能采取任何避免措施,则对参与者来说,不能依据危险分配确认其承担了注意义务。例如,对手术中的病人而言,手术中失败的责任无论如何病人不能承担。当然如是在手术前,或者手术后有应当由病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如不遵照医嘱,由此而引起手术失败,造成医疗事故,病人自应承担违反相应注意义务的责任。该种情况不同于对危险发生不可能采取任何避免措施,而不分担注意义务的原因在于,参与者具有注意能力。
三、信赖原则在过失中的意义
信赖原则,是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也是直接与过失相联系的刑法理论。
所谓信赖原则(Der Vertrauensgrundsatz )是指当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如果可以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的场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过失责任的原则(注:参见[日]西原春夫:《交通事故和信赖原则》,成文堂1969年日文版,第14页。)。
根据以往理论确认过失责任,行为人如有预见危害结果的可能性,则就有预见义务;如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基于该种预见,就负有避免危害结果的义务。例如汽车驾驶者在驾驶过程中,必须将行人有不遵守交通法规之可能性时刻置于注意的范围之内,为时刻预防行人的违反交通法规行为,就必须予以十分谨慎的态度,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否则就要承担过失责任。例如,德国旧联邦最高法院在确立信赖原则之前,曾在判例中就驾驶员的注意义务作出过如下说明:“汽车驾驶人,因不得期待其他参与交通者皆能采取遵守秩序之正当态度;故常须将‘可能有人突自房屋中或人行道上闯入车道’一事,置于念头。仅在‘其他的利用道路者之粗心大意,自吾人日常生活经验观之,实非可能’之情况下,始能否定汽车驾驶人之过失。”(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2年版,第359页。)这也就是说, 认定过失责任之有无,完全是根据客观上发生了危害结果,行为人有无预见可能以及回避结果的可能,均在所不问,甚至,在上述理由中也包含着“只要是驾驶人皆不可能有‘依日常生活经验观之,实非可能’之认识”这种不顾事实的错误观念,而推定皆有预见可能、回避可能性。但在采取信赖原则后,根据信赖原则,即可在行为时持相反的态度,以信赖其他参与者能够遵守交通法规为原则而实施自己的行为。
信赖原则的理论渊源,是以“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而确认的“危险分配”理论,或者说,“信赖原则”是与“被允许的危险”、“危险分配原则”互为表里(注:参见[日]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95页。)。在司法上的实际运用,肇始于德国判例。“信赖原则是在若干先驱判例的基础上逐渐在德国判例中占取稳固地位的,其中突出的体现是1935年12月9 日帝国法院的判决(RG ST70—71)。 该判决对于电车司机撞倒突然从电车修筑区跳到车轨上的行人一案,认为行为人不构成过失。其理由是,机动车驾驶人没有‘考虑到一切不注意行为’顾虑的必要,只要他有‘对所有事情进行合理考虑而可能预见的不注意行为加以注意’的念头,就是已尽了注意义务。”(注:[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263页。 )从该原则所体现出不要求行为人在行为时考虑到他人应注意的义务,即免除行为人预见他人实施不法行为而避免危害发生的义务,可以说该原则是以“危险的分配”为基础,或者说是“危险分配”一方面的问题。
在该判例实质性采纳信赖原则后,相继得到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判例以及学术界的承认和支持。该原则诞生之初,主要适用于公路交通机动车事故案件的处理,但在该原则理论逐渐成熟后,已广泛适用于重要工业领域、医疗业、医药业、食品业以及建筑业、铁路交通业等领域内的事故处理。目前,信赖原则已经成为运用新过失理论在上述危险领域的事故处理中,从行为实行状态上有无错误、失误(行为无价值),以判断有无违反注意义务,确认过失责任有无以及责任程度的重要标准。
信赖原则在适用上,其前提条件在于行为人自己首先遵守应当遵守的注意义务。从参与交通的行为而言,是指从事交通事业的人(如驾驶员)与一般的行人,均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注意义务(适当分配各自负担之危险的注意义务),如果没有特别的事由,可信赖其他参与者(其他驾驶员或行人)能够遵守交通法规及交通道德,在参与交通时采取慎重注意的行为。如果参与者(其他驾驶员或行人)采取不适当行为,即使因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行为人也不承担过失责任。
日本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造成重大事故的现象日益突出,为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则必须限制其速度,然而,如果限制其速度,则不能使其发挥出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作用。根据“被允许的危险”理论,重新认识、评价,确立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作为高速交通工具地位,成为刑法学术界和司法实务中对信赖原则持赞同态度的思想基础。但是,日本学者认为,在战后的判例中有意识地采取信赖原则否定过失责任之前,事实上在大正时期已经存在这样的判例。而战后有意识采纳信赖原则的判例,最初表现在下级法院的审理中(1955年12月21日名古屋高级法院判例)。最高法院第一次正面适用信赖原则否定过失责任的判例,是数年后的1966年6月14日的判决(注:参见[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240—241页。),而第一次在认定交通事故中的过失适用信赖原则的,是同年12月20日的判决(注:参见[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1966年6月14日的判例是:某私营铁路站的乘务员, 深夜从到站的电车上让醉酒、昏睡的乘客起来、下车,但没有在以后进行监视,结果该乘客掉入线路,被行驶中的电车压死。对于此案,否定该乘务员业务上过失责任的判决有如下说明:“在乘务员使醉客下车的时候,除了是根据该人酩酊前的程度和步行的姿势、态度等其他从外部容易观察的征迹可以判断该人有与电车接触、落在线路中的危险这种特殊情况外,信赖该人会为维护安全、采取必要的行为,是相应地对待乘客就够了。”(注:参见[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240—241页。)
1966年12月20日的判例是:汽车在没有实行交通指挥管理的交叉路口右转弯的过程中,在车道的中央附近熄火,再次发动后以约五公里的时速(行人步行的速度)行驶时,从右侧方行驶的摩托车想从该汽车前方超过,结果相撞,致使摩托车的乘者负伤(注:参见[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39—240、240—241页。)。对于本案,否定汽车驾驶者过失责任的判决理由是:“在本案中,对于汽车驾驶者来说,如果不存在特别的情况,他就可以信赖从右侧方向驶来的其他车辆会遵守交通法规、为避免与自己的车相冲突而采取适当的行动,根据这种信赖进行驾驶就可以了。对于认识右侧一方的安全,预见像本案中被害人的车辆一样,竟敢于违反交通法规,突至自己车辆前方的(其他)车辆,据此防止事故发生于未然,不属于(行为人)业务上的注意义务。”(注:[日]中山敬一:《信赖原则》,载中山研一、西原春夫、藤木英雄、宫泽浩一主编:《现代刑法讲座》(第3卷),成文堂1982年日文版,第80页。 )在此之后,日本最高法院又多次作出适用信赖原则的判决,使这一原则逐渐在审判、检察和警察实践中被确立起来。
可以看出,信赖原则设立的出发点,在于调和公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与社会生活、建设中发挥现代化工业事业作用之间的矛盾,缩小过失成立的范围。虽然上述判例中适用信赖原则,均排除了行为人的过失责任。但从适用目的的实质上看,与其说适用信赖原则为排除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倒不如说是运用信赖原则确认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的行为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的分担。这才是信赖原则的实质意义。这正如将信赖原则首先介绍给日本刑法学界、司法界的学者西原春夫所说的,并非是偶然使用信赖原则否定过失犯的成立,与以前认定过失相比,从有意识地采用信赖原则,在确实缩小了过失成立范围这一点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注:[日]中山敬一:《信赖原则》,载中山研一、西原春夫、藤木英雄、宫泽浩一主编:《现代刑法讲座》(第3卷),成文堂1982年日文版,第80页。)。
当然,还应当看到信赖原则从分担过失责任的基本思想出发,基于社会活动中行为人相互间的责任心以及社会连带感,在彼此能够信赖的范围内,实施的一定行为即使导致结果发生,也不承担过失责任。这就为刑法理论上抽象的“被允许的危险”、“危险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具体化标准。所以,该理论对于我们认定违反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等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的。
四、犯罪过失中信赖原则的适用
日本学者对于适用信赖原则处理交通运输业中的事故的探讨较多,在适用要件上,提出了以下见解:第一,适用的主观要件。首先,必须存在着对其他交通参与者对于遵守交通法规以及交通惯例、交通道德的现实信赖;其次,这种信赖符合社会生活中相当性要求。第二,适用的客观要件。必须存在着信赖其他交通参与者根据交通法规采取适当行动的具体状况。具体说,客观上有以下情况不适用信赖原则:(1 )在容易预见被害人具有违反交通秩序的行为的场合;(2 )因被害人是幼儿、老人、身体残疾者、醉酒者,不能期待其采取遵守交通秩序行为的场合;(3)幼儿园、小学校门前, 道路有雪等事故发生危险性高的场所,以及从周围的状况看不能期待采取适当行为的场合。具有上述客观情况的,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注:参见[日]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96—98页。)。
我国学者对信赖原则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有关交通事故中如何适用信赖原则。例如,姜伟博士对此提出了五类不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况:(1)行为人自己违反注意义务, 不能以相信其他人会遵守注意义务为条件避免危害结果;(2)已发现对方有反常行为时, 不能盲目相信对方会履行注意义务;(3)因某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他人违反注意义务的可能性较大时,不适用信赖原则;(4)发现对方是幼儿、老人、 盲人或其他残疾人而且无保护人陪同时,不适用信赖原则;(5 )对方的违反注意义务行为即将造成危害结果,行为人有时间及能力避免危害结果的,不适用信赖原则。相对于德、日等国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广泛适用信赖原则,他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还不能赞同把信赖原则完全适用于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以及国民交通意识等方面,均不具备信赖的前提(注:参见姜伟:《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38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我国目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来看,笔者认为,在具备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可以考虑适用信赖原则确定过失责任以及责任的分担:(1)存在使汽车高速度并且顺利行驶的必要性。例如, 在高速公路。如果无此必要,如在通过行人密集的街道时,就不能以适用信赖原则为由高速行驶。(2)交通设施以及交通环境状况良好。 如交通环境状况达不到能够使汽车高速并且顺利行驶的客观条件,也不存在适用信赖原则的问题。(3)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道德教育普及。 若无此种普及性教育,也不存在适用信赖原则的问题。当然,信赖原则的适用首先以行为人自身遵守规章制度、交通法规为必要的前提。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自己违反注意义务,意味着失去期待他人会采取适当行为的根据;第二,因自己的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可能诱发他人的错误反映,也想违反注意义务;第三,不能以信赖他人会采取慎重的、适当的行为而允许自己不注意,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我国有学者认为,信赖原则“是基于人们的相互信任心、共同责任心以及‘社会的连带感’而产生的,贯穿于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活动之中”(注:侯国云:《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信赖原则产生的思想基础的分析,无疑有正确的一面,但如主张信赖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之中,则失之过宽。事实上,在德、日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务中,不仅在适用信赖原则上有一定范围的限制,而且在适用上要求有客观上应具备的条件。换言之,也就是“适用信赖原则,需要具备对他人采取适切的态度予以信赖的许多条件”(注:参见[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264页。 )。从司法实务上看,笔者认为,有些事故完全不存在需要以信赖原则确定有无过失责任的问题。例如,狩猎中发现猎物附近有人,轻信自己的枪法,贸然开枪射击,因这种不注意而过失致人重伤、过失致人死亡的案件,没有必要以行为人能否信赖被害人注意不移动,来确认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因此,只有在某些特定的生活领域内的事故,才有必要考虑适用信赖原则确认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的问题。
对于在交通领域外扩大信赖原则的适用领域以及适用和原则,日本学者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很值得我们借鉴。
他们认为,信赖原则能够适用于多数人为实现一定的目的,有组织性的分担协助,共同实行有危险性作业的领域。然而,这里所谓的信赖原则,并非针对被害人而言,而是针对分担共同作业的第三者的信赖,即所谓的分业原则(Prizip der Arbeitseilung)。这就是从个人信赖模式向多数人或者有组织性模式的扩大化。例如,对于企业犯罪、公害犯罪,不仅仅是要考虑业务的直接承担者的责任,是否有必要将过失责任扩大至处于监督者地位和上层领导者地位的人呢?在这里,对界定合理的责任应如何考察问题,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点。第一,这里预先确立各人分担的业务,存在着为保障提高共同作业的效率的信赖这一点,与道路交通不同。第二,业务分担者之间,存在指挥命令或者监督关系的场合,命令者或者监督者负有何种程度的责任,在能证明存在着对他人的行为负有监督的注意义务的范围内,存在着有可能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第三,通常,在客观上已经确定损害发生已经迫近,而他人尚未实行的行为已经不再是问题的全部,对此种状况能够适用信赖原则这一点,与道路交通不同(注:参见[日]中山敬一:《信赖原则》,载中山研一、西原春夫、藤木英雄、 宫泽浩一主编:《现代刑法讲座》(第3卷),成文堂1982年日文版,第86—87页。)。笔者认为,以信赖原则确认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的分担,并非在任何过失案件中都需要适用。从德、日两国关于适用信赖原则的判例分析,笔者认为,可考虑以适用信赖原则确认有无过失责任及其责任分担的领域,除交通运输业以外,其他领域,在适用上应当符合下列几点要求:
第一,信赖原则一般只适用于公认的,对社会发展有不可缺少的巨大作用和利益,但又具有危险性的领域内的事故处理时,确认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第二,信赖原则一般只适用于在多人协力为某一目的,且有一定组织性、并在合理分担各自应当注意危险义务的领域内的事故处理时,确认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第三,信赖原则一般只适用于在有具体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调整的领域内的事故处理时,确认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第四,信赖原则一般只适用于在客观上有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当行为条件的领域内的事故处理时,确认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例如,工矿企业的事故、建筑企业的事故、医药事故、医疗事故以及日常社会活动、生活中符合第三、四点要求的事故。
此外,在行为人有违章行为的情况下,是否适用信赖原则,是值得研究的。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由于行为人自身实行的是违章行为且自己已经认识到的情况下,已丧失了可以使他人信赖自己的基础,因而,也没有理由期待他人能够遵守共同的准则或规则行事。但是,这并非绝对不存在适用信赖原则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以下情况可以考虑适用信赖原则:(1)违章行为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2)违章行为并不具有使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增大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