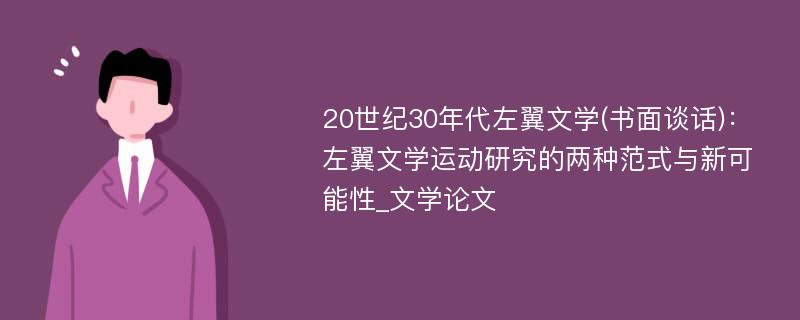
作为问题的30年代左翼文学(笔谈)——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的两种范式与新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笔谈论文,范式论文,两种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和基本格局。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基本都为两种既南辕北辙又暗通款曲的范式所笼罩。
或许是因为“左翼”这个命名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政治立场,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左翼文学的历史似乎从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一视角也构成了迄今为止左翼文学历史叙述的基本框架。不过,对现代文学史学科而言,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若何并非是个歧见迭出的理论问题,而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规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1927-1937年对整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来说是一个“新的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个经典表述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文学史叙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翼文学作为革命文化的一支,总是被置于“围剿”/“反围剿”、“革命”/“反革命”这种非此即彼的框架里来认识。所谓的“左翼十年”,也被描述成一个“我们伟大的奠基者和导师——鲁迅在党的领导之下号召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向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帮闲的走狗们进行坚韧不屈的战斗的年代”[1](P199)。在这里,不仅文学是否具有某种特殊品格的问题从不予以考虑,就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被局限在文学与政治这一个方面,而且这种关系还只是一部“革命史”的简单回声。这种“革命史”的框架特别强调共产党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全面领导,并总是在与国民党政权的对抗性关系(“围剿”/“反围剿”、“革命”/“反革命”)中来确立左翼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然而,当我们试图用这种思路去解释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时,一个当初困扰过成仿吾的问题就再次浮现出来。成仿吾在1928年曾这样描述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革命运动停顿了,革命文学运动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2]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左翼文学运动何以发生的问题,亦即在一个“革命运动停顿了”的时代,为什么“革命文学运动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呢?左翼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一翼,何以却和革命事业的大势正相逆反?不过,成仿吾倒无意(无力?)直面这个难题,只是忧心忡忡地把它偷换成另一个问题——“我们的革命文学为什么落在革命运动这样远的后面?”[2]——便敷衍过去了。反倒是当时作为“敌手”而与革命文学家们论战正酣的鲁迅,把这种政治现实与文学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叙述为一种其来有目的历史过程:
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3]
在这里,鲁迅也如成仿吾那样洞察到中国“革命文学的旺盛”,“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但他并不愿意提供一种抽象化或神秘化的解释。从知识分子与革命斗争的关系角度,鲁迅敏锐地注意到,革命文学从无到有乃是文学家们的实践方式在不同革命阶段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在革命“高扬”时期,他们介入革命的方式是参加各种“实际工作”;当革命遭遇“挫折”,各种“实际工作”已不可能展开的时候,他们则开始“重理笔墨的旧业”或借文学活动暂且“谋生”。革命文学家并非从天而降的“英雄”,而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走出的老将与新兵。换句话说,革命运动虽然一时挫折,但它却为革命文学提供了人员、经验、主题等各种基础。某种程度上,程凯先生最近对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之历史关系的考察,也未始不可以看作是以更翔实的史料坐实和丰富了鲁迅这段简略的描述。
8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步取代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远离革命乃至“告别革命”成为弥漫知识界的普遍氛围,文学史叙述中的“革命史”模式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一系列口号的提出,一种强调文学的艺术性、注重文学的独立价值的“文学”框架开始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占据主流。这种不断“纯化”的文学想像把文学看作是一方“应当”远离政治的净土,在此语境下,左翼文学因其与政治显而易见的联系而备受指责,甚至被视为一种违背了文学自身规律、丧失了文学独立性的“伪文学”和“反文学”。相对于以前总在与政治的关系中来考虑问题,此时对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则更多地在作家、作品、思潮这类“文学”话题下展开。艾晓明那本引人注目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就是试图从“文学思潮探源”的角度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做出解释。这部原名《左翼文学思潮:中国与世界》的著作,从其“中国与世界”的命名方式上就不难看出,作者试图突破过去总在中国语境内部解释左翼文学思潮的范式,把左翼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下,将它的兴起看作是席卷全球的“红色三十年代”风潮在中国的表征。这种“由外向内”的比较文学视角,有时候恰能使我们更好地厘清左翼文学思潮内部的各种分歧,以及它们此消彼涨的演进过程。但饶有趣味的是,像这样一部原本要以比较文学的“外在”视角来重新审视左翼文学运动的著作,却在论述中极少提及左翼文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到头来反而正符合韦勒克文学“内部研究”的标准。这种“内在”视角固然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发展的细节获得较多了解,但也往往会把“多面的历史”单一化,从而影响对左翼文学基本性质的阐释和整体形象的估量。比如,如果剔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迄今我们仍然难以回答诸如“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到底居于何种地位”这样的“元问题”。
不论是把左翼文学运动看作是一个更大的政治运动的产物或者回声,因而具有“政治正确”的天然合法性,抑或是认为左翼文学与政治的深刻纠葛,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纯文学”的自律性。“革命史”的和“文学”的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学史叙述背后,其实分享着同一种看待文学的方式,即它们都始终是在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中界定文学的性质,都始终是在文学与政治的亲疏远近中评判其价值。这与其说是对文学历史做出理解和解释,倒不如说更像是以一种本质主义的先入之见去裁判历史。如果说“文学史始终是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4](P160),那么,这些研究在敞开一些可能性的同时,往往又遮蔽了文学与社会相互连接的更多可能性。比如,近些年来,旷新年先生在其稍嫌仓促的考察中已经注意到,左翼文学的兴起其实得益于一系列物质和文化条件的支持,通过在传统的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引入“现代性”、“文学生产”等新概念,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左翼文学的性质提供另一条途径。
循此思路便不难发现,不但传统的“革命史”或“文学”范式不足以解释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就是那种从人事谱系角度重建左翼文学条件的方式,也仍有其解释的限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为左翼文学的兴起提供一个全息的历史图像,至少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各种潜在的革命文学资源会不约而同地向上海汇聚?为什么恰恰是上海成全了革命文学家们的事业?或者说,上海这座城市为革命文学家们展开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实践准备了怎样的社会条件?实际上,左翼文学运动20年代后期在上海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它是文学激情和意识形态冲动与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的成功“合谋”。上海作为30年代中国惟一的国际大都市,其特殊的政治格局、消费空间和文化氛围,处处为左翼文学运动在彼时彼地的发生与发展准备着外在条件。这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为左翼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所谓左翼文学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首先表现为一种出版运动,因为它首先意味着大量新兴左翼文学报刊、书籍的出版与发行。在现代出版机器的高速运转中,一种左翼文学的声音以理论或作品的形式被“制造”出来,并被导入由出版业构筑起来的文学消费网络。这种声音进而在流通过程中被不断放大和加强,最终回荡成一个强有力的时代声部。在这个意义上,左翼文学运动在它成为一个文学现象之前,也可以说首先是个出版现象。我们固然可以说是“革命文学”论争引发了报刊阵营的混战,但是反过来,也正是《文化批判》、《太阳月刊》、《创造月刊》等七十余种报刊的出版与发行才制造了“革命文学”最初的声音。同时,也正是凭借创造社出版部、春野书店、现代书局、光华书局等六十余家新书店的运营,蒋光慈等人的“革命小说”才可以掀起红色流行风,为左翼文学迅速赢得了大量读者。因此,在“革命史”与“文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对左翼文学运动尝试采取一种“新文化史”的考察方式,或许有助于我们打破文学史和社会史之间的话语栅栏,呈现两者之间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掩盖的流通痕迹。这不同于那种在“文学”内部研究左翼文学运动的方式,而是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重建它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这也不同于那种“围剿”/“反围剿”的“革命史”模式,并不把左翼文学运动与社会的复杂联系简化成文学与政治的单一维度,而是力图展示历史的全息性与多面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做出更加历史化的解释,它通过考察左翼文学与现代出版业、与现代都市的关系,更会使我们在检讨左翼文学之现代性等理论问题时获得一些崭新的理解。
选题策划 张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