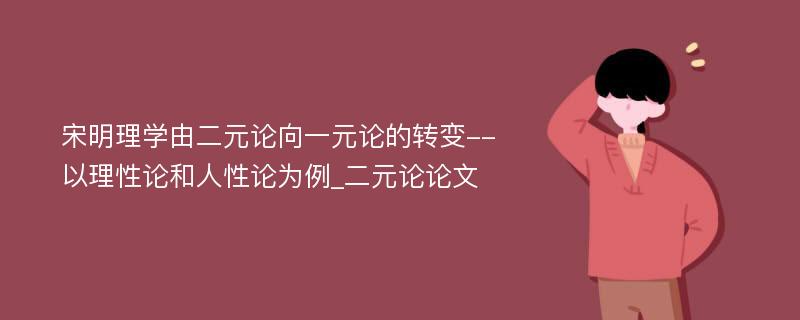
宋明理学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转变——以理气论、人性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论文,为例论文,理学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 在谈到宋代与明代思想的差别时,日本学者冈田武彦曾指出:“一言以蔽之,由二元论到一元论、由理性主义到抒情主义,从思想史看就是宋代到明代的展开。”[1]这种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过渡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即如何成就理想人格以及如何实现理想社会,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宋明理学家的所有理论与工夫都是要弥合现实与理想的鸿沟,套用日本学者荒木见悟的话说就是“本来性”与“现实性”的差距问题。不过,宋明两代理学家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前者更强调高远理想对现实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从而更富有二元论的倾向;后者则更加强调理想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生命及世界的认识与实践之上,从而一元论的倾向更加明显。 为了解释“本来性”与“现实性”的差别,宋代理学家发展出理气论。二程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用它作为构建理想人格与社会的理论基础。张载则建构了一个以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用气的聚散循环来解释宇宙的生化以及人性的形成。朱熹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以理气二元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1)在朱子的理气论中,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理是“本来性”的根据,气则是“现实性”的原则。理与气的结合就可以解释理想与现实的各种问题。一方面,为了说明“现实性”,朱子特别强调理与气的结合,即理气“不离”的一面。基于此,朱子强调要广泛地探究事物中所包含的天理(格物穷理),不能离事言理,而要“即物穷理”。另一方面,为了强调“本来性”,朱子又特别强调理气“不杂”,突出理的超越性与规范性,这在朱子的论述中经常表现为“理在气先”、“理生气”等命题。理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朱子有意识地维持这种张力,从这方面看,朱子的理气论的确有二元论的倾向。(2)在人性论上,朱子也坚持天命之性(后来的朱子学者有时又称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天命之性来源于理,可以说是人的“理性”;气质之性则是理堕入气质中形成的现实人性;天命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同样构成了二元的存在。(3)朱子的心性论也是如此,心与性也是一种二元的结构:心是一个经验概念,而性则是一个先验概念,心属于“现实性”,性属于“本来性”,可以说“性即理”,但不能说“心即理”。(4)性情关系也是如此,朱子坚持“性体情用”:性是无为的、不动的、深藏于内心的道德本体,是未发,而情则是性的发用及外在表现。(5)在工夫论上,朱子也将人心区分为相对静止(未发)与明显活动(已发)两种状态,未发时要用“存养”或“涵养”的工夫,已发时要用“省察”与“克治”的工夫,这就是朱子“静而存养”、“动而省察”的二元工夫论。 因此可以说,二元论贯穿于朱子整个哲学体系中,朱子正是通过这些概念间的二元互动来维持“本来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2] 然而到了明代,作为事事物物之“定理”的客观而高远的天理却受到了质疑,学者们发现这种天理观与人的富有生趣的生命及丰富多元的现实日益远离。随着程朱理学因官学化而日益教条化,这种客观的天理变得越发与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心相隔膜,从而丧失了在道德实践中的规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有见识的学者一方面批评知而不行的“假道学”,另一方面开始重新思考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心与道德规范的天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以王学(阳明学)为轴心的明学,就在这样的风潮中发生、成长起来,这从王阳明所倡导所谓的心学、提倡具有一元论思维结构的心性论和理心论可以窥见其底蕴。”[3] 从明初开始,学者就很重视心与理的关系问题,陈白沙即从思考“此心与此理”的关系开始其心学之路。他早年跟随吴康斋学习,广泛地研读圣贤之书,但是终觉无所体会,“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明儒学案》,卷五)。所以他后来放弃读书,专心静坐,并通过静坐证悟到了心体,开启了心学之路。王阳明早年儒学思想的进学之路则是从探究朱子的格物穷理思想开始的,他少年时连续七天穷格父亲官署中竹子而致病的痛苦经历,预示着朱子格物穷理之学所蕴含的内在困难:穷格一草一木之理如何能够诚得自家的意念,也就是穷格外物之理如何能够与道德实践发生关系,这实际上也是陈白沙所思考的心、理关系问题。在经过了九死一生的艰苦磨难之后,阳明终于在龙场彻悟格物致知之旨。原来物理不在心外,就在自己的心内,心就是道德原理与法则的源泉;“心即理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明儒学案》,卷十)人心具有道德原理,是道德的主体,同时人心又是灵活的、变动不居的,可以因应不同的客观形势作出恰当的反应。放弃对自心之理的认识,去追求客观、外在的物理,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必然会与真实的生命、活泼复杂的现实发生背离。 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次年开始提倡知行合一,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很多士人知而不行、忽视实践的弊病。他认为知行在本体上是合一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明儒学案》,卷十)。真正的道德认识必然与道德实践不可分离。而在他提出“致良知”宗旨之后,良知就成了道德本体,致良知就是道德实践的工夫,通过“致良知”,本体与工夫合而为一。致良知工夫贯穿生活中一切状态,静时要致良知,动时也要致良知,工夫只有一个,更不分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性气也是合一的:“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4]人心道心也是合一的:“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明儒学案》,卷十) 总之,凡是在程朱理学中二元性的概念,在阳明处皆合而为一,以致刘宗周在评价阳明思想时说:“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明儒学案·师说》) 除了阳明学的一元论兴起以外,明代的朱子学实际上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更加重视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二元性的倾向也在削弱。其中,从二元论到一元论过渡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当属理气论。汪晖指出:“在整个明朝时期,思想家们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攻击、批判和摆脱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从心和物(气)这两个不同的方向追求心一元论或气一元论,以弥合理与气的分离。”[5] 在明代中期,大约与阳明同时,朱子学理气二元论开始受到质疑。作为明代最有名的朱子学者,罗钦顺质疑了程朱的理气论: 盖朱子尝有言曰,“气质之性,即太极全体堕在气质之中”。又曰:“理只泊在气上”。仆之所疑莫甚于此。理果是何形状,而可以“堕”,以“泊”言之乎?“不离”、“不杂”无非此意,但词有精粗之不同耳。只缘平日将理气作二物看,所以不觉说出此等话来。[6] 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7] 罗钦顺指出,程颐“所以阴阳者道”、“所以阖辟者道”的说法,朱子太极全体堕入气质之中形成气质之性的说法,以及“理泊在气上”、理气“不离”、“不杂”、“理与气决是二物”等说法,都有将理气看作二物之嫌。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所以名也。……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殆不可易之言也。[8] 理只能是气中之理,只可从气的往来运动的转折处体察其存在,“理须就气上认取”。理是气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据,而不是气中作为气之主宰的另一个实体。他反对“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之说,认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散,是乃所谓理也”(《明儒学案》,卷四十七)。即理就是气聚散的规律或条理,而不是与气的聚散相分离的孤立、静止的实体。 与罗钦顺同时,坚持理气合一的学者还有甘泉学派的王道: 或问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理气之别何居?”曰:“奚别之有哉?盈天地间,本一气而已矣。方其混沦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极。迨夫酝酿既久,升降始分,动而发用者谓之阳,静而收敛者谓之阴,流行往来而不已,即谓之道。因道之脉胳分明而不紊也,则谓之理。数者名虽不同,本一气而已矣。”(《明儒学案》,卷四十二) “理气不杂不离之说非歟?”曰:“非也。黑白相入曰杂,彼己相判曰离,二也。气之脉胳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为物不二也。杂与离,不可得而言矣。”(《明儒学案》,卷四十二) 王道认为,气是宇宙的本体,充满整个宇宙,在宇宙没有分化的阶段,气只是混沦一团,这种混沦一团的气就称为“太极”。这与朱子将太极视为理的看法显然不同。由太极之气分化出阴阳,阴阳不过是一气的屈伸、“流行往来”,这一过程的总体就是道,而理则是其中的具体条理。可以说道是总名,理是细目。因此,太极、道、理不过是同一气从不同方面的称谓。理既然是气之条理脉络,则理气其实是一物,朱子理气“不杂不离”的说法,就有二物之嫌,因此是不对的。 同样,汪石潭也怀疑朱子的理气二元论:“朱子分理气两言之,曰‘得气以成形,得理以为性’,恐非程、张本旨。”(《明儒学案》,卷四十八)崔后渠也说:“朱子谓‘气有聚散,理无聚散’,窃所未详。”“理者,气之条,善者,气之德,岂伊二物哉?”(《明儒学案》,卷四十八)黄泰泉也认为朱子判理气为二是未定之论,批评朱子理乘气犹人乘马之喻,并指出“气之有条不可紊者谓之理”(《明儒学案》,卷五十一)。 王廷相是明代气学的一位大家,他创立了一个以气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程朱理学家认为太极是理,而王廷相则认为太极其实就是“元气”,由元气产生万物,万物皆禀受元气的一部分而生。在理气关系上,他认为理其实就是气的具体秩序与或规律,所以理必须视气的存在为转移,“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9]。就每一个具体事物或现象而言,它们也都有自己的存在原理:“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个差别。”[10] 一般而言,阳明学者比较注重探讨心性问题,对客观的理气论兴趣比较淡薄。不过,在阳明学者中,也有对理气论感兴趣的人,如《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中的杨晋庵: 盈宇宙间只是一块浑沦元气,生天生地,生人物万殊,都是此气为之,而此气灵妙,自有条理,便谓之理。盖气犹水火,而理则其寒暑之性,气犹薑桂,而理则其辛辣之性,浑是一物,毫无分别,所称与生俱生,与形俱形,犹非至当归一之论也。(《明儒学案》,卷二十九) 杨晋庵认为气是宇宙万物存在、生成的本体,而理不过就是气的条理、属性,气与理“浑是一物,毫无分别”,即使说两者同时产生,仍然有二物之嫌。 南中王门的唐鹤征也说: 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极也,太和也,皆气之别名也。自其分阴分阳,千变万化,条理精详,卒不可乱,故谓之理,非气外别有理也。(《明儒学案》,卷二十六) 他认为气充满宇宙,是宇宙生化的根本,所谓的太极、乾元、太和这些概念都是用不同的名称指称气。气变化自有其条理,此条理即为理,气外别无理。这一论说与王道的看法非常相似。 到了明末,倾向王学的刘宗周的理气一元论立场更加鲜明。他激烈批评“理生气”的二元论说法。 或问:“理为气之理,乃先儒所谓‘理生气’,何居?”曰:“有是气方有是理,无气则理于何丽?但既有是理,则此理尊而无上,遂足以为气之主宰,气若其所从出者,非理能生气也。”[11] 刘宗周意识到“理生气”的说法与“理宰气”的说法有某种联系。他承认理的重要性,认为理可以主宰气。在“理宰气”的过程中,理在逻辑上可以说具有优先性、重要性,气在其主宰下活动。这样看来,气好像是从理中生出一样,但实际不然。刘宗周说:“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12]理就是气本身所具有的条理,既不是时间上先于气的存在,也不是空间上外在于气的实体。 可以看出,在明代的确存在一个理气一元论的潮流。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明代学者对于宇宙论方面理气论的关注,或明或暗地是针对朱子的理气论。他们中的有些学者深受张载的影响,用张载的气一元论来反对朱子的理气二元论。如王廷相的气论就继承了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先生主张横渠之论理气,以为‘气外无性’,此定论也”(《明儒学案》,卷五十)。唐鹤征的气论也受张载影响,他说:“盈天地之间,只有一气,惟横渠先生知之”(《明儒学案》,卷二十六)。 明代中后期这个潜在的气学氛围,就直接的理论来源与对象而言,与朱子、张载有关;若抛开纯哲理层面的探讨,将其置入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则气学及理气合一论的兴盛,也许与明代人重视实践、重视情感的倾向有关。明代的郝敬批评理气二元论与佛老之学有相似之处,认为理气二元论可能导致在实践上脱离现实世界而别求空静之理,违背儒家下学而上达的宗旨。 道不离宇宙民物,二氏言道,出宇宙民物之外,理学言道,藏宇宙民物之中,圣人礼乐即道,四科即学。二氏以民物为幻,以空寂为真,故道出于世外,理学以有形为气,以无形为理,故道藏于世中。二氏不足论,儒者学为圣人,分理气为二,舍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别求主静穷理,岂下学而上达之本教?(《明儒学案》,卷五十五) 这说明对理气一元论的重视不仅是理论思辨的需要,而且包含实际的社会关怀、实践需要。 与理气一元化趋向相联系,在明代中后期也存在一个人性一元化的潮流。作为朱子学者,罗钦顺不仅质疑了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也质疑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气质而言之矣,曰气质之性,性非天命之谓乎?一性而两名,且以气质与天命对言,语终未莹。”(《明儒学案》,卷四十七)他认为,天命之性离不开具体的气质,脱离具体的气质则无所谓性,因此气质之性也来自于天命,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只不过是同一个性的两个不同的名称,并不对应两个不同的性。所以将气质与天命对言,这一说法本身就有问题。他认为用“理一分殊”来解释人性最合理: 窃以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盖一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语其一,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其殊,故上智与下愚不移。圣人复起,其必有取于吾言矣。(《明儒学案》,卷四十七) 罗钦顺的“理一分殊”所讨论的内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就人作为一个类而言,有其共性或潜在的可能性,此为理一,因此可以说人人都“性善”,都可以成为圣人;但就每一个个体而言,由于所禀有的气质不同,所表现的现实人性也不一样,此为分殊,分殊则有善有恶。“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明儒学案》,卷四十七)只有将“理一”与“分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解释人性的“本来性”与“现实性”,从而避免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所可能带来的理论困境。 王廷相站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指出不能离气言性。他认为气质之外别无本然之性,追求形气之外的本然之性既是一种支离(本然之性与气质分而为二)的做法,同时也是一种虚无的见解(脱离实际的气质,本然之性则是虚无飘渺的存在),与佛氏没有差别:“故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论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涂。是性之与气,可以相有而不可相离之道也。……所谓超然形气之外,复有所谓本然之性者,支离虚无之见,与佛氏均也。可乎哉?”(《明儒学案》,卷五十) 一般而言,阳明学者基本上是人性一元论者。江右王门的邹东廓说: 天性与气质,更无二件。……先师有曰:“恻隐之心,气质之性也。”正与孟子形色天性同旨。……气质与天性,一滚出来,如何说得“论性不论气”。后儒说两件,反更不明。除却气质,何处求天地之性?(《明儒学案》,卷十六) 他明确反对宋儒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论,并说明他的这一思想来自阳明,在《孟子》中也能找到文献依据。天命与气质不是“两件”,它们同时产生,离开气质,即不存在天地之性。东廓弟子胡直也说:“由是观之,性是性,气质是气质,又乌有气质之性哉!且古未闻有两性也。”(《明儒学案》,卷二十二)他也反对二元的人性论,并否定“气质之性”的说法。 江右王门的章本清同样认为: 夫人不能离气质以有生,性不能外气质以别赋也。谓气即性,性即气,浑然无别,固不可。谓气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气,不免裂性与气而二之,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而自二其性哉!……谓气质天性可也,谓气质之性则非矣。谓人当养性以变化其气质可也,谓变化气质之性以存天地义理之性则非矣。(《明儒学案》,卷二十四) 他明确主张性气合一,反对宋儒将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性论,指出“气质之性”的说法有问题,并认为变化气质之性以保存天地、义理之性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在人性论上,王门后学大多认为他们承接了孟子“形色天性”的思想,一般来说,他们并不认为恶有先天的气质根据,因此他们往往将恶归因于后天的习染。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否定宋儒将性划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进而将某些恶归结为先天气质的看法。尽管王门后学也承认存在与生俱来的气质,承认变化气质的必要,但并不认为气质是恶的先天来源。他们认为,人只要能够保养自己的善性,则气质会随之而变化;性只有一个性,即性善之性,气质自是气质,尽管性与气质不能分离,但人性中绝不存在一个与气质的不同相联系的气质之性。“不齐者,气质也,非气质之性也。”(《明儒学案》,卷二十四)泰州学派的周海门进而认为,如果承认一个与气质相联系的可善可恶的气质之性,那么就等于肯定恶有先天的来源。在他看来,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宋儒的说法容易让人将恶推给先天的气质之性,从而放弃道德修养的努力。 问“气质之性”。曰:“孔子只曰‘习相远也’,孟子只曰‘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言习,言陷溺,分明由我;言气质之性,则诿之於天矣。”曰:“气质之性亦只要变化。”曰:“言习在我,则可变化;言气质之性天赋,则不可变化。”……曰:“然则气质无耶?”曰:“气质亦即是习,自气自生,自质自成,无有赋之者。夫性一而已矣,始终唯我,故谓之一。若谓禀来由天,而变化由我,则成两截。孟子曰:‘非天之降才尔殊也。’言有气质之性则殊矣。”(《明儒学案》,卷三十六) 值得注意的是,周海门与章本清不谋而合,都否认“气质之性”的说法。周海门认为气质来自于后天的习染,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加以改变。如果认为存在天生的气质之性,而且这种气质之性有待人的改变,那么天与人的连贯性就会被打破。况且,根据孟子的说法,每一个人天生的材质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承认有气质之性的不同,则与孟子的说法相悖。 卢冠岩不是王门学者,但也同样批评“气质之性”:“性只是天地之性,无所谓气质之性,性无不善,其为不善,气杂之也。”(《明儒学案》,卷五十四)“性即太极,气只是气,不可复言有气质之性。说着个性,即无不善,其为不善,气有杂糅,而性为所累耳。”(《明儒学案》,卷五十四)性即是天地之性、即是太极,只是善,没有不善,不善来自气的不纯粹。气质与性无关,“气质之性”的概念是不恰当的。站在性气合一的立场上,他甚至肯定告子的“生之谓性”的说法,认为这是先秦古义,并非告子的个人见解,孟子对“生之谓性”的批评是值得怀疑的:“孟子道性善,以生为气,而深闢之,是气之外又别有所谓理者,不分理气为二乎?”(《明儒学案》,卷五十四)意思是说,孟子批评“生之谓性”,将生视作气,同时强调性善,则可能导致性与气的分离,这无疑是承认了理气二分。 东林学派的钱一本也质疑宋儒的“气质之性”概念,认为它不符合孟子性善的思想:“程、张气质之性之说,于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线。”(《明儒学案》,卷五十九)孙慎行亦批评宋儒“气质之性”的说法: 孟子谓“形色天性也”,而后儒有谓“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气质独非天赋乎?若天赋而可以弗性,是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谓“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后儒有谓“论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是“有性不善”与“可以为不善”之说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荀子矫性为善,最深最辨。唐、宋人虽未尝明述,而变化气质之说,颇阴类之。(《明儒学案》,卷五十九) 宋儒提出气质之性概念的本意是想解释为什么人天生就有善恶的差别,他们认为那是由于人们先天所禀气质不同造成的,宋儒将这种因先天气质不同而造成的现实人性称为气质之性。按照这个理解,部分人的先天气质中就可能包含负面的因素。孙慎行则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孟子的思想,他指出,孟子“形色天性”的说法表明,人的感性形体也是来自天赋,也属于天性。但根据张载的说法,气质之性不能被称为性,而是被改造的对象,这就等于说天赋的东西可以被改变,照这样的说法,天命之性也能够被改变。孟子还认为不善并不来自于人的天生材质,而宋儒则认为有些人的材质天生就是“下愚”,这等于承认人性中包含源于气质的先天之恶,从而根本违背了孟子的性善说。某种程度上,宋儒的这些看法与荀子有暗合之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后天的人为来改变其本性,使其向善,宋儒“变化气质”的说法恰与之相似。 今若说富岁凶岁,子弟降才有殊,说肥硗雨露,人事不齐,而谓麰麦性不同,人谁肯信?至所谓气质之性,不过就形生后说,若禀气于天,成形于地,受变于俗,正肥硗、雨露、人事类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谓习耳。今不知其为习,而强系之性,又不敢明说性,而特创气质之性之说,此吾所不知也。如将一粒种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气,生意显然成像,便是质。如何将一粒分作两项,曰性好,气质不好。故所谓善反者,只见吾性之为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气质之不善,而复还一理义之善,则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谓性否?(《明儒学案》,卷五十九) 孙慎行认为,宋儒所说的气质之性是对孟子的误解,是把本来属于习染的东西看作了气质之性。孟子说得很明白:人的先天材质并没有差别,善恶的差别均来自于后天的习染,因此,不能将现实的恶归根于气质。究极而言,性与气质是合一的,气质是性的外在表现,所以气质也应该善。就好比一粒种子,生意是性,生意的流行就是气,生意流行形成可见的苗芽则是质,因此,性与气质不可分离。宋儒变化气质的说法,认为人天生有源自气质的恶根,应该化除,然后义理之性才能显现,这是一种二元人性论。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义理离开气质就失去了载体,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是指同一对象。 黄道周也反对气质之性的说法: 气有清浊,质有敏钝,自是气质,何关性上事?水以润下为性,流者是气,其丽于土而有轻重,有晶淖,有甘苦,是质,岂是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亦就理上看来。(《明儒学案》,卷五十六) 他认为性就是理,纯善无恶,气质与性无关。气质虽然与性无关,但却是性的附丽之所,不可将其分而为二,“性无所丽,丽于气质”,“故言气质,而心性即在其中……不可分天命为理,气数为数,犹不可分性为理,气质为质也”。(《明儒学案》,卷五十六) 刘宗周也说: 只为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分析后,便令性学不明,故谓孔子言性是气质之性,孟子言性是义理(一作“理义”)之性。愚谓:气质还他是气质,如何扯着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清浊厚薄不同,是气质一定之分,为习所从出者。气质就习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气质言性,是以习言性也。[13] 他严格区分气质与性,认为性是气质中所指点的义理,而不是气质就是性。人自出生以后就有清、浊、厚、薄等不同的气质,它们是各种习性产生的根源。因此,气质在人性论中的作用是为习提供基础,而不能将其看作性。气质之性的说法,实际上是把本来属于习的东西当成了人的本性。 刘宗周从这种一元人性论出发,甚至否定“义理之性”的说法。他说: 程子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是性与气,分明两事矣。凡言性者,皆指气质而言也。或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如曰“气质之理”即是,岂可曰“义理之理”平?[14] 在刘宗周看来,天地间只有气质之性,即“气质的本性”,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个“义理之性”。而且从“性即理”的理学定义来说,“气质之性”与“气质之理”的说法是等价的,但是“义理之性”转化为“义理之理”的说法,却会存在问题。因为义理本身就是理,故而“义理之理”的说法是同义反复,没有意义。 可以看出,与理气一元化倾向相联系,在中晚明理学中也存在一个人性一元论的潮流。坚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不仅有阳明学者,也有朱子学者,还有受张载气学思想影响的王廷相,以及东林学派的学者及刘宗周。尽管他们反对天命之性(或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元人性而主张性气合一的主张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共同走上了一元人性论的途径。另外,除罗钦顺、王廷相以外,上述学者共同表现出一种向孟子性善论回归的倾向。他们中的很多人反对宋儒“气质之性”的说法,认为性只有善,不善没有先天的气质来源。站在孟子“形色天性”、性气合一的立场上,甚至可以说气质就是人类善性的载体,性善气质也善,所以变化气质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中晚明理学的一元化思潮不止上述两方面,之所以重点论述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它们表现得较为突出。实际上,除此之外,在人心道心、性情、理欲、本体工夫等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一元化倾向。沟口雄三总结说:“在明代,还有更值得注意的思想潮流,那就是主张理气一元的意思,以及主张道(形而上)与器(形而下),道心与人心,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相互关系的相即不二关系。”[15]嵇文甫也总结了晚明思想发展的几个明显的趋向,其中之一就是反对理气二元论而主张理气一元论。他还指出,就上述几个趋向深求一层:“尚可以看出一个总趋势,即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是也。……从体到用,体虚而用实,从理到气,理虚而气实。……这各种现实主义倾向渐渐汇合成一大潮流,于是乎清初诸大师出来,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16]上述一元化运动一直延续到清代,最后转变为对宋明儒本体、心性观念的排斥,而走入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并最终实现了儒学范式的转换。标签:二元论论文; 一元论论文; 儒家论文; 人性论论文; 人性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理学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国学论文; 明儒学案论文; 刘宗周论文; 宋儒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