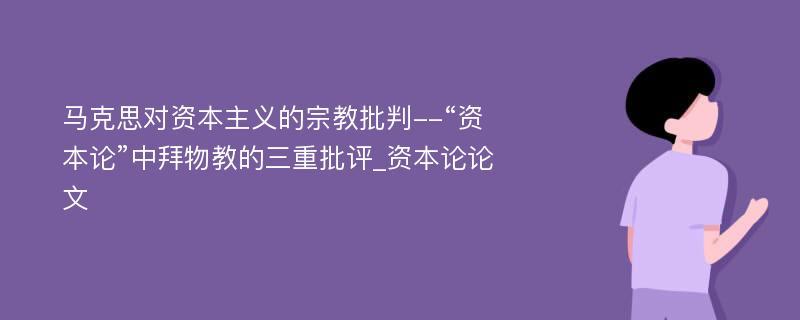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批判——《资本论》的三重拜物教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物教论文,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5-0018-08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得出结论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①以此与其过去的哲学信仰作一了结。现在,马克思把研究重心转向了政治经济学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之上,就宗教本身而言,在之后这一长段时期之内,主要是被马克思当作意识的产物和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一并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而就此后所谓成熟阶段的马克思来谈论宗教批判,表面上看似乎有隔靴搔痒之嫌,但其真正意义在于:此阶段系马克思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学的经济批判中,一方面来实质地推进理论的、天国的宗教批判所要求的现实的、尘世的社会批判,另一方面则是用宗教批判中所抽离出来的宗教异化之理论结构来帮助呈现经济异化之实际状况。“泰米斯托克利斯(即马克思自己)在雅典城(即哲学)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元素上(即在政治和经济实践的元素上)建立新的雅典(即一种崭新的哲学)。”②既然新的雅典城已经找到地方,再到旧“雅典城”里进行宗教批判已经不能为挽救雅典人的命运再贡献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他现在开始全力清理地基来建立这个新的雅典城。这一个工程是浩大而繁琐的,而且不时地要应对敌人的新的侵袭。《资本论》是这一工程最主体的部分,宗教批判所呈现的结构性功能尤其体现在其中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层层深入的批判。
一、宗教批判与《资本论》
同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马克思考察宗教的方式与涂尔干、韦伯截然不同。揆诸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马克思几乎对人类的具体宗教没有任何实质性关注,以至于学者甚至质疑马克思虽奢谈人之现实与未来,却无视于人之基本文化处境。马克思几乎是现成地挪用了费尔巴哈从人本学上考察宗教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哲学的发挥——纯逻辑的加工。而在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如若与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对比,作为文化主体之宗教则远远逃逸于其直接研究的对象之外,其主旨更是远离宗教议题,如是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批判将何从谈起呢?资本主义批判是否纯属一政治经济学议题?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宗教批判的终结和转向,马克思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超越,在马克思宣言式而非求证式的语言中,“超越”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其实是一种后退,“也就是从神话退回到现实”。③马克思非但没有将要求终结的宗教批判束之高阁,而是要求退回到宗教意识的现实前提,并在宗教与世俗的张力当中用宗教中的异化结构来深入剖析人与社会的现实异化,并由此在批判深度上超出他的论敌和朋友。《资本论》把宗教批判“道成肉身”转化成了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用青年时期宗教批判中所呈现的异化作类比,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产生的复杂的异化状态,在此宗教批判成为支撑其资本主义批判的结构指引。另一方面,他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本身当作一种最真实、最深度的宗教批判,这种生产关系本身就是现代社会最大的宗教,它只有在宗教批判中才能揭开其神秘面纱。
就前一方面而言,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导言”中谈到《资本论》的最初方案时,马克思谈到历史自身的自我批判性,即历史的最后形式跟之前形式的批判性关系时是以宗教为例的:“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④
就更为重要的第二方面而言,同样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时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的宗教性,它的内在经济活动的辩证法是神学的辩证法:
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财富本身,即资产阶级财富,当它表现为中介,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中介时,总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而同两极本身相对立;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⑤
神学“三一辩证”的中介关系本身就是资本之为生产与流通、产品与货币的中介、金融家之为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中介的直接写照。而通过宗教批判来支援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纯粹出于学科之间外在的、偶然的相似性,而因为两者实质都关系着人性之最深沉的情感。1867年,马克思年届五十,在流亡英国多年之后,《资本论》第一卷在经历长年反复修改之后终于面世,这是对十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更加深思熟虑、更加系统严密的发挥。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说: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⑥
自由的科学研究,像物理学家研究自然过程一样纯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困难性恰在于它对人类生活的支配性力量,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上寄托了无数人的爱恨情仇、欢喜悲忧,寄托了他们的欲望、生命、意义、希望,以至于对它的研究本身都会招致复仇女神的反对。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物质事实,它关乎信仰,经济与其说承载着人之生存,毋宁说承载着人之希望,拯救之希望。正是在此希望面前,宗教教派的信条和天国里头不会锈坏的财宝在一把火就能点燃现金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曾经不符合教会教义方式谈论太阳和地球的位置关系会被送上火刑架,而今“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接着马克思坦率地说:“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这个“但”字巧妙地提醒了宗教神学家不要忘了在他们不讲道、不写作的时候,上帝到底离他们有多远。进步无可怀疑,“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时隔二十年后,这位饱读史书也饱经沧桑的思想斗士虽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但是已经不再像在《共产党宣言》中那样用缺乏耐心的语调进行讲述了。⑦序言中所包含的对宗教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则以一种方法类比的形式内化在了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各个环节中。
《资本论》某种意义上可算得上是马克思的《精神现象学》,虽然马克思认为他在其中把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颠倒了过来使之成为了现实的、革命的辩证法。可以说,马克思早年宗教批判所呈现的异化的结构特征,继续体现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当中。在这里,一方面,宗教异化结构为马克思从商品这个元素开始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参照,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产生过程研究及其内在本质的发掘,又进一步证实了之前的宗教批判所发现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结构本身。与这两方面相对应的是,基督教《圣经》的隐喻在《资本论》中的运用,以及基督教三位一体辩证神学的发挥。因此,在《资本论》中,宗教批判既是作为前提出现,也是作为结果呈现出来的。
二、商品拜物教批判
宗教批判在此首先表现在对商品拜物教性质揭示当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谈到:“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这一怪诞性不是因它是作为使用价值而显得神秘,比如木头可以做成桌子,或者桌子可以看作木头,或者作为用餐用的餐桌,因为就使用价值而言,它就是人的直接感官经验可以触及的物。其神秘性是当它一旦成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作为某个关联中的中介,并且是既普遍又特殊的中介,那它“就转化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⑧在自然社会中,有用性是交换性的基础,交换不过是由有用排成的物品的属性,而在以商品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社会中,两者的颠倒发生了,从使用价值而来的交换价值转而支配着整个有用价值本身,一切都是为了交换才产生出使用价值来,就像在宗教中的颠倒一样,人头脑的幻想的产物统治了人的头脑。就像耶稣作为木匠约瑟和玛利亚之子是没什么神秘,但是一旦他被看作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之子,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基督,是被差遣来作为弥赛亚,而且在他一旦被看作上帝与人之间中保,那么他就成了最直接、也最神秘的启示了,他既是人,又是神,最后,这个木匠之子就成了一个宗教的象征,他肩负着拯救一切罪人的使命,他承载所有受苦难煎熬的生灵的拯救和永生的希望。所以马克思说: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⑨
商品拜物教的谜底揭开了,它就是人自己的无生命的产品,只是在它融入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后,在人的普遍的构想当中才成为有生命者,成为有灵魂者。拜物教的本质是人的异化了的本质,那么一般宗教也一样。而就宗教本身之为意识形态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关系来看,与商品内在的宗教异化形式相应的是商品世界也确实具有它自身适宜的宗教形式,马克思接着说,“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⑩
因此,在《资本论》中,宗教批判的现实意义得到了真正的落实。既然要消灭宗教,就必须消灭需要以宗教作为慰藉的那个世界,而要消除商品拜物教,也就需要消灭它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即社会生产关系。反之亦然。马克思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与此同时,“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11)这种物质条件的改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决不可误解为自然而然的产物,不论是经历暴力革命还是和平的改革,痛苦的过程总是免不了的。
三、货币拜物教批判
其次就是货币拜物教,在对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中所展现的宗教批判形式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是一致的,但是货币以及到后面的资本阶段,它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幻想的意味更浓也更明显了。货币和商品一样,自身就是作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而出现的,但是它拜物教性质,即它所体现的宗教异化形式表现得更显眼。
商品的神秘性、宗教性的根源在于它进入流通,进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中才出现,而且它本身作为社会关系的实质变成物的性质,这种物的性质本身需要精神才能获得普遍性,正如商品流通需要货币才真正具有普遍性,因此,迎合这一关系物的迫切需要,货币就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了。而如果从社会发展历史看,货币的出现也是在商品社会发展到较高程度才出现的。因为它的一般性,并且从具体的一般性到抽象的一般性(从货币到货币符号),货币的出现成了支配商品世界里的“王”,从而使得商品被赐予了权柄并获得了“精神”生命。“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启11:1)。但是,货币的出现无疑是作为这一流通过程的价值表现,因此它原本不过是一种可供共度的方便手段,不过是一个中介:
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有一种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12)
作为这种流通的中介(圣子)出现的货币,因为它的自然属性满足了公度手段的需要,它逐渐就被看成了纯粹的价值,金、银自从作为成为货币,它们就不再是本来的金属了,它们就是绝对价值本身,就是财富和肉体的拯救,这是货币自身的颠倒。拿撒勒的木匠之子耶稣成为了弥赛亚之后,他就不仅是这个人子了,他是犹太人的王,是万民的福音,他是人子与圣父之子、人性与神性的绝对统一,换句话说,他的肉身存在就抽象成为道本身,成为观念的存在。而货币也就是这种两重性,它既是肉身所成的道,它本身也是道成肉身。商品在货币面前自身的实体性就完全解构了,而纯然成为观念的价值体现,犹如人之为上帝肖像,而货币本身之为商品价值的价值的抽象化身,它自身也可以抽象化、符号化,比如上帝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的符号化,十字架符合本身就成了上帝在想象中的临在,即如金“也可以仅仅用想象的或观念的金”。(13)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货币的这一两重性: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所以,只有在那些从货币的完成的形态出发而从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是商品”才是一种发现。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规定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金银的价值是想象的。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误解里面包含了一种预感: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但是,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这是十八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们还不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时,至少暂时把这种形态的奇异外观除掉。(14)
在货币的这一两重性中,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商品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以货币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颠倒。这也是经济学话语所表述的基督教发展史,通过耶稣,基督教完成对犹太教上帝的抽象化并从民族宗教摇身一变成为普世宗教,同时也实现了天国对尘世的颠倒。循此思路,货币所具有的拜物教性质就变得更为显眼了:“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酌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迷,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5)
随着社会由商品拜物教向货币拜物教演进,社会生产关系在货币的闪光之下进一步被掩盖了起来,世界历史因为基督教的出现就演变成了一段救赎历史,尘世间的一切关系在道成肉身的一刹那就彻底掩盖起了其真实面目,从此就是在耶稣启示的照耀下等待末日审判和救恩的到来。货币的出现,解救了商品本身的局限性——商品的复杂的多样性、脆弱的有用性和有线的流通性,总而言之,它作为差异性的“罪恶”(《旧约》中,这种差异性本身成为上帝恩典的丧失,成为人的异化和原罪)通过货币将得到和解与拯救,就像犹太人“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罗2:19)——和商品社会的局限性。因此,随着货币最后作为绝对价值出现,一切零散的、不起眼的商品都在货币面前获得了表现自身价值的形式。资本主义借使徒约翰之口在《启示录》中预言了这段著名的话:
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它因赐给它们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又有权柄赐给它,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它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启示录》十三章11节至18节)
四、资本拜物教批判
资本就是踏着商品、货币而来行使最后的使命。因此,最后的、也是最神秘的是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所揭示的资本拜物教,就是当前时代的“宗教”,是一种被复杂的教义神学和教会组织及其信众承托起来的普世宗教。世界因为资本才真正成为当今世界意义上的世界。资本是以商品和货币为前提出现的,但是马克思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6)货币转换为资本,是从货币自身的分化开始的,即分化为“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但陈这一形式外,我们还看到具有不同特点的另一形式G-W-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17)
很显然,从W-G-W到G-W-G这个循环的转化过程,物的因素也被扬弃了,资本成了一种精神的运动。“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资本是货币自身的扬弃,货币拜物教的颠倒在于将商品的物质属性连同商品的社会属性都一并消融了,从而以货币本身作为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同样,在货币成为资本以后,货币的两重性也就被作为中介本身给扬弃了。这里,三位一体的整个图景就出现了,它的历史性就是商品、货币、资本的三位一体,它的现实性在资本那里形成的资本利息、地租和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资本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时,再次提到第一卷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简单范畴即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就已经指出了一种它们的神秘性,即“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颠倒。”(18)而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跃进,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极端抽象化的过程,是最彻底的颠倒的过程,是尘世的国以圣子基督为中介向圣父的国迈进,即向绝对的彼岸世界的一次决定性的飞跃,而资本主义生产借着资本本身的魔力也实现了它的超越性。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超越性对人而言不单是指向“因信称义”的个体信仰重要性,正如基督使得世界在精神上成为普遍的,资本主义使得世界真正在现实意义上成为普遍的,基督教的传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内在相通的:
资本主义生产,像基督教一样,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所以,基督教也是资本所特有的宗教。在这两个方面只有人是重要的。一个人就其自身来说,他的价值不比别人大,也不比别人小。对于基督教来说,一切取决于人有没有信仰,而对于资本来说,一切取决于他有没有信用。(19)
而这个彼岸之国对于绝对多数人而言是想望奔赴却遥不可及的,因此只有先知以赛亚才对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罗9:27,赛10:22),就像人们对资本的渴求和自身的贫穷的对立一样,资本王国的窄门永远只是少数剩余者的才能进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20)
在真正由资本在运作着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的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21)而马克思由此在把由政治经济学所揭穿的这些颠倒的、着魔的世界的实质,看作是古典经济学(当然是经马克思的解读的)的它的伟大贡献:“它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22)而无疑,这实质上是由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才真正完成的工作。
总的说来,在资本的世界里,在它看似达到唯物论的极致的过程中,它的唯灵论的实质也就表现得越彻底。在这里,资本彻底成为一种隐匿了的精神,一个至高无上的圣父王国,一个只有凭借它特有的神秘信仰——即资本的信用形式——才能分享的王国。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23)
在马克思的对比中,虽然没有把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准确的表达,但是他很明显地看出了两者的内在关联,当谈论所谓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时,它更核心的意思是指经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基础作用,至于在某个阶段本身,马克思并不否认宗教以及其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能动关系。但是马克思无疑把资本家对货币、对资本的痴迷跟一种宗教信仰的精神性痴迷等同起来。马克思说:“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24)“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熟悉保罗书信的人自然知道这个比喻有多么绝妙,保罗说:“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罗2:28)这就是基督教的保罗神学在马克思眼里化身成了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学。
五、批评与回应
从以上分析可见,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及其相应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剖析中,由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的演进本身就表现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自身的发展当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和黑格尔从精神历史上考察宗教从艺术宗教到天启宗教的发展进程也是相对应的。可以说,其实在马克思对宗教批判作出根本转向之后的思想成熟期,宗教批判作为理论的启发和现实的指引反而更全面地、更深入地映照着他马克思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并且支撑着他对阶级斗争背后作为原生力量在支配着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历程的现象学描述。没有宗教批判的结构支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很难相信它可以不落入马克思后来所揭示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自身的二律背反当中。而没有对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前理解,那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对于解读者而言也会显得更加云山雾罩。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揭示,那么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本身就仅仅是一代热血青年富有灵感的口号罢了。
在此,马克思对资本及其所主导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背后的宗教结构的揭示,引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与基督宗教的精神旨趣和伦理诫命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为后来成为宗教学研究之基本主题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众所周知,这一主题后来在具有更实质的宗教理论关怀的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中呈现了更丰富的内涵。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恰就是以资本主义与宗教的这一关联作为起点而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加以批判的。一方面,韦伯不是把物欲看作资本主义精神,而是看作人性本身的问题——马克思不会反对这一条的,但是他会补充说,资本主义把它放大了。韦伯说:“对物质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更勿论资本主义的精神。还不如说,资本主义在缓解甚至是抑制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作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25)另一方面,韦伯从发生学的角度上提出恰恰是宗教的力量在支配着现实本身:“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这些力量所形成的有关责任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直都对行动发生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26)作为社会学家,韦伯给他的论述提供了丰富的实例和数据作为证据,而且他看起来比马克思具备更为全面的神学知识。比如他把路德对“天职”(calling)概念的解释以及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加尔文派的预定论中对于渴望获得拯救之确信的宗教心理跟资本主义无限制地积累财富的精神关联起来,读者很明显会感觉到韦伯所谓的因果联系更多地是一种时间次序和心理动机上的关联,此外,这里,对基督教伦理采取何种视角来解读才是关键的,即便韦伯的理解是很有创见性和洞察力的,那么也不可否认实在的基督教伦理本身也总是定格在基督教本身在整个现代社会中不断世俗化的一种结果,就好像中国晚近的人间佛学一样。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看到韦伯对宗教伦理的解读符合基督教神学的理解,但是韦伯的社会学跟马克思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倡导一种价值中立下的描述性分析,而马克思则是带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下的批判性分析,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两者对资本主义的宗教背景的解读上,马克思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进行分析的,但是这种批判不能说是截然反对《圣经》的道德教诲的,基督教道德教诲和人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马克思所认同的。由此,马克思本人更多从《圣经》的教诲与基督教诸宗派教义以及现实的运作的矛盾来理解。比如在《创世记》一章28节中耶和华神虽然曾经说过:“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由此赋予人作为这个世界的管理者的使命,经济一词据说就是从此而来的。但在耶稣的教诲中,上帝和金钱是不能一起侍奉的,《马太福音》六章24节中耶稣告诫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耶稣这里非此即彼的抉择在世俗的基督教面前则不得不化解为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划分。但是同样具有隐喻含义的是,据说美元的货币符号MYM就是从耶稣的符号“IHS”(27)借用来的(而事实上美国建国的精神基础就是基督教),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身体作为代赎的价码,而在教会圣餐礼中分发给信徒的象征着耶稣身体的圣饼,它作为上帝的圣灵其实象征着现实中被交换的货币,黑格尔的“精神”这一绝对者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的真实生命,通过圣饼这一货币,它调和了世界的同一和差异以及神性与人性的对立,因此在基督教的资本主义逻辑上,金钱就是上帝,这也是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逻辑。(28)由此也可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精神性和结构性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精神内在的宗教因素之揭示具有复杂的思想背景,在此不再深入展开。
当然,韦伯试图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去颠倒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模式,但是这种差异其实并不像韦伯所设想的有截然的对立,因为在韦伯广博的宗教社会学知识背后尚没有真正深入到形而上学本身对于观念与实在的关系之争,马克思本人也是融合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的不同旨趣的形而上学的要素,同时,马克思宗教批判本身浓厚的隐喻色彩,是可以包容两种不同可能的解释的。而基督教神学本身在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当中也继承了这一主题。此外,正是在此观念与实在交织的困局中,从宗教批判来展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呈现出的深度,亦当可在哲学基础上,为探索现时代市场经济视域下我国社会意识之错综复杂局面作一借鉴。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43页。
②原文出自马克思为博士论文所准备的笔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0卷。此处引文特别转引洛维特的叙述,因为其中他把马克思本人的事业加以对号入座,解开了原文本身的隐喻。参阅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第43-44页。
③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7页。
⑤同上,第293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卷,第10-11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卷,第10-11页。
⑧同上,第88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卷,第89-90页。
⑩同上,第97页。
(11)同上。
(12)同上,第86页。
(1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卷,第115-116页。
(14)同上,第109-110页。
(15)同上,第112-113页。
(1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卷,第198页。
(17)同上,第172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3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5页。
(20)同上,第93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40页。
(22)同上。
(23)同上,第670页。
(24)同上,第1卷,第180页。
(2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龙婧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6页。
(26)同上,第14-15页。
(27)这个符号有四重含义:1.耶稣人类救主,JHS与IHS相同,都是耶稣的圣名,前者是拉丁文Jesus Hominum Salvator的缩写,后者是希腊文Iesus Hagiator Soter的缩写,因此它也是天主教耶稣会的象征符号;2.凭此标帜你将胜利,为In Hoc Signo Vinces的缩写,据传君士坦丁大帝于312年10月下旬出征时,见天空有十字架显现,周围写有这一短语,因此制作了有此标志的十字旗作为军旗,最后凯旋;3.以耶稣为友伴,Jesumhabemus Socium的缩写;4.藉此(十字架)得救,In Hoc Salus之缩写。
(28)Mark C.Taylor,“Christianity and the Capitalism of the Spirit,” in About Religion:Economies of Faith in Virtual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154-158.
标签:资本论论文; 商品拜物教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宗教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