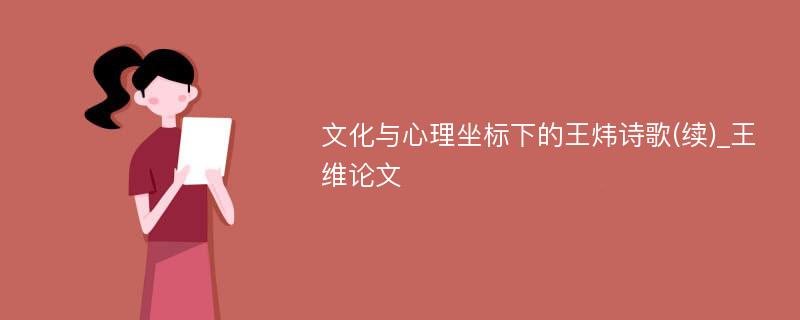
文化与心理坐标上的王维诗(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上论文,文化与论文,心理论文,王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以上三方面特点及其原因,可以说正是王维之所以成为开天时期以都城为中心的诗坛之核心人物的最基本因素。然而,这种与当时的都城文化艺术氛围高度一致的特点,却并不能在长期的文学接受史的淘洗选汰中保持恒固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文学中接受视域及价值构成中,奠定王维诗独创性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的却恰恰是上述之外的内容与特征。简言之,正是以仕途挫折、遭贬出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疏离都城文化为契机,王维的诗歌创作在自心理状态、创作环境到观察角度、构思方式的一系列衍变转化之中,形成更具个性化的意境创造方式与审美建构特征,从而在唐以后艺术意境理论的发展、成熟、精密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审美再发现,并在实际上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实证性的审美范型,这样才奠定了作为正宗唐音的崇高的文学史价值与地位。
王维20岁之前在京城度过出入王府、交游词客的生涯之后,于开元九年21岁时中进士及第,释褐授太乐丞,但不久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事受到牵连谪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这就是说,王维正式踏入仕途之始,也就是其初尝宦海浮沉之时。虽然这一初次挫折,并未拆销其“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悦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的阔大襟怀与济世抱负,然而谪官出贬的本身,使其猛然脱离了优雅安逸的都城文化氛围与生活环境,置身于流离失意的旅途与异乡,客观上已促成创作心理与表现内容的变化与转折。这一转折的最重要表现,首先在于其创作重心由都城诗规范向贬逐诗传统的移转。如果说,都城诗表现重在雄整高华的体格与秀雅温润的词章,那么,贬逐诗表现则重在个人内心的感受与旅途景物的观摹,这也就如同武后时代的著名诗人沈佺期、宋之问从宫廷走向贬途一样,从审美趣味与表现方式看,前一种环境构成群体性表现,后一种环境则催使个性化发展。试看王维贬济州途中所作《宿郑州》: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鸣机杼悲,雀噪禾黍熟。明当渡京水,昨夜犹金谷。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
将此诗与王维遭贬之前在京中所作诗相较,不仅在表现内容上已截然不同,而且在艺术风貌上也显见差异。诗写遭贬出京孤独失落之感,以朴素明畅的语言构成对内心真实情态感受的抒发,特别是“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从一个独特新颖的角度,表达出一种在离别熟悉的环境与亲友之后的旅途生活中人类所共有的普遍心理。对此,明人杨慎曾云:“崔涂旅中诗‘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诗话亟称之,然王维郑州诗‘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已先道之矣”(注:杨慎:《升庵诗话》,按,崔涂诗题为《巴山道中除夜书怀》。)。另一方面,仕途上的挫折与失落,往往造成诗人注意力向自身处境的转移,因而在发抒失落之感的同时,王维又集中描绘了即目所见的旅途景象与农家生活,在细密的观察中透溢出浓郁的日常生活情调。这种观察角度与特点,在《早入荥阳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泛舟入荥泽,兹邑乃雄藩。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野田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旁村。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
泛舟荥泽,城邑雄藩,诗人完全被新鲜的环境所吸引,对山光水色与方言民俗的兴趣几乎熔尽了流贬异乡的孤独与惆怅之感,其主要注意力乃在于对“河曲闾阎”、“川中烟火”、“秋野田畴”、“朝光市井”、“波上渔商”、“岸旁鸡犬”的观察与欣赏,仅于末联略带伤感情调,但“前路白云外”同时也隐含着对迷茫前路中的另一番新奇天地的期待。又如《渡河到清河作》:
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
在这首诗中,诗人对景物环境的着意观察进而推衍为客观景象的动态与主观感受的过程的调适与叠现。诗的开篇展现的是水天一色的混茫一片,随着舟行的动态与视觉的延伸,客观的自然犹如充满生命活力般地顿然开豁,毫无保留地展露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崭新天地,使得主观的视觉与兴致得到愉悦与满足。一般地看,舟行诗写至此,题意已尽,然而,王维却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在尾联以“回瞻”一折,逼使大自然作出二度展露,但这一次展露的内容与结果却恰恰相反,以逆向与消失造成感官的感受向心理的感受的深入。可以说,这种客观景物动态与主观感觉过程、崭新天地的展现与具体地域的消失、感官的感受与心理的感受等诸多因素的融织,其结果实际上正是一种艺术境界的深层的创构。将此诗与代表王维诗成熟境界的《南垞》“轻舟南垞去,北垞淼难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相较,其中景物的动态与感受的过程,以及在两个地域的展现与隐失之中造成一种朦胧性感受的特点,显然已经十分相似。由此可见,王维在首次出贬的旅途之中,由于创作环境的改变、抒发内心感受的需求、注意力重心的转移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诗人对闲逸的农家生活情趣与清妙的山川自然生机的发现与欣赏,从而在较为集中的描写之中显示出独特的观察角度与浓郁的生活情调,实际上已经成为其后成熟的在文学史上具有创造性价值与意义的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序幕与前奏了。
开元二十三年,王维因张九龄荐举,其后数年仕途比较顺利,诗歌创作中亦重新焕发出意气风发的情调。然而,开元后期政治局势的变化,却对其心理深层的变移构成更大的刺激性与推转力。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遭奸臣李林甫构陷罢相,次年贬为荆州长史,这一事件,实为当时政治的转捩点,开明政治宣告结束,从此奸相专权,朝政渐趋腐败,“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立,无复直言”(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王维对此,感受自较常人更为深刻,其《寄荆州张丞相》诗云“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在对荐拔自己的恩相张九龄的失势深表痛惋之意的同时,已初萌“农圃”、“丘园”的退隐之念;《赠从弟司库员外絿》诗云“既寡遂性欢,恐遭负时累”,则表达出置身李林甫专权的官场中的怵惕不安心情;《早秋山中作》诗云:“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又明确表露对陶潜弃官归田的崇仰与追幕。但在实际上,王维并未退出宦途,而是一直任职终身,其《偶然作六首》之三云“日夕见太行,沈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即表明了进退两难的复杂的心理矛盾,可见其身在朝列,心理却郁结难释。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叛军陷长安,玄宗奔蜀,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获,迫授伪职。一年后唐军收复两京,凡授伪职者皆按六等治罪,王维亦因之入狱险遭不测,后虽因其在贼中时曾作“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表达对朝廷的眷念,加之其弟王缙平叛有功并请削官职为其赎罪而幸得恕宥。但这一堪称王维整个政治生涯与人生经历中的最大事件,仍对其心灵造成更为深重的刺痛与压抑,如其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云:“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实为披肝沥胆之词,直至暮年,仍有“仆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然才不出众,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与魏居士书》)之感。
正是这种非乞灵于宗教而不能解脱的心理郁结,促使王维少年时代即深受感染的佛学思想不断浓郁渗化,佛学终于成为其思想中的支配因素。史载王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王维传》。),可见其崇佛信念之深笃。固然,王维信佛自有家庭影响渊源,其母“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请施庄为寺表》),然而,少年王维更以匡世济民为己任,早期作品中表现的也多为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只是随着人生历程的波折才出现“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终南别业》)的心理趋向。王维与佛教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是其与神会相遇于南阳,“语经数日”领悟佛教南宗禅旨(注:《神会语录》。胡适校郭煌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卷一。),并撰写著名的《能禅师碑》,而此事恰恰发生于张九龄失势不久的王维中岁之时。因此,结合王维的人生经历看,其佛禅思想倾向的明朗化,与其说是与神会偶然相遇的顿悟,倒不如说是其本人主观心理之需求与选择。当其因授伪职事坐罪获免之际,更是明确表示“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谢除太子中允表》);垂暮之年,在发出“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的慨叹的同时,亦不忘表明“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心迹,而将一生之事皆纳入空门,已经显然带有对人生归宿与思想认识的总结意味了。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崇佛思想倾向与由贬逐诗传统诱发的发抒个性情怀、感受自然世界乃至萌生归隐趣味的创作心理特征的结合,促使成熟于王维中岁以后的大量山水田园诗中的独特境界的生成。
四
不过,在王维思想的整体构成中,并非仅止佛学一宗,而是与开放型的唐代文化一样,本身就是儒、释、道三教并盛汇融的产物。即使在其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中,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比如《新晴野望》: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谿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
此诗写野望之景,特别是“无氛垢”的感受自显清静本心。然而尾联却突然写到“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的农耕生活情形,表面看来似有不协调之感,但实际上正是植根其思想深处的农业文化意识的显露。王维此诗不仅表达出对农耕生活的关注之情,而且诗句本身亦显然由《诗经·载芟》中的“载芟载柞,其耕泽泽……俶载南亩,播厥百谷”脱化综括而成。《载芟》一篇,影响深远,历朝《郊祀歌》皆由此一脉承传,宋代曾子固作《享祀军山庙歌》仿此叙一年农事,即被王安石赞为有雅、颂之意。由此看来,这种儒学意义上的雅、颂之意,显然也是王维山水田园诗构成的因素之一。再看其《积雨辋川庄作》: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此诗以“淡雅幽寂”的特点曾被奉为唐人七律压卷之作,特别是“漠漠”、“阴阴”一联“极尽写物之工”(注: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然而,其隐居田园的“习静”、“清斋”生活却并不完全等同佛门之空寂,而是在末联运用《庄子·寓言》所载阳子居从老子学得道后客人与之“争席”以及《列子·黄帝》所载鸥鸟与一海边人由相亲到疑忌的典事,以表达自身与人世无隔、与自然忘机的愿望,带有浓厚的老庄哲学意味。这种任运自然的态度,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不仅表现为一种基本的情调,而且常有明确的自觉追求,如《偶然作六首》之四即对“陶潜任天真”、“酣歌归五柳”的生活态度极表赞美与崇慕,在《田园乐七首》中更是以“桃花源里人家”、“五柳先生对门”自况,其《赠裴十迪》诗云“风景日夕佳,与君赋新诗。淡然望远空,如意方支颐。春风动百草,兰蕙生我篱。暖暖日暖阁,田家来致词。欣欣春还皋,淡淡水生陂。桃李虽未开,荑萼满芳枝。请君理还策,敢告将农时”,则显然是对陶潜的《移居二首》之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饮酒二十首》之五“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诗的直接效仿。当然,王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更多地受到禅悦境界的启示,但在其思想的整体构成中,却显然包含着道家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与儒家独善其身的处世观念。
正是由于王维思想整体构成的丰富性,造成他并不盲从一宗的观念与态度。比如他嘲笑作为隐士之祖的高士许由为“耳非驻声之地,声无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之门欤”,认为洗耳去垢乃昧道之举;批评狂逸避世的嵇康为“顿缨狂顾,岂与俯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无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耶”,认为佯狂避世乃碍于表象不悟正性的怪异行为;他甚至不满向以高节为人称颂的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以上皆见《与魏居士书》),认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实乃造成其前后言行矛盾的一时意气之举,也是一种忘大守小的局狭观念。由此看来,王维主要表现于山水田园诗中的隐逸趣尚,与唐代之前的隐士文化传统内涵实有重要区别,而是明显带有体现开天时代精神的阔大胸怀与通达观念。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进而正面阐明自己的人生哲学与处世观念:
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
在这里,既包含“无可无不可”的任运自然的态度,又可见兼济与独善的修身治国的思想,更重要的显然是创造性地提出“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之说,这一方面体现了“尽诸有结,心得自在”的佛家心性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显示出王维对风行当时的佛家南宗禅旨的修正。禅宗至慧能以后,特别强调“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以及人的正常思维程序与认识作用一概否定,在认识方式上更表现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特点。这种认识与修行的方式与特点,虽然具有极度普及的便利性,但同时也造成极度随意的虚幻性。王维则以“身”、“心”并列,“理”、“事”齐观,这就承认了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并存,同时,他提出以“身心相离”的认识方式以达到“理事俱如”的理想境界,也就避免了那种纯主观的虚幻性。
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构成看,也可以发现这种思维认识方式的影响与渗透。当然,作为诗歌意境创造的本身,王维诗突出体现了佛学境界向艺术境界的转化,特别是注重于山水自然中直觉悟道并将禅悟引向意境体验的禅宗思想方式与禅悦境界的直接启示与借用,比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所处”以及《酬张少府》、《送别》等等,不仅皆充满禅趣机锋,甚至与禅宗“从上相承以来,不曾教人求知解”的以个体的直观式感悟与凝练含蓄、双关暗示的语言为特征的表达手段与传道方式几无差别。但是,王维诗的意境又不仅仅在此,而是显示出更为丰富的包容量,比如其诗中多有“关门”意象,从《山居即事》云“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归辋川作》云“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云“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淇上田园即事》云“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济州过赵叟家宴》云“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等诗看,其“闭门”不仅多在“归来”、“落日”的傍晚时分,而且也有白昼之时,可见“闭门”意在避世,联系其“空山不见人”、“独坐幽篁里”的退居山林的孤独处境,则很难说这种避世不带有“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道德观念;与此截然不同的,王维诗中几乎往往同时又呈现出另一种境界,从《终南别业》“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山居秋暝》“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归嵩山作》“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戏赠张五弟諲》“人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等句看,其不仅在与王孙或林叟的相处中随意自如,而且在赋予流水、鸟兽人格化的同时与之忘机相待,这又显然表征着返朴归真的道家自然哲学。可见,无论是投身大化,还是闭门独处,王维都处在一种适意自如的境界,这似乎是参透了天地间大道、透析了人世间纷扰的境界,其诗中“夜静春山空”、“涧户寂无人”之类的独处之“静”以及“空居法云外”、“遥知空病空”之类的涵纳万有之“空”的大量运用,正是这种境界的真切展示。然而,在这“静”、“空”之中又并非真空无物,试看《鹿柴》之“空山不见人”的背后却传来“人语”之“响”,《山居秋暝》的“空山新雨后”的空间实际上包蕴着一个“明月”、“清泉”、“浣女”、“渔舟”的有声有色的自然、人世;同样,《鸟鸣涧》的夜之空寂环境实际上充满月出、鸟鸣、花落
、人影的声响动态,《辛夷坞》的无人之静谧氛围中亦深藏着一个生机勃勃、热烈鲜明的自然世界。这种复合状境界的呈现,乃是诗人生性修养与造化精神相互体现的结果,是心灵与自然在澄映融接之际对“人的真我、万物的本来面目和互相依存”(注: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文化序》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的领悟。
就王维的现实处境而言,这种认知境界的升华,无疑有赖于心灵的容涵与情思的净化,正如其《登河北城楼作》诗云“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青溪》诗云“我心素已闲,清川淡如此”,如清川之淡,才有可能澈照本心真性;如广川之阔,也才可能映纳乾坤万有。同时,由心已固闲、清川似心看,心已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将其与同时诗人相较,这一特点则尤为清晰,如孟浩然《万山潭作》“肃肃长自闲,门静无人开”,是在静境中始能自闲,与王维相比,心境高下自见。因此,就王维诗境创造的主体因素而言,无论是借助于佛学禅宗的境界转换,还是儒家独善操守的道德观念,抑或道家返朴归真的自然哲学,归根到底,显然都是其“身心相离”的人生哲学与思维方式这一中轴线上的主要构成内容与诸种表现侧面,并体现为一种复杂的交织、渗透与融合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