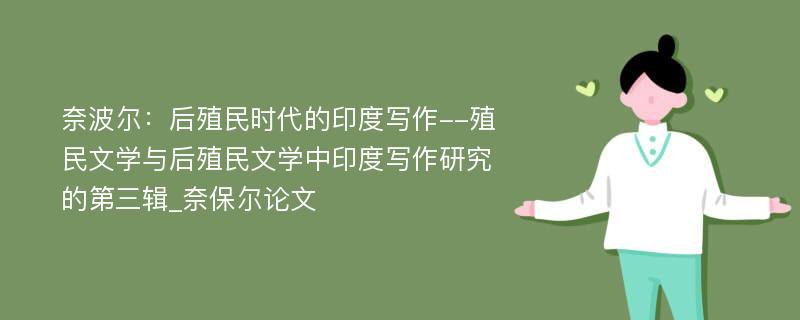
奈保尔:后殖民时代的印度书写——“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研究系列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保尔论文,之三论文,系列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0月,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印裔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V.S.Naipaul)被授 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的印度情结尤为强烈。他曾说过,印度是他的祖先之邦 ,“由于所受的教育,我对印度十分亲近。我在一个非常非常纯的的印度家庭中长大。 那就是我的世界。”(注:德洪迪:《奈保尔访谈录》,邹海仑译,《世界文学》,200 2年第1期,第115、124、116页。)他曾先后三次赴母邦印度“寻根”,并于1964、1977 、1990年分别发表“印度三部曲”即《黑暗地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 历经百万叛乱的今天》。本文拟从奈保尔的印度书写入手,并将其与殖民时期曾经书写 印度的西方作家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奈保尔的印度叙事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研究中的深 刻意义。
一、奈保尔笔下的印度世界
奈保尔说过:“我从我的过去而来,我就得写我所来之地的历史——写被忘弃的人民 。我必须写印度。”(注:德洪迪:《奈保尔访谈录》,邹海仑译,《世界文学》,200 2年第1期,第115、124、116页。)他的印度情结使他一次次走进神秘古老的佛教发源地 。
初次踏上印度次大陆,强烈的“文化冲击”迎面而来,几乎要将奈保尔淹没。在《幽 暗国度》的开始部分,奈保尔便为我们展示了因为随身携带的两瓶洋酒被没收而闹出的 风波。印度海关呆板机械的官僚作风于奈保尔而言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仪式。取 回洋酒的过程也就是感受印度的第一课。慢慢安定下来以后,奈保尔开始以西方人兼印 裔后代的独特视角来打量印度文明。
使奈保尔印象很深的是印度落后的民间生活场景。印度的乡村到处是狭窄残破的巷弄 、流淌污水的排水沟、狭小众多的泥巴屋子、混乱相处的垃圾、食物、牲畜和人。在马 德拉斯,高等法院旁边的巴士站常被人们当作公厕使用。在果阿,清晨时分,居民们在 河边蹲着长长一排人影方便。他们认为,大便是一种社交活动。他们对禁止污染河水的 葡萄牙文广告视而不见。让奈保尔惊讶的是,北方邦一位英俊的回教小伙子竟然将大便 作了一番借题发挥。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族。他自己因为是个诗人,热爱 大自然,常常跑到旷野上大便。“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 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注:奈保尔:《幽暗国度》,李永平译,三 联书店,2003年,第79页。后引用此书只注明页码。)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圣雄甘地号召 向西方学习公共卫生几十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在奈保尔的疑惑面前,印度人的反应是 ,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才真的是令人不敢恭维。
印度种姓制度世界闻名。奈保尔的观察没有绕开它。在他看来,同样的种姓制度,在 特立尼达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在印度却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在印度,种姓 却蕴含一种强制且残酷的劳力分工……在印度,种姓可不是好玩的东西。”(P16)奈保 尔列举速记员蓝纳士与有留美经历的新上司马贺楚的冲突说明了这一点。结论是:“种 姓制度的恶果不止是不可接触制和对污秽之物的印度式神化,还在于它加诸于人的全面 顺从、自我满足、不思进取以及人之个性和灵性的剥蚀。”(注:V.S.Naipaul,India:A Wounded Cicilization,Penguin Books,1979,p171、171、86、175、129.)奈保尔对于 种姓制度持鲜明的否定态度。
因为对农民的同情和印度局外人的视角,奈保尔对于至今一直困绕印度人、特别是广 大农村的贫困问题非常关注:“印度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P35)“印度的贫穷在 颤抖。”(P68)他引用印度作家的话说:“如今回想起来,我才领悟,透过卡纳克昌德 ,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印度那颤抖的贫穷。”(P71)他认为,仔细玩味这一奇特的措辞 “颤抖的贫穷”,虽然显得有些夸张造作,但用来描摹印度之贫困却也十分生动真实: “印度的贫困比任何机器都更加毁灭人性。”(注:V.S.Naipaul,India:A Wounded
Cicilization,Penguin Books,1979,p171、171、86、175、129.)在他第二次印度之行 中,他观察到,印度农村生活仍然追随着自然的节拍。“12小时的白昼后紧接着是12小 时的黑夜。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与远古时代并无两样。”(注:V.S.Naipaul,
India:A Wounded Cicilization,Penguin Books,1979,p171、171、86、175、129.)更 令人担忧的是,农村的发展带来极端的不公平。印度的贫困问题成为印度政界和学术界 所普遍关心和长期争论的问题。奈保尔对此问题的重视有其特殊意义。在奈保尔的意识 中,印度文化里充满了神秘和象征。在跟随香客前往艾玛纳锡洞窟时,他发现,被印度 人称为神祗而供奉在洞中的是“一根巨大冰冷的阳具。”他由此感叹:“印度教的哲学 思维是那么高超、繁复,而它的仪式却又是那么原始、单纯。”奈保尔认为洞窟中的阳 具是印度的象征。借着西方的视角,奈保尔判定:“被它(阳具崇拜)贬损、摧残得不成 人形的印度教徒,却依旧把它的标记看成欢乐的象征。”(P224)这种看重象征的行为即 使在民族英雄甘地也不例外:“身为印度人,甘地不得不跟象征打交道……甘地亲手操 作的纺车,并不能提升印度劳工的尊严,它被吸纳进庞大的印度象征体系中,很快就丧 失它的意义。”甘地是印度精神文明的最新象征,他已经被吸纳进印度混沌的精神世界 里。然以今天眼光看,不幸的是:“在印度,甘地早已经退隐到历史中。感觉上,他仿 佛活在一个古老的时代。”奈保尔眼光锐利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印度人将对象征的崇拜 天衣无缝地嫁接到对于“圣雄”甘地的尊从上,而这又引起了更加不妙的后果:“印度 毁了甘地。他变成了‘圣雄’。印度人敬仰他的人格,至于他一生所传达的讯息,则无 关紧要。”(P95)
在奈保尔看来,印度人不敢正视历史和现实:“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 境,免得被他们看到的悲惨景况逼疯。这种心情我们能体谅。同样的,我们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 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痛苦和愤怒呢?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躲藏 在宿命论里。”(P294)他还认为,印度人有一种向后看的特性,他们喜好从历史深处打 捞今日所需的东西。印度一惯地以旧融新,用老方法使用新工具。他认定,甘地作为古 老印度文明的最新阐释者,已将印度导向末路。他说:“印度的危机并非政治性的…… 这种危机也并非只关涉经济方面。政治或经济危机只是更大危机的一些方面而已。这是 属于文明日渐衰朽的一种危机,摆脱它的惟一希望寄托在这种文明加速加倍的衰朽之上 。”(注:V.S.Naipaul,India:A Wounded Cicilization,Penguin Books,1979,p171、1 71、86、175、129.)印度作为一个伟大的东方文明古国,其珍视历史遵从元典早已成为 不争的事实。从近代的拉姆莫汉·罗易到泰戈尔再到圣雄甘地,他们在向印度引介西学 注入新风的同时,从未忘记到自己的经典和传统中去找寻革新印度乃至医治世界文明痼 疾的良方。事实上,他们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甘地设计的印度独立路线经过实践证明 是正确的。奈保尔虽有以极端凌厉的气势警醒印度人不要沉迷于历史之中的用意,但是 他把印度文明的希望寄托在其尽快的衰朽之上,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不过,联系到当 代印度政治中以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印度教特性”和“印度教认同”为强国之本,他的 警示还是有其现实意义。毕竟:“印度教认同”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思想“鼓励了印度 教当中出现的向后看的顽固保守状况……不利于提升印度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注: 邱永辉、欧东明:《印度世俗化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第283页。)
作为一位来自后殖民地区的印裔后代,奈保尔对于同样属于后殖民地区的印度与前宗 主国英国之关系也即印度与西方之关系特别感兴趣。他认为:“直到今天,这个英国依 然活着。它存活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和层面。”(P275)“印度当下着力信奉的清规戒律和 实用技艺皆为舶来品。甚至印度人对于自己文明成就的认识,本质上也是19世纪欧洲知 识分子启蒙之结果。单靠自己,印度不能重新发现或评价自己的历史。”(注:V.S.
Naipaul,India:A Wounded Cicilization,Penguin Books,1979,p171、171、86、175、 129.)的确,奈保尔指出了英国殖民之于印度社会发展“建设性”的一面。他没有忽视 西化大潮前印度本土保守的一面。奈保尔敏锐地注意到,印度人在张开双臂接纳西方的 东西时,内心深处却不自觉地排拒这些东西所蕴含的价值观。基于此,奈保尔不无担忧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历史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 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 。”他认为,印度人过份强调民族特性,会导致创造力的消退停滞,而这种状况在印度 现实生活中已有反映。奈保尔的结论有些夸张:“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了。”(P318)
综上所述,奈保尔关于印度世界的观察既有深刻准确的一面,也有偏颇失实甚至杞人 忧天的一面,这是文化外来者即“无根人”直面和思考东方文明的必然现象。
二、殖民文学中的印度叙事:奈保尔的参照系
当代后殖民理论之父萨义德在其代表作《东方学》中曾经智慧地断言:“只要考虑东 方就无法回避印度。”(注: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 1999年,第97页。)在殖民时期以来东西方不断邂逅遭遇的历史进程中,印度成了西方 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历史学家等)无法回避且不断关注的主题。这种趋势从殖民时期一 直延伸到当下奈保尔书写印度的后殖民时代。事实上,从R·吉卜林、E·M·福斯特、 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再到奈保尔,西方英语世界关于印度的主题叙事连绵蜿蜒,值得研 究梳理。
吉卜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07年)的英国作家,他于1865年12月30日生于印 度孟买,后来在印生活多年。在印期间,吉卜林遍游印度各地。他对印度的风土民情有 了透彻的了解。这些都在他关于印度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其作品带有浓烈的殖民心态: “吉卜林将印度问题视为白种人责任的一部分。因此,他竭力论证英国控制和规训新近 被征服而不屈服的印度人的合理性。照他看来,英国是为印度自己的利益而来……因此 ,吉卜林代表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它以冥顽不化的帝国主义姿态对待印度人。”( 注:K.Bhaskara Rao:Rudyard Kipling's Indi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1967,p10.)吉卜林的笔下存在两个印度世界。首先是“个人化印度”,这一“ 印度”给他提供马车和仆人之类的物质便利以及文学声望;其次是“殖民地印度”,这 后一“印度”仿佛上帝恩赐英国托管,它有许多传奇故事供吉卜林编撰记录。吉卜林的 作品基本上没有正面表现改变殖民地印度历史面貌的民族斗争。例如,在关涉印度世界 的重要小说《基姆》中,弥漫着对印度淡淡的思念愁绪,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冲突已经弥 合,种姓林立、信仰风俗各异的印度没有内部冲突,即使俄国人的威胁也只是小菜一碟 。(注:Phillip Mallett:Rudyard Kipling:A Literary Life,Palgrave Macmillan,20 03,p118.)在《基姆》中,吉卜林有意隐蔽了大英帝国秩序的挑战者。为了涂抹一幅与 大英帝国统治相和谐的虚幻图景,吉卜林将印度民族主义者完全排除在叙事场景之外。 《基姆》中唯一一位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印度人穆克吉没有透露出一点民族主义情结。 小说中基姆等人所玩的殖民色彩浓厚的“大游戏”(Big Game)也不是用来对付印度民族 主义者的。“基姆的所有敌人来自于英属印度边界以外。边界以内,一派歌舞升平。” (注:John A.McClure:Kipling & Conrad:The Colonial Fi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80.)吉卜林作品中的殖民地印度在此浮现出一派虚假的图景。我们发现,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是一个男孩眼中的印度,里面充满孩童的兴味和喧闹冒失。因此,有论者揶揄道,《基姆》中基姆眼中的印度面临两个敌人,其中之一便是基姆的成熟长 大。“吉卜林必须在基姆成年晓事以前结束小说。”(注:Meenakshi Mukherjee(ed.):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A Book of Readings,Pencraft International,
Delhi,1999,p147.)这与着力表现印度下层贫民生活艰辛与社会潮汐动荡的奈保尔是一 明显对比。奈保尔曾这样评价吉卜林:身为大英帝国的代言人,吉卜林“有时会装出一 副忿忿不平的模样,大声疾呼,从而产生出一种假惺惺的、咄咄迫人的、自怜自艾的效 果,简直就像一出‘戏中戏’。”(P278)一句话,吉卜林没有真正走进印度、走进印度 人的生活与心灵世界。吉卜林几成经典的殖民话语是:“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 ,二者永不聚首。”(注:Rudyard Kipling:Barrack-Room Ballads And Other Verses ,Methuen And Co.Ltd.London,1913,p75.)
吉卜林的同胞E·M·福斯特于1879年1月1日生于伦敦。福斯特曾于1912和1921年两度 访问印度,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Passage”既 暗示存在一条经由西方到达东方的通道,又隐喻西方求索通往印度乃至东方心灵世界道 路之漫长。他曾说,他的《印度之行》是“一条搭设在东西方之间的同情桥梁”。(注 :Judith Scherer Herz:A Passage To India,Nation and Narration,Twayne
Publishers,New York,1993,p29.)与吉卜林傲慢自大的帝国心态相对应,福斯特的《印 度之行》可以视为一种矫正。福斯特在书中着力表现印度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含辛茹苦、 忍辱偷生。福斯特是在一种开明的英国政治和文化气氛中进行写作的,这种自由主义气 氛反对当时张伯伦政府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严肃地质疑大英帝国在印存在的必要性。 福斯特敢于直面印度惨淡的殖民现实景况,展示东西方文化冲突,而吉卜林却无此勇气 ,只得取回避姿态。该小说的价值不止于此,他还蕴涵了比较前卫的反欧洲民族中心主 义观点,展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作者把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希望寄托在 民族文化平等和民族独立之上。(注:杨汩:《论<印度之行>的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观 》,《国外文学》,1998年第3期,第40页。)《印度之行》全书三章的题目分别是“清 真寺”、“石窟”和“寺庙”,它们皆是印度各宗教神灵驻足之地,折射着印度民族文 化精神。这使该书成为表现印度以及印度与西方关系的隐喻。奈保尔的《幽暗国度》中 关于艾玛纳锡洞窟的描写以及对印度民族文化心理的分析,显示了福斯特与奈保尔潜在 的思想关联。
列维·斯特劳斯,1907年生,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他曾经实地考察过 现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创作于1954—1955年的代表作 《忧郁的热带》里,对印度有过描述。他在印度河河谷考察印度河文明发源地时抒发了 如下感慨:“这整个遗址令造访者想到现代大城市的优点与缺陷;它预示了后来较进步 的西方文明模式,那种模式的典范是今日的美国,连欧洲都得师法。”“当旧大陆(印 度次大陆)还年轻新鲜的时候,它已经预示新世界的特色了。”(注: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155页。后引用只标页码。)这里, 列维·斯特劳斯那种福斯特式反西方中心的立场隐约可见。他在观察印度次大陆的风土 人情时心态暧昧复杂:“夹在无人之沙与无土之人的中间,印度具有一种非常暧昧的外 观……印度绝对和新世界无任何关联。”(P157)他还说:“在印度,我们深以为耻的那 些东西,视为一种癫痫症的东西,是城市现象。”这种“城市现象”是:人群拥挤,脏 臭混乱,残壁矮屋,泥泞灰尘,牛粪小便,脓汁排泄和溃烂。“印度城镇需要这种环境 ,才能繁盛。”(P159)他对印度的贫穷落后印象颇深:“印度的伟大失败可以给我们上 一课。”(P179)他在参观印度的耆那教堂时有感而发:“在我看来,此地的石膏阁楼, 外面饰有各式各样的玻璃镜子,到处都可闻到香水味,这是我们祖父母那一代人在年轻 时所想像的高级妓院最野心勃勃的表现……印度人,我们的印欧弟兄,似乎是映照出我 们自己的一幅色情形象。”(P522)列维·斯特劳斯落入了东方主义俗套之中。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奈保尔印度叙事的“来时路”和参照系。虽然奈保尔 与上述三位欧洲人相比,多了一层印度后裔的身份,也的确以“无根人”的身份寻找文 化和意义之家园并有着人类写作意识,因此,他们确乎有着某种学脉思想的隐蔽联系。
三、奈保尔印度叙事的后殖民观照
奈保尔的文化身份非常独特而复杂。他是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的后裔,却远离母邦本 土文化的大氛围;他出生在特立尼达,但不满其后殖民地的岛国的历史文化之贫瘠;他 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并定居英国,可又无法摆脱身处“中心”时的“边缘”感。这样一种 特殊复杂的文化身份使得奈保尔的印度书写呈现出一种斑斓多彩的和声复调,同时也使 他与上述欧洲人的印度书写体现出异中有同且同中有异的格调。
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有帝国话语笼罩下的殖民地的一面,也有流浪的精神家园的一面 。1889年吉卜林回国后,常常沉浸在对印度的思念之中,印度成为他精神流浪的永远故 乡:“除了法国以外,也许只有印度才能让吉卜林完全感到宾至如归……吉卜林幻想被 人再次带回印度,靠近印度就仿佛走向家园。”(注:Hilton Brown:Rudyard Kipling:A New Appreciation,Hamish Hamilton,London,1945,p45.)《基姆》中基姆在印度大地 上的东奔西串和精神探索象征了吉卜林对印度文明的某种回归。“喇嘛是基姆道德觉醒 的主要源泉,对于基姆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注:B.J.Moore-Gilbert:Kipling And “Orientalism”,Groom Helm,London & Sydney,1986,p129.)通过基姆与精神导师喇嘛 的亲近,吉卜林暗示,虽然英国在物质力量上强于印度,但印度人的宗教比英国人的要 优越。因此,“《基姆》中关于基督教代表人物的描写很少有积极的赞许态度。”(注 :Phillip Mallett:Kipling Considered,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89,P37.)或 许是因为吉卜林对异质文化的热爱和创作中地理场景的不断变换,有人评价道:“无根 性是吉卜林作品的本质特征。”(注:David Gilmour:The Long Recessional: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Tohn Merray,London,2002,p3.)而对于奈保尔来 说,自幼年时代起,他就形成一种“漂泊意识(a sense of dislocation)”。“奈保尔 的漂泊意识也是文化和历史性的。”(注:Richard Kelly:V.S.Naipaul,Continuum,New York,1989,p2.)与吉卜林的笔下存在两个印度世界相仿佛,奈保尔也有自己心目中的两个印度,即“个人化印度”与“后殖民地印度”。他的前一个“印度”带有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之旨趣,后一个“印度”则是他冷静清醒观察印度文明后的实录而非吉卜林式的传奇,尽管其间也有诸多与事实不尽吻合之处。
奈保尔曾如是说明他创作《幽暗国度》的动机:“我认为它(指《幽暗国度》)不是那 样的,不是攻击印度的。我认为它是对我的不幸的一个记录。我不是在敲打任何人,实 际上它是一个令人极为感伤的体验。”(注:德洪迪:《奈保尔访谈录》,邹海仑译, 《世界文学》,2002年第1期,第115、124、116页。)奈保尔将自己视为前殖民地的居 民,而今成为一个“居无定所的世界主义者”。因为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自己和反映个 人历史,人们可将之视为论述透析当代世界的“个人化体验”。(注:Bruce King:V.S.Naipaul,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3,p2、63.)与吉卜林将印度视为提供物质 便利的场所不同,奈保尔重在“无根人”心灵痛苦的衍射,对象就是“幽暗国度”。因 此,“他的心绪在对印度毫无掩饰的愤怒和痛苦的自我审视之间徘徊游弋”。(注:Rob Nixon:London Calling,V.S.Naipaul,Postcolonial Mandar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80.)他在第一次印度之行结尾时回顾道:“直到返回伦敦,身为一个无家 可归的异乡人,我才猛然醒悟,过去一年中,我的心灵是多么的接近消极的、崇尚虚无 的印度传统文化;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和情感的基石。”(P403)尽管他接着声称回到 西方世界以后,印度文化精神从他的身边悄悄溜走,但事实上,一场关于印度文化的个 人体验确乎已经发生。
奈保尔与福斯特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之处在于,两人都在寻求东西方世界的汇合与人类 心灵的沟通,并且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碍。不同的是,前者以富含隐喻色彩的杰作《 印度之行》为手段试图打通横隔在东西方民族之间的屏障,后者则以自己数次亲临母邦 印度考察的经历来论证东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相信任、互相理解。
前面说过,奈保尔作为印度后裔和英国居民,再兼之其深厚的西方学养,使其文化身 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如果说福斯特的两次印度之行是纯粹的西方人了解东方世界 ,那么,奈保尔的三度印度之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克隆。虽然我们承认奈保尔 的印度之行确有寻根之意,但这与他借助西方文化视角观察印度文明并不矛盾,也与他 在印度无意中创造的东西方民族交往之个案并无抵触。
奈保尔的确踏上了去印度的文化寻根之旅,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东西方之间的 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 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但却可让印度人退守其中。”(P317)这仿佛吉卜林关于东西 方关系断言的老调重弹,定下了他的寻根之旅的基调,也预示了作为西方文化载体之一 的他在邂逅印度文明时的陌生情感与逃避姿态。他说:“身在印度,我总觉得自己是一 个异乡人、一个过客。它的幅员、它的气候,它那熙来攘往摩肩擦踵的人群——这些我 心理早有准备,但它的某些特异的、极端的层面,却依旧让我觉得非常陌生。”印度的 自然景观也过于苍凉杂乱,让他感觉“格格不入”。(P196—197)也许正是这种与印度 隔阂陌生的心理作梗,奈保尔竭力想认清他的印度朋友亚齐兹的本来面目,“虽然他对 印度的了解不可谓不多,但他仍然未能成功。对他而言,印度仍然是一个黑暗地带,不 管他如何声称自己身在其中,他仍是一个局外人。”(注:Bruce King:V.S.Naipaul,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3,p2、63.)而一旦回到自己赖以安身立命和界定生 存意义的西方文化中间,他就发现:“印度精神悄悄地从我身边溜走了。在我的感觉中 ,它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回来的真理。”(P403)
奈保尔提供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个案。它对探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民族交往融合有着 不可忽视的价值。奈保尔不经意之间点出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性质殊异,同时也提 出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西方怎样看待东方?西方怎样走向东方?这是福斯特与吉卜林已经 不同程度地给出过各自答案的问题。奈保尔在后殖民时代再次艺术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的确值得人们三思。虽然他用语言和行动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按照当今全球 化的发展趋势和时代标准,他的答案显然值得人们、特别是东方人质疑。
奈保尔从希腊开始感到欧洲世界的逐渐隐没消逝。他觉得,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充 满东方风味。而一旦到了埃及,“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脏乱、盲动、喧嚣、突 如其来的不安全感——你突然发觉,四海之内皆非兄弟,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 ”(P4)奈保尔就以这样一种陌生而畏惧的感觉开始跨入印度次大陆。
据他观察,从希腊的雅典到印度的孟买,一路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化之中: “你会发现一种对你来说崭新而陌生的权威和服从。”“一路上你看到的人类,仿佛缩 小了、变形了,他们一路跟着你,伸出手来苦苦哀求你赏几个钱。我的反应只能用‘歇 斯底里’来形容。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不容 人侵犯,因此,在恐惧心理驱使下,我对那些人的态度显得颇为凶暴、残忍。至于我究 竟透过谁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和工夫从事 这样的反省。”(P8)在安德拉邦,奈保尔发现:“那儿的居民个头非常瘦小,身体十分 孱弱,让人怀疑大自然是不是在开玩笑,把印度人的进化过程往后推。在这样的地方, 悲悯和同情实在派不上用场,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精致高雅的希望。我感受到的是莫名 的恐惧。我必须抗拒内心涌起的一股轻蔑。”(P37)这种不同于西方“精致高雅”的生 活场景让奈保尔无所适从:“初抵印度,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宛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向 我逼近过来,而我却不能像在亚历山大港、苏丹港、吉布地港和卡拉奇时那样,逃躲回 船上去。”(P38)参观孟买时,奈保尔则注意到:“戏院门口的印度电影海报,比英国 和美国的电影海报还要酷和性感;剧照中的印度女明星,展示着比好莱坞姐妹们还要丰 硕的臀部和乳房,浑身洋溢着无比旺盛的生殖力。”(P39)
奈保尔毕竟是成长于英国这一典型的西方文化环境里,他在观察印度文明时,不可避 免地带有一种列维·斯特劳斯式的东方主义情调,它折射出奈保尔隐蔽而复杂的心态。
奈保尔虽然一次次走进印度世界,但他依然无法达成文化身份认同,其原因在于,他 的文化血脉里流淌得更多的是西方的学养。他的视角是西方的视角,并且是一种列维· 斯特劳斯式的目光,而这样的视角和目光下的印度世界,就成为一个典型的东方“他者 ”。印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幽暗国度”与“受伤的文明”,印度的人与物也就成为 神秘诡异和令人恐惧的代名词。如此一来,奈保尔与印度及印度人的隔阂陌生也就成为 必然。奈保尔所指代的西方与东方印度的文化邂逅也就只是一场真正的邂逅罢了。不过 ,正因如此,当我们不只从文化寻根的意义上、而且从后殖民时期的全球化时代处理东 西方关系的层面来观照打量,奈保尔的印度书写便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值得人们认真 思索。
标签:奈保尔论文; 吉卜林论文; 世界文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基姆论文; 印度之行论文; 福斯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