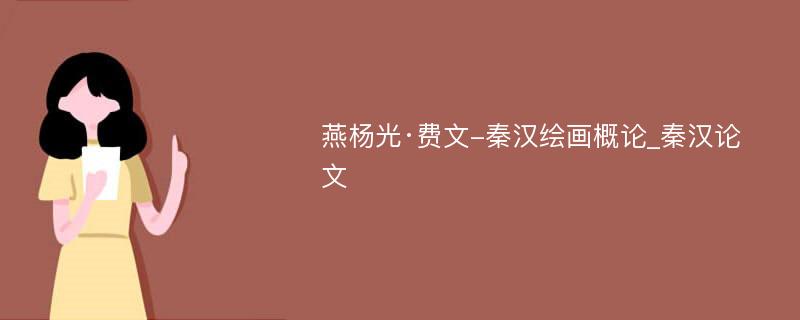
焱焱炎炎 扬光飞文——秦汉绘画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概论论文,扬光飞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32;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1)01-0001-07
“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这是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一句名言。他指出中国有记载的高水平绘画是从秦汉开始的,从而充分说明了秦汉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开拓地位。
确实,绘画在秦汉时代已发展为美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在所反映的内容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人间冥界、天象地理、山水植物、动物祥瑞无所不包;在表现技法上,发展了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墨为主要材料、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各种手法及相关的各种造型观念;在画家构成上,以黄门画工、民间画工为主体,并已有文人投入画事。多种可利用的载体被利用于绘画、帛画、壁画、漆画、陶器画等,成为秦汉最有时代特色的画种。秦汉绘画多方面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中国美术的雄厚基础,使其以后在与外来的佛教美术的交流中从容不迫,得到更广博的发展。秦汉以后,绘画便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美术最主要的代表。
但是秦汉绘画却屡遭厄难。尤其在秦末、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分别蒙受项羽、王莽、董卓、五胡之乱,秦咸阳、西汉长安、东汉和西晋洛阳等名都,被兵火焚烧一空,建筑壁画、宫室藏缣帛绘画化为灰烬。历经长期的战争,不仅正史记载的、而且所有地面上传存的秦汉绘画已经消失,以至自称遍览天下名画的张彦远也不得不叹惜:上古“画之踪迹,不可具见”[1]。以后,历代文人、史家无不发出秦汉绘画早已绝迹的悲鸣。傅抱石在20世纪30年代还令人痛心地断言,秦汉时代“纯绘画的遗品没有存留。自清代以来,关于建筑雕刻的画像石、墓碑、墓阙之类,已是考察汉代绘画的唯一标本”。
随着近代西方考古学的引入和20世纪对秦汉帛画、壁画考古成果的总结,我们对于秦汉绘画的历史,才有了较全和正确的认识。
一、大一统的历史文化背景
1.“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
秦代的疆域之广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但国祚极短,不过15年。在考古上由于缺乏精确的断代依据,很难把秦代绘画从秦国(传统的继承上)、六国(横的交流和总的汇合上)、西汉早期(对后代的影响上)的绘画截然分割出来。然而,这也说明秦代绘画正是在继承秦国传统、汇合六国之萃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对汉代产生极大影响。
早在商鞅(约前390~前338年)任秦国大良造时,秦国就重视美术的政治功能。秦孝公十二年(前356年),秦国由雍(今陕西凤翔南)迁都咸阳,遂仿效魏宫,营造冀阙,以扬秦威。处于蓬勃上升期即统一中国前的秦国和统一中国后的秦朝,分别受荀子、吕不韦、韩非、李斯以及方术的思想影响较深。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是战国末期从孔而变的儒学大师,秦昭王时赴秦,曾见昭王游说。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间接作用于秦国和秦朝的。吕不韦(?~前235年)的思想见《吕氏春秋》,特点是崇道,“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亲理国事,罢免吕不韦相职。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集战国法家思想之大成,秦王政读其著作大为赞赏,邀其入秦。李斯(?~前208年)先入秦为郎、长史,后为秦国廷尉,官至秦朝丞相。于是,荀子、吕不韦、韩非、李斯的思想成为秦国和秦朝的主流。当时的历史注定战国社会只能在由最贪婪的欲望所激发的最残酷的斗争中前进,秦国要征服六国、统一天下,必须彻底抛弃孔孟温良恭俭让的仁义道德。荀子认为:“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富国》);“不全不萃之,不足以为美也”(《劝学》)。由此,美化装饰被帝王用于维护、巩固和扩大自己统治和尊严的手段。因此,秦朝美术建立在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的基础上。韩非论画认为描述现实事物“难”,表现幻想世界“易”。他强调其难,正是鼓励人们去表现。
另一方面,秦地方术盛行,辄通过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自然的变异现象,并推测吉凶祸福,分析气数命运。以秦居水德,水色黑,因而规定服装、旌隆、节旗皆尚黑。秦始皇尤信神仙方术,多次巡狩各地,又遣人求仙,求长生不老之药。
据史籍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2](《秦始皇本纪》),因此秦朝宫殿集六国宫室之精华,并且有辉煌的壁画。它显示出大统一后艺术之博大宏恢气魄,令司马迁极其赞叹:“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泾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3](《秦始皇本纪》)然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项羽入兵关中,焚烧秦宫,居然烧了3个月。壁画随之烟飞云散。另据《世说新语·无为篇》记载:“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取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地方,从宫廷到民宅,壁画制作盛行。
2.“非壮丽无以重威”
汉代绘画以其雄浑的气魄和阔大的胸怀,包容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精华,尤其是周秦理性绘画和楚巫奇幻画的精华。由于处于长达400年的大统一时代,汉代才有可能达到荀子、秦始皇崇尚而未能完成的雄大伟美的境界,又出现他们因时代局限而不能预见的新特点。它正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描绘的那般壮观:“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烂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振摇。”在汉以前,绘画从未达到如此灿烂多彩的程度。
汉代绘画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界,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以前为汉代绘画风格的初创期,以后为其完善发展期。
汉初的绘画并没有形成汉代本身的风格。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并不重视绘画。他在思想上是急功近利的法家最后代表人物,本质上与秦始皇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对于“汉承秦制”起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刘邦本人及开国文武勋臣,几乎全是楚人,这又保证了汉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所谓“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4]之极论,实际上概括汉初文化较为妥当,但泛用于整个汉文化就失之偏颇。在汉代绘画和文化的总体发展上,存在着从“巫”到“史”的过程。汉初,则明显是楚巫文化和绘画占优势。
汉朝开国丞相萧何是刘邦最重要的助手和管家。早在随刘邦入兵咸阳时,其他部将皆去抢夺宫室财宝美女,独萧何先封取图书,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立下头功。秦以前的图书都是有“图”的,实际上也就是继承了图画。难怪《历代名画记》为之记道:“萧何先收,沛公乃王。”汉高帝九年(前198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天下匈匈,共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旧宫室。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悦)。”萧何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威”,是对荀子“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思想的继承。这种追求壮美风格和使美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对汉代绘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曹参在萧何卒后继为丞相,“萧规曹随”。因战争创伤未愈,经济疲惫,曹参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这种源于黄老的无为思想,为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四代的指导思想。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认为:“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因此,美术的发展暂时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汉文帝刘恒自奉节俭,在位23年,宫室苑圃、车骑服御,一无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所宠爱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凡史家无不赞及,文帝曾想造一座露台,听说花钱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便毅然作罢。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刘恒却很重视绘画“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的政治作用。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于未央宫承明殿画屈秩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獬焉”[4]。从而,开创了汉代政治性绘画的先河。
自称遍览古画的张彦远也不由悲叹:“汉魏三国,名迹已绝于代。”[1]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才略见一斑。马王堆汉墓的13幅帛画(文帝年间及以前)、2具棺画(文帝年间),以其精彩的画面昭然面世。
二、鲜明的时代特色
1.“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
虽然有记载的绘画从秦汉开始,而且不能不说很丰富。但在考察秦汉绘画时,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遗憾的事实:凡见于文献记载的绘画作品全部失传,并且历经秦汉本身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多次战乱和浩劫,最迟在唐代就全部荡然无存;而幸存到今天的所有绘画遗品全都不见于文献记载,都是20世纪以来的田野考古从地下发掘的。因此,秦汉绘画在理论上可以截然分为虚实两大部分:虚,即以文献记载为中心的绘画;实,即以出土文物为中心的绘画。为了方便叙述,把前者称之为“文献绘画”,后者称之为“出土绘画”。应该说,文献绘画是当时最重要的和水平最高的,出土绘画是次要的和水平相对低的。
在秦汉以前,绘画作品一般都不见于文献,而全部得之于出土,即全部为出土绘画;秦汉以后,绘画作品虽见于文献,但主要以传世的方式保存至今,即大多为传世绘画。唯有秦汉绘画中,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两者泾渭分明。它们又虚实相生,互为印证,构成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奇特现象。痛失文献绘画,使只能从支离破碎的文字记录上凭借想象去构筑当时的宏伟图景;复得出土绘画,有幸亲睹甚至作古千年的张彦远也未曾知晓的遗宝。
由此,它导致了秦汉绘画研究中两种基本方法:文献研究和出土研究。文献研究是在田野考古未传入中国前最为普遍的传统研究方法。它根据遍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典籍,得到一大堆由支言片语汇集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是信史,但它们主要记载宫廷绘画,而对地方和民间的绘画则语焉不详。更致命的弱点是所描绘的作品已不存在实物。因此实际上无法从中判断秦汉绘画的水平。出土研究是20世纪产生的方法,主要依据出土的绘画实物。它的可视性使人百闻不如一见,它所带来的真切感觉和审美体验是文献说千道万所不能替代的。但是,出土绘画毕竟是有限的,还远远不能反映秦汉绘画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因此,文献研究往往容易导致苍白干瘪、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材料堆砌,而零散的出土物又不足以反映出秦汉绘画的博大精深。真正的秦汉绘画史,只有在文献研究和出土研究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写成。文献研究的意义在于把握秦汉绘画的发展脉络,鸟瞰它的概要。出土研究的意义在于以生动的直观材料,使文献研究有骨有肉。
2.强烈的功利目的
秦汉绘画大多服从于一定的功利目的。功利目的中主要的是三种:教化作用、象生意愿、升天理想。这是秦汉绘画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如前所述,秦汉绘画分为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两种形态。文献绘画属于地上人间的绘画,如宫廷壁画,主要服从于政治教化的作用;出土绘画大多是地下墓室的壁画和帛画,主要服从于冥间象生意愿;升天理想则同时存在于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中。
张彦远所强调的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在秦汉的绘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反映现实生活、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角度看,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绘画像秦汉绘画那样强烈。它之所以如此,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绘画本身发展的原因。秦汉以前,绘画长期附属于工艺美术,人们对绘画潜在的巨大政治作用尚未充分认识。至战国,绘画所具备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表现能力比美术的其他门类如建筑、雕塑、书法和工艺美术都更直接、更强烈,并且制作方便,表现力丰富。所以,秦汉的统治者大多高度重视绘画,将绘画作为自己的统治手段之一。又由于秦汉人对绘画政治作用的认识,还笼罩着商周美术祭祀作用的影子,所以当时的绘画带有浓厚的祭祀列祖列宗的色彩,但又增加了思贤戒恶的时代意义。文献绘画大都为三皇五帝、先哲古贤造像,也为本朝建功立业的帝王勋臣树碑立传,兼绘亡国之君桀、纣之像,以达到吸取经验教训、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3.先帛后壁的发展和南帛北壁的格局
出土绘画中的棺椁帛画和墓室壁画,在黑暗的地下沉睡了2000年左右才重见天日。秦汉人“事死如事生”,所以,这些绘画表达了一种象生意愿和死后升天的理想。秦汉人的生死观和丧葬观比前人有很大转变,即由薄葬变为厚葬,厚葬之风盛行。中国墓制在汉代发生划时代的变化,横穴式洞墓开始取代竖穴式洞墓,墓的建筑材料由木头变成砖石。在关中和中原等政治中心地区,这种变化最先发生,横穴式洞墓中已用砖和石料构筑坚固的墓室,形制上完全模仿死者生前的地面底邸的内空间。内壁上绘有壁画,有的照搬府邸的建筑壁画,有的专为墓室而作。壁画内容主要有墓主的生平事迹、经史故事、神灵祥瑞、天象星云等,表明墓主试图将人间生活照搬到冥间,甚至在冥间也不忘求仙升天。
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以及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则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乃至整个汉代。木椁墓不适合作壁画,侧安置帛画。有的帛画类似旌幡,带有明显的招魂安魂性质,画面既有墓主在龙凤等神灵引导下升天的图像,也有墓主生活的图像。升天图像可看出与楚帛画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生活图像是楚帛画没有的,可看出汉代的新内容。另一类帛画则直接表现墓主的生活内容,没有升天的意义,是墓室壁画的先驱。
从考古的年代上看,帛画墓起源于战国中期,目前最早者为江陵马山1号楚墓,盛行于西汉早期,以后衰落;壁画墓始见于西汉中期以来,目前最早者为商丘梁王墓,东汉大盛;画像石墓始见于西汉晚期,目前有纪年的最早墓是南阳冯君孺人墓(新莽天凤五年,即公元18年),东汉大盛。而从形式上,帛画出自先行的竖穴式木椁墓,壁画出自后起的横穴式砖石墓。即使是同期的帛画和壁画,帛画也代表着更古老的传统。此称之先帛后壁的发展。
从出土的地域看,帛画墓在西汉初期主要见于湘江一带,中期少量流布于淮海和河西地区;壁画墓在西汉中晚期最初集中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和中原,东汉以后扩散于长城沿线、辽河流域和河西,淮河秦岭以南则除了广州南越王墓的壁画图案外绝无仅有。因此在本质上,帛画墓基本上属于长江流域的文化,壁画墓基本上属于黄河流域的文化,称之为南帛北壁的格局。
从文化的内涵上看,汉代的帛画属于泛楚文化,早期的壁画如梁王墓、卜千秋墓壁画虽带有帛画的某些性质,但已属于真正的汉文化。帛画以楚巫文化为特色,壁画以汉史文化为特色,存在着从巫到史的发展过程。打虎亭汉墓并存壁画和画像石,说明这两种样式在此交替。
4.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中国绘画的基本表现形式,随秦汉绘画的繁荣发展已大体完成。首先,秦汉绘画尝试了各种工具、材料、载体后,最后形成了中国画以毛笔为基本工具、以墨为基本材料、以绢纸和壁画为基本载体的传统。中国画最主要的形制——卷轴画,可以在帛画中找到它的源头。第二,秦汉绘画已完成中国画以线条造型的特点,讲究笔墨色彩,通过笔墨色彩的状物传神,表现主观的审美感受,工笔重彩画已见成熟。第三,秦汉绘画虽以人物画为主,但人物画中已出现山水、花鸟的画面。第四,秦汉绘画对于对象的观察认识,是在流动中从多角度形成的。其对空间关系的表达和位置的经营,已初步形成了中国绘画的特点,并能以概括性较强的形色语言表现对象的神韵。
三、文献绘画
1.“四渎五岳,龙凤骞翥”的神仙绘画
王子年《拾遗记》载:“始皇元年,謇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烈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像。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虽然如鲁迅指出,《拾遗记》“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漫无实”[5],但它对于窥察秦代一些绘画现象还是有意义的。所谓“魑魅及诡怪群物之像”、“四渎五岳列国之图”、“龙凤骞翥若飞”之画,应是当时流行的神灵祥瑞题材。再与前述《太平御览》中秦始皇令人画海神的故事相联系,可知都与秦始皇求仙访道、企求升天长生的思想有关。汉武帝亦醉心于封禅、郊祀。尊礼方士,迷信神灵,幻想升仙。这些题材在宫廷绘画中时有表现。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2](《孝武本经》)。
2.“明劝戒,著升沉”的宫廷绘画
在汉代绘画尤其是文献的绘画中,教化的题材代表主流。它主要体现在宫廷绘画中。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获得空前繁荣。“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平准书》)汉武帝刘彻为了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上“独尊儒术”,在政治上开疆拓土,打开中外交通,鼓励人们建功立业,使汉朝由无为走向有为,由幼弱走向强盛。
刘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划时代的作用。他用绘画形式为古代圣贤、当世勋臣树碑立传,借以巩固和扩大统一。他又警惕前朝灭亡的教训,亦绘夏桀、商纣等亡国之君作反面教员以戒世。由此,壁画进入鼎盛期。
未央宫麒麟阁、甘泉宫、桂宫明光殿是宫廷壁画集萃之地。这些壁画的政治意义姑且不论,在绘画史上则促进肖像画、历史画的兴旺发展。在汉代,尤其在宫廷中。肖像画并不是可以任意为之的,被画肖像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和地位。这种资格和地位主要是:(1)古代圣王,如三皇五帝;(2)古代贤臣和哲人,如周公、孔子;(3)开国元勋,如张良;(4)当世功臣,如赵充国。当世人物入画麒麟阁肖像者掌握极严,需经特别的批准。
麒麟阁的肖像画据说画得生气勃勃,以后司马迁在看到其中的张良像时曾叹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2](《留侯世家》)张彦远也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麒麟阁功臣图的粉本。
金日磾之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于甘泉宫,署曰‘休屠二阙氏’。”[6](《霍光金日磾传》)甘泉宫中,汉武帝还使人图绘了他追怀德李夫人肖像。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令人在桂宫明光殿“画古列士,重行书赞”。在其晚年的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不得不考虑到死后依赖霍光辅助他的幼子继承帝位,“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6](《霍光金日磾传》)。这在形式上仅是图绘历史故事,实质上则是借绘画肯定霍光今后的政治地位,表达托孤于他的重大决策。
西汉晚期,由于对匈奴战争和安抚羌人的胜利,“四夷宾服”。“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始入朝”,汉宣帝刘询感怀勋臣功绩,“思股弘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6](《李广苏建传》)。该图总计十一功臣,中有武、昭、宣三朝重臣霍光、入匈奴坚贞不屈的苏武、安羌功臣赵充国,皆有传。这些画像的粉本还一直流传到唐代。以后,汉成帝刘骜在西羌再次骚乱时,“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6](《赵充国辛庆忌传》)。东汉思想家王充以后特别援引汉宣帝图绘当世功臣的例子,说明它激励后人的作用:“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其图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由此可见,被图绘于麒麟阁是功臣最高等级的象征,所以被大家羡慕和追求。班固在其《西都赋》中,用华丽的辞藻极其铺陈了西汉长安宫廷壁画的盛况:“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裹以藻绣,络以纶连。随候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壁,是为列线。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
到了东汉,古代圣帝贤后壁画进入庙堂。曹植《画赞序》载:“惜明德皇后,美于色,厚于德。帝(光武帝刘秀)用嘉之,尝从观画。过虞庙,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为妃如是’。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为君如是!’”这段故事说明图绘圣帝贤后的意义乃在思贤戒恶。以后,这种绘画有增无减。“汉明(刘庄)雅好丹青,别立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1]鸿都学中,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还为鸿都文学三十二人画像立赞,以劝学者。永平三年(公元60),汉明帝“追思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7](《二十八将论》)张彦远由此联想至汉武帝对绘画的贡献而评道:“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1]汉明帝也是汉代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对绘画的重视一如汉武。
汉灵帝刘宏沿袭明帝风气,使戒恶果思贤的绘画再度大盛。他“诏(蔡)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及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1]。由此开诗书画三绝之先声。熹平六年(177年),“灵帝思感(胡广)旧德,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诏议郎蔡邕为其颂之”[7](《邓张徐张胡列传》)。蔡邕死时,“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兖州、陈留,皆画像而颂焉”[7](《蔡邕列传》)。顺烈梁皇后则“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7](《皇后纪》)。
西汉的各诸侯王国也上行下效,大肆营造小朝廷宫室,绘制壁画。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好宫室、台榭、苑圃、狗马”。中元元年,又建灵光殿并满绘壁画。东汉辞赋家王延寿(顺帝和桓帝之间人)游鲁时,感叹于西汉宫室皆毁,唯鲁灵光殿岿然独存,因而作《鲁灵光殿赋》。赋中对其栋宇结构、彩绘雕刻、雄伟气势作了细致而丰富的描绘。其中,描述彩绘的生动多姿:“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海神灵。写载其装,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又记壁画画面有:奔虎攫拿、虬龙腾骧、朱鸟舒翼、白鹿孑鲵、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黄帝唐虞、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它之所以“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是为了“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3.“宣示汉德,威怀远夷”的州郡绘画
汉代各郡国州部也有相应的制度,凡殿堂、祠庙、官署、府第、驿站都有壁画。东汉各州郡首领,也受命利用壁画图绘当地历代官吏的图像和事迹以示鉴戒。《汉书·郡国志注》载:“郡府厅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25~56年),迄今阳嘉(132~135年)。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是以劝惧。”延熹末年,司隶校尉应奉“下诏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其子应劭根据征集的材料,编纂了《状人纪》一书[7](《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司隶校尉是汉代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在朝廷中举足轻重。东汉时,它的权势更大,常常劾奏三公等尊官,故为百僚所畏惮。应奉下令各官府郡国上报前任首官的图像和事迹,当是表明了东汉皇帝的旨意。
各州还应用壁画表彰在军事上或政绩上有所建树的属吏,益州尤甚。永平年间(58~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以壁画“宣示汉德,威怀远夷”。“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炫之。夷人益畏惮焉。”郡尉是东汉州部下属郡的军事长官,他们的府舍有使夷人畏惮的壁画,证明当时西南边郡对夷人采取武力征服兼攻心怀柔的两手策略。直至东汉末年,益州画事不衰。汉献帝时,益州刺史张收在成都学画有盘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壁间。张彦远甚至将成都学壁画与汉明帝的宫殿画并列,极赞绘画的重大政治意义:“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都学堂,义存劝诫之道。”[1]可见,东汉绘画的经史内容比重加大,教化作用发挥得最为充分。
对于两汉绘画的教化作用,三国初人曹植曾有精辟的总结:“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1]
因此,从文献绘画的发展看,也存在着由“巫”到“史”的发展过程。
四、从黄门工匠到名人儒士的画家
1.秦代随军画工和丹青漱地的烈裔
有绘画,便有画工。从“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看,秦国已有画工随军,至六国绘制六国宫殿图。《太平御图》载:“秦始皇求与海神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入海三十里与神相见。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形。”这个“巧者”可能是随行画工。尽管这个故事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秦始皇曾去海上求仙却有史有据。而且,既然有画工随军,那么画工随驾也并非不可能。至于骞霄国所献“刻玉善画工名烈裔”,则是秦代唯一存名的画家。
2.两汉黄门画工和民间画工
汉高帝时,萧何营作未央宫,当有画工绘制壁画。文帝“于未央宫承明殿画屈秩草”等,当为黄门画工所作。精美的马王堆帛画和棺画、梁王墓壁画也应出自诸侯国名匠之手。汉武帝重用董仲舒,表彰六艺,尝置秘阁,搜集天下法书名画。其使令之臣,隶属于黄门者,亦有画士以备诏。诸如麒麟阁、甘泉宫、明光殿的大规模壁画,无一不是这些黄门画工的作品。黄门令官署的画工集体,甚至成为以后宫廷画院的雏形。
汉元帝时,毛延寿是第一个知名的黄门画工,以擅长人物画而著称,尤其是直接导致昭君出塞这一传颂千秋的历史故事而闻名天下。《西京杂记》记其曰:“杜陵人,画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元帝时,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独王嫱(昭君)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乃穷案此事。画工毛延寿等皆同日弃市。”同日弃市者,还有画工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5人。弃市的6人,竟然是西汉名存史籍的全部画家,并且都出生于关中、中原一带,都是宫廷画家。《历代名画记》载:“陈敞、刘白、龚宽并工牛马,但人物不及延寿。阳望、樊育亦善画,尤善布色。”
昭君出塞的意义,历代人见仁见智,或曰深宫秋怨,或曰大义和亲,但对于毛延寿则多加痛责。只有宋人王安石为其叫屈:“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从纯绘画艺术的角度看,毛延寿无愧为出色的人物画家,“丑好老少必得其真”,汉元帝可按其图召幸后宫美女。而且,他还可以按照个人意图将人美化,使“诸宫人皆赂”,得以受幸于皇帝;或将人丑化,使“貌为后宫第一”的王昭君因不肯贿赂而“不得见”,以致皇帝误以为其貌丑而发配匈奴为阏氏。总之,毛延寿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西汉绘画的较高水平。另外,比之更早的马王堆、金雀山帛画上均有相应的墓主人像,其水平之高亦可反证毛延寿的肖像画水平并非空穴来风。
东汉时期,统治者更重视宫廷画工,人数扩大。汉有帝“雅好图画,别立画宫……取诸经史故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从而,绘画与历史、文学结合起来,历史画获得长足发展,宫廷画工的分工更为细致。和熹邓太后(80~121年)的一份诏令中,就曾提到画工达39种之多。
名存史籍的东汉画家与西汉一样,恰巧也是6人,即:张衡、蔡邕、赵岐、刘褒、刘旦、杨鲁。其中,“刘旦,杨鲁,并汉灵帝光和中画手,待诏尚方,画于洪(鸿)都学。”[1]
汉代民间画工姓名大多湮没无闻,只有极少数通过漆画留名而流传下来。汉乐浪郡(今朝鲜平壤)出土的西汉漆器上,记有画工名字数十人之多,如“画工半”、“画工文”、“画工定”、“画工长”、“画工恭”、“画工壶”、“画工谭”、“画工武”、“画工广”、“画工敖”……从长沙、江陵出土的漆器彩绘上,都可以见到民间画工的精湛技艺。
3.名人儒士从画:张衡、蔡邕、赵岐、刘褒
西汉和东汉的画家相比,西汉的6名画家皆为宫廷画工,又全都因中国绘画史上首号冤案才得以留名,东汉的6名画家中有4名是著名人物,即:大科学家张衡、大文学蔡邕、名士赵岐、高官刘褒。
张衡(78~139年)字平子,是东汉中期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年轻时曾去洛都学六艺,亦有画名。《历代名画记》载其“高才过人,性巧,明天象,善画。”“昔建州浦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潭中不出。或云:‘此兽畏人画,故不出也。可出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兽,今号为‘巴兽潭’。”张彦远为之作按:“《三齐记》云:‘昔秦始皇见海神,使左右巧者以足画之。’又按应劭《风俗通》云:‘公输班见水上(上豕下虫)形,以足画之。’”从而评道:“巧者非止于手,运思脚,亦应乎心也。”历史上的张衡却是极力主张写实的,他在批驳图纬虚无时指出:“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7]“可出纸笔”,证明张衡已用纸作画,因而张衡是第一个被记载用纸作画的人。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1957年在西安灞桥西汉早期墓中发现一些麻类纤维残片,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纸。1986年又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早期墓中发掘纸质地图残块,更有力证明西汉早期已将纸用于书写。东汉和帝年间(88~106年),蔡伦集中前人经验,生产出价格低廉、便于书画的“蔡侯纸”。张衡活跃的年代恰与蔡伦同期而滞后,他利用纸来作画是可能的。
蔡邕(132~192年)是东汉末期文学家,“工书画,善鼓琴。建宁中为郎中,校书东观,刊正六经文字,书于太学石壁,天下模学,又创八分书体”。如前所述,汉灵帝曾诏蔡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其作赞并书。蔡邕遂以诗书画擅名于世,时称三美,有《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世。
赵岐(约110~201年)多才艺,善画,“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由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7](《赵岐传》)。赵岐的记事表明东汉人未死即为自己修墓室,作壁画,而且由名士自己画,并作赞。自画像居主位,经史人物居宾位,实际上是儒家礼仪受到削弱,画家个性得到加强。这种方法为今见东汉墓室壁画普遍模式。
刘褒在汉桓帝时任蜀郡太守,“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1]。是直接以绘画表现《诗经》中《云汉》和《北风》这两首诗的意境。它无论从题名还是从内容,都应该是山水画。由此,山水画的滥觞期可以追溯到东汉。
从画家队伍的发展可以看出:(1)绘画越来越普及,由宫廷走向社会。(2)已有文人士大夫从事画艺,有助于提高绘画的社会地位,成为士人画的先兆。(3)墓室壁画普遍流行。(4)西汉出现一些善画牛马的画工,东汉出现山水画的苗头。(5)纸已开始运用于绘画
收稿日期:2000-10-02
标签:秦汉论文; 汉朝论文; 壁画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东汉皇帝论文; 汉代建筑论文; 历代名画记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西汉论文; 张彦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