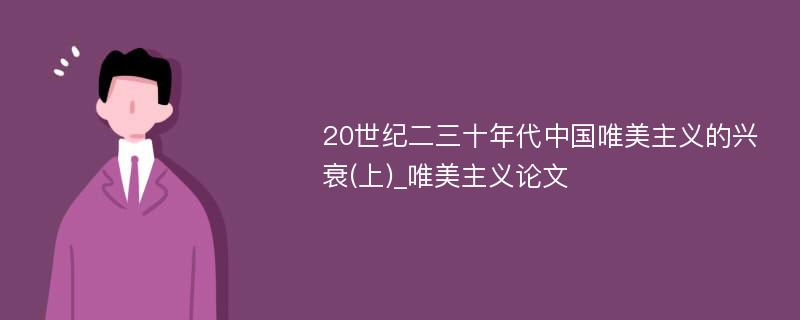
二三十年代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兴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二三论文,唯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唯美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它的总纲领、总口号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术语是法国哲学家库辛于1818年首次提出的,而确定它的概念则是诗人、小说家戈蒂耶。戈蒂耶在《(阿贝杜斯)序言》(1832)和《(莫班小姐)序言》(1834)中指出:“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繁荣,是灵魂在欢乐中的充分发展。绘画、雕塑、音乐,都不为任何目的服务。”又说:“真正称得上美的东西只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需要。”年轻些的诗人波德莱尔也表达了相同的见解:“诗歌除了本身以外别无目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目的。”这种唯美的思想在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聚会中已经在发展着,当雨果率领开始第二次浪漫主义大进展时,它无疑已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热忱阶段了,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不自觉的,唯有戈蒂耶和波德莱尔是以它作为最终目标,也即是宣告艺术的绝对独立。戈蒂耶在小说《莫班小姐》里表达的是这种思想,波德莱尔从爱·伦坡那里学习的也正是这种思想,并将它运用到自己的诗集《恶之花》上面。正是有了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和实践,法国的这一文学才在国外产生了影响,尤其影响到海峡彼岸的英国。
在伦敦,一群“波西米亚人”经常谈起戈蒂耶和波德莱尔。一小批宣传者四处奔走,传播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诗人史文朋。他读过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61年修订本,并且给作者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作者见解超群,“胆敢公然宣告:诗歌艺术和训诫教化毫不相干。”他对戈蒂耶的《莫班小姐》也备加推崇,称它为“美的金书”。史文朋的见解连同这种崇拜,得到美国画家惠斯勒的赏识,于是两个人的结识产生一个结果,史文朋将惠斯勒介绍给了罗塞蒂和他的朋友莫里斯、琼斯、布朗。
罗塞蒂是拉斐尔前派协会的三个发起人之一,另外两个是韩德和密雷。这个协会成立于1848年,1850年出版刊物《萌芽》。在协会成立的前后,他们读过霍顿写的《济慈传》,重新引起对这位浪漫主义时代第三个伟大诗人的兴趣,从他的诗歌看出了古典与浪漫,灵与肉的最圆满的调和,觉得那正是他们在美术里企望不到的境地。为此他们将它移植到自己的画里,并开始崇尚1508年拉斐尔离开佛罗伦萨以前的作品所具有的真诚率直的画风,以反对当时流行的学院式艺术。这本是绘画上的一场革新活动,因为罗塞蒂不仅是画家,还是诗人,所以他把协会的美的理想传播到文学创作中。他的著名诗篇《神女》(1850),描写圣女升天后还眷恋世上的情侣,通过肉的灵化和灵的肉化幻想出在天国和情侣永不分离,体现了一种灵肉合致的思想。《生命之家》这个诗集也包含了类似的主题,以致使布卡南等批评家以“肉体派的诗”相非难。史文朋没有参加拉斐尔前派,但他是罗塞蒂的热烈支持者。他和拉斐尔前派一起被卷入了称之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奇特狂潮。
1866年史文朋的诗集《诗歌与谣曲》出版,是标志这一运动到来的文学先兆。这本诗作的风格,正如批评家佩特写到的:“其色调错综复杂,光怪陆离,有如‘红莲花’一般。夏日的影响有如血液的毒汁。”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清规戒律的一次严峻挑战,其结果是引来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佩特正是通过史文朋的影响吸取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并作出种种努力来解释它,使之渐渐变成一种美学体系。他于1897年结集出版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的结论中写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充实刹那间美的感受。”他重申由感觉取得经验,说:“并非经验的结果是目的,经验的本身就是目的。”主张在经验之上放置生活的焦点,“使得强烈的,宝石般的火焰一直燃烧着”,永远“保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就是“人生的成功。”他认为,艺术才是充实生命和无数瞬间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你从事艺术活动时,艺术向你坦率地表示它所给你的,就是给予你的片刻时间的最高的质量。”这种由感觉主义、刹那主义酿出的艺术至上主义,曾给予唯美主义运动以不可思议的影响,他的声望也由此达到顶点。
名重一时的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在给友人路思的信中,说到自己在牛津大学上一年级时就爱读佩特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并且承认在自己的生命中没有一刻不对佩特表示尊敬。他在佩特那里还结识了西蒙·所罗门,并为所罗门那种为艺术本身的艺术精神所迷住。带着同样的热忱,他在惠斯勒举办的一次早餐会上认识了惠斯勒。惠斯勒是创造艺术的人,而不是美学家,王尔德觉得从这儿学到的比在牛津大学学到的多。惠斯勒说的“艺术家要高于自然”,使他念念不忘,从而认定自己要做一艺术的辩护士。于是一出牛津大学,就大胆发挥他的主张,到处宣传他的主义。1881年,他把毕业前后写的诗集成一册,题为《王尔德诗集》出版,轰动了当时文坛。他从美国演讲旅行回国后不久,便来到唯美主义者喜欢逗留的地方——巴黎。
巴黎对王尔德的影响几乎和对乔治·摩尔影响差不多。摩尔在那里认识了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并在于斯芒的《逆向》启发下写了用“亚里斯多德式的欢悦”轻松愉快地对待唯美主义的“一位青年的自由”。王尔德在那儿很快就结识了爱德·龚古尔、都德、马拉美,还从于斯亡的“逆向”里,形成了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的最初构想,并受于斯芒和福楼拜的“希罗底”的启发,写下了诗剧《莎乐美》。这两部作品,写的都是灵肉冲突而结果是肉的悲惨命运,充满着病态的色情和神秘主义倾向,堪称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作,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1891)中借亨利勋爵之口说出的一句话:“通过感官治疗灵魂的创痛,通过灵魂解除感官的饥渴”,已经成了唯美主义的一句格言。《莎乐美》是1892年王尔德在巴黎用法文写出的,1894年由他的好友道格拉斯译回英文在英国出版。英译本所附的插图出自青年画家比亚兹莱之手。画面上,莎乐美浑身珠光宝气在希律王面前跳着淫荡的舞蹈,而先知约翰的头颅却在银盘上鬼魂似地熠熠生辉。这种堕落的场面和华丽的内景,使人联想到邪恶、放纵与奢侈。不过对比亚兹莱来说,他确实获得了成功,《莎乐美》使他一举成名,而他又使《莎乐美》名声大振。
受出版商约翰·雷思的鼓励,比亚兹莱担任了一本新季刊的美术编辑,这本刊物名叫《英皮书》,它由黄颜色封面的法国小说而得名。诗人道生、西蒙斯和画家琼斯是最卖力地为它呐喊的人,并组成一个更为颓废的联盟。1895年,一个名叫《萨沃伊》的新杂志创刊,比亚兹莱马上画了一系列画,并创作一部题为《在山下》的爱情浪漫小说,通过夸张的语言表现对邪恶事物一种亲近态度,充满了性的想象和怪异的修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笔下图案在文学中的回声。1898年,年仅25岁的比亚兹莱的旧疾复发,写下一封浪子迷途知返的绝笔信后病逝,一场声色动人的唯美主义运动也随之停顿下来。走完英国唯美主义最后阶段,或者说把它推向终结,就剩下西蒙斯和围绕他周围的几位年轻诗人。他们都在寻找新的动力,最后奔向分明是印象主义所引导的方向,成为英国近代文学的一个支流——象征主义诗派。
英国唯美主义运动虽说于19世纪90年代末结束,然而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却像一阵风似的漂洋过海,在东西文坛上产生着不同的反响。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俄国的“纯艺术诗派”中,或者现当代欧美层出不穷的艺术流派中,都可见出唯美主义的色彩和倾向。在20世纪初的日本,唯美派不仅形成一个整体,而且于明治末大正初的大约五年多时间内,取代了自然主义成了文坛的主流。它的诞生是从1909年1 月《昴星》的创刊为起点,通过《昴星》森欧外和上田敏实际上成了日本唯美派的两大先驱、平野万里、石川啄木等也即是它的阵容。此外,《三田文学》的永井荷风、佐滕春夫,《新思潮》的小山内薰、谷崎润一郎也表现出明显的共同性。这几派的交流逐年深入,最终以“面包之会”的形成汇为一流了。在数量可观的唯美主义作品中,森欧外的《假面具》。上田敏的《漩涡》,本下圭太郎的《和泉号染房》、永井荷风的“冷笑”,谷崎润一郎的《文身》均是压轴之作,由此可以看出支撑了他们后来长期创作的丰厚功底,以及唯美派文学得以继续存在的可能。
中国的新文学生产较晚,比日本相差还将近半个世纪,因此在短短的十多年间,西欧百年来活动过的文学倾向、都在这里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甚至表现主义、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也在这里露过一个面目,所以中国的唯美主义就像浪漫主义一样没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素质。尽管如此,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毕竟是出现了,以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后五年到第二个十年(1922—1937)整整15年间起伏不断,形成一段从兴到衰的历史,数十上百个作家受其影响,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一串串鲜明的足迹和一批批创作的实绩。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却不为经过的人所注意,所瞩目,偶尔有一些人还记得它,也只记得它负面的影响,而对它各个藏着的意义大抵未必去留心。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接近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这份重要遗产,在这篇文章里,还将对唯美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形成和来龙去脉,主要作品的思想艺术特征,以及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必要的描述和分析,力求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形成与来龙去脉
中国新文学运动从1917年发轫起,经第一个十年前五年创作界的“寂寞”,而到了后半的五年情形就大不同了,不仅思潮涌起,流派丛生,创作及理论批评蓬勃发展,而且所有这一切几乎是通过纷纷成立的文学社团的活动来实现。两个成立最早也是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对立,就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文学倾向不同,前者提倡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后者则标榜新浪漫主义,主张“为艺术的艺术”。
关于文学的倾向和主张,本来往往含有个人的嗜好和时代潮流的影响。创造社是留日学生单独建立的文学社团,最初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陶晶孙等十来个人。因为在国外住的久,当时日本及欧美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就使他们倾向到浪漫主义和与此一脉相承的唯美派、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郭沫若是创造社当时活动的中心人物,在他准备回国创办《创造》季刊时,陶晶孙问他说,“那么有什么方针办,他是一句:新浪漫主义。”〔1〕
《创造》季刊于1922年5月1日在上海创刊,比预告出版日期推迟了四五个月。郁达夫在预告上说过一句“有人垄断文坛”的话,被好些人认为在讥讽文学研究会,由此便结下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不解之怨,并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笔战。为了应接这次笔战,郭沫若成仿吾曾花费了许多气力,而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也正是在这里得到了发挥和引申。
郭沫若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第一次攻击艺术上的功利主义,他说:“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还说:“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说,以前我也曾怀抱过来,有时在诗歌之中借披件社会主义的毛皮,漫作驴鸣犬吠”,“但是我在此如实地告白:我是完全忏悔了。”在《文艺之社会使命》中,郭沫若进而提出文学无目的论,他说:“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此时郭沫若还有其它唯美的观点偶尔一现,例如他在《创造》季刊第四期的“曼衍言之二”写道:“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自然’不是浅薄的功利主义者,毒草不是矫谲媚世的伪善。”后来,成仿吾发表了《新文学之使命》、《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所持的也是唯美的见解。而最能表示他艺术至上主义的莫过于《新文学之使命》里的一段话:“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
创造社的唯美主义倾向,其实也是不满于“粗制滥造”而发出的一种高调,因为在当时文坛上是有所指的,所以招来的诅骂和攻击不少。而与胡适一派的笔战,则使不少青年团结在创造社的周围。后来,《创造周报》发刊了,接着又出了《创造日》,创造社的活动顿然有了声势。除了季刊时新加入的滕固、方光焘经常撰搞外,还有不少的青年作者如邓均吾、倪贻德、周全平、王以仁、淦女士、敬隐渔,也已崭露头角。他们中间有写诗,写小说,写杂文的,文风也不一样,并在不同倾向中早蓄着各人有各人的前途的成分。当坚持了最久的《创造周报》宣布停刊后,他们便各奔东西了。在《创造周报》终刊号的前一期上,有创造社与《现代评论》合并的宣言,这是郁达夫与成仿吾商量后作出的。然而性质倾向两不相同的团体,合作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郁达夫的宣言,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创造周报》的停刊,实际上就是创造社前期活动的结束。不过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却已在文坛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就在他们离散前后,闻风兴起者大有人在。
1923年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2〕它是由林如稷发起,约集在上海的邓均吾、 陈翔鹤和在北京的陈炜谟、冯至等组织起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四川人,与创造社的作家都有过交往。因为爱好文学,林如稷在上海读书时就结识了郭沫若、郁达夫。邓均吾是在泰东书局编辑所与郭沫若、成仿吾相识,并在他们提携下走上文坛。冯至上北大时就开始写诗,而他的若干首诗能在《创造》季刊上登载,则是由创造性作家张定璜推荐的。陈翔鹤是写小说的,在创造社的作家中给他影响较深的是郁达夫。
浅草社办有《浅草》文艺季刊,于1923年3月25日正式创刊发行。 虽是力量太小了,可他们愿做“农人”,在“沙漠”和“荒土”中撒播几粒“种子”,以新萌的嫩绿来灌溉这枯燥的人生。〔3 〕这可以说就是《浅草》的办刊宗旨。为了避免卷入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去,他们不但取消了批评栏,还表明了同人的态度:“我们不愿受‘文人相轻’的习俗熏染,把洁白的艺术的园地,也弄成粪坑,去效那群蛆争食。”“我们以为只有真诚的忠于艺术者,能够了解真的文艺作品:所以我们只愿相爱,相砥砺!”〔4〕为此他们的季刊, “每一期都是业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个世界,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5〕
1923年下半年,浅草社成员逐渐星散,加之书局方面的拖延,致使《浅草》在1924年中断,于1925年2月出刊第一卷第四期后, 即行停刊。同年秋天,冯至和杨晦、陈翔鹤、林如稷在北京另立沉钟社,先是出版十期《沉钟》周刊,继之而起的是十三期的《沉钟》半月刊。间隔五年,1932年3月《沉钟》半月刊又重新复活起来, 继继续续出至第三十四期终刊。《沉钟》类似《浅草》,专登创作和翻译而很少发表评论。在上面发表作品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五个最初成员外,还有蔡仪、修古藩、左谷兰等人,他们“径一周三”,“摄取来的异域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at Wilde),尼采(Ff.Nietzshe), 波特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tev)们所安排的。 《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秋,’玄发朱颜,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6〕
在上海还有着为艺术的艺术的一群,那就是崛起于1923年3月, 出版有《弥洒》月刊的弥洒社。它由胡山源、钱江春、赵祖康发起,最初成员有陈德征、唐鸣时、曹贵新、俞翼云、赵景云等。“弥洒”,是拉丁文Musa、英文Muse的译音,现通译为缪斯,即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之女神。这名称是胡山源提出来的,他还曾带着拟就的《弥洒临凡曲》,专程去了一次杭州,约到之江大学几个先后同学,作为社员。这首诗其实就是弥洒的宣言:“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7 〕《弥洒》专事创作不及其他,似乎正合他们的主张。钱江春曾说:“我们都认出版这月刊只是一时的灵感,并不要借此宣传文学上主义,或要像人家说用文人的心血来灌溉枯燥的人生。”“作家兼了批评,总引起了无谓的纠纷,减少出品的能率。”〔8 〕所以到了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这种“非旗号的旗号”,事实上是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的《编辑余谈》说了:“近来文艺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在物质文明使人们卧到冰房里去的时候,要搅动人们的感情,舍文艺之外,可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9〕
《弥洒》月刊出到第六期,由于社员大都散处四方,经济上又不能维持,就只好停止。此后,钱江春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还继续为弥洒努力,分别于1924年10月和1925年10月出版了《弥洒创作集(一)》和《弥洒创作集(二)》,收入弥洒的大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大抵很致力于优美,“翩迁回翔的舞着,宛转抑扬的唱着”,然而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有时显出过度的敏感来。
引创造社为同调者,并将文学研究会和胡适一派作为攻击对象的唯有清华文学社的人。该社起先是由梁实秋、顾毓秀(一樵)、张忠绂、翟恒等组织的“小说研究社”,经闻一多提议于1921年11月改名而来的,并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闻一多、吴景超、谢文炳,和被称为“清华四子”的朱湘(子远)、孙大雨(子惠)、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这本是一个以兴趣结合的学生文学团体,却偏要以“艺术为艺术”的主张现于社会之前,其原因正如闻一多所说的:“我们耳闻诗坛叫器,瓦缶雷鸣,责任所在不能不指出他们的迷途来;我们相信自己的作品虽不配代表我们的神圣主张,但我们籍此可以表明我们信仰这主张之坚深能使我们大胆地专心地实行它。”〔10〕文学社的人大多是写诗的,对当时的几部白话诗集颇有一些意见。《冬夜》里有的“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之句,《草儿》里有“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事”之句,他们都认为俗恶不堪,就诗讨论倒是《女神》的评价最高,由此闻一多写了篇《冬夜评论》,梁实秋写了篇《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出版后,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刊登了冷嘲热骂的短评,一个是《女神》作者郭沫若的来信赞美。闻一多得知郭沫若的赞成,惊喜欲狂,还说:“因为我们若要抵抗横流,非同别人协力不可。现在可以同我们协力的当然只有《创造》诸人了。 ”〔11〕
文学社同人的作品是以美为艺术之核心的,大多发表在《清华周刊》以及《文艺增刊》上。为在文坛上打出一条道来,他们拟出一份文学季刊,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却终末能实现。其后社友的许多作品都送到《创造》去刊登。1923年秋,梁实秋经上海时,创造诸人欲将《创造》季刊编辑事托他与闻一多代办,然而则得不到其二人的应允。原因是他们此时最不满意于创造社之辈的偏狭,“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12〕其次就是已经注意到郭沫若所讲美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话与他们主张纯艺术主义者的论点发生了冲突,而且不易解决,分明是不能再一同协力了。
由于个人间的意见龃龉,田汉不发出冲突于1923年离开了创造社,成了脱离创造社的第一个人。1924年1月, 由他与妻子易濑瑜自费创办的《南国》半月刊正式刊出发行,是为南国社活动之始。因经济负责担太重和易濑瑜劳瘁成疾而心力两疲,《南国》月刊仅出至第四期就告停刊了。1925年1月,易濑瑜病逝,田汉堕入感伤,夏天与三弟田洪、 叶鼎洛离开长沙到上海,居保康里,仍终日饮酒肆间以解愁绪。后因同学之劝由8月29 日起在国家主义者编辑的《醒狮周报》上附刊《南国》特刊,发刊至28期终止,田汉许多悼念舅父、亡妻的散文皆写于此时。1926年夏,他与唐槐秋、唐琳等就新少年公司的旧址,组织起南国电影剧社,发起启事写道:“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魅力也最大,以能白昼造梦也。……吾国电影事业发达未久,以受种种限制,至相率不敢作欲作之梦。梦犹如此,人何以堪?同人等有慨于此,乃有斯社之组织,将群策群力,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以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电影剧社的唯美主义旗帜虽然已经张起,但没有多少实际的活动。1927年1月,田汉开始写作《银色的梦》长文, 陆续发表在《银星》电影杂志上,文章引用谷崎润一郎、佐滕春夫和小池坚治的观点,说明电影所有的引诱力和麻醉力。同年秋,他受聘于私立上海艺术大学任文学科主任,后将其改名为南国艺术学院并任院长。学生60余人,如张曙、王素、郑君里、吴作人、刘菊庵、陈明中、赵铭彝、陈白尘、金焰、杨闻莺等均为以后南国戏剧运动的中坚。陈凝秋、左明、安娥等也由北方到上海参加南国社。
1929年1月,田汉率南国社赴南京作第一次公演, 剧目有《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古潭的声音》、《颤栗》、《秦淮河之夜》。七个剧目都是出自田汉一人手笔,完全是带着感伤主义、唯美主义的色彩。这些剧作大都发表在田汉自己主编的《南国》月刊上,该刊创刊于1929年5月,出至1930年8月二卷四期停刊。同年9月,左明、赵铭彝合编的《南国》周刊也在上海创刊, 出至1930年6月第十一期终止,这一时期是南国社的鼎盛时期, 社员人数也激增至百余人。1930年5 月田汉在《南国》月刊二卷一期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和在《电影》杂志第一期发表《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表明整个南国社开始一种转变,和当时整个进步文化运动合流。
1926年4月1日,《晨报·诗镌》的创刊,是新月诗派活动的开始,也是唯美主义力量的一次聚集。这次活动是由诗坛的两位名人发起的,一位是徐志摩,另一位是闻一多。徐志摩在组织新月社时,本希望像罗塞蒂兄妹在艺术界里打开一条新路,或像萧伯纳及其费边社在政治思想界里开辟一条新道。可是,这个希望成了泡影,“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13〕而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曾一再表示要领导一种文学潮流,却苦于没有一个刊物来施展抱负。1925年5月,闻一多留美回国, 徐志摩也刚从欧洲归来,两个相见如故。后由徐志摩的介绍,闻一多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也因徐志摩的关系,闻一多和赵太侔、余上沅等一起加入了新月社。他们本想通过新月社的援助筹办一个梦想了五年的艺术剧院,结果依然是有心无力,只在艺专开办了一个戏剧系。不久,因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闻一多懊丧极了,另找了一个住处安下家来,“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次之则邓以蛰,赵太侔,杨振声等。”〔14〕经刘梦苇提议,他们商定借《晨报副镌》的版面办一个诗的刊物,派人与该刊的编辑徐志摩接洽,于是徐志摩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15〕并加入进来,《诗镌》就这样问世了。
《诗镌》每周四出一期,共出十一期,参与活动的除了徐志摩,闻一多,还有被称之清华‘四子’的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和刘梦苇,蹇先艾、朱大楠、邓以蛰等。刘梦苇是朱湘的同乡,于赓虞和蹇先艾都是经过刘梦苇进入这个圈子的。徐志摩所作的《诗刊弁言》,表明了他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提出“一首诗的音节……实在包含得有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等等的相互关系”;闻一多的《诗的格律》,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都是在理论上支持了他们的这个信心,因而深受同人的鼓励。至于他们刊出的作品,可以跟得上理论的虽则不多,总还有,闻一多的三首诗《春光》、《黄昏》、《死水》,都是完全站得住的。
诗刊同人对新诗形式上的注意,不单是个文艺观点问题,还包含着对文学潮流的看法。“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闻一多就认为王尔德这句话说得很对,而且照这样讲来,“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在他看来,又一种打着浪漫主义旗帜的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注重到文艺的本身,”他们的目的只在披露自己的原形,顾影自怜,善病工愁, 风流自赏。“要他们遵从诗的格律来做诗,是绝对办不到的”。而这也正是他和朋友们反对“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缘由。梁实秋远在美国,也在《诗镌》上发表文章,批评浪漫主义者太贵重人的心,对自己的生活作不必要的伤感。饶孟侃发表的专门评论,则指名道姓批评创造社的“感伤主义”。他说:“近年来感伤主义繁殖的这样快,创造社实在也该负一部分的责任”。〔16〕在当时,就连《诗镌》内部的人也难免受到“感伤主义”的指责,于赓虞则是突出的一例。他说:“在那些朋友中,说我的情调未免过于感伤,而感伤无论是否出自内心,就是不健康的情调,就是无病呻吟”。〔17〕因为对此不满,大概在《诗镌》出了六七期后,于赓虞就同它绝了缘。
《诗镌》于1926年6月10日暂告结束,此后改出剧刊。赵太侔、 余上沅等在剧刊上所主张的国剧,其实也是一种超人生的艺术,不以“利用艺术去纠正人心改善生活”为然,而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在他们看来,中国戏剧运动的失败在于“艺术人生,因果倒置。”他们这个国剧,是希望建筑在旧剧上面的,“它至少有做到纯粹艺术的趋向”,有做到歌、舞、乐三方面都是尽善尽美这一步的可能,所以他们“终于承认了它高贵的价值。〔18〕《剧刊》共同十五期,国剧运动过一阵,并没有什么实绩,因为他们初衷也是想“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国情与注意”。〔19〕
1927年春,新月社的一伙人萍踪偶聚在上海,合力办了一个新月书店,并于第二年3月10日出版了《新月》月刊。 《新月》版型是方方的,蓝面贴黄签,模仿了19世纪末英国《黄皮书》杂志的形式。这《黄皮书》内有诗、小说、散文,最引人注目是多幅比亚兹莱的画,“古怪夸张而又极富颓废的意味,志摩、一多都很喜欢它。”《新月》发表了一些文史哲的文章,但绝大篇幅是登文学作品和评论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沈从文的小说,陈楚雄的剧本,较有特色。新诗创作的阵容已不如以前的《诗镌》,于赓虞早就逃脱,朱湘留学美国,蹇先艾转向小说创作,杨世恩、刘梦苇、朱大楠三人先后去世,留下的是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从出第二卷以后,才有陈梦家、方玮德、方令瑞、沈祖牟、梁镇、俞大纲等新秀的出现。陈梦家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法律系时已开始写诗,曾受闻一多赏识;方玮德低陈梦家一年级读的是外文系,曾是闻一多的学生。这两人足以使闻一多自豪,他说:“拿《新月》最近发表的几篇讲,我的门徒恐怕已经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着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据吗? ”〔20〕
1930年前后,陈梦家与方玮德结为诗友,《悔与回》是他们二人同题诗歌的唱合之作。因为玮德的九姑方令孺的表兄宗白华也在南京,还有六合田津,他们几个算是小文会,各个写诗兴致正浓,写了不少诗。其中徐志摩每星期到中央大学讲两次课,认识了梦家和玮德两个年青的诗人,徐志摩说:“他们对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我奄奄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21〕这个诗刊是季刊,1931年1月20 日创刊于上海,徐志摩、邵洵美编辑。徐志摩在第二期的《前言》中说,五年前的《诗镌》“我们得认是现在这份的前身”,“我们这少数天生爱好与希望认识诗的朋友,想斗胆在功利气息最浓厚的地方和时日,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此刊以发表新诗创作为主,间有讨论和译诗。作者有已为《新月》撰稿的诗人外,再加入在北京的林徽因、卞之琳、曹葆华等。《诗刊》共出四期,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逝世,第四期为志摩纪念号。1932年7月30日,《诗刊》的停刊, 实际上是宣布新月的解散,因为在当月由胡适出面已结束了亏空的新月书店,新月所出的书籍包括《新月》杂志都已转移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唯美主义的另一支力量,是成立于1925年的狮吼社。该社出版的《狮吼》杂志,三年有过三次变化,“狮吼半月刊变成新纪元,新纪元变成狮吼月刊,狮吼月刊又变成狮吼半月刊了。”撰稿人有滕固、方光焘、章克标、张水洪、黄中、浩文、邵洵美,朱维基等。由于郁达夫、徐志摩与邵洵美趣味相投,往来密切,成了《狮吼》的知音,对邵洵美的诗、章克标的散文、滕固的小说都是称赞有加。
章克标、滕固、方光焘早年留学日本,受到过谷崎润一郎、厨川白村等唯美派作家的薰陶与影响。1920年在东京、滕固和方光焘共读佩特的论著,才启示了他对英国近代文学的爱好,后来又和邵洵美时时谈论先拉斐尔派的诗歌,使他不间断夙昔的爱好。〔22〕邵洵美、朱维基都曾到过欧洲,而诗的行程却是洵美的奇特,“以莎弗发见他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特莱尔,凡尔仑。当时只求艳丽的字眼,新奇的词句,铿锵的季节,竟忽略了更重要的还有诗的意象。”〔23〕为此,徐志摩还给过他一个“一百分的凡尔仑”的过分奖誉。
1928年12月1日,《狮吼》半月刊出完第十二期, 即改为《金屋月刊》,邵洵美、章克标编辑,新加入的撰稿人有叶鼎洛、倪贻德、曾虚白、郭有守、郭子雄、戴望舒、梁宗岱、何家槐。发表在第一卷一期的《色彩与旗帜》,表明了编者彻底的唯美主义观点:“我们决不承认艺术可以被别的东西来利用”,“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时代观念的工具文艺,我们要示人以真正的艺术”,“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从1929年1月1日至1930年9月, 《金屋月刊》共出十二期,以发表创作为主,兼有翻译,邵洵美、浩文的诗,章克标、滕固的小说,倪贻德、曾虚白的散文均占有显著的地位。
将唯美主义推向一个极端、一个顶点的是绿社。它成立于1930年,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人:朱维基、芳信、林微音。他们办有《绿》杂志,朱维基写诗,芳信写散文,林微音写小说。《绿》从1930年出至1933年,以后改出《诗篇》月刊,朱维基主编,1933年11月1日出版第一期。 发表在第一期上的《第一次说话》,是实际上的发刊词:“在一个伟大的激荡里,四周有无数支的急流无定地,相反地或是交叉地流动着,我们要站定我们的辉发着力的光芒的身体,……殉道地为艺术而中砥着这引导到万劫不复境界去的狂潮。”“我们要怀抱着凄寂、悲愤,或着激昂的情感的微妙唱出我们的无可奈何的歌曲,为情或是为美。”
《诗篇》月刊共出四期,于1934年2月1日停刊。前面三期还颇为热闹,邵洵美、庞薰琹、文怀朗、徐圩等诗人也参与了活动。其实,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在他们不顾一切地推崇美的后面,似乎隐藏着一种缺乏自信和焦虑不安的感觉,所以《诗篇》出了第三期后,他们便风流云散了,只剩下朱维基一人为第四期撰稿,这种结局使他自己好不尴尬,难以堪当。
唯美虽然不是多数人的见解,但它在有限范围内毕竟产生深远影响。不经过一番最后努力,这一场文学运动是不会自行消失的。曾经以自己的热情支持过这一运动的作家,现在正汇于一处,突然闪出一丝光亮,这就是1935年11月出现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诗刊》。孙大雨、梁宗岱、闻一多、林徽因、方令孺、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孙毓棠、曹葆华等参与了这新《诗刊》的活动,他们一开始所表现的实际是继续着新月派的探索,与唯美主义还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关系。不过在中途,却不知不觉地转了方向,多少像在暗示一个有待去发现的新的艺术领域。及到1936年,戴望舒邀请孙大雨、卞之琳、梁宗岱、冯至共同主编的《新诗》杂志创刊后,就明示了一个道理:唯美主义文学已不可避免地要被现代派所取代,这没什么可忧虑的。一个时代已告结束,新的时期就要开始了。
注释:
〔1〕陶晶孙:《记创造社》,收入《牛骨集》上海太平书1944 年版。这句话也许可信,因为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佐滕春夫、厨川白村等当时标榜的她就是新浪漫主义,创作社的作家喜欢读他们的作品,还多少有过交往,受他们的启发,同时有心想和文学研究会对垒,遂以新浪漫主义作为旗帜也正是情理之中的事。
〔2〕鲁导:《现代小说导论(二)》,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3〕参见《卷首小语》,载《浅草》第一卷第一1923年3月25日。
〔4〕林如稷《编辑缀话》,载《浅草》第一卷第一期。
〔5〕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
〔6〕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
〔7〕灵感。
〔8〕《一封叙(弥洒)起源的信》,载《弥洒》1923年第4期。
〔9〕《载以弥洒》1923年第一期、第二期。
〔10〕《致吴景超、梁实秋》(1922年10月10日),《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致梁实秋》1922年11月26日)。
〔12〕《致闻家四》(1923年中秋前一日)。
〔13〕徐志摩《剧创始业》,载《晨报副刊·刊》创刊号,1926年6月17日。
〔14〕闻一多:《致梁实秋》(1926年1月23日)。
〔15〕《诗刊弁言》,载《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号。
〔16〕《感伤主义与创造社》,载《晨报副刊·诗镌》第十一号。
〔17〕《(世纪的脸)》,北新书局1943年6月初版。
〔18〕余上沅:《国剧运动》。
〔29〕徐志摩:《剧刊始业》。
〔20〕《致朱湘、饶孟侃》(1930年12月10日)。
〔21〕《(猛虎集)序》,新月书店1931年8月版。
〔22〕唯美派的文学)自记》,光华书局1927年7月版。
〔23〕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4月初版。
标签:唯美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莎乐美论文; 郭沫若论文; 创造社论文; 南国论文; 闻一多论文; 诗歌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