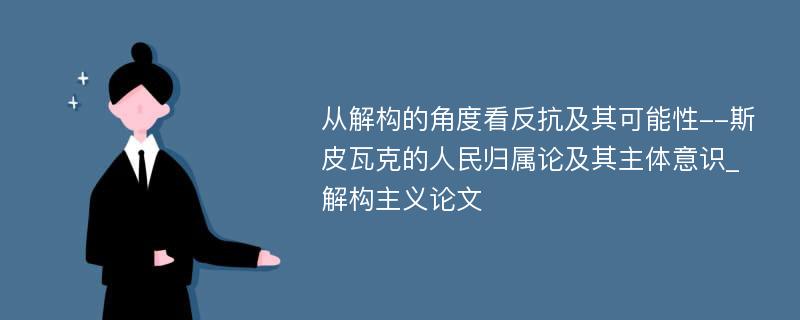
解构视野下的反抗及其可能性——斯皮瓦克论属民阶层及其主体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皮瓦克论文,阶层论文,可能性论文,视野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皮瓦克(G.C.Spivak,1942-)是当代美国最具有冲击力的批评家之一,通常她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并称,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文化理论著称于世的。但是,斯皮瓦克的批评杂糅了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方面,以至于人们通常也称斯皮瓦克是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Spivak IO ix)。斯皮瓦克的批评所涉及的这些理论资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叠加,而是呈现出她所说的理论“协商”的状态:相互碰撞和暴露其历史局限,同时也相互补充,使其更能适应新的现实。解构主义对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影响就是如此。例如在《他者的世界》(IO)中,斯皮瓦克在谈到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时说:“在过去几年里,我同样开始明白,不仅仅是解构简单地为女性主义者开掘了道路,同样,女性主义者也为德里达提供了空间”(Spivak 84)。而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碰撞结果则是暴露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和经济决定论等问题的本质主义倾向;相反,解构主义则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显示出它对于现实问题的忽视,因此斯皮瓦克明确反对为哲学而哲学、为理论而理论的方式去处理德里达,相反,她认为需用政治的方式去解读(Landry 75)。 整体上说,解构主义对斯皮瓦克的强大影响在于为其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她认为“解构主义,它实际上是一个方法的名称[……]它是看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做事情的计划,是看待做事情的方法的一种方式”(Hara-sym 133)。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对独断性的解构,同时达成对差异性的解放。显然这与传统形而上学以牺牲特殊性来追求普遍性,最后以真理的名义达到普遍性的独断这种本质主义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如果把斯皮瓦克的解构主义思维仅仅看成是对本质主义的颠覆和否定,那也是有问题的。这一点与我们表面上对解构主义的那种激进式的理解不同。解构主义对斯皮瓦克的吸引力与其说在于这种简单而痛快的否定,不如说更在于对这种过快的、激进的否定的再否定。她曾经说过,“当我第一次阅读德里达时,我不知道他是谁,看到他事实上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去揭露西方的哲学传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Harasym 7)。应当说,这种从哲学内部进行的“颠覆”的方式,才是吸引斯皮瓦克的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其提供的“革命性的思维方式转换”的关键点。有时,她也把这种方式称为对于“我们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东西”的批评。这种我们“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东西是什么呢?恰恰就是各种形式的本质主义。换句话说,我们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非本质主义的途径,如果存在这样一种非本质主义的途径,那解构就只能是一种没有任何依托的虚无主义和以游戏为主的空洞的享乐主义。当然,解构的“本质主义”只是一种方式和策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不是把它作为事物存在的方式,而是作为人们对有些事物进行批评时必须采纳的某种方式”(Harasym 51)。因此,这是一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 解构主义的策略性,尤其是对本质主义的策略性理解不仅对斯皮瓦克重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重申马克思的核心批判精神提供了重要方法,同时也为斯皮瓦克探讨反抗之可能性的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 斯皮瓦克认识到,解构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我们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东西”的批评,批评的手段本身就不得不来自于批评对象。但不同的是,一个在于隐藏本质化过程中的主体参与,一个承认这种参与的存在;一个在于使本质权威化,而一个在于临时性的采用本质的实践作用。正是在这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斯皮瓦克找到了“策略”存在的空间。从辩证的关系来看,批评实践要产生作用,也必然要求建立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的临时稳定性。因此,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拆解性的工作,因此要发挥解构主义的颠覆性作用,那么抵抗实践则必须依托某种“建设性”或者肯定性,以找到可以称之为“反抗”的可能性和反抗的力量来源。就这个问题而言,斯皮瓦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建构属民群体的主体意识。在这里,“属民”(Subaltern)及其“主体意识”正是斯皮瓦克策略化地使用的本质主义式的概念。 斯皮瓦克的“属民”这个概念,特殊的地方在于其“不能说话”,①即缺乏主体意识这一方面,因此建构属民的主体意识就显得十分迫切。事实上,在葛兰西首先使用“属民”这一概念的时候,它就具有“不能说话”的初步特征,它主要被用来指南部意大利的乡村农民这个没有组织的人群,这个群体没有一种作为一个群体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并因此而容易顺从于统治观念、文化和政府领导,他们是“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级”。“在定义上,下层阶级是不统一的,也无法统一”。“下层社会集团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即使他们有统一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会“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打断”(葛兰西36)。从这些特点我们看出,属民的“不能说话”,最重要的是没有一种统一的集体性,最终的原因则是由于文化上的顺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印度“属民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Group)扩展了葛兰西这个概念的原初含义,用来指“南亚社会中的从属群体的普通属性,不管它是根据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务还是根据任何其他方法来进行表述”(Guha 35)。而斯皮瓦克心目中的“属民”则具有更加宽泛的所指:“知识暴力所标示的封闭地区的边缘”,或者“被压制的、沉默而不出声的中心。”“处于文盲的农民、部族、城市亚无产阶级的最底层的男男女女们”(罗钢 刘象愚118)。不仅在范围上有一定的变化,同时最重要的是,斯皮瓦克强调了这一群人所遭受的知识和文化暴力,即他们的“沉默”特性。当然,这种“不能说话”主要来自于他们没有独立再现自身的意识和话语方式,只能处于“被别人说”的状态,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绝对他者”。由于主体性的缺失,他们既不能表达自己,同时也不可能被别人真正表达,这样一来,他们一方面司空见惯,但另一方面却有些类似于“外星人”。属民的这种“绝对他者性”,在解构主义的伦理问题上有所涉及,并且是一个解构意义上被永远延迟的、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困境”(aporia),是一种“子非鱼而安知鱼之乐”的困境。既然如此,让属民群体渐渐学会“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最终摆脱顺从的命运何以可能?显然,针对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反本质主义进行绝对化,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谈论属民及其主体意识,当然也就谈不上抵抗的问题。 在反抗的问题上,法国当代思想家们留下了许多新颖而又值得争论的话题。其中就包括把反本质主义绝对化的倾向。无论是德里达还是福柯,拉康还是巴特,他们在理性反思大潮中,几乎都对人的主体性持怀疑态度。某种意义上说,对主体的自我同一性的怀疑甚至是整个后思潮的核心所在,这也可以说明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对德里达的强大影响。②总体上讲,这种解构的激进倾向对西方文化传统尤其是知识传统来说,发挥了十分犀利的批判和揭露作用。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实践问题上,落实到我们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霸权等问题上,我们就会突然发现激进的批判理论变成了保守主义,甚至完全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共谋,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在解构批判对象的时候,把反本质主义绝对化了,没有注意到本质主义的策略性存在空间,因此不得不面临自身也被解构的问题,绝对化就是忽视策略性,也就是忽视敌我的区分,这就真的变成了德里达说的“既是解药,也是毒药”的情况。 在《属民能说话吗?》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对福柯和德勒兹的批评所针对的正是这个问题。由于坚持对理性主体的解构,并且把哲学上的严格放到实际的日常实践中,福柯和德勒兹对边缘人群的反抗不得不放弃知识介入,形成著名的“自动斗争论。”与此相应的还有今天媒介研究中的“符号斗争”、列菲伏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符号游击战”、博德里亚的“沉默的反抗”,等等。③这些思想家都因为后时代的主体观念,尤其是对集体性主体观念的怀疑和反对,在反抗的问题上不得不放弃集体性力量,甚至放弃有意识的主体抵抗行为,从而把抵抗问题变成了一种基于欲望和本能的东西,变成了条件反射式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甚至把一切的符号领域的非统一性看成是斗争的一种表现。那些在各种领域中遭受压制的人群,尤其是像斯皮瓦克说的属民这种他者群体,他们不仅丧失了集体性成为单个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丧失了理性主体,成为了一个本能的人,从此也就不得不一个人,而且只能在梦中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那些遭受压制的人群的命运实际上不再有任何关系,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形式的暴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最终与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个目标相违背,因为当初宣称“理性主体的解体”,正是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对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丢失,也许正因为如此,福柯才遭到赛义德等人的强烈批评。④ 根据解构主义理论,事物的本质,或作为其根据和起源的东西是一开始就缺场的,本质只是建构的产物。⑤真正存在于起源之处的只能是事物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事物借这种差异来对象化自身,并从这种差异中留下本质的踪迹化形态。但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隐藏了这种差异关系。反过来说,要确立对于事物的稳定的、“本质”性的认识,必然要求这一隐藏行为,“他者”作为非本质的东西被排斥出去,进入一个绝对的沉默的深渊之中。但是,本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知识、真理的建构特性和对他者的压制性等,哲学地讲,又是一种不可能避免的东西。“解构不是说没有真理,没有主体”(Landry 27-28),而是说我们必须要清楚真理和主体的建立过程,搞清楚哪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彰显,哪些东西又被遮蔽起来。也就是说,要反对的不是本质的建构本身,而是对本质进行权威化的倾向以及它对建构特性、压制特性的隐藏和否定。另一方面,在一个二元对立体中,受压制的他者一方要真正摆脱自己的处境,则首先必须从本质主义的角度保持自身的同一性,也就是保证一种反抗的主体性力量的存在,而不是首先把自己“解构”掉。这是推翻等级压迫的第一步,其次才是对自身权威也进行“擦除”。从这个角度上说,解构主义的反抗首先不是二元对立的消除,而是二元对立的反转。而“策略上的本质主义”正是为了确立这种反转的力量,这有点类似于“以暴制暴”。斯皮瓦克认为,这本身也是德里达倡导的一种解构策略。假如没有这种策略性的考虑,反抗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策略上的本质主义”首先是对二元对立等级秩序的一种颠倒,斯皮瓦克引用德里达的话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熟悉的哲学上的二元对立中,一直存在粗暴的等级。一个控制着另一个,占着优越的位置。解构这个对立,首先要做的就是推翻这种等级,以暴制暴。(Spivak TP lxxvi) 当然,对二元对立进行颠倒,不是让弱势一方取得新的霸权;相反,斯皮瓦克也强调,策略的含义还在于,这种本质主义只在具体的反抗中起临时性的作用,它是首先要做的,但不是最终目的,而最终要做的,则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本质的临时性质,并且在事后进行严格的“擦除”,以免成为新的压制力量。 在这个方面,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恰恰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解构主义者,他的许多概念都被批评为犯了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的错误,但是斯皮瓦克经过分析后认为,这些概念的建构恰恰都是从策略性考虑的,换句话说,是从实践需要而不是从哲学上的“正确”去考虑的。例如他的“价值”概念,“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等等。尤其是“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她认为,马克思发明这一概念的目的不是要发现和永远地确立这样一个阶级,相反,是为了消除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一切阶级。这就充分表明,无产阶级的概念作为一个忽略了内部存在的相当多的异质性因素的本质主义的概念,只是在策略上使用的,正因为其反抗的是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目的恰恰在于解放各种差异,因此这种本质主义的使用也就具有了合法性。就反抗的实践而言,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一样,斯皮瓦克的“属民”、“属民女性”等概念也主要着眼于树立反抗的主体意识和力量,通过策略性的命名来“号召”一种在具体情境中可供集中力量的共同性。正如斯皮瓦克认为的:“阶级意识并不是指那种基础意义上的意识——即普遍意义上的意识。[……]阶级意识本身在描述的意义上是策略性的、人为的和号召性的”(205)。同样,提倡“女性意识”、“女性经验”也不是为了找寻一种关于女性的恒定、客观的“本质”,并把它与“男性”截然对立起来;相反是为了消除这一对立意义上的“女性”,最终形成平等的、既有差异但又无中心的延异局面,等等。 但是,“命名”只是一个基础,一种知识分子或者说批评主体的“号召”而已,它是某种建构的集体的“共同性”的名称,但并非事实上的“共同性”本身。并且,这种“共同性”的建构也不是任意进行的,“无产阶级”也好,“属民”也好,也绝不可能仅仅是“能指的滑动”,完全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相反,对其“本质”的把握和建构,是以交往经验为基础、以“属民”本身的异质性和他者性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一种斯皮瓦克说的尽量尊重差异的“共同性”,一种“最小化的共同性”。只有这样,一种具有其自身统一性的主体意识才有出现的可能,才可能真正作为一种力量“发出声音”。而要找到这种他者的“本质”,必然要求首先建立批评主体和作为属民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但问题在于,他者之所以是他者,就在于其不能表达自己,它没有自身的话语来表述自己的经验。这就使得双方的交往是有缺陷的,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厢情愿的单向交往,这使得属民阶层的主体意识积累表面上看是一种简单的命名行为,而实际上则是一种漫长而困难的积累过程。因为,要避免简单命名和强制性动员带来的粗暴和伤害,建构一种尊重差异的,有自身主体依据的集体性主体意识,是一种既主动又被动的过程,所谓主动,是指主动交往,而被动,则是指交往的最后结果是没有保证的。这种交往,也就是德里达后期十分关注的解构伦理,或者“他者伦理”问题。 按照斯皮瓦克对解构的策略性的理解,以尊重差异为基础的“最小的共同性”,是他者事物的某种类似于本质的“东西”,并且这种“本质”只能是在某个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临时的稳定性”,而不是普遍化和恒久化的,否则就与形而上学的本质观念无异,谈不上解构的“策略性”了。但即使是一种“临时的”东西,它总归是某种意义上的“有”而不是“无”。既然如此,那这种临时的“最小共同性”是一种怎样的共同性呢?“绝对他者”既然是一个处于黑暗之中的、“沉默”无声的对象,那我们如何才能得到支撑这种“共同性”的材料以建构其主体意识呢?在这里,斯皮瓦克同样从解构主义的角度认为,虽然“他者”的本质就像事物的本质一样是缺场的,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留下了“踪迹”。 转向“绝对他者”之后的德里达把“绝对他者”的“踪迹”称之为“不可能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impossible)。德里达的这种“经验”观来自于他的解构伦理,并且建立在勒维纳斯的关于“他者”问题的伦理观念之上。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德里达认为,勒维纳斯对“他者经验”的注重,为批判和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事业带来了希望和梦想,因为他呼吁我们“从希腊逻各斯中脱位”,回溯到一个“甚至不再是源头和场所的东西[……]某种不仅先于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甚至先于所有希腊源头就已被突出的先知语言,趋向那个希腊的他者。”而这种思想要求一种“伦理关系”,即“无限作为他者的那种与无限性、与他人的非暴力关系——因为唯有这种关系方能够打开超验的空间并解放形而上学。”而这种与他者的非暴力伦理关系必须求助于“经验”,“要求在对经验本身的某种求助[黑体为原文所加]中获得理解。而经验本身和那种经验中最无法还原的东西指的正是朝向他者的通道和出口;而他者本身和他者中那最无法还原的他性,就是他人。”正是独特的、无法还原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朝向他者(“他性”或“他人”)的通道和出口。也就是说,正是这一“经验”达成了我们走向他者的桥梁。尽管他者仍旧是“完全他者”,一种“拒绝任何范畴和整体将之封闭起来的东西”,是“不再由传统的概念领域进行描述的”、“抗拒一切哲学素的东西”,但他者与主体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得以相互反馈其经验的临时空间,而经验本身则为这种相互反馈的伦理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基础(136-37)。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勒维纳斯的伦理观同德里达解构思想一样,认为在这种“经验”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强调他者的伦理优先性,而不能从主体中心出发。也就是说,“我”时刻准备为了他者,并在完全他者的踪迹出现之前就已经准备着。主体(subject)本身就内含了服从的意思,因此,“主体性”也就是“我”毫无保留地服从他者的“服从性”。德里达认为,正是根据“我”对他者的这种“责任”的不可化约的优先性,这种优先于“合法化”和“普遍化”的责任,使得勒维纳斯的伦理学超越了属于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的传统伦理学(Critchley 17-18)。对他者伦理的关注,使得解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通向“沉默的他者”的、与他者“对话”的可能性。对他者的经验是一种对“那建构了起源而又本身不是起源的事物的踪迹”的经验,德里达称之为“不可能的经验”即一种经历“绝对他性”(radical alterity)的经验(Spivak CP 426)。而这个过程必然是一种“困境”(Aporia),例如,我们只能通过自身对“生”的经验来“经验”和思考“死亡”,但“生”的经验本身又不是对于“死亡”的真正经验,因此它是不可能的经验。同样,正是从“非正义”的经验中,我们“经历”了“不可能的”“正义”,从“不自由”的经验中我们揭示了“自由”,斯皮瓦克说: “困境”是在被经历过的经验中才为人所知的,尽管他们是不可能经历的(non-passages)。它们因此在被抹擦的过程中被揭示,因此成为不可能的经验。(Spivak CP 426) “在抹擦中被揭示”与“不在场的同时留下踪迹”表述的是同一种意思。“经验”在这里既意味着抹擦,也意味着保留。抹擦的是那种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客观的“本质”,而“经验”中保留的虽不是“本质”,但与“本质”相关。从主体的非本质的、片断的、历史性的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某种与本质相关的东西,并得到一个人对自身主体位置的感知和把握。⑥同样,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经验那充满各种异变性和差异结构的汪洋大海中,获得绝对他者的主体信息,最终形成一种斯皮瓦克称为微积分效果(calculus of action)的东西。如果形成这种效果的所有经验可以称作内容的话,那这种效果就可称作“本质”,这是一个必须建立的最低限度的基础: 在我看来,本质就是某种内容,但全部的内容不等于就是本质。为什么我们对这个词如此敏感?为什么不抛开本质这个词?因为没有一种最小程度的本质,一种剩余和保留下来的东西,就不会有交流。差异决定了这些可流通的本质。(Spivak OT 18)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斯皮瓦克的最终的目的,那就是使我们找到一个相互流通、关联并可能形成集中的基础,即作为痕迹之总效果的“最小程度的本质”,否则,差异是什么“东西”之间的差异?在这个问题中,“东西”就是那最小程度的本质。在反抗的主体意识问题上,这种策略上的、能够在反抗中起到临时作用的“本质”就是主体意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不可能的经验”在策略的意义上打破了差异个体之间的坚硬外壳,从而在主体性上获得了反抗的可能性,这大概也是解构的他者伦理所具有的建设性和干预力量所在。 首先,斯皮瓦克十分注重她称之为“心理传记”的东西。这些“传记”作为一种经验的微积分材料,使得逐渐唤起被压制者或“属民阶层”的主体意识具有了可能性。通过发掘女性自身的“心理传记”,即注重女性自身的独特生活经验,就可以逐渐走上“渐有声息”的道路,从而最终走出男性话语的阴影。更具体地说,是通过女性的“性主体经验”和“生产经验”两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女性的心理传记的“写作”。因为这正是女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性失去自身言说能力的最重要的领域。她通过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认为女性应该意识到在性快感方面所处的受压制地位,找回自己作为性感主体的经验;另一方面同时强调“子宫”在生产经验问题上的重要性,把它进一步同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联系起来。通过女性的这些“共同意识”、“共同经验”的挖掘,一步步确立起沟通基础,渐渐寻找并形成一种“主体”效果,从而为她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中所遭受的“双重压迫”和“超级剥削”提供可能。⑦ 而在属民阶层“不能说话”的问题上,斯皮瓦克认为,属民的主体经验实际上面临的是一种十分复杂和宽广的领域。属民作为一个阶层的声音在已被“认知暴力”限定甚至消除的情况下,它的主体意识只能从有限的反抗经验中得到恢复。当然这种反抗经验不是直接的对抗,而是所有存在于殖民话语边缘的那些不协调的声音,因为那些直接的反抗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各种精英话语和殖民话语所污染了。它已经变成了民族解放和殖民拯救叙事的一个部分。因此,斯皮瓦克有所保留地赞同印度“属民研究小组”的那种开拓性工作,即通过重新发现属民反抗经验的历史,打断精英话语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下的历史叙事,暴露其局限、揭示其虚假的同一性,从而标识出属于属民阶层自身的位置。当然,由于“认知暴力”和精英话语的既存性,这些声音不会是纯粹的,这也是斯皮瓦克批评“属民研究小组”的历史写作倾向的原因。这些声音分散、不连续、零碎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让我们更加体会到“经历”那“不可能性”的含义。但也只有从霸权话语的“打断”和“空白”之处,才能反观自身经验的存在,从而在微积分的意义上渐渐形成主体意识,走出属民“不能说话”的困境。在这个方面,斯皮瓦克身体力行,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档案中,通过大量的边缘文本的解读,去发现殖民话语和帝国主义叙事文本中的裂痕,并努力从中放大边缘的和潜在的反抗声音,尤其是那些处于帝国主义和男性双重压制下的第三世界女性的声音。这既是对帝国主义殖民话语的直接挑战和解构,同时也是对属民主体意识的一种艰苦的“微积分”过程。 也许正是因为对“微积分”过程的注重,斯皮瓦克宁愿通过各种复杂的文本批评、文学作品解读、世界范围的文学比较,通过研讨会、教学以及田野调查、走访和体验它认为的属民群体的生活等等方式,来唤起和重建女性和属民的主体意识,而不愿意采用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方式。科林·麦卡布(Colin Mac Cabe)在为斯皮瓦克《他者的世界》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曾经对斯皮瓦克的工作进行了评价,她认为,斯皮瓦克与那些对起源的原初性的解构式怀疑不同,她对现代性或者六十年代那种复苏解构的激进潜能没有什么热情。她巨大的当代热情在于发挥了六十年代的某些概念和方法,把它运用到了对复杂的当代情势的定位和把握之中。它既不是美学,也不是政治学,而是一种知识伦理(Spivak Io xii)。斯皮瓦克之所以更倾心于这种“知识伦理”,这种类似于启蒙的方式,原因在于她对集体性伦理和集体性政治的反思。 在新近出版的斯瓦番·查克拉巴蒂(Swapan Chakravorty)与斯皮瓦克的访谈中,斯皮瓦克清晰地说明了他对集体性表示怀疑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集体性几乎总是太快地就被建构起来”。而“国际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上的变革,而只是一味地动员。集体性是人为的,没有连续性并且过快地制造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要使他们向往一个坏的资本主义是十分容易的原因”(113)。相反,资本主义的成功则是“通过像儿童电视这样的商业文化的一步一步的精心的打造过程”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的优点是从点滴做起,“剥削者也是知道不可能通过集体性来进行的”。在她看来,国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曾关注底层人的主体性问题。他们所做的就是动员”,这太快了,而历史是漫长的。虽然一个政治家选择集体性在有些时候是必要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关注的则是主体意识的问题:“我现在感兴趣的是对主体结构施加影响,希望出现不自觉的主动行为。既然这是我能够做的事情,无论好坏”(Chakravoty 113-15)。不过,如果我们由此就认为斯皮瓦克完全否定了集体性的作用,那也是有问题的。根据解构主义的双重性和策略性,我们应该认识到她所反对的不过是那种“过快的”、动员性质的集体性,当然更反对那种以普遍性为目的的、本质主义的集体性。因为这样的集体性是纯粹号召的、没有基础的,因而也只能是通过强制才能达到同一的集体性。它不仅本身造成压制,同时这种集体性也随时可能崩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缺乏主体意识的支撑。如果有利于唤醒这种主体意识,有利于积累批判力量并且只是作为策略,而不是把他经验主义化,那么集体性就依旧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一切都要落实到实践的问题上,而不是死守某种精致的理论。从这个角度看,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就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实证概念,而是为了分析雇用问题而进行的“一种修辞性上的虚构”,是“必要的方法论前提”(Harasym 114)。同样,她认为,“对我来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叙事不是一种主导性叙事,阶级的观念也不是不可动摇的观念。生产方式叙事是一个在上下文中起重要作用的前提假设。[……]如果我们自己亲自看看马克思自己的文本,在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文本的基础上,我们就会得到另一个版本的马克思”(Harasym 161-62)。她反对只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主义的做法,强调不能用那种机械的、非策略性的眼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包括他的“阶级”概念。她批评了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写作中“把阶级范畴完全琐碎化”的倾向:“他们不使用阶级概念,不是去完善、扩展阶级概念,而是作为一个未经检验的普世性概念而简单拒绝”(Harasym 152)。 因此我们看到,解构主义的“踪迹”除了否定的意义,同时也有着明确的“肯定”的意义,斯皮瓦克认为要避免解放事业成为无政府主义,批判和反抗力量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有必要策略性地使用这种肯定性,即一种有意识的本质主义的借用。要真正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各种本质主义思维和中心主义思维进行有效反对,这种本质主义的借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而从文化政治和知识伦理角度去关注属民阶层及其主体意识,积累自身的反抗力量,正是这样一种策略化的借用过程,也是反抗之可能性所在。 斯皮瓦克把解构主义思维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实际上是用一种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实践意义的方式承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她不断地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极端态度,努力从解构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写作进行情境性的辩护,另一方面也顺势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进行解构性重铸,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尽可能地发挥其批判资本主义的潜能、发挥其反压制和反剥削的作用。因此,斯皮瓦克的解构思维,不仅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说是一种以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内在的颠覆”,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也是一种“从内部进行的批判”,因为她一方面坚持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合理性,尤其是作为一种再现方式的策略性和合理性,同时又看到了新时代背景下把“阶级”概念中心化会带来的问题。与解构主义对策略性和情境性的关注一样,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本身也是一个情境性的和再现性的概念,斯皮瓦克对阶级概念进行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处理,同样也是从情境性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当然,对阶级概念的种族化和性别化处理,也并非要彻底否定马克思说的那种阶级的存在,应该说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最终都指向资本主义批判。这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状况,也许正是斯皮瓦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之独特性所在。 ①见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9。 ②可参考Derrida."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Writing and Differen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8.196. ③可参考罗杰·迪金森等编《受众研究读本》中的相关讨论,单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詹姆斯·库兰等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等。 ④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London:Faber and Faber Led.,1984.158-60,246-47.另可参考中译本:《世界、文本、批评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八,九,十章。 ⑤关于起源问题的讨论,可参阅Derrida.Of Grammat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1976.61-62,74-75. ⑥参见Harasym,Sarah,ed.The Post-Colonial Criti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0.68. ⑦可参考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见Spivak.In Other Worlds.New York:Metheun,198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