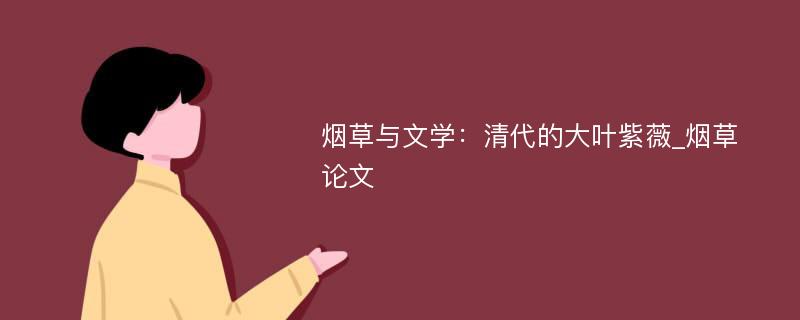
烟草与文学:清人笔下的“淡巴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人论文,笔下论文,烟草论文,文学论文,淡巴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2)03-0083-(11)
明朝万历年间“淡巴菰”(烟草)传入中国,很快便南北风靡。笔者认为,它应先由西班牙商人自南美传入吕宋,再依次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中国各地,时间则迟至万历中叶(1600年前后;若由葡萄牙人首先传人,时间上不至于如此之晚)。烟草之名,本写作“菸”,后来有“淡巴菰”、“金丝醺”、“盖露”、①“佘糖”、②“发丝”(以上名称均见于姚旅撰《露书》卷十),“丹白桂”(《清实录·太宗实录》),“仁草”、“八角草”(熊人霖撰《地纬》),“淡把姑”、“担不归”、“淡肉果”、③“金丝烟”(均见于方以智撰《物理小识》卷九),“干酒”(叶梦珠撰《阅世篇》卷七),“烟酒”(杨士聪撰《玉堂荟记》卷四、汪灏等撰《广群芳谱》),“香烟”(《在园杂志》卷三),“打姆巴古”、“大籽古(菰)”、“醺”、“芬草”(均见于汪师韩撰《谈书录一卷》及《金丝录·题词》),“相思草”(阮葵生撰《茶余客话》卷九),等等;“淡巴菰”、“淡把姑”、“淡白果”、“丹白桂”、“打姆巴古”显然都是西班牙语tabaco的不同音译(按:疑“担不归”亦为“淡巴菰”的转音)。当然,最普遍流行的词就是“烟草”。
明清文献对烟草之来源论说纷纭,除源于吕宋、日本、朝鲜诸说之外,尚有“见于佛经”(如纳兰性德《渌水杂识》卷二、④方孝标《钝斋诗选》卷一六、⑤田霡《鬲津草堂诗注》及赵之谦《勇庐间诘·自序》)、“见于唐诗”(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见于《宋史》(陈琮《烟草谱》卷四引石杰语,无出处)者。因久无确解,最后竟一致认定“淡巴”源于邻近吕宋之小国,“淡巴菰”自然便是此国独有的“菰”种了。⑥
烟草在中土得到迅疾播传,至崇祯末年便已“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问”;⑦方孝标(1617—1697)于顺治后期得见塞上烟草种植之风,其《吃烟》诗云:“革囊铜管偕刀璲,已见吹嘘遍九州”;⑧乾隆时期,吴江人陆耀(1723—1785)撰《烟谱》,称其时“士大夫无不嗜烟,乃至妇人孺子亦皆手执一管。酒食可缺也,而烟绝不可缺。宾主酬酢,先以此物为敬”。⑨这样一来,烟草种植日益拓展,自然要侵害粮食生产,影响国民生计。以此之故,自明崇祯朝以及清天聪初年以来,历朝皆有烟草之禁。⑩禁烟对吸烟之人影响有限,但使不少名公巨卿谀颂烟草的诗词很少收录于自己的诗文别集。不过,无论如何,烟草事实上自晚明伊始便以骎骎之势广泛介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乃至生命之中。
关于烟草的记录,晚明文献甚少,而有清一代则歌咏词唱相对较为丰赡,并有烟草专书数种。这些著述自然蕴含了一些烟草与文人骚客的话题。不过,大多为文献辑录,很少就现象再作更深层的思考。清末民初周馥(1837—1921)赋《悯农》诗五首(辑入徐世昌编《晚晴移诗汇》卷一百六十八),分别吟咏麦、樵、烟、茶、田,可见烟草至20世纪初已成为农业生活的一部分,词人骚客之讽咏也在在皆有。但是,相比于学界对酒、茶、樵等与文学之关系的论述,烟草与文学之关系可称被全然漠视。有鉴于此,笔者欲对其稍作探讨。因资料绝大部分出自清代,故以“清人笔下的‘淡巴菰”’为副题。
一、“淡巴菰”与名公巨卿
烟草传入中土,名公巨卿多酷嗜者。据《玉堂荟记》,晚明天启年间烟草流行,一亩之收可敌田十亩,民多种植者。崇祯十二年(1639)有烟禁之令,后洪承畴(按:事在崇祯十四年)以戍边兵士之需为由而解禁。(11)明清鼎革之后,吸烟风尚依然如故,酷嗜者之中不乏位高权重的大臣。据李调元(1734—1803)《淡墨录》云,康熙不吸烟,也厌恶大臣吸烟:“上南巡,驻跸德州,命侍卫传旨:朕平生不好酒,未能饮一斤,总是不用。最可恶的是用烟,诸臣在围场中看我竟日曾用烟否?每见诸臣私行在巡抚账房偷吃,真可厌恶。且是耗气的东西!不但我不吃烟,太祖、太宗、世祖以来都不吃烟,所以我最恶吃烟的人。”(12)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则记录康熙南巡驻跸德州时,以水晶烟管赐酷嗜淡巴菰的陈元龙(1652—1736)和史贻直(1682—1763),“一呼吸之,火星直达唇际,二公惧而不敢食。遂传旨禁天下吸烟。蒋学士陈锡《恭记》诗云: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怀。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13)但是也有别的文献表明,康熙并不拒绝西洋传教士所贡烟草。《熙朝定案》载,康熙首次南巡(1684)至南京,耶稣会士汪儒望(Jean Valat,1599—1696,法国人,1651年人华)、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1623-1696,意大利人,1659年入华)献方物4种,康熙命留“西蜡”,赵之谦《勇庐间诘》认为所留者乃烟草;(14)另据意大利人、遣使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1710年入华)记载,传教士在康熙花甲之寿时献巴西烟叶与欧洲葡萄酒,被康熙视为最稀罕之物。(15)
乾隆时代吸烟风气更盛,李伯元(1867—1906)撰《南亭笔记》载:“北京达官嗜淡巴菰者十而九,乾隆嗜此尤酷,至于寝馈不离。后无故患咳,太医曰:‘是病在肺,遘厉者淡巴菰也。’诏内侍不复进。未几病良已,遂痛恶之。”(16)据此,则乾隆亦曾嗜烟。李伯元《南亭四话》又载,咸丰曾赐长洲彭文敬(按:即清道光、咸丰间名臣彭蕴章)一白玉烟壶,上镌山水,一背纤,一乘舟,极其工细,并有乾隆手制诗。诗云:“船中人被名利牵,岸上人牵名利船。江水滔滔流不住,问君辛苦到何年?”(17)由此可知,彭蕴章应该也是烟客。
鼻烟自晚明起也传入中土,烟叶便不仅用嘴“吸”,同时亦可用鼻“嗅”。不少文献表明,各色各式的鼻烟壶常常成为清中前期外交场合的新宠儿;(18)使用者多为高官显贵,而且整个清代盛行不衰。如光绪嗜鼻烟,据载每晨必饮茶、闻鼻烟少许之后,方“诣孝钦皇后宫行请安礼”;(19)李调元咏鼻烟诗称“达官腰例佩,对客让交推”;(20)嘉庆、道光间升寅(1762—1834)撰有《戈壁道中竹枝词》,一云:“皮冠冬夏总无殊,皮带皮靴润酪酥;也学都门时样子,见人先递鼻烟壶”;(21)吴省钦(1729—1803)认为,吸烟“于味不于臭,勿乃享敝帚”,不如鼻烟“顿消肤粟寒”、“扶病豁朦瞍”;(22)晚清传抄的“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云,和宅抄没的巨量财物中有大量的西洋器物,其中,白玉烟壶800余个、玭尔烟壶300余个、玛瑙烟壶100余个、汉玉烟壶100余个,(23)这些都是鼻烟壶。又据记载,晚清时某宗室素喜鼻烟,壶盖或珊瑚、或翡翠,灿烂大备,宗室摩挲爱惜,较胜诸珍。宗室生子,长曰奕鼻,次曰奕烟,三曰奕壶,四曰奕盖,合之则鼻烟壶盖也。(24)
好烟成瘾的贵介公卿为后人留下了不少逸闻趣话,而清代烟迷最痴者莫过于韩菼(1637—1704)、陈元龙和纪昀(1724—1805),三位都官至礼部尚书。韩菼和陈元龙曾赋《咏烟草诗》各4首。韩氏4首,袁枚于《随园诗话》卷九曾提及,后似已失传;陈氏4首则收录于《莲坡诗话》卷下,都是倾心谀烟之辞。(25)
至于韩茭、纪昀的嗜烟趣话,以下清人笔记两则可作代表:
韩慕庐宗伯(菼)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与余同典顺天武闱,酒杯烟筒不离于手。余戏问曰:“二者乃公熊、鱼之嗜,则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庐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众为一笑。后余考姚旅《露书》“烟草产吕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庐,慕庐时掌翰林院事,教习庶吉士,乃命其门人辈赋《淡巴菰歌》。(26)
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值,正吸烟,忽闻召见,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又嘲之为“李铁拐”云。(27)
这两则轶事流传较广。韩慕庐的故事又见于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黄之隽《烟戒》、徐以升《淡巴菰歌》、全祖望《淡巴菰赋》、史梦兰《止园笔谈》卷三、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等,细节方面有所演绎,说韩氏所好有三:酒也,棋也,烟也,必去其一,则去棋;再去其一,则去酒。纪昀的故事,又见于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卷二十九、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清人轶事》、方溶师《蕉轩随录》卷六、徐珂《清稗类钞·诙谐类》、葛虚存《清代名人记》卷十二、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上、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五等等。
王士禛(1634—1711)所说韩菼命庶吉士赋淡巴菰一事,确实可信,但韩氏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方为翰林掌院学士(迄于1703年),距离王士禛所言戊午(1678)同典顺天武闱之事已近20年。查为仁《莲坡诗话》载:“韩慕庐宗伯掌翰林院事时,曾命门人赋淡巴菰。诗多不传,惟慈溪郑太守(梁)为庶常时所作,存《玉堂集》中。(28)”郑梁(1637—1713)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并选授庶吉士,此时韩菼从苏州回京未久,出任原职翰林院侍读学士。所以王、查所说命庶吉士赋淡巴菰一事,当在韩茭任侍读学士时所为(1678年和1688年,韩氏均任此衔),《玉堂集》及《玉堂后集》正是郑梁在翰林院期间所作。今查《四库存目丛书》据康熙间刻本影印的《寒村诗文选三十六卷》,其中《玉堂集》及《玉堂后集》均未收《淡巴菰赋》;倒是四、五十年之后进入翰林院的徐以升(1694年以前—1753年以后)和全祖望(1705—1755)先后闻风而起,所撰《淡巴菰歌》(1743年)与《淡巴菰赋》都流传至今,分别收录于朱铸禹汇校集注的《全祖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徐氏《南陔堂诗集十二卷》。(29)为《南陔堂诗集》作序的著名诗人沈德潜也有咏烟之作,即:“八闽滋种族,九宇遍氤氲。筒内通炎气,胸中吐白云。助姜均去秽,遇酒共添醺(注:名‘盖露’者可以醉客)。就火方知味,宁同象齿焚。”(30)末句所云“象齿”,指烟筒为象牙做成,是极名贵的一种,当然这也只有名公巨卿或豪富之人方可拥有了。
二、“淡巴菰”与江南文人群体
现存咏烟诗词,多出自江南文人。袁枚(1716—1798)(31)论浙西学人之诗,特别标举诸锦(1686—1769)、汪师韩和翟灏(?—1788):
学人之诗,吾乡除诸襄七、汪韩门二公而外,有翟进士讳灏、字晴江者,《咏烟草五十韵》警句云:“藉艾频敲石,围灰尚拨炉。乍疑伶秉箭,复效雁衔芦。墨饮三升尽,烟腾一缕孤。似矛惊焰发,如笔见花敷。苦口成忠介,焚心异郁纡。秽惊苓草乱,醉拟碧筒呼。吻燥宁嫌渴,唇津渐得腴。清禅参鼻观,沆瀣润咙胡。幻讶吞刀并,寒能举口驱。餐霞方孰秘,厌火国非诬。绕鬓雾徐结,荡胸云叠铺。含来思渺渺,策去步于于。”典雅出色,在韩慕庐先生《烟草》诗之上。(32)
诸、汪、翟三人均嗜烟,而且彼此互有往来。汪师韩除前揭《金丝录一卷》之外,另有《咏烟七律四首》(收入陈琮《烟草谱》卷六),第三首所云“词林名重淡巴菰”,可能是对乾隆年间江浙文人群起而和厉鹗《天香》词之事的描述(详下文)。翟灏有上述《咏烟草五十韵》(收入氏撰《无不宜斋稿》卷一)。诸锦则有《烟》诗:“我性不嗜烟,六十始爱烟。是名淡巴菰,见之姚旅编。方寸多魁磊,以烟全其天。一吸四体和,悠然见神全。摧刚化为柔,刷方以为圆。五味近乎辛,养恬兹取怜。高鸟聚密林,游鱼守潜渊。醉乡不到此,那识羲皇年!”(33)翟灏之诗模拟吸烟时诸种状貌情态极为细腻妥帖,故深得时人赏识,袁枚之外,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亦引录此诗,称其“组织工细,布置妥帖”。(34)此诗结尾所云“损益人凭说,辛芳尔不渝。诗肠感熏染(按:王端履引作‘诗肠缁恐涅’,反用孔子‘涅而不缁’之语,与原诗意蕴不合),吟谢淡巴菰”,(35)与诸锦“醉乡不到此,那识羲皇年”,同为期冀借烟草来超脱名利纠葛、俗务烦扰的表达。翟灏的友人万光泰(1712—1750)也赋有《烟》诗:“小草纷缠市,何年火利开。神农经不载,吕宋国移来。叶槁干时切,花红露下栽。曲生风味似,为尔减深杯。”(36)万光泰在音韵学、元史及上古算学等领域多有建树,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学者,(37)英年早逝之后,其《柘坡居士集十二卷》由同里好友汪孟绢(1721—1770)刊刻传世。万氏特别推服的全祖望为其撰写墓志,尤表彰其“《周髀》之学”,称“卓然独绝”。(38)汪孟鋗、汪仲鈖兄弟同于乾隆十五年(1750)中举,士林传为佳话,但汪仲纷三年后即辞世,他的儿子汪如洋(1755—1794)不但弥补了乃父未成进士的遗憾,而且一举在乾隆四十五年殿试拔得头筹,此人有咏烟词一阕《沁园春·咏淡巴菰》(《烟草谱》卷八著录)。
诸锦、翟灏、万光泰以及同样来自浙江的厉鹗(1692—1752)、杭世骏(1695—1773)、汪沆(1704—1784)、钱陈群(1686—1774)、吴廷华(1682—1755)、陈皋(字对鸥)、刘文煊(字紫仙),等等,都与水西庄查氏家族之查为仁、查礼(1716—1783)等往返密切。这些人大都嗜好吸烟,而且除万光泰之外,汪沆、厉鹗、刘文煊也有咏烟诗传世。乾隆二年,汪沆、刘文煊、万光泰与查礼撰有长诗《烟草联句》,收入查氏《铜鼓书堂遗稿》。(39)厉鹗的咏烟词曾遍传江南士林,题曰《天香·咏淡巴菰》,序云:
烟草,神农经不载。出于明季,自闽海外之吕宋国移种中土,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见姚旅《露书》。食之之法,细切如缕,灼以管而吸之,令人如醉,祛寒破寂,风味在麴生之外。今日伟男髫女,无人不嗜,而予好之尤至。恨题咏者少,令异卉之湮郁也。暇日斐然命笔,传诸好事。(40)
此作先后引来了众多的附和者,仅《烟草谱》所录之“天香”咏唱者便有:陆培(字恬浦)、陈章(字授衣)、郑廷旸(字隅谷)、朱方霭(1721—1786)、朱研(字子成)、吴烺(字荀叔)、王昶(1725—1806)、(41)王又曾(1706—1762)、徐宝善(号穆堂)、凌应曾(字祖锡)、吴泰来(1722—1788)、朱昂(字适庭)、赵文哲(1725—1773)、朱汉倬(字凌霄)、张熙纯(1725—1767)、吴元润(字泽均)、蒋业鼎(字荪湄)、吴锡麟(字圣征)、吴蔚光(字想甫)、许宗彦(1768—1818)。从厉鹗、杭世骏、钱大昕、王昶、曹仁虎等人现存诗文别集来看,除年资较晚的许宗彦之外,上述诸人之间往来相当密切,并且大都在当时便负有盛名。其中,王昶、吴泰来、赵文哲均属乾隆年间“吴中七子”。“吴中七子”之钱大昕(1728—1804)、曹仁虎(1621—1787)虽未和“天香”之词,却也有咏烟之诗。不过两人对于烟草之好恶恰恰相反:钱氏以为,烟草处处流行,伤人肺腑又碍事靡财,故于质问“滥觞起谁某”之余,期冀“安得拔其根,卮茜种千亩”!(42)曹仁虎自云“学得餐霞法,筠杆巧制宜。吹嘘长日便,冷暖一心知”,(43)为嗜烟的瘾君子无疑。
厉鹗、陈章、郑廷旸、朱研、朱方霭、朱汉倬、张熙纯、吴锡麟、许宗彦的上述“天香”词,均被王昶辑入《清词综》。该书还收录了《烟草谱》漏选的淡巴菰“天香”词两阕,分别由过春山(字葆中)和朱位恭(字叔曾)所撰。而上述和作“天香”词的文人当中,讽诵烟草诗词最多者正是王昶。其他人皆各和一阕,独王昶奉和两阕。此外,王昶还有《金缕曲·碧梦剧梅枝为饮烟筒嘱赋》、《采桑子·再赋梅筒》及《烟草花》诗一首,此三者不是“被动”应和之作,自然更有韵致。(44)明代遗民、著名文学家董说(1620—1686)入清后撰《石马烟谣》,自序虽说为“伤烟满江南”而作,但所咏当地风俗(作者为浙江吴兴人)却颇有情趣。(45)
自然,烟草虽号称“仁草”,却远非“仁者无敌”。在江南文人之烟草“歌德派”大行其道之时,非议者也屡有其人。如顺、康年间戏剧家徐沁(1626—1683)撰《香草吟》,剧中人物俱用药名,正派如桑寄生、红娘子、刘寄奴、蜜陀僧,反派如木贼、葳灵仙夫妇。桑寄生等欲清剿木贼等反叛军队,经蜜陀僧指点,取“淡把姑”(淡巴菰)以毒攻毒。蜜陀僧在介绍此物之“威力”时说:“乍吸头先晕,频吞体遍麻。略尝滋味浑难罢,半晌昏迷魂欲化。千番呜嘬唇还咂,口角流涎堪讶。似醉酒眼乜斜,如病疟脚波查”;至于其出处,则是“神农未尝,本草不载,佛说《楞严经》中列于五辛,名曰兴渠,比于腥血之秽。有误食者,须忏悔四十九日,方许礼佛。《法苑珠林》诠释甚详。……用火酒制造,内加砒霜,酷烈无比。人一尝之,刻不能少,以致焦灼肺腑,呜乎哀哉!”(46)乃人间剧毒之物。“淡把姑”在此剧中堪称关键“意象”,待到桑寄生、红娘子等得胜归来,剧本便以“淡把姑”作结,并借“丑角”与众人互动,反复致意于烟草之害。如“丑”言:“世间无不散的筵席,譬如演戏,终要收场。便与君等奉别,并无他语叮咛。只是扫除木贼的淡把姑,原系劫药。前者偶然撮弄,不期广播人间,流毒无穷,灼人肺肝,迷而不悟。自今以后,但愿宰官们各发婆心,转相劝诫,使众生一切人等,断除勿食,即此公德,不可思念。”(47)李渔(1611—1680)评点此剧时说徐氏曾“刻烟诫劝世,阐发曲尽”。(48)后来全祖望《淡巴菰赋》又云“琅琦督相,视为野葛;梁溪明府,指为旱魃;黄山征君,明火勿汗”,(49)是说宁波钱肃乐(1606—1648)、歙县宗谊(字正庵)等三人厌恶吸烟。“明火勿汗”,意为“别用烟草弄脏了炉火”,全氏《又拟薤露词九首》之《污吾火》即云此事。(50)再如王元启(1714—1786)云,刘汶恶烟草妨农,作《种烟行》以讥之,其卒章曰:“往者岁歉难举炊,谁家食烟能疗饥?”(51)总体而言,非议烟草最主要的理由便是钱大昕、查慎行所言的伤农、靡财以及害身。赵翼(1727—1814)《吃烟戏咏》(撰于1808年,诗人82岁)诗云:“淡芭味不入咸酸,偏惹相思欲断难(注:古诗‘相思若烟草’)。岂学仙能吸云雾?几令人变黑心肝!喷浮银管香驱秽,暖入丹田气辟寒。赢得先生夸老健,鼻尖出火骇旁观。”(52)据此可知,赵翼也嗜吸烟,但他又深知其害,爱恨交加、欲断偏难。知其害而形诸文字者,还有清初名诗人施闰章(1619—1683)的《矩斋杂记》,记“烟害”三事,兹引其中之二:
一友酷嗜烟,日凡百余吸,已得奇疾:头大如斗,牙龈溃脓升许,秽闻列屋,死而复甦。
南乡孟氏家蓄蜜。旁有种烟草者,蜜采其花,皆立死,蜜为之坏。以是知烟之为害,不可向迩。(53)
施氏并引养生家言附于后曰:“咽津得长生,故活字从千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为活,计可乎?”(出处同上)又,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撰《七招》赋,云古剌之丸、欧罗之表及吕宋烟草乃“好事所未见述,古者所不闻”。其言烟草云:“含茹则火入四肢,呼吸则烟腾百窍,蒸淫不歇,薰炙子鼻,五官拉杂,黑塞窍穴,珠胎既凌刳,玉孕复剖裂。”(54)施、洪二人言吸烟之害如斯其烈,想必均非嗜烟之徒。而乾隆时期的著名诗人黄之隽(1667—1748)正是深知其害,晚年才毅然戒烟。黄氏曾作《烟筒铭》曰:“此尝草、食火、飞灰之管,盘古以来见者罕,今世耽之逝不返。”(55)说“逝(誓)不返”,可见沉溺至深;晚年却鉴于“历验老寿无吃烟者”而作《戒烟》以“自戒”,所叙既爱又恨的心情颇为动人。《戒烟》诗云:“幼骇所见,折芦为筒,卷纸于首,纳烟于中。或就火吸,忽若中风,闭睫流涎,谓醉之功。久而流行,遍种斯草。晒叶剉丝,匪甘匪饱。铜竹镂工,荷囊制巧。缨弁横衔,脂鬟斜咬。吾独违众,誓不沾牙!嫉如治葛,屏若颠茄。有里前辈,向予褒嘉:不逐流俗,非君子耶!逮三十五,暨阳舟次。岁暮晓寒,拥衾不寐。卬友津津,曰媛且醉。遽丧其守,索而尝试。入唇三咽,启齿一呼。四肢软美,八脉敷舒。相遇恨晚,大智若愚。四十余载,晷刻必需。亦润文心,亦绵诗力。思之不置,弃之可惜。如惑狐媚,如蛊妖色。一朝觉寤,忍为残贼?昔韩尚书,嗜酒与烟,不得已去,二者何先?答曰去酒,佳话流传。囊余附和,今谓不然。咽喉寸肤,食草吞火。非兽非鬼,奚颐之朵?熏舌尚可,焚肠杀我!老耄作戒,铭诸座右。”(56)烟草之害,明清时期已广为人知,故历朝烟禁不绝,而戒烟者亦屡屡有之,可见人的意志力在诱惑面前并非全然无所作为。
三、“淡巴菰”与妇女之关系
烟草风行中土,至清中前期已如陆耀所言“士大夫无不嗜烟,乃至妇人孺子亦皆手执一管”。关于妇女吸烟的情形,清人时有记录。方文(1612—1669)于顺治五年(1648)在京师游览,撰《都下竹枝词二十首》,其中两首便是咏烟之作。一首咏士大夫吸烟风气称“金丝烟是草中妖,天下何人喙不焦!闻说内廷新有禁,微醺不敢厕宫僚”;另一首即咏妇女吸烟云:“侵晨旅舍降婵娟,便脱红裙上炕眠。傍晚起身才劝酒,一回小曲一筒烟。”(57)这种妇女,压酒劝客,昼伏夜兴,恐怕是旅舍招待女。康熙年间,山西介休梁锡珩(字楚白,号深山)撰有《偶咏美人吃烟》,诗曰:“前身合是步非烟,弄玉吹箫亦上天。红绽樱桃娇不语,玉钩帘外晚风前。”固该诗既以唐传奇《非烟传》之“红杏出墙”的女主角为况,所咏之“美人”应是青楼女子。此诗之妙,在于不直言“吃烟”,但以“步非烟”衬托“美人”于烟雾缭绕之中的轻盈风姿(按:唐传奇《非烟传》云,步非烟“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59)以此可想见此诗之“美人”的体态柔弱轻盈),可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久之后,著名诗人尤侗(1618—1704)也撰《董文友有美人吃烟诗,戏和六首,用烟字韵》,(60)亦用“步非烟”之典,故所咏者似同为青楼女性。诗人从其早晨起床梳妆开始,至夜晚挂帐燃篝重眠,始终都不离吸烟之“题”,所叙“侍儿吹火”、“玉唇含吐”、“低晕春山髻半偏”等情状,表明尤侗对这类女性之生活常态相当熟悉。
如果说上述三例所咏只是青楼女之嗜烟,那么乾隆时期杭州纪氏兄妹围绕烟草的彼此唱酬则纯属士绅大户的生活写照了。纪氏原籍安徽歙县,寓居杭州。《纪氏联句诗》之咏烟篇记录纪氏一家平素以吸烟为乐。《烟草谱》还收入纪兆芝(字仙岩,长兄)、纪兆蕙(字蓉圃,次兄)、纪兆莲(字吟房,长妹)咏烟诗各一首,均颇具姿致。(61)纪兆蕙还以其兄妹烟草诗求和于东南士林,海宁祝德麟(1742—1798)、无锡顾皋(1763—1832)之和作现存于世。
江之兰(字含征)撰《文房约》称,江南之宾朋宴会,无人不吸烟,“尤可骇异者,豪右之门,召集女客,不设簾箔,观剧飞觞,二八妖鬟,手擎烟具,先尝后进,一如姣童之奉其主。甚至含烟缓吐,视生旦之可意者而喷之,无所顾忌”。(62)金学诗(字韵言)《无所用心斋琐语》记苏州缙绅大户之女耽于安逸,往往日高而犹酣寝不起,妆毕第一件事便是“吸烟数筒”,以至向午时分方出闺房。(63)江之兰系清初名医,金学诗乃金士松(1730—1800)之弟,两人的记载可证清初直至乾、嘉之际士绅望族女性吸烟风气之盛。前揭“天香”诸词中,多篇牵涉深闺吸烟场景,亦可印证上述风气。
乾隆时期的常熟女诗人归懋仪(字佩珊,上海监生李学璜之妻,与母李一铭撰有诗歌合集《二余草》)有《烟草吟》,诗曰:“谁知渴饮饥餐外,小草呈奇妙味传。论古忽惊窗满雾,敲诗共讶口生莲。线香燃得看徐喷,荷柄装成试下咽。缕绕珠帘风引细,影分金鼎篆初圆。筒需斑竹工夸巧,制藉涂银饰逞妍。几席拈来常伴笔,登临携去亦随鞭。久将与化嘘还吸,味美于回往复还。欲数淡巴菰故实,玉堂文已著瑶篇。”(64)很显然,这位善于吟讽的大家闺秀(乃巡道归朝煦之女)也是瘾君子。
四、“淡巴菰”与笔记小说
烟草在清代中前期的广泛播传,增添了笔记和小说的表现内容。有关烟草之出处、种类、流布、性状、功能、做法、吃法以及烟筒、烟壶、鼻烟等各方面的内容均有记录。尤其是在功能方面,“歌德派”之谀词较盛,如陈琮引述宋代罗景纶言槟榔之功“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而盛称“烟草亦然”:“灼以管而吸之,食已,气令人醉,亦若饮酒然,盖醒能使之醉也。酒后食之,则宽气下痰,余酲顿解,盖醉能使之醒也。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盖饥能使之饱也。饭后食之,则饮食消化,不至停积,盖饱能使之饥也。”至于“其禀气辛辣而多芬,赋性疏通而不滞,又在槟榔之上”(《烟草谱》卷二)。陆耀总结出烟草之宜者“八事”、忌者“七事”、吃而宜节者“七事”以及“吃而可憎者五事”,饶有情趣,或有可供当今瘾君子参考者。(65)还有些记载,或别致、或风趣,为叙述增添了异样的情调与丰采。如《红楼梦》第52回叙宝玉给晴雯治病,便是让麝月取来一个金镶双金玻璃小扁盒儿,“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见怎么;便又多挑了些抽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脑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66)清人在使用鼻烟时,往往再加入一些别的东西,如兰花籽磨成的粉末或芥末,以增加芬香或提高通气的效果,所以贾宝玉可拿它来给晴雯治感冒。
再如李伯元所记晚清宝文靖(按:应为咸丰、同治、光绪间三朝大臣宝鋆)事亦颇精彩,其中玉烟壶为叙述转捩之一关键。(67)纪昀虽酷嗜吸烟,却很少刻意为烟草歌功,其《阅微草堂笔记》三处与吸烟相关的记载都是间接描述,均事关“烟筒”。其中,两处皆出自《如是我闻》:一说医者胡宫山,年八十余,轻捷如猿猱,技击绝伦,“尝夜遇盗,手无寸刃,惟倒持一烟筒,挥霍如风,七八人并刺中鼻孔仆”;另一说“宛平何华峰,官宝庆同知,时山行疲困,望水际一草庵,投之暂憩。榜曰‘孤松’,庵门联云‘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有老僧应门延入,具茗茶颇香洁,而落落无宾主意。室三楹亦甚朴雅,中悬画佛一轴,有八分书,题曰:‘半夜钟磐寂,满庭风霜清。琉璃青黯黯,静对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联曰:‘花幽防引蝶,云懒怯随风。’亦不题款。指问:‘此师自题耶?’漠然不应,以手指耳而已。归途再过其地,则波光岚影,四顾萧然,不见向庵所在。从人记遗烟筒一枝,寻之尚在老柏下。竟不知是佛祖,还是鬼魅也”。(68)文中所述之世外高人(老僧)似亦一嗜烟之人。第三处是《槐西杂志》所记甘肃李参将,精于占事,曾以烟筒占人:
(李)至京师时,一翰林拈烟筒。曰:“贮火而其烟呼吸通于内,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显,尚待人吹嘘故也。”问:“历官当几年?”曰:“公勿怪直言。火本无多,一熄则为灰烬,热不久也。”问:“寿几何?”摇首曰:“铜器原可经久,然未见百年烟筒也。”其人愠去。后岁余,竟如所言。
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观其复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于床,是曾经停顿也;然再拈于手,是又遇提携复起矣。将来尚有热时,但热又占与前同耳。”后亦如所言。(69)
上述例子说明烟草也是一般士大夫的生活需要,故鼻烟与烟筒被顺手拈来,成为叙事的材料。
有的小说,甚至让吸烟不限于作为叙述的材料,而直接使之成为叙述的目的。如张潮(1650—?)《虞初新志》和浙江海盐董潮(1729—1764)《东皋杂钞》所记吸烟的故事纯然以吸烟本身为目标。限于篇幅,此处仅录张潮所述如下:
皖城石天外曾为余言:有某大僚荐一人于某司,数日未献一技。忽一日辞去,主人饯之。此人曰:“某有薄技,愿献于公。悉召幕中客共观之可乎?”主人始惊愕,随邀众宾客至,询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烟。”众大笑,因询能吃几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砌,客吸之尽,初无所吐。众已奇之矣,又问:“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之以烟若干,客又吸之尽:“请众客观吾技。”徐徐自口中喷前所吸烟:或为山水楼阁,或为人物,或为花木禽兽,如蜃楼海市,莫可名状。众客咸以为得未曾有,劝主人厚赠之。(70)
上述故事里,吸烟便不复某一单纯的生理需要,而是颇具观赏价值的“游戏”,吸烟因之成为一种技艺,故表演之人可自视一“技”在身,并凭此回报蓄养之“恩”而无愧色。
倘若没有烟草,这样精彩的文字自然也不会存在了。
五、结语
明末清初以海洋探险为契机所展现的中西文化大碰撞,持续了200余年的时间,对中西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典籍所蕴含的自律性文化品格给西方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力,而瓷器、茶叶、香料等物产的大量西传让产自南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天主教东传虽然成效有限,但伴随天主教而来的“副产品”却宏图大展:西洋大炮加剧了明清国运鼎革;传教士主修之崇祯历书成为国人生息行藏的“正朔”凭依;其他如历算、水利、机械、逻辑、宗教、美术、语言等领域对我国学术之影响,时贤论之甚详,不必赘叙。不过,就时间的持久性、空间的广阔性以及感受的切身性而言,烟草造成的影响,他者实罕有其匹。
借助上述文献之钩沉抉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清代的文人知烟草为“淡巴菰”而酷嗜如命者莫可名数,却鲜有因其为异域之物而予以排抵拒斥的(禁止的理由主要是伤农、靡财以及害身)。而同为远西舶来之物,上自天主教,下迄可以利用厚生的象数之学,如火炮、历算、水利、机械等,都曾遭遇到本土的激烈反对和排斥。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士人尚不知“淡巴菰”来自远西之美洲、欧洲,而以为乃吕宋所产,故“淡巴菰”在整个清代均未曾激起因其为远西之物而有意排斥、厌恶的反应。
其二,“淡巴菰”传入中土不久,国人对其利弊两端便有清楚认知,禁烟之举,历朝皆有;恶烟之人,屡见不鲜。何以屡禁屡恶而难绝呢?全祖望《淡巴菰赋》所作之答案,其思考允称完备:“岂知金丝之薰,足供清欢;神效所在,莫如辟寒。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槟榔消瘴,橄榄祛毒,其用之广,较菰不足。而且达人畸士,以写情愫;翰林墨卿,以资冥功。于是或采湘君之竹,或资贝子之铜,各制器而尚象,且尽态以极工。时则吐云如龙,吐雾如豹,呼吸之间,清空杳秒;更有出别裁于旧制,构巧思以独宣,诋火功为下策,夸鲸吸于共川,厥壶以玉,厥匙以金,比之佩镌,足慰我心。……或者惧其竭地力,耗土膏,欲长加夫屏绝,遂投畀于不毛。斯非不为三农之长虑,而无如众好之难回。观于‘仁草’之称,而知其行世之未衰也。”(71)时至今日,烟草之害举世皆知,然全氏“仁草”之辩似仍有其合理性。烟草行世之将盛耶?将衰耶?至少现在仍然难以料定。其故何在?似可成为另一研究课题。
其三,烟草至清代前中期,举国嗜之若狂,殆无疑义。刘廷玑言清初之“黄童白叟,闺帷妇女,无不吸之”,而且“时刻不能离”者“十居其八”(《在园杂志》卷三“烟草”),有人甚至说:“士不吸烟、不饮酒者,必无风味。”(蔡家琬《烟谱》)对文人骚客而言,烟草又有催发灵感、润绵诗文之力,故嗜之者尤甚。但总体而言,付诸歌咏者不多,故陈琮集20余年之力,饾钉必录,所汇辑者亦不过区区230余篇/首,其中,40多首还是因陈琮之邀约而作(多为吴中当地士人)。笔者于此之外又搜抉到40余篇/首,不乏才力雄健之作,但相比于咏唱酒茶之浩瀚篇章,仍显数量匮乏。笔记、小说、戏曲等其他文类之烟草描述,多是偶然提及,鲜见其为叙述之关键者。看来,烟草之于清代文学,其催发灵感、滋育巧思的间接“贡献”,远大于对吸烟及烟草的直接描述。反过来说,这也许还是明清文人吟咏不足而今人钻研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注释:
①“盖露”指烟草顶上的三片叶子,由之而成的烟丝最为名贵,故又有“醉仙桃”、“赛龙涎”、“胡椒紫”、“辣麝”、“黑於菟”等别名。
②《在园杂志》作“佘塘”,认为它与“石马”、“浦城”、“济宁”一样,是“因地得名”。详见刘廷玑撰《在园杂志》卷三“烟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7页。
③晚清张煜南(1861—1911)云,肉字当是白字之误,“淡白果”即“淡巴菰”之转音也。见氏撰《海国公余杂著》卷一。
④《渌水杂识》卷二云:“今所啖之烟草,孙光宪已言之,载于《太平广记》: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按:同‘燃’)烟,啖之可以解倦。则西域之啖烟三千余载矣。”(见于纳兰性德撰《通志堂集十八卷》之卷十六,《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47册,影印清康熙三十年徐乾学刻本,第378页)按:这一推断把烟草一直追溯至佛祖释迦牟尼时代,故称“三千余载”。
⑤方氏诗《吃烟》自序引僧人言:佛藏之南藏“以”字函、北藏“下”字函“根本一切昆尼杂事部”记录具寿比丘病,服烟药而愈。请于世尊,世尊许之,始以碗合而吸,后改为木筒,又改为铁筒,即今之制。详见方孝标撰《钝斋诗选》卷一六,见于《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5册,影印清抄本,第442页。按:这里也把吸烟与佛祖相联系。
⑥博通如全祖望(见氏撰《淡巴菰赋》)、俞正燮(见氏撰《癸巳存稿》卷十一)皆以地望释之。清代嘉庆、道光间松江青浦人陈琮所撰《烟草谱八卷》博采群书,最称专门,其释“淡巴菰”亦云:“淡巴,国名菰菜类也,盖淡巴国所生之菰耳。”详见氏撰《烟草谱》卷一“淡巴菰”,清嘉庆间刻本。按:“淡巴”国名见于王圻《三才图会·地理卷十三》、清初陆次云《八舷译史》(卷二)以及《明史·列传·外国六》(《明史》卷三百二十五),这是全、俞、陆诸人以地望误释“淡巴菰”的重要依据。
⑦明张介宾撰《景岳全书》卷四十八,见于《四库全书》第778册。
⑧清方孝标撰《钝斋诗选》卷一六,见于《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5册,第441—442页。全诗云:“塞俗如同麻麦收,翠茎红蕊种三秋。沙畦摘焙传方法,土坑宾朋当款留。金碗吸如鸿渐品,玉山颓似杜康谋。革囊铜管偕刀琏,已见吹嘘遍九州。”
⑨清陆耀撰《烟谱一卷》之“好尚”,《昭代丛书》世楷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17册,第484页。
⑩据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载,崇祯帝之谕禁烟,相传是因其“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详见《玉堂荟记》卷四,民国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顾湘舟藏本,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211页。按:这一揣测很合乎崇祯帝善于猜疑之性格,故可聊备一说。
(11)杨士聪撰《玉堂荟记》卷四,民国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顾湘舟藏本,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211页。谈迁撰《枣林杂俎中集·荣植·金丝烟》(中华书局,罗仲辉、胡明校点校,2006年版,第478页)认为勒禁之年在崇祯十六年,不如杨说可信,因为杨氏亲身经历此事。
(12)李调元《淡墨录》卷六“不吃烟应制诗”,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13)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圣祖不喜吸烟”,详见中华书局杨璐点校本1989年版,第72页-73页。
(14)《熙朝定案》乃晚明即开始编纂的天主教史文献,版本甚多,此据韩琦、吴昊校注之版本,即《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5页;赵之谦撰《勇庐间诘一卷》,《丛书集成新编》第47册,第763页;张义澍认为,“西蜡”乃“士那(按:鼻烟之译名)之音转”。详见氏撰《士那补释·序》,《士那补释》,第1页,见于刘声木辑《鼻烟丛刻》,清光绪间直介堂丛刻本。
(15)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16)李伯元撰《南亭笔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大东书局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3年版,第5页。
(17)李伯元撰《南亭四话》卷一,上海书店据大东书局1925年版复印,1985年,第46页。
(18)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以及赵之谦《勇庐闲诘》、张义澍《士那补释》等著述。不过,中国文献有关鼻烟的最早记载似迟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方见于王士禛《香祖笔记》。详见《香祖笔记》卷七,收入《四库全书》子部第870册,第469页。按:《香祖笔记》皆康熙癸未、甲申(1703—1704)间所记,王氏称其所见各式贮烟之玻璃瓶乃内府制造,故可知其流行时间应早于康熙癸未、甲申间。
(19)徐珂撰《清稗类钞·饮食类》。
(20)全诗见于金武祥撰《勇庐闲诘评语·序》,周继煦《勇庐闲诘评语》,第1页。收入刘声木辑《鼻烟丛刻》,清光绪间直介堂丛刻本。
(21)引自方濬师撰《蕉轩随录》卷六,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41册,第387页。
(22)吴省钦撰《小极试鼻烟戏作》,见于氏撰《白华后稿四十卷》卷三十六,清嘉庆十五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48册,第693页。按:吴省钦对于烟草流行,以致“满座围高朋,十可醉八九”不予认可。即使鼻烟,他以为也是“小利害差大”,对众人嗜烟而毁茶废饮颇为不满,故吟诗而予以“弹纠”。详见上揭长诗《小极试鼻烟戏作》。
(23)详见薛福成撰《庸庵笔记》卷三,清光绪丁酉(1897)刻本,《四库存目丛书》第1182册,第652页。按:周寿昌(1814—1884)撰《思益堂日札》亦录有查抄和珅府的“籍没单”一份,其中玉鼻烟壶只有24对。见《思益堂日札》卷四,清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1册,第403页。
(24)李伯元撰《南亭笔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大东书局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3年版,第9页。
(25)查为仁《莲坡诗话三卷》卷下,清乾隆刻蔗塘外集本,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第145页。
(26)王士禛撰《分甘余话》卷二“韩慕庐嗜烟”,《四库全书》子部第870册,第558页。
(27)陈其元撰《庸闲斋笔记》卷五,中华书局杨璐点校本,1989年版,第112页-113页。
(28)查为仁《莲坡诗话三卷》卷下,清乾隆刻蔗塘外集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第145页。
(29)徐以升撰《南陔堂诗集》卷六,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30)沈德潜撰《咏烟草》,见于氏撰《归愚诗钞余集》卷十,清乾隆刻本,辑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24册,第528页。
(31)袁枚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历为1798年1月3日。详见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4页。
(32)袁枚撰《随园诗话》卷九,清乾隆十四年刻本。按:袁氏本人似乎并不吸烟,亦无咏烟之涛。他在《犊外余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习俗移人,始于薰染,久之遂根于天性,甚至饮食男女,亦雷同附和,而胸无独得之见,深可怪也!烟草的是何味?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也。悲夫!”(详见《随园全集》第4册,东方文学出版1936年版,第6页)从指摘严厉的语气可以推知上述结论。
(33)诸锦撰《绛跗阁诗稿十一卷》卷十一,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按:此诗辑入陈琮《烟草谱》卷五,所引“高鸟聚密林,游鱼守潜渊”一句,《烟草谱》作“餐霞自有客,吐火宁无仙?”
(34)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十二卷》卷一,清道光丙午年(1846)刻本。
(35)翟灏撰《无不宜斋未定稿四卷》卷一,清乾隆刻本。
(36)万光泰撰《柘坡居士集十二卷》卷八,清乾隆二十一年汪孟绢刻本。
(37)袁枚曾记程晋芳(1718—1784)读万光泰五七言古体诗而拜服之事。详见袁枚撰《随园诗话》卷一,乾隆十四年刻本。按:程晋芳亦有咏烟诗:“渔洋才调接元虞,迟日闲寻主客图。沈叹宗风太牢落,凉花开遍淡巴姑。”收入氏撰《勉行堂诗集》卷七,清嘉庆二十三年邓廷桢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3册,第150页。
(38)全祖望撰《万循初墓志铭》,收入氏撰《全祖望集》,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
(39)查礼撰《铜鼓书堂遗稿》卷二,清乾隆查淳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1册,第15页。
(40)见厉鹗撰《樊谢山房集》卷九,《四库全书》集部第1328册,第140页。
(41)王昶生于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历为1725年1月6日。详见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42)钱大昕撰《咏道中所见草木》第八首,见于氏撰《潜研堂诗集十卷》卷六,清嘉庆十一年刻本。按:著名诗人查慎行对于农村弃本业(农业)而逐贸易之现象也深表忧虑,曾赋诗《自汶上至济宁田间多种蓝及烟草》,诗曰:“本业抛农务,群情逐贸迁。刈蓝初用染,屑草半为烟。树艺非嘉种,膏腴等废田。家家坐艰食,那得屡丰年。”见于氏撰《敬业堂集》卷四十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83册,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本。
(43)详见陈琮《烟草谱》卷七,清嘉庆间刻本。
(44)王昶撰《春融堂集》卷二十七,清嘉庆丁卯(1807)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第544、640页。
(45)董说撰《石马烟谣》,见于氏撰《丰草庵涛集十一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3册,英印民国吴兴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第47页。
(46)徐沁撰《香草吟传奇二卷·第二十四出“烟诫”》,辑入李渔撰《李渔全集》第18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47)徐沁撰《香草吟传奇二卷·第三十二出“丸散”》,辑入李渔撰《李渔全集》第18卷,第202页。按:李渔认为,此剧以“淡把姑”作结,堪称“妙不可言”。因为,烟草之迷诱众人,“有如夫 妇两同床,胶还着漆,蜜里加糖。比名利一般,待开交依然欣往”(《香草吟传奇二卷·第三十二出“丸散”》)。点出追名逐利才是众人之贪嗔相,其害更有甚于烟草。
(48)徐沁撰《香草吟传奇二卷·第二十四出“烟诫”》之李渔评点,辑入李渔撰《李渔全集》卷十八,第181页。
(49)全祖望撰《淡巴菰赋》,见于《全祖望集》,朱铸禹汇校集注,第79页。
(50)见于《全祖望集》,朱铸禹汇校集注,第2449页。
(51)王元启撰《烟草小论》,见于氏撰《祗平居士集》卷一,清嘉庆十七年王尚绳恭寿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0册,第487页。
(52)赵翼撰《吃烟戏咏》,见于氏撰《瓯北集》卷五十,清嘉庆壬申(1812)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179页。
(53)施闰章撰《矩斋杂记二卷》卷上,清康熙乾隆间刻《施愚山全集》本,见于《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49页,第591页。
(54)洪亮吉撰《七招》,见于氏撰《卷施阁集·文乙集卷二》,清光绪三年《洪北江全集》增修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67册,第372页。
(55)黄之隽撰《堂集》卷二十四,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见于《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71册,第463页。
(56)黄之隽撰《堂集续集》卷四,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见于《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71册,第777页。
(57)方文撰《北游草》,辑入氏撰《涂山集》,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00册,第156页。
(58)此诗辑入邓之诚撰《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39页。
(59)详见皇甫枚撰《非烟传》,周广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唐代笔记小说》第二册,影印《说郛》清刻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60)尤侗撰《西堂小草》,辑入氏撰《尤太史西堂全集三种六十一卷附湘中草六卷》,清康熙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9册,第435页。
(61)可参看尤侗撰《西堂小草》。
(62)江之兰撰《文房约一卷》,辑入《丛书集成新编》第6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第547页。
(63)见于陈琮撰《烟草谱》卷三,清嘉庆间刻本。
(64)见于陈琮撰《烟草谱》卷六,清嘉庆间刻本。
(65)清陆耀撰《烟谱一卷》之“好尚”,《昭代丛书》世楷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17册,第484页。
(66)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三家评本排印1988年版,第837页-838页。
(67)李伯元撰《南亭笔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大东书局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3年版,第1页。
(68)见纪昀撰《纪晓岚文集》,第2册,孙致中等校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第162页。
(69)同上,第371页。
(70)张潮辑《虞初新志》卷十六,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按:此为张潮自述之故事,系于周亮工撰《因树屋书影》之后。
(71)全祖望撰《淡巴菰赋》,见于《全祖望集》,朱铸禹汇校集注,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