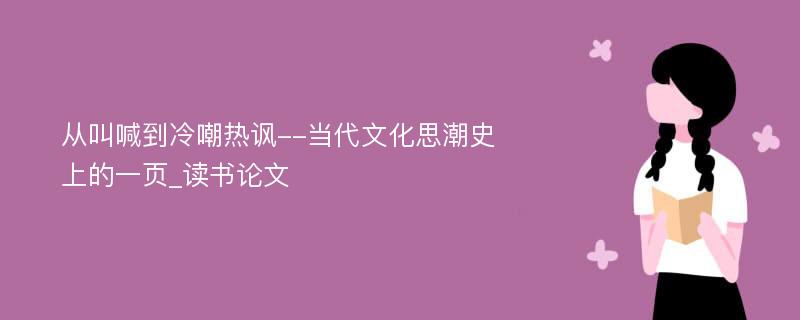
从呐喊到冷嘲——当代文化思潮史一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冷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史上一个基本问题。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开创新文化运动史到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分化、大改组再到运动年代(1957~1976)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苦难历程直至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讨论——一切都令人百感交集,如果说,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那末,知识分子问题就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现代化的前景。
现在,让我们看看:当代文化人在探索知识分子出路、思考知识分子命运方面走过的奇特旅程吧。
70年代末~80年代初:含泪的颂歌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再次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历程后,再次扬眉吐气。一批歌颂知识分子的作品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断产生轰动效应,最早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接着是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小说《公开的情书》重见天日,此后,话剧《丹心谱》、小说《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报告文学《大雁情》、《小木屋》、《祖国高于一切》……这些作品既是对知识分子的歌颂,又是对知识分子苦难悲剧的控诉。今天回过头再去重读那些作品,我注意到:除去《地质之光》、《公开的情书》,其余大部分作品都浸透了冤屈的血泪。这种“含泪的颂歌”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绝非偶然,它记录了知识分子的屈辱历程——与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浪漫旅程相比,这一代知识分子活得多么窝囊。不要说鲁迅式的呐喊、郭沫若式的热狂、林语堂式的闲适已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中,就连郁达夫式的浪漫、周作人式的叹思也没有,有的只是逆来顺受——但在那政治高压的时代,不逆来顺受又如何?多少人甚至逆来顺受也没换来那份可怜的安宁!
作家们的出发点也许只是“为知识分子请命”,但“含泪的颂歌”已在冥冥中导向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审判”。
1980:张贤亮打开“潘多拉之匣”
1980年,张贤亮发表《土牢情话》,小说还原了知识分子在高压下沦为“苟活者”的生存本相。石在的卑怯、懦弱直接导致了乔安萍的毁灭,也使自己的灵魂注定了不得安宁。由此产生了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忏悔”主题。当时的张贤亮对此未必有着充分的自觉(否则,他就不会在稍后的《绿化树》中流露出应该在血水中浴三遭的病态心理)。令人欣慰的是,即使没有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忏悔”的主题也必将敲响知识分子危机意识的警钟。证据是:青年批评家们的犀利文论——我一直以为:那些富于思想锋芒的文论对于当代思想史,具有十分可贵的思想史资料的意义。显然,从“文革”中跋涉出来的青年学者不可能对知识分子的悲剧历程视而不见。对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与沉思不仅是反思历史的必要,也直接关系到后来人的前途。因此,当张贤亮的名作《绿化树》作为优秀的心理分析小说、人民的颂歌而洛阳纸贵时,青年批评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小说的主题毛病上大作文章。在1984~1986年间,黄子平、季红真、许子东、王晓明都著文批评了《绿化树》的病态主题。黄子平批评:“对苦难的‘神圣化’和对农民的‘神圣化’”是值得怀疑的,是误把“目的论的东西引入历史哲学”。①季红真则进而分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构成: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影响和中国当代文化教育“形成了他们精神的内在矛盾。前者使他们在严酷的时代活动中软弱无力,后者则使他们习惯于自我否定。”②许子东在深入探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忏悔”主题后指出:“这种根植于启蒙意识的惭愧变成尊敬变成崇拜甚至再变成某种‘恐惧’,‘忏悔’也就由内心观照上升为反省上升为自我批判再上升为精神自杀”。③王晓明也指出:深入的“自剖”必须要在先清除了自身从地狱带来的“鬼气”才能实现。④——这样的批评对张贤亮具有重要的意义。1985年发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后,他走出了“讴歌苦难”的误区,而成为深入解剖知识分子病态心理和苦难根源的圣手,《习惯死亡》、《烦恼就是智慧》都是震撼人心的记录。
这一切发生在1984~1986年之间,仅仅是因为《绿化树》的缘故吗?不完全是。
请看赵园的专著《艰难的选择》。这部书完成于1985年。这是一部通过分析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与形象创造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思考知识分子命运的力作。书中闪烁着批判与反思的光芒。余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随想》更是一篇宝贵的思想史资料,其中激荡着这样的哲思:“该按照何种‘模子’来改造一下中国人,使我们自身,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性格更臻完善呢?”⑤“改造国民性”的世纪文化主题至此进一步具体落实为“改造知识分子性格”的话题。但这已是完全不同于“改造世界观”的文化命题了。
正是在1986年,《中国青年报》发起组织了《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的讨论,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向被扭曲了的知识分子人格模式发起了冲击,青年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坦荡、潇洒、不再委琐、不再懦弱、不再逆来顺受的新风貌;也正是在1985年左右,老作家巴金发出的泣血之声——“我忏悔!”——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空前的反响,这是良知的呼声,是甩掉历史重负的呐喊,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决不象懦夫那样自欺欺人的心声;正是在1985年左右,青年作家赵玄在长篇小说《红月亮》中深刻反思了“文革”的悲剧:“全体中国人——每个人都是这场悲剧中的角色,也都是导演。我们自己捉弄自己,自己毁灭自己……要责怪,只能怪自己,因为,首先,我们自己没有当好自己的领袖。”⑥也正是在1985年左右,一贯温柔敦厚的王蒙发表了寒气逼人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刘心武称之为“审父”之作:这一代人敢于对父辈呐喊——“父辈啊!你们走过怎样的路,你们的心灵不管怎样挣扎也毕竟不能清白,你们有那么多不好意思说出来不好意思承认的隐秘的卑微、卑鄙、卑琐,你们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多么不幸!”⑦尽管在倪吾诚的时代与石在的时代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尽管《活动变人形》与《土牢情话》的艺术风格、文学观念大不一样,但倪吾诚与石在却有着令人震惊的相似——都委琐、都可怜、也都卑鄙!
也还是在1985年左右,一批青年学者推出了影响极大的《走向未来》丛书。在这套旨在介绍当代最新成就的综合性丛书中,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占了不小的比重——《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摇篮与墓地》、《儒家文化的困境》、《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等等。1986年以后,《读书》杂志以醒目位置相继推出青年学者许纪霖、黄克剑、黄子平、刘小枫、吴方、汪晖、钱理群、赵一凡等人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中沉思知识分子命运、研究知识分子心态、展望知识分子前途的书评,这些书评也以深沉的情感、睿智的哲思而具有思想史资料的意义:它们不仅是这一代学人总结历史的心得记录,也体现了这一代学人达到的历史高度——在世纪末的低谷,回首几代人的坎坷历程,提出一系列古老而常新的思想命题:从中国士大夫的矛盾心态到近世知识分子的宝贵探索;从知识分子的困惑分析到“现代化与终极关怀”的沉思;从审视前辈的人生缺憾到展示当代学子的远大抱负……相对于创作中“含泪的颂歌”,这些思想评论更富于“理想的激清”。“含泪的颂歌”令人叹息,“理想的激情”则催人奋起。
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讨论,就这样在80年代中期风云际会,与同时期关于现代化建设、关于“球籍”与“危机感”的议论、关于文化转型与“世纪末回眸”的放言的一系列讨论一起,构成了当代思想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从控诉到自首、从“含泪的颂歌”到“审父意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再次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自我否定”,也是一次伟大的“自我重新设计”。
一切似乎正在巨变,天翻地覆慨而慷……
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入文化低谷、走向自嘲
就在知识分子在历史舞台上摆出了雄壮的阵势、打起向现代化进军的先锋旗帜,“文化低谷”却猝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喧哗音犹在耳,却何曾想个体户、“大腕”转眼间以“经商热”吸引住了全社会的目光!
《读书》杂志在1988年第9、11、12三期均以头条位置分别推出三篇长论:许纪霖的《商品经济和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卢中原的《迎接中国的“企业家时代”》、周彦的《我们能走出“文化低谷”吗?》——这一切似乎纯系偶然,但也于冥冥中昭示了时代精神的变迁:文化精英走入了“文化低谷”。这是当代中国特有的奇怪现象。如果说1985年以后“文坛失去轰动效应”也可以解释为文学发展与文化的必然,那么,“教育危机”则使人仰天长啸,欲哭无泪。
尽管1986年还产生了陈祖芬的《理论狂人》那样的“含泪的颂歌”,但1988年以后,连这样的颂歌也越来越少了,创作界中似乎除了张承志的《金牧场》中那个独往独来的青年学者还使人感受到一些理想主义的阳刚正气以外,已没有了“含泪的颂歌”,甚至连“忏悔”的呐喊也再也激不起回声了,于是,“冷嘲”的主题登场,并很快风靡文坛。
事实上,早在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已以黑色幽默的笔法嘲弄了僵化的贾教授,但那还只是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到了1987年,陈世旭发表《校长、教授、助教和红房子》,已从生存困境的层面嘲弄了校长的无能,教授的懦弱、助教的窝囊(为了分房先是溜须拍马,后是老拳相向);1988年,刘恒发表《白涡》,1989年,陈村发表《张副教授》,立意都在鞭挞、嘲讽知识分子的虚伪、猥琐。而教授出身的汤吉夫在80年代初曾写出过那么多“含泪的颂歌”(例如《心》、《归》、《同志》等),可到了1984年,他的《朋友》已转为冷嘲,章学纯的刁钻、刻薄、虚伪令人感慨。如果说,石在的懦弱还可以令人同情,那末章学纯的卑劣则只能使人鄙弃。1987年以后,汤吉夫以《小城旧梦》、《苏联鳕鱼》、《本系无牢骚》、《新闻年年有》、《上海阿江》……等一批小说不断刻画知识分子一穷二酸的众生相,那夸张的漫画笔法尽情嘲弄了知识分子的尴尬生存状态。90年代以后,刘心武的《风过耳》、方方的《行云流水》、《无处遁逃》、《祖父在父亲心中》也与汤吉夫一样,致力于揭示知识分子的卑污灵魂或者生存困境。他们的作品使人不禁联想到《儒林外史》……
就这样,罩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精英”光环被作家们无情地消解了。在中国文化日益走向世俗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与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同步)中,知识分子的“自审”与“自嘲”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一方面打破了“精英”的神话,另一方面也昭示了这样的事实,在政治的高压已被驱散的新时期,经济的困境逼使知识分子继续在堕落、沉沦的下坡路上急速滑行……“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穷得象教授傻得象博士”、“硕士生不如狗,博士生满地走”这样一些新的俗语和“孔雀东南飞”、“新‘读书无用论’流行”之类热门话题,都表明: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仍未有穷期。
叹息归叹息,自嘲归自嘲。更不可思议的是“如今竟轮到王朔那样的“痞子”出来嘲弄知识分子了。王朔在80年代末的独领风骚、轰动文坛,具有很复杂的社会原因。而“王朔热”风靡不衰这一现象本身也足以耐人寻味的了:玩世不恭、放浪不羁。“过把瘾就死”已成为新的时代时尚。王朔有他的“历史哲学”——“痞子创造历史”(“改革开放的所有动力,来自痞子。是痞子作生意、经商、办工厂、开商店,是他们的疯狂推动社会运转”。⑧;他更以一个成功者的口吻大谈:“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他们已经习惯于受到尊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体面的生活一旦丧失,人也就跟着猥琐。”至此,他陈述的是一种可悲的事实。但接下去,他又说:“象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⑨这才是王朔的真心:嘲弄知识分子,为的是出一口恶气。
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叹息、自嘲与来自王朔式“痞子”的兴灾乐祸,足以彼此印证: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远未终结。
既然知识分子如此窝囊,那末,谁来充当现代化的先锋?王朔的回答是:痞子。然而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历程却证明: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才是现代化的旗手、“上帝的选民”。“痞子”创造历史?不错。但恐怕只是在一个“初级阶段”的国度、一个处于失序状态的“过渡时期”。未来的风流人物,必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精英。
不信,咱们走着瞧。
知识分子中的民粹主义情绪面面观
如果说,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叹息、“自审”与冷嘲还有“哀其不幸”的意味,那末,当作家中有人从冷嘲也走向了王朔式的鄙夷而毫无怜悯之心时,那就更令人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承志。
张承志与王朔,代表了当代文化思潮的两极:张承志是九死不悔的理想主义者,是历史学家,知识精英;王朔则是“一点正经没有”的世俗主义者,是“顽主”、“痞子”。“要末张承志,要末王朔”——一位评论家将这种两极的抉择摆在了时人的面前。张承志与王朔,不可同日而语。我历来喜欢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及其充溢着阳刚正气的作品,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评论。
但我终于发现:至少在两点上,张承志与王朔殊途同归——
第一,在《金牧场》这部小说中,张承志记下了他的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思考:是那些“胡同串子”烧汽车的行动“粗野地撕下了历史的旧一页。……他觉得他从此和北京痞子之间建立了不能割断的情谊。那一页又霉又烂,可是从来没有人敢掀,更不用说撕了它。……你只敢用小里小气的伤感来发泄。……然而痞子们是伟大的……”瞧,这不是“痞子创造历史论”么?而且,比王朔的哲学提出得更早,不过当时(1987年)没人注意罢了。但张承志的思考却立足于这样的基点:“革命运动是什么?人民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四五运动”的答案与教科书上的介绍相去甚远。张承志由“胡同串子”烧汽车顿悟了革命的复杂内涵、人民的复杂成份、历史的复杂意义。联系到张承志的粗犷个性、生命激情、革命理想,我们不难发现他在“痞子创造历史”这一点上与王朔的同中之异。
第二,张承志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金牧场》中,就记载了历尽苦难的大学教授周先生在日本人面前哭诉苦难的卑琐,尽管周先生等人德高望重、思想自由,但却没有一根“自由的骨头”!因此,他不愿意成为周先生那号学者,他甚至说:“再见吧学者。”他因此真的就离开了学者的队伍,成为一个自由作家,去西海固那片贫瘠而神圣的土地上去寻找精神的家园了。此后,他不断地嘲弄、指责、批判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中国文艺痞子们不会懂,为什么‘爱’首先是一个宗教概念。”“‘家’意识……知识分子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那么蠢笨和迟钝。”⑩十九世纪知性的象征——实证主义,与二十世纪末迷茫混乱的现代思潮,都无法拯救这些惶惶无路的智识者”。(11)“在中国穆斯林中间,特别是在他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常有一种现象,那就是信仰肤浅、责任感缺乏,往往乐观而且言过其实。”(12)——这些偏激的言辞击中了知识分子的要害:缺乏阳刚正气,被世纪末情绪所裹挟,迷惘、猥琐。与王朔不同的是:张承志的出发点不是“暴发户”的出恶气,而是为这个时代缺少“圣性”而不满、愤激。当整个时代都朝着世俗化的方向狂奔时,张承志却狂热地走向了神圣的理想国——哲合忍耶。
张承志一直恪守着“为人民”的宗旨。对于世俗的人们,“为人民”早已是一个过时的口号。在竞争的时代,个性、个人主义势必风行。但张承志凛然不屈,他因此而成为当代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
“为人民”,是一个内涵极其复杂的口号。它曾经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也曾异化为骗子们欺世盗名的工具。而对于张承志,它意味着一种信念,一种民族自尊心,一种决不媚俗的使命感。张承志之所以能在世纪末的世俗化大潮的冲击下岿然不动,高举着理想之旗,与此有很大关系。
民粹主义在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几十年的跨度中,曾是许多热血青年的精神支柱。在战争年代,他们象他们的俄国先驱一样,走向民间,从民众中汲取改造世界的力量,到了动乱年代,他们之所以能逆来顺受地熬过漫长岁月,也与这种情感的支撑有关。从这种意义上说,张贤亮的《绿化树》中把苦难和民众神圣化的倾向,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典型性。与《绿化树》在主题上颇相似的,是先于《绿化树》问世的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在这部纪实性颇强的作品中,王蒙歌颂了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保护了他、哺育了他的边疆人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着那样炽热的火焰。……太值得了,生活,到人民里边去,到广阔而坚实的地面上去!”(13)——这里不也是历经磨难、无愧无悔的乐天情怀么?
不仅仅张承志、张贤亮、王蒙,还有张炜(《古船》的结尾,隋抱朴说:“要紧的是和镇上人一起。”)、矫键(《河魂》的主题是:民族之魂、集体的力量,永远是生命的根本源泉),还有“寻根派”(他们多从民间汲取信念与力量)——都或多或少是当代的民粹主义情绪的代言人。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后来离开了民粹主义,走向新潮,走向世俗化,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却一直不曾中断过——直至1992年,张承志的《心灵史》还在文坛上掀起过一阵狂风呢。
民粹主义是一种圣结的情感。尽管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但耐人寻味的是,当代正气激荡的作品,独钟民粹主义者,反而是那些最富现代意识的作品,浸透了令人迷惘沮丧的世纪末情绪。王朔的小说潇洒轻松,读后仍使人感到迷惘,症结恐怕亦在于此罢。
然而,民粹主义情绪又实在是对现代意识的挑战,对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历史课题的消解。张承志之所以倍感孤独、苦闷,张贤亮、王蒙之所以后来也悄悄离开了民粹主义的旗帜,“寻根派”们后来也渐渐分化了、沉寂了,都是耐人寻味的。可以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声势只能走向衰落;但作为一种抗拒世纪末情绪侵蚀的信念,甚至作为一种中国热血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它还会延续下去,并在历史发生倾斜的时刻,充当某种平衡的砝码。
21世纪:知识分子向何处去?
控诉也罢,忏悔也罢;自审也好,冷嘲也好;——都有道理。全部问题在于:既然现代化的先锋非知识分子莫属,那末,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摆脱掉苦难的重负、心理的疾患,以现代文化精英的面貌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似乎是一个富于理想化色彩的课题)
鲁迅之所以成为许多当代青年学子的人生楷模、精神寄托,不是偶然的。他们一方面还鲁迅以“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的本来面目,并借此表达自己的病苦灵魂,另一方面仍以鲁迅为榜样,在“绝望中抗战”,“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继承了鲁迅的人格与事业。鲁迅精神在世纪末思想界大放异彩,是希望的象征。(钱理群通过“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动向的剖析”,发现“绝大多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都是积极进取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隐士’是不多的”。(14)许纪霖也认为:“在中国五四的知识群中,在虚无中沉沦下去的人毕竟不多,大部分人仍在积极寻找新的信仰,渴慕着重新安置自己的终极关怀”。(15)
鲁迅的精神注定不会“与光阴偕逝”。
鲁迅的道路是“斗士”的道路。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仍然有许多“斗士”承担着“批判现代化”的使命,这一事实似乎表明: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角色,永远为社会进步所需要。
还有“圣徒”的道路可供选择:刘小枫、史铁生、张承志继承了周作人、许地山、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事业,在“精神迷失”、“信仰危机”的现代化进程中,力图以宗教的神性疗治“世纪病”。他们“坚决拒斥任何形态的虚无主义”;(16)刘小枫、史铁生从基督教中汲取爱的希望、自救的希望,张承志则从伊斯兰教中“追求高于公道冤直的绝对真理”。(17)诚然,宗教可以使俗众迷狂,但思想者却从宗教中获取了坚定的生存信念。据说,在台湾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大批知识分子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精神的归宿。这一过程会不会在大陆重演?不妨拭目以待。
还有“学者”的道路:做学问本身也是一种活法,一种自救。在这方面,80年代末悄然兴起的“胡适热”、“钱钟书热”(需要指出的是:“钱学”的兴起决非因为《围城》被搬上荧屏之故。《钱钟书研究》第一辑出版于1989年,就是明证,而电视剧《围城》的播出则是1990年的事)和“陈寅恪热”,对于当代读书界、学问界同仁的人格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甘于淡泊,以求知为乐事,以做学问为精神寄托,相信“吾侪所学关天意”,相信治学也能“维系这已微的‘人心’与已危的‘道心’”,(18)——这便是以陈平原、葛兆光、陈来以及《学人》杂志所选择的人生寄托。用陈平原的话说:“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19)——“为学术而学术”,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诗而诗”一样,也是一种圣洁的选择。从这层意义上说,置身学问热忱也是一种“准宗教情感”(姑妄名之)。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活法:或者“下海”经商,走“文化大款”之路以自救;或者象阿城笔下王一生那样“呆在棋里舒服”,活个自在;……只要不再逆来顺受、自暴自弃,只要不再提心吊胆、唉声叹气,只要不被世纪末的悲凉之雾吞没,就是希望。
从西方知识分子阶级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来看,现代化对知识阶级最大的威胁是“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20)——在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物质消费中迷失了知识阶级应有的信仰。事实上,这样的威胁已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中国知识阶级在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怎样以其特有的优势,“以其强大的文化释谜能力和广泛社会责任感,为人类历史打出最有希望的一张王牌”?(21)——这也许是21世纪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的头号重大课题。
1993年6月13~17日于华中师大
注释:
①《我读〈绿化树〉》,《“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第152-15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②《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读书》1985年第6期。
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之间》,《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1期。
④《所罗门的瓶子》,《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⑤《艰难的选择》,第3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⑥载《中国作家》1986年第5期,第70页。
⑦《地球村、审父,自剖》,《当代》1986年第4期。
⑧香港《镜报》1993年第2期。转引自《文艺报》1993年5月22日。
⑨《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⑩《禁锢的火焰色》,《收获》1988年第2期。
(11)《心灵模式》,《读书》1990年第10期。
(12)(17)《心灵史》第112、67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
(13)《淡灰色的眼珠》(后记)第323页,作家出版社,1984年。
(14)《心灵的探寻》,第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15)《终极关怀与现代化》,《读书》1991年第1期。
(16)《拯救与逍遥》第5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8)葛兆光:《吾侪所学关天意》,《读书》1992年第6期。
(19)《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
(20)韦伯语,引自赵一凡:《白领·权力精英·新阶级》,《读书》1987年第12期。
(21)韦伯语,引自赵一凡:《白领·权力精英·新阶级》,《读书》1987年第12期。
标签:读书论文; 张承志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张贤亮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王朔论文; 金牧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