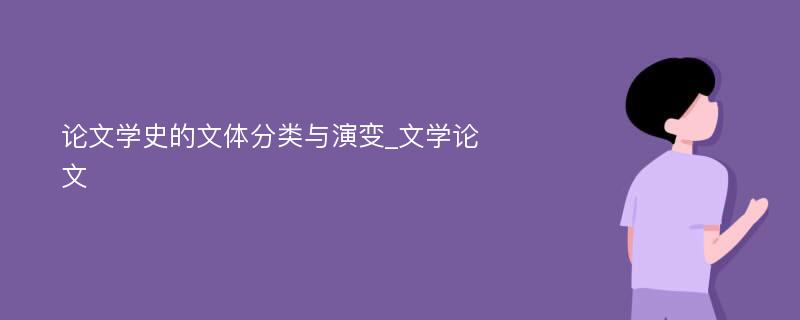
论文学史的文体分类及其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体分类是撰写文学史必先解决的问题。不论文体分类存在多少麻烦,文学史家总是选择某种分类方法,“事先在心中有某种临时性的目标或模式”(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文体分类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没有文体分类,无法开展文学史的叙述,没有文体流变的阐释,就没有真正的文学史。
一
综观古今中外关于文体与文体分类的诸多叙述,我们感到,文学史中的文体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重要性,文体研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它往往成为文学史家关注的中心。二是它的复杂性,文学史中的许多文体研究都具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但又都有某种不足。这两个特点与文体的性质、文体分类的特征密切相关。
什么是文体?我们认为,文体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形态、结构形态、表述形态诸要素的有机统一,它是文学作品的体式和类型。如果把类型简称为类,那么体式就可以称为亚类、亚亚类。
文体研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正是由文体的性质所制约。艾布拉姆斯在他的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构成的,在这四要素中,作品处于中心地位。作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形态、结构形态、表述形态诸要素的有机统一体的文体,集中显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文学史研究以历史与美学观点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地考察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及其变迁,文体也就必然成为关注的中心。正如有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文体是个性的外化……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的探索表现为文体的革新。文学构思的怪异表现为文体的怪诞。文学思路的僵化表现为文体的千篇一律。文学个性的成熟表现为文体的成熟。文体是文学的最为直观的表现。”(注:王蒙:《〈文体学丛书〉序言》,《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没有文体,文学作品便不复存在,文学史也无从谈起,文体史最集中体现了文学史的特殊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文学史也是各种文体兴衰嬗变的历史。人们在文学史研究中,常常以占一定历史时期主导文学地位的文体作为文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阶段,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当然,在文学史研究中,不仅要关注占主导地位文体的流变,也要注意非主导地位的文体的流变,更不能忽略那些对后来新文体的形成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文体。我们可以从文学观念、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的大视角中考察文学的变迁,文学史的叙述亦可以有不同方式,但文体流变应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专门的分体文学史如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戏曲史等是如此,通史类的文学史是如此,文学史中的作家作品研究也是如此。以史的视角分析作家作品,不仅要说出作家写过哪些作品及作品的意蕴,更要说出意蕴如何通过文体得以显现,指出作家作品对于文体的新创造新贡献。
如果说文体的性质使文体流变成为文学史关注的中心,那么,文体及文体分类的特征则使得文学史编撰所需要的文体分类成为可能并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特征之一——文体分类的相对性。文体的分类受到过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的质疑。他在谈论喜剧时指出,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霍布士、康德等人对喜剧的界定都是一些“含混的字眼”,“他们无法用逻辑的方法下喜剧的定义……谁会用逻辑的方法定一个界线,来划分喜剧的与非喜剧的,笑与微笑,微笑与严肃呢?或是把生命所流注的有差别而却又相衔接的整体,割成无数分得清楚的部分呢?”(注: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第102~103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克罗齐把文学分类的相对性特征延伸至一个极端。我们认为,文体世界是一个个复杂丰富、形态各异的精神个体性存在,选择不同的视角,依据不同的标准,文体分类的结果也就不同。“二分法”以文体的语言有韵无韵为标准,“三分法”按摹仿所用的媒介、所取的对象、所采的方式的不同为参照,“四分法”依据作品的形象塑造、结构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的不同进行分类。一些文体亚类的划分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如诗歌的分类。有的以不同的抒情言志方式把诗歌分为叙事诗、抒情诗。有的以是否有一个较为严格的组织结构和规范设计把诗歌分为古诗、格律诗、自由诗。有的以每句诗采用的字数把诗歌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有的以特定的时代产生出的特定诗歌形态分出楚辞、汉乐府等。也有的把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均有很大差异的诗歌分为诗、词、曲,认为词为诗之余,曲为词之余。又如小说的分类。有的按运用语言的差异把小说分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仅以文言小说来说就有若干种分法。明代胡应麟把小说分成六类:曰志怪,曰传奇,曰杂录,曰丛谈,曰辩定,曰箴规。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分小说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纪昀与胡应麟的分类作一比较后提出自己的分类看法:“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指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定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注:《鲁迅全集》第九卷,第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文体分类的相对性不仅通过分类的多样性而且通过不同文体的互渗性表现出来。分类后的文体往往互相包容,互相渗透,甚至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分难解的情况。《离骚》是公认的我国古代长篇抒情诗,诗人的崇高理想和炽热感情迸发出异常灿烂的光彩,但是其中的叙事成分又很多,“几乎可以看作诗人的‘自叙传’,它曲折尽情地写出了诗人大半生的思想和行事”(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一,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红楼梦》作为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当属叙事一类,但作品又包含了诗、词、骚、赋乃至灯谜、对联等各式抒情文体。当代美国汉学界有不少关于中国叙事文学中的抒情境界问题的研究,如高友工教授20多年前就曾提出:“中国小说中的抒情境界问题”,余国藩教授的论文《情僧的索问——〈红楼梦〉的佛教隐意》亦体现这方面的成果。叙事与抒情在同一文体中的交融极为普遍,因为文学作品往往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叙事与抒情的统一。不同文体交织融合的表现形式很多。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亦剧亦诗,明显兼有两大文类的特征。散文诗既是散文又是诗。寓言既具有小说特征又具有散文特征。
特征之二——文体分类的先导性。文学的历史不是一系列文学概念范畴的逻辑展开,而是以一个个体现“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的具体可感的文体呈示在我们面前。没有文体分类,色彩斑斓的文学史可能是混沌一片。事实上,如果没有文体分类,就不可能撰写出文学史。文学创作论中有“文章以体制为先”即文体认识在先,文学创作在后的说法,文学史研究也是如此,文学史的考察要以对文学与文体的认识为先导。克罗齐指出:“从希腊文明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漫长历史时期内不存在美学科学,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们没有关于诗或艺术的一般概念(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这种说法本身在认识形式上就是荒谬的,因为认为精神没有对自身的感知,没有基本的概念,这在思想史的任何时期是都不可思议的,与事实也是完全抵触的。”(注: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第290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 人们研究古希腊文学史,必须在接触大量文学史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诗的概念以及关于诗的分类的认识,而后才能展开对荷马的史诗、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等作家作品的论述。中国古代人心中的文体形态很多。《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关于文体的三十几种分类反应了当时人们对于文体认识的实际,今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虽然要有关于现代文学观念与文体分类的认识,但不能按照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分古代的文学范围,也不能按照现代的文体分类方法划分古代文体的类别,而是要顾及古代人的文学观念,古代人“关于诗或艺术的一般概念”,去划分古代文学的文体类别,展开古代文学史的论述。
特征之三——文体分类的变易性。这一特征的形成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们对于文体的认识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纵观文学研究的历史,人们每提出一次新的文体概念,都是对文体的一次新的发现,即使某种文体概念只是对于特定时期的特定文体的概括,普遍性永久性并不强,也有其价值和意义。第二,文体自身的发展变革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其一,每一文体流变都有孕育、诞生、发展乃至成熟的发展历程。以中国古代戏剧来说,王国维认为“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6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任二白在《唐戏弄》中认为戏剧在唐代大体完备。不论哪种说法都承认中国古代戏剧从巫觋、俳优、百戏,到“真正之戏剧”产生,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历程,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可以有不同的称谓。其二,每一文体发展至成熟之时就会为自身的某些规范所束缚,而规范一旦成为僵死的教条,某一文体或衰落或终结必然随之发生。例如,中国文学史上的骈体文与八股文的命运就是如此。任何一个较为成熟的文体都要不断吸取新的东西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变易性乃是文体生命永不枯萎的内在需求和保证。其三,每一新文体的产生常常是旧文体的蜕变或多种文体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文学实践经验的累积,旧文体如果不断汲取新的因素就可能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孕育出新的文体。文体间的相互作用,或者是文体与其它艺术要素的融合,也会产生新的文体。我国古代的四言诗到五言诗、七言诗,后出的诗体都是在前一种诗体的基础上孕育诞生。词的产生是诗在其发展过程中汲取、顺应其它艺术特别是音乐艺术要素的结果。20世纪以来出现的电影文学这一新的文体是在小说、戏剧、散文、诗歌诸文体的基础上,吸取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语言(如蒙太奇等)而产生的新的文体,电影剧本既是拍摄电影的文学基础,也是可供阅读的文学作品。
特征之四——文体分类的稳定性。从文学史的历史长河考察,文体及文体分类总是处于变易的动态过程之中,从文学发展的具体时段甚至是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某种文体的变易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文体的结构、语言、叙述等呈现出相当的稳定态,因此,我们在叙述文体变易性特征的时候,同时要看到文体分类的稳定性,这一特征使文学史研究中文体分类成为可能。韦勒克认为:“文学类型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秩序的原理,它把文学和文学史加以分类时,不是以时间或地域(如时代或民族语言等)为标准,而是以特殊的文学上组织或结构类型为标准。”(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25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形态既是组成文体的要素也是决定文体的重要因素,结构形态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例如,中国古代由《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体发展至五言诗体,一字之增,标志着诗体内在组织结构的突变。从节奏形式上看,五言诗体变为“二一二”或“二二一”节奏,或者说是“二三”节奏,从语义方面看,五言诗体的每一单句基本上可作为一个独立的表意系统,不像四言诗非两句合成一完整语义单位。纵观四言诗发展至五言诗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成熟的五言诗体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而四言诗的结构形态有着相当的稳定性,占据诗坛主导地位数百年之久。
文体分类是复杂的。翻开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文学史,没有公认一致的文体划分。以小说文体的亚类型划分来说,美国学者韦斯坦因曾有力地批驳过学界流行的各种划分方法,可是自己却拿不出一套“术语前后一致,符合常理”的新方法来取而代之(注:参见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五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这并不妨碍文学史研究者在把握文体与文体分类特征的基础上,“事先在心中”确立某种原则和方法,着手具体的文体分类,展开不同文体流变的论述。
二
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流变的阐释是其中的重点。文学史要论述文体变迁的种种复杂现象及其原因,探寻内在的规律,揭示文体发展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为人们尽可能自觉地去创造条件促使文体的发展、出新、繁荣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各种文体的变化既有内在的原因,又有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也许鉴于文学史中文体流变研究的重要与复杂,以及文体流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体发展的历史被认为“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1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我们认为,文体流变的历史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考察文体自身内在要素变化运动的轨迹与文体间的交互影响。
语言形态是构成文体的要素之一,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语言和社会都是变数,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互相变化,历时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的这种历史变化。就世界范围来看,各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都有从古代语言演进为近代语言的过程,在文学发展历史上,也都有一个由古代语体向近代语体演变的过程。中国古代小说就语体而言有文言和白话两种,用古代书面语言写小说,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近代,与后来用近代语言的口语写成的小说并行,形成两种语体小说相互对峙又相互渗透的文学现象。直到“五四”时期,出现文言与白话之争之后,白话文体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语体的变化成为新的文体如自由诗、话剧产生的主要内力。
结构形态的变化是文体流变的另一个主要内力。法国文学批评家茨·托多罗夫认为,“任何作品都被认作是一种抽象结构的展现,是这结构具体铺展过程中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的体现”,“只有从结构的层次上才能描绘文学的演变”(注:胡经之等:《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第310、3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文体的结构形态的演变。其一,注意文体结构要素的变化。中国古代诗歌由四言诗发展至五言诗,不只是诗句的一字之增,它显示出诗句的内在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古代戏曲剧本中,人物的科介、宾白、歌曲等成为戏曲文体结构形成的基本要素,戏曲结构形态的演变明显地体现在这些要素的变化之中。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列专章论述“元剧之结构”,认为“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其记动作者,曰科;记言语者,曰宾、曰白;记所歌唱者,曰曲”(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9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并具体对上述要素进行了详细而切实的分析。其二,注意文体结构线索的变化。李渔在论述戏曲结构时提出“立主脑”之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注:引自《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第245页,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传统的中国叙事文体主要以人物事件作为结构的主线。这显然与现当代叙事文体的结构线索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现当代作品以人物的心理或深层心理为线索来展开叙述,有的以隐喻、象征作为结构线索,替代传统的矛盾冲突,单一的线型的结构形态发展为复合的、网状的结构形态……这些都是文学史家在论述文体流变时应该揭示的。
叙述形态的变化是文体流变的又一内部动力。叙述形态主要体现在叙述人的口吻、叙述人的视角、叙述的方式等方面,叙述形态的研究对考察叙述文体的流变尤为重要。阅读一部叙事文学作品,人们会感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事件本身的声音,另一是讲述者的声音,也叫“叙述人的口吻”。有学者认为,“叙述人的口吻”有时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叙述人’(narrator)的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而‘叙述人的口吻’问题,则是核心中的核心”(注: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导言》,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同样是叙述三国的故事,无名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用的是说书艺人的口吻,以局外人的视角讲述历史,评说历史人物功过,很少去揭示历史人物的情感世界。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用的是文人小说家的口吻,他在全书叙述中灌注了个人的情感,儒家的仁政思想贯穿全部情节,统率着对全部人物的评价。《三国志演义》的叙述视角、叙述方式都有较大的突破。在叙述三战吕布的故事的时候,《三国志平话》只是粗略的梗概叙述,《三国志演义》不仅对座骑、兵器、人物神态等都作了描写,而且改换了叙述者作为局外人的单一视角,多次变换观察主体,这种变换带来的不仅是情节的扩大,篇幅的增加,而且是叙述形态与文体的质的变化。王国维论述元杂剧之渊源时敏锐地发觉叙述形态的变化对于戏曲产生所起的作用,认为元杂剧之所以比前代的戏曲有进步,表现在两个根本方面。其一是乐曲的进步,“其二则是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也……此二者之进步,一属形式,一属材质,二者兼备,而后我中国之真正戏曲出焉”(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6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文体间的交互作用对于文体流变亦有较大的影响。如果说,考察文体要素的变化偏重历时性地去研究文体的流变,那么,分析文体间的交互影响则是偏重共时性地去研究文体的流变。其实,文学类型的疆界本来就不是不可穿透的墙壁,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一种现象向着另一种现象过渡的边缘地带。“夫文本同而末异”,各种文体都有共通之处,一种文体接受别种文体影响或影响别种文体,是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例如,散文吸取诗歌的因素,诗歌容纳散文的因素,都极为常见。宋诗以散文入诗的特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相互影响的诗歌散文之间的边缘地带,产生出不少交叉过渡的文体,像自由诗、无韵诗、散文诗、有韵的散文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文体流变必须重视的。
第二,考察环境对于文体流变的影响。
社会环境是文体流变最重要的外力,文体流变的研究应置于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之下。社会环境作用于文体流变的力量是多方面的。政治因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政治因素对于文体流变的影响历来为我国文学史研究者所重视。班固在他的《汉书·礼乐志》中指出政治对文学以及文体的决定性作用:“周室大坏,诸侯恣行……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论述了政治教化对包括文体在内的文学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建国以来,我国的文学史著极为重视政治因素对包括文体在内的文学的影响,这从一些文学史著的若干专节的标题即可窥见一斑,如“秦汉之际的社会变化和汉初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汉武帝的文化政策和文学”,“西汉末叶到东汉末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等(注:参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目录》。)。世风世情是影响文体流变的最直接的社会环境因素。一个时代的世风世情是一个时代主导的精神文化氛围,它有力地作用于文体的变化。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出乎纵横之诡俗”(注:《文心雕龙·时序》。)的世情世风。建安文学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注:《文心雕龙·时序》。),因而文体显得慷慨而富有气势。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世虽然艰难,但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注:《文心雕龙·时序》。)。六朝的世风世情直接催发“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产生,对此,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作过独到的分析。
自然环境对于文体流变亦有不小的影响。丹纳的《艺术哲学》把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发展归之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力量,而环境则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的文学史论也有这方面的见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认为,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尚武风气,也影响了当地诗歌的特点。唐魏征《隋书·文苑传》序论中指出南方与北方文学由于环境不同产生语音、风格等方面的差异。王国维阐述南戏与北剧之异同时认为:“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此由地方之风气及曲之体制使然。”(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2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第三,考察读者的审美心理对于文体流变的作用。
读者不是文体的被动接受者,读者的审美需求、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对文体流变的影响是很大的。某种文体一旦固定化模式化,自然会失去其新鲜魅力,不能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文体变革也就随之发生。古人有“诗不如词,词不如曲,固是渐近人情”(注:引自《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第16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的说法。“人情”随时代变化而趋向细密、复杂、多变,旧的文体不能适应人情,不能适应人的审美心理的发展,于是更近人情、更快人情、更畅人情,更符合人们审美心理的新文体便可能产生。中国古代话本小说这一文体的产生发展充分展示出读者大众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话本小说的本源是“说话”,从古代的说故事,到汉魏以来的佛徒宣讲佛经,唐代的“俗讲”,无不与民众的审美需求、审美趣味息息相关,“俗讲”推动了说唱文学的发展,对于“说话”伎艺产生尤有深刻的影响。“说话”在宋代成为职业化的伎艺,宋代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刺激着演艺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戏曲杂伎的游艺场所如“瓦子”、“勾栏”应运而生。然而,仅如此仍然不能满足以市民阶层为主的大众主体的审美需求,到瓦子勾栏听“说话”毕竟要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将“说话”书面化,使之随身携带,随时阅览,一旦印刷条件具备,这种愿望便成为现实。当然,像“三言”这类以统一的体例、统一的结构方式、统一的叙事风格的话本小说的规范性文体的确立,并不仅仅由于读者大众的作用,但话本小说的产生发展始终受到大众审美心理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第四,考察作家的创作个性对于文体流变的影响。
文体流变的动因无论是外力还是内力,都得通过作家的创作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影响文体流变的是最直接因素。屈原那充满“上下而求索”的悲剧精神与志洁行廉的创作个性决定了他的作品的文体风貌,真所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注:《文心雕龙·辨骚》。)。元杂剧之所以能够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能够有“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02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的意境, 元杂剧作家的创作个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王国维对元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元杂剧文体特征的联系作了深刻的论述:“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01~102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文体流变的动因分析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上述四方面的考察体现了文体流变的内力与外力的统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当然,文体的变易过程相当复杂,所受的各种力量相互交织而成为“合力”,其组合的方式不一,比例也不同。文体变易呈现的形态有的是量的变化,文体保留原有的名称,有的是质的变化,它可以是新文体突破旧文体规范以至取代旧文体形态的变化,也可能是一种全新文体的诞生。文体流变在文学史研究中始终是十分吸引人诱惑人的领域。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体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宋元戏曲史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王国维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