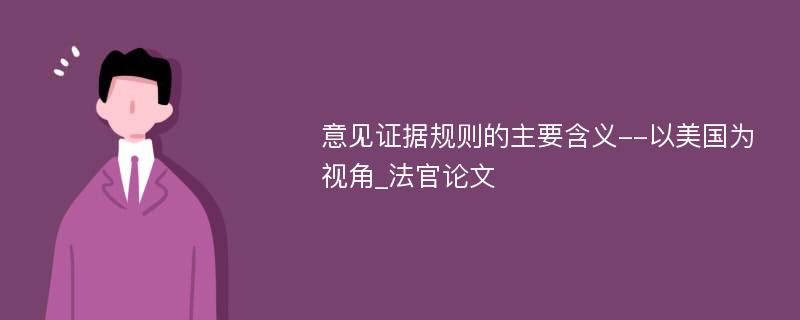
意见证据规则要义——以美国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义论文,美国论文,视角论文,证据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26(2012)05-0517-17
同样是现代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相较于最佳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等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受到的关注及在法学实务界的适用均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层面。尽管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57条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评论性的语言。”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46条强调,“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之后的十年里,少有听说证人证言因属于意见而被排除的案子,相反,实务中却时有采纳普通证人意见证据的案件。①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上述两个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被誉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更引发了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证据裁判、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等问题的热烈探讨。可《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2条第3款确立的我国刑事意见证据规则,“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却并没有吸引多少眼球——虽然该规则与前述我国的民事及行政意见证据规则相比,明显有了巨大的进步:规定了意见证据可被采纳的例外,使得意见证据规则更具科学适用性。
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能够指导实务的开展,而实践中揭示或暴露出的问题又将促使理论研究更为深入、更有针对性。但目前,我国理论研究者似乎遗忘了意见证据规则,如有学者明确表示,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意见证据规则的研究成果非常少,研究深度也不够,②实务工作者对其也是视而不见。这种冷落无疑不利于我国现有意见证据规则以及与鉴定意见有关的证据规定的真正运行,其应有的作用也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对其加以完善以期更符合审判实务需要的工作也难以进行。因此,从理论上探究意见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价值内涵、法理基础、例外或相对性、制度性要求等,引起大家对意见证据规则的关注,进而认识到意见证据规则的存在价值并积极主动地让法条中的意见证据规则鲜活地运用于实务中,应该是当前首先要做的工作。
一、意见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价值内涵和法理基础
意见证据规则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并在美国得到了最为广泛的适用及发展。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等传统上区分证人为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因此,意见证据规则实质上同时调整着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作证时所给出的相关意见的证据资格问题,规范或约束着证人作证时的内容。③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意见证据规则可区分为普通证人意见规则和专家证人意见规则。
按照中世纪法律的古老法则,普通证人讲述的,应该是其所闻所见的事实——“我说我所闻,我言我所见”。正是基于此,意见证据规则要求法官排除普通证人就争议事实给出的相关意见:证人只能就其感觉、感知的事实给出具体的陈述,但不能给出自己基于这些感觉、感知的事实得出的推论、看法、猜测或观点等。④遵循该证据规则,唯有亲眼目睹张三开枪打死了李四,否则证人不能说“是张三开枪打死了李四”。他可以陈述他听到的事实“我听见了一声剧响”,⑤但他不能在没有看到张三开枪打死李四、只是听见这声剧响后便说:“……因此,我认为是张三开枪打死了李四。”“我认为”这部分内容因意见证据规则的存在将被排除。
而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即我国的鉴定人),显然异于普通证人(lay witness)。虽然专家有可能并没有像普通证人那样亲历案件事实,但却拥有专门知识或经验,而该专门知识或经验恰恰是事实认定者缺乏的,是构建某一事实时不可或缺的。由此,意见证据规则允许专家证人作证时给出推论、观点、看法。例如,根据该规则,专家证人就嫌疑人张三虎口处的提取物进行射击残留物鉴定后,可以说,“我认为是张三开枪打死了李四”,且该“我认为……”不会因其是意见而被排除。
源自英国的意见证据规则在美国得到了最为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联邦证据规则》701、702、703、704等条款分别就普通意见证据和专家意见证据的证据资格即可采性作出明确规定,结合《联邦证据规则》602等条文,这些规定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内容。
1.普通证人作证,需其对所证事项有个人知悉,即有感觉、知觉上的直接接触,否则不得作证。
2.除非证人是以专家的身份作证,否则他不得给出意见或推论形式的证言。但如果证人给出的意见或推论形式的证言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则可被法庭采纳:(1)合理基于证人自身的知觉;(2)有助于清晰理解证人证言或对争议事实作出判定;且(3)不以科学、技术等专业知识为基础。
3.专家证人可因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而作证,其作证的缘由是,相关科学、技术或其他特定知识能够帮助事实认定者理解证据或者裁断争议的事实。作为专家证人,他可以以意见或推论等作证,但前提条件是:(1)意见证言以充足的事实或数据为基础;(2)意见证言是依据可靠的原理和方法得出的;且(3)专家证人可靠地将这些原理和方法适用于本案事实中。
4.关于终极问题,(1)在刑事案件中,就被告之精神状态或状况作证的专家证人,不得就被告是否构成被指控犯罪要件或辩护因素的精神状态或状况陈述意见或推论。该终极问题属于事实认定者应独立决定的事项。(2)除了前述(1)的规定之外,证人其他可采纳的意见或推论等,不得因其包含有需由事实审理者裁决的终极问题而受到异议。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有关意见证据的条款同时兼顾了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人意见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较为细致、周密,因而可以说是现代证据制度中较为完善、并可称作典范的意见证据规则。
之所以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确立有意见证据规则,其根本原因在于,意见证据规则的存在,能够确保相关证据客观、真实、可靠。而追求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则是这些国家严格而又不懈的目标。英美法系国家最为古老、最为传统的最佳证据规则或原物原件规则,以及在英美证据制度中占绝对比重的传闻证据规则与意见证据规则一样,均是为了确保证据的可靠性而诞生的重要证据规则。
当人类的司法证明由曾经的非理性渐次走向理性时,证据便成为探求案件真相时不可或缺的方法。而证据裁判主义的确立——通过证据来求证案件真相,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不得裁判,不仅区分了非理性司法证明和理性司法证明,更是将我们不得已而又盲目信赖的神示证据转变为对现代意义之证据的可靠性的普通关注上。因为,只有客观、真实可靠的证据才能实现公正这一司法目标,才能真正定纷止诉。
一般而言,证据的可靠性与证据来源的可靠性密切相关,而证据来源的可靠与否又往往取决于证据提供者的能力与知识,⑥因此,严格掌控证据提供者的能力水平及其知识内容便成为确保证据真实可靠的关键环节之一。而意见证据规则恰恰便是从证据的源头,也就是从证据提供者的能力和知识内容的角度为证据的可靠性架构坚实的屏障。
就证据提供者的能力而言,意见证据规则要求证言的提供者有着与其作证身份相称、相适应的能力。若是普通证人,应具有普通人通常拥有的一般心智,对于发生于周遭的事实、现象、味道等要有相应的感知、记忆、表达能力。普通证人的感知、记忆和表达是证人证言形成的生理基础,其在这三种能力方面的高低或是否有缺陷决定了相应的证人证言是否可靠。若是专家证人,也即我国的鉴定人,不仅应具有前述普通人通常具有的一般心智,否则他同样无法作证。更为重要的是,他应具有解决、分析、判断专门性问题所必备的专门能力,而该专门能力所依赖的科学、技术等专业知识或特定知识,既可源自他受过的教育、培训,也可源自他长期从事某专门性或特定工作所积累的经验。
就证据提供者的知识内容而言,意见证据规则要求证言的提供者应占有与其作证身份相吻合的具体知识。若是普通证人,其占有的知识应是其感官直接接受外界信号刺激而在其大脑皮层留下的印象或痕迹,这种直接的印象或痕迹通常被称为第一手知识,也被我国学者称为“亲身知识”⑦或“直接知识”⑧。普通证人之所以能被要求作证,恰恰是因为他占有这种第一手知识。他具体、如实、中性地陈述了第一手知识,他便给出了可靠的证人证言。若是专家证人,其占有的知识并不必须是第一手的,他的知识可来源于自身的实验,可来源于教育或培训,可来源于其实际工作的经验,可来源于他的同仁、助手等等,但不论这些知识源自何处,其均应是解决诉讼中相关专门性问题必不可少,并以非普通人通常能够拥有的相应科学、技术、经验等为基础。专家证人之所以能被要求作证,恰恰是因为他具有普通人通常不具有的专门性知识。因为有这些专门性知识作为基础,并结合了个案的具体情况,所以其给出的专家证言,即推论或意见,也就被认为具有可靠性。
为什么意见证据规则会针对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给出完全不同、大相径庭的做法?即意见证据规则的法理基础是什么?这显然是研究意见证据规则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此问题,有学者认为:“英美证据法学理论一般认为,意见证据不可采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所证明的事实,证人的意见不具有相关性:如果待证事实属于需要专业知识的事实,非专家证人的意见显然没有任何证明价值;如果待证事实属于不需要专业知识的事实,由于事实裁判者同样可以进行判断或推论,证人的意见又显得没有充分的相关性。第二,该一般原则可以阻止证人僭越事实裁判者的权力。证人职能与裁判职能的区别是意见规则的一项重要理论基础。”⑨“之所以排除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是基于一个前提和两项理由。一个前提是证人证言中的事实和意见是可以明确区分的,证人可以在其作证过程中将其所感受到的案件事实和其对案件情况的推断意见完全区分开来,并只将其中的案件事实告知事实审理者。两项理由是:(1)侵犯事实审理者的职权。在诉讼中,从事实出发进行推理判断是承担事实审理职能的法官或陪审团的职权,如果允许普通证人提供意见证据,就相当于允许普通证人代替事实审理者在诉讼中进行推理判断,这就会侵犯事实审理者的职权,造成诉讼中的混乱。(2)可能造成偏见或预断,影响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超出了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可能误导事实审理者,以至于错误认定事实。”⑩“对于普通证人而言,证据法之所以排除意见形式的证据主要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证人发表的意见并非是自己亲身感知的事实而是对事实的看法或观点,这样的看法或观点有可能是一种主观猜测,容易发生错误;第二,对证人所感知的客观事实作出评价应当属于法官的职权范围,允许证人对自己所感受的事实发表所谓看法或者观点,有侵犯审判权之嫌疑。”(11)
诚然,这几位学者就意见证据规则排除普通证人的缘由给出了不尽相同的理由,但他们均认为,如若普通证人给出的意见证据具有可采性,那么法官,也就是事实审理者裁判的职能便被普通证人所僭越,最终认定的事实就有了不可靠的可能。
但在笔者看来,单纯讨论意见证据规则排除普通证人意见证据的缘由,无疑会认为,事实审理者也即事实认定者不可让渡的职权是根本所在。但如果同时考虑意见证据规则对专家证人之意见证据的容忍态势,我们便能发现,事实认定者的职权该否让渡、或者是否被僭越并不是意见证据规则决定意见证据之取舍的根本原因:如果作证的是专家证人,依据意见证据规则的基本判断原则,其给出的意见证据具有可采性,那么此时事实认定者的裁判职权就没有被僭越?最终认定的事实就一定可靠吗?
就此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理性’的证明制度是一种使用推理来决定纠纷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方法。”(12)显然,现代诉讼离不开理性的证明制度,“使用推理并作出决定”,无疑是事实认定者依法享有的职权:“在诉讼中,从事实出发进行推理判断是承担事实审理职能的法官或陪审团的职权”(13)。专家证人的意见证据,实质是专家证人基于数据、现象或者该个案中的其他证据,借助专业知识给出的推论、推理、推断。该推论、推理、推断,如“根据现场的指印和被告人王五左手拇指指印,可以认为两者来源于同一个手指头,即均来自被告人王五的左手拇指”,本应由事实认定者作出,但因事实认定者没有能力作出这样的推理、推断,只能假专家证人之手而完成,因而也就不得不认可专家证人的意见证据,视其具有可采性。此时,专家证人无疑代替事实认定者行使了本应由后者行使的法定职权,但此时为何又不以侵犯或僭越了事实认定者的职权为由去排除该专家证人的意见证据呢?显然,事实认定者裁判职权是否会被僭越,并不是意见证据规则决定普通证人或专家证人之意见证据可否成为裁判依据的根本缘由。
那么决定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人意见证据之取舍的根本缘由到底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决定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人意见证据之取舍的关键,是事实认定者的“能”与“不能”。
无论作为职业事实认定者的法官,还是作为非职业事实认定者的陪审员,之所以可以依法行使裁判权,是因为他们具有满足相应职能要求的“能”。对于陪审员而言,其行使事实认定之职能的要求是,他“能”基于确实、充分的证据就某些争议事实是否存在给出独立的判断,当然,该判断的给出无疑要借推理、推论而行。但作出该推理、该判断所需的“能”只是常人所具有的普通“能”,并不苛求其在法律或其他专业方面要“精”或“专”。对于法官,无论是否有陪审团审判,其行使职能均要求他不仅要有陪审员那样就事实的存在与否给出基本判断的普通“能”,而且还要、并特别要有熟谙法律条文、精通法律适用等的法律专业之“能”,否则,他就不能被冠名为“法官”。
因此,除却职业的事实认定者即法官必须要有法律专业“能”的职业要求外,法官及陪审员应具有的基本“能”是相同的,该基本“能”也正是一般民众通常具有的。
当普通证人就案件中的某一事实陈述其当时、当地的所闻所见时,其陈述的是现象、外观等客观存在,由这些客观存在推导出某结论,只要不涉及专门性问题,(14)完全可由具有一般民众、也即普通证人之基本“能”的陪审员、法官来完成。因此,普通证人在陈述完所闻所见之后,或在陈述所闻所见的同时,发表个人意见或看法显然就属多余:这时的推理、分析判断并不深奥复杂,如果任由普通证人去完成,那么法官、陪审员又该做什么?法官、陪审员认定事实的职权在此时当然有被僭越之嫌,排除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也就顺理成章,更何况普通证人还可能不够聪明,给出的推论或意见还可能是错误的,进而对法官、陪审员造成不当影响。
无疑,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规则,实际上只是让普通证人充当事实认定者的眼睛、耳朵等感官。当事实认定者借助普通证人知悉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那他就处于如证人一样好的位置,就能得出合理的推论了。”(15)换言之,对于普通事项,可以借助普通证人去看、去听、去闻,普通证人的眼睛、耳朵、鼻子等感官就是裁判者的眼睛、耳朵、鼻子,但之后的思考,却因事实认定者有能力独自完成,自然就不需要再借用了。
当需要专家证人出现时,必然是诉讼中涉及专门性问题,如现场指印的来源、火灾的起火原因、炸药的种类及具体数量、现场弹头的发射枪支、现场轮胎痕迹的遗留车辆、死者体内精斑的所有者、死者死亡的原因等等。即使是尊为法官的事实认定者,他们虽精通法律专业知识,但面对这些通常与科学、技术、特定知识等密切相关的专门性问题,他们也是束手无策,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普通“能”去加以解决,更遑论普通的陪审员。因此,此时再讨论是否会僭越认定事实的职权已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明知自己的职权将被僭越,但因自己没有这个“能”,也就只能认可暂时且部分地将作出推理、推论的职权让渡与专家证人。“尽管对于法律事务而言,法官具有优于常人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具体到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某一专业问题,法官在法律事务上的优势往往从反面提示了其对该问题的无力和无奈。”(16)而专家证人,因为占有事实认定者普遍来说并不具有的专业知识、技术这种“能”(17),所以就事实认定者感到无力和无奈的专业性问题,其所给出的推论、意见的可靠性,相应地就远远高于无此“能”的事实认定者了。
因此,笔者并不赞同英美证据法理论的一般观点及我国一些学者的看法:意见证据规则排除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主要是为了防止裁判者的裁判职权被僭越。事实上,美国的立法例及某些学者的论述也表明,笔者就意见证据规则的排除缘由所给出的观点更为准确、贴切,即决定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人意见证据之取舍的关键,是事实认定者是否有能力就某事实进行推论或判断。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1条规定,“如果证人不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作证,那么证人作证时的意见或推论形式的证言仅限于下列意见或推论:(a)合理基于该证人的知觉;并且(b)有助于清晰理解证人证言或对争议事实作出判定:以及(c)不是基于科学、技术或其他属于规则702条范围的专业知识。”(18)按照该规定,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是存在不被排除之例外的。判断是否是这种例外的重要依据是,如果某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是合理基于证人的知觉,并且不是以科学、技术或其他属于法定范围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得出的,而且还“有助于清晰理解证人证言或对争议事实作出判定,那么该意见证据就可采。撇开是否基于证人的知觉、是否属于专业知识不谈,因为这两点是辅助“有助于”这一实质评判标准而存在的限定条件。我们需要讨论何为“有助于”?在笔者看来,在“清晰理解证人证言”或者在“对争议事实作出判定”时还需要外界的帮助,则表明裁判者在此方面的能力存在缺陷。正是因为这样的不“能”或缺陷,也就只好允许普通证人意见证据的存在,也就只好向普通证人让渡自己的裁判权了。“然而有时,证人所处的位置很优越。于是我们说证人的意见对陪审团的理解很有帮助,因而他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19)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格拉汉姆·C.利里教授的这番话也表明,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如果对陪审团的理解能力有帮助,那么它便具有可采性。
总之,意见证据规则之所以对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人意见证据的可采性通常做出大相径庭的取舍,其根源在于,事实认定者面对普通知识和专业知识时,自身能力存在的普遍差异性。准确把握了这一点,在构建我国的意见证据规则时,便能较好地根据普通裁判者的一般能力,科学地确定普通意见证据及专家意见证据在可采性方面的一般和例外。
二、意见证据规则下普通证人的意见与事实之区分
根据意见证据规则,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区分普通证人作证时的事实与意见,无疑就是准确适用意见证据规则的前提。表面看来,区分“事实”与“意见”易如反掌,因为“意见”不过就是证人对其所观察到的“事实”作出的推论、概括或总结的总和。(20)但实际上,何为“事实”?何为“意见”?许多情况下我们难以回答。正是由于难以区分“事实”与“意见”,《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才专门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或许通过下述证言,我们能够明晰区分事实与意见的难度。
“那片林子茂密得很,中间还夹杂着几棵饱经风霜、行将腐朽的大树。”“我看见一辆桃红色小轿车从我身边驶过,速度有90公里/小时。”“那人很老了,足有75岁。”“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老张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当太阳出来时,他已是精疲力竭且着急不堪。”“当听说女儿还是跟着那位画家走了时,她妈妈很生气。”“在楼道里,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当进到房间时,房间里满是血腥味,丁某倒在血泊里。”
类似陈述在证人作证时司空见惯。那么,“茂密”、“饱经风霜、行将腐朽”、“红色小轿车”、“90公里/小时的车速”、“75岁”、“精疲力竭、着急不堪”、“很生气”、“血腥味”、“枪响”等,究竟是“事实”还是“意见”?换言之,在适用普通意见证据规则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普通证人当前的陈述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意见”。然而,看似简单的“事实”与“意见”的区分当与实务挂上钩时,区分不那么容易了。而这种不易区分,不仅使得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规则的适用处于两难,还有可能令普通证人在作证时不知如何是好:怎样陈述,才能“避免自己的证言不被自己的意见或推断注水”?(21)
以语词而不是画面方式(如播放摄像)重现曾经发生的事情,决定了“事实”与“意见”之间的区分并非看上去那般清晰明确。“实际上.描述事实与给出意见或结论之间,所谓的区别只是描述到底是概括、还是特定这么一回事。对事实描述得越特定,那么它看上去似乎更不像是由事实得出的一个一般概括。”(22)换言之,“事实”与“意见”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的差异只是体现在程度方面:有关“事实”的证言通常是具体、细致并且是中性的;而有关“意见”的证言往往是概括、粗略且表现出一定的偏好。例如,“从李四家院子出来时,王五的眼睛血红,走起路来忽而歪向右方、忽而倒向左方,有时则张开双臂上身往前扑,但脚却没有跟着挪动,因而差点摔到地上;他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把那杯酒给我、给我’;当我试图去扶他时,他则一把推开我,并问到‘要占我便宜,咋的?’时不时地,王五还弯下腰来要呕吐,可他什么都没吐出来,只是呼出更为刺激的酒味”。“王五从李四家院子里出来时醉醺醺的。”这两种描述中,前者,因为具体、细微且中性,所以被认为是“事实”;后者,因为概括、粗略且有一定的偏见,因而被看做是“意见”。换言之,“事实”和“意见”不过是两个标签,被我们分别贴在对同一事件的两种细致程度不同、概括程度不同的表述上了。
当然,前述例子似乎还是能让我们“准确地”将它们分别贴上“事实”或“意见”的标签。但如果证人作证是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三年、甚至三十年,他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形、具体细节,可他印象深刻于自己得出的“王五醉醺醺”结论并就如此概括地说了出来,那么此时是否因该表述是“意见”而应将其予以排除呢?又如果,证人作证时说,“那个老人大概有75岁”,这是“意见”还是“事实”呢?类似的还有关于车速、声音、气味、颜色等的表述。如果说“75岁”、“血腥味”、“90公里/小时”、“红色小轿车”等是“事实”,那么证人又是如何确定的?“90公里/小时”的车速是他根据被观察到的那辆车驶过的距离除以对应的时间算出来的吗?显然不是。而就同样的问题,其他证人则可能会说是“85岁”、“死鱼味”、“80公里/小时”、“砖土色赛车”,因而这些表达终归是“意见”——来自个人当时直接感知后,经由与自己以往的经验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或看法。但如果这些有关年龄、气味、时速、颜色、车型、人的身高或胖瘦、声响的大小和性质等的表述被当做是“意见”,那么当证人作证时涉及这些问题,他又该如何就这些非用具体数字、味道、颜色、形状就无法表达的现象给出最为准确的陈述?
显然,“事实”与“意见”相互胶着、相互庇护的情况使得我们难以将其分清,而事实的认定或最终的裁判却必须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撑、来帮助。也正是因为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1条及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才对意见证据规则作出例外规定。
按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1条的规定,普通证人当不是以专家身份作证、且作证时不以特定的专业知识为基础,那么他是可以给出意见证据的,只要该意见证据是合理地依据该证人的知觉,并且有助于裁判者清晰理解证人证言或有助于裁判的作出。此处对“该证人的知觉”之强调,突出了证人给出的意见只能依据其自身获得的第一手知识,这是对“亲身体验”之证人身份的格外重视!至于“合理”,其潜台词无疑是,“你以前见过很多喝醉酒的人”、“你平时对人的年龄与外观的表象总是判断得很一致”、“因为工作的原因你经常闻到血腥味或来苏水味、柴油味”、“你是猎人,能够准确听出某声响是枪声”、“你是出租司机,能够准确判断出车速”等等,所以,这些相应的经验积累使得你在目击该案件当时的某一情形时,你便能给出较为贴切的结论和推论。而这样的结论和推论虽属意见,但因可以帮助裁判者清晰理解你的表达——有时,证人将构成意见之基础的基本情节细致地描述了半天,可裁判者却不能明了他说的是什么,但证人如若将自己的“意见”呈递上:“那是硫化氢的味道”,则裁判者立即能明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事实”——或者有助于裁判者作出判断,那么这样的结论和推论也是可采的。
虽然,与英美法系的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规则相似的规则早已通过《民事证据规定》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在我国初步确立,但直到2010年7月1日生效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我国的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规则才真正算得上是较为完整、科学并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为它正视了“事实”与“意见”之区分的艰难和不易,允许在适用意见证据规则时采纳那些由证人得出的意见——只要该意见是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得出的,并符合事实。换言之,我国刑事诉讼中目前也已经允许证人以概括、抽象的语言,给出与当时该证人亲身观察、体验到的现象或与事实相符合的意见。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1条以高度概括的方式给出了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在特殊情况下可被采纳时的评判标准。此外。其还用鲜活而又丰富的判例,以较为具体、便于理解和掌握的方式表明,当涉及以下内容时,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可经裁判者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具有可采性:身份、笔迹、数量、价值、重量、尺寸、时间、距离、速度、外形、年龄、力量、热度、冷度、疾病及健康,性格、脾气、愤怒、恐惧、兴奋、迷醉、诚实、普通性格等。(23)
综合而言,这些内容通常与个人的精神面貌或身体状况,个人的性格或声誉,个人的行为、表情显示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以及物体的客观物理状态等有关。如果要求证人将亲身观察到的构成身份、数量、热度、兴奋等诸如此类意见的基础事实或者物理指征细细地描述出来,那么这既不符合人类普遍的表达习惯,并且还有可能不被裁判者准确理解。实际上,普通证人给出的“我哥生气了”、“那天天气很热,至少有40度的高温”等结论性证言,也就是意见证据,并非没有具体的行为、现象等物理指征作支撑,他也确实观察、感觉到了这些具体的指征,但是,人的观察、记忆和思维模式,决定了证人对这些指征的观察和记忆并非以独立、片断的方式进行。在观察、记忆之初,这些指征就已经潜意识地被集合在一起“注册”或以类似于“速记”的方式“翻译”成“我哥生气了”、“那天天气很热,至少有40度的高温”等整体性事实。虽是证人经亲身感受具体指征后得出的意见,但在证人的脑海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又如何要求证人再将它分解回去呢?更何况裁判者面对费时、耗心的分解式陈述,还是难以得出一个结论。基于此,美国还存在一个同样被普遍使用、被视为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规则之例外的评判标准,即:“集成事实规则”(the collective facts rule)。该规则也称为“速记翻译规则”(the shorthand rendition rule)。根据该规则,普通证人作证时,如果其给出的意见或结论性证言是基于无法以其他方式具体表达的众多特定事实得出的,那么该意见或结论性证言便可视作“集成事实”而具有可采性。(24)
对照《联邦证据规则》701条的规定,“集成事实规则”显然能够满足其要求:“集成事实”是证人在其亲身感知的众多特定基础事实之上形成的,其集成式记忆、存储、表达的方式符合人类观察、记忆、存储及表达的习惯,因而集成事实的得出具有合理性;“集成事实”对裁判者清晰理解该证人的证言、或者准确作出裁判显然有帮助;该名证人并不是利用某专业知识来得出这些可称作“集成事实”的意见。因此,可以认为,“集成事实规则”并非《联邦证据规则》701条之外的又一新规则,它只不过是该规则的具体化体现而已。
我国刑事意见证据规则的出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它承认意见证据规则在我国也有例外。但是,仅“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这样一句话,显然过于抽象、概括,不利于其具体的适用。而前面有关美国意见证据规则之例外的讨论,应能给我国相关立法以足够的启发并供我国司法实践借鉴。
三、意见证据规则下专家意见的可靠性
如前所述,因为事实认定者,即法官或陪审员们不具有与案件中专门性问题有关的专业知识,没有能力就该专门性问题给出相应的推理、判断,所以此时必须引入专家,借专家的“能”弥补法官或陪审员们的“不能”,裁判职能在此时的让渡是为了保证与专门性问题有关的推理、判断具有可靠性。换言之,在专门性问题上,专家给出的意见较法官们的意见更为可靠,所以专家可以给出意见,专家给出的意见普遍不会被排除。
那么,是否只要是“专家”给出的意见便绝对可靠、便不需要再经审查判断而直接加以运用?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出于对专业知识和专家的崇拜、敬重,人们普遍对专家意见,也即我国的鉴定意见,持信从甚至是盲目服从的态度。那么,该如何看待专家们的意见?如何看待得到意见证据规则首肯的专家意见的可靠性呢?
按照现代证据法理论,证据能否在诉讼中被采纳、采信,首先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即该证据是否客观存在、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是否满足法律就证据而作出的特殊规定。当在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方面得到了肯定也就是获得可采性之后,证据将接受证据力也就是证明力的评价:证据是否真实、是否对案件待证事实具有证明价值。(25)获得了证据资格之后,本身不仅真实,而且对案件待证事实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才可能成为裁判的依据。
无疑,“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证明价值”是诉讼双方提交至法庭的证据真正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五个核心要素,而证据的可靠性,实为证据五个核心要素中“客观性”、“真实性”这两个要素的别称:唯有客观、真实反映了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该证据才称得上是“可靠”。如我国学者便认为,“所谓证据的客观性,指的是作为证据内容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即证据事实必须真实可靠,而不是主观想象、猜测和杜撰的……”(26)同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门等也认为,“……我们在此提及的,是证据的可靠性,也就是证据的真实可靠性。”(27)“的确……该上诉法院裁定。‘在涉及科学证据的案件中,证据的可靠性将以科学可靠性为基础。’”(28)
基于证据的可靠性与证据的客观性或证据的真实性同义,那么,意见证据规则对专家意见之可靠性的肯定意义何在?就此,笔者认为,意见证据规则无论是对普通证人意见的一般排除,还是对专家证人之意见的一般肯定,均主要只是从可采性角度规范证据的使用:普通证人之意见,通常难以保证具有可靠性,所以一般而言需要被排除;专家证人之意见,因为基于事实裁判者不具有的专业知识而存在,通常具有可靠性,所以一般而言不需要排除。既然是可采性层面的问题,那么此时证据的“可靠性”更多涉及的是“客观性”:普通证人也就被要求客观陈述所闻所见,专家证人则被要求务必基于其拥有的专业知识就案件中的相关事实给出专家意见。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普通意见证据规则之例外而具有可采性的普通证人意见以及作为专家意见证据规则之常态而具有可采性的专家证人意见,就一定完全真实可靠。事实上,证据的采纳和证据的采信从一定视角来看,是从普遍和特殊两个层面分别约束着我们对证据的使用:证据的采纳仅仅是从普遍性入手,判断哪些类别的证据可被法庭所接纳——也正是基于此,在美国专家意见证据规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多伯特案(29)明确赋予法官以看门人(gate keeping)职责的原因。看什么门?看的显然是诉讼证据的准入大门,即哪些类型的证据可以迈过诉讼证据的门槛进而步入下一程序。而证据的采信,则往往要从个案的维度讨论,已经获得证据资格的具体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方面所要求的真实可靠。虽然,证据可采性层面的一些约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证据的可靠性,(30)但证据是否真正真实可靠、是否准确反映了相应的案件事实,还需从采信层面来关注。换言之,意见证据规则对专家意见之可靠性的肯定,只是在证据的资格层面、在证据的可采性层面做了基础的筛查工作,并不大涉及具体专家意见本身的真实可靠性。这一点,从美国的专家意见证据规则发展史上的两个典型案件即弗莱伊案件(31)和多伯特案,特别是后者便可窥得。
弗莱伊案于1923年在哥伦比亚联邦巡回法院尘埃落定,被告弗莱伊希望法院能够接纳由当时的一种测谎仪检测得出的结果为证据,但最终,该检测结果因为测谎技术没有在其所属的特定领域得到普遍接受而被审判法院排除,并得到上诉法院的维持:“科学原理或发现究竟在何时跨越了实验和证明阶段之间的界限是难以界定的。在这个黎明地段的某一时刻,科学原理的证据力量必须得到承认,然而在采纳由公认的科学原理或发现演绎而来的专家证言方面,法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充分证实的是,由演绎推理得出的事情在其所属特定领域已经得到普遍接受。”(32)
显然,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这番话是站在证据的采纳层面加以论述的。它并没有仅从弗莱伊案的测谎结果就事论事地讨论该案中的测谎结果可靠与否,相反,它从测谎原理的科学可靠性入手,从根基上动摇了整个测谎技术或知识的科学性、成熟性——一个不为其所属特定领域普遍接受的东西如何称得上可靠?基于这种称不上可靠的东西又怎能得出可靠的专家意见?弗莱伊案上诉法院对专家意见证据的这一逻辑处理方式最终形成了被称为“普遍接受性”的弗莱伊标准,并在直到1993年多伯特案件出现之前的70年时间里,被不少法院当成评判具体案件中专家意见有无证据资格的标尺。也就是说,在这70年的时间里,某些专家意见,比如说测谎结论、笔迹鉴定意见、声纹鉴定意见、DNA鉴定意见、受虐妇女或儿童案中施虐者心理特征测试结果等等,在某些法院均因未通过弗莱伊的普遍接受标准而夭折于诉讼证据的大门之外!难怪乎有学者评论道,“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弗赖伊标准一直受到一些批判性的分析、限制、更改,并最终遭到了彻底的拒绝。一些法院发现,弗赖伊标准与专家证言相冲突,适用该标准,则会出现争议中的技术太新,甚至未经实验、检验的结果太没有确定性,因而不能为法院所采用。一些法院在继续坚持弗赖伊标准的同时,主张将普遍接受的标准运用到科学证据的证明力而非可采性之中。”(33)
而且,弗莱伊标准的出现还令法院备受责难。依据该标准,某专家意见是否具有可采性,并不是由法官说了算,而是由该专家意见所属特殊专业领域的专家们说了算。他们普遍接受了该专家证据意见所基于的科学原理、技术或知识,那么此专家证据意见就可采,否则就不可采。既然是专家们说了算,那还要法官干什么?
在弗莱伊标准既妨碍了新兴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结果在诉讼中的应用,又涉嫌令法官拱手将本应由自己行使的对证据资格加以认证的权利交给了专家们的当口,多伯特标准因“多伯特诉梅里尔·道制药有限公司案”于1993年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得以确认。
多伯特和夏勒(Schuller)是先天畸形幼儿。他们与其父母一道在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起诉了梅里尔·道制药有限公司,认为他们的畸形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梅里尔公司销售的抗恶心处方药苯涤汀(Bendectin)的结果。因涉及跨州销售业务,该案应梅里尔公司的要求移交联邦法院系统。至联邦最高法院向下级法院发出调卷令时,该案已经历了地区法院判决、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的两次审判。
而整个案件,归根结底,在于原告多伯特等提供的8位证明苯涤汀与胎儿畸形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专家证言是否具有可采性。在由布莱克门大法官主笔的判决书中,开篇就明确:“本案中,要求我们决定在联邦审判中采纳专家科学证言(34)的标准。”地区法院及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均认为,8位专家的证言不满足弗莱伊的“普遍接受”标准,因而不具有可采性,不能成为案件裁判的依据。
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普遍接受”之弗莱伊标准因《联邦证据规则》的生效而被取代,而《联邦证据规则》中与专家意见的采纳与否密切相关的具体规则,即规则702并没有任何地方表示出“普遍接受”应是专家意见可被采纳的前提,也没有吸收“普遍接受”标准的任何意图,它更多强调的是证据的“相关性”——专家科学证言与案件的相关事实有关联,它就该具有可采性。虽然弗莱伊标准本身未被《联邦证据规则》所吸纳,但它所倡导的应该在可采性层面对据称科学的证据是否可靠作出判断的做法却值得肯定。因为唯有基于“科学、技术或其他特定知识”的专家才是《联邦证据规则》702条所认可的。换言之,法官不仅要判断某专家证言是否对事实认定者理解证据或者裁断争议事实有帮助,即是否具有关联性,还要判断该专家意见所基于的科学知识是否可靠。法官要成为审查判断专家意见是否可靠、是否可采的看门人,而弗莱伊标准却将法官理应发挥的看门人作用交付给了专家,显然不当。“那么,面对所提供的专家科学证言,审判法官必须一开始就依照规则104(a)来决定:专家正准备作证的是否为(1)科学知识,(2)将辅助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裁断有争议的事实。这就要求,对证言背后的推理或方法论是否具有科学效力,以及推理和方法论能否合理地适用于争议中的事实,作出初步评估。我们相信。联邦法官拥有对此作出审查的能力。许多因素都将对这种审查产生影响,我们并不指望提出一个正式清单或检验标准。但是,某些一般性意见是需要的。”(35)随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借多伯特一案给出了一般性意见,形成了被称作多伯特标准的裁量准则,供裁量专家意见是否可采时参考:(1)专家意见所基于的假设是否可检测或已经被检测;(2)所基于的理论或技术是否经过同行评审并公开发表;(3)所运用的技术或方法是否已知或可能存在很高的错误率,并是否对该技术或方法的操作有可控制的标准;(4)所用方法在适用时是否有相应的标准以及是否普遍接受。(36)
在给出评判专家意见之可采性的前述选择性参考因素,(37)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还明确,“我们强调,规则702条所预设的审查是很宽松的。它的宗旨是关于所提交公断的原理之科学有效性,也就是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当然,其焦点必须集中在原理和方法论本身,而不是它们所产生的结论。”(38)从证据法学角度看,“集中在原理和方法论本身,而不是它们所产生的结论”恰恰强调的是专家意见在可采性层面的可靠性,而不是由原理和方法论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后者,显然是专家意见在采信层面的问题了。
在多伯特案及锦湖轮胎案(39)的共同影响下,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于2000年为其规则702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在“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特定知识能够帮助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者裁断争议的事实,那么因其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就此以意见或其他形式作证。”之后增加了“但需符合下列条件:(1)证言基于充足的事实或数据;(2)证言是可靠原理和方法的产物;且(3)证人可靠地将这些原理和方法适用于该案的事实。”(40)
仔细品味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条,特别是增加的(1)、(2)、(3)这三项,不难发现,美国意见证据规则对专家意见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层次清晰的。它首先强调,专家意见在诉讼中可以采纳,但专家意见是否可以被采纳、并进而被采信,则取决于它是否在采纳及采信层面分别具有可靠性:(1)专家意见不得凭空而生,应有充足的事实或数据作支撑,且应是可靠原理和方法的产物;(2)专家意见同时还应是可靠原理和方法与具体案件事实的有机适用和结合。显然,(1)是采纳层面的可靠性问题,如DNA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法医鉴定、笔迹鉴定、指纹鉴定、枪弹鉴定等等,通常是可靠原理和方法的产物,且有充足的事实或数据作支撑,所以一般而言,不会被法庭所排除。但这些鉴定应用于某案件时是否得出了可靠的结论,即是否具有证明力,则需要结合该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衡量:接受鉴定的检材和样本来源是否可靠、是否受到污染、是否得到稳妥且科学的保管,鉴定时所用的仪器设备是否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所用的试剂是否过期或受到污染,所用的方法、技术是否合乎技术规范等等,这些方面的任何差池均有可能使得本有可靠原理、方法作基础的某一鉴定活动,最后得出不可靠的专家意见即鉴定意见。因此,在采纳层面获得了肯定的专家意见。还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接受证明力的评价,而这恰恰是(2)所关注的。
在我国,没有“专家意见”、“专家证言”、“专家证人”或“科学证据”等等术语,但却有着本质上与“专家意见”等语词一样的“鉴定结论”之说。虽说我国少有人将鉴定结论与意见证据规则相提并论,但我国法律却认可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均明文规定,鉴定结论或鉴定意见是法定证据形式之一。这表明,鉴定结论在我国诉讼中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障碍。问题是.基于对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科学原理的崇拜,诉讼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是冠以“鉴定结论”的名头,当事人、检察官、律师甚至法官就可能不再怀疑它的可靠性,而是直接将其用作定案的证据。或许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加审查判断就直接使用鉴定结论的状况,并从观念上让人们接受“鉴定结论”一定程度上的非唯一性和主观性,2005年10月1日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第1条、第10条用“鉴定意见”一词代替了“鉴定结论”;而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两个证据规定”也不再有“鉴定结论”的踪影,取而代之的同样是“鉴定意见”。至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和民诉法修正案于相继出台,我国目前的三大诉讼法已有两大诉讼法将“结论”修正为“意见”。由“结论”至“意见”的变化,清楚地表明鉴定人或专家们给出的是“推论”或“意见”,而不是定论,因此,对其不应盲目相信,而是要给以必要的审查判断。(41)
相较于美国而言,我国对能够给出专家意见也即鉴定意见的专家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即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第4条、第5条,唯有在获得行政许可的鉴定机构里执业的鉴定人,才能给出鉴定意见。而美国,则允许最广泛意义上的专家为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提供意见:“……专家不仅是在最严格意义上使用的表达,例如医师、物理学家、建筑学家,而且有时包括大批被称为‘有技巧的’证人的人,例如为地价作证的银行业者或地产者。”(42)理论上说,我国这种鉴定人、鉴定机构资格授予的形式更有利于为鉴定意见的可靠性把关,因为它通过行政审查的方式已一定程度上将某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伪专家”排除在外了,但却有可能使得那些本就因崇拜科学而迷信鉴定意见者更疏于关注鉴定意见的可靠性。他们会天真地认为,给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及其所属的鉴定机构可都是依法经审核后才获得资质的,由他们给出的鉴定意见怎可能会不可靠?(43)
事实上,无论是美国那种广泛意义上的专家证人,还是我国较为狭隘的资质许可式的鉴定人,其给出的专家或鉴定意见均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推论或意见。因为这种推论或意见不是常人能够得出且有助于事实审理者裁判案件,所以美国及我国均将其区别于普通证人的意见,并认可其证据地位。但这种区分和认可只是在证据的可采性层面对鉴定意见或专家意见之可靠性的一般认可,具体到个案,则还需要从证明力的层面加以进一步审查,以判断某案中相关的鉴定意见或专家意见,究竟有多么可靠、其证明力究竟有几何。因此,我国不仅要通过《司法鉴定管理决定》以及其后由司法部颁发施行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对能够就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给出专家意见的“专家”作出最为基本的筛选,而且.还需要对每个鉴定意见有正确的认识。要着重考查,是否有充足的事实或数据作支撑、并属于可靠原理和方法之产物的鉴定意见,在当前的案件中,是否将相应原理和方法与具体案件事实有机结合在一起了。
四、意见证据规则下的终极问题原则与专家意见的受限性
无论是普通证人还是专家证人,按照英美法传统,在意见证据规则约束下,均要受一个原则的限定,即就案件中事实或法律的最终结论,他们不能表达意见。该原则被称为“终极问题原则”(Ultimate Issue Doctrine),并曾经被英美国家最为严格地遵守着——只要当证人作证时给出的意见或结论涉及案件的终极问题.那么这些意见或结论就不得被当做证据。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原则存在,是因为普遍认为,一旦允许证人就案件的终极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事实认定者,即陪审团或法官认定事实的职能便完全被证人篡夺了。例如,“张三实为疏忽大意”、“李四的行为是非法的”、“丁六没能力判断这样做会将自己的钱财撒光”。这里的“疏忽大意”、“非法的”、“没能力判断”等显然均是终极的法律结论,这些终极法律结论本最应该由陪审团或法官作出,但却经证人的嘴给出,陪审团或法官无疑被彻底架空了。
理论上说,法官和证人各自的职责清晰而又界限分明。因不占有某些知识,或者不具有解决某专业性问题所必备的特殊能力,故而陪审团或法官有时必须将自己的权能让渡给普通证人或专家证人,但显然,这种让渡只应是暂时的,且仅仅只在涉及案件的基础事实时出现;一旦涉及案件争议的终极事实,则有权定夺的,显然应是陪审团或法官,否则,陪审团或法官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换言之,意见证据规则对意见证据的允许均限于所涉事实不是案件的最终事实或法律结论,而如若涉及案件的最终事实或法律结论,则有权做出者,只能是陪审团或法官,而不能是证人。事实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出台前的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一直严格地认为,关乎案件的终极事实或法律结论时,证人不得以意见介入。
但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4条基本抛弃了终极问题原则。说它“抛弃了”终极问题原则,是因为按照704(a)的规定,“除了本条(b)项规定的以外,依其它规定已具可采性的意见或推论式证言,不因其涉及本应由事实裁判者裁决的终极问题而受到异议”,(44)普通证人意见或专家证人意见,只要不属于(b)项言及的特殊情形,只要按照前文探讨过的适用条件已经具有了可采性,如意见证言合理基于证人的知觉、对陪审团等事实裁判者有帮助,或意见证言是专家基于充足事实或数据、并将可靠原理和方法有机适用于相关案件得出的等,那么哪怕它涉及案件的终极问题,也不被排除。显然,它更强调证人意见的实用性,并姑且放弃了本应由裁判者一握在手的裁判权。
说它只是“基本”抛弃,是因为704(b)为终极问题原则留下了一丝存活余地。即“刑事案件中,就被告的精神状态或状况作证的专家证人,不得就构成刑事指控或辩护之要件的被告精神状态或状况,陈述意见或推论。此类终极问题应是事实审理者独自决定的事项。”(45)而这一存活余地的出现,始于1984年里根总统被刺案后国会的修法,并使得专家意见在内容上有了明确的受限性:专家们可以自由地就被告是否罹患精神疾病或是否有精神残缺作证,并描述这种精神疾病或残缺的症状、特征是什么,但专家们却不能作证说,该精神疾病或残缺使得被告无法懂得某行为的错误性。(46)此时,专家意见所受的限制在于,他可就被告的精神状况陈述医学结论,但却不能就其精神状况表达法律结论。
按照《联邦证据规则》起草咨询委员会的说法,美国基本抛弃终极问题原则的原因在于,该原则“是过分的,难以适用的,而且一般而言只起到剥夺事实裁判者获得有用信息的作用。”(47)但笔者认为,其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出台,为普通证人意见和专家证人意见的可采性提供了较为缜密、完整而又统一的标准,即以规则701、702为核心,以规则403(48)、602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只要法官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严格按照该评价体系的规定自行裁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即使关乎案件的终极问题,普通证人或专家证人的意见根本不会动摇事实认定者的裁判权或影响诉讼结果的可靠性,因而采纳它又何妨?换言之,终极问题原则已基本上被由规则701、702、403和602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所替代,不再具有存在的现实意义。事实上,规则704(a)对终极问题原则的抛弃是有前提条件的——该条文中那两个不起眼但却必不可少的词汇“otherwise admissible”(本文将其译为“依其他规定已具可采性”)起着关键作用。能够真正抛弃终极问题原则,或者说能够在关乎终极问题时仍被采纳的证人意见,首先要满足一些与意见证据有关的其他可采性标准,否则,终极问题原则无疑还将发挥作用。
基于“otherwise admissible”的存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4(a)的适用实质上又回到了根据规则701、702和403、602的综合规定,对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人意见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审查的问题上来。换言之,是否关乎终极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意见是否对认定事实确实有帮助:有帮助者,虽涉及终极问题也具有可采性;无帮助者,虽不涉及终极问题也不具有可采性。
明晰终极问题原则被基本废弃的原因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某人是否疏忽大意”、“某人有无能力”之类的意见证据仍然会被排除。因为在获得了证人给出的一些基本事实陈述之后,陪审团完全可以就“某人是否疏忽大意”、“某人有无能力”等问题得出自己的判断。此时,证人给出的“疏忽大意”、“无能力”等意见显然就归于无帮助之列了。
如前所述,我国针对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规则在21世纪初才见之于司法解释中,但仅仅还只有三条法律条文,远远无法规范意见证据规则所应涉及的众多问题。虽然在我国与专家证人意见规则同义的鉴定制度在近几年明显为众多学者、实务者所关注,相关的制度构建和完善也在进行中,但与鉴定、鉴定意见密切相关的各种规定明显表现出彼此间少有照应、各自为政的状态。(49)加上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因而有关意见证据的终极问题原则在我国几乎是闻所未闻,更别说对其初始被美国全盘抛弃,随后又略有保留的动态变化和相关原因进行研究了。
尽管笔者并不盲目认为美国的终极问题原则就至为先进,但该原则对事实认定者职权的维护及其近几十年来的动态变化和动态变化的原因,在我国开始尝试规范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和鉴定人鉴定意见之可采性的当前,却可给我们以积极的启发。
(1)就案件中最终争议的问题,也就是终极问题,有权给出结论的只能是事实认定者,如人民陪审员或法官。
(2)事实认定者对终极问题的裁判权,也就是终极问题之结论的给出权,可以让渡与普通证人或鉴定人,也可以保留。但如若让渡,则前提应该是有一套完备、周严、缜密的意见证据规则。普通证人或鉴定人给出的、有关终极问题的意见,首先应该满足相应的可采性要求:该意见对事实认定者有帮助,如若是普通证人给出的,需是以其亲身感知的知识为基础,且不是专家才能给出的;如若是鉴定人给出的,需是以充足的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并是可靠科学原理和方法与具体案件的有机结合。
(3)鉴定人在刑事案件中就被告之精神状态给出鉴定意见时,只能就有无精神疾病或缺陷以及这种疾病或缺陷的主要特征或症状是什么给出意见,而不能就有该精神疾病或缺陷的被告在实施某行为时是否意识到该行为的违法性、不当性发表看法。
就(1)而言,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树立相应的观念。就(2)而言,我们需要做的,则是在裁判职权让渡与否的问题上做出选择:在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多样、各种知识爆炸式涌现的情况下,指望事实认定者成为“万事通”,占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并进而可以自如完成其终极问题裁判职责似乎不大现实,那么让渡其裁判职权似乎也就成为不二的选择,此时,显然我们应该梳理、完善现有的用于评判意见证据之可采性的各种标准,使之形成一个精炼、完备、周严、缜密的意见证据可采性评价体系。
至于(3),则恐怕是我们不得不施以“手术”的项目。因为在我国,在《司法鉴定管理决定》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约束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于1989年7月11日颁布,同年8月1日施行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司法精神病鉴定均不仅仅限于被鉴定人精神疾病状况的鉴定,有关各种“能力”,如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诉讼能力、服刑能力,民事案件中被鉴定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民事诉讼能力,以及各类案件中被害人等在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对侵犯行为有无辨认能力或者自我防卫、保护能力等,都是司法精神病鉴定人有权鉴定的内容。被鉴定人是否罹患某种精神疾病,其症状或外在表现、特征如何,显然属于医学知识范畴,理应由具有精神病学这一科学知识和经验的专家或鉴定人根据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给出;具有精神病学科学知识和经验的专家或鉴定人给出的结论也因此具有可靠性——正是对这种结论或意见之可靠性的渴求,意见证据规则才允许专家或鉴定人自此介入诉讼。但前述各种“能力”,无论是刑事责任能力还是民事行为能力,无一不是法律上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内涵,明显有别于普通人(包括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理解,“而证人和陪审团对能力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于法律的规定”。(50)当然,我们可以在诸如司法部颁布的标准化鉴定方法等规定中加上这样的文字,“运用精神病学及法学的理论和技术”但有了这种文字,精通精神病学知识的鉴定人就拥有了法律专业知识吗?就能深谙并能准确把握法律概念上“能力”的内涵、外延及具体适用吗?当然,也许有人可能会说,诸如“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标准”之类标准的出台,能够帮助精神病鉴定专家就法律上的“能力”作出分辨和评断。既然普通人(当涉及法律问题时,精神病鉴定专家充其量也不过只是普通人)就能依据该标准分辨并评断法律上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够在精神病鉴定专家就被鉴定人的精神状况或缺陷及具体表征给出医学方面的专家意见之后,让事实认定者参照“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标准”之类的标准就法律上的“能力”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履行自己本该履行的职责呢?意见证据规则对专家意见证据地位的首肯起因于专家拥有事实认定者不拥有的专业知识及依附专业知识而存在的推理、判断能力。即使不是案件的终极问题,但如果对事实认定者没有帮助,即事实认定者本身有知识、有能力解决,如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将该问题交给其他人解决,否则,就真正成了裁判职权的被剥夺。事实上,我国的司法实务特别是刑事司法实务中,涉及精神病鉴定的案件之所以争议颇多,与精神病鉴定专家额外负担了本应由事实裁判者完成的“能力”评判工作不无关系。因此在我国,有必要还原精神病鉴定专家的本职功用,将其专家意见的给出限定在对被鉴定人之精神状况或状态的诊断方面,并在经诊断确定被鉴定人患有某精神疾病时允许其陈述,“这种疾病或缺陷通常会表现出××症状或特征。”至于有这些症状或特征的精神病患者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责任能力”或“行为能力”,则并非精神病鉴定专家之医学知识所能解决的,所以应返回并由事实认定者自身来解决。显然,在实施该终极问题还原“手术”的过程中,美国对终极问题原则的全盘放弃以及重新适当肯定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五、意见证据规则的适用要求
意见证据规则在我国虽经《民事证据规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和“两个证据规定”得以先后确立,但仅有十年左右的历史,而且相关的理论研究还非常薄弱。因此,意见规则的适用到底需要怎样的环境,到底会有怎样的效果,目前还难有定论。但是,意见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的发展史却告诉我们,意欲发挥意见证据规则的应有功效,确保普通证人之意见不轻易篡夺事实认定者的职权,确保专家证人之意见能被可靠采纳,我们的诉讼环境应当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一)法官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并能自如、自觉地行使
意见证据规则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意见”区别于“事实”,有可能令事实认定者形成偏见进而影响诉讼的公正性。但如前所述,“意见”与“事实”的区分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恰恰是这种区分的不易,使得意见证据规则的适用要极大地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此外,无论是普通证人意见还是专家证人意见,如果其涉及案件的终极问题,那么它是否已具有了可采性,则取决于根据意见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此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法官自行裁量。无怪乎,有学者认为,“正常理性要求赋予法官更大自由裁量权,至少可以对证据是‘事实’还是‘意见’加以区分,而且也需要授予其批准甚至是意见证据(也可采纳)的权力。”(51)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对案件的处理更多是严格依照严苛的法律条文。但因法律不可能完全具体、精细地反映复杂而又多变的社会,所以在制定粗略、概括、抽象、滞后、不周延、模糊的法律条文时,我们不得不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我国的刑事意见证据规则来看,“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法律无疑赋予法官相应的自由裁量权——就“何为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法官有权自行决定。但问题是,我国整个的法律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及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结果的评价,却似乎对法官自如、自觉行使自由裁量权设置了一定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要使我国在立法层面已经得到认可的意见证据规则真正得以有效适用,为法官们创造一个其能自如、自觉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氛围很有必要。
(二)质证程序得以充分保障并能有效实施
与其他证据规则一样,意见证据规则的适用并非独立的过程,它需要程序的保障,而在众多的保障程序中,质证应该是最为关键的程序之一。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如若撇开证据的合法性这一蕴含有丰富价值追求的社会属性不谈,证据的生命力显然在于证据的可靠性。而意见证据规则恰恰就是为了确保证据有着基本的可靠性。诚然,法官可依法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而定夺哪些证据可采纳、哪些意见得排除、哪些虽是意见但却可采纳等等,但法官行使该裁量权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就某陈述是“意见”还是“事实”有争议、有质疑,如果没有争议、没有质疑,也就不需要法官来裁量了。而对陈述的争议、质疑,恰恰就是质证,故而没有质证程序,意见证据规则就无以适用,就无以从可采性层面切实保障相关陈述的可靠性。进而言之,获得可采性的意见证据,其是否真实可靠,是否真正具有证明力,则还需要当事人双方借助直接询问、交叉询问的质证程序才能完成。因此,意见证据规则的适用离不开质证程序。
经过司法改革,经过借鉴、吸收先进发达国家的法治精华和经验,虽然从质证程序设计上说已经为我国现行诉讼法所确认,但因案件负担沉重,或者对质证的价值认识还有局限性,质证在实务中往往流于形式。再者,我国现行诉讼法的制度设计还存在着本质的缺陷,以至于与意见证据规则适用密切相关的质证程序根本无法落实:就普通证人的陈述而言,质证由律师甚至当事人本人即可完成。就鉴定人给出的鉴定意见而言,质证如若仅仅依靠律师及当事人,则显然难以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因为鉴定意见所基于的专门知识、技术、原理等,非常人所能理解。也恰恰是这一原因。我国《民事证据规定》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均明确许可鉴定意见的不利方可以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即专家辅助人)参与对鉴定意见的质证。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虽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通常支持控方的起诉),但相关的法律却没有允许辩护方获得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帮助,也就是说,即使鉴定人应辩护方的要求出庭接受质证,但因辩护方并不拥有相关的专门知识,所谓的质证特别是交叉质证,只能是“隔靴搔痒”。
值得肯定的是,将于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则有可能使这种局面不再存在。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根据这一规定,不仅仅是辩护方。而且包括公诉人、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均能在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帮助下真正质疑鉴定意见。而今年8月3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在其新增的第79条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性问题提出意见”,使得曾经只是由《民事证据规定》这一司法解释来规范的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得以正式法律化。这些变革对于意见证据规则在我国的有效适用无疑大有裨益。(52)
(三)实践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互动促进现有意见证据规则体系逐步科学化、缜密化
意见证据规则于我国法制而言,无疑是舶来品,其真正嵌入我国法律条文中只不过十余年。嵌入我国法律中的意见证据规则到底有无生命力,在实务中到底有无具体适用,且适用过程中到底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无疑需要我们去探寻、去研究、去总结。同时,我们应该一改当前理论界少有人关注意见证据规则的现象,多关注意见证据规则的价值内涵、适用基础、实质内容等问题,力图实现理论与实务良性互动,才可能将舶来的意见证据规则真正鲜活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此外,考虑到专家意见证据与普通意见证据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有些规定就必须站在意见证据规则的制高点加以统一规定,而不是像当前那样由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地规定并施行。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科学、缜密的意见证据规则体系,以便普通证人的意见及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均能有机地得以适用。
注释:
①参见何挺:《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可采性与运用规则》,《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0期。
②参见马贵翔、张海洋:《意见证据规则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③这就与同样是为了确保证人证言之可靠性的传闻证据规则有了根本的区别:意见证据规则从作证内容上要求,普通证人通常只能给出事实证言,专家证人则可以给出意见证言;而传闻证据规则则是从作证地点上要求,证人的证言通常应该当庭给出。
④这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普通证人”在英美法系学者著述中又被称为“事实证人”。参见杨良宜、杨大明:《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美证据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⑤严格说来,证人陈述时所说的“剧响”中的“剧”也属于一种观点、看法,也即意见,因为所谓的“剧”无疑揉入了证人的看法——该声响很大,而不是弱的、小的。但如果不允许证人在陈述响声大小时使用“剧”、“轻”等字眼,那么,又该如何或者又该用怎样的语言描述这一声响的大或小呢?显然,有些事实、现象可以用中性的、纯描述性的语言相对具体地陈述出来,但有些事实、现象则难以如此表述,因而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规则不得不正视“事实”与“意见”之区分的艰难性、不易性,而允许某些“意见”以“事实”的面目出现,进而不被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规则所排除。详见后文第三部分内容。
⑥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⑦[美]罗纳德·J.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⑧前引⑦,第708页。
⑨宋英辉、吴宏耀:《意见规则——外国证据规则系列之四》,《人民检察》2001年第7期。
⑩前引①。
(11)前引②。
(12)汤维建:《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代译序)》,载[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3)前引①。
(14)要注意的是,如果涉及专门性问题,此时就不会是要求普通证人,而是要求专家证人作证了。
(15)Graham C.Lilly.Principles of Evidence,the 4th edition,Thomson/West,St.Paul,2006,p.15.
(16)汪建成:《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法学家》2009年第4期。
(17)在我国,有学者称这种与“专业知识、技术”有关的“能”为“技术能力”。参见前引⑨。
(18)Allen, Kuhns, Swift and Schwartz,Evidence:Text,Problems,and Cases,4th edition,Aspen Publishers,New York City,2006,p.611.
(19)Supra note (15)。
(20)前引⑦,第716页。
(21)Supra note (15)。
(22)Mark Reutlinger,Evidence:Essential Terms and Concepts,Aspen Law & Business,1996,New York,p.182-183.
(23)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24)Supra note (22),p.184~185.
(25)“证明力的主要内容是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参见前引⑥,第249页。
(26)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7)Supra note (18),p637.
(28)Supra note (18),p641.
(29)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509 U.S.579(1993).
(30)评价证据是否可采所依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与评价证据是否可信所依据的真实性、证明价值,并不能完全分开:证据如若真正客观、如若真正与案件有关联,并且不因取证的非法性而“屈打成招”,那么该证据相应就会真实可靠、相应就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参见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
(31)Frye v.United States,293 F.1013(D.C.Cir.1923).
(32)Frye v.United States,293 F.1013(D.C.Cir.1923),转引自:Allen,Kuhns,Swift and Schwartz,Evidence:Text,Problems, and Cases,4th edition,Aspen Publishers,New York City,2006,p632.
(33)此段话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法院在适用专家意见证据规则时,首先解决的是可采性即证据资格的问题——而弗莱伊标准的基础便是,某些专家意见,因其基于的原理、技术缺乏可靠性,所以不具备证据资格。参见[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第5版)》,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34)“专家科学证言”也即“专家意见”。因专家证人给出专家意见通常基于科学原理、科学知识而得出,所以“专家意见”、“专家证据”、“专家证言”又被称为“科学证据”或“专家科学证言”。
(35)前引⑦,第733页。
(36)Supra note (15),p364。
(37)所谓“选择性参考因素”,是指在考虑专家意见是否具有可采性时,不必要求其同时满足这些因素,如若能满足其中一条、或几条就可以。显然,这比弗莱伊的“普遍接受标准”要宽松了许多,更适宜新科学、新技术应用于解决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
(38)前引⑦,第734页。
(39)锦湖轮胎案(Kumho Tire Company,LTD.v.Carmichael)于1999年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审结案。从实质上看,该案与多伯特并没有不同,即均是关于专家意见之可采性标准的判例,所不同的是,多伯特案涉及的是科学知识方面的专家意见、而锦湖案涉及的则是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方面的专家意见。由布雷耶大法官(Justice Breyer)主笔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认为:多伯特案确立的法官作为专家意见之守门人的职责,不仅在专家意见涉及科学知识时具有,在专家意见涉及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时也同样具有;当专家意见涉及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时,法官在完成其职责时,也应该考虑由多伯特案给出的那四个衡量因素。
(40)Supra note (18),p628.
(41)当然,由“结论”至“意见”的词语变化,还使得我们能够在对意见证据规则加以研究、适用时,更好地将“鉴定意见”考虑在内。
(42)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咨询委员会对702条的部分解释,转引自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5页。
(43)在我国,对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登记许可可以说是形式上的,如申请做鉴定人,只要满足基本条款上的要求,即遵守法律、具有相应要求的职称、或受过高等教育并从事相关工作达一定年限、且身体健康等,就可获得相应资格。这种较为宽泛的、非实质性登记许可制严格说来,并不能真正保证从事鉴定工作的人的实际能力,因而其出具的鉴定意见必然在可靠性上还需要进一步的评判。
(44)Steven Goode and Olin Guy Wellborn Ⅲ,Courtroom Evidence Handbook:2006-2007 Student Edition,Thomson/West,2006,p218.
(45)Id.
(46)Supra note (44),p221。
(47)转引自前引⑦,第788页。
(48)“尽管某证据具有关联性,但如果其具有的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或误导陪审团的危险,或者考虑到过分拖延、浪费时间或无谓地出示一些重复证据等因素,已实质上超过其证明价值时,那么该证据也可被排除。”受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没有讨论规则403条对意见证据规则的具体影响。
(49)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涉及专门性问题时可启动鉴定,并认可了鉴定意见的法定证据地位;有关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刑事诉讼中的“两个证据规定”对鉴定的启动或鉴定意见的可采性该如何评价有一定的规定;全国人大颁布施行的“司法鉴定管理决定”虽原则性地涉及了某些鉴定的行政管理问题,但具体实施管理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各自出台的管理规范却不尽相同、甚至有所冲突,这都使鉴定意见最终在法院的可采性上出现一定的问题。
(50)Supra note (24),p187.
(51)[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52)但即将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如同《民事证据规定》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一样,均没有明确,所谓“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是否只能是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员,是否可以包括那些具有相关专门知识,但却不拥有鉴定资格的专门人士。因而,笔者认为,刑事诉法法修正案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即使生效,实务中还会出现一些问题,以至于对鉴定意见的质证仍然有可能不能完全有效。
修回:2012-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