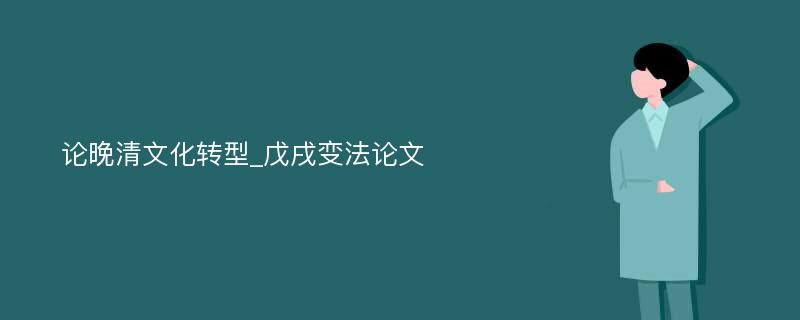
论清末的文化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的文化转型,是指中国文化由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确切地说,始于本世纪初。它表现为:突破以体用为中西文化定位的“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而欲建构一种以西学为主导的“会通中西”的新的文化模式。这标志着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的进一步深化,已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
本文的论述将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切入,着重探讨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性质、特点。
一、中西体用之争
考察本世纪初的文化转型,必须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说起,因为它是本世纪初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是中日甲午战后高涨起来的变法维新思潮的必然产物。
如所周知,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甲午战争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局面。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求进步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当时的维新派看来,只有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实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为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而作的最初尝试。“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这次运动的目的;变更政体、行君主立宪,是这次运动的政治纲领;而宣传西学、批判旧学,则是这次运动的文化纲领。维新派宣传西学的重点在“伸民权”、“倡平等”,而他们批判旧学的重点则集中在封建君权、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和人性学说等方面。他们对于西学的提倡和对于旧学的批判,不但激发了人们“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更使资产阶级思想得到大发扬。因此,戊戌变法不仅是一次爱国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一思想启蒙运动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突出表现为文化思想上的两重性。例如,它倡言变法维新,却又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它宣传西学,却又披上今文经学的外衣;它批判旧学,却又尊孔孟;反程朱,却不反陆王;反古文经学,却不反今文经学。凡此种种,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文化思想上的弱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唤起了人们的思想觉醒。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更从文化思想的深层次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这突出表现在:它突破了以“体用”关系为中西文化定位的“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而欲建构一种以西学为主导的“会通中西”的新的文化模式。
以“体用”关系为中西文化定位,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一种思维模式。根据这一思维模式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主张。在19世纪末以前,基本上是两种文化主张,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和维新派的“西体中源”说。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由冯桂芬发其端。他于19世纪60年代初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冯氏此说成为后来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张本。然而,这一口号的规范提法直至19世纪80年代中才见之于报端。至于对这一口号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释,使之成为洋务派“自强新政”的理论根据和文化主张,则是由张之洞在19世纪90年代完成的。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一种体用二元的文化观。所谓“中体”,质言之,是指正宗儒学所倡导的封建纲常名教。他们认为这是治国之“道”,立国之“本”,为国家命脉之所系,故又称之为“体”,它不能变。所谓“西用”,质言之,是指西方近代的物质技术,属“器物”之“用”的范畴。他们认为可以“用”它来“应世事”,达到强“本”固“体”的目的,故“西用”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实质,是试图在不改变中国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借引进西方近代的物质技术来强“本”固“体”,维护封建统治。显然,这是一种强“西用”以就“中体”的文化主张。虽其初有针对封建守旧派“不知通”的一面,但更有针对维新派“不知本”的一面。随着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这一理论旨在卫“道”固“本”,反对变法维新的实质也就更加凸显起来了。
“西体中源”说是维新派的变法理论和文化主张,目的在于为他们的“托古改制”提供历史根据和理论支持。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理论与“西学中源”说虽同属一个思路,但内涵、意旨各异。
“西学中源”说早在明代后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其时,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李之藻(公元1565—1630年)等人在介绍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时就持这种观点。但是,这一观点之广为流行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以后。当时,洋务派提倡“西学中源”说,是为了给他们的“西用”论提供合法的历史根据。所以,他们所说的“西学”,始终是局限于西方近代的某些科学技术。这是一种专讲“器物”之“用”的所谓“实学”,即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
维新派所说的“西体”,不等于洋务派所说的“西学”,而是指西方近代的政体。康有为倡言此说最力。他于19世纪90年代初专门写了《孔子改制考》一书系统阐发此说,其要点有二:一曰,“托古改制”,历来如此。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子就是“托古改制”的祖师。二曰,西方近代的政体,中国古已有之。为此,他把西方近代的政体与所谓的“孔子改制”联系起来,认为在儒家经典中已经有行“共和”、“开议院”的主张,只要对儒家经典重新加以诠释就可以从中找到西方近代民主政体的原型。这种西方近代政体中国古已有之的“西体中源”说,与洋务派的“西学中源”说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与意旨迥异,是显而易见的。
维新派的“西体中源”说,是为了打破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将中西体用二元化的理论格局,试图借“西体中源”说为“中体”注入“西体”的内容,以论证其变更政体的合法性。考其初衷是为了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然而,事与愿违。究其原因:其一,从学理看,“西体中源”是要证明中西二“体”同“源”,而且是“西体”源于“中体”。这是以“中体”为本位的文化观,它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以“中学为体”的文化观是一致的。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而归宿点相同,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可谓“殊途同归”。其二,从研究问题的思路看,“西体中源”说是一种以古证今的思路,其结果自然是古的拖住今的,终将为古所累。其失败是必然的。可见,直到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文化观仍然徘徊在“中西体用之间”,还没有发生新的突破。文化观的新突破,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事。
二、文化观的新突破
戊戌变法失败后文化观上的新突破,其主要表现是:以体用一元论代替体用二元论,以“会通中西”的文化模式代替分中西为体用的文化模式。这是本世纪初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体用二元论的文化观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理论根据,在19世纪后半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戊戌变法的失败促使当时的有识之士“从文化根本上”进行反思。
在维新派中,最早向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体用二元观发难的,是严复。他于1902年致函《外交报》,尖锐批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体用二元观,并提出“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
首先,他针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指出:“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认为“中体西用”论就是属于“合之则两亡”的理论,必须予以否定。他进而指出:“一国之政教学术”,犹如具备有各种器官的动植物。假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颈,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认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之说就是属于取马之四蹄加之于牛之脖子一样的荒谬,既不能行千里,也不能耕田陇。虽然严复仍以体用论中西文化,但是,他主张中西各自有其体用,就在实际上否认了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体用关系,因而也就突破了以体用关系为中西文化定位的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严复继而提出“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在“会通中西”的同时,更要分清轻重缓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求中国“所本无”;“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同上)可见,严复“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是以宣传西学为当务之急,而他所要建构的文化模式是以西学为主导而又兼通中西的文化模式。显然,这是一种从根本上有别于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新的文化模式。
与此同时, 梁启超也致力于“从文化根本上”进行反思。 他于1902—1903年以“新民说”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比较中西文化差异,同样提出要建构“会通中西”的文化模式。他在解释“新民之义”时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这是说,既要磨砺中国“本有”的文化使之发扬光大,又要吸纳中国“本无”的西方文化“以补我之所未及”。这与严复“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是一致的,其重点也在宣传西学。他要求用西方近代的文化观念来改造国民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一句话,即“新民质”——认为这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从梁启超“新民说”的内涵来看,他是以“会通中西”来建构一种以西学为主要特色的中西合一的文化模式。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即“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这与严复所要建构的文化模式可谓异曲同工。
由此可见,随着本世纪初文化观上的新突破引起了文化模式的转型,即由19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中学为主导的“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向本世纪初以西学为主导的“会通中西”的文化模式转变。这是本世纪初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三、文化论争的新进展
本世纪初的文化转型标志着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
如所周知,文化的构成是多层面的,但最基本的构成,一般认为,是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精神层面的文化属于深层次的文化;相对于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而言,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化属于浅层次的文化。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也是如此。先是学习西方近代的物质技术,进而学习西方近代的经济、政治制度,最后是从精神层面学习西方近代的思想学说。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这一历史进程。可以这样说,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西文化论争大体上是围绕着“中体西用”论展开的。所争的重点在要不要“西用”的问题上。守旧派反对“西用”,认为这是“舍本务末”;洋务派力主“西用”,认为这是强“本”固“体”之“术”,而非“舍本务末”。正如上面所说,洋务派所讲的“西用”仅限于西方近代的物质技术,如“汽机兵械”一类。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主要是在物质层面上进行。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中西文化论争的重点已经转移到要不要变更“政体”的问题上。维新派主张变更“政体”、行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就是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张之洞于此期间发表《劝学篇》,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论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继续坚持强“西用”以就“中体”的文化主张,就是直接对抗维新派变更“政体”的变法运动的。可见,甲午战后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由物质层面转到制度层面上来,它反映了这场论争的逐步深入。
戊戌变法的失败既是清末开始的文化转型的契机,也是这场文化论争向深层次发展的重要转折。这一重要转折反映到思想领域里,表现为:更深入地开展对宋学及其理论支柱道统论的批判:反映到学术史领域里,则表现为:“采西学新说”以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
宋学亦称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得到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表彰,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从学术思想层面批判宋学,表明这场文化论争已经深入到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从精神层面上批判封建统治的具体表现。当时的革命派是批判宋学的主力军。他们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宋学之专制”,认为它“钳锢天下之人心,束缚天下之才智”(《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 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35页),是为封建君主实施思想专制的政策服务的,而理学家的道统论则是旨在确立“宋学之专制”的理论。因此,为了提倡“学术自由”、批判“宋学之专制”,就必须反对理学家的道统论。他们宣称:“且学术所以进步者,由于竞争也。”因此,主张用学派来对抗道统,认为“学派贵分,道统贵合;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学派主日新,道统主保守;学派则求胜前人,道统则尊尚古人;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道统辨》,同上第3集,第735 —739页)从他们对学派和道统的一褒一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他们提倡的是学术自由竞争、学术民主平等、学术开拓创新;他们反对的是学术专制独断、学术等级划分、学术因循守旧等。质言之,他们提倡的是属于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而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它表明了这一时期新学与旧学斗争的深入,而这正是中西文化论争向深层次发展的突出表现。
“采西学新说”以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是这场文化论争向深层次发展的又一突出表现。
大家知道,就文化形态而言,中国历代的学术史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传统性质。从内容看,它所要概括和总结的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属于以儒学为主体,儒、佛、道三家思想兼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从形式看,它用以概括和总结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方法,基本上是传统的方法,即中国传统史学修史通常所采用的“寓论于史”的实证方法,并体现为四种主要的学术史书编纂体裁——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和学案体。宋明以来、理学盛行,为学讲“性道”,治经重“义理”,修史续“道统”,蔚然成风。在学术史领域,它表现为:重在为理学家修史立传,以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它千载一脉,亘古不变。这样的一种学术史模式,自宋及清,循而未改。直至本世纪初,才由梁启超首先发难,突破这种学术史模式。他于1902年发表了题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文集》之七)的学术史专著。此书虽系未完成之作,但从已有的框架结构来看,仍不失为一部卓然自成体系的学术史新著。
其一,它提出新的学术史分期法。
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来,学术史的分期除以朝代先后为序外,更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氏此书,打破了传统的学术史分期法而另立新章法。他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据此,他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或曰七个“时代”。这就是: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春秋战国为“全盛时代”,两汉为“儒学统一时代”,魏晋为“老学时代”,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清代亦称“近世”为“衰落时代”(同上书,第3页)。 这样的学术史分期是否恰当,另当别论,但是,他试图按学术思想的内涵和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分期的标准,较之传统的分期法,显然更能深刻地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因而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不仅如此,这种新的分期标准还体现着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在作者看来,历史上的学术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性质和特点。这就打破了宋明以来道统文化史观所建构的学术史模式,因此,在中国学术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二,它提出关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新解释。
以往的学术史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只述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缺乏对于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原因的探讨。梁氏此书不仅把学术思想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还深入到这一过程的内部探索其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例如,在论述“胚胎时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源泉”时,他不仅将这种“源泉”概括为“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三端”,更进而求“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的“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二曰由于人为者”(同上书,第6页),试图从自然地理环境和中国古代先民的“民族性”去探讨中国学术思想所以产生的原因。又如,在论述“全盛时代”即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他不仅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而且还专门探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即“求其所以致此”的道理。梁启超列举了“七端”,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即由于周室东迁,王权旁落,“诸侯放恣,处士横议”,西周原有之“虚文仪式”已不足以规范人心,而“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思想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二是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如“文字之趋简”、“讲学之风盛”和“人材之见重”等(同上书,第12—15页)。再如,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儒学统一的原因,他列举了“六端”,概言之: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说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三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其思想体系更具有包容性,“所以诸统中绝,而惟此为昌也”,而这一切又是与儒学“以用世为目的”的思想宗旨分不开的(同上书,第40—41页)。至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沉滞”等(同上书,第53—56页)。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309页)的最初尝试,具有以西学因果论反对旧学道统论的近代文化特色。
其三,它首创了中国学术史编纂的新体裁。
如上所述,以往的中国学术史编纂体裁主要有四种——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和学案体。其主要特点是:详“史”略“论”,重“述”轻“作”或“述而不作”。它们往往通过体例编排、材料取舍和记述的详略来表达学术史书作者的思想观点。即使是学案体,它虽集中国传统学术史编纂体裁之大成,使中国传统学术史从内容到形式更臻于完善,但是,仍然没有突破以人为纲、依人立传、详“史”略“论”、重“述”轻“作”的体例格局,仍然缺乏对于学术史发展过程的正面系统的论述,更谈不上对学术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探求。梁氏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既“述”且“作”。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之不同立若干节,如原因、派别、结果等等,以烘托每章之主题。从章节安排中即可以了解到此书的基本结构和框架,思路和观点。这是中国学术史在形式上的创新,它更能展现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
总之,梁启超这部学术史新著,不仅论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而且更深入到历史过程的内部,探求其间的因果关系,既述其当然,更求其所以然,对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作出新的解释。他还创立了学术史的新体裁,以章节体的学术史新形式代替传统学术史的旧形式。凡此种种,足以表明梁氏此书立意新颖、思路清新、形式别开生面,具有创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采西学新说”而建构的中国学术史新体系。它的问世是中国学术史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堪称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史的拓荒之作。可以这样说,梁启超所开创的中国学术史新体系,是本世纪初文化论争深化的产物,也是文化转型的一项积极的成果,它标志着新的文化模式在学术史领域开始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