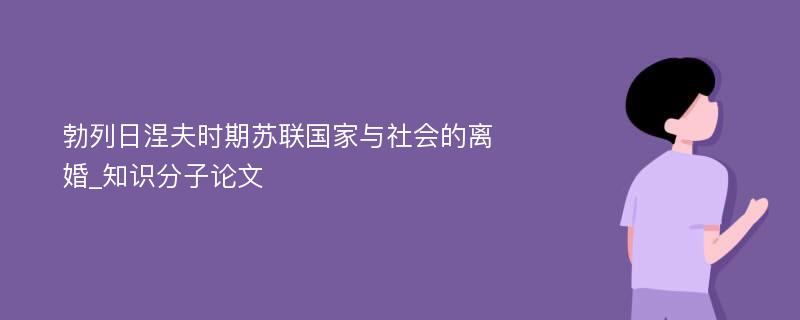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与社会的离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勃列日涅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大林时期,苏联形成了社会高度国家化,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压制了社会活力和创造力,造成了很多严重的消极后果。斯大林去世后,这种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勃列日涅夫掌权长达18年之久,表面看来,这时期苏联国家和社会极为平静,没有什么大的动荡,苏联国家及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权力也从未受到什么大的威胁。实际上,在此期间,苏联政治社会却发生了十分巨大的潜在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离异上。这里所谓的“离”是指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指社会脱离国家的控制而独立承担一部分职能,体现着社会与国家职能上的分工;“异”是指社会与国家间在目标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体现着双方的矛盾。
苏联国家与社会的离异有其独特的背景。首先是历史的背景。斯大林时期,社会的国家化是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剧变而实现的,包括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尤其是卫国战争使国家与社会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赫鲁晓夫时期,以一次次的政治、思想、生产运动将群众调动起来,以赶超英美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见前景来持续激发群众的热情并使社会和国家的目标保持一致。因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一致还是主要的方面。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群众对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各种运动已经厌烦,而在经历了国家一个个允诺目标的落空之后,群众也已不再相信国家新的目标允诺,这时,“人们的心理状态的特点是,他们对喋喋不休的许诺说经济繁荣近在眼前——已听得不耐烦了,对于响亮的空话已经根本不相信了。”①这时,群众的政治热情低落,对国家目标丧失了兴趣,社会和国家间一致性的纽带越来越松。
六、七十年代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和全球化的浪潮也对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是发生第三次科技革命最早的国家之一,它在原子能、航空航天、合成材料等领域都有重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由于社会的国家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对国家的依赖,它的科技革命也是在国家的领导下发生的,没有国家的指令科技革命不能对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不存在将科技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社会机制,因此它的科技革命并没有迅速带来产业革命。在国家的控制下,苏联的科技革命除了对军事和航空航天两大领域的发展有巨大推动外,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则微乎其微。由此,在西方国家因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而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时,苏联却长期处在短缺经济的困扰之下。社会的国家化不仅阻碍了科技革命的进程,而且妨碍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延缓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使得社会出现不满,社会与国家的一致受到威胁。此外,现代科技革命也推动了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现代交通、通讯、出版印刷等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信息的交流日益便捷,主权国家的边界已经不能阻挡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这样,了解了西方发达社会状况的苏联人便有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而对尽量隔绝苏联人与西方的联系并将西方描绘成没落社会的苏联国家也产生了不信任。
再者,无论在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下,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总是有着多种多样的欲望和目标选择,尤其是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人和群体的欲望和目标选择越来越丰富多彩。相对来说,国家的目标是稳定而简单的,从历史上看,苏联国家的长期目标主要集中在建立一个重工业强国上,并保持多民族国家的安宁和稳定。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越是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目标越有可能出现分歧,甚至是背道而驰。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在经历了长期的一致之后,便出现了分歧和背离的状况。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与社会的离异表现在多个方面。我们先从几个阶级(阶层)来进行分析。
苏联的工人农民被集中于企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当中。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工农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他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却大大降低,对生活的热情也日益衰退。1919年出现了被列宁讴歌为“伟大的创举”的星期六义务劳动,1935年出现了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那时,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也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义务劳动就从未间断过。但进入70年代,广大群众参加劳动竞赛和义务劳动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各单位组织的劳动竞赛和义务劳动成了一种半强制的活动。由于劳动报酬与劳动质量和数量的脱节,工农不真正关心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造成生产消耗大而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浪费十分严重,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想买一台在保修期内不出现一次故障的电视机,是根本没有希望的②;同时,工人农民的旷工、误工和消极怠工、甚至罢工的现象也十分严重,1972年全苏因工人怠工而造成的工时损失竟占到总工时的20%,比美国工人公开罢工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③到70年代中后期,“工业工人对劳动报酬的不满在增长,这种不满的后果是酿成了对那个时期的苏联来说异乎寻常的事件——罢工。”④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立陶宛、乌克兰等许多地区发生了罢工事件。此外,企业要求工人在休息日加班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也引起工人的反抗。如在克麦罗沃州的矿井,1980年中的7个月有30个星期日,平均有26-28个星期日被占用,工人们起来反抗,1979年发生了300次拒绝上班事件,1980年的7、8月份就有22次共2206人拒绝上班⑤。日用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住房紧张,除了等待国家的解决外工人不存在自己解决问题的任何可能,只能生活在焦虑的等待之中。农民生活的最大改善是取得了与工人同样的劳动和生活保障权力,尤其是他们的退休生活也有了国家的福利保障。但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组织领导下,农民年复一年地劳动并不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倒是他们自己的宅旁园地和自己喂养的家禽家畜总能为他们带来额外的收获,在平淡的生活中增添一些亮点。所以,农民总是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宅旁园地上,对集体劳动则是消极应付,敷衍了事。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酒精消耗量的大增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苦闷情绪。没有生活热情的工人农民们将大量的自由时间消耗在小酒馆中,借酒浇愁,插科打诨。在亲朋好友之间,则吐露真情,相互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工人农民的这种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反映了他们对国家的不满和失望,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的迷茫,他们并不知道,在失去了国家的保护之后,应该怎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工人农民与国家间完全的一致性已经消失,呈现的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这个特殊时期,只能是采取措施恢复工农对国家的信心,但这种措施必须摒弃以往国家对工农的单方面的强制性特征,而是通过国家与工农的双向变化,以引导的方法使双方的目标重新趋于一致:一方面,国家需调整自己的目标选择,切实关心工农的切身利益,把提高工农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工农需向社会化方向发展,消除对国家的单纯依赖性,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建立自我发展的机制。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目标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艰苦的改革过程,这是因为,国家目标的调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克服这些制约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工人和农民由于长期形成的对国家的过分依赖使其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机制,这种机制的重新培养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做这样的改革努力,使得苏联丧失了最好的改革时机,形成了“停滞社会”,这倒是验证了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国家的权力越增加,它对公民的幸福就越不关心。”⑥勃列日涅夫时期不进行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与苏联国家权力的长期膨胀有直接关系。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环境已大不如前,而改革者又没有考虑到制约国家目标转变的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不切实际地幻想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结果导致国家权威的丧失,而工农在失去了国家的保护后并没有形成自我发展的机制,自然就出现了工农社会的危机。
知识分子是苏联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阶层。在经过了长期的国家建设和教育发展后,勃列日涅夫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加,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与苏联国家直接联系在一起。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苏联知识分子的一切是由国家安排的,是被国家化了的知识分子;更为突出的是,就连苏联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也是苏联国家作用的直接结果,即是苏联国家的基础教育投入和长期的思想培养造就了苏联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投入最多的社会阶层之一。发达的思维是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征,但对苏联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思想也都是由官方确定的,他们具有千篇一律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和思想特征。信奉国家统一的理论学说、诠释国家领导人的话语是苏联知识分子必须的义务。
但是,从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完全统一,但惟有思想不可能完全统一;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剥夺,但惟有思想的自由不可能被剥夺。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也反映了这一人类历史的铁的规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前,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就并非铁板一块,与国家不和谐的声音并不少见,但这些大多被苏联历史的和声淹没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的离异却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夜间人现象”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所谓“夜间人现象”是指在苏联形成的一种背离官方社会的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现象,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朋友之间、友好的同事之间,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通常是在夜间)集聚在一起,发表与官方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在官方生活和非官方生活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反差。如果说官方的世界是傲慢的、千篇一律的和口是心非的话,那么非官方的世界则是生动的、真诚的。”⑦“官方的世界”和“非官方的世界”之间的反差实际就是国家与知识分子社会的反差,“两个世界”的形成也充分表明了国家与知识分子社会之间的离异。
如果说“夜间人现象”表明了苏联国家与知识分子社会之间的离异的话,那么“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就已经发展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了。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这样定义“持不同政见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依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⑧麦德维杰夫的这一概念特别适合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持不同政见者”,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则并非任何社会都有。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在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试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背景下出现的,此后一直贯穿勃列日涅夫时期始终并出现了几次高潮。“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有多种类型,其政治主张也多种多样,围绕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扩大和发扬民主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最主要主张,进入70年代后,“持不同政见者”逐渐走上了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道路。苏联领导人只看到了“持不同政见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们主张中积极合理的一面,所以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一味镇压措施,从而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久拖不绝,造成双方的长期对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典型反映了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危机的重要表现,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没有从持不同政见运动中看到自身蕴藏的危机,因此也没有做出任何适应社会的自身调整,从而使国家日益失去社会的信任,濒临危机,乃至以后的解体,而“持不同政见者为以后苏联社会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⑨。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有巨大影响的是民族精英集团的形成。这里所指民族精英集团主要是那些有较高知识水平、在民族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民族知识分子和加盟共和国民族干部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中,他们往往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为本民族谋取尽量多的利益。苏联民族精英集团首先是在现代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下形成的。民族主义是20世纪重要的世界思潮之一,六、七十年代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新一轮浪潮。世界民族主义浪潮不可避免地对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产生影响,促进不同民族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促进民族精英集团的形成。经过长期的建设,苏联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此基础上,民族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各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意识也在不断加强。苏联国家的某些民族政策也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民族精英这一特殊社会集团的形成。
民族精英集团并非天然就是多民族国家分离力量,如果国家的民族关系处理得好、真正做到各民族平等,完全可以使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繁荣,民族精英集团则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建设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社会力量。但令人遗憾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却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它的民族政策给多民族国家带来了隐患,并促成了民族精英集团与国家的逐步分离,成了潜在的多民族国家的离异力量。民族精英与苏联国家的离异主要表现在由他们所代表的地方民族主义的膨胀。在此我们先来考察致使地方民族主义膨胀的原因。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的民族政策中有许多因素大大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的膨胀:首先是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包括颂扬沙俄帝国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美化俄罗斯人的领导、强制推广俄语、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于其他共和国之上等等,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遭到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其次是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高度集权制,民族加盟共和国实际权力很小,使得各民族不满;再次是对各共和国经济的拉平政策,既使得落后民族产生依赖心理并认为国家对它们的支持不够,又使得较发达民族共和国心存怨气,责备中央政府有意降低它们的生活水平;最后是对一些遗留的民族问题未能妥善处理和继续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不仅不能缓和和解决民族矛盾反而使一些民族矛盾激化。以上这些是导致地方民族主义膨胀的主要原因,而民族精英则做了地方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民族知识分子主要在语言、文化方面宣扬民族观点,民族干部则主要在行动中争取更多的民族利益,两者相辅相成,得到地方民族群众的支持。此外,作为最大民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膨胀也不可忽视。尽管俄罗斯处在统治地位,但俄罗斯的民族精英们并不满意,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在苏联国家中吃了亏,给了其他民族过多的援助,苏联境内的落后民族拖了他们的后腿,等等。所以俄罗斯的民族精英们也对现状不满,表现出与统一的苏维埃国家的离异。
应该看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精英集团虽然是民族利益的代表,但他们在多民族国家利益和民族共和国国家利益之间并没有明显地偏向于后者。他们兼民族知识分子、民族干部和苏联知识分子、苏联国家干部于一身,并且首先是作为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国家干部的身份而出现的,大多数的民族精英是以多民族国家的利益的维护者的身份而出现的。但是,由于以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族精英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民族利益一边,一些民族精英还公开地站出来,批评苏联国家的民族政策,维护自身民族的利益,如人所共知的乌克兰作家久巴所写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民族干部中最典型的就是身居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谢列斯特出版了《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所有这些都是地方民族主义膨胀的典型体现,也表明了民族社会与多民族国家离异的趋势。
民族精英集团的形成和它所表现出来的加盟共和国与多民族国家离异的趋势,给苏联国家提出了极为严峻和紧迫的任务,需要及时调整民族政策,正视民族主义高涨的现实,将它们引导到加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上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总的来说政局稳定、国家实力增强,这时它完全有能力调整民族政策,巩固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但遗憾的是,这时的苏联国家领导人盲目地陶醉于“苏联人民”的理论,声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没有正视国家仍然存在的民族问题,并对公开出现的民族精英分子一味地打击,其结果是使得民族精英分子离国家越来越远,在一定的环境下,他们就会最终抛弃苏联国家而去。苏联国家的最终解体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特权阶层的形成给苏联国家造成了最明显的伤害,也是国家与社会离异的重要表现。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特权阶层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这是因为:首先,勃列日涅夫时期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在他执政期间,从不轻易地撤换一个干部,更没有进行过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的政治机构改革,再加上领导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越来越老化的干部队伍。这一稳定的干部队伍就是特权阶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队伍在稳定的同时还在不断扩大。在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改变,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需要设立更多的管理机构和增加更多的管理人员;同时,为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政府也不断地增加机构和人员;再者,在搞关系、“走后门”成风的社会中许多人想方设法地钻入权力机关;最关键的是勃列日涅夫思想保守僵化,对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多的现象视而不见,从未对此进行过相关改革。所有这些使得苏联的机构臃肿,官员队伍迅速扩大,“上级任命的干部不断扩充官僚机构”:全苏和联盟共和国的部长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160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总数达1800万人⑩。干部是特权阶层的主要来源,不断扩大的干部队伍使享有特权的人不断增加,特权者也逐渐由少数人扩大为一个社会阶层。
勃列日涅夫个人追求奢侈和享乐,所以他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极少阻止甚至有时放任和鼓励,这使得享受特权的人和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就越来越多,大大助长了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上行下效,“其他干部效仿勃列日涅夫利用各种可以行得通的手段建立私人财产”(11)。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分层始于高层权力人物的个人所有权、个人特权及财富的建立”(12)。于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特权阶层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建立起来。
勃列日涅夫时期,享有特权的人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阶层。但是这个阶层不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主要是来源于官员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人。“一个人为的、不加掩饰的圈子是存在的。它包括各种类别的负责人。生产方面的、党的、苏维埃政权方面的,国家机关的,各种团体的负责人都应该算进这个独一无二的圈子中。”(13)
应该说,当社会被国家化的时候,那些行使管理职能的国家干部就已是实际的特权者,他们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凸显出来并形成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给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讲,就是国家管理者阶层对国家利益的背离,这种背离对国家造成的伤害极其巨大。
从特权阶层自身来讲,他们已将国家利益放到了个人利益之后,当国家利益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并且在行动中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而首先满足个人利益。就拿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来说,在70年代抓住机会进行改革是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他们却为了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而拒绝了改革,从而使苏联国家丧失了最好的改革时机;再拿苏联存在的军事—工业集团来说,为了维护集团利益,他们左右国家长期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结果阻挠了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使国家在军备竞赛中被彻底拖垮。
对整个社会来讲,因为特权阶层以国家管理者的身份出现,所以其他社会阶层自然地将他们等同于国家,他们的腐败就被视为国家的腐败,他们的自私自利就被视为国家从不顾及全社会的利益。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其他社会阶层对国家的不满,使国家与社会间的离异程度大大加深。
从以上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分析来看,该时期苏联国家与社会的离异己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处在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苏联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是这种探索中出现的新模式之一。苏联自斯大林以后既使社会高度国家化,又剥夺了社会的所有独立性特征。而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社会所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事实证明社会创造力的发挥有赖于社会独立性的增强。所以,苏联的问题不在于社会的国家化模式上,而在于这一模式的长期不变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现代化水平至少也在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时要想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必须大力发挥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因此,改革长期以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将国家与社会剥离开来,让它们各得其所、各尽其能,这样就可以使社会与国家之间“离”而不“异”,并使两者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应是苏联改革的方向。但是,苏联领导人保守僵化,死死抱住旧模式不放,并对来自各方的对旧模式的改革和冲击进行压制和打击。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是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的尝试,是试图激发社会的积极主动性,而勃列日涅夫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公然给改革泼冷水说:“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谁又懂得这个?需要更好地工作,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14)当社会上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时,苏联领导人从未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主张进行过认真研究分析,对他们所有的上书都置之不理,而将他们一概视为反苏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以镇压。苏联领导人这种一味保守旧模式的做法只能加大社会与国家间的裂痕,延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国家的最终解体,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保守僵化难辞其咎。
注释:
①[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陈恕林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8页。
②[苏]阿甘别吉扬著:《苏联改革内幕》,常玉田等译,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③唐士其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④[俄]皮霍亚:《1945-1991年苏联政权史》(Пихоя P.Г.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Историявласти 1945-1991.)莫斯科1998年版,第371页。
⑤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5页。
⑥(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8页。
⑦(俄)К·Г·巴尔巴科娃,B·A·曼苏洛夫,《知识分子与政权》(К.Г.Ъарбакова,B.A.Maнсуров.Интеллигенц ия и власть)莫斯科1991年版,第165页。
⑧(苏)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⑨唐士其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⑩A·H·萨哈罗夫等主编:《20世纪俄国史》(A.H.Cax ар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 X век)莫斯科ACT出版社1996年版,第581页。
(11)C·阿卡波夫、H·图列耶夫:《1953-1996年俄国史》(C.Aкопoв、H.Tуре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53-1996),莫斯科1997年版,第226页。
(12)C·阿卡波夫、H·图列耶夫:《1953-1996年俄国史》(C.Aкопов、H.Tуре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53-1996),莫斯科1997年版,第224页。
(13)(法)亚历山大·阿德勒等:《苏联和我们》,王林尽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
(14)(俄)Ф·布尔拉茨基著:《言说的自由》(Ф.Ъурдацг ий,Глоток свободны.),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