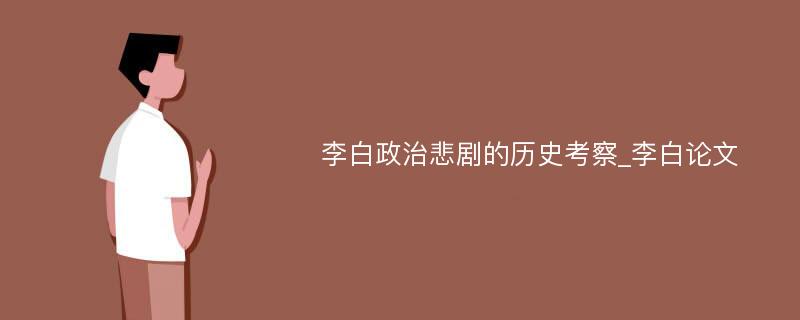
李白政治悲剧的历史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悲剧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2000)05-0074-07
李白的诗歌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似银河泻地,气烁古今。即使是抒发个人怀才不遇、命途多舛之作,也往往是悲歌慷慨,狂放豪雄。如《将进酒》: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以一代“诗仙”名动天下,饮誉后世,但这并非诗人初衷所及。李白的毕生宏愿乃是自布衣直取卿相,“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云游四海。故李白在诗文中常以范蠡、张良自许,一再表白自己具有为王者师的政治才能,只是苦无机缘施展。
李白的政治抱负可谓远大,治国信心可谓充沛,但遗憾的是诗人有济世之愿,却并无济世之才。“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①李白许多歧路徘徊、苦闷与希冀交织的诗歌,则正是诗人毕生仕途失意,政治受挫,但却缺乏明智的自我反省与清醒的客观认识的痛苦宣泄和狂傲不平之鸣。
李白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体,道家、纵横家学说为用,另杂糅名、墨、法、兵诸家思想。其思想体系之博杂,古今罕匹。然渗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无疑是儒家“亚圣”孟子的修、齐、治、平思想及其调和儒、道二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说。故与先秦至盛唐众多知识分子先入世、后出世的人生选择如出一辙,李白终其一生,均对博取高官、建功立业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
李白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盛唐时期国势的空前强盛和政治的相对开明,使广大知识分子处于积极用世的进取心态之中。同时,从武后朝开始的科举与征辟并举的选仕方法,又向士林敝开了希望之门。李白生逢其时,岂甘寂寞,他从青年时代始,就开始了对功名的热衷追逐。只是因其文才盖世与傲骨天成,李白不屑于循行常规的应举之路,他选择了先借隐居获取声誉,然后通过王公巨卿举荐引起帝王重视乃至重用的所谓“终南捷径”。
李白天资聪明,且幼承家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从小即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开元七年,李白19岁,他暂时中断读书生活,师从善谈纵横之术的赵蕤,漫游蜀中。次年,李白自恃才高,于路中投刺新到任的益州长史苏颋。苏颋观书后赞叹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与相如比肩也。”②李白有感斯言,退而博览群书,潜修学业。直到开元十三年25岁时,始辞亲远游,乘舟出蜀,寻求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出蜀后“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开始了漫游全国各地的侠隐生活。开元十四年,李白与故相许圉师之孙女成亲后,“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开元二十三年,李白出蜀整整十年后北游太原,识郭子仪于行伍间,“脱其刑责”。③次年从太原返安陆后,第一次取道南阳进入长安,向唐玄宗献《长杨赋》,未获赏识和召见,但此行结识了玉真公主、崔宗之等要人。④其后李白东之齐鲁,寓家任城,与孔巢父等人会徂徕山,酣饮纵酒,号“竹溪六逸”。天宝元年42岁时,蒙玉真公主、道士吴筠等友人的鼎力举荐,李白始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并被册封为翰林供奉(闲职)。但待诏翰林院不到三年,李白因醉酒狂放,招致宫内诋毁,玄宗疏远,被迫自请出宫,开始第二次长期漫游。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隐居庐山。次年冬,永王李粼以平乱为号召,在江陵起兵,聘李白参加幕府,李白接受了邀请。但殊料肃宗李亨认为李粼率兵东下是同他争夺帝位,下诏讨伐,李粼兵败被杀,李白以“从逆罪”身系浔阳狱中,虽经郭子仪力救免死,仍被流放夜郎,后在巫山途中遇赦。此后,他辗转于金陵、宣城等地。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听到李光弼率军讨伐安史余孽时,不顾衰老,请求从军杀敌报国,后因中途罹病,未能如愿。宝应元年,李白病逝于当涂,年六十二岁。
纵观李白一生,自25岁出蜀,至62岁病逝,漫漫37年,他始终在寻找施展才能、匡时济世的机会。但除了天宝元年至天宝三年获取翰林供奉这一闲职外,李白在仕途上可说是备受挫折、困顿终生,在政治上一无所成。
李白早在青年时代,就曾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过精心策划。他30岁前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毕生心愿: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虬蟠龟息,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喟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飡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愿望而奋斗,但结果既未能自布衣直取卿相、兼济天下,也未能从宦途从容隐退、独善一身,而是栖栖惶惶,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飡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⑤。李白一辈子也没有弄明白,自己的政治宏愿何以不能实现?他为此深感痛苦和悲哀,并在诗文中进行过苦苦探讨。在42岁待诏翰林前,李白将自己的入仕无门溯因于“豺狼当道”,贤能遇阻;在45岁唐玄宗赐金遣返后,他则将自己的政治失意归罪于佞臣诋毁,“浮云蔽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⑥历代文人因叹服李白的旷世诗才,也爱屋及乌,习惯于从纯客观的角度解释李白的坎坷遭遇。如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其怀念李白的诗歌中便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⑦“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⑧“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⑨等语。李白“怀才不遇”,似已成为中国文人的千年遗憾。然而,撇开对李白诗歌成就的崇敬与热爱之情,冷静地审视历史事实,李白之所以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除了政治黑暗和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白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
在中国古代,大凡自布衣直取卿相,且在政坛上颇有建树者,在其从政之前,均十分关注社会和人生,对国运时局了如指掌,具有高人一筹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如管仲施政、商鞅变法、范蠡灭吴、张良兴汉、诸葛亮治蜀等等,无一不是未雨绸缪,成竹在胸。李白尽管经常以历史上的这些名臣贤相自励,并深信自己具有王佐之才,倘能风云际会,必然大有作为,但实际上却对政治幼稚无知。如李白现存诗文千余篇,虽说是“历经丧乱,十不存一”,但从所存诗文来看,除了“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⑩之类的高谈阔论,以及“为君谈笑静胡沙”、“调笑可以安储皇”之类的牛皮大话之外,实在看不出李白有何成熟的政治见解及主张可言。李白居楚时曾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荐其德行才能,文中共举四、五事:其一是“曩昔东游淮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其二是“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禅服恸哭,若丧天伦……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与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其三是“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余,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四是昔于蜀中投刺益州长史苏颋,苏颋赞其“若广之以学,可与相如比肩也”;其五是昔曾谒见安州郡督马公,马公赞其“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由此观之,李白自诩的德行才能无非是行侠仗义、高蹈绝俗、文采动人,而与“济苍生,安社稷”的经世之才则南辕北辙,相去甚远。另唐代是继秦、汉、晋、隋之后又一统一强盛的封建王朝,春秋战国时期那种诸侯割据、合纵连横的政治环境早已不复存在。但李白的求仕方式却仍然停留在苏秦、张仪式的纵横家时代,梦想通过“遍干诸侯”、“游说万乘”直取卿相,较之其同时代的张九龄、高适等封侯拜相的务实文人,其不谙世事可见一斑。又天宝初年为唐代繁荣昌盛的顶峰时期,然各种矛盾的积聚又使它成为唐王朝由盛入衰的转折时期。李白待诏翰林期间,唐王朝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繁重,权臣弄政,藩镇跋扈。但是时的李白对此茫然无知,从现存诗文来看,他除了写过诸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类的几首无聊的宫体诗外,并未上文陈述过有益苍生社稷的任何政治建议。碑铭所载李白“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辍”,[11]想来也不过是如后世所传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之类驰才逞辩、华而不实的文字。特别是安禄山久藏野心,且经常出入内宫,邀宠于杨贵妃,李白身为翰林供奉,倘略有政治敏感,对此应有所觉察,但遗憾的是,李白只有事后的追忆,却并无事前的警悟。与此相反,当时的权相李林甫倒是已有预言在先。至于李白的晚遭“李粼之变”,则更是说明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稚嫩和盲目性。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李白的大言不切于实和虚名不适于用。因此,当天宝三年李白迫于无奈自请出宫时,唐玄宗亦认为他“非廊庙之器”,予以赐金遣返。
人生如白驹过隙。中国历代成功的政治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善于捕捉其从政生涯中的每一个发展机遇,及时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构筑自己的千秋伟业。如孔子、孟子的周游列国,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范蠡扶越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张良兴汉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诸葛亮治蜀的“七擒孟获”、“六出祁山”,无一不是夙兴夜寐、孜孜以求。李白尽管满脑子都是风云际会、青史留名的故事和奇思异想,但却从来不善于把握自己的人生机遇。开元一十三年,李白25岁出蜀,其时风华正茂,按照他出蜀时“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12]之志,本应直取长安,博取功名,乘年轻有为好好干上一番事业,藉以“荣亲报国”。但讵料他在安陆与许氏成亲后,则誓言全忘,因留恋小家庭生活,而“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而这整整十年,恰恰是唐玄宗执政期间政治较为开明的时期,与李白年龄相当的张九龄、贺知章、崔宗之、高适等文人,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步入盛唐政治舞台的。开元二十四年,李白大梦初醒,终于首次进入长安谋职,此行虽未得到唐玄宗重视和接见,但已结识玉真公主、崔宗之等要人,倘能从容周旋,仍不乏入仕机会。但李白竟因此心灰意冷,一筹莫展,为寻求解闷而沉沦于斗鸡赌博之中,并曾受到斗鸡之徒的群起围攻,亏得安陆县宰的解救方得脱围逃出。[13]如此游戏人生,又何成大器!天宝十四年,李白出宫11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志士莫不请缨,如当年曾获李白营救的郭子仪即已闻风而动,领兵平叛。李平生自诩汉飞将军李广之后,秉先祖遗风,“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14]如所言属真,时当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岂非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况且李白正值壮年,完全可以投奔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但遗憾的是,李白放弃了人生最后一次机遇,而是在“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15]的感叹声中,远离战场,隐居庐山去了。在人生的几次大好机遇中,李白均未能把握,以致坐失良机,徒成悔恨。
在中国封建时代,由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制约,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故行方智圆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成功的重要素质。历代著名的政治家诸如管仲、晏婴、范蠡、张良、诸葛亮等人,都能恪守封建礼教,善于适应政治环境,巧于应付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乃至不惜取退为进、以屈求伸,最终获取成功。李白生于西域,长于蜀中,在胡风边月和巴山蜀水的熏陶下,虽天纵诗才,但对封建礼教和从政谋略却懵然无知,而是一任自己的傲骨与天真,高自期许,狂傲不羁,致使自己一生均处于物议与毁谤之中。早在李白隐居安陆时,他的狂言僻行即招致了人们的非议。其《鞠歌行》云:“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诋毁。”其《上李邕》诗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其处境之不妙,可见一斑。对此,李白本应反躬自省,砥砺名节,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但李白显然缺乏自知之明,反而在自我陶醉中变本加厉,将自己的桀傲不群推向极至。天宝元年,承玉真公主、道士吴筠等友人举荐,唐玄宗诏征李白进京。李白大喜过望,赋诗相庆:“……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16]其得意忘形与狂态毕现,真是匪夷所思。李白入京后虽平步青云,待诏翰林,但其言行仍未加丝毫检点,依然以自我为中心,恣意妄行。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自由散漫与蔑视王法,令人为之捏一把冷汗。又据《新唐书·文艺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泼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启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蝘、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若此记载属真,则李白的仕途失意非但咎由自取,乃至他能在冷酷腐朽的阉党政治和威重于天的赫赫皇权前保作生命,已属不幸中之万幸,更遑论什么“愿为辅弼”,辅佐帝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17]了。李白毕生仅有的一次从政机遇也就此葬送,且了无回旋余地。
中国历代成功的政治人物的又一特点,是具有恒定的奋斗目标和稳重的品性情操。贫贱不夺其志,富贵不迷其途,喜怒不形于色,雷霆不动其形。观乎诸葛亮治蜀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等精诚坚忍;观乎谢安拒秦的弈棋对敌,东山报捷,又何其镇定从容。李白尽管也十分景仰诸葛亮、谢安等古代名相的政绩,但其志行的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息多变,则显然有悖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
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仕宦文化既互相对应,又互相依存、互为转化的一种文化体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已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千百年来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仕宦文化溯源于儒家学说,隐逸文化则滥觞于道家思想,两者均具有深厚的思想土壤。故仕隐之间的两难选择,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国历代杰出的政治家们虽然也逃脱不了仕隐之间的矛盾选择,他们或由隐入仕,奋斗终生,如管仲、诸葛亮等;或由仕入隐,功成身退,如范蠡、张良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旦步入仕途,均能潜心静虑,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李白则不然,他虽然深信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18]俨然是经邦济世之才,但终其一生,均未在仕途上作过认真的努力,而是时反时覆,任凭自己的心境波动,游戏于仕隐之间。李白开元十三年出蜀后,初隐于安陆,再隐于任城。天宝元年,李白奉诏进京,册封翰林供奉,本为其人生的一大转机。但李白亦未加珍惜,依然率性而行。“衣宫锦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19]“沉湎于至尊之前,啸傲御座之侧,目中不知有开元天子,何况太真妃高力士哉!”[20]当他的任诞行为招至朝臣非议、天子疏远时,李白不思己过,而是意气消沉,在“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言”、[21]“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22]的满腹牢骚中,轻易辞职离京,再度落魄江湖。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时年55岁,若能乘时而起,杀敌报国,尚不失封侯拜将机会。但此时的李白又一反初衷,避隐庐山。诗人晚年遭李粼之变后,虽一度复萌追随李光弼杀敌建功的爱国壮志,无奈已是风烛残年,力不从心。
至于李白的情绪多变,同样令人惊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23]的雄心壮志,也有“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24]的颓唐潦倒;既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5]的进取精神,也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26]的消沉意态;既有《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与韩荆州书》的张扬自我,不卑不亢,也有《上安州李长史书》的曲意逢迎,自责自怜;既有“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27]“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28]的爱国赤诚和民本良愿,也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29]“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30]的泄愤恶念……察李白生平行事,常令人有“此一李白,彼一李白”之感。李白在人生道路上一旦遭受挫抑,往往习惯于借酒浇愁,狎妓解闷,赌博忘忧,狂言泄愤,以极度狂放潦倒的方式毁损自己的生命意志,葬送自己的政治前程。李白自叙诗:“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31]“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32]“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33]……即为其人生行状的自我写照。在礼教思想已深入人心的盛唐社会,李白的这种畸行又何能见容于当世,见用于朝廷?!杜甫系李白至交,他一方面惺惺相惜,理解和怜悯李白的怀才不遇:“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34]另一方面,也对李白的自暴自弃深感不满:“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35]李白的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早已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运。
李白终其一生,均沉醉在拜相封侯、匡时济世的美梦之中,直到晚年在江南酒楼与大书法家张旭相遇时,仍以“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36]互勉。但在盛唐政治黑暗和仕途坎坷的客观环境中,李白由于政治素质和政治才能的匮乏,他的夙愿不仅始终未能实现,反而弄得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屡遭失败,几乎丢了性命。李白成了中国古代文坛上的一个典型的政治悲剧人物。
李白的政治悲剧不仅属于个人,同时也是盛唐时期一代文人的性格弱点及其政治悲剧命运的集中反映。开元、天宝年间国势的空前强盛,使当时的文人莫不深受鼓舞而雄心勃发,一个个大有孟子早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和抱负,但初唐以来长达一百余年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裕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从未经受过任何磨炼,反而在人格品性上染上了许多的轻狂、浮躁和纨绔之气:心比天高,命如纸薄;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大事干不成,小事又不干……当他们带有这些性格弱点自命不凡、一派天真地步入荆棘丛生、危机四伏的仕途时,其结果往往是四处碰壁,铩羽而归。据《明皇杂录》称:“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使然也。”虽不尽然,但却不无见地。
历史的辩证法原则往往出人意料。李白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失败,反过来又促使诗人“不平则鸣”,在文学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37]李白是一位集盛唐知识分子优秀品质与不良习性于一身的典型文人,当他涉足冷酷而又陌生的仕途时,诗人的性格弱点全盘暴露,惨无立足之地;但当他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转移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时,诗人的爱国赤诚、善良人性、潇洒风神、天赋才情和主体精神则如大江奔海、熔岩乍喷般挥洒自如,并幻化成无数叩人心扉的千古绝唱。晚唐皮日休评李白诗云:“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38]北宋徐积《李太白杂言》云:“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变万化、雷轰电掣、花葩玉洁、清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诗!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贾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缧绁,当须荦荦不可羁;乃知公是真英物,万叠秋山耸清骨!”李白未能成为盛唐政坛上的范蠡、张良,但却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史上雄视千古的泰山、北斗。李白的人生价值,终于以他始料未及的方式得到充分体现,这是李白个人的不幸,然而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之大幸!
收稿日期:2000-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