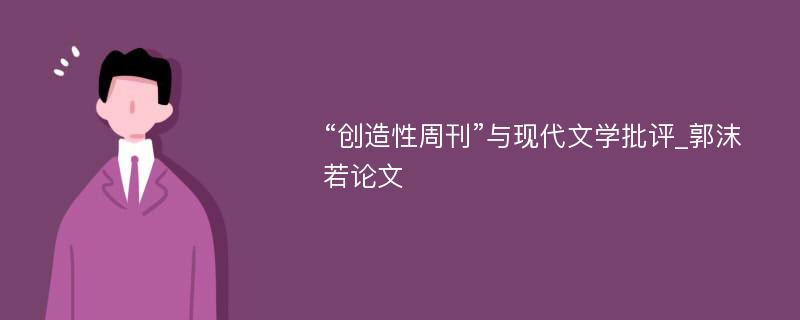
《创造周报》与现代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周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6-0115-07
1923年5月1日的《创造》季刊上,登出了一则《预告<创造周报>》启事。在这则言语 平淡、公文气十足的启事中,创造社同人说明了《创造周报》的性质,称她与一年前出 版的《创造》季刊是“姊妹”,“想偏重于评论介绍而以创作副之”[1]。与《创造》 季刊创刊号锋芒毕露的亮相相比,《创造周报》的出现要温和的多。但可能除了创造社 诸同人,任谁也难以看出这则冠冕的启事背后隐藏的郁积以久的义愤和摩拳擦掌的激动 。甚至一年后的成仿吾仍难掩对其时澎湃激情的神往和壮志未酬的失落:“我誓要扫荡 新诗坛上的妖魔,写几篇批评近日的新诗的文字……我们秉着这种精神,一年以来,对 于卑鄙的人们曾张过几次杀伐,然而我们毕竟势孤力弱,托荫在资本家的高墙下的他们 ,依然在肆行无忌,在暗咒而静待我们的疲惫而死。”[2]作为创造社颠覆精神的延伸 ,《创造周报》实际上带有极大的功利性,这可以用郑伯奇的话作很好的注解:“当时 ,创造社胜利地回击了胡适一派的猖狂进攻,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信任,但也招来 了敌对方面的更多的谩骂和攻击。在这样情况下,光凭三个月出版一次的季刊来应战, 的确显得太不及时了……大家主张另出一个机动刊物来应付斗争的需要。”[3]“周报 不过是适宜于战斗的一种轻便的刊物而已。”[4]由此,如郭沫若所说“对于别人的攻 击,只有隐受一途”[5](p.194)的局面柳暗花明。然而,愿望归愿望,对创业的艰难有 着切肤之痛的创造社同人,深知没有经济基础的一切只能是镜花水月。幸好诸同人已非 昔日阿蒙,创造社丛书的热销,《创造》季刊的风靡,俨然已使“创造”二字成了金字 招牌,“泰东方面没有料到会有这样好的销路,反而懊悔季刊出版日期相距过远,于是 便自动降格相求,请郭沫若能代他另编一份周刊,这便是继《创造》季刊而出的《创造 周报》。”[6]万事俱备,东风又至,创造社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战斗阵地”。双重 功利的融洽相拥,催生了把创造社推至时代风口浪尖上的《创造周报》。
既然《创造周报》是用来战斗的,那么第一期就需要一个“开门红”。于是,异乎勇 猛的成仿吾“在周报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诗之防御战’的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 的中国的所谓诗坛,爆击的比今年的闸北怕还要厉害。”[5](p.243)这颗“爆击弹”名 为“防御”,实为主动出击。以蓄积于胸的对新文坛现状的忧虑与激愤为火药,它的进 攻对象是周作人、胡适、冰心、俞平伯等新文坛的大腕和主将,因此,想不轰动恐怕都 不行。这颗“爆击弹”不仅把成仿吾炸成了手持板斧杀伐于文坛的“黑旋风”,而且由 于蕴涵其中的反权威的颠覆意识与创造精神为青年所竞逐,使《创造周报》一时之间洛 阳纸贵。在20年之后郑伯奇仍惊叹于当年的盛况:“《创造周报》一经发刊出来,马上 就轰动了。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 ,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 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情。”[4]于昀也说:“其中特别是《创造周报 》最受欢迎,刊行数由初刊每期三千份增加到后来的六千份,仍不敷销售,还要经常再 版。”[7]二人不约而同地把《创造周报》时代看作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期。
正如鲁迅所言:“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8]《创造周报》的一 纸风行使创造社风华冠绝,尽显荣光。然而,令每一位创造社同人始料未及的是,《创 造周报》同时也将他们带入了一个万分尴尬的境地,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他们跌 入了甜蜜与悲愁的无底深渊。一方面是四面出击后得胜的快感,是新文坛话语权的确立 和霸主地位的巩固;另一方面却是四面树敌,遍地楚歌,应对不暇。郭沫若在十年后反 思道:“一鼓的作气的确是很勇猛,使敌人对于我们也隐隐的生了一种畏惧。”“因为 有了那场‘防御战’,在敌人的阵营里并没有损得分毫,把自己却弄得一个焦头烂额… …”[5](p.244)成仿吾也不无气愤地哀叹道:“这三年的中间,我的反抗有时虽然也成 了功,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弄得几乎无处可以立足,不仅多年的朋友渐渐把我看得不值 一钱……我也不仅遭了许多名人硕学的倾陷,甚至一些无知识的群盲也群起而骂我是黑 旋风,骂我是匹疯狗。”[9]
在《创造周报》一年52期中,这种对新文坛左冲右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延续,似乎“ 防御战”的余响一下子中断了。自《创造周报》第二号始,便已经没有了《诗之防御战 》主动出击、冷嘲热讽的凌厉之气,仅有《通信四则》、《暗无天日的世界》、《评< 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等少数几篇因打笔墨官司而来的被动回应而已。初衷与践行如 此背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或许创造社同人已经意识到,似这般一味批判 、疲于应战而于新文学毫无建树可能真要落得个“疯狗”的骂名,显赫的声名也将沦为 尘烟。文坛上的许多宵小鼓噪出的许多喧嚣不都在若干年后化为乌有了吗?创造社同人 对文学怀有炽热的爱,由这种爱生发出的对新文学的忧思不由得他们不拿起批判的武器 ,但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构。在批判的基础上搭建自己的理论之厦,真正在新文 学的发展中留下自己的声音,不正是创造社同人美好的愿望之一吗?因此,以应战的功 利目标为旨归的《创造周报》方露锋芒便逐渐脱离了原定的轨道,转而立论多于驳论, 建设多于批判,尤其是其对文学批评的自觉的建构意识,使《创造周报》为新文学批评 乃至现代文学批评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理论资源。
1
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的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余韵犹存。旧的价值体系与文 学范式惨遭重创,新的规范尚未确立。失范的文学理应呈现出一派众生喧哗、异彩纷呈 的局面。然而,在《创造周报》的批评家眼中,情况绝非如此甚至更加糟糕:“……到 了四五年以后的今日,早已暮气沉沉,日趋衰运。一种萎靡不振的空气重重地压被在方兴未久的新文坛上。要从此继续下去,新文学只有堕落之一途。”[10]《创造周报》的批评家表现出对新文学前景的焦虑,他们在私下认定新文学这种“暮气沉沉”的态势是由少数人“垄断文坛”所致。正是这些新文学的所谓领军人物为刚破除的旧规范文学又创立了新的规范,设置了新的限制。“我们的新文学正在建设时代,我们要秉我们的天禀,自由不羁地创造些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不可为一切固定的形式所拘束了。”[11]创造社同人对任何压制与束缚均深恶痛绝,他们怀抱利器,甫一出道便把枪口对向新文学对准俨然已成为文坛中心的文学研究会,开始了漫长的“打架”之旅。已多有论者对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争端作了详尽的整理与分析,认为争端乍起不是艺术观的根本分歧,而是创造社为自己争夺文坛话语权的一种斗争策略。此论似对创造社有失公 允。创造社主动挑起争端固然处于谋求话语权的努力,但他们并非无理取闹、无事生非 ,而是深怀对新文学前景的忧思,针对文学研究会一统天下对新文学无形中形成拘限的 事实生发的。仅就《创造周报》上的文字而言,无不显露出他们对新文学弊病的真切体 认,对新文学发展前途的深切眷顾。他们的论调在当时可能石破天惊,但如今看来,尽 管语调强烈稍嫌夸大,却颇多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处。单就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多元优 于一元。创造社的出现,打破了文学研究会一统文坛的局面,实现了文学社团的相互制 衡和相互促进,为新文学提供了多种可供发展的范式,促进了新文学的繁荣。
《创造周报》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文学内容的苍白与表现力的薄弱。诚如郭沫若愤 然指出的:“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打上了几个补丁,在污了的粉 壁上虽然涂上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的内容仍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粪土。”[12]郑伯 奇也为新文学敲起了警钟:“总而言之,现在的新文坛,表面上似乎尚热闹可观,其内 容则实是贫弱空虚。”[1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在确立了白话文学的正宗地 位、解决了新文学发展中的语言形式问题的同时,对于新文学的内容却缺少现代性的厘 定与廓清。“历史的事实是,他们只是以新的‘文以载道’取代了旧的‘文以载道’。 尽管所‘载’之‘道’不同了(以新思想、新道德置换了旧思想、旧道德),但文学作为 从属的工具地位却没有变。”[14]许多作家仍注目于语言革新这一形式层次,而没有致 力于由语言革新所引起的内容革新甚而思维革新的现代转换。正因如此,尽管白话的语 言形式已经深入人心,位居正统;但表现内容的功利性导致了文学表现力的衰弱。《创 造周报》批评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似乎我们的这个运动,有点换汤不换药便满 足了的样子,就形式上论,有人说不过加了一些乱用的标点,与由之乎也者变为了的底 吗啊。就内容论,有人说不过加了一些极端抽象的语言如生之花、爱之海之类,其实表 现的能力早愈趋而愈弱了。”[15]“五四”新文学改文言为白话,其意就在于提高文学 的表现力,如今的发展却悖离了“五四”文学的初衷。《创造周报》批评家从丰富新文 学的内容提高其表现力的任务出发,“要打破从来的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 现”[12]。他们反对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取向,把文学的指向拉回人的内心世界:“文 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他的终结。”[11]“文学既是我们内心的活动之一 种,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内心的自然的要求作他的原动力。”[15]以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 及精神世界来充实新文学的内容,以意识领域内的多维活动来增强文学的表现力。他们 把文学的视角对准主体自身,进而强调艺术的美:“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 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15]“艺 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样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 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16]对美的追求自是文学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这种对文学本 已性与本源性的自觉的价值诉求,无疑意味着一次新的文学革命,对新文学的冲击可想 而知。“从1920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开始活动起到‘五卅’为后期,才算是纯粹的新 文学运动的时期,也就是说,‘新文学’从这以后才有他独自的纯文学的发展。”[17] (p.76)《创造周报》批评家凭借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大胆的艺术魄力,还文学给文学本身 ,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传统,一方面又有所超越,实现了新文学一次意义重大 的美学转型。
2
依循对新文学弊病的明察洞见,《创造周报》展开了它对新文学的批评与建设;也正 基于此,《创造周报》批评家深切体会到文学批评于新文学之意义重大:“我诚确的感 觉着,现今国内文艺界实在最须要批评的工作,并且是须要消极的批评工作。”[18]创 造社同人正是持一种无畏的姿态闯荡文坛进行批评的。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在为批评的 同时,能倾注心力于文学批评本身,努力阐明文艺批评的根本原理,对文学批评文体进 行有意识的系统性建构。
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质已为太多的论者所关注,但对于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似少有 人提及。事实上,几乎就在现代文学谋求现代性的同时,现代文学批评也开始了有意识 的现代性追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追求实际上是对一种科学的完备的理论思维 形态的不断趋进。在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进程中,《创造周报》的推动与建设功不可 没。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以评点式、随感式、印象式的评论为主,还没有清醒的文体意识 。文学批评只是作为文学作品的点缀或与其他样态的批评如文化批评混为一体。《创造 周报》批评家首先肯定了批评本身的创造性和独立性。文学批评要摆脱它原有的附庸地 位,必须先确证它是与创作同具创造性的工作。“批评应该在这种创造中意识到自己是 一种具有独创性的顽强的创造力量。”[19](p.164)创造性的定位方可确定批评文体的 独立性。成仿吾的认识颇有见地:“在这创造的工程中,有与创造的工作一样重要而有 重大关系的另一种工作。我们称这另一种工作为批评。”[20]郭沫若也说:“批评与创 作本同是个性觉醒的两种表现,本同是人生创造的两个法门。”[21]正是创造社同人对 批评本质的充分揭示和强调,使批评具有了与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批评方获得了 文体学上的独立性。批评既然与创作地位相同,那批评家自然获得了与作家相提并论的 权利:“批评家由自己所构成的建筑,再来批评作者的表现方法与描写时,批评家是与 作者并肩而立,一同对着这座建筑。”[22]
通过肯定批评本身与批评主体的独立性,《创造周报》批评家成功地将文学批评从各 种关系中剥离出来,赋予其文体价值,并对其进行单独的有意识的审视和思索,得出了 许多有价值的论断。《创造周报》批评家是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来观照的, 他们意识到:“文艺批评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本无一定的系统和方法可言。”[23]清醒 的缺失意识带给他们建设的动力。虽然“现代文学批评从其开始就往往存在着批评的感 想杂感化的特点,缺少理论深厚、方法得当的批评,其弊端导源于批评界对批评的常识 性问题认识的模糊与肤浅”[24](p.126)。然而,《创造周报》上的批评理论,内容丰 厚,涉及面广,无不表现出创造社同人自觉的结构意识。其论述大致涉及批评目的论、 批评主体论、批评过程论等诸方面,解决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
对批评目的的认识显示了《创造周报》批评家抽象的理论思维形态。他们不再把批评 归一于解读和评判文学作品,而是把它看作是谋求普遍原理的具象化努力。“批评的工 作决不止于辨别自己所得的印象,也决不止于由事实中求出个个的法则,我们要进而求 出事实中的统率的普遍原理。”“批评的究竟的意义是在阐明真理。”[20]由此,批评 具有了价值论意义的本质目的,纠正了人们对批评轻视以及批评活动主观化、浅薄化的 不良时风。
面对文坛现状,创造社同人深觉批评之意义非常。然而,“……神圣的批评每不能不 被宵小利用,作成发挥个人私欲的器具”[25],“我们现在的评坛,在别的合理的方向 总无进步,只在这些异端上用工夫,实是很可叹息的一件事”[22]。文坛萧瑟,评坛又 如此不堪,欲要肃清评坛的创造社同人,自然而然地把目光对准了批评主体即批评家。 《创造周报》中许多文字均论及批评主体的应有品质。他们首先要求批评主体必须具有 独立的人格,在进行批评活动时要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思维世界,不为外物所惑:“我 们要注意立在一个不受催眠暗示的地方,换一句话说,就是不可盲从,不可崇拜偶像, 不可服从多数,不可人云亦云。”[25]惟如此,方可得出严正的批评。批评家的道德和 良知尤为《创造周报》批评家所关注。他们把衡量批评真假的标准定为批评主体是否具 备道德和良知。郁达夫说:“道德的本质是天良,天良的运用是良知,纯正的批评便是 良知的表现。”[25]郭沫若也有同样的论调:“我以为批评的真假不能以批评的方法和 趋向上区分,批评的真假应该以批评家的人格为准衡。”[23]成仿吾更是强调:“真的 文艺批评也必有批评家的人格在背后。”[26]批评实践与批评主体就是如此互为表里相 互表现的。于此,批评实践便打上了道德烙印,中国传统文化中强大的道德使命感与归 罪意识可能会令批评主体不得不为真正的批评。《创造周报》批评家此论可谓用心良苦 意味深长。以道德和良知人格为支撑,批评主体在进行批评活动时,还需要做到不为一 己私欲,保持无功利的心态。《创造周报》批评家对破坏批评真实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 批评万分愤恨:“至于单因是自己的朋友,便不惜颠倒是非,破坏批评的信实,自欺欺 人,这是我们所决不能容许。”[26]他们希冀批评家能摒绝门户之见、行帮之争,保持 一颗不偏不袒的心,不受任何私心杂念的干扰。成仿吾认为作为批评家,“我们应当超 越一切偏执的见解”。“……我们的心境当如一碧的澄空,没有丝毫云雾,而又能把一 切的个体包涵。”[22]郭沫若也把“没利害的心境”当作批评家的先决条件,郁达夫更 是“痛恶”那些“若有丝毫不纯的私心存于其间,甚或至于弄卑鄙的手段,来报其睚眦 之仇”[25]的批评家。保持无功利的心态,谋求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才能得出真确的评 判。在《创造周报》批评家眼中,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决非易事,除却以上几点, 还得满足学养上的要求。成仿吾一再强调“批评家要有十分的学识”[27],“我们应当 囊括一切部分的知识”,“要有十分的感触力……要有十分的想象力”[22]。知识是批 评主体的底蕴,早应是批评的应有之义了。
作为批评主体思维结果的外化,批评多在意识域内进行。因此,批评的过程便显得异 常复杂,难以把握。《创造周报》批评家学习了基欧、瓦特裴德等批评家的批评方法, 结合自己的经验,对批评过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批评的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 在感受的基础上进行的科学的逻辑的思维阐发。在成仿吾那里,批评过程被这样叙述: “批评家原来也是一个赏玩者,不过当他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 整个时,他是要批评这些部分的感触有效没有效,具体的整个完美不完美,尚不止此, 批评家还要由全体的意义,反而批评作者之表现的方法的。”[22]在“赏玩”的基础上 ,将“部分的感触”进行理性整合,进而由此来评价作品,他对批评过程的看法是科学 的。郭沫若更将批评的过程分为三个部分:“(1)感受to feel;(2)解拆to disengage ;(3)表明to set forth。”[23]这三个简短的部分其实清晰地表明了批评由感性到理 性的思维理路。
《创造周报》批评家对批评目的的深刻认识,对批评主体的理性期待,对批评过程的 科学解析,构成了一个系统而又近乎科学的批评理论体系,在现代文学批评实现现代性 转换的进程中,这一理论体系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
《创造周报》批评家以自身的批评实践指陈了新文学发展中的弊端,凸显了他们“自 我表现”文学观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他们又以自觉而系统的对批评文体 的科学建构,推动了现代文学批评现代性的进程。然而,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创 造周报》的理论与批评难免存在缺憾。
首先是《创造周报》“战斗”性质的预设。这一预设分明是以创造社诸同人强烈的团 体意识亦即“行帮意识”为前提的。在战斗的假想氛围中,“行帮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一人受到批评,众人都来维护。这就使《创造周报》批评家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相 互错位,或多或少有些言行不一。成仿吾口口声声说“我们要常为自我的批评”[20], 但在《创造周报》中却见不到他“为自我批评”的只言片语,而只有他批评他人、回应 批评为自己辩护的篇章(《诗之防御战》、《评<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另外,他们 强调批评的无功利性,反对任何偏见的介入,更不能存私偏袒。但事实却是他们容不得 有人批评同人中的任何一位,对别人的批评反应敏锐,睚眦必较(郭沫若《暗无天日的 世界》)。这一预设又使《创造周报》批评家很难摆脱批评目的的主观功利性。为了说 明自己批评行为的合理性或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他们不得不夸大新文化运动的不足和新 文坛的弊病,抹杀新文化运动的伟大之处和新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成仿吾把新文化运动 看成“这宗生意”,把它当作“政界的缩写”,他说:“……这种所谓新文化运动不过 几个学政客不成的没事做的闲人硬吹出来出出风头的一种把戏;……想起了运动开始的 当初便只有一部分品学俱坏的不安分读书的学生跟着瞎闹,想博得一点声名,好弄到一 个往外国去游逛一回的机会。”[28]尽管新文化运动存在不少纰漏,但它毕竟是一场开 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的文化运动,将其贬斥得一钱不值,实是缺乏史家风范。
其次,《创造周报》批评家仍难以完全脱离印象化的主观主义泥淖。他们其实是强烈 反对批评实践的印象化、主观化的。成仿吾说:“浅薄的印象主义的批评,也不知是谁 贩了进来,这几年来好像正合了在吃奶的作家们的脾胃。”[26]郭沫若要求批评家“要 泯却科学的态度与印象主义的畛域”,说“他不是漫无目标的探险家,他不是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的陶醉者”[23]。真正的批评本质上是在审美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 科学化的理论思维样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29]。以其实践来印之,《创造周报》的 批评理论就打上了理想化色彩,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履行,仿佛成了空头的理论家。 《诗之防御战》虽然指出了新诗发展中的积弊,但缺乏学理的分析,有很多直观感受式 的评叹。这点当时的旁观者心明眼亮:“内中尤以我们湖南底成仿吾先生,骂人太不留 余地了,批评太不讲理了!”并称《诗之防御战》“失了批评家的风度”[30]。如评俞 平伯《仅有的伴侣》曰:“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11]出于对新诗坛现状的 激愤,发几句牢骚之言自无不可,但作为文学批评却有违连他自己都倡行的批评规范。 《创造周报》批评家这种理念与实践悖离的行为,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战斗”的意气而 有意为之,但更重要的,是现代批评思维的匮乏。如前所述,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归 根结底是中国传统的直觉感受型思维形态向科学化、理论化的思维形态一步步趋近的过 程,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对诸多现代文学批评的先行者而言,他们一方面积 极引进并有意识运用西方批评理论来进行批评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他 们又难以摆脱潜藏于意识深处的传统思维方式之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使他们的批评文本 点缀上了一些生动却肤浅的主观之花。这一心理动因无一例外地存在于现代文学批评发 生之初的批评家们身上,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概莫能外。对《创造周报》批评家而 言,这种主观情绪的自然显现,即使有意规避也在所难免。
《创造周报》批评家就是这样怀抱理想与壮志,依靠天赋与才华,凭借勇气与胆魄, 旗帜鲜明地活跃在文坛上。他们对新文学现状忧思之深和批判的激烈,对现代文学批评 重建的勇气和实绩,都使《创造周报》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收稿日期:2004-09-20
标签:郭沫若论文; 成仿吾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创造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创造社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