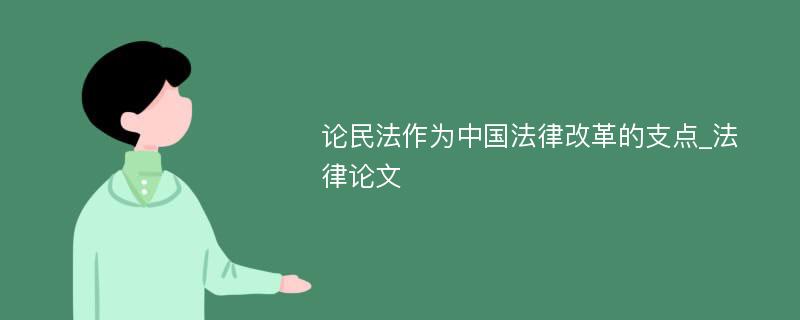
论民法是中国法制改革的支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法论文,支点论文,中国论文,法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法系有漫长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但是,在近代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法系逐步走向崩溃。从清朝末年法律改革到今天,已有百余年历史。从历史的观点进行观察,今天的法制改革实质上是清末法制改革的继续。它表现了一个文明古国力图走向法治化的艰苦努力。
在中国法制改革进程中,究竟什么是核心与关键问题?学者们可能见仁见智。但是,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法制中最弱的部分,恰恰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最弱而又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西方法学所称的“私法”。
中国古代虽有私法因素,但未形成私法传统,其原因甚多;新中国成立后,私法处于几近被取消的状态,其原因也甚多。由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的文明史上缺乏私法传统,因此,构建现代中国合理的私法体系,必然成为中国法制改革的支点。
在中国历史上,私法并不是治世之权威手段,往往强调“治乱世用重典”。所谓“用重典”即用刑法。中国古代最早的刑就是肉刑和死刑,如墨、劓、剕、宫、大劈,后来才逐步演化为“笞、杖、徒、流、死”。于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法就是刑法,而刑罚就是苦刑。对于法律,广大人民视之为异己的力量,视法如虎,唯恐避之不及。可以说一句极而言之的话:中华民族的广大人民在长期的发展中实际上是不知民法为何物的。
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当然是有法律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律没有形成独立发展,而是模糊于伦理之中。“验之中国法律发展的史实,我们发现,在我国古代的青铜时代,法治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的区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起,法律与伦理又开始接触融合,尔后,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到隋唐而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这一情形延至清末而毫无变化。”①伦理化对法治造成的危害极大,它破坏了法律的机制,使法律丧失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特征,使法律丧失了作为法律的功能,最终沦为伦理学的附庸,使个体的人完全淹没在王权、族权、夫权、父权的等级专制体制之中。中国古代法律尚不独立,何谈法治,更谈不上建构私法体系。
中国古代私法不独立,得不到发展,除了法律依附于伦理之外,统治阶级的法律原则是王权大于个人的利益。个人从法律上获得的利益只能是被“怜恤”的结果,而不是法律上的一种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大多是规定“不应如何”,而不是规定“应该如何,可以如何”。法不是世俗社会中所有个人合理安排生活的善良而公正的艺术,因而忽略对个人利益的明确界定,并且法是以反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标准的。但是,这种所谓反广大人民的个人利益正是为少数封建统治者的最大私利服务的,因而法成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奴役、剥削广大人民的一种暴力工具。
中国古代私法不发展,更有其经济上的原因。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私人生活关系相对简单。在封闭的自然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家长制,等级制和皇权政治,以“重义轻利”、“忠、孝、仁、义”等为观念,推行封建伦理道德,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了重伦理,轻法律;重公法,薄私法;重行政权力,轻民事权利等等传统。作为一种传统,必有其历史惯性,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
一个国家的法律应当是一个由众多部门法组成的相互协调统一的体系。从近代各国法治发展的经验来看,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一方面制定宪法,用以巩固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制定民法,用以巩固经济制度。如果从人类法律发展的长河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宪法是私法史上的一块界碑,它巩固和发展了私法。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民法是健全的,那么这个国家法治的纲领和基础是良好的。
私法这个概念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包含了民法和商法;在民商合一的国家,私法即指民法。我国系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因此,我们所说的私法即是民法的同义语。
“民法为众法之基。私法固不待论,欲治公法者,亦应对于民法有相当了解,而后可得其真谛。”②因为“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③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④民法是在承认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基础上,用权利这一法律细胞来界定自由的,并为解决权利与权力、私权与公权的关系奠定了法律前提。因此,权利乃民法的基点。权利的明确界定则为经济关系中的利益找到了适当的法律外壳,使自由成为法律保护的权利,意志不得逾越权利的范围,秩序是一种权利关系,国家是权利关系的集合体,使自由、意志、秩序、国家都得到权利的界定,这是法治的基础。从这一点上讲,民法是万法之基。
民法不仅以权利这一精巧的法律单元奠定了法治的根基,而且以“行为”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贯彻意思自治和机会平等原则,为民事主体供应了一个合理生活的手段,创造了权利平等的法律环境。刑法、行政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民法所造就的法律环境不致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而设置的。从这一点来考虑,我国法学基础理论是否应当以此作为创新的基础呢?
由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法没有形成传统,因此,从法律上确立人(包括能够作为主体的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在封建专制和自然经济制度下,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民事主体没有赖以产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等级限制独立、特权推残自由,自然经济把人们的身份关系牢牢捆住,对生存的人(或组织)之所以为人没有法律的确认。法律是人制定的,但法律不是为人制定的。如果法律是为人制定的,那么法律一定要首先对人作为民事主体加以界定,对人们的民事权利和法律行为加以规定,这是对民事主体价值的具体化与法律化。但是中国古代法基本上不具备上述内容和特征。
中国封建专制国家重视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经济收益,无视人民的个人人格与权利,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不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灌输“重义轻利”思想,“存天理,灭人欲”使天理、人情优于法;推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原则,个人本位和个人利益缺乏成长发育的土壤。民法规范多杂于刑法、行政法之内,国家也更习惯于以刑法、行政法手段调整民事关系,违反民法规范一般要受刑事处分。封建统治者极为漠视民事关系,不是把民法作为一种主要的治国手段。在古代法制中,从来没有合同的订立程序、合同的内容、签署方式、合同履行、合同的担保、合同的解除与终止、合同责任等具体规定。官府对参与解决民事纠纷的态度冷漠,百姓总是不得已而告之,官府则是不得已而理之。因为民法规范不成体系,极其缺漏,所以司法官员审理民事案件,往往不能依法办事,而是基于“情理”这一模糊标准作出道德评价⑤。在封建专制之下,人这一“天地之精华”完全被扭曲,表现出来的就是“狂人”⑥。
法治是指世俗社会以法而治,法律是治世之权威手段,即社会的控制力量形式。因此,法律应当是明确、肯定、能够预测的,具有内部和谐一致的逻辑品格,具有一体遵行的效力。法律权威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法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要求权力运作必须依法,防止权力意志的任性。和非法律因素对法治的威胁;法律权威与社会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法治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它要求法律成为广大社会普通成员的常识和意识,就广大社会普通成员来说,他对法律精神的把握,往往与其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个人利益在法律上是界定和明确的,可以把握和确定的,即个人利益权利化,法律就会起到正确指导、鼓励个人去明确追求其正当利益,维护国家和他人的正当利益的权威作用。
广大社会普通成员(包括法人)因相互间是平等的,我们称之为平等主体,也称民事主体。在最根本意义上说民事主体乃社会及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其他一切主体的基础。民事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法治化,实在是整个社会法治化的基础。
民法是民事主体之间利益关系法治化的基本部门法。它是以对生存的人(包括能够作为人的组织)确立为人为根本出发点,并以人的彻底解放为终极关怀的。
从整体上观察,民法是人法,充分认识民法的人法属性,至关重要。
民法是人法,包含下列含义。首先,民法在整体上就是一个关于标准的人的样板规定,即为人立了一个法。比如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就是关于人的资格的规定。
凡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者就是人。因此除自然人外,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组织也是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是人能够享有民事权利的范围,比如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自由权等人格权,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等身份权,自物权、他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现权、发明权等知识产权都是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由此可见,民法上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都是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民法法理上称为客观权利。这种客观权利与法律上所树立的一个标准的客观人结为一体。民法上所树立的这个标准的法律人是一定社会中的一个理想的普通成员。现实生活着的人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即都具有取得上述各种民事权利的可能性。但是,作为民事主体是否已经取得了某项民事权利,除自然的人格外,是要通过一定的法律事实才可以实现的。因此,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并不等于民事主体已经现实地享有了这种权利。比如说公民都可以享有著作权,而甲公民一生没有任何作品,就不能现实地享有任何著作权。因此,法律上规定的权利是一种“机会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是机会平等。当然,一旦民事主体现实地享有了某项民事权利,那就是把法律规定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行使和保护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如果一个现实的人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利,那未他就达到了法律规定的那个标准民事主体的境界,不仅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主体,而且也是一个极为丰富和高尚的主体;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力,那么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条件的不同,人的差异是很大的。在庞大的民事权利体系中,任何民事主体或多或少都能根据自己的条件现实地享有某些民事权利,而法律规定民事权利的目的在于鼓励每个民事主体都尽可能多的甚至全部地实现这些权利。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人人皆可以达到民法人的境界,即所谓的“人人可以为尧舜”,借用宗教一句名言:“人人皆可成佛”。因此,民法为民事主体展示了一条自我解放的“大道”。
其次,民法上的人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普通成员。因为民事权利的取得,除了人格权外,都需要通过民事主体的行为才能实现。在行为中除了非表意行为外,所有的表意行为都是以民事主体有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的。而民事主体有无民事行为能力又是以其有无意思能力为基础的。自然人的意思能力是自然人具有的自然精神能力,包括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即合理的认识力和预期力。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才能实施各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它从逻辑上概括说明了民事法律关系因意思表示而发生的一般原理,它以行为人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和内容合法、妥当为有效条件。民事法律行为充分体现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自治之手段。所谓私法自治,是对理性的人不断追求人格独立、人格完善、充分开发智慧、大力进行创造性劳动,争取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的自主选择的尊重。但是,现实生活着的人并不是都达到了这种理性程度,很可能出现利用意思自治支配、控制弱者,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等等。于是民法又通过意思表示瑕疵,内容不法等范畴,对意思自治的消极作用加以限制,因此,民事法律行为为一个理性的人设立了一个表意行为标准,并依法自主地实施此行为去取得、行使和放弃权利、承担义务、责任和风险。从行为制度上尊重民事主体作为人的价值,同时限制违法作为,并与之作斗争。
第三,民法上的人是一个负裁着丰富文化价值的社会普通成员,即一个法律文化主体。文化是人创造的。但是,文化世界一旦被创造出来,各文化世界的人们就会从文化世界获得价值意识并进行价值思维、判断、选择活动,于是文化又创造了人。人的本质说到底是他的文化存在。现代人作为一个文化主体,当然也是一个法律文化主体,因为法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民法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上的人就是一个民法文化的主体。人类民法文化已有数千年之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法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方法。现代民法上的人作为民法文化的主体,首先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对上述民法文化进行接受并内化为价值意识的主体,然后才是民法文化再创造的主体。把民法上的人塑造成社会普通成员的典型,是因为他具有一般性。社会普通成员的大脑及各种心理生物机制是一致的。人类获得文化经验包括民法文化经验及建构价值包括建构民法文化价值所遵循的道路与法则也是一致的。并且在社会文化包括民法文化创造、积累、发展过程中也都面临着大体类似的基本社会文化结构包括民法文化结构及群体参与,社会互动的文化历史过程。尽管人们具体生活的文化环境、情境、情况千差万别,人类基本的价值需要及价值意识结构层次还是一致的。因此,人们的价值思维,判断及其价值实现也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法则、规律和必然性。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我们把民法上的这个典型的人,作为社会普通成员进行民法价值思维、判断及其价值实现,进行民法文化创造和实践活动的代表。
在当代社会,普通社会成员并不是都能意识到自己是法律的存在者和实践者,特别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法的存在者和民法实践者。应当说,在我国,许多社会普通成员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只有意识到自己是民法的存在者和民法的实践者,才能成为民法文化价值的主体。这是一个民法文化价值哲学认识论问题。民法上的人是一个全面、完整、系统地从文化世界特别是从法律文化世界更重要的是从民法文化世界意识到其主体地位并占有和享用上述文化价值的主体,不仅指自然人,也指法人。这种人不仅是民法文化价值的认识主体、评价主体,而且也是选择主体和改造主体,即实践主体。因此,民法人的行为是一种文化行为。民法人的理性是建立在丰厚坚实的民法文化基础上的,使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一种人和群体价值实现的文化关系或联系。当自然人、法人按照一定的民法文化价值意识进行社会历史活动并结构成关系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该社会历史活动的民事主体,通过民事主体间在历史活动中的参与,互动行为,以波澜壮阔的力量推动历史的发展,并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我国民法实乃民事主体自我发展,自我解放的法律。
第四,民法上的人是市场经济基础上诞生的人。市场经济是平等的多元化主体分权、自主决策,以市场为基本的资源配置协调手段,来调节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体制。“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⑦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经济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⑧“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⑨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和交换是由民事主体自由行为实现的。交换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契约,因此,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契约的社会,每个市场经济关系主体以其对市场讯号的敏捷反应,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最优化的利用。在具体的交换关系中,国家不直接干预,而是实现宏观调控。“一切特定的限制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显、最单纯的自由权利制度将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每个人在他遵守正义的法律时应完全自由,在自己的方法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以其劳动和资本,加入对任何其他人或其它阶级的竞争,监督和指导私人产生的义务,君主应完全解除。”⑩
市场经济是民事主体的舞台,是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是民商法经济。因此,市场经济关系只宜采取民事法律关系的形式,市场经济关系的主体只能是民事主体。市场经济是民事主体发育、成长的摇篮,民事主体是市场经济关系主体内在本质属性的体现。民事主体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就位,行政主体从市场经济关系中退位,这是任何一种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首要条件。可以说,民法是一个用人的声音宣布的时代思想,用人的理性设计的法律大厦。在此基础上,民事权利才能得以正确界定,市场行为才能得以正确规范,民事责任才能得以真正落实,社会秩序才能得以合理建立,从而在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经济极大发展与人的觉悟极大提高的过程中推进人的发展与解放的过程,使民法的最高价值——正义,不断实现于市场经济中,最终造就出新人和新的关系,完成民法的历史任务。
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基点,以行为为手段,以责任为保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治化作出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基础法律体系以及成熟的法治模式和法律方法。这是数千年人类民法文化发展、积累的结果。人类历史传统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法律上层建筑,应以发达完善的民法作为支点进行构造。对于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来说,应当也是不能例外的。但是,果如此,那将是中国数千年法制传统的一个根本改变,意味着治国手段的根本转变,并将使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法治重心的转移,必然要求我国基础法学理论及包括民法在内的各部门法学理论的创新。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巨大历史命题和艰巨的宏伟工程。在这里最为困难的是中国长期封建法制传统观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巨大力量对现代中国人的制约,使中国广大人民一般理解法只是一种威慑性的权威,而不是他们诚实生活的“文明常识”;他们以“良心”指导自己行为的愿望要比自觉地以“法律”指导自己行为的愿望强烈得多;他们对“清官”的期望超过了对“法治”的信赖与渴望;他们的“臣民”思想扼杀着自身的“主体意识”;等等。因此,中国现代法治建设要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相当深入的法治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体系性的立法是要务,而法学基础理论的创新是关键。不仅要对中国封建法制传统进行清理与批判性研究,而且要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基础形成的法制理论进行科学的评价;不仅要对市场经济需要法治作出科学的说明,而且要研究这种法治的经济理论前提;不仅要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规范体系进行总体研究,而且要进行社会主义法文化的深入讨论;不仅对法要进行宏观研究,而且要分部门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法治呼喊着法学理论的革命。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基础法学理论的创新又绝非易事。但是,既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历史前进的发动机,而且这个发动机已经点火起动,那末中国的历史车轮就不允许倒转。为了使其正常运转,必须使之法治化。一切法学主张都将在它的面前接受考验,在法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更加科学的理论,造福于当代的中国人民及其子孙,贡献于世界人民。
注释:
①张中秋:《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1期,第3页。
②史尚宽《债法总论》自序。
③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大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4页。
⑤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3页。
⑥鲁迅语。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2-4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0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5-196页
⑩亚当·斯密《国富论》第9章。
标签:法律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民法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法律主体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法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