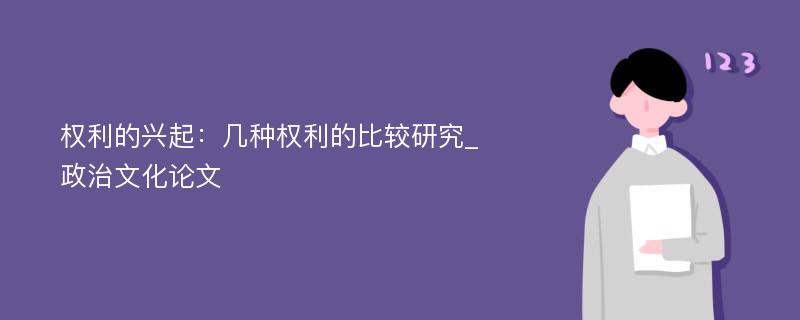
权利的兴起:对几种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与“个人权利”这一概念有关的传统的中国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中的道德和思想的种种“风貌”。在具有儒教传统的中国,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文化发出的道德主义的强大呼声,阻碍了任何权利观念的发展。古代希腊人也认为个人应服从较大的社会群体——这里指的是城邦。然而,希腊人关于正义的概念,无疑地为后来的关于权利的思想铺平了道路。罗马的法学更明显地含有现代权利的萌芽。中世纪世界中同样存在预兆现代权利的因素。从17世纪以来,关于权利的论述在西方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上占据着主导地位。权利的兴起可用这样一些概念加以解释:(1)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2)道德和宗教的复杂性,(3)“可感知的”文化,和(4)市场资本主义。因此,在“权利”现象和“现代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和无法解脱的关系。
关于个人享有种种权利、侵犯这些权利是不道德的行为和这些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产物。它不存在于现代以前的各种社会的思想领域中,这些社会包括伟大的轴心期(Axial Age)[**]的古希腊—罗马世界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或传统的中国文明。本文力求探讨和比较上述四种文明中有关个人权利的概念的道德风貌和政治—法律结构的各个方面,并试图对现代情况下的“权利”现象提供一种解释性的理解。
关于“正义”、“公正的做法”或“正当的做法”的词语和表述,存在于许多古代的和现代的语言中,但“权利”这个词却是比较现代的发明[①]。它被引进到欧洲的语言中是由于拉丁语词“ius”(“jus”)在用法上的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发生在14世纪和15世纪。[②]“ius”这个词获得了它在古典时期所没有的更多的含义,即人类有一种固有的特性,按照这种特性,一个人应当拥有某些东西,能够做某些事情,或应当不受某些干预,这乃是正确的和公正的。[③]在谈论同一个人打交道时“什么是正当的”(或“什么是公正的”)与谈论“一个人享有什么权利”之间的不同之处似乎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从全面的或整体的观点,从社会、社会秩序或从一种超然的道德秩序的观点来看待正当和公正;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是从有关的个人的观点来谈论什么是公正。[④]关于权利的词汇的实用意义是它能够使个人(和集体)要求并声称某些利益和权益是他们应当得到的,并给这些声称赋予道德的合法性。[⑤]关于权利的语言是一种特别有力的表达方式,它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⑥]
传统的中国文明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统治了两千年。正如这种哲学的奠基人所宣讲的那样,这种文化的道德结构的核心是家庭伦理。社会被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皇帝被认为是天子,奉天命进行统治。儒教的道德理论期望他关心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关心子女一样。官员们被称为“父母官”。[⑦]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不存在关于个人及其权利的概念。[⑧]没有把人看成是这样一个抽象的和自主的实体,这个实体拥有可以用关于权利的语言来描绘的特性。在中国的思想中,人是用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人类关系来定义的,[⑨]人性的实现是完成与个人担任的社会角色相联系的道德义务的问题。[⑩]不存在纯粹的个人——只有儿子、女儿、父亲、丈夫、妻子、臣民、统治者、官员,等等。[11]因此,被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质。[12]人无法摆脱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随时随地被这些关系所包围,而社会只不过是家庭关系和其他人类关系的网络。[13]儒家宣扬仁,仁应当从一个人的家庭成员和亲属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的人类关系。[14]
在这个道德领域里,有五种主要的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的三种关系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另外两种也被认为是按照家庭关系的模式建立的。[15]这些关系包括相互的在道德上的期望[16]以及(在前四种关系中产生的)权威、服从和依附,它们构成了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基础。[17]关于遵“礼”行事的社会压力保证了人们的举止循规蹈矩,“礼”是礼貌、礼仪、仪典和仪式的传统的习惯性的规范,它表达的是与各种社会角色和人类关系相联系的要求和期望。[18]一般认为,“礼”是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个性的发展以及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19]统治者被指望去教导人们遵守这些道德规范,而他们自己则作为伦理的表率。[20]这样提倡的主要的美德包括对统治者的忠诚(忠)和对父母的孝顺(孝)。[21]
家庭和人类关系的伦理居于主导地位显然是中国文明最突出的特点之一。[22]个人对家庭的依附导致缺乏一种自主的、自立的和拥有权利的个人的概念。[23]中国文化的强烈的道德主义的呼声,与社会和谐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以及与自然[24]结合在一起,也阻碍了任何权利观念的出现。儒家的道德思想对“义”(正当或正义)和“利”(收益或利益)作了严格的区分。[25]道德上的正义在于按照道德准则行事,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按照自己对社会关系中的另一方(例如一个家庭成员)所负的责任行事,而不顾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被认为是私利),并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对待他人。任何关于自身利益(“权利”)的主张都是道德上可疑的和非法的,[26]因为一个有良好道德的人是不自私的人,他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而且他是礼让的——即在他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冲突时,他愿意放弃(“让”)、妥协和作出让步。[27]因此,不鼓励以诉讼作为解决争端的方法;宁愿调解和在法庭外解决,并认为这样有利于社会和谐。[28]关于个人权利的概念(从在利益互相冲突的情况下把自身利益作为合法主张提出的意义上看)是与道德上的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的,这种理想主义支持一个由人类关系网络构成的“以诚信和道义为组织基础的社群”,其特点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自我克制,相互尊重,和团结的意识。[29]
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古代希腊人的世界观有某些相似之处,[30]这些相似之处也许使它们彼此更为接近,不像古典的和现代的西方文明之间那样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或象征性的秩序上的巨大差距。和中国人一样,希腊人也认为社会等级制度是顺乎自然的,认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人格是道德成长和个性发展的问题,认为培养美德和发扬人类的优点重于追逐物质利益,认为责任优先于权利,以及认为个人应服从一个较大的社会群体和它的权威、要求和目标。正如上文提到的,对中国人而言,个人不被认为是抽象的孤立体而是一个社会存在。在古典的希腊,人被认为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如果说家庭是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思想的焦点的话,希腊思想中相应的焦点是城邦。这里也不存在作为最小单位的自立的个人的问题;参与城邦的共同生活就是人性的本质的一部分。
如果说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家庭和人类关系是自我实现的手段的话,在古典的希腊哲学中,城邦的公民身份就是相应的手段。城邦中的公民生活包括民主参与和自治;共和制度和法治提供了创造美好生活的环境。公民们被期望献身于和致力于城邦的共同利益。在为城邦的生存或荣誉而战时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当一个人在其公民同胞们的心目中赢得了荣誉和尊敬并受到城邦的集体铭记时,他就是实现了生命的意义。
在古典的希腊文中,没有一个字眼表达我们的关于一项或多项“权利”[31]的概念,尽管希腊哲学对正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雄辩的讨论:什么是公正,什么是正当。“正义”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包括服从法律,整顿社会秩序,和在利益互相冲突的情况下给与每个人应得的份额。[32]可以论证的是,希腊思想中关于正义的后一种意义给以后的罗马法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罗马法学又给现代的权利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古典的希腊文中,同一个词语用来表达“正义”、“法官”和“直线”。[33]在有互相冲突的主张引起诉讼或可能引起诉讼的情况下给与每个人以他应得的份额的这一概念,[34]预示人们关于自身利益的某些主张可能是合法的;而且可能值得给予法律上和司法上的承认。[34]因此,这就暗含有关于权利的概念。这一思想模式与中国模式恰恰相反,后者视对簿公堂为可耻之事,并且认为任何坚持一己私利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可疑的。
古典的罗马法学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说法之一是,“正义”(‘iustitia’)就是持续而经久地决定使每个人得到公正(ius)。”[35]在这里,“公正(ius)”可以最好地翻译为“他的份额”,“他值得得到的东西”,或“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现代欧洲的权利概念来源于中世纪对“ius”一词的含义和用法的扩大和修改。在古典的拉丁语中,“ius”至少有10种含义,其中4种可以用于那些使用现代词语“权利”的场合。[36]“ius”的主要含义是正当或公正。[37]关于法律的概念也可以用“ius”表达,法庭和判决也是如此。它还可以用来包罗我们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概念。[38]没有明确的和显著的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权利”的概念,或至少没有有效的语言手段用来集中表达这种概念。[39]这一点进一步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无论是“dominium”(拉丁语“财产所有权”)还是“libertas”(拉丁语“自由”)都不被认为是“ius”(公正)。[40]
尽管没有明确的关于权利的概念和词汇,罗马世界的法律和正义与现代世界的个人权利之间的差异,不像传统的中国秩序与后者之间的差异那样大。主要的一点是罗马没有笼统地从道德上贬低个人的物质私利。相反,罗马的私法对契约和财产交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私利的性质、范围和实现作了精辟的界定、说明和阐释。从把权利说成是道德上合理的主张,到从法律上承认物质私利,罗马法学含有对个人权利的有力的、尽管是默示而不是明示的肯定。在斯多葛派的影响下,一种把“ius gentium”(国际法,或适用于罗马帝国统治下不同地区的人民的法律)与“ius naturale”(自然法)联系起来的倾向,开创了按照人类理性可以发现的关于正义的普遍原则来评价或形成实证法的可能性。这就为以后的自然权利概念铺平了道路。
现代西方文明的双重来源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和希腊—罗马遗产。后一种,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可以说含有现代权利的萌芽。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两种传统在很多方面处于紧张和敌对的状态。关于权利作为对物质私利的合法主张的问题,耶稣的登山宝训中的下列章节值得人们深思:
“如果你被控告,在法庭外就与对方和解。……若有人掌掴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吧。若有人控告你,要夺取你的衬衫,连外衣也给他
。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41]
这段话使人不禁想起中国儒家对待和解、体谅、向别人让步而不坚持自己权利的态度。的确,它们反映出一条共同的路线,这条路线显然贯串轴心期各种文明中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和哲学的道德思想:施惠要比受惠好,自我克制要比从他人身上谋利好,奉行利他主义要比奉行利己主义好。
中世纪鼎盛时期的最高思想成就是古典的希腊哲学和罗马的法学思想与基督教信仰的融合。亚里士多德的用目的论解释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框架被赋予基督教的内容。拯救个人的灵魂被视为宇宙活动的主要目的。教会作为信徒们的团体和拯救灵魂的工具,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然而,在维持法律和秩序上,政治体制也起了有益的作用。正如在希腊思想中那样,政治体制,连同它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和符合人的本性和需要。它的存在被庄严地批准,而且它构成了更大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42]
“个人”这个词在中世纪时期是不存在的。[43]然而,在中世纪世界的确存在这样一些概念上的和社会政治的因素,这些因素预示后来出现的对权利的要求。首先,每个个人都有灵魂,它和任何别的个人的灵魂一样具有无限的价值。这个信念为人的尊严和对人格的尊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4]第二,法治概念,包括神法和自然法,被坚持用来反对专横独断的权力。[45]第三,私有财产制度得到肯定,尽管只是作为对人类薄弱意志的一种让步和需要以物质奖励的形式提供刺激。[46](但应当指出,在这方面像儒教和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中世纪基督教也轻视追逐物质利益的本身;贪婪是一种罪恶,放高利贷或在交易中谋取不合理利润的行为受到谴责。)第四,领主—部属关系具有契约的性质,导致互相承担义务和有所期待。第五,中世纪社会政治秩序的分散性和多样化,使得各种不同的团体(例如教会、统治者、贵族、城镇、行会,等等)为了维护或增进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地与其他团体进行谈判或斗争。不像在中华帝国那样,这里没有全面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力量能够有效地和有力地把这种对权利和特权的要求加以非法化和压制。[47]
关于权利的现代词汇的创造可以溯源到一些中世纪的基督教作家,特别是奥康姆的威廉[48](在14世纪从事写作)和热尔松[49](在15世纪早期从事写作)。他们的做法是把拉丁语词“ius”的用法加以修改,背景则是(由圣芳济各会修士们奉行的使徒贫穷原则发起的)关于财产的持有、使用和所有权的讨论。[50]现代语言中关于权利的表述显然是在17世纪早期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的著作中确定的。[51]在同一个世纪中,霍布斯和洛克发展了关于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这种理论的基础就是个人有自我保护的权利(霍布斯语)或有生存、自由和获取财产的权利(洛克语),而且从那时以后,关于权利的论述在西方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的地位。[52]这种论述模式在20世纪后期仍有巨大的影响。在本文的下余篇幅中,我试图从四个有利之点对权利的这种上升状态作出一些解释,这四点本身提供了权利的现代性的轮廓。
(1)正如上文指出的,关于权利的语言使得有可能从个人的观点讨论正义问题。因此,它很符合现代世界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人类学家路易·迪蒙曾经仔细研究这种意识形态(定义为指流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性质,并把它与各种传统文明的意识形态相比较。[53]他得出的结论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赋予个别的人:在别的文明里,社区、社会秩序或整体,总是处于优先的地位。他追溯这种独特的个人主义的来源在于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才孕育出现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基督教徒个人原来是一个“超凡出世的”个人——基督的王国不在这个尘世上,基督教徒的注意力被引向另一个世界。然而,由于天主教会参与世俗政治的结果,而且,最终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要求基督教徒积极参与现实世界的事务的结果,诞生了现代的个人主义。
(2)在优先考虑的是权利而不是良好的道德品质或精神愿望时,关于权利的语言说明实际上存在一个有着各种各样道德和宗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于人类存在的主要目标不可能再有一致同意的看法。早期的权利理论者和社会契约论者生活在一个有着激烈的宗教斗争的时代,[54]在那个时代里,由于统治者和他的臣民中不奉国教者之间、坚持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各部分人口(尽管都是基督教徒)之间的斗争,使得社会秩序十分紧张。关于权利、特别是人身自我保存权利和信仰自由权利的理论,只给社会秩序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基础。[55]迄今为止,在西方和在像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中,统治者(或者在西方的情况下是统治者与教会联合)有责任和权利教导他们的臣民什么是生活的真谛,并引导他们走向美好生活或拯救灵魂的道路。权利论,特别是革命的和前所未有的关于思想和信仰自由的权利论,取消了政治上的掌权者在宣告和宣传善良和美好生活的概念或理想上的权威,并把他们降低到只起保护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的作用。
(3)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最适合于一个已经经历了韦伯所说的“觉醒”和“合理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拥有索罗金描述的“可感知的”文化。索罗金把历史上的文化形式分成三个层次[56]:“想像的”、“理想的”和“可感知的”,其中理想的文化是想像的文化和可感知的文化的混合物。在想像的文化中,最终的现实和价值被理解为超然的神或来世的秩序,而使人类达到完美境界的途径在于道德的和精神的训练和培养,在于神秘的对神灵的感应,在于对同胞的爱、奉献和团结。在可感知的文化中,所有的现实都是可以感觉到的,即是说,可以由我们的感官察觉的。人类追求幸福就是要满足他们对于娱乐、舒适、财富、权力和地位的种种欲望。
作为一位哲学家,A·I·梅尔登明确地解释说,[57]在一个没有权利语言的道德世界里,对一个人施加的侵害行为,仅仅是违犯了上帝的戒律,违犯了神法或自然法,或者违犯了社区法;加害人对上帝负责,但不对受害人直接负责,也不需要请求受害人宽恕。另一方面,如果侵害行为被认为是侵犯了受害人的权利的话,受害人作为道德执行人的自主和尊严就得到了确认。因此,他将把开展关于权利的讨论认为是一种进步。[58]然而,我认为,现代对权利讨论的使用,以及现代人越来越依赖它进行关于道德和政治的讨论,是与一个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超然王国从他们的道德世界中消失这一事实相联系的。由于从想像的文化转变到可感知的文化,当一项侵害行为实施时,唯一的现实就是给受害人造成了危害(表述为侵犯了他的权利);但并没有违犯超然的秩序中现实的和客观的规范。
(4)最后,鉴于财产权和契约权是现代权利思想中的基本权利,权利现象可被理解为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市场资本主义的产物,“从身份过渡到契约”(如曼恩所理解的),从礼俗社会过渡到法理社会(如特尼斯所理解的),[59]从“机械的”到“有机的”团结(如迪尔凯姆所理解的),从“人身依附关系”到“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人身独立”(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初稿)》),[60]或者从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主到以人与物的关系(迪蒙指出的现代意识形态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61]为主,这种过渡主要包括那些把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社会通常是由共同的文化、宗教或等级制度的理想团结在一起的,在这种制度中,人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任务,感觉在世界上过得很自在,并与其所属的社会集体的成员们团结共处。相比之下,现代世界是在市场协调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基础上运作的,在这个世界里,占支配地位的是从功利主义出发斤斤计较自身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是依附和献身于一个社会集体。
因此,可以看出,由于现代性与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合理化和市场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由于权利观念与上述现代性的四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之间的联系,因而在现代时期中,关于权利的论述是无法遏制的,而且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回顾起来,权利观念从17世纪以来的兴起乃是历史的必然,或者甚至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需要它而且依赖它。关于权利的论述是否会延续到后现代性时期,似乎取决于这种后现代性的性质,特别是取决于个人主义(相对于公有制社会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于重新出现的对美好事物或“超级美好事物”的一致意见)[62]、觉醒(相对于再迷惑)和市场资本主义(相对于某些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
周叶谦 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1883—1969)在其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为轴心期(公元前800—200年),在此期间,几乎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中国(先秦诸子)、印度(释迦牟尼)和西方(荷马、柏拉图等)产生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译者
注释:
① 见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著《追求美德》(After Virtue.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第65—67页:“……英语中‘权利’之类的词语和英语及其他语言中性质相同的术语,只是在语言史上较晚的时期,即中世纪将近结束时方才出现。……直到中世纪即将结束时为止,在任何古代的或中世纪的语言中没有任何词语可以用我们的‘权利’词语加以翻译;在大约公元1400年以前,无论是古典的或中世纪的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或阿拉伯语中都没有任何表达权利概念的方式,更不用说在英语或日语中,直到19世纪中叶还没有这种方式。”关于“权利”一词用作名词时的语言学上的分析,见罗斯科·庞德著:《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Hamden,Conn:Archon Books,1968,初版于1942)第87—91页。
② 参见约翰·芬尼斯著《自然法与自然权利》(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第206—210页和埃尔西·L·班德曼和伯特伦·班德曼编辑的《生物伦理和人的权利》(Bioethics and HumanRights.Boston:Little,Brown & Co,1978)第44—50页马丁·P·戈尔丁著“权利概念:一个历史的概述”中的历史的分析。
③ 同注①中庞德的著作,第85页;罗斯科·庞德著《法律史阐释》(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0,初版于1923),第158页;同注②中芬尼斯的著作,第206—207页。
④ 同注②中芬尼斯的著作,第205页。
⑤ 乔尔·范伯格著“权利的性质和价值”,载注②班德曼和班德曼所编书,第19—31页(他指出,说某人对某物拥有权利是指他可以把它作为他应得之物而要求得到它,或者他有理由声称它是他应得之物(第21页),即他可以提出对它的正当要求而把他人排除在外(第24页);“(权利的)典型运用和明显地适于运用权利的事物,就是可以声称、要求、肯定、坚持拥有的事物”(第27页);“简单的结论是:拥有某项权利就是可以针对某人提出某种主张,根据某些管理规章或道德原则要求该人承认这种主张是有效的”(第31页);马丁·P·戈尔丁,“权利语言的意义”,《哲学问题》(Philosophical Topics),第18卷,第1期(1990)第53页;“人们彼此针对对方提出的主张和要求,是理解权利概念的关键。……权利被用来支持某种主张或要求。权利似乎是一支“道德枪”,尽管不是一支有形的枪,是一种道德权力,尽管不是一种有形的权力,我们用它从道德上执行我们的主张”(第57页);A·I·梅尔登,《道德生活中的权利:一篇历史—哲学论文》(Rights in Moral Lives:AHistcrical-Philosophical Essa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关于权利的谈论发生在——通常,至少发生在——当人们坚持或要求他们的权利的时候”(第11页);权利是“行为人的道德财产”(第76页),是“某种可以被主张、要求、拒绝、剥夺、放弃、转让、没收、遵守、移交,等等的东西。”(第76页);“主张自己的权利就是以自己的名义要求权利,即是说,表明自己有权力限制他人的某种自由,当自己拥有这样做的权利的时候”(第81页)。
⑥ 梅尔登(同上注)争辩说,现代的关于权利的论述把个人的道德力量说成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个人拥有针对他人的某种道德权力或权威。由于现代以前的关于道德的论述未能直接集中于权利概念而且强调人的本身只是道德的执行人,因而在现代出现的权利思想代表道德思想上的一种进步。见戈尔丁对梅尔登的这一观点的评论,“权利语言的意义”,同上注,第55页及以后各页。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渊源:现代身份的构成》(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第11—13,395页中也赞扬现代创造的关于权利的论述。他指出,很多文明都肯定这样一个原则:所有的人都应受到尊重。在这些高级文明中,现代西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已经从权利的角度赞成建立这样一种尊重的原则。”(第11页)他认为,这种现代的关于权利的论述表明对人的道德自主有了深入的认识:关于权利的论述不仅表明传统的“尊重人的生活和人格完整”的道德原则,而且认为人们是确立和保证尊重他们应当受到的尊重的积极的合作者”(第12页);“关于主观权利的说法提出了一个规定某些重要的豁免权和利益的方式,它还提出了关于自由民的尊严的某些概念,因为它把这些豁免权和利益说成是自由民的一种财富,这种财富可以由自由民用于他自己的目的”(第395页)。对泰勒的这些观点的讨论还见于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性和觉醒:某些历史的反思”,载詹姆斯·塔利编《多元主义时代的哲学:查尔斯·泰勒哲学质疑》Philosophy in an Age of Pluralism:The Philosophy of Charles Taylor in Ques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第3章。
⑦ 参见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章(“家与国”);James C Hsiung(编)《东亚的人权:一个文化透视(Human Rights in East Asia:A Cultural Perspective.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86)第1章,第4章(“儒教承认‘国’和‘家’的双重结构”(第9页);“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中国是一个‘家庭化的国家’: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扩大的家庭”(第88页);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6年重印版,第三章(“民本的思想”),第29页:“天的观念与家族的观念互相结合,在政治上产生出一新名词焉,曰‘天子’。”……“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皇帝一面为天之子,一面又为民之父母,形成了“格于上下”的媒介。这种思想是简单的,但体现了很高的政治思想。
⑧ 路易·迪蒙,“非现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论”,载《代达罗斯》(Daedalus)1975年春,170之153,提及Francis L Hsu,“社会心理状态的相对稳定和仁:高级心理人类学的思想工具”,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73卷,第1期(1971)第2页。迪蒙还引证Chie Nakane,《日本社会》(Japanes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而且指出在传统的日本社会同样缺少现代西方的关于个人的概念。
⑨ 杜维明,“儒教”,载阿尔文·夏尔马(编)《我们的宗教》(Our Religion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33)第3章:“儒教关于自我的概念不是建立在以个性作为人的核心的概念上(不像犹太—基督教关于灵魂的概念或印度教关于“我”(atman)的概念)。而是把自我常常理解为各种关系的中心。”(第205页)并见成中英:《知识与价值》,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398页:“在儒家社会伦理的礼法中,人是被各种关系所界定,也在各种关系中发展。”
⑩ 亨利·罗斯蒙特(小),“为什么看重权利?儒家的批评”,载勒鲁瓦·S·鲁内,《人权和世界宗教》(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第10章(罗斯蒙特指出,儒家关于自我的概念完全不同于“着重把自我看成是一个自主的、可以自由作出选择的个体的自身。对早期的儒家来说,不可能有从抽象意义上考虑的孤立的自我:我是在与特定的其他人生活中角色的整体。我不是扮演或完成这些角色;我就是这些角色。……在早期的儒家看来,通过执行这些关系所界定的义务,我们就是在走人的道路。”(第177页,着重点是原有的);成中英,同注⑨,第390页:“人的责任和权利,即在经过修养,俾使各种关系达到完美境地,这种修养的结果即称为‘德’”。并见梁启超,同注⑦,第74—75页;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8版,第120页。
[11] 梁漱溟,同上注,第90—91页:梁氏引张东荪先生所言:“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Dependent Being),不是指其生存必须依靠于他人而言,乃是说其生活在世必然尽一种责任,即无异为了这个责任而生。……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Families)。……在这样层系组织之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夫,就是妇。不是兄,就是弟。”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中国传统文化不外是家的文化,孝的文化,它完全不承认个人的存在。”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在(传统的)政治方面,个人不具备“公民”那样的独立的社会政治身份。每个人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伦理身份,即作为父子、兄弟、男女、夫妻的血缘身份。由于家国一体,血缘身份与作为君臣官民良贱的社会身份又是相通的。”
[12] 罗斯蒙特,同注⑩:“如果一贯地解释早期的儒家著作的话,应当理解它们是坚持人类生活的总的社会性质”(第176页)。另见罗杰·J·艾姆斯,“礼仪作为权利:儒家的抉择,”载鲁内,同注⑩,第12章:“……中国传统中的人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人”(第205页)。
[13] 梁漱溟,同注⑩,第81页:“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杜维明,同注⑨,第141页:“通过一个包含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和世外在内的不断扩大的网络,儒家力求实现无所不包的完美的人道。”(第141页)
[14] 梁启超,同注⑦,第三章。他指出,“仁”〔可以被翻译为英语的benevolence(仁慈)〕是一种同情心和同类意识。“孟子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又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类莫不有同类意识,然此‘意识圈’以吾身为中心点,随其环距之远近以为强弱浓淡。故爱类观念必先发生于其所最亲习。……由所爱以‘及其所不爱,’由所不忍以‘达于其所忍’,是谓同类意识之扩大。……儒家之理想的政治,则欲人人将其同类意识扩充到极量,以完成所谓‘仁’的世界,此世界名之曰‘大同’。”
[15] 梁漱溟,同注⑩,第28页。关于五种关系的简要说明,见杜维明,同注⑨,第186—193页。并见王赓武,《中国的中国性》(The Chineseness of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第9章,尤其是第172页。
[16] 关于儒家关系中的相互性,见梁启超,同注⑦,第74—75页;王赓武,同注①⑤,第170,176页。
[17] 见杜维明,同注⑨:“用现代的平等和自由的观点来看,儒家伦理的最不美妙的遗产是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历史上,三纲的概念出现在……孟子首先提倡“五伦”之后约四百年。……三纲完全改变了孟子想要把平等精神作为基础的意图。显然,以统治/服从为基础的三纲强调等级关系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不可违反的原则。”(第193页)。
[18] 史华慈,“论对待中国法律的态度”,载M·卡茨(编),《法治与个人》(Government Under Law and the Individual.Washington,D.C.: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57)第28—39页:“社会角色是儒家关于社会结构的定义中的关键术语:社会结构基本上是担任某些社会角色的人们之间的一张关系网。……在这个结构内,‘礼’指的是这些基本关系中包含的行为规范。它们是指导个人在扮演他自己的社会角色时的行为和他对待别人在扮演他们社会角色时的行为的规则。实际上,“礼”有广泛的含义。……当我们研究一下在“礼”这个项目之下的一些具体规定时,我们发现其中很多涉及礼仪、礼节、礼貌、姿态和风采的问题。”(第29—31页);艾姆斯,同注[12]:“‘礼’是构成社会和产生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的、主要是社会的机制。……‘礼’这个字一般被翻译成“礼仪”、“仪式”和“礼节”……遵守礼仪就是……成为它所界定的社会的一部分,从而被它所塑造和社会化。……礼仪是在保存和传播文化。……仪式的作用是使人们在社会上成长。”(第199—200,202页)
[19] 正如梁启超指出的,儒家的目标是通过伦理、教育和政治的融合来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见梁启超,同注⑦,第78—84页)。并见艾姆斯,同注[12],他谈论“自我修养和人格化在使礼仪成为构成社群的要素中所起的作用”(第201页):“在中国的传统中,对人道本身没有作本质的界定。它被理解为一种进步的文化成就。有一种质的优势……它反映一个人通过礼仪活动改善自己的程度。”(第202页)
[20] 梁启超,同注⑦,第81页:“儒家固希望圣君贤相。然所希望者非在其治民莅事也,而在其‘化民成俗’”;史华慈,同注[18],第31页:“好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们应该一方面根据礼给人民提供良好行为的榜样……另一方面用礼教育人民。”并见杜维明,同注⑨,:“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内圣外君’”(第147页);“孔子及其追随者从未忘记指出,美德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的结果,它是政治领导的一个不可分的方面”(第150页);儒家的概念〔是〕政治主要是道德感化”(第151页);“统治者被认为是伦理的示范者,他用道德领导和示范教育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第185页)。梁漱溟(同注⑩,第216页)指出,在传统的中国,“士人于是就居间对双方作功夫:对君主则时常警觉规谏他,要约束自己少用权力,而晓得恤民。对民众则时常教训他们,要忠君敬长,敦厚情谊,各安本分。”
[21] 但是,正如王赓武指出的:“20世纪初期的改良者和革命者并不全都抨击儒家政治的主要理论,那些抨击的人只是抨击要求全体中国人履行的两项特殊的但是绝对的义务,即对统治者尽忠和对父母尽孝。……毫无疑问,忠和孝是传统的中国两项最突出的义务。”(王赓武,同注[15],第169页)
[22] 见梁漱溟,同注⑩。
[23] 正如自黑格尔以来的一些思想家们指出的,由于家庭之内的人类关系的特点是爱、信任、团结、共同生活和有共同的目标、自我奉献甚至自我牺牲,家庭成员并不声称作为个人拥有针对其他成员的权利。这种看法如果与家庭伦理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放在一起,就给传统的中国缺少关于权利的概念或论述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见《黑格尔的权利哲学》(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英文译者T·M·诺克斯;Oxford:Clarendon Press,1942):“家庭……的最大特点是爱(第158段,第110页)……爱的第一个要素是,我不希望成为一个自我存在的和独立的人,而且,如果我成为这样一个人的话,我会感到有缺陷和不圆满(增补第158段,第261页)……因此,在一个家庭中,人们不是独立的人而只是一个成员。(第158段,第110页)……个人由于家庭整体而享有的权利……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时……方才采取权利的形式。这时,那些应该是家庭成员的人……开始成为自我存在的人(第159段,第110—111页;着重点是原有的)”;K—H·伊尔廷,“文明社会的辩证法”,载Z·A·佩尔琴斯基,《国家和文明社会: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研究》(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Studies 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211:“在一个家庭里……权利和义务是不明确的,只有模糊的界定,家庭成员还构成一个社群,在这个社群里,个人在彼此打交道时不是完全独立的。如果他们终于独立了的话,家庭就实际上已经解体了。”(第213页);Z·A·佩尔琴斯基,“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中的政治社会和个人自由,”载佩尔琴斯基,同前书,第55页,“〔家庭〕要求每个人经常做出自我牺牲和把个性淹没在共同生活中。……〔家庭的经历〕形成个人的天性并教给他伦理生活的要素——承认和接受各种各样的义务和道德教育,以克服种种奢望和私欲(第69页);查尔斯·泰勒,《黑格尔》(Heg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家庭是一个感情的集体,爱的集体。人们感到自己是家庭的成员,而不感到是一些彼此拥有相对的权利的人。当权利进入家庭时,家庭正在解体。”(第431—432页;着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戈尔丁,“权利语言的意义”,同注⑤:“权利主要产生于彼此疏远的、没有人情的关系中,法院倾向于把各当事人之间看成是这种关系——即他们彼此都是陌生人……谈论权利往往是某种关系破裂的迹象,例如当亲戚们彼此因要求实现某项主张而提起诉讼的时候。”(第63页)
[24] 杜维明指出,在儒家的世界观(特别是宋朝以后的新儒家的世界观)中,理想的景象是人们生活在社会和谐中并实现人道和自然(“天”或“天地”)的统一。他把这称之为“人类与宇宙融合的景象”(“anthropocosmic vision”):“衡量人道的适当标准既有从人类出发的标准,也有从宇宙出发的标准;实际上它是‘人类与宇宙融合’的标准”。(杜维明,同注⑨,第145页)“儒家认为,存在的一切形式——人、自然和精神世界——互相有内在的联系。这种形而上学的(人们可以称之为生态学的)景象使得儒家有可能宣扬人在人类社会上体现其自身的重要性和宣扬人类与苍天的合一。”(同注⑨,第196页)并见夏勇,同注①①,第189页:“中国的情形有些不同。如前所述,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不存在西方那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的分裂、对抗。先民们追求天人合一、孝悌忠义,讲究‘和为贵’,不尚争斗。在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和谐观念的运用不免偏向连结、合一,强调礼让、奉献,因而未能创造出一套发达的权利制度和人权观念。”
[25] 正如夏勇指出的(同注[11],第29页),在中国思想史上“将‘义’同‘利’对立起来,从而使‘义’具有‘给予’‘提供’‘出让’的含义,‘获取’‘应得’‘接受’被视为‘小利’,与正义不相容。……追逐私利是极不光彩的。因为私利不仅有损于‘公’(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而且有碍于一个人立德成圣。也就是说,明辨义利、舍利求义、背私向公、大公无私,既是社会原则,也是人生主旨。义利一旦对立,利就丧失了正当性和权威性。……倘若个人利益丧失了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便不可能生发出现代意义的权利概念。”并见梁启超,同注⑦,第85页:“孟子之最大特色,在排斥功利主义。”他谈到“权利观念,可谓为欧美政治思想之唯一的原素。”(第87页)“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直是无从理解,父子夫妇间,何故有彼我权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领略此中妙谛。……权利观念全由彼我对抗而生……其本质含有无限的膨胀性,从无自认为满足之一日。……孟子以为凡从权利观念出发者,皆罪恶之源泉也。”(第87—88页)
[26] 卢西恩·W·派伊,“中国:不稳定的国家,受挫折的社会,”《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0年秋季号,第56页:“反对个人宣称拥有自己的物质利益的这种统治,使得自私自利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罪恶。由于公开提倡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可耻的,因而甚至对中国的政治词汇也施加了严格的限制。中国的政治语言大都限于支持道德秩序的价值观念。”(第66页);梁漱溟,同注⑩:“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第260页)“一个人在中国只许有义务观念,而不许有权利观念,乃起因于伦理尊重对方,反而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各人站在自己立场则相争,彼此互为对方设想则相让。”(第266页);艾姆斯,同注[12]:“认为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传统中有无私这一特点,是由于混淆了自私和无私。儒家的立场是,由于自我实现基本上是一项社会任务,个人主义的“自私的”考虑就会妨碍自我实现。历经许多个世纪的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的利与对包括个人在内的所有有关的人来说是合适的和重要的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对立。前者是与被压抑的个人发展(小人)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则是自我实现的模范人物(君子)的支柱。(第205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27] 史华慈,同注[18]:在儒家的概念中,“个人有合法的利益……〔但是〕给这些利益加上神圣的气氛并把它们称做‘权利’,把维护这些个人利益提高到道德品质的水平,‘坚持自己的权利’——那就完全违反了礼的精神〔礼在这里用在礼仪或礼节的意义上〕。对待个人利益的正确的处理态度是放弃而不是坚持的态度。”(第31—32页);梁启超,同注⑦:〔与西方关于权利的概念截然相反,〕“我儒家之言则曰:‘能以礼让为国,夫何有’。此语入欧洲人脑中,其不能了解也或正与我之不了解权利同。彼欲以交争的精神建设彼之社会,我欲以交让的精神建设我之社会。彼笑我懦,我怜彼犷。”(第88页);梁漱溟,同注⑩:“〔中国〕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第83页)“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取义于家庭之结构,以制作社会之结构;——此即所谓伦理。……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第89页)“〔西方关于权利的概念〕……权利……不出于对方之认许,或第三方面之一般公认,而是由自己说出。……要之各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与,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第92—93页);夏勇,同注[11],“中国文化里的个体人,是内省的、让与的、利他的、与人谐和的道德主体,不是外制的、索取的、利己的、与人争斗的利益主体。这种个体容易成为普遍的义务主体,不大可能成为普遍的权利主体。”(第185页)
[28] 梁漱溟,同注⑩,“彼此调和妥协——彼此遇有问题,即互相让步,调和折衷以为解决,殆成中国人之不二法门,世界所共知。‘一争两丑,一让两有’为我南北流行谚语。此以争为丑之心理,固非西洋人所了解。……旧日更有‘学吃亏’之说,饱经世故者每以此教年轻人。……中国伦理推家人之情以及社会一切关系,明著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总使它对立不起来。在西洋,则几乎处处形见对立之势,虽家人父子夫妇不免。”(第209页);夏勇,同注[11],“礼〔礼仪或礼节〕不是争权夺利、相互冲突的根据,而是人们谋求无争无讼、和合谐一的凭藉。……人与人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相争相索的利害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爱互助的道德关系……中国古代最理想的政治原则是仁义、中庸、和谐,不是西方式的与权利义务纠纷相联系的公正或正义。”(第181页);并见杰罗姆·A·柯恩,“中国在现代化前夕的调解工作”,载《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California Law Review)第54卷(1966)第1201页。
[29] “以诚信和道义为组织基础的社群”(fiduciary community)这个词是杜维明创造的,“儒教:在当今时代的标志和实质”,载R·W·威尔逊和S·L·格林布拉特(编)《中国社会中的价值变化》(Value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y.New York:Praeger,1979)第46页。梁漱溟在说明中国社会的特点时强调家庭伦理的支配地位是它的基本组织原则:“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这是由近以及远,‘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伦理为此一人与彼一人(明非集团)相互间之情谊(明非权力)关系。(梁漱溟,同注⑩,第139,196页)。黄仁宇概括中国许多个世纪的儒家的基本的治理原则是“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版,第137,200,235,253页)而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第200页)。
[30] 与此有关的古代希腊人的看法,见利奥·斯特劳斯,《国民权利与历史》(Nation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戴维·L·诺顿,《民主和道德的发展》(Democracy and Moral Develop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托马斯·L·潘格尔,《崇尚民主》(The Ennobling of Democracy.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R·N·伯基,《政治思想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London:Dent,1977)第3章;G·G·萨拜因和T·L·索尔森,《政治理论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Dryden,第4版,1973)第一部分。
[31] 正如梅尔登指出的那样(同注⑤,第1章);戈尔丁,“权利语言的意义”,同注⑤第53页;庞德,《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同注①,第83—84页。
[32] 见梅尔登,同注⑤,第2—6页;戈尔丁,“权利概念:一个历史的概述”,同注②,第46页;斯特劳斯,同注[30],第127页;夏勇,同注[11],第32页。
[33] 正如夏勇指出的那样,同注[11],第31—32页。
[34] 见夏勇,同上注;庞德,《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同注①,第83—84页。
[35] 正如理查德·塔克指出的那样,见《自然权利理论:它们的起源和发展》(Natural Rights Theories: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13页。
[36] 见庞德,《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同注①,第183页;夏勇,同注[11],第35页。
[37] 塔克,同注[35],第7页。
[38] 同上注,第8页;夏勇,同注[11],第136页。并见芬尼斯的讨论,同注②,第209页。
[39] 指出这一点的是塔克,同注[35],第7页;还有庞德,《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同注①,第183页。
[40] 塔克,同注[35],第7页,26页。
[41] 《马太福音》,第5章,第25节,第39—41节。
[42] 见奥托·弗里德里希·吉尔克,《1500—1800年的自然法和社会理论》(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1800.E·巴克译。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第40页。关于中世纪的世界观,见伯基,同注[30],第4章;萨拜因,同注[30],第二部分;A·J·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类型》(Categories of Medieval Culture.G.L.坎贝尔译,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
[43] 正如安东尼·布莱克在《1250—1450年欧洲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 1250-14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31页中指出的;并见埃里奇·弗罗姆,《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New York:Avon Books,1965,初版于1941)第56—60页。
[44] 见路易·迪蒙的讨论,《个人主义论文集:人类学分析中的现代思想》(Essays on Individualism: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第27,30—31页。
[45] 见古列维奇,同注[42],第5章。
[46] 正如弗罗姆指出的,同注[43],第71页。
[47] 见布莱克书中的讨论,同注[43],第28页;万金·卡门卡,“一个观念的剖析”,载尤金·卡门卡和艾丽斯·埃—桑·泰(编)《人权》(Human Rights.London:Arnold,1978)第1章,第8页。见约翰·A·霍尔,《权力和自由》(Powers and Libertie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s,1986)第5章。
[48] 见戈尔丁,“权利概念:一个历史的概述”,同注②,第48页;塔克,同注[35],第22—24页。
[49] 见塔克,同注[35],第25—26页。
[50] 同上注,第50页。
[51] 同上注,第54—55页,第60页;戈尔丁,“权利语言的意义”,同注⑤,第57页;戈尔丁,“权利概念:一个历史的概述”,同注②,第48页;芬尼斯,同注②,第206—207页。
[52] 见查尔斯·泰勒的评论,“原子论”,载阿尔基斯·康托斯(编),《权力、财产和自由》(Powers,Possessions and Freedo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9)第39—61页。
[53] 迪蒙,“非现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论”,同注⑧,第158—159页;迪蒙,《个人主义论文集:人类学分析中的现代思想》,同注[44],第9,23—25,44—50—56,61,279页;路易·迪蒙,《从曼德维尔到马克思》(From Mandeville to Marx.Chicago:Unvi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第4,7,15页。并见梅尔登,同注⑤,第73页;弗罗姆,同注[43],第60页以后各页和第76页。
[54] 见理查德·塔克,“权利和多元主义”,载塔利(编),同注⑥,第10章,第162页。罗杰斯·M·史密斯,《自由主义与美国宪法》(Liberalism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第14—15页;潘格尔,同注[30],第133—136页;伯基,同注[30],第125页;迪蒙,同注[44],第72页,94页。
[55] 见斯特劳斯,同注[30],第180—187页;诺顿,同注[30],第20—27页;伊恩·汉普舍—蒙克,《现代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Oxford:Blackwell,1992)第4页。
[56] 皮蒂里姆·A·索罗金,《我们时代的危机》(The Crisis of Our Age.Oxford:Oneworld,1992,初版于1941),特别是第16—19页,66页以后,114页以后,138页以后各页。
[57] 梅尔登,同注⑤,第80—81页,140—143页。并见戈尔丁,“权利语言的意义”,同注⑤,第57,63页;乔尔·范伯格,“权利的性质和价值,”载班德曼和班德曼(编),同注⑤,第19—31页。
[58] 梅尔登,同注⑤,第91,101页。
[59] 见尤金·卡门卡和艾丽斯·埃—桑·泰书中的讨论,“超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当代法律和法学思想的危机,”载尤金·卡门卡和R·S·尼尔(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其范围以外》(Feudalism,Capitalism and Beyond.London:Edward Arnold,1975)第6章,第135—137页;卡门卡,“一个观念的剖析”,同注[47],第6页。
[60] 见迪蒙书中的讨论,《从曼德维尔到马克思》,同注[53],第178,185页。
[61] 见上注,第6,54—60,67,81页;迪蒙,《个人主义论文集:人类学分析中的现代思想》同注[44],第61—62页;迪蒙,“非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论”,同注⑧,第158页;C·B·麦克弗森,《持个人主义观点的政治理论(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第1—3,263以后各页。
[62] 关于“超级美好事物”,见泰勒,同注[52],第3,4章。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古典语言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