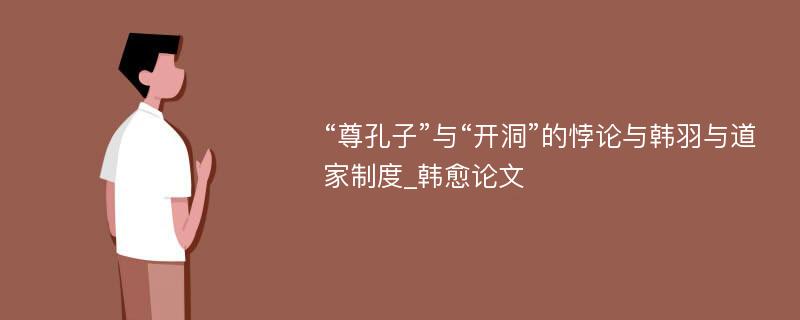
“尊孔”与“释孔”的悖论——兼及韩愈与道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统论文,悖论论文,韩愈论文,尊孔论文,释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6)04—0001—05
(一)
研究儒学必须跳出孔子(避免以“此孔子”与“彼孔子”论战),跳出具体的儒学经典(避免以此经典与彼经典论战),必须从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经世致用等不同角度,对儒家进行综合考察与评价。
世界容二而不容一,具有多样性与互融性,强使归一必生悖论。所谓悖论指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性质豆萁相煎,互不相容。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思想文化由圣人创造,由贤者阐释,由传话者传播。出现歧义由“新圣人”斡旋与仲裁(归于“一”)。盖世必有非常之圣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功,有非常之事功,然后有非常之学术。中国历史由一个个“非常之圣人”与“非常之事功”串接而成。由一连串的“圣人”构筑一个学术、一个体系、一个道统,万宗归一,无有旁门。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中国的学术与思想很难生出二。“一”横绝六合、纵贯千古。中国人以相对的“不变”应付绝对的——这种做法在世界上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中国人因独有的治学方法形成自己独特的国民性:道沿圣以垂文,圣因贤而标高;高扬古道,陈义迂腐,依典取兴,引类癖喻。这一千古不变的治学范式,积久成习,不病亦病。中国人深信,圣人“其教有适,其用无穷”。亵渎之罪莫大,孰敢当之?苟圣人言与现实抵牾,人们必想错在己而不在圣。
习惯成自然,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生存与求知方式天经地义,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以“一统”为荣,以一统为生存与处世的武器。最早为“一统”造势的当是吕不韦:“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吕氏春秋》)。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的主要动机就是将地域的、行政的“一统”与思想、学问的“一统”合为一轨,形成学政合一的“一统”,这种“一统”排斥异端,扫除个性,堵塞文化多元化(尽管《吕氏春秋》本身是兼收并蓄的)。
(二)
孔、孟的思想极有价值,然而被篡改后千疮百孔,阐孔释孟大师无超过孔、孟者。
尽管一波三折,汉武帝以还,孔子作为伟人却是没有争议的(争论限于尊其为圣还是尊其为师)。似乎孔子的微言大义、奇言瑰行不是为解人困惑的,而是供后人穿凿附会、揣赏把玩的。孔学被游戏化、工具化、实用化之后被“各取所需”了。在很大程度上,孔子的事迹与思想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与士大夫文化游戏的资源。这种文化资源为无能而又想逞能的人提供方便,举世从风,攀附高轨,造就出不计其数的句剽字窃、依样葫芦的抄家与释者,他们堂而皇之地靠吃孔孟饭过活。
后儒所言,许多不过是改头换面,信否?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将其改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颜回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将颜、孟的意思改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已无新意,然而竺道生(一名道生)还是将其强改为:“一阐提皆得成佛”(与其后出版的大本《涅槃经》说法同);到此仍未结束,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尧舜”、“禹”、“佛”、“圣人”,看似甲乙,实为同物。
孔子曰:“欲,焉得刚?”;孟子改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意思都是极好的,然而到了朱熹那里,被改为“存天理,灭人欲”,似改实篡,面目全非。
孟子曰:“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夫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也是极好的,然而被朱熹改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桎梏,东施效颦,越学越丑。
难怪司马迁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欲解开悖论,未果,毋宁说康有为不自觉也卷入了这个悖论。“托古改制”之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秦朝郡县制以还,中国的政教之“制”(非行政体制之制)并没有被有效地“改”。改的只是对圣人话语的阐释方式。换言之,“改制”仅仅局限于细枝末节,无关宏旨。同为圣人言,今日作此解说,明日作彼阐释,朝三暮四,令人眼花缭乱。这正好符合统治者口味:反正版本多多,需要哪个版本就将其拿来,不合适再换。如此,一切错误都不难找到依据。
按说镇国之学一言九鼎,实际不然,儒学极为懦弱,人皆可欺,言之凿凿的一句话,甲可以将其解释为黑,乙则可以将其解释为白。朱维铮教授有一段精辟生动论述,笔者甚为赞成:
即使在经学“一统”时期,它的内部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倘说一以贯之的传统,只有通经致用的传统,学随术变的传统。这是经学作为(中略)统治学的必然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学的传统精神,而是历史趋向。因而肯定这样的传统,便意味着否定经学本身具有一贯传统。孟荀出而孔学变形,经学出而儒学变形,通学出而经今古文学都变形,郑王学分而通学变形,南北学合而郑王学都变形。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八世纪的经学,其过程便是一部变形记。在变形的每一个转折点上,与其说是在为保存先辈传统而尽力,不如说都在为否定先辈传统而操劳①。
“学随术变”,中的!中国几千年一直是“术”强“学”弱。“术”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掩盖着“学”的停滞不前。这一情形至今犹存。不是吗?孔子被尊为圣人的时候,儒学是辉煌的、健康的,因为那时儒学可以不断受到其他学派(比如墨家)的批评。汉武帝以还,儒学而经学,而谶纬之学,而理学,而考据学,虽说都打着“学”的名号,已经不是正桩儒学。至西汉末年,孔子再不是老师,不再是学问家,不再是谆谆善诱的长者,变为“通天神人”,变为神之子(煞有介事地传说孔子是某某神的儿子)。孔子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不语怪力鬼神的他竟然被请进神殿。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
孟子所言已经尽妙,董仲舒却莫名其妙地制造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天”,演绎出“君权神授”。从此,“君”和“民”一神一人不能同论轻重,孟子的民本思想就此成为绝唱。如果说孔孟儒学与西汉儒学有什么区别的话,民由贵变贱是也。董仲舒不愧“魔术师”,三下两下就将孔孟的民本思想变没了。
(三)
儒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十年一小变,百年一大变,从未定型。每出一位新圣,如贫得宝,如暗得灯,顿解精神饥渴,似乎一切矛盾也都有望得到解消。实际上每一次嬗变都会给儒学带来重创。儒学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无论是多么才华横溢的阐释大师,都不可能由其一人独举释儒大纛,不可能长期独霸学坛——包括朱熹那样的大儒。尊孔(向心力)与释孔(离心力)形成的强大悖论给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带来的最大困惑是:一方面需要高举孔子的旗帜,另一方面又为孔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而犯愁。于是不断地出现阐孔释经大师,由他们来排忧解难。他们使用的方法非常奇怪,不是用孔学解释现实,而是反过来,根据现实需要牵强附会地曲解孔学,改塑孔学,用孔学“指导”现实。古汉语的不确定性为这种做法提供了方便(比如“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就因句读不同而产生不同解释)。在中国,“读经”与“致用”是被颠倒的,中国人宁信尺不信足。
“尊圣”、“释圣”悖论造成一种奇特景象:圣人经典不过薄薄一册,而释经之书汗牛充栋。经书酷似“母机”,一切机器都由“母机”制造,所以任何机器都不可能超过“母机”。同一种社会现象,可有多种解释,每一种解释都可以凿凿有据。两人辩论,一人称引圣人此说,另一人称引圣人彼说,两种说法都适用于解释同一问题,这时就看谁嗓门高,看谁气势凌人,看谁权力大。官高言重,人微言轻。居高官者未必占有真理,占有真理者可能因“人微”而没有发言权。权力、学术成为拴在一条线上的两个蚂蚱,跳则同跳,息则同息。
在某种意义上,“官本位”是“尊圣”、“释圣”悖论的产物。遇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尴尬场面,唯求助于权力。
“释圣人者”与圣人都是变化的。孔子、孟子、周公、颜回等先贤,看似安卧于九泉,实际上一日也未安宁过。
圣、贤、师是三个不同概念。按照龚自珍的理解:创物前民曰圣,躬行孝悌曰贤,守文抱道曰师。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动态的,飘忽不定的。他名为圣人,却难以将任何一个称号保持长久,总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换言之,即使死后两千年,仍然不能像常人那样被“盖棺论定”。他到底是圣,是师,还是王、公,聚讼不休。此乃胎衍于“尊圣”与“释圣”悖论。既然是“释”,就一定会产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
文人狎圣,由来久矣。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被尊称为“素王”(无权力、无名分之王)。但后人并未买汉武帝的账。汉成帝“封孔子后以奉汤祀”,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意思是孔子乃周公事业之绍继者,是“公”,而非“素王”。更有甚者,东汉时还将孔子后裔的封号由“公”降为“侯”。无错而遭贬谪,孔子冤枉哉!
在白虎观经学会议上,汉章帝做出惊人之举,他重新规制了“圣人”概念,削减圣人数量,宁缺勿滥,严格把关,规定只有学问的“开山鼻祖”才可称“先圣”,其余无论如何功绩卓著,都不配“先圣”称号。这样一来,只有周公被封为“先圣”,孔子只好充当“先师”。
北魏孝文帝建造孔庙,给孔子升格,谥孔子以“文圣尼父”号。这是中国在首都建孔庙祭孔圣人之滥觞。至北周,时兴复古,取消孔子“先圣”称号,复还周公。孔子仍为“先师”,封“邹国公”。此举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事出于北周崇尚周礼,相传周礼为周公所制,故而推崇周公,竭力将其地位拔高。就这样,你来我去,周公与孔子之间的争圣拉锯战一直持续至唐。唐太宗恢复孔子“先圣”称号,称颜回“先师”,后又续封了二十二位“先师”,与颜回并列。立孔庙祭祀,周公封号被撤销,作为武王陪祀,其牌位被移至周武王祠中。唐朝尊颜回极盛,尊颜几近尊孔。颜回被玄宗封为“亚圣”,开二圣并存之先河。二圣、二十二“先师”、“孔门十哲”……不一而足。封号之多之滥,创了纪录。平息安史之乱后,为缓和政局,笼络民心,孟子被提升,《孟子》由“子部”升至“经部”。然而,孟子每每被皇帝诋毁,这是另话不提。
(四)
唐朝大学者韩愈提出了“道统”,形成又一个悖论:
韩愈提出道统
韩愈未入道统
一个怪异的悖论。
在中国,道统波谲云诡,不可端倪。孔子而后,由谁接续道统,聚讼不休。自从孔子被尊,圣人就成为有为士大夫朝思梦想的目标。韩愈是这类士大夫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志欲干霸王”,是极有抱负的士大夫。韩愈极力主张以尊孔孟代替尊孔颜。从广义或抽象出发,韩愈所做没有太多意义,是在为“小脚学问”布道;从狭义与具体角度出发,韩愈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如果孟子能够进入圣人殿堂,至少在表面上,中国就有了“民为贵”的一个版本。比起孟子来,颜回几乎只具有道德价值。颜回的思想价值不如孟子高。然而在中国,孟子为亚圣抑或是颜回为亚圣,是经过相当长时间斗争的,中间几经曲折变故。较为开明的唐朝冲破禁忌,不惧怕孟子的“爱民”、“伐君”,给孟子以较高评价。北宋常秩认为孔庙正庭应该立孟子像,并取消颜回“先师”称号。这便是以孔孟作儒教“通天教主”之滥觞。须知,此时,距离孔孟时代已有一千多年。后来孟子始终是中国统治者心中一块心病。朱元璋还删过《孟子》,竭力回避他思想中积极的部分,只取其消极部分。
在对待孟子的问题上,中国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孟子的忌讳。伐放昏君(天皇)的事情屡见不鲜,有的被伐放得很惨。而在中国,孟子的这一思想只是说词,很难付诸实施。
韩愈使儒家道统清晰化了:道统始于尧、舜,而后依次为: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根据是《论语·尧曰》中有尧舜传授之言,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韩愈本人竭力排斥佛教,写过《论佛骨表》的排佛檄文,力证“佛不足事”。然而韩愈是细心研究过佛学的,他之“道统”构想,实际上受到佛教诸宗祖统体制的影响,佛教中,佛有排位,乘有大小,宗有南北,条分缕析,秩序井然。韩愈仿照佛教祖统模拟建立儒家道统,隐含着这样一个秘密:正如佛教徒人人觊觎身列祖统一样,韩愈也希望进入道统,以享后人供祀。韩愈自况接续孟子的“圣人”。
韩愈知人论事,通圣人学,继天立极;其文谲丽多趣,网天罗地,不泥窠臼,观点爽怡清新,并时无两。其通天之才,绝不在颜回、曾子之下,与孔孟比肩亦不为过。他志气宏远,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则大家子气立显,无人可敌。韩愈在治学方面不失谦虚,曾言“告我以吾过者,吾之师也”。然而,韩愈为道统奔走呼号,自己却被摈于道统之外。韩愈蛮以为自己进入道统、垂于圣林十拿九稳。韩愈不乏“追星族”,晚唐皮日休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按说,韩愈是可以进入道统的,然而由于悖论当道,事情却并未像韩愈所预想的那样发展演变。在宋人心目中韩愈不过是个“杂家”而已(当然韩愈也非完全失败,道统说一直被后人沿用,而且北宋二程、朱熹还接续了道统)。韩愈失意的原因,在于统治者不容韩愈其人。二程、朱熹等辈比较乖顺,知道如何讨君主欢,韩愈却拙于此道。二程所宣扬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与统治者想法暗合。统治者需要一套能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理论。“经术”正,就可以顺利地“经世务”。为让经术更神秘些(东方普遍崇拜神秘主义),朱熹用“理”将“经术”包装起来,使统治术臻于完善。韩愈未进入道统,意味着儒家道统不需要真才实学,只需要讨帝王欢的“谄谀学”。韩愈之学是真学,不是政用之学,每每忽略帝王的偏好。二程、朱熹则大不同,他们精于此道,加之才华横溢,入道统也就理所当然了。
韩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立德立言、留名青史的愿望,希望通过尊圣人而被后人尊。但他所言所写又不像是“圣人”,随举一例: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中略)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疏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已,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
“博爱”之说固然源于仁义道德,疏浚如导壅,发明如烛暗,藏理于平淡之中,大义于微言之内。然而韩愈忘记了:统治者不喜欢“博爱”,博爱了,谁还爱统治者?皇帝希望自己是唯一的被爱。做不到,退而求其次,让儿女爱父母,进而引申为臣爱君。二程批评过韩愈“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是“乱说”(《二程语录》)。他们不仅篡改韩愈之说,而且把孔孟之说也篡改得面目全非, 最终建立了与孔孟之说大相径庭的道学。
韩愈针砭时弊的文章亦不能为当局所容。《原毁》对社会压抑后进人才表示强烈不满,说这是由于“怠与忌”造成的。韩愈摒弃引经据典的写作套路,即使引用前人言,也是“师其意,不师其辞”,总是使用自己的话语,远远避开阐释学,这也是韩愈不能为统治者所认可的重要原因。大家都不引用圣人言,极容易“出轨”,造成言路洞开,这是统治者所不希望的。韩愈的文章往往不合道统,为帝王所忌。
韩愈的道统对统治者有利,故被采纳下来,衍于后世。韩愈不讨统治者欢,就只好栖居在唐宋八家之首的位置上。我想,韩愈是因祸得福,因为唐宋八家之首,这是永恒的荣誉,比辉煌于一时的“圣人”,价值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不知地下之韩公同意吾说否?
收稿日期:2006—02—20
注释:
① 《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转载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标签:韩愈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时间悖论论文; 国学论文; 中国尊论文; 吕氏春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