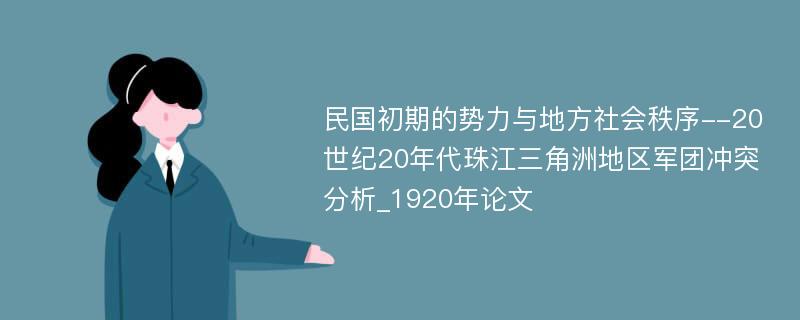
武力化与民初地方社会秩序——1920年代珠三角地区军团冲突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军团论文,化与论文,秩序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K26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145-10
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不仅工商业发达,也是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民初珠三角地区社会的剧烈动荡,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的转型。192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集中爆发的军团冲突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它不同于农团冲突,并非阶级矛盾的对立,实则军队、民团、盗匪三者之间为争夺地方利益的纠纷。军团矛盾演变为冲突,与民初地方社会的武力化过程密切相关,是民初以来广东地方社会权势格局变动之产物。本文意在通过对军团冲突中武力因素的探究,重现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权势多元化过程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从地方社会角度增进对民国军阀政治之理解。①
一、1920年代军团冲突的典型案例:九江事件
民国初年的广东社会相当混乱,各派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同时,军队与地方民团之间也不断发生摩擦与冲突。尤其是在1920年代上半期,军团冲突的数量多且规模大。从地域上看,这些冲突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据报道,当时影响较大的事件有:
1924年1月,新会县大泽墟,滇军第七旅某营因争收赌规,与当地乡团发生冲突。双方交战激烈,死伤数人。后官方从会城调来游击队将其弹压,以大泽墟罚款5000元结局。[1]
1924年3月,省城广州,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团的士兵因强用手票与商店发生纠纷,引发与省城商团的冲突,商团打死两名军人。[2]
1924年4月,番禺县高增墟,广东警卫军第三团因筹款向过往船只勒收保护费,与当地商团、民团发生冲突,双方交火战斗,结果民团包围军队,缴去枪械。[3]同月,南海县官山,地方要求撤调驻军,以求自治,与隶属滇军中路第一独立旅的陆领部队发生冲突,官山沙头各乡联团缴走军队部分枪械。[4]
1924年8月,东莞县虎门,西路讨贼军第四师因缴收船捐,与当地商团产生冲突,互相攻击,最后地方士绅出面调停,商团出款和解。[5]
1924年9月,东莞县莞城,因军队骚扰,地方不满,桂军严兆丰部与莞城商团及四乡乡团冲突,冲突中城内商民受损,城附乡村遭劫,事后防军退出,民团驻城守卫。[6]
1924年11月,李福林部粤军第三军第十七旅李群部在南海县西樵、塱心等地搜捕私铸机关与乱团,当地民团以为军队收缴枪械,双方发生冲突。西樵百余乡乡团武装出队,福军增兵至2000余人。[7]同月,东莞县虎门莲溪堡,驻防的桂军谭启秀部士兵因买菜起口角,与当地乡团商团发生冲突,后由莞籍军人王若周、张作东出面调解平息。[8]
1925年1月,新会县,建国粤军第一军梁鸿楷部第26团截查印花税,与当地商团冲突,商团军打死军方排长。军方乘机勒索商人赔偿人命银28000元,制造了所谓的“二万八事件”。[9]
1925年5月,中山县城,建国粤军第三警备队第五营前往县学宫操场操练,与当地联团游击队因误会而冲突,双方发生枪战,附近商店遭劫。[10]等等。
表面上看,这些军团冲突很大一部分与滇桂等“客籍”军队入粤有关系。实际上,此类冲突并不是滇桂军队所带来的,军队与地方民团冲突是双方对地方利益的争夺。既有经济利益的争夺,如地方税收、捐抽等,也有政治斗争的体现,如1924年11月东莞县莲溪堡军团冲突,表面上是谭启秀部士兵在墟镇买菜起口角而引发冲突,实际上却是当地民团与驻军宿怨的结果。莲溪堡南栅乡团长王孝伦本是地方一霸,“平日专以藉势敛财为事”。在廖湘芸任虎门要塞司令时,经乡人控告,曾将其逮捕,“即置诸刑”,被释后“因以廖为西路军官,因恨廖氏之故,遂西路各部亦恨之,乃积极而为驱逐西路军之运动”,“藉以谋危联军后方”,“实有政治意味”。[11]1920年代集中爆发的军团冲突,与民初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相关,是军队、民团、盗匪多种武力在地方争夺的表现。九江事件清楚体现了这点。
九江为南海县的一个大市镇,位于南海西南,与鹤山县隔河交界,明朝中后期以后,因桑蚕农业而丝织业兴盛,民国初年,商业空前繁荣,有“小广州”之称。1923年初驻粤滇军招抚九江当地著名盗匪朱联(又名朱池)、吴三镜(又名朱明新),委以九江警备司令。盗匪队伍二百余人相应摇身变为隶属于滇军第六师的军队。可是,穿上军装的盗匪贼性如故,藉滇军名义,“报复私仇,将该乡西方十一约地方焚杀掠掳,毁去屋宇二百七十余家,损失数百万”。[12]当地民团起而反对,引发冲突。滇军第六师师长胡思清发布告示,“一面严饬该司令朱池,严令该部士兵,各守军纪,不准稍有逾越”,也警告乡团,“若该乡团等不遵训诫,竟敢挑逗,则本师长惟有立遣大军,从严剿办,事关军法,慎勿视为具文”。[13]
滇军收编九江当地盗匪队伍,本意“藉资镇慑”,借以控制地方。盗匪与民团之间存在矛盾对滇军控制不利,为平息事件,保住地盘,滇军以正规军保荣光旅二千余人出兵九江,剿办了朱联,并进驻九江。盗匪首领吴三镜有幸逃脱,匿聚大同下墟一带,“派人分向顺德三十六乡及鹤山高明三洲太平等处匪帮运动,准备反攻”。[14]
滇军进驻九江后,新的矛盾随之出现。一方面,朱联盗匪余党“以是多衔恨滇军,伺机报复”。[15]而民团也与盗匪联合,北方民团分所成立时,接纳了吴三镜的盗匪队伍,“并藉其曩日声势,即推吴主持团务,以杜外匪侵入”。此举引发滇军极大不满,“出文稍后,尚未到达,而滇军以吴三镜为漏网著匪,竟敢出头冒称团长,若不剿除,恐贻后患,遂于本月(1924年7月)七日拂晓,动员前进,双方接触,互有伤亡”。[16]因盗匪问题,军队与民团之间矛盾凸显。
另一方面,滇军“给养需时,皆属就地筹款,前之开收鱼苗丝茧杂税,军民已生龃龉”。[17]九江商会曾上书孙中山,要求阻止滇军抽收九江出口土丝捐。[18]而“滇军自以为有为地方除患之功,而商民反不见谅,反对其抽捐,大失所望;而商民则以滇军自驻扎该镇以来,每日收入各地赌饷,不下五六百金,如此尚不知足,得寸进尺,将来无厌之求,不知底止,如是对于滇军抽捐一举,誓死力争,如滇军强硬征抽,则商民方面,以武力正当防卫”。矛盾迅速激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九江商团武力有限,“不过四百余人,知非滇军之敌,于是转而招集北方民团加入,以壮声援”。[19]军地矛盾又集中到军队与民团之间。
商团的邀请给了吴三镜报仇良机,7月27日,吴三镜率民团与滇军交火。在首次交战中,民团败退,而乱兵趁机抢劫,“数百家之财物,悉数被洗劫一空”。滇军的抢劫激起更大民愤,数日内,民团与滇军的冲突迅速升级,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激烈战斗,滇军调集军队逾千,兵分十一路,向民团“大举包围”。[20]
1924年7月矛盾的初露,实际上是商民不满滇军擅抽丝捐所致。商团首先表明了与驻军对抗的态度,由于自身仅有400余人力量,才招集附近各乡民团加入,准备以武力作后盾而抗衡。民团卷入后,滇军以“剿匪”为旗号,主要攻击与之有旧怨的吴三镜之民团。商团虽不敢公开站在民团一边,却暗中助战。当来援九江的滇军要求借驻由商团掌握的炮楼时,商团严词拒绝。同时,商团打着保护地方商场的旗号,从外地征调南(海)鹤(山)14埠商团开赴九江,名义上“协同当地防军,相机协剿”,实则厚积兵力。[21]
战争造成重大社会损失。当地商民四处呼援,社会各界竟相关注。在多方压力与请求下,孙中山政府派出南海县长及滇军有关人员赶赴九江调解。但在退兵问题上,互不相让,九江商民要求滇军先退,而滇军指称民团实为土匪,应解散或先退,始可调停。经多方努力,滇军答应退兵,却要求九江商界提供70000元的开拔费,“由县署将该属烟酒税分四期拨交”。而九江商团却认为滇军与民团的交战已使商民受损惨重,“不下数百十万元”,坚决拒绝。商团本已对滇军没有好感,滇军提出近似于“勒索”的退兵条件后,更是愤慨,公开发表宣言,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加入民团阵容,联合对战滇军,军队与地方的冲突进一步扩大。[22]
军团冲突再次发生后,孙中山即要求省长廖仲恺、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军长蒋光亮“秉公查办”,一面要求省长转饬商团“务须严守自卫范围,不得稍有越轨之举,尤不得援助土匪以抗军队,致干究办”;一面也要求滇军“严约部队,不得扰害地方,将所抽一切苛捐实行停收”,并要求保荣光部队“静候解决,不得妄启衅端”。[23]8月,孙中山下令要求滇军撤出九江,“嗣后无论何项军队,非奉本大元帅命令,不得擅往九江驻扎”;九江地方防卫由南海县接管,“饬南海县转饬该乡,迅即整顿民团,以维治安”;吴三镜则由县长缉办。[24]1924年8月,滇军内部争防,在石围塘发生冲突,撤离九江。政府在解决九江事件的特别会议上答应九江代表李卓峰,“准予九江自卫,嗣后永不驻兵”,九江军团冲突暂告平息。[25]
滇军撤离后,政府并未在九江恢复强有力的控制。尽管商团势力因广州商团事件受到打压,而民团在当地的影响仍不小。吴三镜并没有得到追究与惩处,仍占据民团长职务,且势力愈来愈大,既招集附近悍匪雷公全、何柏、张歪嘴裕等数百人编为团丁,又收容反政府的“逆军”数百人,并私制枪弹。而且随即又卷入了国民革命政府与陈炯明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乘大军出发东江之际,勾结土匪,图谋不轨”。革命政府认为九江民团明显“助逆”,调派李福林第五军李群旅前往剿办,再次引发军团冲突,经过几日激战,民团败走,九江镇再遭浩劫,据称此次冲突造成难民不下十万,全镇损失“总计在千数百万元”。[26]剿办吴三镜后,李福林虽表示福军“自应返回原防,整理捕务”,却又建议国民政府“应派别军部队前往驻扎”,“劝导从速改组民团”。[27]
1923年至1925年间发生在九江的军团冲突事件一脉相承,是民初军团冲突的典型事例。从中可见,矛盾主要来源于军队、民团、盗匪三股势力之间。军队为何会与地方民团发生冲突?盗匪本是地方民团的对头,为何二者能够“合作”?军队驻防本来更可以确保社会治安,为何地方民团不予支持,反与盗匪联合对付军队?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民初以来珠三角地区军队、民团、盗匪等武力的发展及其影响历史做一番探讨。
二、剿匪、捐税与军地矛盾
辛亥革命以后,在珠三角地区活动的军队名目繁多,派系分立,既有由外地进入广州地区的所谓“驻防军”,也包括改编的地方武装。因为剿匪和抽收捐税,各式军队与地方社会关系密切,成为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
清末民初珠三角地区匪患尤为严重,张之洞曾说:“粤省盗案之多,以南海、番禺、顺德三县尤为甚”。[28]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未能及时有效控制地方社会,会党势力抬头,民军遣散后重操旧业,“弄得珠三角一带,遍地皆匪”,当时就有“粤匪甲于他省,广属甚于外属”的说法。[29]为遏止匪患,新生的军政府别无他策,参照清末巡防营办法,将警卫军、陆军派驻各乡镇,沿用“清乡”旧法打击盗匪。②匪患越严重的地区,军队也就越多,在号称“盗风最炽”的顺德,“警卫军密布至十一营,此外尚有海军游击队来往巡缉”。[30]到1913年6月,全省警卫军(由民军和旧巡防营改编)有60余营的兵力,除南韶连绥靖处8营、高雷阳6营、潮梅2营、惠州8营及炮队1连、钦州3营、琼崖3营、肇庆4营、罗定3营外,其余23营分布于广州地区。[31]清乡剿匪意在维护社会秩序,然由于清乡军队素质低、纪律差,不少就是盗匪转换而来,军队“藉围捕为名,擅入民家,妄拘良善;并有藉词搜查军火,摄取财物;甚且侦探不确,辨别不清,每因一二之匪家,竟毁全村之民屋;更或本非真匪,误被拘牵,严鞫难堪,遂罹刑戮”,以致“闾里之民,既遭匪祸,又怨兵凶,一闻清乡兵至,相告失色,惊惶失措,畏兵之来甚于畏匪,而匪徒反得勾结扰乱,煽惑人心”。[32]清乡军队的骚扰甚至激起了民众的反抗,1912年11月,顺德县甘竹黄姓被清乡军队枪毙十多人,村民烧掉军队营房以为报复。[33]李福林带兵在番禺县高塘清乡时,村民“集众千余人,白旗招展,枪声隆隆,环向福军轰击”。[34]在革命政府时期,军地矛盾就已经出现。
龙济光据广东后,建立了一支以济军为骨干的庞大军队,到1914年2月底,粤省军队有118个营和两个连,还有数量不少的警备队、游击队、护沙警察、海军舰队等。[35]龙济光利用这些军队打击革命党人,“清乡”剿匪。《广州绥靖处清乡办事细则》规定,军队之布置,由“各委员会商水陆防营之上级军官,查明所属地方之重要,匪情之缓急,将军队分配驻扎,预备调用”。[36]军队纷纷进驻各地,如南海县金溪墟一带驳壳会匪横行,1913年10月应当地商人之请,当局“准令赵(定国)抽派军队前往驻扎”。[37]匪患相对严重的顺德县仍是“清乡”重点,军队密布,“驻扎军队地点,则以东马宁、甘竹等处军力最厚,赵定国则率警卫军驻于勒楼行营,黄连海口一带,有全属游击队勇船十余艘湾泊,清乡委员更饬随营之警卫军分扎各处隘口,以截匪去路”。[38]李福林统领的“福军”,系本地士兵,熟悉地方情形,被委以“清乡”重任,分调南海、顺德、番禺、新宁(今台山)、新会、赤溪(今届台山)、东莞、增城、新安(今属深圳)、龙门等县驻扎。[39]如此分散驻防,使得清乡军队与地方关系相当密切。尽管当局制定了所谓的“清乡暂行军律十二条”,约束军队,诸如“强卖强买,勒索商民者”、“开场聚赌收赌规者”、“擅执军械行凶伤人者”,均将枪毙处置。[40]但实际上,清乡军队违法乱纪、骚扰地方的事情不断发生,“纵勇殃民,最属惨事,营员犯此被控者,已数见不鲜”。[41]龙济光只好发布告示,呼吁防营顾全名誉。[42]新宁县清乡委员黄绍宽因“私招兵勇,藉捕抢掠、勒索”,激起民愤,“绅商指证,数逾千人”。[43]清乡扰民,成为军地矛盾焦点之一。
清乡扰民,也与军费有关。据广东财政厅统计,军费支出的比例一直很高,③政府无力承担。据1914年巡按使李国筠报告,当时“国家岁入仅得一千五百余万,而支出之数,共有二千六百余万之多,出入相衡,已不敷一千一百余万,其中支款最巨者,莫如陆海军费,年支一千九百余万,即将国家岁入全数拨出,所差尚在四百余万”。[44]因经费短缺,清乡军队借驻扎之机,搜刮地方财物,已是常事,甚至成为“清乡”的主要目的。紫金县绅商学界曾联禀当局,指责驻防军队,“均得规庇赌,置捕务而不理,以致迭生劫掳巨案,伤毙人命多名”。[45]南海县鳌溪团练局也反映,驻地营勇“坐收赌规,日入不菲,而于地方劫掳一事,从未闻破获一案,即白日匪党携枪,兵贼相遇,熟视无睹”。[46]在顺德县马岗乡,也曾发生过因军人“鱼肉商民”,蹂躏商场,抢劫财物,引起商民罢市的事件。[47]在龙济光的专制统治下,军队下乡剿匪进一步激化了军地矛盾。
1916年10月,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逼走龙济光,拥兵割据,建立了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阀武力。莫荣新接任广东督军后,将广东境内的军队编为五个军,除李福林、魏邦平两支广东军队外,在广东的桂军有40个团,约四万人。[48]1916年和1917年,每年军费支出约1300多万元;1918年和1919年,每年达2700余万元,超过了龙济光时期。④桂系军阀政府一面举借内外债,一面向百姓巧取豪夺,听任军队在各地包赌庇烟、敲诈勒索。1917年8月,驻省城滇军第四师因伙食费未发,“将西关新城一带防务经费,收归自办”。滇军第34团,“亦以伙食无所赔垫”,而将“老城各段赌博收归自办”,出现了各家赌馆“有滇军二人荷枪守卫,军容极为严厉”的景象。[49]军队驻乡搜掠之事,比比皆是。统领王得庆的军队在香山乾雾乡围击乡民,焚毁屋宇,引起公愤,商民强烈呼吁,“不加严惩,不足以对香山人也”。[50]军队越来越不受地方欢迎,台山县朱洞乡向称多盗,300多人的军队进驻后,令乡民供应伙食,并时取猪羊屠宰,乡民不得已,议定无论贫富,每户每日捐银一毫、米一升,“久之力有不逮,相机逃避”,后只好再出花红2000元,请军队移营别处。[51]抗拒军队的事情亦屡有发生,顺德县督办刘志陆派队前往古楼等乡围捕,被乡人抢夺枪支,“枪伤兵线,留押士兵多人”。[52]1918年底统领欧阳荣派队前往香山黄梁镇催收护沙款,村民“放枪拒抗,弹如雨下,无可退避”,附近村庄村民亦“四出放枪助击”。[53]
1923年初,滇桂联军入粤后也大肆侵扰地方。据丁文江记述:“当滇桂联军抵粤之初,民政长官皆去职,征收机关纷纷为军人所据,沈鸿英占盐署及造币厂,滇军占补抽厂、东西税厂、烟酒税、沙田清理官产各机关。继桂军以盐税无起色,造币厂不能开工,遂起而包开杂赌,继番摊。滇军踵起效尤,赌捐乃为军队所专利。孙文回粤,收回盐政。沈鸿英去北江,造币厂亦归财厅,然广三铁路又为蒋光亮所据。及徐绍桢为省长,杨西岩任财政厅谋收回征收机关,滇军不听命。徐、杨去职,廖仲恺、邹鲁继任,沙田官产陆续收回,然各厘税机关,则盘踞如故也。西江五邑财政,名属于厅,而人由防军荐任,款由防军截留,其实与占据等。”[54]有的军队还与盗匪“合作”强行征收捐税。军队为征收军费而争夺防地的事情常有发生,引起地方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在孙中山政府时期,军地矛盾也未能得到有效缓和。
“清乡”剿匪也是军队势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重要方式。自晚清以来,广东匪患积重难返,盗匪数量多,且呈分散活动的局面,机动性很高。所谓“清乡”剿匪往往是“兵来贼去,兵去贼来”。多数情况下,军队都以招抚来求暂时的安宁。由于政权不稳定,当权者很难给受抚的盗匪提供足够的生存条件,盗匪往往“贼性不改”,打着军队的旗号,肆无忌惮。军队则通过“收编”地方武力,在地方社会植入势力,并借助这些势力,达到抽收捐税、筹措军饷的目的。军队十分重视防地的占有,“军饷之丰绌,既视防地为准,各军皆不愿出征,攻城得地,则纵敌不追,从事敛聚,友军奉调,常阻止不使入境,入则冲突”。[55]军队敛聚必然侵蚀地方的利益,冲突不只限于军队与军队之间。由地主、旧绅、商人等乡村权势所控制的地方民团本身就有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职责和防盗的名义,所以,无论抽收捐税,还是招抚盗匪,军队在地方的活动对地方权势都形成了直接威胁。为争夺地方利益,军队与民团的冲突不可避免。如1914年7月,清乡营长捏报匪情,督兵围攻新会县罗坑乡团,夺走枪支,锁拿团丁,以图邀功。[56]1915年9月,佛山太平沙乡团则察控警察队有“诬赃夺艇”之事。[57]九江事件中,滇军与九江民团的冲突也是如此。
三、民团职能衍变与地方势力伸张
民团作为民间自卫武力,由地方社会应对盗匪问题的需要而促成。地方社会组建乡团、商团以及专业性的护沙队、护商队等自卫武力,其本意在于防盗自卫,通常都会标榜对其他事务不加干预。《南雄全县地方保卫团细则》中明确规定,“各团局于盗匪事件外不得滥行收受民词”。[58]1923年12月,粤省商团总公所向各分团发出的训令称:“本商团之设,原为实行自卫起见,如非本团职责范围之事,不应干预”,要求各团军“勿得逾越范围,以维军纪,而保声誉”。[59]1924年4月成立的“航商自卫队”也是“以捍卫航商来往,防御盗贼抢劫起见”。[60]
不可否认,各地乡团在防御盗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报纸上也常可见到此类消息,如:1924年9月,200余盗匪假冒军队持械进入顺德县豸浦乡劫掠,“乡团当即鸣锣闭闸,一面出赴迎头痛击”,避免了一场匪劫。[61]1924年,自陈炯明的军队占据东莞后,袁虾九、跛手忠、黄贵人初等股匪盘踞莞城及石龙等处,东莞各属乡团,“为保护桑梓防御盗贼起见,一致联合驱逐匪党”。[62]1924年9月,大帮沙匪围劫香山县下基,小榄商团出队抵御,相持一个多小时后,终将沙匪击退。[63]等等。
然而,由于政局动荡,政府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商团、乡团等的社会角色与作用发生了改变。有的民团成了土豪劣绅等小部分人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甚至与匪勾结,横霸一方,危害社会,乃至对抗政府。花县土豪劣绅大地主招集盗匪组成民团,藉清乡之名,肆意勒索,欺压民众,以致该县各界联合请愿,要求解散民团。[64]有的民团形同盗匪,或打着捕匪的旗号,行劫掠之事,或借保护之名,勒收行水。民初陈炯明就曾直言,各地民团有“招集匪类藉团滋扰”的现象,“入为乡团,出为劫匪,抢掳勒索,无所不至者,比比皆是”。[65]
民团苛抽的现象也不少见。由于民团经费自筹,有的由民间捐助,有的则由田亩分摊,为民团苛抽提供了机会。1915年12月,番禺沙湾联保局绅向巡按使禀报,香山县黄阁乡“藉团苛抽,每亩抽收团费八毫,其有不肯遵缴者,佃户即被锁禁”。[66]清远县咸泰乡民团局“创设田亩捐,每亩多至一元,专向业主剥削”。[67]番禺县新爵乡民团向农民勒抽所谓的“禾更谷捐”,一有迟缓,动辄罚款,罚款不应,则率团丁放火烧谷。[68]顺德县民团总局曾因向城厢内外各当按押店征收年捐,引起行业罢市反对。[69]由于可以藉团抽捐,乡团某种意义上变成地主豪绅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
民团也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军事斗争。在讨伐陈炯明的战事中,东莞县石龙附近村民,不仅为孙中山的军队“代办米菜各项”,且直接支援战斗,“冲入陈军阵地,将其驱逐”。[70]而在袁带响应陈炯明占领香山县,进攻顺德县的行动中,也有民团附和,以致汪精卫电令在香山的福军“严惩附逆民团”。[71]无论民团卷入各派军事斗争的具体原因何在,民团的这些动向,意味着地方自卫武力的职能业已改变,民团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纷争中的一股力量。
民团成为地方权势与官方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后,直接助长了地方势力的膨胀,有时甚至发展到与政府政治对抗的地步,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就是典型的事例。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事变的导火线是“扣械风波”。而所谓的“扣械风波”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其内在原因比较复杂。⑤本是民间防盗自卫武力的商团,缘何要公开反叛政府?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商团势力已经对政府权力构成威胁。随着商团力量的发展,商团不再是单纯的民间防盗自卫武装团体,已演变为商人上层争取权力的工具。应该说,在商团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保持了商人自卫本色,不甚介入政治,在各种政治斗争中也大体保持中立。早在1911年筹划设立商团之初,岑伯著、陈廉伯等人就认为,办商团是为了一旦政治变动,商人可以自卫,免受政潮牵累。[72]1915年,因有个别人“参与政治风潮”,粤商团军还特致书团长岑伯著,要求岑团长再三告戒团友,“须遵守团规,尊重法律,凡商团范围外之事,不宜参预,免招物议,而保名誉”。[73]陈廉伯接任团长后,情况明显改变。1919年3月,陈廉伯于就职宣言中立定了所谓的“四大宗旨”,强调商团的独立性及表示要扩大商团的决心。[74]商团职能不再囿于“防盗”。1923年,孙中山依靠滇桂等外省军队驱除陈炯明,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孙中山缺乏对这些军队的约束力,留驻广州的“客军”不断与商民发生冲突、摩擦,商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3年初,滇军刚进入广州,就因包赌同商团发生冲突。[75]1924年春节,因使用军用手票,“商团与湘、滇、粤、桂各军滋闹事件,实有七八起之多”。[76]在与军队的交涉中,商团有时态度相当强硬。[77]4月,湘军借口搜查军火,拘捕了一名商团团员,引发冲突。商团不仅发表通电,要求禁止军队擅行查捕,而且借湘军的申明,通令全城商团,拿办“藉名敲诈”的军队。[78]对于广大商民来说,不法军队的骚扰与盗贼的危害也许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各派军队毕竟不同于盗贼,它在很大意义上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商团与军队的冲突,虽也有出于保护商民财产及经营活动的需要,却同时为商团活动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商团自卫不再远避政治。商团的政治野心也日渐凸显,1924年5月,全省商团在广州成立联防总部,“主持全省各埠之商团军之命令统率事项”,“对于各属分团来往函件,均袭取政府公文程式,发号施令,商团总部不啻一中央政府机关”,[79]无异于另外一个权力中心。
事实上,后来,商团介入政治斗争态势也越来越明显。国民党改组时,商团攻击孙中山的农工政策是“挑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恶感来坐收渔人之利”;制造“广州共产在即”的谣言;还与工会、工团为敌,到处围困工会,捕杀工人,摧残工人运动,走上了“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军阀相勾结,直接阻止国民革命之进行”的道路。⑥1924年以后,随着商人对孙中山与国民党“共产”的疑惧,与对客军及政府税收政策的不满,部分商人上层企图建立“商人政府”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⑦广州商团助长了商人权势,孙中山就认为,商团事件是陈廉伯“欲藉商团之力,以倾覆政府,而步意国墨素连呢之后尘”。[80]商团叛乱,实质上是商人上层利用商团与政府政治对抗的一场较量。显然,在这场冲突中,广州商团发挥的作用与其早期一贯标榜的不涉政治、专意防盗的立场相去甚远。
四、盗匪权势的形成
晚清以后,广东匪患日益严重。珠三角地区的盗匪利用邻近港澳的地理优势,获得了大量武器,成为一类颇具实力的地方武力。⑧盗匪武力很大程度上是非法分子夺取财物的一种工具,因其反社会性而不为正常社会所接受与认同,被排斥于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之外,远离社会的权力中心,甚至活动于偏僻的区域。民国以后,由于政局动荡不安,政府控制力衰微,社会危机加重,广东盗匪势力不断在地方社会伸张。
首先,连年不断的战争扩大了兵匪对流,为盗匪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民初军政府遣散民军后,盗匪仍有大量“由匪而兵”的机会。龙济光掌权时,推行所谓的“剿抚兼施”的政策,不少盗匪乘机摇身变为军队,却贼性不改,亦兵亦匪,“横行无忌,劫收行水,更甚于前”。[81]军阀争夺中,不少盗匪绿林分子又被各方招纳为“兵”,充当战斗队。民国初年广东纷乱的局面中,盗匪大受“青睐”。龙济光被驱出广东后,不甘心失败,“乃因敌陆莫而引贼以自用”,四处招抚盗匪,扩充力量。[82]孙中山南下护法,革命党人组织军队的主要手段也仍然是发动民军,运动绿林。入粤的客军也招匪扩军。1924年有人就感慨而言:“今之欲扩军力,以招民军者多矣!”[83]同时,不少战败失势的军队又溃散为匪。1925年的报纸说,“粤省因频年战争,溃兵散卒,流为贼匪,以致群盗如毛,各乡人民居无宁处,河道梗塞,商旅裹足,农辍于野,商罢于市,匪氛之炽,迄今日而已极”。[84]
“兵匪混杂难分”给盗匪提供了合法外衣,盗匪竞相打着“军队”旗号公开活动。1924年南海县长李宝祥向广东省长公署报告称:“粤省自民国以来,迭次军兴,匪徒均乘机而起,军队每藉收编匪徒以增实力,匪徒则假藉军籍以为护符,聚则高悬军队旗帜,散则佩带军籍襟章,名虽受编,实别为匪,公然挟械横行,打单掳掠,寻仇报复,卖烟开赌,为所欲为,遇有缓急,不听调遣。团警见之,兵匪莫辨,不敢过问,若因围捕擒获或枪毙,则军队又复为之出头干涉,或函请提释,或强索抚恤,匪徒有恃无恐,益无顾忌”。[85]兵匪对流将广东盗匪卷入社会生活的主流,使之接近地方政治斗争,趋向“中心”,“彼辈始得藉军队为护符,结队愈大,其势愈凶,初则啸聚于乡镇,继而纵横于都会,司令统领,滥竽武职,手枪短剑,朋比歹类”。[86]
其次,社会危机加重,地方藉匪自救,盗匪借以跻身社会权力体系。直到20年代末,广东警政建设仍没有明显的成效。1928年民政厅调查全省警务状况时发现,受多年政局动荡的影响,全省警务“日形衰落”。[87]民初治盗仍然主要寄望于军队的清剿。而实际上军队也无法保护地方社会。时人批评说:“政府向来最大错误的一种见解,每凡剿匪都依赖巡防营式的军队。”[88]前文已及,军队骚扰地方,勾结盗匪之事,常有发生。至于军队在各地横行不法,强索强夺,包赌截税等种种骚扰,更是屡见不鲜。[89]
政府不能给地方社会以治安的保障与信心,地方社会转向寻求其他的出路。除了组织地方民团等自卫武装外,不少地方为保全局部利益,依匪自卫,以盗匪充当民团。据曾亲身组织民军工作的陆丹林说,“乡团的管带,他们的出身十之五是土豪流氓,十之五是投降匪首”,与附近的盗匪也“声气相通”。[90]地方势力勾结盗匪,助长了盗匪势力的发展。时人指出:“这几年来,乡人以军队之搜刮惨酷过于土匪,安份的宁纳贡给土匪,请求保护,再不敢领军队的教。土匪乃代军队而兴,以维持一地之秩序;不安份的便趁势入伙,而土匪声势遂日益浩大蔓延”。[91]
民初广东盗匪不再是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盗匪武力俨然衍变为可以控制和干预地方,甚至与官方对峙的一种特殊地方权势。盗匪凭借武力对顺之者保护,逆之者惩罚,在地方形成了小范围的武力割据,盗匪集团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地方权力机构。新会著匪胡须浓因崖西仙洞乡民募勇防卫而对之“封锁”,实施公开的“惩罚”,完全不怕政府、军队、乡团。[92]东莞县道滘著匪刘伦则以改组民团的方式扩张势力,控制地方,“其法先推广村乡,入其党羽,入党羽后,代其改组民团,以便调遣”,结果使“自皇[篁]村以上,河田以下,尽入刘伦范围之内”。[93]从上述九江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著匪吴三镜“被举民团长之后,野心大炽,招集附近悍匪雷公全、何柏、张歪嘴裕等数百人,编为团丁”,且私制枪械,扩张羽翼,建筑堡垒,挖掘壕沟,成为九江的地方实际控制力量。[94]政府的征税权也有落入盗匪之手的。因为盗匪与土豪勾结,政府在中山县沙田区征收的沙捐、特别军费,都通过沙匪实行。[95]
盗匪甚至公然向“合法”权力挑战。1926年的报纸称,顺德县内的盗匪,“纠党竖旗,拦河截劫,公然与官军对抗”。[96]番禺县属茭塘一带是著匪黄贵人初、黄济军泰兄弟的“势力范围”。1924年6月黄贵人初竟然纠党数百人将东江剿匪司令徐树荣的部队包围,“意图缴械”,枪伤官兵,并逼走了官军。[97]1927年初,当番禺县长部署各乡建筑炮楼、购置巡舰,筹办自卫时,盗匪“力谋破坏”,纠合袁虾九、跛手忠等各股悍匪数百人,“由茭塘乡分乘轮船匪艇运载巨炮,并机关枪二十余挺,突向冈尾社现有县兵驻防之明经乡袭击,分数路扑攻入村”,[98]公开与官方争夺地方的控制权。盗匪并不真正具有原始的政治动机,其反抗社会与政府的行为,更多的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救形式”。[99]其躲避官方的追捕与抗拒进剿,也是“求生存”的表现。然而,盗匪公然向“合法”权力挑战则超出了上述两种理解的含义,体现了盗匪以一种地方势力而存在的姿态。因而,有人说,民国初期广东土匪“恃有枪械,鱼肉人民,横行于乡村间,且代清代之绅士而称霸”。[100]在很多地方,盗匪成了实际上的控制力量,“弄到匪区简直是别有政府,保护往来是土匪,保护开耕是土匪”。[101]广东土匪成为了“第二政府”。[102]
五、简单的结论
通过上述的历史考察,结合九江事件,我们可以简单地回应前文所提到的问题。
首先,民团的发展已经不再固守初始的“防盗”之唯一职责,民团衍变为地方势力维护与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当军队可能攘夺地方社会的权利时,就与民团成为了矛盾的两端。当双方利益分割的要求不能协调时,矛盾必然激化,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特殊的时代背景,促成了广东盗匪成为地方势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广东盗匪拥有大量武器,是其他势力都想争取利用的武力。共同的利益需求,可以形成“兵匪一家”的局面,也可能促成民团与盗匪的“合作”。对盗匪而言,与既有权势的“合作”是其从边缘趋于中心,分享地方社会权势的有效途径,所以盗匪不是真正的“反叛者”。
与1920年代后期发生的农团冲突不同,军团冲突反映的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各种权势争夺地方利益的矛盾爆发。这种矛盾并不具有某种天然因子,而是各种势力生成、衍变的后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武力。民团因为拥有武力,可以成为地方权势,盗匪依靠手中的武器,也能够分割地方权势。军队恃持武力,也力图控制地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此种局面体现了民国初期地方武力化所造成的地方控制权分散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民团代表着地方势力,军队则可以视作官方或是企图控制社会的某种政治势力的工具。民团与军队的冲突内含着地方势力向政府权力挑战的意义,反映出民初地方势力的伸张与政府控制力的弱化。1920年代珠三角地区军团冲突为理解民初军阀政治提供了一个地方性视角。
注释:
①关于民初广东民团的研究,可参见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民团》(《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②参见邱捷《1912-1913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军政府清乡》,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③1913年7月至1914年6月,占70.1%;1914年7月至1915年6月,占54.4%;1915年7月至1916年6月,占46.9%。引自余炎光、陈福霖主编《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42页。
④转引自余炎光、陈福霖主编《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棠》,97页。
⑤关于商团事变的原因,学界从不同角度做了专门的探讨。参见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邱捷教授认为,即使没有扣械事件,政府也会找出其他理由解决商团问题,而商团和广州商界也会因别的借口同广东政府发生严重对抗(《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63页)。
⑥转自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85-186页。
⑦时任商会会长兼商团团长的陈廉伯有政治野心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有人就说:“有钱、有人、有枪,陈廉伯起了野心,是可以理解的”。《工商界老人回忆商团事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1963年),49页。
⑧有关民初广东盗匪的武器情况,可参见邱捷、何文平《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