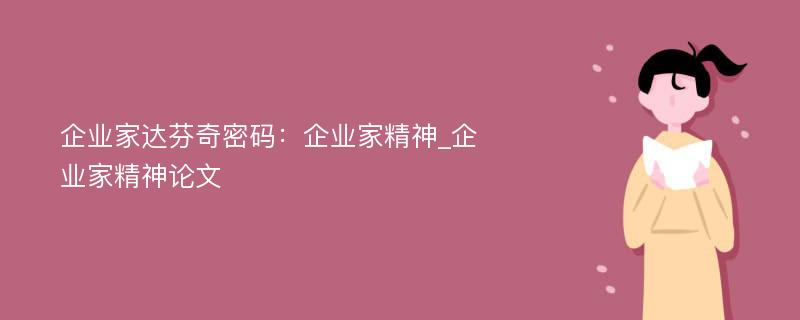
企业家的达芬奇密码:企业家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达芬奇论文,密码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世界万物看来杂乱无章,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每一种美德也必然会得到适当的报答,得到最能鼓励它、促进它的那种补偿;而且结果也确实如此,只有各种异常情况同时发生才会使人们的期望落空。什么是鼓励勤劳、节俭、谨慎的最恰当的报答呢?在每项事业中获得成功。这些美德是不是有可能在整个一生中始终得不到报答呢?财富和人们的尊敬是对这些美德的恰如其分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它们是不大可能得不到的。什么报答最能促使人们做到诚实、公正和仁慈呢?我们周围那些人的信任、尊重和敬爱。许多人并不追求显赫地位,但是希望受人敬爱。诚实和公正的人不会因得到财富而欣喜,他感到欣喜的是被人信赖和信任,这是那些美德通常会得到的补偿。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企业家精神描述的是企业家的一种特有的气质,它能够使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创新跨越企业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障碍。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是企业家对组织成长的持久不断的渴望以及所具备的随需应变的能力。正是这种渴望使得企业家不断追求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而随需应变的能力则帮助企业家敏锐地把握市场的脉搏,并迅速在通过管理和创新推出最适应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生存壮大的一幅惊险刺激的图景。
真正的企业家赚钱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业的保障,其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境界——能够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并对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如宗教般坚定追求。
天福茶庄的老板、闽籍台商李瑞河,经营茶叶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心迷上茶文化,一心只想回报桑梓,不辞劳苦,终于在云南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一种梦寐以求的原始野茶树,证明了茶的原产地是中国,而不是国际上有人说的茶叶产自印度。据说,李瑞河当时对着这棵2700年树龄的野茶树顶礼膜拜老泪纵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李瑞河还在福建老家漳浦建造了全国最大的茶博物馆,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这个茶商的境界,已不是经营茶叶赚钱,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茶叶是他的一切,茶叶是神,是一种宗教。
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终生都在研制、改进、生产、销售感光胶片,赚的钱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按理说他应该很满足了,但他觉得自己追求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感光胶片事业上的完美。到了晚年,当感到自己的事业再也无法突破时,他采取跳海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典型的企业家。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窥探到一个真正企业家的内心世界,那种对理想如痴如狂的追求。
当代中国企业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企业处于埋藏状况:2008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23家企业,很少有人知道其企业家是谁。由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中国企业家的能力难以得到应有的提升,甚至导致阻碍与削弱。而中国未来如果没有自己的摩根、罗斯柴尔德,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吴春波教授指出:“遍寻中国企业,除了那些大型或特大型、以各式垄断而‘出名’的国有企业外,我们很难找到一家以企业家精神为统领,依靠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真正做大、做强的中国企业。……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虽然有了为数不少‘国’字头的世界500强,但还没有一家被国际承认的世界级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按照欧美、日本人的经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三十年足够了;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群体’,六十年亦足矣。”
我们紧抱《国富论》,却抛开了《道德情操论》
商业社会需要有商业社会的信仰。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智慧横无边际,决非人的世俗胸量与一般经验所能包容。一切文化传统的生机,无不首先表现为破除现实迷雾,涤荡现实尘沙,烛照现实误区。只想在传统中寻找身心的归宿,却不想让它及早归正现实的言行、风气与力量,传统便只是一个幌子,于人于世毫无益处。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一个精神萎靡的民族无法实现现代化。多少年来,中国西部成了一个落后的代名词。即使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东部渐入改革与发展佳境的今天,西部却仍然在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浓厚的封闭氛围中酣睡。企业家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主体。尽管我们坚信西部的企业家个人与自我同样具有无穷大的潜力,但在长期的农耕社会秩序和经济文化的压抑与麻醉下,其企业家精神被掩盖到了无意识的最底层,似乎连西部企业家自己都感觉不到了。在现实的中国西部大开发中,西部人太需要拥有这种能够给予他们足够自信和创造力的精神力量了。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的危机既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政治哲学的危机,即“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义的或者好的或者最好的社会秩序”。西方的危机同样也是东方的危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是由于我们的精神观念一直都没有改造过。改革需要从表层的日常生活、中间层的制度、深层的精神观念一起进行操作。其联结点可能还是产权和道德问题。我们喜欢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带来的物质享受,但是我们没有体会到他为什么要提倡“道德”。我们紧抱着《国富论》,却抛开了《道德情操论》。
道不通,则术不行
《德鲁克日志》在论述“精神的价值”时指出:“人绝不仅仅是生物生理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更是一种精神存在。”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只有同情能够拯救认知,我所担负的无以言传的责任的认知,是对精神的认知。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价值的回归,——并不是说要抛弃所有物质的东西,而是为了使物质充分创造价值。”
企业家是谁?从何而来?因何而来?要到哪里去?为何而去?如果将企业家能力喻为“术”,则企业家精神应是“道”。道不通,则术不行。
企业并不仅仅是个利润的实体,它首先得是一个精神的载体。一个伟大的公司的必要条件,是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家精神主导的独特的管理模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受到这种哲学的主宰。无论一个人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事业成功的真正本质经常不在于其技术方面,而在于他所拥有的哲学思想。在企业家身上,这种哲学思想便为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内涵。企业家不仅要在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方面起到火车头一样的作用,还要以自己的精神为社会塑造一种气质。
一个缺乏积极企业家精神的人,即使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可能将其内在的潜能变为创造社会价值的实际能力;不仅如此,还有可能利用其“才能”对企业、对社会价值的创造产生负作用,甚至是巨大的破坏作用。反之,一个具有忠诚、守信、责任感等精神素养的人,即使是力量弱小、天赋不强的人,也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原文标题:解开企业家的达·芬奇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