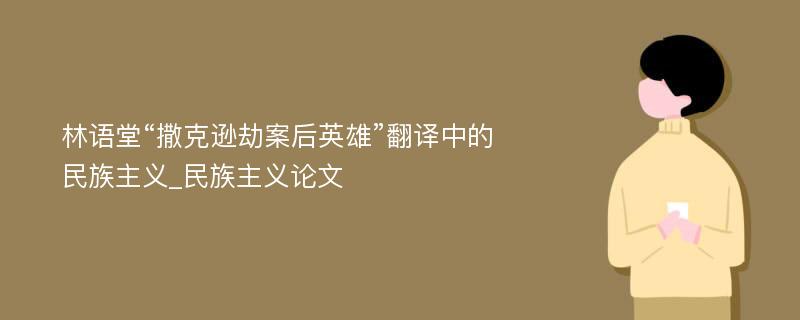
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的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撒克逊论文,民族主义论文,英雄论文,林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动力,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从其广度、韧性、变化来说,民族现象主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①虽然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学界的热点,在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领域备受关注,但什么是民族,如何给民族一个确切的定义却仍旧未有定论。盖尔纳提出了民族的两个定义,其一是“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其二是“根据共同的成员资格而坚定地承认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②后者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 吉登斯指出:“民族—国家只存在于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体系性关系之中”,③民族—国家诞生之时,国际关系也就开始了。近代中国被强行拉入这个“体系性关系”当中,从自居中心的天朝大国到任人欺凌、宰割,中国有志之士很快敏感地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意识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抵御外侮中的迫切性。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或绍介西方民族理论,或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掀起了了“民族”热潮,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此同时,小说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位移,成为“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司各特的民族“中间道路” 从词源来看,“nation”一词在古罗马时期意指“因出生地结合而成的一帮外国人”,后来具有了由出身决定的共同体以及有着相同意见和意图的群体。到13世纪又有了“文化与政治权威的代表”的含义。16世纪初的英格兰,民族被用来指英格兰的全体居民,“这一语义变更标志着在我们今日所理解的该词的意义上,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出现了,并且它还开启了民族主义的时代。”④“nation”与“people”具有相同的意义,而同一民族不同阶层的居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nation”后来意指“全体居民”,自然而然与国家相关联,并演化出“主权人民”的意思,这样便与政治、族裔联系起来。“主权在民并且承认各个阶层在根本上的平等,这构成了现代民族观念的本质”。⑤ 英国早期的民族主义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伊丽莎白女王成为“新教徒与民族事业之间联系与统一的象征”。⑥19世纪初期的欧洲,在经历了拿破仑铁骑威胁之后,所有民族“或是本能地或是有意识地,都在从本民族的生活源泉中汲取使自身重新振作起来的活力。”⑦民族意识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各个民族的作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民族历史、风俗以及神话传说的建构当中。在司各特生活的年代,统一的英国民族身份开始形成。“英格兰民族意识准确地说存在了5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但有争议的是,19世纪它消失了,融入一个英国民族意识之中,英格兰人倾向于认为这种民族意识适合于自己的属性。许多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也接受了这种英国民族意识,但也有一些人仍然认为自己属于苏格兰民族或者威尔士民族,但他们共同拥有对英国国家和英国帝国的忠诚。”⑧司各特便是如此,他坚信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苏格兰人”⑨,但同时又对英国王室一片忠心。他的作品深深根植于苏格兰文化中,景色奇丽的苏格兰高地为司各特提供了发思古之幽情、倾诉民族情感的绝佳场域。借助历史,阐发对民族问题,尤其是苏格兰与英国双重的民族性的思考在《艾凡赫》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艾凡赫》有三对主要矛盾:撒克逊人与诺曼人之间的矛盾、“狮心王”查理与其弟约翰亲王之间的矛盾以及塞德里克与艾凡赫父子之间的矛盾。其中,撒克逊人与诺曼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小说的核心矛盾,其他两对矛盾均为民族矛盾的解决而设置。小说主要由三个主要情节构成:比武大赛、城堡争夺战以及蕊贝卡会审。如果说比武大赛揭开了民族矛盾的序幕的话,精彩纷呈的城堡争夺战则是民族矛盾的完全展开:诺曼贵族掳走了塞德里克一家,绿林好汉在查理王与罗宾汉的带领下攻破了城堡,大败诺曼贵族。最后一个场景则为民族和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小说中的民族矛盾折射了司各特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对苏格兰民族身份的坚守与对英国身份的认同相互纠缠,促使他想到了中世纪诺曼征服之后诺曼人与撒克逊人之间存在着类似的矛盾。卢卡契认为司各特“企图揣摩英国整个历史的发展,来为自己在两个相互敌对的力量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他高兴地发现,英国历史中最动荡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平息下来,转到一条光荣的‘中间道路’上。正是这样,在撒克逊人和诺曼人的斗争中产生了既非撒克逊族也非诺曼族的英国民族;在血腥的玫瑰战争以后,也同样产生了都锗王朝、特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盛世”。⑩卢卡契准确地指出了司各特的在这部小说中的核心思想:只有民族融合才是民族问题解决的必由之路。 二、从race到“国” 1905年,林纾翻译了Ivanhoe,将其更名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部译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自初版后,先后编入“说部丛书”初集、“林译小说丛书”、“万有文库”以及“新中学文库”等丛书。凌昌言指出:“司各特是我们认识西洋文学的第一步;而他的介绍进步,其对于近世文化的意义,是决不下于《天演论》和《原富》的。”(11)郭沫若也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对其后来的文学倾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2) 林纾为什么要翻译这部小说?译成之后何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小说的艺术特色显然一个重要原因,林纾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发现了小说与古文相通的地方,并指出此书结构“变幻离合,令读者若历十余年之久”,语言符合人物身份,“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语,肖盗贼也;述顽固语,肖顽固也”。(13) 但是如果考虑到林纾将书名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再对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加以考察,此部译作的成功恐怕另有原因。书名的改译对后来的译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谢煌的同名译本,到施蛰存的《劫后英雄》,再到陈原的《劫后英雄记》等均受到林译的影响。虽有论者认为“书名《艾凡赫》就未必比《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更好”(14),但改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减弱了艾凡赫作为中心人物来联结敌对双方、串联结构的重要性。“撒克逊劫后”点明了主题,将民族矛盾推到前台。固然这样改动不违原旨,民族矛盾确实是小说的核心问题,但林纾将其明确化,说明了林纾对民族问题的重视与迫切。“英雄略”的语义范围更广,其所指不仅仅是艾凡赫一人,而是书中所有的英雄。 在序言中也可以看到林纾对于民族问题的关注。在林纾心目中的“八妙”中,有“两妙”提到了民族—国家。其一是对犹太人被迫害的感叹:“犹太人之寓欧,较幕乌为危,顾乃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国为何物。此书果令黄种人读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此又一妙也。”其二是对撒克逊人无法完成复国大业的感慨:“今书中叙撒克逊王孙,乃嗜炙慕色,形如土偶,遂令垂老亡国之英雄,激发其哀历之音。愚智互形,姸娸对待,令人悲笑交作,此又一妙也。”(15) 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是林纾早期译作,在林译小说中属上乘之作,茅盾曾与郑振铎讲过:“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16)在这个“意译为风尚”的时代,林译确能够较为忠实地传译原作,韩南甚至称林纾为“保存派”(17)。但如果对原文与译文详加辨析,就会发现林译中也隐藏着不少改译。其中一些改译就与民族主义相关。 小说开端交代了故事的背景:“李却第一已为四世,而土著之人与脑门豆人(即惠连种人)犹同水火,语言既异,而脑门豆人复自居为贵种。而土著心痛亡国,至于切齿。顾国权已归脑门豆种人,复用大力抑制土著之人,先畴私产,悉夺而有之,素封者悉跻贫户。”(18)与原文相比,林译的变动很小,基本译出了主要信息。但将“while the other groaned underall the consequences of defeat”(P.30)译作“而土著心痛亡国,至于切齿”,则与原文有所出入。原文只是强调战败,在翻译中成为了“亡国”。其后诺曼贵族所拥有的“power”也译作“国权”。原文中这一段话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那就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林译在此处的创造性叛逆同样为整部译作的改译奠定了基调,那便是不断提及原文中没有的“国仇”。 猪倌葛尔兹与汪巴之间的对话在译文中也被注入了国家的元素。“今亡国之余,凡诸物产悉归法人掌握,唯此区区空气属我辈耳。”(P.8-9)其中“亡国之余”为原文所无。诺曼贵族一方的艾梅向布里昂描述塞德里克:“弟识之,此老国仇心笃,疾视我辈,而又不畏强御。……自言为绿林喜德华子孙,以侠为命,与脑门豆世仇也。凡人恒讳其籍贯,不为撒克逊人;彼独沾沾自喜,未尝隐其族氏。”(P.14)原文中塞德里克在敌对势力眼里傲慢、凶狠,仇视诺曼贵族。林译过滤了其中的贬抑之语,即便在敌人口中也成了一个爱国英雄的形象:“国仇心笃”“不畏强御”,这体现了译者急于让爱国英雄出场的心态。 化解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内容,而矛盾得以解决的关键人物是狮心王查理。身为诺曼贵族,查理理应站在撒克逊人的对立面,但约翰亲王一方面勾结国外势力,意图篡位,一方面实施暴政,使诺曼人与撒克逊人之间的矛盾更为激化。查理回国之后,为夺回王权,势必与约翰展开斗争,这样便与撒克逊人有了共同的目标。虽然查理在两个民族中都有极高的威望,但因为儿子追随查理与儿子断绝关系的塞德里克,是如何转变对于查理的态度,并最终臣服于查理的呢?在比武结束之后的宴会上,约翰要求塞德里克为一个诺曼人干一杯酒,塞德里克怒气冲冲地说:“王命我举脑门豆人为臣所心服者,此亦大难。其事似力制其奴,颂其主人盛德者。须知亡国之俘,心怀故君,已不胜其悲梗,乃复令反颜颂其胜己之人,今日之事,宁毋类是?然大王有命,老臣胡敢不言。臣意中之人,在彼种类中极善战,地望亦高,亦其族中有人心、有天良者,老臣今日之饮,为狮心李却王寿也。”(P.74)这段话的翻译中,林译有两处地方的改译值得玩味。其一是增译了“亡国之俘,心怀故君”一句。撒克逊人固然被来自欧洲大陆的诺曼人所征服,但其时已经过了四代人,矛盾有之,仇恨有之,但自称“亡国之俘”,还是有夸大之意,虽然塞德里克冀望于罗文娜与阿泽尔斯坦结合,以有义举之旗帜,但“心怀故君”却是原文所无。其二是塞德里克对于查理王看法与态度在译文中有所不同。原文中塞德里克敬佩查理王的显赫武功和极高的声望,但在译文中,却增加了“有人心,有天良者”一句。林译加深了诺曼人与撒克逊人之间的矛盾与仇恨,将民族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国家层面,但国仇兼家恨化解起来更为困难,所以此处的改译就不难理解了:查理不仅有战功,有地位,而且有人心,有天良。如是,查理就是一个值得追随的良主,从而为塞德里克日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艾凡赫救出蕊贝卡之后,查理随后而至,放逐了圣殿骑士团,此时“群众现在才对着离开比武场的队伍,发出了微弱的呐喊,像一只胆小的狗,直等它所仇恨的人转身走开之后,才开始吠叫”(19)。林译将这句话译为:“百姓见太姆不拉人行尽,亦一一归心于李却。”(P.228)查理复位之后,以塞德里克为首的撒克逊人不再反抗,他们知道无法推翻查理的统治,但查理的缺点——对于朝政漫不经心,“时而宽仁放任,时而又近乎暴戾”(P.455)——在林译中却不见踪影。就这样,查理的形象在林译中完成了一个转变,成为了有天良、有仁义、得人心的君主。只有这样的国王才能消弭撒克逊人在林译中更为深重的国仇家恨。 艾凡赫的行为在林译中也许难以解释。因为追随查理,艾凡赫遭到塞德里克的放逐,在林译中也被父亲怒称为“忘国仇”的“逆子”(P.86-87)。如此激烈的父子矛盾如何化解?译者如何理解艾凡赫的行为?艾凡赫与蕊贝卡在诺曼贵族城堡中被困,蕊贝卡给艾凡赫描述战况,艾凡赫说为了荣誉一切都可以牺牲,蕊贝卡却说为了虚名,牺牲的是家庭、情爱与幸福,艾凡赫反驳道:“女郎止,汝何知英雄行状?天下人品之贵贱,即分别于此。国仇在胸,不报岂复男子!汝奈何以冷水沃此嚼火?我辈即凭此好名好勇之心,以保全吾爱国之素志,或不至于无耻。汝非基督教人,故愧心不炽;若吾基督教人见人战胜,则以为至荣。我实告汝,凡人畜有此心,则报国仇,诛暴君,复自由,均恃此耳。”(P.149)原文中,艾凡赫慷慨激昂地将以获得荣誉为最高目标的骑士精神称为高尚的感情,这种情感可以使人战胜困难,能够激励骑士去为他人申冤、抵制专制、保护自由。林译完全改写了这一段话,将核心语词“chivalry”置换为“英雄”,对骑士精神的诠释也成了对英雄的理解:英雄行状首要便是爱国、报国仇。在短短的一段话,原文没有的“国”提到三次。林纾如此改译,或许是未能理解中世纪的骑士文化,属无意误译,但在无意误译中,又有明显的改写意图,林纾找到了对于艾凡赫背叛行为的合理解释,那就是艾凡赫的行为同样是爱国,只不过对爱国与其父有不同的理解,选取了不同的爱国的方式。塞德里克爱的是撒克逊民族,试图复的是撒克逊的民族国家,艾凡赫爱的是“仁义”的君主统治下的结合了诺曼与撒克逊两个民族的国家,报国仇的目标指向的是窃取国家的约翰亲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林纾的改译明显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司各特在谈到两个民族时使用的词是“race”,这个词显然没有建立在种族差异基础上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内涵。既然没有使用“nation”,也就没有“nation”以个人权利与义务为基础的政治涵义。在林译中,几乎所有的“race”都翻译为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的“国”,显然是译者的一种自我折射。虽然司各特时代的欧洲因为拿破仑的存在,民族国家的意识得以加强,但对英国来说,拿破仑未入侵本土,外部威胁并不大,所以司各特主要思考的问题还只是国内各民族的融合问题。对于林纾来说,则有灭国亡种之虞,种(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有研究者指出:“‘国’和‘种’在成组的短语如‘爱种爱国’或‘国界种界’中经常并置,这也对将种族的建构整合进民族主义的观点做出了贡献。正如一个民族主义者所解释的,‘国’不仅是一种地理表达,还有着种族的意蕴。严复甚至公开宣称‘爱国之情根于种性’。”(20)爱国显然比爱族有着更为强烈的情感表达,林译将“race”译成“国”就不难理解了。在翻译中,林纾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剧,从而也加剧了他弥合两者矛盾的难度。因此他不得不通过对查理王、艾凡赫等人加以改写,为两个民族归于和好进行铺垫。查理王不仅武功显赫,而且深得民心,艾凡赫的骑士形象被置换为爱国的英雄,这样,父子矛盾的解决顺理成章,民族矛盾的化解也不至于显得突兀。 三、清末民初关于民族问题的论争 从读者反应同样可以看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成功确与其涉及民族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周作人曾经回忆:“使得我们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21)晚清学者孙宝瑄1906年读完此书后,在日记写下四首组诗,其中的两首为:“秋风禾黍太萧瑟,日夕牛羊欲下来。蠢尔何知亡国愤,黄金将尽不胜哀。”“河山黯黯百年仇,老去悲吟涕未收。可叹王孙空乞食,中兴心事付东流。”(22) 中国历史上不乏民族纷争,甚至异族入侵,但与国家与主权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意义的民族还是诞生于近代。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23)在列文森看来,天下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的概念,包括文化与道德在内的整个价值体系都属于天下,而国是一个权力体,不仅意味着土地和人民,而且还包括对土地和人民所提供的武力保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说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24)作为政治体的国家是暂时的,而作为价值体系的天下却是永恒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为中华民族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预设性的认知框架,诸如权力的神圣性、道德的绝对性、秩序的天然性等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基本命题都由此生发出来。”(25)在空间上,认为天圆地方,华夏族生活在大地的中心,四周则是蛮夷之地。感化四周的蛮夷之地是文明华夏的使命。因此,罗志田指出:“内外观念、中央四方论,以及夷夏之辨观念是构成古人天下中国观的基础理论。”(26) 这种秩序和观念在近代遭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之后,逐渐消融、崩塌,在以武力殖民为特征的全球化早期,中国被抛入到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当中来,中国人不会再以为其他国家不过是身处边缘的蛮夷。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士人面对西方的态度从“夷学”到“西学”,再到“新学”,不仅不再自居中心,反而甘于承认自身无论在器物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的落后,不仅意识到要以西学为用,而且认识到“中学不能为体”(27)。从中心滑落到边缘,天下观自然也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便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民族主义。 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酝酿,民族意识与情绪逐渐加强并走向成熟,在梁启超笔下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表达。1901年,梁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民族、国家思想。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认为国家思想经历了从帝国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民族帝国主义的变迁。在西方,民族主义兴盛于19世纪,目前向民族帝国主义过渡,而中国则处于由帝国主义向民族主义过渡的阶段。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主义最为关键,“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脑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英雄哉,当如是也!国民哉,当如是也!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28)故而,中国应“速养”民族主义以抵制帝国民族主义。 1903年梁启超出访北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29)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思考也日臻成熟。他对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家的理论加以绍介,指出民族特征与地域、血统、体型、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生计相关,而国家则有赖于具备“人格”与“法团”的国民的形成。民族可以大于国家,也可以小于国家。联系到中国,梁提出了“大民族主义”的概念:“由此言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30)中国的问题是反对独裁政府,而不是排满,排满可以作为鼓舞之手段,而不是最终之目的。合汉、满、蒙、回、苗等组合成一个大民族,“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才会让有志之士所同心醉。 晚清政府对外昏庸无能,丧权辱国,对内在改革中不愿意放弃满洲贵族的特权,因此,反对专制统治与反对异族统治这两个目标便重合在一起。再加上两百多年来对汉人的民族压迫,利用民族主义来推翻清政府成为一种颇为有效的方式。“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将“民族”与“种族”这两个有关联却也有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同种族才可以组成民族。“一国之内而容二族,则合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否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已。”(31)章太炎也说:“吾以外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也。”(32)故而,在革命者看来,欲御外侮,须先清内患,而“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所以应该“磨吾刃,建吾旗”,以“驱逐凌辱我之满人”。(33) 一部作品的选择、翻译和接受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联满与排满的尖锐对立当中,在不民族则国危、“爱国保种”的呐喊声中,描写了两个民族的矛盾、冲突与斗争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中国大受欢迎。四个世纪以来撒克逊人在异族统治下的屈辱与苦难、摩擦与抗争在身处内忧外患的国人心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邹振环就指出:“使林纾感到震动的还在于此书叙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受到异族压迫,广大农民沦为农奴,原撒克逊封建主也受到了征服者的欺凌。”(34)震动之余,林纾以其妙笔为小说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政治情感与民族情感,在林译中,民族矛盾因被赋予了更为崇高的国家理念变得更为尖锐。 林纾对民族融合的态度却值得玩味。在其解读这部小说的“八妙”中,林纾并未对小说民族融合的核心思想做出回应,而是对“垂老亡国之英雄”无法完成复国大业心生感慨,对撒克逊王室后人“嗜炙慕色,形如土偶”感到悲愤。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以撒克逊人归附、两个民族和解来收场,让林纾感到遗憾,这一点从书名到译序再到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就可以看出。孙宝瑄以“中兴心事付东流”来回应林纾,展现了译者意图贯彻的效果。司各特在小说中提出来的民族“中间道路”与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不无巧合之处,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但林纾面对民族融合的态度却暧昧不清,隐隐透出保留与怀疑的态度。 尽管译者对作者的基本观点并不完全肯定,但还是设法使民族和解的结局看起来更具有合理性。林纾偏离了原作,拉大了两个民族的距离,又设法加以弥补,在绕了一个圈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点。在隐喻层面上,翻译是否如民族主义一样,具有坚韧又强大的力量,尽管会有迂回,但最终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注释: ①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郑文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页。 ②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③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④⑤⑥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谢虎、胡婷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导言第5页,导言第9页,第51页。 ⑦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徐式谷、江枫、张自谋译,1997年版,第1页,第123页。 ⑧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⑩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文惠美编选:《司各特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11)凌昌言:《司各特逝世百年祭》,《现代》1932年第2期。 (12)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13)(15)林纾:《撒克逊劫后影响略·序》,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林纾、魏易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第2页。 (14)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99页。 (16)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 (17)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18)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林纾、魏易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页。原文见:Sir Walter Scott.Ivanhoe.NY:Penguin Putnam Inc.,2001,p30.以下引用在文中注出页码。 (19)司各特:《艾凡赫》,刘尊棋,章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52-453页。以下引用在文中注出页码。 (20)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1页。 (21)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78-79页。 (2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71页。 (23)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2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4页。 (25)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26)(27)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2页,第93-118页。 (28)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张枬、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2页。 (2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3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5-76页。 (31)余一:《民族主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张枬、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86-487页。 (32)章太炎:《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张枬、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8页。 (33)(34)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张枬、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8页,第665页。